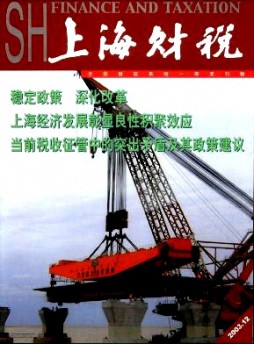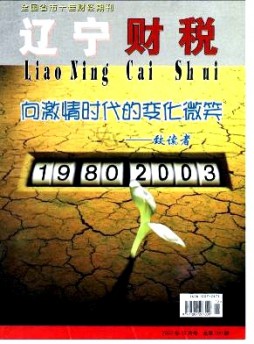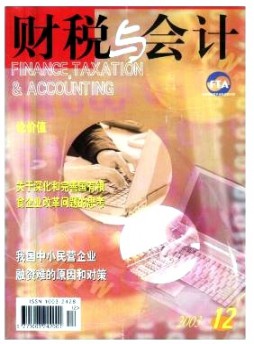財稅法學(xué)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財稅法學(xué)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中國稅法學(xué)研究掉隊的成因分析
稅法在現(xiàn)行執(zhí)法體系中是一個分外的范疇,它不是按傳統(tǒng)的調(diào)解對象的尺度分別出的單獨部門法,而是一個綜合范疇。此中,既有涉及國家底子干系的憲法性執(zhí)法范例,又有深深浸透宏觀調(diào)控精神的經(jīng)濟(jì)法內(nèi)容,更包羅著大量的范例辦理干系的行政規(guī)則;除此之外,稅收犯法方面的治罪量刑也具有很強(qiáng)的專業(yè)性,稅款的掩護(hù)步驟還必須警惕民法的具體制度。因此,將稅法作為一門單獨的學(xué)科加以研究不光完全須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當(dāng)憲法學(xué)熱衷于研究國家底子政治經(jīng)濟(jì)制度而無暇顧及稅收舉動的合憲性時,當(dāng)經(jīng)濟(jì)法學(xué)致力于宏觀調(diào)控的政策選擇而不克不及深入稅法的制度籌劃時,當(dāng)行政法學(xué)也只注意最一樣平常的行政舉動、行政步驟、行政幫助原理而難以觸及稅法的特質(zhì)時,將全部的與稅收干系的執(zhí)法范例聚集起來舉行研究,使之形成一門獨立的法學(xué)學(xué)科顯得尤其重要。這樣可以博采眾家之專長,充實警惕干系部門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要領(lǐng),使稅法的體系和內(nèi)容改正完備和富厚。
然而,當(dāng)前我國稅法學(xué)研究的現(xiàn)狀是,主攻方向不明確,研究氣力疏散,研究要領(lǐng)單一,學(xué)術(shù)底細(xì)不夠,理論深度尤顯短缺。經(jīng)濟(jì)學(xué)者只珍視稅收制度中對屈從有龐大影響的內(nèi)容,法學(xué)家們也只饜足于對現(xiàn)存端正服務(wù)論事的表明,稅法在法學(xué)體系中底子上屬于被人忘記的角落。隨著社會主義法治歷程的深入,依法治稅越來越成為人民日益體貼的現(xiàn)實標(biāo)題。人們不光體貼稅收舉動的經(jīng)濟(jì)效果,更體貼怎樣議決周到過細(xì)的執(zhí)法步驟保證本身的正當(dāng)職權(quán)不受侵陵。稅法的成果不光在于保障當(dāng)局正當(dāng)使用職權(quán),同時也在于以執(zhí)法的情勢對干系主體的舉動舉行束縛和監(jiān)視,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運轉(zhuǎn),不至于侵占百姓的權(quán)利和優(yōu)點。恰恰在后一點上,我國稅法學(xué)的研究相當(dāng)單薄。如稅收法定原則的貫徹落實,稅收征管步驟優(yōu)化籌劃,納稅人權(quán)利的掩護(hù)等,都是我國財稅法學(xué)研究亟待增強(qiáng)的地方。
第2篇
2012年8月21日,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鄒恒甫教授在微博爆料:“北大院長在夢桃源北大醫(yī)療室吃飯時只要看到漂亮服務(wù)員就必然下手把她們奸。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夢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鄒恒甫,北大棍太多。”此舉在網(wǎng)上引起軒然大波。8月31日,北大發(fā)表聲明,稱鄒恒甫的言論嚴(yán)重?fù)p害了北京大學(xué)的聲譽(yù)和教師隊伍的形象,決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9月7日,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宣布“北京大學(xué)訴鄒恒甫侵犯名譽(yù)權(quán)糾紛”已經(jīng)正式立案。
北京大學(xué)賀衛(wèi)方教授在《南都周刊》撰文指出:由于鄒恒甫使用了全稱判斷,舉凡北大男性院長、教授、主任都是適格的原告人,北大作為法人,依據(jù)《民法通則》第101條,也有權(quán)提起民事侵權(quán)訴訟。然則,北大是否為本案中名譽(yù)權(quán)受損的當(dāng)事人呢?依據(jù)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頒布的《關(guān)于審理名譽(yù)權(quán)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司法文件,凡法人提訟者,大都因為其商業(yè)信譽(yù)受到了實際損害。北京大學(xué)法學(xué)博士侯健在其博士學(xué)位論文修改成的著作《輿論監(jiān)督與名譽(yù)權(quán)問題研究》中也明確提出:“針對政府機(jī)構(gòu)的批判性言論,不論真假不論主觀意圖,皆免卻其侵害名譽(yù)的民事責(zé)任。”北京大學(xué)乃是中國公立高等學(xué)校之“翹楚”,其經(jīng)費來自財政撥款;鄒恒甫教授的“批評性言論”顯然不會侵害到其“商業(yè)信譽(yù)”或給其帶來經(jīng)濟(jì)損失,從目前來看也未對北大的教學(xué)科研秩序構(gòu)成任何困擾。北大在鄒恒甫“爆料”之后作適當(dāng)、理性之回應(yīng),足以消除“微博事件”的消極影響;若反應(yīng)過于激烈,反而有悖于北大“自由”、“兼容”的傳統(tǒng)聲譽(yù)。
那么,鄒恒甫教授的“爆料”是否侵害了北京大學(xué)所有“男性院長”、“教授”、“主任”的名譽(yù)權(quán)呢?回答這個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鄒恒甫教授的“爆料”是否已經(jīng)確實、特定地指向了北京大學(xué)的全體教授、男性院長及主任。從表面上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然則,正如民法學(xué)者楊立新教授等人所言:“因為特定人名譽(yù)是否受損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是社會評價,因此,所謂特定指向最主要的含義應(yīng)該是使公眾理解指向何人。”事實上,任何具有中等理性判斷能力的公民,均不會相信鄒恒甫教授的“爆料”會真的指向“全體北大教授”。鄒恒甫教授在隨后的微博中承認(rèn):“我籠統(tǒng)地寫北大院長、系主任、教授在夢桃源當(dāng)是太夸大了,我當(dāng)然是指我了解到的少數(shù)院長、副教授教授如此。我說話往往夸大,這是我的一貫風(fēng)格。了解我的都曉得我的這一特點。”其實,即算“不了解鄒恒甫教授的人”,在看到其微博“爆料”之初也會知道其“夸大性”;換而言之,公眾所理解的“北大教授”,其實并非“全稱判斷”,而是“不確定特指的部分北大教授”。北大教授之名譽(yù),可謂“清者自清”,不會因此受到實質(zhì)影響。
第3篇
論文摘要:量能課稅原則作為稅法的基本原則,是稅收公平原則在稅法中的具體體現(xiàn),具有引導(dǎo)我國稅法改革的功能。在學(xué)理上探討和界定量能課稅原則的內(nèi)涵和 法律 地位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指導(dǎo)意義。
一、量能課稅原則的內(nèi)涵
談到量能課稅原則,我們有必要先討論稅收公平原則。稅收公平原則是與稅法的另一基本原則—稅收法定原則相對的一種原則,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稅收法定主義的一種補(bǔ)充性原則。①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稅收法定原則的主旨主要是法律形式主義的,它要求國家在征稅時嚴(yán)格依據(jù)法律形式上的規(guī)定,而較少考慮納稅人的實際負(fù)擔(dān)能力。相反,稅收公平原則更多的是從實質(zhì)平等、實質(zhì)正義的角度考慮問題,它要求國家在征稅時不僅應(yīng)考慮納稅人量的負(fù)擔(dān)能力,更應(yīng)考慮質(zhì)的負(fù)擔(dān)能力,實現(xiàn)稅收征納的人性化,從而有效地保護(hù)納稅人的財產(chǎn)權(quán)、自由權(quán)、生存權(quán)等基本人權(quán)。
那么,量能課稅原則與稅收公平原則在稅法中存在著怎樣的關(guān)系呢?其實,關(guān)于稅收公平原則更為詳細(xì)的含義,一直存在兩大傳統(tǒng)—利益賦稅原則和量能課稅原則。在稅法學(xué)的 發(fā)展 歷程里,學(xué)者們圍繞這兩大傳統(tǒng)進(jìn)行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于何者更有利于公平的實現(xiàn)。利益賦稅原則認(rèn)為稅收是社會成員為了得到政府的保護(hù)所付出的代價,納稅人根據(jù)各人從政府提供的服務(wù),即公共服務(wù)中享受利益的多少而相應(yīng)的納稅。量能課稅原則則認(rèn)為稅收的征納不應(yīng)以形式上實現(xiàn)依法征稅、滿足財政需要為目的,而應(yīng)在實質(zhì)上實現(xiàn)稅收負(fù)擔(dān)在全體納稅人之間的公平分配,使所有納稅人按照其實質(zhì)納稅能力負(fù)擔(dān)其應(yīng)繳納的稅收額度。
比較這兩大傳統(tǒng),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利益賦稅原則把稅收公平的基點定位在納稅人從公共服務(wù)中享受利益的多少,而量能課稅原則將稅收公平的基點定位于納稅人稅收負(fù)擔(dān)能力的強(qiáng)弱上。實際上,進(jìn)一步思考,我們會發(fā)現(xiàn),衡量稅收公平的這兩種不同的價值判斷標(biāo)準(zhǔn)實質(zhì)上反映了對稅法性質(zhì)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認(rèn)識和態(tài)度。利益賦稅原則的著眼點和落腳點在于征稅主體—國家一方,體現(xiàn)的是一種“國家利益”至上的思維模式,它只要求納稅人根據(jù)其從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wù)中獲得利益的多少繳納相應(yīng)的稅賦,而不考慮其實際負(fù)擔(dān)能力。換句話說,只要納稅人從國家的公共服務(wù)中享受到了利益,不管有無支付能力,都必須依法納稅。在這種原則指導(dǎo)下制定的稅法必然是一種征稅者之法,即保障征稅者權(quán)力之法,保障國家稅收之法。在人類已經(jīng)跨入21世紀(jì)的今天,在人權(quán)保障呼聲日益高漲、世界人權(quán)事業(yè)蓬勃發(fā)展的 現(xiàn)代 法治社會里,這樣的稅法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時時刻刻都有可能對公民的自由權(quán)、生存權(quán)、財產(chǎn)權(quán)等基本人權(quán)構(gòu)成威脅甚至侵蝕。它賦予了征稅主體—國家強(qiáng)大的稅收課征權(quán),而忽視了另一方主體—納稅人的基本權(quán)利保障,致使弱小的納稅人根本無法對抗強(qiáng)大的國家機(jī)器,這樣的稅法明顯不符合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趨勢,在未來的稅法改革中必須摒棄這種“惡法”。而量能課稅原則的著眼點和落腳點在于納稅主體一方,體現(xiàn)的是一種“個人利益”至上的思維模式,它在保障國家稅收收入的前提下,開始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納稅人的個別性上。它要求國家在征稅時,必須充分考慮納稅人的實際負(fù)擔(dān)能力, 經(jīng)濟(jì) 能力強(qiáng)的多納稅,經(jīng)濟(jì)能力弱的少納稅,無經(jīng)濟(jì)能力的甚至可以不納稅。如果堅持這種原則的指引,那么,制定的稅法就必然是一種納稅人之法,即保障納稅人權(quán)利之法、保障納稅人的自由權(quán)、生存權(quán)、財產(chǎn)權(quán)等基本人權(quán)之法,這種法律必然是一種“良法”,定會得到納稅人的廣泛認(rèn)同和遵守,從而實現(xiàn)法律實施的預(yù)期效果和目的。
二、量能課稅原則的法律地位
量能課稅原則作為稅收公平原則的法律價值判斷標(biāo)準(zhǔn),雖然可以較好的解決稅收在納稅人之間的公平分配問題,但是從稅收觀念過渡到可以統(tǒng)帥稅收法律規(guī)則的法律原則卻仍然需要法學(xué)做出諸多的努力。近年來,隨著稅法學(xué)界對量能課稅原則的研究不斷升溫,關(guān)于這一原則的定位也開始引起學(xué)者們越來越多的關(guān)注,對于這個問題,學(xué)者們有著不同的認(rèn)識,概括地說,大家的分歧集中在量能課稅原則究竟是一種財稅思想還是一項稅法的基本原則的爭論上。如日本學(xué)者金子宏將量能課稅原則并入稅收公平主義原則之中,作為稅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我國 臺灣 學(xué)者葛克昌、陳清秀也持有相同的觀點。另外,日本學(xué)者北野弘久認(rèn)為,量能課稅只是立法原則,不是解釋和適用稅法的指導(dǎo)性原則。當(dāng)然,也有很多學(xué)者對此觀點并不贊同,在此不一一列舉。②
筆者以為,稅收作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國家對公民財產(chǎn)的一種“合法占有”,從形式上看,侵犯的是公民對其私人財產(chǎn)所享有的獨占的、排他的所有權(quán),這種私人財產(chǎn)權(quán)是一種憲法權(quán)利,是一種基本人權(quán),我國憲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條前兩款明確規(guī)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chǎn)不受侵犯;國家依照 法律 規(guī)定保護(hù)公民的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和繼承權(quán)”。因此,為了對公民的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提供充分、有效的保護(hù),確保納稅人的憲法權(quán)利能夠切實得以實現(xiàn),稅法必須對國家的課稅權(quán)進(jìn)行規(guī)范和限制,防止國家權(quán)力濫用,否則,將有可能造成對納稅人基本人權(quán)的不適當(dāng)侵犯,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我國稅法未來的變革方向應(yīng)當(dāng)走“納稅人之法”的道路。目前學(xué)者們對于稅收法定主義是稅法的基本原則已達(dá)成共識,但是,單靠稅收法定主義不足以支撐、維系整個稅法“大廈”,難以對納稅人的基本人權(quán)提供天衣無縫的“保護(hù)網(wǎng)”。因此,必須在稅法中引入另外一項基本原則,使它和稅收法定原則一道來共同防御國家權(quán)力對公民財產(chǎn)權(quán)的威脅,并指引以后的稅法改革。而量能課稅原則的重心在于實質(zhì)合理性,根據(jù)納稅人的稅收負(fù)擔(dān)能力公平分配賦稅,這兩種原則一剛一柔、一表一里,既能從形式上保證國家課稅權(quán)的依法行使,又能從實質(zhì)上確保納稅人之間的稅負(fù)公平。因此,將量能課稅原則確立為稅法的另一基本原則,使之規(guī)范稅法的各個領(lǐng)域,將會有效地調(diào)節(jié)稅收法定主義的形式剛性,并最終實現(xiàn)“納稅人之法”的改革目標(biāo)。
注釋:
擴(kuò)展閱讀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財稅法論文
- 2財稅大數(shù)據(jù)分析
- 3財稅信息化論文
- 4財稅合規(guī)管理
- 5財稅管理
- 6財稅立法論文
- 7財稅報表審計
- 8財稅金融論文
- 9財稅管理論文
- 10財稅管理服務(w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