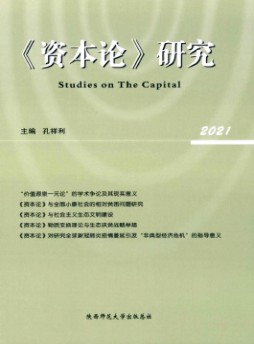資本論對(duì)法治中國(guó)建設(shè)的啟示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資本論對(duì)法治中國(guó)建設(shè)的啟示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學(xué)界對(duì)于《資本論》法律思想的分析寥寥,但并不代表《資本論》與法無涉,恰恰相反,其對(duì)于我國(guó)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背景下的全面依法治國(guó)十六字方針的落實(shí)具有重要啟示。從法與經(jīng)濟(jì)基礎(chǔ)間的關(guān)系出發(fā),科學(xué)立法須基于唯物主義的前提,秉持資源分配與權(quán)利保護(hù)的立場(chǎng),堅(jiān)持民主立法,不以犧牲生態(tài)環(huán)境為代價(jià)。從商品價(jià)值與使用價(jià)值的關(guān)系出發(fā),法律首先必須得到嚴(yán)格執(zhí)行。從商品價(jià)值尺度的角度來看,司法公正就是依法、釋法基礎(chǔ)上的同案同判。從商品與貨幣的關(guān)系來看,全民守法就是發(fā)揮法的評(píng)價(jià)作用和指引作用,使人的行為發(fā)乎利,合乎德,止于法。
關(guān)鍵詞:資本論;商品;依法治國(guó);法的關(guān)系
誠(chéng)然,《資本論》不以法律現(xiàn)象作為專門的研究對(duì)象,但馬克思在分析資本運(yùn)動(dòng)過程和規(guī)律的同時(shí),也展示了資產(chǎn)階級(jí)和小資產(chǎn)階級(jí)形形色色的法律幻想與謬論,雖然其法律思想散見各卷,未成體系①,但無可否認(rèn)的是,其對(duì)資本主義法律思想、制度的批判,反過來看即是對(duì)社會(huì)主義法律思想實(shí)質(zhì)以及制度特征的揭示。在法治中國(guó)建設(shè)穩(wěn)步推進(jìn)的當(dāng)下,隨著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進(jìn)一步深化,新舊社會(huì)矛盾反映到法律制度層面即是“無法可依”“法非良法”“執(zhí)法不嚴(yán)”“司法不公”“有法不依”等。為此,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全面依法治國(guó)十六字方針:“科學(xué)立法、嚴(yán)格執(zhí)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對(duì)于如何把這一方針落實(shí)到政治經(jīng)濟(jì)生活當(dāng)中,《資本論》具有重要啟示。
一、科學(xué)立法:羊不能把人吃了,人也不能把羊吃了
立法,即法的產(chǎn)生。不同于龐德將法作為社會(huì)控制方式的一種[1],馬克思認(rèn)為法是一種關(guān)系②。更確切地說,這是一種“權(quán)利關(guān)系或意志關(guān)系”,“反映出一種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來”。具體到商品交換過程里,此所謂“權(quán)利關(guān)系”即“他們(商品所有者)必須互相承認(rèn)私有者的權(quán)利”,而這種“權(quán)利關(guān)系不問是不是依法成立的,他總歸是在契約的形式上———是一種意志關(guān)系”[2]55。這里的意志關(guān)系就是共同意志行為,即現(xiàn)代私法所說的意思合致,即商品所有者通過交換商品來相互發(fā)生關(guān)系。這里提到的“商品所有者”,就是將人的意志滲透在商品內(nèi),從而獲取這一身份,可以交換商品,發(fā)生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在這里,人的意志被物化了,也就使得意志被物所束縛。“意志在經(jīng)濟(jì)上是被迫的。”[3]因此,是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決定法的關(guān)系。基于此,如何才稱得上“科學(xué)立法”?首先,立法必須基于唯物主義。與之相對(duì)的是唯心主義,其典型論調(diào)如黑格爾在《法哲學(xué)原理》中所聲稱的:“法的基地一般說來是精神的東西,它的確定的地位和出發(fā)點(diǎn)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構(gòu)成法的實(shí)體和規(guī)定性。至于法的體系是實(shí)現(xiàn)了的自由的王國(guó),是從精神自身產(chǎn)生出來的、作為第二天性的精神的世界。”[4]10然而,這種脫離物質(zhì)基礎(chǔ)的法是不存在的,只能是幻想。是以具體到立法過程中,立法調(diào)研之所以必要,是因?yàn)橹挥芯邆淞爽F(xiàn)實(shí)立法需要與客觀立法條件,才有立法之必要,否則便是“拍腦袋立法”,屬于立法權(quán)濫用。其次,從《資本論》對(duì)權(quán)利、意志、商品交換的關(guān)系描述中可以發(fā)現(xiàn),法律所基于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發(fā)生在人與人之間,因此,在立法中必須考慮并重視個(gè)人。當(dāng)然,這不是所謂的“人權(quán)口號(hào)”,而是根植于生產(chǎn)關(guān)系,因?yàn)樯a(chǎn)關(guān)系就是生產(chǎn)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體現(xiàn)的是經(jīng)濟(jì)社會(huì)中人對(duì)資源、權(quán)利的支配性。這就意味著,立法尤其是行政領(lǐng)域立法,必須具有資源分配意識(shí)與權(quán)利保護(hù)意識(shí),必須認(rèn)識(shí)到,所立之法不僅僅是表面的調(diào)控工具,更是調(diào)節(jié)相應(yīng)領(lǐng)域資源分配狀況的方式和保護(hù)個(gè)人合法權(quán)益的強(qiáng)力,唯有如此,所立之法才能為社會(huì)接受,為個(gè)人接受。再次,立法必須民主。《資本論》早已揭示資本主義將勞動(dòng)力作為商品,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余價(jià)值,這就是資產(chǎn)階級(jí)法律虛偽的經(jīng)濟(jì)根源所在,因?yàn)橥渌麆兿麟A級(jí)(如奴隸主)的法律相比,不過是更具隱蔽性罷了。事實(shí)上,1848年的《共產(chǎn)黨宣言》就已經(jīng)揭示法律是由物質(zhì)生活條件所決定的,但物質(zhì)生活條件是有階級(jí)屬性的③。所以,只有立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讓立法回應(yīng)最廣大人民的物質(zhì)生活需求,才能確保所立之法是社會(huì)主義法律,避免重蹈彼時(shí)資本主義圈地式立法的覆轍。顯然,這里的民主立法不是過去國(guó)際工人協(xié)會(huì)的“人民直接立法”。同時(shí),這也是對(duì)法的經(jīng)濟(jì)作用的正確使用。最后,立法必須堅(jiān)持綠色原則。一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寫,法律“這種權(quán)利關(guān)系或意志關(guān)系的內(nèi)容,也就由這種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規(guī)定”[2]55。如果說商品經(jīng)濟(jì)塑造了資本主義立法,那么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也塑造了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立法。黨的報(bào)告提出了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與美麗中國(guó)建設(shè),這意味著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將是綠色的,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立法也應(yīng)當(dāng)是綠色的,這就要求立法過程中要貫徹綠色原則,將生態(tài)環(huán)境從過去的犧牲對(duì)象轉(zhuǎn)變成保護(hù)對(duì)象。此四點(diǎn),即科學(xué)立法的前提———確有所需且正當(dāng)其時(shí),立場(chǎng)———資源分配與權(quán)利保護(hù),基礎(chǔ)———人民的根本利益,底線———不以犧牲生態(tài)環(huán)境為代價(jià)。
二、嚴(yán)格執(zhí)法:法律的價(jià)值
在于執(zhí)行商品必須先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再論其使用價(jià)值[2]56。同樣,法律必須首先得到遵守,再論其善惡與否。執(zhí)法之所以需要嚴(yán)格,一個(gè)重要的原因是,由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決定的法律在其施行過程中將會(huì)反作用于經(jīng)濟(jì)基礎(chǔ),這也是法的經(jīng)濟(jì)作用。如此,若不嚴(yán)格執(zhí)行由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所決定的法律,則上層建筑與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不相適應(yīng)或是不完全適應(yīng),一方面會(huì)對(duì)當(dāng)前經(jīng)濟(jì)造成損害,另一方面也會(huì)阻礙經(jīng)濟(jì)往預(yù)期方向的發(fā)展。再一個(gè)重要的原因是,在科學(xué)立法的前提下,若不嚴(yán)格執(zhí)法,違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所謂法律就會(huì)成為一紙空文,因?yàn)闊o人遵守的法典不過是一疊廢紙。任何一種妄圖用法律等形式?jīng)Q定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內(nèi)容的行動(dòng)都是徒勞而錯(cuò)誤的,即便當(dāng)時(shí)因?yàn)閺?qiáng)力得以執(zhí)行,但這樣的法律觀念不可能長(zhǎng)期存在下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生活由法律所調(diào)整的前提是該法能反映或基本反映經(jīng)濟(jì)規(guī)律,如若失去這一前提,則法形同虛設(shè),但若滿足這一前提的法得不到嚴(yán)格執(zhí)行,結(jié)果很可能比形同虛設(shè)危害更甚。再者,法之所以可以嚴(yán)格執(zhí)行,是因?yàn)樯鐣?huì)主義立法制定的是人民的法。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的運(yùn)作,揭示了資產(chǎn)階級(jí)法仍屬于剝削階級(jí)法的本質(zhì)。資產(chǎn)階級(jí)法與封建制法相比確實(shí)是一大進(jìn)步,但它是資產(chǎn)階級(jí)意志的體現(xiàn),“資本在它認(rèn)為必要的時(shí)候,就通過強(qiáng)制性法律來實(shí)現(xiàn)它對(duì)自由工人的所有權(quán)。”[5]662資本主義國(guó)家的統(tǒng)治者有種種辦法使自己規(guī)避法律,因?yàn)閺S主制定法律時(shí)從來沒有將自己與工人一視同仁,“例如,頒布工人不得在期滿前離廠的法令時(shí),馬上就規(guī)定了離廠的懲罰,甚至還規(guī)定了像逮捕這樣嚴(yán)厲的懲罰。再如法律規(guī)定,工人罷工要受逮捕甚至監(jiān)禁的懲罰,而廠主違背條例引起罷工,只不過罰款而已。”抑或者,資本家們通過法律將自己的違法成本降到最低,甚至借此牟利,如“法律要求廠主在星期日和節(jié)日讓工人休息,一晝夜不得要工人工作11個(gè)半小時(shí)以上,但沒有規(guī)定不履行這些要求要受什么懲罰。廠主破壞這一法律會(huì)引起什么后果呢?至多是被拖到治安法官那兒去,課以50盧布以下的罰款,或由工廠管理局自己決定處罰,那也只是罰款而已。難道50盧布的罰款會(huì)嚇住廠主嗎?要知道,他強(qiáng)迫工人為他多做一夜或者一個(gè)節(jié)日的工作,他所得到的利潤(rùn)可就不是50盧布!違反法律而交付罰款對(duì)廠主是直接有利的”[6]254。資本主義社會(huì)的政府是資產(chǎn)階級(jí)的政府,法律是資產(chǎn)階級(jí)的法律,這樣的法律執(zhí)行越嚴(yán)格,對(duì)于廣大工人來說卻非幸事。而社會(huì)主義法是廣大人民意志的體現(xiàn),因?yàn)樯鐣?huì)主義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不是資本。社會(huì)主義并不天然排斥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因?yàn)樯唐方粨Q本身是值得肯定的進(jìn)步,與資本主義只關(guān)注資產(chǎn)階級(jí)如何在商品交換中掠奪生產(chǎn)資料、剝削工人的剩余價(jià)值不同,社會(huì)主義著眼于交換天生的平等屬性,提倡的思想是“為公是更好的為自己”,與資本主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思想截然不同。因此,在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個(gè)人與個(gè)人通過商品交換形成市場(chǎng),產(chǎn)生交易習(xí)慣;市場(chǎng)交易及其調(diào)控形成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產(chǎn)生市場(chǎng)規(guī)則。市場(chǎng)規(guī)則是一系列交易習(xí)慣的最大公約數(shù),當(dāng)它符合國(guó)家意志時(shí),便會(huì)被上升為法律規(guī)定。所以我們說,社會(huì)主義法是個(gè)人、社會(huì)、國(guó)家意志相統(tǒng)一的體現(xiàn),而不是資本主義法那般以犧牲一個(gè)階級(jí)為代價(jià)去維護(hù)另一個(gè)階級(jí)的利益。彼時(shí),資產(chǎn)階級(jí)為了確立新的生產(chǎn)方式,對(duì)農(nóng)民土地的掠奪因?yàn)榕狭朔赏庖露儽炯訁枴?duì)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其稱之為“合法手段實(shí)行掠奪”,“這種法律,使共有地化為地主私有,使人民被剝奪”。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迅速被消滅了,私有制財(cái)產(chǎn)確立了,但隨之被粗暴乃至血腥奪去的還有農(nóng)民的土地和自由。農(nóng)場(chǎng)變成牧場(chǎng),牧場(chǎng)的一部分還變成鹿場(chǎng),國(guó)家越來越富有,民眾卻在法律恐怖下連自家的院子占地幾畝,是否可供他人借宿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在資本的原始積累中,“國(guó)民之富”與“民眾之貧”這一悖論是顯而易見的,但在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法律所追求的是國(guó)富民強(qiáng)[2]755-758。對(duì)于這樣的法律,除卻國(guó)家統(tǒng)治的需要,人民同樣希望其得到嚴(yán)格執(zhí)行,因?yàn)檫@與人民自身利益不僅不相矛盾,反而兩相符合。
三、公正司法:從商品價(jià)值的一般尺度理解
同案同判司法之所以備受關(guān)注,套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話,是因?yàn)樗鞍讶藗冃闹凶罴ち摇⒆畋氨伞⒆類毫拥母星閱酒穑汛硭饺死Φ某鹕裾俚綉?zhàn)場(chǎng)上來”[2]4。馬克思在原文中形容的是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但放在司法這里同樣貼切。法律是最后的紅線,訴訟是最后的救濟(jì)。法庭之上不談動(dòng)機(jī),不問感情,只看行為與結(jié)果。更重要的是,相比于高高在上不知何時(shí)才能用上的國(guó)家立法以及雖在身邊發(fā)生但自身未受針對(duì)的行政執(zhí)法,司法程序一旦啟動(dòng),就意味著有私人利益受到了侵害,此時(shí)受害人的訴求無疑最為迫切,也更加關(guān)注法律適用的公平與否,因?yàn)閭€(gè)案中的公平與否將直接影響其自身利益的盈損。但公正是法學(xué)領(lǐng)域討論千百年未有定論的議題。何謂公正,諸賢多有言辭。從《資本論》來看,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的司法公正,應(yīng)當(dāng)包含以下幾層含義:第一,公正的第一層含義即合法。前文已述,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的法律是個(gè)人、社會(huì)、國(guó)家意志的統(tǒng)一,不僅執(zhí)法須嚴(yán)格遵守,司法更不例外。依法審判的案件或許不一定個(gè)案公正,但不依法審判的案件一定不公正,即便在結(jié)果上或許實(shí)現(xiàn)了糾紛雙方的利益平衡,但無視法律規(guī)定的審判活動(dòng)已經(jīng)對(duì)司法權(quán)威造成了實(shí)質(zhì)損害,因?yàn)樗痉ǖ臋?quán)威來自于法律的權(quán)威,而法律的權(quán)威來自于嚴(yán)格的執(zhí)行。人們所期望的公正審判首先應(yīng)當(dāng)是結(jié)果可預(yù)期的,因?yàn)椴豢深A(yù)期的審判帶來的只能是恐怖,因此審判的依據(jù)必須是明確而公開的。在此基礎(chǔ)上,人們期望審判結(jié)果是可以解釋清楚的,這是對(duì)可預(yù)期性的必要補(bǔ)充和延伸。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對(duì)蒲魯東“永遠(yuǎn)的觀念”的批判一樣,將審判依據(jù)歸結(jié)于“永遠(yuǎn)的正義”“永遠(yuǎn)的公道”“永遠(yuǎn)的真理”等,“并不能使我們多知道一些什么”[2]55。能夠給出解釋的只有法律,這既是因?yàn)榉l明確而具體,也是因?yàn)榉l背后所反映的是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這就使得經(jīng)濟(jì)生活中的人們有理解的能力。第二,公正的第二層含義即法官釋法。首先應(yīng)當(dāng)明確的是,法官釋法必須建立在依法審判的基礎(chǔ)上,不具有優(yōu)先性。之所以說個(gè)案的公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法官對(duì)法條的解釋性適用而非機(jī)械適用,是因?yàn)榉梢?guī)定本身的不完全性,這種不完全性表現(xiàn)為法的觀念與產(chǎn)生它的所有制關(guān)系不可能完全符合。法的觀念與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之間不是鏡子式的映像,而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反映,或是部分超前,或是部分落后,這在我國(guó)轉(zhuǎn)型期法律中表現(xiàn)的十分明顯。也正因如此,馬克思說,法的觀念的這種包含反作用在內(nèi)的相對(duì)獨(dú)立性,“要專門加以確定”。更明確地說,在不違反法律規(guī)定的前提下,法官應(yīng)根據(jù)事實(shí)基礎(chǔ),靈活運(yùn)用法律技術(shù),盡可能地讓落后的法律規(guī)定適應(yīng)當(dāng)前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讓超前的法律規(guī)定可以涵蓋當(dāng)前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從這一角度來看,不難發(fā)現(xiàn),法律的承繼與移植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承繼與移植,至于實(shí)質(zhì)內(nèi)容,則依靠法官根據(jù)現(xiàn)實(shí)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進(jìn)行合法限度內(nèi)的解釋。一個(gè)典型的例子是,“買賣”這個(gè)概念古羅馬法中就有出現(xiàn),但彼時(shí)可指奴隸買賣,現(xiàn)在看來不能接受。又如“出行工具”這一術(shù)語,千年前的人們對(duì)其的解讀更多是馬車、轎子,而現(xiàn)在則包括汽車、火車、飛機(jī)等。第三,公正的第三層含義是同案同判。究其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上的原因,《資本論》同樣給出了啟示,那就是價(jià)值尺度。在商品交換中,形形色色的商品如何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的量化,馬克思提出了價(jià)值尺度這一概念。“把商品價(jià)值表現(xiàn)為同名稱的量,使其在質(zhì)的方面相等,在量的方面可以互相比較。這樣,它成了價(jià)值的一般尺度了。”也正是在此基礎(chǔ)上,貨幣這一一般等價(jià)物存在[2]65。同樣的,人的行為形形色色,如何使其能夠?yàn)閿?shù)量有限的法律所評(píng)價(jià),進(jìn)而使得法官據(jù)此作出裁判,所依靠的就是行為的類型化,也即行為的“公約”。例如,開車撞死他人、持刀砍死他人、下藥毒死他人、多人合伙殺死他人等,都是殺害行為。接著以刑法為例,定罪情節(jié)考察的是行為,量刑情節(jié)考察的也是行為,如果同一類型的行為得到不同的法律評(píng)價(jià),如甲與乙都只有一個(gè)故意殺害行為,但一個(gè)獲罪,一個(gè)無罪,自然會(huì)引發(fā)民眾不滿。類比到商品交換中,同樣的兩件商品,只是因?yàn)樗姓叻謱俨煌膬扇硕鴥r(jià)值大小差異顯著,自然不為市場(chǎng)所接受。也是在此基礎(chǔ)上,司法公正的一個(gè)重要表現(xiàn)是依法釋法基礎(chǔ)上的同案同判。
四、全民守法:讓人們像自發(fā)使用貨幣
一樣遵守法律商品交換時(shí)為什么需要貨幣流通?《資本論》給出了至少兩個(gè)答案:第一個(gè),貨幣評(píng)價(jià)商品。“不是因?yàn)橛胸泿牛陨唐酚泄s的可能。正好相反,是因?yàn)橐磺猩唐罚?dāng)作價(jià)值,都是對(duì)象化的人類勞動(dòng),所以他們有公約的可能,所以他們的價(jià)值能由一個(gè)特殊的商品來計(jì)量,所以這個(gè)特殊的商品轉(zhuǎn)化為共同的價(jià)值尺度,即貨幣。”即便放在今日,也無可否認(rèn),馬克思的這一段描述清楚且透徹[2]55。第二個(gè),貨幣成為商品流通的媒介。《資本論》指出,商品的總形態(tài)變化總是由買和賣兩個(gè)互相反對(duì)卻又互相補(bǔ)足的運(yùn)動(dòng)構(gòu)成。有買,就一定會(huì)有一個(gè)賣與之對(duì)應(yīng)存在,反之亦然。所以,在一次商品交換中,商品轉(zhuǎn)變成貨幣(賣),復(fù)由貨幣轉(zhuǎn)為商品(買)。這就是商品流通,與直接的物換物有著本質(zhì)差別,關(guān)鍵就在于貨幣。流通使貨幣不停奔走,結(jié)果是越來越遠(yuǎn)離出發(fā)點(diǎn),因?yàn)樯唐沸螒B(tài)變化的循環(huán)排斥貨幣的循環(huán)。貨幣在商品流通中扮演了商品的價(jià)值形態(tài)(值多少錢)與暫時(shí)的等價(jià)形態(tài)(可以買到什么),也因此變成了媒介[2]85。而在“全民守法”語境下,人們的行為就好像是商品,法律就好像是貨幣,人們的行為需要法律予以評(píng)價(jià),人們行為的規(guī)范需要以法律為標(biāo)本。“商品是戀著貨幣的,但‘真的戀愛的路’殊不平坦。”[2]79同樣的,全民守法亦是不易。全民守法,不是讓人們生活在法律中,而是讓人們的行為接受、認(rèn)同、共享法律的評(píng)價(jià)。為此,首先需要讓人們樹立將自身行為進(jìn)行法律評(píng)價(jià)的意識(shí),這就要求人們識(shí)法。識(shí)法之后便是用法,而用法的同時(shí)也促使人們識(shí)法。在整個(gè)社會(huì)評(píng)價(jià)體系中,對(duì)人行為的評(píng)價(jià)并非單一,俗話說的情理法,就包含了利益評(píng)價(jià)、道德評(píng)價(jià)和法律評(píng)價(jià)。就好像對(duì)商品的評(píng)價(jià),于我沒用,于他人有用,值多少錢。筆者認(rèn)為,對(duì)人的行為三種評(píng)價(jià)間的關(guān)系應(yīng)當(dāng)是發(fā)乎利,合乎德,止于法。在此基礎(chǔ)上,法律還將發(fā)揮其指引作用,因?yàn)橥ㄟ^法律的評(píng)價(jià)作用,人們將可以預(yù)判自己的行為是否合法,或有多大的違法風(fēng)險(xiǎn),為了不擔(dān)負(fù)法律責(zé)任,受到國(guó)家暴力的懲戒,人們會(huì)自發(fā)地調(diào)整自己的不當(dāng)行為,避免其演變成違法犯罪,這十分類似于市場(chǎng)交易中的趨利避害,也就不難理解。我們無法要求每一個(gè)人都成為君子或是圣人,但在一個(gè)法治國(guó)家,我們完全可以期待人人都成為一個(gè)守法公民。
參考文獻(xiàn):
[1][美]羅斯科•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huì)控制[M].徐顯明,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4.
[2][德]馬克思.資本論:上[M].郭大力,王亞南,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3]毛信莊.揭開法權(quán)關(guān)系的神秘面紗———《資本論》法律思想撅談[J].上海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1(3):76-80.
[4][德]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M].范揚(yáng),張企泰,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1.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列寧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作者:賈韶琦單位:湘潭大學(xué)法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