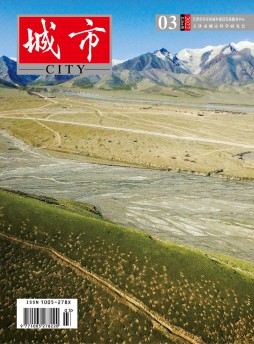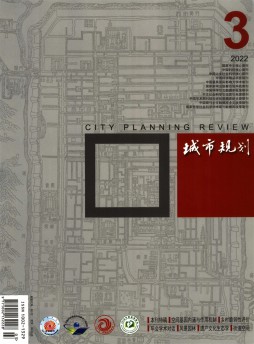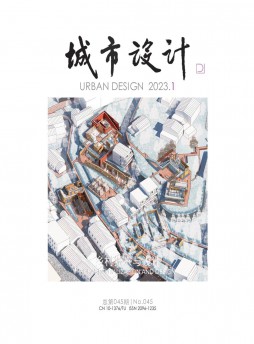城市偏向與城鄉(xiāng)服務(wù)均等化研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城市偏向與城鄉(xiāng)服務(wù)均等化研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廣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4年第四期
一、理論模型
本文構(gòu)建一個(gè)簡(jiǎn)化的模型來(lái)分析中國(guó)的財(cái)政分權(quán)體制下地方政府偏好與其公共決策的關(guān)系。為此假定:(1)公共品完全由轄區(qū)地方政府供給,不存在其他提供公共品的組織;(2)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分為城市部門(mén)公共品和農(nóng)村部門(mén)公共品兩類;(3)城市和農(nóng)村部門(mén)公共品的生產(chǎn)函數(shù)是相同的①;(4)資源投入不存在轄區(qū)之間的外溢性,投入城市的資源只影響城市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和公共品供給,投入農(nóng)村的資源只影響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和公共品供給;(5)謀求最高的政治地位,或者說(shuō)最大的晉升可能性是地方政府官員的目標(biāo)。借鑒馬驍?shù)?2011)[34]構(gòu)建的政治支持函數(shù)的思想,根據(jù)我國(guó)地方政府官員晉升機(jī)制的特點(diǎn),構(gòu)建如下地方政府官員晉升的可能性函數(shù):其中,W代表地方政府官員獲得晉升的可能性,G代表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率,政府對(duì)城市與農(nóng)村投入的資源eu、er是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率的影響因素之一,其他一切影響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率的因素的集合表示為x;Qu代表城市部門(mén)的公共品,它取決于政府投入城市的資源eu,Qr代表農(nóng)村部門(mén)的公共品,它取決于政府投入農(nóng)村的資源er;k1、k2分別代表城市部門(mén)公共品和農(nóng)村部門(mén)公共品對(duì)地方官員晉升的影響力,k1>0,k2>0;上述函數(shù)G、Qu、Qr均為e的增函數(shù),且假定為凹函數(shù),符合標(biāo)準(zhǔn)Inada條件。(1)式表明,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率越高,公共品提供得越多,晉升的可能性越大。然條件的制約較強(qiáng),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不高、農(nóng)產(chǎn)品附加值低,而農(nóng)村地區(qū)的公共產(chǎn)品投資大、建設(shè)周期長(zhǎng),對(d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作用具有間接性和滯后性。在我國(guó)現(xiàn)階段,對(duì)比農(nóng)村地區(qū),城市地區(qū)在資金、人才、技術(shù)和信息水平上都具有優(yōu)勢(shì),作為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主要?jiǎng)恿Φ亩⑷a(chǎn)業(yè)也聚集于城市,因而投資于城市的收益率更高,經(jīng)濟(jì)拉動(dòng)效應(yīng)更強(qiáng)。即我們假設(shè)同樣的資源投入到城市和農(nóng)村產(chǎn)出的公共品相同。然而,由于公共產(chǎn)品本身屬性的差異,對(duì)政府官員的政績(jī)反映卻不同。一般而言,城市公共產(chǎn)品“可見(jiàn)度”高,能更好地反映官員政績(jī),比如城市市政建設(shè)等,而農(nóng)村公共品“可見(jiàn)度”低,對(duì)政績(jī)的反映不顯著,比如鄉(xiāng)村公路(劉成奎和王朝才,2008)[35]。此外,城市居民相較于農(nóng)村居民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和社會(huì)地位,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同時(shí),對(duì)政策的認(rèn)知度與關(guān)注度也高于農(nóng)村居民,再加上更便捷的城市通訊和媒介網(wǎng)絡(luò),信息獲取能力強(qiáng),有更好的反饋機(jī)制與發(fā)聲渠道,從而對(duì)地方政府形成政治壓力的能力更強(qiáng)。城市公共產(chǎn)品本身更高的“可見(jiàn)度”與城市居民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使得提供城市公共品對(duì)晉升的邊際影響更大。由以上分析可知,地方政府官員基于最大化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優(yōu)資源配置方案在e*u>e*r的點(diǎn)取得。然而,地方政府官員的資源配置方式還受到中央政府或上級(jí)政府的制度約束,更受到地方政府財(cái)政能力的制約,而與地方政府財(cái)政能力直接相關(guān)的就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程度與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在短期內(nèi)我們可以合理地假定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既定,則地方政府的財(cái)政能力與財(cái)政分權(quán)水平正相關(guān)。因此,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官員能夠按照其意愿進(jìn)行資源配置的自由度越大,從而其選擇的資源配置方式越有可能接近使其利益最大化時(shí)的最優(yōu)解,即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越高,資源配置的城市偏向可能越嚴(yán)重。在我國(guó),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wù)的供給上占絕對(duì)主導(dǎo)地位,體制外的其他投資主體相對(duì)欠缺,由假設(shè)(3)可知城市部門(mén)與農(nóng)村部門(mén)公共品生產(chǎn)函數(shù)相同,又因?yàn)镼為e的增函數(shù),故有Q*u(e*u)>Q*r(e*r)。可見(jiàn),地方政府資源配置上的城市偏向最終導(dǎo)致了城鄉(xiāng)公共服務(wù)供給的非均衡。以上分析表明,由于城市在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方面貢獻(xiàn)突出,而城市公共品的“可見(jiàn)度”高于農(nóng)村公共品,再加上城市居民的政治影響力大于農(nóng)村居民,因而地方政府存在著優(yōu)先發(fā)展城市、更多考慮城市利益進(jìn)而實(shí)施城市偏向的資源配置政策的激勵(lì),而在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越高的地方,這種傾向被實(shí)現(xiàn)的可能性與程度也越大。據(jù)此,我們提出以下兩個(gè)命題:命題1: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在財(cái)政支出上的城市偏向越嚴(yán)重。命題2:地方政府官員的城市偏向不利于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實(shí)現(xiàn)。
二、實(shí)證檢驗(yàn)
為了檢驗(yàn)上述模型,本文利用中國(guó)26個(gè)省份①的面板數(shù)據(jù)進(jìn)行實(shí)證分析,分別驗(yàn)證財(cái)政分權(quán)與地方政府城市偏向、地方政府城市偏向與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關(guān)系。
(一)實(shí)證分析模型變量與數(shù)據(jù)說(shuō)明根據(jù)前述實(shí)證分析假定,本文構(gòu)建兩個(gè)實(shí)證分析回歸模型:(1)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水平(Index)。由于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度量并不存在統(tǒng)一的、權(quán)威性的指標(biāo),而且有關(guān)農(nóng)村公共安全、公共環(huán)境的數(shù)據(jù)缺失較多,本文只采用基礎(chǔ)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huì)保障和基礎(chǔ)設(shè)施四項(xiàng)指標(biāo)的綜合指標(biāo)來(lái)度量基本公共服務(wù)供給的整體水平,并設(shè)定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指數(shù)=各地區(qū)農(nóng)村基本公共服務(wù)人均指標(biāo)/各地區(qū)基本公共服務(wù)人均指標(biāo)[36]。(2)城市偏向(Ubias)。因缺乏直接度量指標(biāo),轉(zhuǎn)而以各省三農(nóng)財(cái)政支出①占各省財(cái)政支出比重表示對(duì)農(nóng)村偏向,則非農(nóng)村偏好就表示城市偏向。衡量政府偏好的最直接指標(biāo)是政府的財(cái)政資源配置偏好,其在農(nóng)村配置資源越少則意味著在城市配置資源越多。可以合理預(yù)期城市偏好對(duì)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影響系數(shù)符號(hào)應(yīng)該為負(fù),但因?yàn)楸疚闹胁捎萌r(nóng)支出占比來(lái)表示,則其在實(shí)證分析結(jié)論中影響系數(shù)符號(hào)預(yù)期為正。(3)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Fd)。對(duì)財(cái)政分權(quán)指標(biāo)的度量多采用各省本級(jí)人均財(cái)政支出占全國(guó)人均財(cái)政支出的比率來(lái)衡量(喬寶云等,2006;Xie等,1999),本文采用各省本級(jí)人均財(cái)政收入占全國(guó)人均財(cái)政收入的比率來(lái)衡量。各地財(cái)政分權(quán)表征了地方政府財(cái)政自主性的大小(傅勇和張晏,2007),一般分權(quán)化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財(cái)政資源越多,根據(jù)晉升激勵(lì)官員可配置資源越多,越有可能表現(xiàn)出城市偏向,對(duì)“三農(nóng)”的投入越少,預(yù)計(jì)對(duì)城市偏好的影響系數(shù)為負(fù)。(4)人均實(shí)際GDP(Rgdpp)。這是體現(xiàn)地方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重要指標(biāo),不同經(jīng)濟(jì)發(fā)展階段地方政府的公共決策偏好存在一定差異,但其對(duì)公共政策的影響方向尚無(wú)法明確預(yù)期。(5)城鎮(zhèn)化率(Urbanr):用城鎮(zhèn)戶籍人口占總?cè)丝诘谋戎乇硎尽3擎?zhèn)化率高意味著城市人口增多、農(nóng)村人口減少,從而引致農(nóng)村基本公共服務(wù)供給成本與規(guī)模效應(yīng)下降,但城市地區(qū)基本公共服務(wù)供給規(guī)模效應(yīng)增加;同時(shí)城鎮(zhèn)人口規(guī)模的擴(kuò)大也會(huì)增強(qiáng)城市居民的話語(yǔ)權(quán)與公共決策的影響力,進(jìn)而可能會(huì)更加強(qiáng)化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6)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Incgap):用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衡量。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表明社會(huì)收入分配的兩級(jí)分化越嚴(yán)重,抑制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應(yīng)該是必然選擇,而增加對(duì)農(nóng)村地區(qū)的財(cái)政投入是有效手段之一,由此可能會(huì)抑制公共決策中的城市偏好。由此預(yù)期,該指標(biāo)與政府的城市偏向存在負(fù)向關(guān)系。此外,我們還加入了工業(yè)化率(Indus)、對(duì)外開(kāi)放度(Trade)、民營(yíng)化率(Private)、人口密度(densi-ty)、人口增長(zhǎng)率(N)等反映地方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特征的控制變量。其中,對(duì)外開(kāi)放度用當(dāng)年的按美元與人民幣中間價(jià)折算的進(jìn)出口總額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來(lái)衡量,民營(yíng)化率則為非國(guó)有單位職工占總職工人數(shù)比重。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指標(biāo)來(lái)源于劉成奎和王朝才(2011)[36],其他數(shù)據(jù)主要來(lái)源于《中國(guó)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guó)財(cái)政年鑒》《中國(guó)農(nóng)村統(tǒng)計(jì)年鑒》、“中經(jīng)網(wǎng)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庫(kù)”以及“高校財(cái)經(jīng)數(shù)據(jù)庫(kù)”。
(二)實(shí)證結(jié)果分析本文實(shí)證分析分兩步來(lái)進(jìn)行,首先檢驗(yàn)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對(duì)地方政府城市偏向的影響,再檢驗(yàn)地方政府城市偏向?qū)Τ青l(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影響。1.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對(duì)地方政府城市偏向的影響分析財(cái)政分權(quán)對(duì)地方政府城市偏向影響的實(shí)證分析結(jié)果見(jiàn)表1。根據(jù)Hausman檢驗(yàn)的結(jié)果,表1中(1)~(5)模型分析結(jié)果均顯示應(yīng)采用固定效應(yīng)模型。同時(shí),為了避免變量之間的自相關(guān),在模型(2)~(5)中加入了AR(1)項(xiàng),結(jié)果發(fā)現(xiàn)D.W.值接近2,能夠較好地消除變量間可能存在的自相關(guān)性,其擬合優(yōu)度也較好。模型(1)~(5)中報(bào)告的回歸結(jié)果顯示,財(cái)政分權(quán)與城市偏向之間負(fù)相關(guān),也就是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增加不利于以三農(nóng)財(cái)政支出占總財(cái)政支出比重來(lái)衡量的城市偏向,即有利于增加對(duì)城市地區(qū)的支出。這與一般理論模型的結(jié)論一致。實(shí)際人均GDP指標(biāo)系數(shù)為正,而實(shí)際人均GDP的平方系數(shù)為負(fù),說(shuō)明人均實(shí)際GDP對(duì)城市偏向的影響是非線性的,同時(shí)也說(shuō)明對(duì)GDP的追求確實(shí)引致了政府的城市偏向,而且影響效應(yīng)是遞增的,雖然增速在放慢。進(jìn)一步分析模型(2)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數(shù)據(jù)集中在遞增的區(qū)間上,當(dāng)實(shí)際人均GDP低于4.4萬(wàn)元時(shí)①,“三農(nóng)”支出比例隨實(shí)際GDP上升,高于4.4萬(wàn)元時(shí)則相反。由于我們以2004年為基期計(jì)算的實(shí)際人均GDP基本都低于4.4萬(wàn)元,因此擬合的結(jié)果是“三農(nóng)”支出比例隨實(shí)際GDP上升,但上升的速度逐漸降低。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對(duì)城市偏向的影響在模型(1)~(5)中均顯著為正,說(shuō)明其有助于弱化政府的城市偏向。而為了避免與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偏向之間可能存在的內(nèi)生性,模型(3)中用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的滯后一期替代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而在模型(4)中采用工具變量法,將滯后一期的實(shí)際人均GDP和滯后一期的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作為當(dāng)期的工具變量進(jìn)行回歸,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模型(2)、(3)、(4)差別不大,說(shuō)明結(jié)果比較穩(wěn)健。城市化率對(duì)城市偏向的影響在模型(1)~(4)中系數(shù)符號(hào)、顯著性變動(dòng)均較大,說(shuō)明其影響不夠穩(wěn)定。這與城市化對(duì)城市偏向的影響確實(shí)存在雙重效應(yīng)與不確定性有關(guān)。城市化進(jìn)程與政府城市偏向的關(guān)系較復(fù)雜,一方面城市化意味著人口和資源向城市集中,此時(shí)政府對(duì)城市的投入更容易產(chǎn)生規(guī)模效應(yīng),獲得更高的生產(chǎn)效率和收益率;而另一方面在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區(qū),政府可能更傾向于集中資源投資于城市的發(fā)展,因而財(cái)政支出上體現(xiàn)出更強(qiáng)的城市偏向性,兩個(gè)方向的作用使得兩者關(guān)系不確定。在模型(5)中則加入了全部的控制變量,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財(cái)政分權(quán)、實(shí)際人均GDP、城市化率、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系數(shù)都符合預(yù)期且通過(guò)顯著性檢驗(yàn),而控制變量除了工業(yè)化率與城市偏好負(fù)相關(guān)外②,其他變量都不顯著。為了進(jìn)一步檢驗(yàn)回歸的穩(wěn)健性,本文按照兩類方法來(lái)進(jìn)行分地區(qū)考察③,一種是按照我國(guó)東、中、西部地區(qū)劃分標(biāo)準(zhǔn)分別進(jìn)行東、中、西部地區(qū)的回歸(見(jiàn)模型6~8),另一類借鑒張晏和龔六堂(2005)以及王文劍和覃成林(2008)[39]的做法④進(jìn)行回歸(見(jiàn)模型9~11),表2報(bào)告了穩(wěn)健性回歸結(jié)果。結(jié)果顯示,模型(6)~(8)中財(cái)政分權(quán)與城市偏向的關(guān)系都是相當(dāng)穩(wěn)健的,實(shí)際人均GDP、實(shí)際人均GDP平方、城市化率、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均通過(guò)了顯著性檢驗(yàn),而且系數(shù)也符合預(yù)期結(jié)果。模型(9)~(11)中財(cái)政分權(quán)與東中西部虛擬變量的乘積與城市偏向的結(jié)果均符合預(yù)期,說(shuō)明穩(wěn)健性也相當(dāng)好。而實(shí)際人均GDP、實(shí)際人均GDP平方、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也通過(guò)了穩(wěn)健性檢驗(yàn),但是城市化率在三類地區(qū)的檢驗(yàn)均不顯著,估計(jì)與城市化進(jìn)程對(duì)城市偏向的影響存在雙重效應(yīng)有關(guān)。2.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qū)Τ青l(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影響分析以上證實(shí)了財(cái)政分權(quán)與城市偏向之間存在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而城市偏向與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程度之間理論上應(yīng)該存在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這需要進(jìn)一步的驗(yàn)證。表3報(bào)告了針對(duì)中國(guó)省級(jí)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分析結(jié)論。Hausman檢驗(yàn)結(jié)果顯示,應(yīng)采用固定效應(yīng)模型。同時(shí),考慮到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程度類似于一個(gè)存量的概念,因而很可能與前一期的均等化程度高度相關(guān),我們將上一期的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指數(shù)也作為解釋變量之一引入模型,模型(12~14)回歸結(jié)果顯示,D.W.值均接近2,調(diào)整的R2均大于0.93,較好地消除了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自相關(guān)性,擬合結(jié)果較好。模型(12)中的城市偏向?qū)Τ青l(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系數(shù)顯著為正,說(shuō)明二者之間確實(shí)存在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模型(13)(14)中分別加入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率、城市化率、工業(yè)化率、民營(yíng)化率、對(duì)外開(kāi)放度、人口密度等變量后,城市偏向與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之間均存在顯著的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此外,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滯后一期的數(shù)據(jù)也與當(dāng)期均等化指數(shù)顯著正相關(guān),這也說(shuō)明均等化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是一個(gè)漸進(jìn)過(guò)程,前期的均等化基礎(chǔ)也是后期均等化程度的重要影響因素。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率指標(biāo)與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顯著負(fù)相關(guān),這與人們一般認(rèn)知的經(jīng)濟(jì)越發(fā)達(dá)公共服務(wù)供給水平應(yīng)該越高恰恰相反。但是這種現(xiàn)象在發(fā)展中國(guó)家卻是常見(jiàn)的,因?yàn)樵贕DP導(dǎo)向明顯的發(fā)展中國(guó)家,追求GDP政策必然會(huì)引致城市偏向,從而不利于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實(shí)現(xiàn)。而在控制變量中,除了工業(yè)化率指標(biāo)與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負(fù)相關(guān)外,其他都無(wú)法通過(guò)顯著性檢驗(yàn)。為了檢驗(yàn)表3的報(bào)告結(jié)果的穩(wěn)健性,這里繼續(xù)采用表2中穩(wěn)健性檢驗(yàn)的方法分地區(qū)進(jìn)行考察,模型(15~17)是按照我國(guó)傳統(tǒng)的東、中、西部地區(qū)劃分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分類,模型(18~20)是借鑒張晏和龔六堂(2005)[38]以及王文劍和覃成林(2008)[39]的做法進(jìn)行的回歸,表4報(bào)告了穩(wěn)健性回歸結(jié)果,得出了無(wú)論按照哪一類檢驗(yàn)方法,城市偏向?qū)Τ青l(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影響系數(shù)都顯著為正的結(jié)論,證實(shí)了二者存在負(fù)相關(guān)的假設(shè)。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率對(duì)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影響系數(shù)顯著為負(fù),證明了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并不必然引致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偏向以及基本公共服務(wù)自身屬性①也存在關(guān)鍵影響。而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滯后一期對(duì)當(dāng)期均等化的影響也存在顯著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
三、結(jié)論與政策啟示
由于城市地區(qū)的公共服務(wù)有助于展現(xiàn)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jī)并使其得到較多的晉升機(jī)會(huì),因此存在經(jīng)濟(jì)人特性的地方政府官員在公共決策中難以避免具有城市偏向。并且在城鄉(xiāng)間配置公共服務(wù)資源的財(cái)政能力受到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的制約,在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較高的地方,其政府官員擁有的財(cái)政資源越多,從而有可能形成更為明顯的城市偏向。地方政府官員的城市偏向直接影響了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水平,越強(qiáng)的城市偏向越不利于實(shí)現(xiàn)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由此可知,要達(dá)到實(shí)現(xiàn)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的目標(biāo),應(yīng)該從以下幾個(gè)方面進(jìn)行:第一,切實(shí)扭轉(zhuǎn)地方政府公共決策中的城市偏向,關(guān)鍵在于改變長(zhǎng)期以來(lái)單一的“以GDP論英雄”的績(jī)效評(píng)估模式,提高為轄區(qū)內(nèi)農(nóng)村地區(qū)提供公共服務(wù)或者促進(jìn)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在地方官員晉升中的考核權(quán)重。第二,力求最優(yōu)的財(cái)政分權(quán)程度①(過(guò)度分權(quán)與過(guò)度集權(quán)都不利于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既要保證地方政府在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中具備足夠的經(jīng)濟(jì)自主權(quán),又要保證中央政府調(diào)控全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供給公共服務(wù)的能力。同時(shí),對(duì)地方政府配置自有財(cái)政資源、轉(zhuǎn)移支付財(cái)政資源時(shí)施加必要的約束與規(guī)范,尤其是對(duì)轉(zhuǎn)移支付財(cái)政資源要盡可能地貫徹地區(qū)公平、城鄉(xiāng)公平,約束地方政府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來(lái)配置資源的傾向。第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務(wù)供給在官員績(jī)效考核中的權(quán)重,讓基本公共服務(wù)供給績(jī)效較高的官員得到優(yōu)先晉升的機(jī)會(huì);而對(duì)那些在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供給績(jī)效明顯低于平均水平的地方政府官員要予以懲戒或降級(jí)降職。當(dāng)然,執(zhí)行這些政策的前提是按照統(tǒng)一規(guī)則、統(tǒng)一口徑編制各地區(qū)基本公共服務(wù)供給績(jī)效指數(shù),從而保證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指數(shù)的權(quán)威性、統(tǒng)一性與應(yīng)用性。第四,賦予農(nóng)民更多的話語(yǔ)權(quán),鼓勵(lì)農(nóng)民積極參與公共事物,健全農(nóng)村公共品的需求表達(dá)機(jī)制,減小城鄉(xiāng)居民的政治影響力差距,以弱化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行為,提高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wù)的均等化水平。
作者:劉成奎龔萍單位:武漢大學(xué)經(jīng)濟(jì)與管理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