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的入黨資格思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主人士的入黨資格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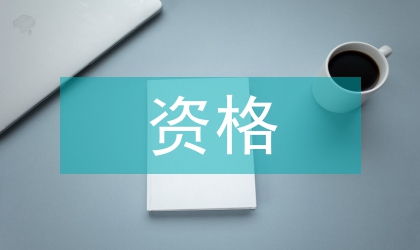
《黨史文苑雜志》2014年第十四期
一、沈鈞儒一生三次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日本侵華、民族危亡而國民黨消極抗日共產黨積極抗戰的歷史背景下,沈鈞儒毅然放棄功名利祿,向正義一方靠攏。他以“共產黨朋友”定位自己的政治身份,常去曾家巖“周公館”與共產黨員商討國是。在此過程中,他接觸到了更豐富的馬克思主義并深感可信。于是,1939年夏,他向在重慶的首次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當時,考慮到沈鈞儒是救國會和民盟等多個政治組織的領袖,在民主人士中聲望很高,留在派中意義更大,“先生現在是派的負責人,不參加比參加了作用更大,對工作更好”[6]P224。沈鈞儒認為的答復有說服力,就暫時擱置了入黨的想法,為民族大計需要,“做個非黨的布爾什維克”。事后,沈鈞儒同古念良的談話中提及了入黨之事,“我很想能再活二十年,做個光榮的共產黨員,可恩來先生說,我留在黨外能起著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從黨的決定,做個非黨的布爾什維克”。雖然入黨的愿望沒能實現,但這并沒有打消沈鈞儒了解中國共產黨政治理論和救國的念頭,他反而更加積極閱讀關于延安的報道和學習馬列主義、思想著作。2.新中國成立后的1950年,沈鈞儒向董必武、林伯渠提出了入黨請求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和各派并肩作戰,致力于同國民黨一道建立真正民主的、人民的聯合政府。可國民黨當局一意孤行,單方面撕毀《雙十協定》,發動內戰,政治上打壓派、迫害左派民主人士。尤其是將當時勢力最大、組織最廣的派———民盟,污蔑為“與共匪勾結一氣”,宣布為“非法團體”,要求“解散總部”“停止盟員活動”。沈鈞儒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及從革命教訓中認識到妥協退讓毫無意義,必須同一切反動政權斗爭到底。他堅決反對國民黨的這一無理行徑,他說:“民盟一定要繼續搞下去,內地不能公開搞,就到香港去搞。”[9]P641948年1月5日,應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和幫助,沈鈞儒轉戰香港,于歷史轉折關頭重建民盟總部,恢復民盟活動,組織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這件事不管是對沈鈞儒一生的革命事業還是民盟的政治前途都具有歷史性的轉折意義。沈鈞儒在聲明中號召民盟數十萬盟員“為徹底摧毀南京反動政府,為徹底實現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斗到底!”
隨后,他還在民盟一屆三中全會開幕式上指出民盟的奮斗方向“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團結各派合作,與中共在和平民主事業上密切合作”[8]P367。可見,是沈鈞儒在千鈞一發之際力挽狂瀾,領導民盟與國民黨徹底決裂,而選擇了“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10]P647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此后,沈鈞儒代表民盟積極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發表“五五通電”,表明今后的政治立場和前進方向是要與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1]P6。在所有派人士和社會賢達之士中,對新政協會議的召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沈鈞儒是最直接、最豐富、最偉大的貢獻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后,身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沈鈞儒,在思想上、行動上已經完全馬克思主義化,完全具備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條件。為此,1950年7月30日,沈鈞儒致函董必武,第二次提出了入黨請求。8月1日,他接到了董必武的復信。信中說:“衡老:大示奉悉,您誠懇地熱烈地企望入黨的心情,我和許多同志都能理解,而且應當說不是從現在始。我擬將您的信轉給中央諸同志一觀,請他們考慮。”[6]P350為進一步落實入黨大事,次日,沈鈞儒懷著誠懇而急切的心情登門訪問林伯渠,討論了入黨的愿望,并希望林伯渠能代為轉達。結果,中共中央考慮到他身份的特殊性依然沒有批準。3.逝世前的1962年,沈鈞儒向中央統戰部提出了入黨請求沈鈞儒第二次入黨的請求雖然仍未如愿,但他一不埋怨,二不氣餒,繼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民盟、政協、人大工作竭盡余力。然而,天不假年,1962年,87歲的沈鈞儒身體每況愈下,一直處于休養狀態。他擔心去世之后仍不能實現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便于9月9日在頤和園介壽堂與胡愈之、沙千里、薩空了、范長江、沈譜、王健談話時,第三次提出了入黨問題,談話中甚至提出了“如生前不能入黨,希望在我死后追認為共產黨員”的打算。他嚴肅地說:“我很早就期望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前曾為此寫信給董老,董老回信說要和黨內同志研究。我想可能是因為民盟的工作,還不好參加。現在我仍懇求黨加以考慮,如生前不能入黨,希望在我死后追認為共產黨員。”
沈鈞儒的這次談話精神由胡愈之整理成文,呈遞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統戰部收到報告后第一時間討論研究沈鈞儒是否該入黨的問題,經協商并得到中央領導人同意后鄭重給出了與前兩次一樣的處理意見。當時中央統戰部分管干部處的金城回憶說:“縱觀沈老一生的言行,無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都稱得上是黨的親密戰友,革命的左派,可以認為,他確已具備了入黨條件,甚至比民主人士中某些已入黨的同志革命歷史更長。”[5]P308據此可知,民主人士成功入黨已有先例,而沈鈞儒更加具備入黨的一切條件。既然如此,中央為什么不同意呢?金城的回憶給出了答案:“若將他作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作為黨外的共產主義者,來鼓勵、團結廣大黨外朋友,更有他特殊的意義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所起不到的作用。……經部常委會討論決定后,十月二十七日,內部正式向中央寫了報告,闡述了一致的意見:‘以民主人士中的一個左派旗幟來肯定他的貢獻更為有利。’”[5]P308-309隨后中央批準了這一意見。據此可知,中央沒有批準沈鈞儒入黨,是經過統戰部、中央主管同志和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慎重思考后作出的重大決定。
二、沈鈞儒一生中三次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原因
沈鈞儒自1907年的而立之年參加請愿運動始至1963年逝世,幾乎經歷了中國近現代史上所有的重大革命運動。他的一生,經歷了由一名憲政改良主義者向國民革命主義者再向民主法治運動者的轉變。無論政治思想和救國理念如何變化,有一條“紅線”始終貫穿他的一生。這條“紅線”,就是他的政治思想隨著革命進程的推進不斷馬克思主義化的歷程。而這恰恰正是他三次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原因。沈鈞儒一生與馬列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淵源頗深,最早可追溯到后期。其間,他先后認真閱讀過《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這在他的日記和家信中都有記載。“馬克思的大著作《資本論》,更將共產黨宣言底量及質加以擴充。資本論所貢獻之盈余價值觀,他自認為說明資本主義掠奪之實在的工具。……據我的意見,資本論中最好的部分,就是討論經濟的事實,因為馬克思對于這些事的知識,非常精博。”[12]大革命時期,沈鈞儒與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中共黨員宣中華和潘楓涂有著思想碰撞和實踐合作。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中共黨員的影響,他的思想和行動日益左傾,逐漸向共產黨靠攏。為此,他還遭受國民黨右派的迫害而鋃鐺入獄。全面抗戰爆發后,他的政治主張則完全偏向中國共產黨一派,因為他認為“共產黨是人民的黨,它的政治主張是正確的,是得到人民擁護的”[7]P56。解放戰爭中期,他的思想已完全“一面倒”,倒向中國共產黨開辟、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他在民盟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式記者招待會上對外宣布民盟放棄走歐美資產階級議會制的所謂“中間道路”,“必須在真民主真和平之中認清敵友,在是非之間,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是沒有‘超然的’或者‘中間路線’的存在可能”[8]P403。之后,他又在民主人士招待會上號召各派放棄“在國共之外造第三條船”[13]P645的道路。“沈鈞儒指出過去一些所標榜‘中間路線’,現已走不通。除參加革命或反革命,即無路可走。”
在沈鈞儒看來,真正的“中間路線”是不存在的,所謂的中,要么偏左,要么偏右。這一時期,他還仔細研究過思想的理論著作,他曾于1948年2月18日和2月20日閱讀的《新民主主義論》,并予以高度評價。新政協會議召開期間,他受《新民主主義論》的啟發,于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提出了符合新民主主義原則的建國總路線,“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構,再加上民主集中的組織,團結協商的精神,這就成為目前我們所可能采取的總的方向和總的路線”[8]P588。新中國成立后,沈鈞儒從未停止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更加堅信自己對黨的判斷和選擇。據許崇清回憶,沈老多次教導民盟全體盟員要做到“聽黨話,跟黨走”[7]P74,一再勉勵家人和晚輩要“活到老,學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7]P74,還經常教導大家“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要好好學習著作,并虛心向工農學習”[7]P74。1962年,已過耄耋之年的沈鈞儒對中國共產黨和的感情更篤,佩服更甚。1962年10月1日,年近90的沈鈞儒依例參加國慶慶典時,在天安門城樓上問候他的健康狀況,散會后還親自扶他同下電梯,他異常興奮,回到家后,激動地說到:“我又見到了”,“我們要永遠聽的話,永遠跟中國共產黨走”。[9]P139“永遠跟中國共產黨走”,這既是沈鈞儒豐富人生的經驗總結,也是對子女后代們的諄諄囑托。沈鈞儒逝世后,在清理遺物時,人們發現他的臥室書桌上擺放著《實踐論》《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等著作。桌上還放置著畫像和歌頌延安的詩詞。他一生“又紅又專”,“能黨能群作前鋒,先生先覺老更紅,全心全意為救國,立德立言又立功”[9]P170,不愧為一名黨外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
三、小結
沈鈞儒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受其影響,思想偏于左傾。大革命時期,沈鈞儒的救國理念和政治實踐日益向中國共產黨靠攏。自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沈鈞儒從歷史與現實、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鮮明對比中,發現中共才是國家和人民的救星,他逐步吸收和靠近馬克思主義和思想,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帶領統一建國同志會、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民主同盟等政治團體與中國共產黨協同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最終成為了一名非黨的“布爾什維克”。沈鈞儒一生三次在歷史轉折關頭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其根源在于他自幼形成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和自晚清憲政運動以來培育的救國救民政治抱負。此外,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政黨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也深深地吸引了他。即是說,沈鈞儒入黨的原因有兩個層面,一是愛國主義情懷,這是他畢生走在革命潮頭,追求進步的不竭動力;二是中國共產黨的救國主張和指導理論,馬列主義、思想是完善沈鈞儒政治理論和革命實踐最重要的“精神食糧”。
作者:肖建平單位:湖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