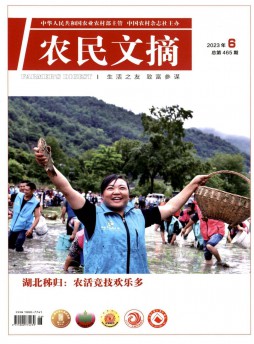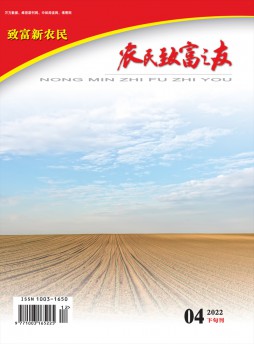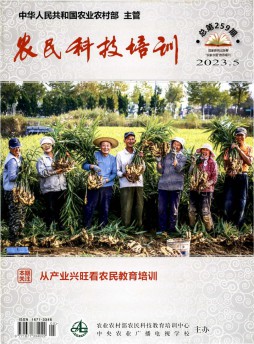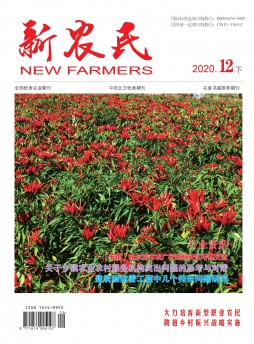農民走向市場經濟阻礙因素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農民走向市場經濟阻礙因素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80年代以來,從農村開始的由農民們首先掀起的這場具有“革命意義”的中國經濟改革,震撼華夏大地,給中國帶來了勃勃生機。然而,當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最終定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社會寓于對中國農民的傳統認識與成見,流行將農民“逼”入市場“推”向市場的提法,似乎是農民們不歡迎、不愿意進入市場,其實,如果僅說在“冒險”與“競爭”面前會有幾份膽怯或畏懼,那這就不獨是農民如此,就是對其他階層的人們來說,也是一種心理上的正常反映。可是,當前中國農村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農民們首先所遇到的主要障礙絕不是這種可用“逼”之、“推”之就能解決的農民自我心理上的不適應,而是他們邁向市場經濟的航道不暢,甚至有難以逾越的屏障。
(一)
走向市場經濟的農民,其用以參與市場經濟競爭的基礎是從事農業經營,但是,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決定了再生產過程受自然條件的限制,生產周期長,資金投入回報率一般低于其他產業,同時,從事農業勞動比較艱苦,農村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不及城市,與其他產業相比,農業經營還處于自然風險和較大的市場風險雙肩擔的不利地位。因此,農業在經濟資源的競爭中常處于較弱與不利地位,是社會經濟中的弱質產業。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在經濟資源的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大量經濟活動主要靠市場調節,社會經濟資源流向,主要受市場價值規律和供求規律的支配。自然,農業經營者的行為也是由利潤目標決定的,它要求經營農業的比較利益逐步同其他產業基本持平。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加快,當非農產業預期收益率明顯高于農業,農業經營的機會成本明顯趨高時,當農業的投資效益和勞動報酬明顯低于其他產業時,中國的農業經營者——廣大農民要把生產要素轉向非農業,這本應是情理中之事。
然而,“民以食為天”。12億人口的中國,吃飯為天下第一件大事。作為主要農副產品的糧食,不僅僅是一般商品,而且還是特殊商品,為當代中國領導人稱之為“萬物之寶”[1]。因此,農業實際上是一個自身經濟效益低而社會效益高的不可削弱的社會基礎產業,有鑒于此,中國歷代政府主觀上都以“重農”政策作為基本國策,而世界上各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和實現工業化之后,政府都以不同方式,通過宏觀調控對農業采取特殊的扶持政策,如政府承擔了大量的對農業公共服務的開支,對生產者的價格補貼以及農貸、利率、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以抑制農業在市場經濟中弱質的影響,使經營者的實際收略高于經營其他產業的收入,至少不低于或接均收益,以利農業真正的穩定發展。我國現在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政府在重視效益的同時,正確處理好農業弱質產業的地位問題,實際上是能否給農民一個公平競爭機會的問題。
新中國建立后的前30年中,中國農民在計劃經濟的監控下,默默地為工業化貢獻積累,除國家支農返還的部分外,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的積累也達4481億元。生產責任制實行之后,這種狀況得到緩解,然而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化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低于機會成本高的問題日益顯露出來。老實巴交的農民也開始不再死守土地,有了自己的選擇。與此同時,農業的基礎地位也有動搖跡象。無疑,黨和國家歷來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切實加強農業已成為國家領導人反復強調的大政方針,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重視農業沒有真正到位,尤其沒有落到切實保障農民經營農業的收益上,“口號農業”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人們都說,發展農業,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然而,實際情況怎樣呢?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在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比重仍在逐年不斷下降[2];農業信貸也難以到位,1993年中央11號文件說給農業增加225億元貸款,結果是政策性貸款變成商業性貸款,最后又成為只給信貸規模,不給資金,一分錢未出銀行[3]。由于投入少貸款到不了位,致使農業基礎設施落后,農業科技推廣網絡處于“錢緊、線斷、網破、人散”的危急狀態[4]。農業經營的風險保障機制也遲遲建立不起來。工農業產品剪刀差越拉越大。1994年是糧棉油提價幅度較大的一次,但也就僅能達到93年農資漲價的補償水平。于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兩難的局面;農資限價限不住,糧油補貼補不起,國家苦苦找不到抑制農資價格上漲的辦法,但是,糧棉是特殊商品沒有變,國家只好以定購辦法來控制1000億斤糧食和幾千萬擔棉花。農民在完納農業稅之后,這定購的糧棉又成了農民的任務和義務。
國家每年給農民下達的定購糧棉,既是任務,又是義務,農民當然不能不種,不能不交。上面規定,“省長負責米袋子”,糧食的完成更有保證。但是,這些糧食是農民用市場高價農資生產出來的。自1990年到1993年,農資的零售價格指數上漲21.7%;1994年國家較大幅度提高糧油棉價格,農資則以更大幅度上漲,有的“甚至翻番”[5]。根據湖南有關部門統計,1994年早稻收購價每擔谷44元,生產成本41元,一擔稻谷的勞動報酬僅3元錢。根據今年農資價格上漲情況,預計每擔稻成本上升為57.8元,如收購價不便,農民生產一擔稻谷的報酬就是坐定賠他7.8元[6]。如以市場價和收購價相比,每斤糧食至少比市場低出2~3角錢,僅1000億斤定購糧計,農民每年就少收入200~300億元。棉花也是如此,1993年9月起每擔價格由300元提到400元,但到11月下旬,市場價已是每擔800元,市場價與計劃竟相差一倍[7]。據國家計委的監測,進入今年以來,農資價格的逐月攀升,1月份比上月上漲3.1%,比去年同期上漲28.5%,2月份又增加里2.1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上漲30.6%[8]。農民反映:“工業品是一年幾個價,糧食是幾年一個價”,糧食是微調,農資是倍漲[9]。若是老天保佑遇豐收年,賣糧難又困擾農民。由于沒合理的最低保障線,農民豐年還是困難。即使這樣,我們還只能是力爭不給農民打“白條”,有的報紙甚至還把銀行不給災區糧農棉農打“白條”作為頭版新聞報道加以表揚[10]。所以,農民調侃說:“省長負責米袋子,市長負責菜籃子,就是沒有負責我們的錢袋子”[11]。天天說重視農業,到處講把農民推向市場,原來是讓我們農民走“市場經濟的投入,計劃經濟的產出”的道路[12]。話雖刺耳,卻道出了當前農民走向市場經濟過程中的困境。
價值規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遵循市場經濟基本規律與原則,加強農業政策保護,增加農業投入,進而處理好農業弱質產業與糧食特殊商品、農業市場經濟投入與計劃經濟產出的關系,合理地制定糧食的收購價和具有實質意義的主要農產品保護價格,使農業經營的比較效益逐年同其他產業基本持平,是當前穩定社會和培育農村市場經濟應急需解決的問題。把農民推向市場,首先要給農民一個平等競爭的機會。
80年代中期尤其是進入90年代之后,中國農村社會的熱點和焦點之一,就是造成農民沉重負擔的“三亂”問題(亂攤派、亂罰款、亂收費)。如果說,農業是立國之本,糧食是特殊商品,為大局計,不得不暫時讓農民在市場經濟中處于尷尬的不利地位,那么,“三亂”無度,則直接與社會的治亂與農村市場經濟的發育背道而馳了。
說起1990年前的農村“三亂”,真是使人感慨,令人瞠目。本來,按政府規定,農民的負擔包括農業稅/集體統籌和地方提留三大類13種,總負擔額不能超過上年純收入的5%。對于這些,農民一般是能夠承擔并大都是忠實的納稅者,然而“三亂”風起,各種攤派/集資收費數額扶搖直上,各種罰款名目層出不窮。據1990年的統計,僅國務院25個部門下發的文件中,涉及農民各項負擔的就有8大類148項之多[1]。90年代初期,河南全省幾年內下發的有關農民負擔的文件有46個,涉及向農民攤派收費的項目達182個[2]。到了縣、鄉,各項收費/攤派更是有增無減,四面八方都向農民伸手。以致弄到:“你要攤派,我要攤派,一旦有權,就敢攤派;富要交錢,窮要交錢,只要被管就得交錢”[3]的局面。于是,工商稅務一齊來,七站八所一齊要,吃喝拉撒還要農民包,那七扣八扣的賣糧款和匯回家的打工錢也給你變成了“白條”與“綠條”。青年農民結婚,除登記費、結婚費與體檢費外,還得繳納新婚費、準生費、母子平安費、禮品費、晚婚費、計生押金費,多至13項,費用高達1470.50元。[4]尤其是一些鄉鎮的“大蓋帽”,連制服著裝也向農民要。據農業部的調查,1990年農民社會負擔(主要是亂攤派和亂收費)共計達136億元,人均16元,而國家征收的農業稅,當年只73.3億元,社會負擔超過國稅近一倍;另外,農民繳納的集體提留與鄉統籌費兩項共計達359.4億元,人均達到41.15元。農業稅外,農民負擔合計495.4億元,占上年農民純收入的10.95%,這還不包括一些無法統計的負擔。[5]在湖南省攸縣的高和鄉小塘村,僅鄉統籌、村提留就人均高達112.75元,占全年人均收入的1/4。[6]攤派收款雖無章法,然而農民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識少,只能服從,少敢違抗,否則,定你個抗拒或“踩線”之罪,公安、治保找上來,抓人又罰款,叫你吃不了兜著走,還得貼上一份人情錢。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收款、攤派、罰款也實行承包,且多交由編外人員執行,“三亂”之風更為肆虐。農民嘆言,過去割農民資本主義尾巴是“一批二斗”,現在讓農民勞動致富則行“一罰二扣”。[7]
在“三亂”行為中,使步向市場的農民感到膽寒的莫過于各地工商行政部門濫設各種關卡。這些關卡多設于各交通要道,市場貨物來回暢流之處,可謂扼住敢闖市場的農民的要害部位。在這里,一些執法人員任意擴大收費范圍,提高收費標準和重復收費,強行扣罰沒貨物,不怕你不交錢,就怕你不上路。1990年8月30日,一輛載有5噸鮮葡萄的卡車從山東曲阜上路,運往福建省光澤縣銷售。起運前,貨主為怕路上受阻,各處稅費、手續均在產地一應辦齊。然而在卡車到達目的地的1000余公里的道上,竟遭到百余個關卡的刁難或重復收費,其中九個關卡扣留,被重復收費1200多元。結果,本可3天到達目的地而費去8天,5噸葡萄全部爛掉,損失1.1萬元。[8]這個市場弄潮兒終于栽倒在關卡之下。1991年9月,另一位山東農民在陜西某縣收購6噸石榴,運往深圳銷售,上路前也在產地辦好所有的稅費、證件手續。結果,在路上處處遭卡,重復交費1000多元,6天后到達深圳,石榴已成爛醬,整整貼了3萬多元。這位農民從此背上了深重的債務包袱。[9]目睹這種狀況,當事農民欲哭無淚,其他農民則望市而卻步。
1993年春天以后,整治“三亂”和減輕農民負擔,聲勢最為浩大,對“三亂”和涉及農民負擔的文件,全國上下都進行全面整頓。到1994年七月,國家22個部委先后取消了450項涉及農民負擔的項目與文件,各省(區、市)相繼取消與同類項目有關文件則達到27000多項。各級人大都先后頒布了減輕農民負擔的法規和條例,發放了被農民稱之為“明白紙”的《農民負擔卡》[10],以杜絕卡外收費。僅1993年夏到1994年夏的一年間內,全國減輕農民負擔103億元。[11]應該說,幾年中的治理“三亂”,成績不謂不大。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頑癥”由來已久,“三亂”病根并未完全鏟除,農民負擔回升與被撤關卡撤而復設時有耳聞。有的農民手持“農民負擔卡”再次表示困惑:為什么有了“明白紙”,負擔仍舊沒有減輕?原來,有的黨政領導在農民純收入做文章,搞虛報浮夸,讓農民負擔的提留款及其他稅款按夸大的數字標準繳納,大大加重了農民的負擔[12];有的地方則在農民負擔的5%以外做文章,把種種不好公開的攤派收款轉到水電費等不在5%限內的費用中[13];有的則采取集體承包工程,以不付或克扣民工工資的辦法增加農民負擔[14];有的則把各種攤派費轉入鄉鎮企業中支付[15];有的地方還以增加新稅種和賣城市戶口等方法變相搞“三亂”[16];有的農村干部為避免將來攤派收錢困難,干脆將《農民負擔卡》堆放在自己家中,為“三亂”回潮留下后路[17];據8月份出版的95年第15期《半月談》報道,不久前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局聯合調查的結論表明,1994年農民的社會負擔比上年增長38.2%,金額達85億元。顯然中央的“減負”政策在農村并沒有真正落實。
再看那連接市場的紐帶——縱橫交錯的公路國道,隨車暗訪的記者驚呼:“千里國道,‘三亂’又回潮”。那是今年3月,運菜的卡車自海南至武漢,2000多公里的交通干線上,共遇各種檢查站卡47個,平均每公里被攔車檢查或交費一次,罰款與收費共計2086元,一些工作人員甚至還毆打貨主、司機[18]。5月,江西省農業廳廳長劉初潯隨生豬運輸車暗察公路“三亂”,但見江西到廣州的路段,關卡林立,呼吁急需引起重視[19]。而在遼寧省康平縣,該縣的專賣局于今年4月竟憑17年前省“革委會”發的246號文件在公路上設卡收費、罰款,更令人感到“三亂”頑癥難治[20]。事實證明,整治“三亂”的任務仍十分嚴峻。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遵守規則,管理循章法,市場則活,社會則活,生產有后勁,市場趨繁榮;亂了規則,予取予求,市場則亂,社會也將萎縮。“三亂”實為當前中國農村市場經濟正常發育和農民邁向市場的大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