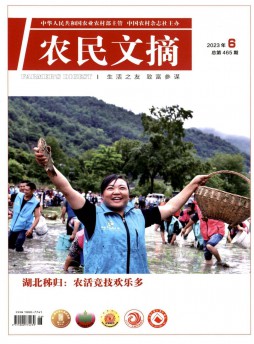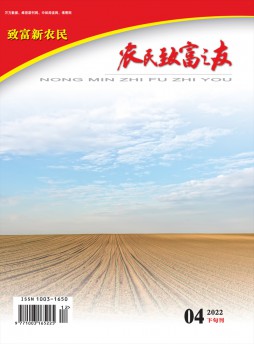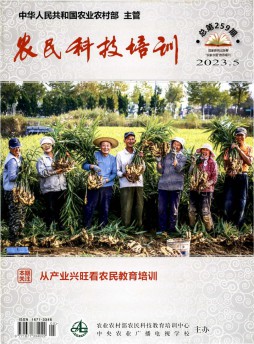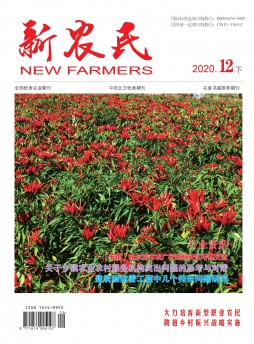農(nóng)民財產(chǎn)權利的思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農(nóng)民財產(chǎn)權利的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我國城鎮(zhèn)化滯后,城鎮(zhèn)化率偏低,也與農(nóng)民財產(chǎn)權利難以實現(xiàn)有著直接關系
2012年我國城鎮(zhèn)化率已達52.3%,但按戶籍人口計算也僅35%左右,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這是因為按現(xiàn)行法規(guī),農(nóng)民戶籍要“農(nóng)轉非”成為市民,首先,要退出承包地、宅基地;其次,農(nóng)民成為市民,一要有住房,二要有社保,三要有就業(yè),這三樣都需要農(nóng)民自己拿出一部分錢來。住房和社保可納入國家統(tǒng)籌,但就業(yè)則主要靠農(nóng)民自己來解決。大多數(shù)農(nóng)民文化低,無專業(yè)技術,難以參與勞動力市場競爭,而自己做小本經(jīng)營又缺乏資金,因而許多農(nóng)民想成為市民卻又不敢成為市民。說到底,成為市民是需要成本的。據(jù)有關部門測算,農(nóng)民成為市民,其個人成本在1.8萬元左右,政府成本在8萬元左右。因此,農(nóng)民財產(chǎn)權利能否實現(xiàn),直接影響和決定著城鎮(zhèn)化進程的推進。
二、現(xiàn)行土地征用制度是農(nóng)民財產(chǎn)權利難以實現(xiàn)的最大障礙
(一)長期以來對農(nóng)民的土地征用是行政行為而不是市場行為目前我國的《土地管理法》是1998年修訂的,基本沿用了計劃經(jīng)濟時期的指導思想和做法。只側重于保護國家利益而嚴重忽視勞動者個人利益。它規(guī)定,農(nóng)民的承包地服從用途管制原則,只能農(nóng)地農(nóng)用,農(nóng)地變非農(nóng)用建設用地,必須實行國家征收或征用。即農(nóng)村集體土地要轉為城市建設用地,必須經(jīng)過政府征用,變集體所有為國家所有。這樣,農(nóng)村集體土地的產(chǎn)權主體就被排斥在了市場交易之外,而農(nóng)村土地變?yōu)槌鞘薪ㄔO用地后,產(chǎn)生的巨大級差地租收益,農(nóng)民則無權參與分享,政府在土地一級市場用極低的征用費拿到土地,然后在土地二級市場競價拍賣,這中間的暴利正是催生近年來各級政府產(chǎn)生土地財政的根源。有報導披露,2002年,某市政府向農(nóng)民征地,每畝最低8萬元,最高20萬元,而轉手拍賣每畝最低120萬元,最高980萬元。這種經(jīng)營土地獲取高額利潤的做法,已成為近年來不少地方政府創(chuàng)造政績,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改善部門福利的一條主要途徑。
(二)現(xiàn)行法律法規(guī)對被征地用途的補償標準缺乏明確規(guī)定由于一直以來法律對被征用農(nóng)地用途的補償標準不明確,這樣,各級政府便根據(jù)征地用途參數(shù),各自制定補償標準,這便造成了同一村的土地,由于公路建設、企業(yè)用地、商品房開發(fā)等用途的不同而補償標準相差數(shù)倍,從而引起失地農(nóng)民的強烈不滿,并引發(fā)一系列矛盾。并且,現(xiàn)行補償?shù)姆煞ㄒ?guī)不能真實反映補償土地年產(chǎn)值的真實價值。如種糧的土地與種特種經(jīng)濟作物的土地在年產(chǎn)值上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政府的補償往往一般都按種糧來計算,這樣的結果吃虧的是失地農(nóng)民。同時,補償規(guī)定里只有最高補償標準限制。如農(nóng)民集體土地轉為國有,政府按土地產(chǎn)值給予不高于30倍補償,這其中包含了農(nóng)民失去土地的補償和無法務農(nóng)的安置補償,但卻沒有最低補償標準,這就為一些政府機構盡量壓低補償標準提供了可能。
(三)現(xiàn)行的土地征用制度缺乏對失地農(nóng)民的社會保障和再就業(yè)功能在現(xiàn)行征地補償標準下,失地農(nóng)民得到的各種補償根本不可能靠它來養(yǎng)家、養(yǎng)老和維持自己的生存。他們需要最低社保來解除后顧之憂,需要再就業(yè)來增加收入,但現(xiàn)行的法律法規(guī)卻缺乏這方面的規(guī)定和保障。現(xiàn)行的三種對失地農(nóng)民的安置辦法是:一是屬村集體安置的將安置費支付給村集體;二是屬用地單位安置的,將安置費支付給用地單位;三是不須安置的將安置費直接發(fā)放給個人。在市場經(jīng)濟下的今天,這三種辦法都難以解決失地農(nóng)民的生活保障和再就業(yè)問題。首先,把安置費支付給村集體,一旦村集體經(jīng)營不善而破產(chǎn),則失地農(nóng)民將血本無歸而無法生存;其次,由用地企業(yè)安置,在市場經(jīng)濟下,由于失地農(nóng)民的年齡、文化、技能等因素制約,用人單位或難以接受,或暫時接受,以后也會不管,因企業(yè)沒有義務包管終生;第三,將安置費給予農(nóng)民“一次性了斷”,而失地農(nóng)民因自身因素,再就業(yè)難,又無低保,靠那點安置費,在物價年年上漲情況下,再精打細算也會坐吃山空。
三、創(chuàng)新土地征用制度,探索實現(xiàn)農(nóng)民財產(chǎn)權利的有效途徑
(一)修改有關法律法規(guī),政府退出非公益性用地行政征收現(xiàn)行的征地制度法律規(guī)定,農(nóng)村土地在轉為建設用地前,必須先被政府征用,轉為國有土地,再由政府處置。這些年來,這種征地制度在市場經(jīng)濟下,在推進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過程中,逐漸演變成了政府用行政的、強制的、壟斷的政府行為,低價獲取農(nóng)民的土地后,再高價出售,這種做法嚴重侵害了農(nóng)村集體土地產(chǎn)權和農(nóng)民的切身利益。對現(xiàn)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必須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改革:第一,修改現(xiàn)行《土地管理法》《土地法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guī)。我國憲法規(guī)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guī)定對土地實行征用”。但《土地管理法》等法規(guī)并未對公共利益作出明確規(guī)定和法律解釋,從而留下了較大的法律漏洞,造成許多地方政府所征用的土地超過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將多征的土地用來拍賣獲利。因此,必須在修改后的法律條文中對“公共利益”作出明確的司法解釋,防止一些地方政府亂打公益的旗號而隨意侵占農(nóng)民的土地。第二,對非公益性用地政府不再插手漁利,讓農(nóng)民集體土地所有權人在土地市場直接與企業(yè)、開發(fā)商談判土地出讓價格,以確保農(nóng)民的土地財產(chǎn)權利不受損失、并真正得以實現(xiàn)。
(二)農(nóng)村集體建設用地在農(nóng)村產(chǎn)權交易市場直接入市農(nóng)村集體建設用地又叫非農(nóng)用地,它是指現(xiàn)行土地制度管理下,由農(nóng)民集體所有,經(jīng)依法批準用于建設的土地,包括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用地、鄉(xiāng)鎮(zhèn)村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yè)建設用地、村民宅基地。這些年來,由于現(xiàn)行征地制度的障礙,農(nóng)村集體建設用地不管什么用途,一直是先被國家征用轉為城市建設用地后,再由政府處置。在政府處置中,有用于公益性的,但更多是用于非公益性的,這樣,農(nóng)民的這塊財產(chǎn)權利便受到了極大的損害。2008年10月13日,成都市正式掛牌成立了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交易所,在該交易所里,農(nóng)民承包經(jīng)營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林權、農(nóng)村房屋產(chǎn)權等均可公開流轉。當年,成都市錦江區(qū)就依照國有土地“招、拍、掛”的出讓方式,掛牌出讓了兩宗集體建設用地,以每畝80萬元、使用期40年的商用土地競價,被一家民營企業(yè)購得。以后又進行了數(shù)次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出讓,成都市這種農(nóng)村集體建設用地,在土地一級市場直接出讓非公益性用地,已突破了現(xiàn)行征地制度的法律限制,但事實證明,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使農(nóng)民的財產(chǎn)權利得以實現(xiàn)。
(三)農(nóng)民承包地實現(xiàn)財產(chǎn)權利最大化的渠道18億畝耕地的紅線絕不能被突破,這是關系國家糧食安全的底線。但如何讓農(nóng)民承包耕地的財產(chǎn)權利發(fā)揮最大財富效益,給農(nóng)民帶來真實的財富,有三條渠道可探索:第一,“農(nóng)不轉非而集中使用”。農(nóng)地農(nóng)用、農(nóng)地不能轉為非農(nóng)用地,這是國家嚴格規(guī)定。但個別農(nóng)戶土地流轉與村集體組織的土地規(guī)模流轉,財富效應大不一樣。現(xiàn)在中西部丘區(qū)、山區(qū)農(nóng)戶之間的土地流轉一畝一年約500~800元,而如果是連片幾百畝、上千畝,時間10~20年等,流轉給公司、大戶,則每畝可高達兩三萬元,并流轉后農(nóng)民可直接在流轉的公司打工。第二,農(nóng)地“農(nóng)轉非”,即在保證18億畝耕地的前提下,通過“增減掛鉤”“占補平衡”的原則,利用土地指標(地票)在農(nóng)村土地交易市場異地置換,從而使農(nóng)地變成建設用地,而被占農(nóng)地的面積同時也得到了補償。這樣,既確保了18億畝耕地的紅線不被突破,又滿足了交易雙方的各自需求,農(nóng)民也通過出賣建設用地指標使土地的財產(chǎn)權利得以實現(xiàn)。第三,利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賦予農(nóng)民的承包經(jīng)營權的抵押擔保權能,用承包地向金融機構申請、抵押貸款所需資金,以用于生產(chǎn)經(jīng)營、創(chuàng)業(yè)等需要。但這需要金融部門用改革、創(chuàng)新的工作方式方法來大力支持。
(四)農(nóng)村宅基地通過農(nóng)民集中居住,復耕宅基地、節(jié)約出建設用地指標競價出讓農(nóng)村宅基地屬非農(nóng)用地,在現(xiàn)行土地制度下,農(nóng)村宅基地既不能對外流轉,又缺乏退出機制。隨著城鎮(zhèn)化的推進,農(nóng)村人走房空,無人居住的“空置房”日漸增多,已造成了農(nóng)村土地的大量浪費。如果通過建設農(nóng)村居民新區(qū),把這些大量分散的宅基地復耕后,可節(jié)約出大量土地。而這些節(jié)約出的土地按照“城鄉(xiāng)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規(guī)定,即可置換成建設用地指標(地票),在土地交易市場競價出讓。這樣,農(nóng)民既住上了水電氣、通訊、交通、商店等生活設施都十分完善的新居,又節(jié)約出了大量的土地,并且這些節(jié)約出來的土地,又可作為建設用地指標在土地市場變成巨大財富,從而使農(nóng)民的財產(chǎn)權利真正得以實現(xiàn)。
作者:舒克龍單位:中共綿陽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