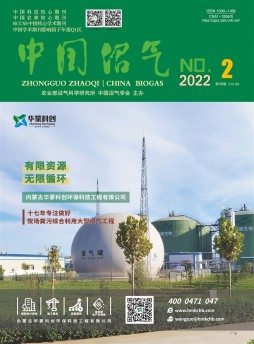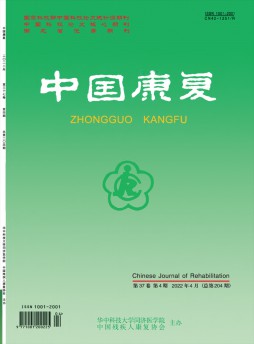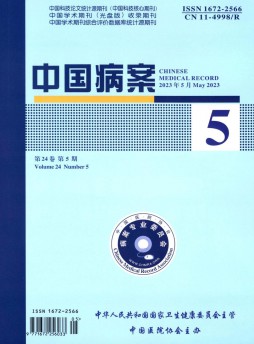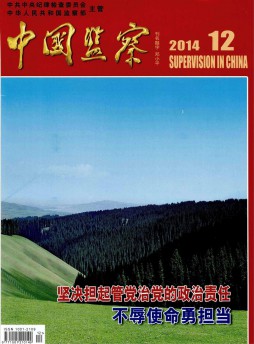中國律師業(yè)務(wù)空間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中國律師業(yè)務(wù)空間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引言
自1980年恢復(fù)律師制度以來,銷聲匿跡20多年的中國律師業(yè)不僅得以恢復(fù),而且的確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到2005年6月為止,中國執(zhí)業(yè)律師已達(dá)11.8萬多人,律師事務(wù)所11691家,每年辦理訴訟案件150多萬件、非訴法律事務(wù)80多萬件,開展義務(wù)法律咨詢260多萬件,辦理法律援助案件10.3萬多件。早在上個世紀(jì)末,即有學(xué)者用“中國律師業(yè)以其迅猛的發(fā)展、驕人的業(yè)績和嶄新的風(fēng)貌展示在20世紀(jì)中國社會的舞臺之上”來描述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中國律師業(yè)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然而,在為中國律師發(fā)展歡欣鼓舞的同時,我們不能不正視這樣的一個現(xiàn)實:本來應(yīng)該屬于中國律師的法律服務(wù)市場卻一直并且正在遭遇方方面面力量的蠶食,中國律師的業(yè)務(wù)發(fā)展空間不斷受到這些力量的擠壓。在來自法律服務(wù)所、外國律師代表處、法律咨詢公司、企業(yè)內(nèi)部法律顧問、老法官協(xié)會、離職甚至在任的公檢法人員、無兼職律師身份的法學(xué)教研人員等等勢力對法律服務(wù)市場混亂而無序的搶奪面前,中國律師業(yè)務(wù)市場份額呈相對萎縮趨勢,在法律服務(wù)市場實有領(lǐng)地正在相對縮小。從戰(zhàn)略層面考慮,中國律師拓展自身業(yè)務(wù)、表達(dá)法律正義的前景令人關(guān)注及擔(dān)憂。
本文試圖跳出在考察行業(yè)發(fā)展時一般來說難以擺脫的“縱向一比歡天喜地”的思維定勢,從“橫向一比危機(jī)四起”的角度,對中國律師拓展法律服務(wù)市場時遭遇的無序競爭以及本來應(yīng)該屬于自己的法律服務(wù)市場被蠶食的現(xiàn)狀進(jìn)行敘述,以期引起關(guān)心中國律師業(yè)發(fā)展人士對這一問題的關(guān)注和重視。
二、中國律師的“業(yè)務(wù)領(lǐng)地”應(yīng)該有多大?
考慮這個問題,可以從《律師法》等法律法規(guī)關(guān)于律師開展業(yè)務(wù)的授權(quán)性規(guī)定以及對非律師人員從事法律服務(wù)禁止性規(guī)定入手,弄清中國律師在法律服務(wù)市場上應(yīng)有的業(yè)務(wù)地位及不容他人動得的“業(yè)務(wù)奶酪”。
2001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25條對律師可以從事的法律服務(wù)進(jìn)行了廣泛授權(quán),即律師可以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聘請,擔(dān)任法律顧問;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當(dāng)事人的委托,擔(dān)任人,參加訴訟;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請,為其提供法律咨詢,申訴、控告,申請取保候?qū)彛邮芊缸锵右扇恕⒈桓嫒说奈谢蛘呷嗣穹ㄔ旱闹付ǎ瑩?dān)任辯護(hù)人,接受自訴案件自訴人、公訴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的委托,擔(dān)任人,參加訴訟;各類訴訟案件的申訴;接受當(dāng)事人的委托,參加調(diào)解、仲裁活動;接受非訴訟法律事務(wù)當(dāng)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務(wù);解答有關(guān)法律的詢問、寫作訴訟文書和有關(guān)法律事務(wù)的其他文書。從這些列舉性的授權(quán)規(guī)定來看,可以認(rèn)為律師從事法律服務(wù)的領(lǐng)域非常廣泛,從咨詢、顧問,到、辯護(hù),以及可以推論出來的律師見證、主持調(diào)解等等,幾乎沒有限制,可謂是“領(lǐng)地廣袤”。
另一方面,律師法第14條又明確規(guī)定,“沒有取得律師執(zhí)業(yè)證書的人員,不得以律師名義執(zhí)業(yè),不得為牟取經(jīng)濟(jì)利益從事訴訟或者辯護(hù)業(yè)務(wù)”,對非律師人員進(jìn)行了兩個方面的限制,一是不得使用律師名義,二是無論是否使用律師名義,不得開展有償訴訟、辯護(hù)業(yè)務(wù)。換言之,有償訴訟及辯護(hù)業(yè)務(wù)是中國律師法定的專屬領(lǐng)地,其他任何主體不得插手。有關(guān)訴訟法規(guī)定的非律師及辯護(hù)主體,如所謂“公民”等,只應(yīng)無償工作,而不得謀取經(jīng)濟(jì)利益。
三、中國律師業(yè)務(wù)領(lǐng)地被蠶食的現(xiàn)狀及分類
蠶食的中國律師業(yè)務(wù)領(lǐng)地主體和方法多種多樣,如前面提到的法律服務(wù)所、外國律師代表處、法律咨詢公司、企業(yè)內(nèi)部法律顧問、老法官協(xié)會、離職或在任的公檢法人員、無兼職律師身份的法學(xué)教研人員以外,“討債公司”、“私家偵探社”一類的主體也在悄然侵占律師的法律服務(wù)領(lǐng)地。按照蠶食方法的不同,可以粗分為體制性、違法性蠶食、腐敗性蠶食和法律漏洞性蠶食。現(xiàn)分別討論。
(一)體制性蠶食
最為典型的就是基層法律服務(wù)所和“基層法律服務(wù)工作者”(原來干脆就稱“法律工作者”,概念外延之廣,幾乎覆蓋了整個法律職業(yè))。從合法性來說,法律工作者并非律師,即便規(guī)規(guī)矩矩按有關(guān)規(guī)章或地方法規(guī)從事訴訟業(yè)務(wù),也存在一個“為牟取經(jīng)濟(jì)利益從事訴訟業(yè)務(wù)”、違反律師法第14條的違法性問題。
但是,由于司法部規(guī)章,如1987年的《關(guān)于鄉(xiāng)鎮(zhèn)法律服務(wù)所的暫行規(guī)定》(現(xiàn)已廢止)、2000年的《基層法律服務(wù)工作者管理辦法》以及基于這兩個規(guī)章演繹出來的眾多的地方法規(guī)或地方規(guī)章的庇護(hù),名義上除了刑事辯護(hù)以外,基層法律服務(wù)工作者幾乎就是“第二中國律師業(yè)”,形成了“按章合章”(而不是“依法合法”)執(zhí)業(yè)的制度;在“基層”的名義下,任何地方,包括上海、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基層法律服務(wù)工作者都可以唐而皇之地蠶食律師的業(yè)務(wù)。在合憲性司法審查制度缺乏且人大合憲性審查又蒼白無力的中國,政府部門的違憲造就了“基層法律服務(wù)工作者”這樣一支龐大的、有“執(zhí)照”的法律服務(wù)隊伍,律師法的禁止性規(guī)定時時刻刻在被違反、被架空。至于基層法律服務(wù)所實際執(zhí)業(yè)過程中超越規(guī)章的約束,從事刑事辯護(hù)業(yè)務(wù),那還是另外性質(zhì)的違法問題。
(二)違法性蠶食
如果說基層法律服務(wù)所違法從事有償業(yè)務(wù)還有規(guī)章及地方性法規(guī)作為擋箭牌的話,對律師業(yè)務(wù)的違法性蠶食就是公然的違法了。主要表現(xiàn)形式有以下幾種:
1、外國律師事務(wù)所中國代表處蠶食中國法律事務(wù)。按照2001年國務(wù)院《外國律師事務(wù)所駐華代表機(jī)構(gòu)管理條例》,外國律師事務(wù)所中國代表處不得從事中國法律事務(wù),不得解釋中國法律,也不得聘用中國執(zhí)業(yè)律師,所聘用的輔助人員不得為當(dāng)事人提供法律服務(wù)。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乎所有的外國律師事務(wù)所駐華代表機(jī)構(gòu)主要活動恰恰就是上述法規(guī)所禁止的行為!因為如果依法開展工作,幾乎所有的“代表處”都會付不起高檔寫字樓的房租而“關(guān)門大吉”。
作為一種直觀經(jīng)驗,筆者認(rèn)為,絕大多數(shù)外國律師對中國法律都是一知半解,甚至根本就在自以為是地充當(dāng)“假行家”,在厚厚的英文(其他文字的并不多見)文件下兜售的往往是按照其本國法律精神改造后的“中國法律”,其英文寫作水準(zhǔn)要遠(yuǎn)遠(yuǎn)高于中國法律水準(zhǔn),蒙蔽、誤導(dǎo)當(dāng)事人以及曲解中國法律現(xiàn)象非常嚴(yán)重。
例如,筆者受合資中方當(dāng)事人之托參與過的一件合資合同談判及訂立法律事務(wù),外方委托的是該國一家律師事務(wù)所上海代表處。事實表明,該代表處不僅一知半解地從事中國法律事務(wù),而且常常曲解中國法律,甚至告訴其當(dāng)事人“中國法律不當(dāng)真”。面對這種情況,筆者當(dāng)即指出的其無權(quán)解釋中國法律的規(guī)定以及其中國法律上的知識缺失,但該代表處的外國律師百般欺瞞其本國當(dāng)事人,造成的惡劣效果可以料想。另外的一個國際技術(shù)轉(zhuǎn)讓非訴案例中,對方聘請的美國律師提供的技術(shù)轉(zhuǎn)讓合同文本中充斥著我國法律所禁止的“限制性條款”,但對方律師似乎“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面對筆者的提醒,顯得十分茫然。筆者無奈,只好拿出國際經(jīng)濟(jì)法方面的法律資料供其“現(xiàn)場學(xué)習(xí)”(該律師倒也“謙虛”,經(jīng)現(xiàn)場閱讀中國法律相關(guān)規(guī)定后,取消了合同當(dāng)中的絕大多數(shù)限制性條款。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為對方當(dāng)事人化數(shù)萬美金聘請過來與中方談合資及技術(shù)轉(zhuǎn)讓合同的“律師”,從事的正是其無權(quán)從事、且并不熟悉的中國法律事務(wù))。
2、“討債公司”及“私家偵探”。由于司法體制、司法官員素質(zhì)等多方面的原因,司法解決糾紛、實現(xiàn)司法正義的程度與效率都難以令社會公眾滿意,“贏了官司輸了錢”、“法律白條”現(xiàn)象使得“討債公司”及“私家偵探”一類的機(jī)構(gòu)獲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間。本來這侵犯的似乎是國家公權(quán),與律師無涉。但是,律師訴訟業(yè)務(wù)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法院處理案件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當(dāng)事人對司法的信心,可以說律師與法官的應(yīng)然關(guān)系是“充分表達(dá)”與“公正判決、有效執(zhí)行”,或簡化成“表達(dá)與判斷”的關(guān)系,因為執(zhí)行是判斷的延續(xù)而已。如果判決不公、執(zhí)行不力,法院失去案件的同時也讓律師丟失了業(yè)務(wù),因為律師利用證據(jù),運用法律,充分表達(dá)當(dāng)事人對司法正義的訴求的行為,在法律體制外尋求“公正”的場所--“討債公司”及“私家偵探”面前,實在是沒有多少施展的余地的。所以,類似“討債公司”、“私家偵探”一類的機(jī)構(gòu)不僅侵犯了司法公權(quán),實際上也附帶掠奪了諸多潛在的律師業(yè)務(wù)。
3、企業(yè)內(nèi)部法務(wù)人員。姑且不談在正常的律師制度以外,通過部門規(guī)章另設(shè)一類法律職業(yè)人員這一制度設(shè)計的合理性,就是按照國家經(jīng)貿(mào)委《企業(yè)法律顧問管理辦法》規(guī)章的界定,“企業(yè)法律顧問,是指具有企業(yè)法律顧問執(zhí)業(yè)資格,由企業(yè)聘任并經(jīng)注冊機(jī)關(guān)注冊后從事企業(yè)法律事務(wù)工作的企業(yè)內(nèi)部專業(yè)人員”,企業(yè)法律顧問應(yīng)該是企業(yè)內(nèi)部人員而不是社會律師。然而,不少企業(yè)法律顧問考取律師資格證書或法律職業(yè)資格證書后,春光盡占,利用律師管理上的一些疏漏,充當(dāng)起“兩棲明星”來:一方面拿著企業(yè)工資,一方面又在律師事務(wù)所注冊,當(dāng)起律師來。如此對潛心從事律師業(yè)務(wù)的律師而言,自然形成業(yè)務(wù)上的擠壓和不公平競爭。
4、假律師、“黑律師”。名目張膽赤膊上陣假冒律師、騙取錢財?shù)目赡苓€是少數(shù),很容易被查處,實在不是“明智”的做法。律師法、甚至刑法的嚴(yán)厲制裁使得沒有任何“依靠”的假律師、“黑律師”變換花樣來蠶食律師業(yè)務(wù),例如,通過雇傭有證律師辦理并操縱律師事務(wù)所,充當(dāng)起“隱名合伙人”甚至“合伙人的老板”角色;充當(dāng)掮客或律師“業(yè)務(wù)合作伙伴”的角色與律師分享業(yè)務(wù);等等。有些往往也是“腐敗性蠶食”的根源。
5、其他。違法的表現(xiàn)形式永遠(yuǎn)多于法律規(guī)定。除此之外,“老法官協(xié)會”、退休公檢法人員、甚至“法學(xué)專家”一類的主體也會無視律師法關(guān)于非律師人員不得從事有償訴訟及辯護(hù)的規(guī)定,在“發(fā)揮余熱”或其他美妙的借口之下蠶食律師業(yè)務(wù)。不少腐敗性蠶食也源于此。
(三)腐敗性蠶食
這類蠶食當(dāng)然也屬于ldquo;違法性蠶食”的一種,只不過蠶食者往往直接或間接掌握著權(quán)力資源,如國有企業(yè)甚至黨政部門、司法部門的官員;或者可以溝通、“溝兌”權(quán)力,如退休政法官員。與單純的違法性所不同的是,蠶食律師業(yè)務(wù)領(lǐng)地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腐敗行為的發(fā)生。如某中級法院原經(jīng)濟(jì)庭法官姚某長期與律師“合伙”開展律師業(yè)務(wù),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為自己承辦案件的當(dāng)事人介紹律師,其實律師業(yè)務(wù)也有他的份,每年的“兼職律師收入”十分可觀。事情敗露后,干脆“提前退休”,公然充當(dāng)“律師”,生意還非常興隆;此外,黨政要員、司法官員幕后興辦律師事務(wù)所的現(xiàn)象并非絕無僅有。如此腐敗性蠶食不僅打壓了律師業(yè)務(wù)空間,還產(chǎn)生巨大腐敗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如利用其開辦、控制及操縱的律師事務(wù)所直接進(jìn)行貪污受賄,或為貪污受賄進(jìn)行洗錢等等。
更為嚴(yán)重的是,國家官員如公安(含海關(guān)緝私偵察部門)、檢察、法院這些政法官員“假退休”--通過“內(nèi)退”等方式,一方面國家官員身份、待遇照樣享受,另一方面“打擦邊球”(“內(nèi)退”好歹有個“退”字)、領(lǐng)取律師執(zhí)照從事律師業(yè)務(wù),如此具有“雙重身份”的“律師”出馬,其蠶食性腐敗程度往往要遠(yuǎn)遠(yuǎn)甚于公安(含海關(guān)緝私偵察部門)、檢察、法院真正退休人員的不當(dāng)律師業(yè)務(wù)行為。
(四)法律漏洞性蠶食
就是法律咨詢公司或其他法律咨詢服務(wù),如法學(xué)專家的法律咨詢服務(wù)。表面上看來,似乎“法無禁止即授權(quán)”,既然律師法沒有禁止法律咨詢業(yè)務(wù),那么,開設(shè)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的法律咨詢公司并無不妥。這里存在一個法律漏洞問題,即中國法律法規(guī)沒有嚴(yán)格禁止非律師從事法律咨詢、法律顧問及其他非訴訟法律事務(wù)。但是,應(yīng)該注意到的是,法律服務(wù)不同于一般服務(wù),實行執(zhí)業(yè)準(zhǔn)入與行政許可為絕大多數(shù)國家所采用的管理方法,也是國家法治及法制統(tǒng)一所需,任意可以開展非訴訟法律事務(wù)將使律師法第25條的絕大部分規(guī)定顯得毫無意義,破壞法律向現(xiàn)實的轉(zhuǎn)化。至于法學(xué)專家專為正在審理的案件“論證”,律師再拿此種論證意見書說服、借法學(xué)名人“打壓”司法官員,既作踐了律師(律師本來就是法律實踐方面的專家,如需要法理上的支持盡可援引已經(jīng)存在的觀點即可,私下就案件請教專家也無妨。但如讓當(dāng)事人再花錢召開“論證會”,恰恰說明律師對自己觀點的底氣不足),又作踐了法學(xué)專家(法學(xué)家是客觀研究法律的研究者,而并非披“專家”之外衣,當(dāng)律師之幫手,分、訴訟之份額,掠當(dāng)事人之費用,壞“司法獨立”之基礎(chǔ))。
筆者同時也注意到,不僅僅法律咨詢公司,就是一般的“經(jīng)濟(jì)咨詢公司”,居然也在訴訟案件,甚至到最高人民法院出庭。可見面對法律漏洞,有關(guān)行政部門如工商行政部門,不應(yīng)采取利用、擴(kuò)大的管理辦法,否則法律漏洞性蠶食將會越來越大。
四、對中國律師業(yè)務(wù)被蠶食的憂思
從歷史淵源來說,現(xiàn)代意義上的律師并非我國“古已有之”的國粹,而是西方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產(chǎn)物,對于我國而言,律師制度完全是“泊來品”,完全是法制近代化與現(xiàn)代化過程中移植過來的產(chǎn)物。無論是晚清的封建社會,民國時期的資產(chǎn)階級獨裁社會,還是改革開放前的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也許是經(jīng)濟(jì)制度、政治體制、社會基礎(chǔ)與文化觀念等方面的原因,我國社會天然缺乏對律師及律師制度的親和力,律師業(yè)得以植根成長的土壤難稱肥沃,西方有關(guān)律師應(yīng)有的法理地位與我國律師實有的現(xiàn)實地位形成強(qiáng)烈的反差,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甚至動蕩,在制度和理念上,我國律師似乎根基難定,身似浮萍,大有被邊緣化的危險。而業(yè)務(wù)空間的遭擠壓和業(yè)務(wù)份額的被蠶食,又加劇了這種邊緣化,使得律師業(yè)務(wù)不再專為律師所有,而是“人人得而食之”的“唐僧肉”。
《中國律師》主編劉桂明先生在論述中國律師業(yè)面臨的難題時指出,面隊人數(shù)眾多遍及城鄉(xiāng)的法律服務(wù)所和眼前境外律師機(jī)構(gòu)駐華辦事處的監(jiān)管不力問題,中國律師業(yè)的市場秩序“既要安內(nèi),又要攘外”;“業(yè)務(wù)開拓單靠政府推動,還有多大的潛力?而僅僅依靠個人,那又有多大空間和多少前途?這不能不讓我們居安思危,夜不能寐”,流露出強(qiáng)烈的憂患意識。的確,撇開其他的難題不談,就是僅僅從律師業(yè)務(wù)領(lǐng)地被體制性、違法性、腐敗性和法律漏洞性蠶食的現(xiàn)狀來看,反“蠶食”的“安內(nèi)”及“攘外”工作十分艱巨,中國律師業(yè)務(wù)發(fā)展空間與業(yè)務(wù)發(fā)展前景不容過分樂觀。
問題盡管復(fù)雜,甚至都可以用“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來”描述,例如解決基層法律服務(wù)所問題,如果一味關(guān)閉以適應(yīng)合法性要求,似乎一夜之間砸了那么多人的飯碗,同時讓經(jīng)濟(jì)落后地區(qū)的民眾得不到廉價的法律服務(wù),弄不好還會影響社會穩(wěn)定。但是,這種不是想辦法解決問題、而是想辦法不解決問題的思路不僅忽視了守舊的成本和改革的收益,而且也讓經(jīng)濟(jì)落后地區(qū)的廣大民眾永遠(yuǎn)得不到真正優(yōu)質(zhì)的法律服務(wù),并且不利于基層法律服務(wù)所提高自身素質(zhì),擺脫靠行政保護(hù)、掩飾其水平低下的宿命。
改變目前狀況的辦法不是沒有,至少說憂思之余解決問題的思路不是沒有。筆者認(rèn)為,在中國司法漸進(jìn)、成功進(jìn)行改革,實現(xiàn)司法權(quán)力配置科學(xué)化、司法體制獨立化、司法運行公正化、司法公正效率化、司法官員職業(yè)化等中國司法現(xiàn)代化目標(biāo)的前提下,通過行政規(guī)章、地方法規(guī)的合憲化從源頭上堵死法律執(zhí)業(yè)主體設(shè)置上的無序,通過法律服務(wù)準(zhǔn)入化禁止未經(jīng)法律許可的法律服務(wù),通過法律職業(yè)一元化消除體制性的業(yè)務(wù)蠶食,通過市場監(jiān)管的有效化來規(guī)范律師業(yè)務(wù)市場的秩序等方法,盡管比較“粗線條”,但可能會有助于中國律師業(yè)在拓展業(yè)務(wù)空間時必須實施的“反蠶食戰(zhàn)略”,消除中國律師業(yè)務(wù)發(fā)展遭受的各種蠶食,為中國律師業(yè)進(jìn)一步健康、長足的發(fā)展和中國社會的法治化打好扎實的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