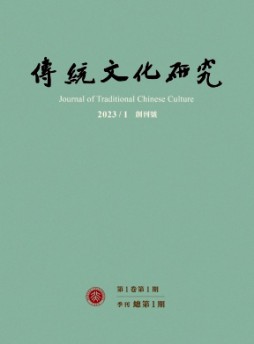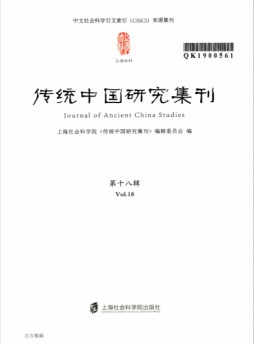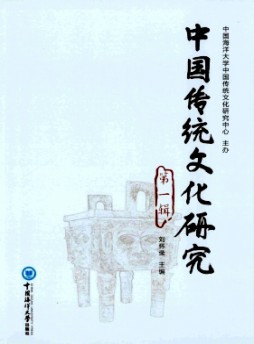傳統法學思維批判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傳統法學思維批判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法律的經濟分析》這部享譽世界的法律經濟學著作,將經濟學運用于許多非市場的行為,如,犯罪、起訴、離婚、意外事故、反種族歧視法等等,從而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全新的、廣闊的、全方位的視角。效益被看作是法律的基本價值,法律的效益價值理論和經濟分析方法是法學研究理論領域和方法論上的重大突破。本文試圖勾勒出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學的思想輪廓,并對社會現實作出適當的反思,以求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建設。
關鍵詞:法律經濟學,波斯納,經濟分析,效益
一、引言
經濟分析法學(economicanalysisoflaw)又稱為法律經濟學,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國興起的西方法學思潮之一。法律經濟學使法學的研究手段拓寬到經濟領域,使法學研究的視野不再局限于公平正義的權衡、選擇,從而為法學理念的重新定位開辟了一條法學與經濟結合的新徑。法律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首推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波斯納,他被譽為70年代以來最為杰出的法律經濟學家之一。其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法律的經濟分析》全面地闡述了他的學說,標志著一個新的法學流派-經濟分析法學派在學派林立的法學界已占據一席之地,為法學研究開辟了一塊嶄新的領地。
波斯納在第一版中文版作者序言中指出,《法律的經濟分析》旨在“將經濟理論運用于對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在第一篇導論中指出,《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的寫作是建立在經濟學是分析一系列法律問題的有力工具這一信念的基礎之上的。他認為,“經濟學是人類在一個資源有限、不敷需要的世界中進行選擇的科學”,將經濟學看成是一門關于我們這個世界的理性選擇的科學(thescienceofrationalchoice),即在這個世界,資源相對于人類欲望是有限的――資源具有稀缺性。它的假設是:人是對自己的生定目標,自己的滿足,也即我們通常所講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而“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這一概念暗示,人們會對激勵(incentive)作出反應,即,如果一個人的環境發生變化,而他通過改變其行為就能增加他的滿足,那他就會這樣去做。這就是法律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二、法律經濟學視角下的反思
(一)法律經濟學視野中的法律基本概念
波斯納認為,經濟學與法學這種學科兩分法將法學現象與經濟學現象之間事實上的距離人為地夸大了。他認為,經濟學對法律進行規范分析是一個有力的工具,在一個資源稀缺的世界,效率是一個公認的價值,表明一種行為比另一種更有效當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傳統的法學觀念與此相差甚遠。正是由于法律經濟學與傳統法學的分野,直接導致一系列由傳統道德背景下所構造的法律概念在法律經濟學的視角中發生變化、甚至沖突。因此,我們要了解法律經濟學,就不得不重新對一系列的法律概念進行認識,筆者試圖從經濟分析的角度,對“法律”和“權利”作出一些新的詮釋。
1.關于法律
中國傳統的法學理論一般從意識形態出發,都將法律定位為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但是在法律經濟學的視角中,法律沒有被披上太多的意識形態,而是更多地注重對社會的實際作用。因此在這里,法律表現出來的特征是實用性。在傳統的視角里面,法律都是處在消極的地位,一般都是進行事后的調整,缺乏前瞻性;法律的改變多是隨社會的變化而變化。法律經濟學卻認為,法律除了事后的調整外,更多的應該注重事前的預防。因為損失的發生在很多情況下是難以彌補的,例如在一宗交通事故中,行人被機動車(司機存在過錯)撞到而失去了一條手臂。交警當然會要求司機作出賠償,賠償,只是財富從司機一方轉移到行人一方,社會的總財富并沒有因此而改變。但是不管事后怎樣彌補,行人還是失去了一條手臂,社會總財富減少了,因為行人不能再創造比以前更加多的財富。法律的前瞻性在這里顯得非常必要。而法律經濟學借助經濟學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手段,尤其是采取經濟人假設和激勵機制,預測人們對一定法律環境的的反應,從而制定一些更加有利于增進社會財富的法律。另外,法律制度必須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科斯第一定理告訴我們:法定權利的最初分配從效率角度看是無關緊要的,只要交易成本為零;然而現實中,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是沒有的,這個現在誰都知道,科斯當然比我們知道的更早,于是在交易成本不為零的現實世界,人們又推導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情況下,權利的初始分配將影響資源的配置效率。法律制度本身的運行是需要成本的,因此良好的法律制度一方面有助于節約社會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交易費用的降低,交易效率會隨之提高,所以又會促進社會總財富的增加。法律一旦忽視交易成本的因素,則法律反而是阻礙社會進步的絆腳石。
2.關于權利
關于權利,傳統的法學理論習慣于從權利的靜態,至多是從它的排他性出發,認為權利與權利之間是可以劃清界限的,當嚴格依法界定并保護一個人的合法權利時,實際上也就界定和保護了他人的權利。然而,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寫道:“人們一般將該問題視為甲給乙造成損害,因而所要決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這是錯誤的。我們正在分析的問題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對乙的損害將會使甲遭受損害。必須決定的真正問題是,是允許甲損害乙,還是允許乙損害甲?關鍵在于避免較嚴重的損害。”科斯認為權利具有“相互性”(reciprocalnature),紛爭的產生源自社會資源的有限,問題不在誰對誰應付賠償責任或免除損害責任,而是如何減少損害,只有從雙方性的觀點去看損害賠償的問題,才能真正達到社會財富最大化的目的,社會資源才能獲得最有效率的運用。
(二)法律經濟學在我國實踐中的嘗試
1999年沈陽市頒布了《沈陽市行人與機動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該辦法的主要精神可以概括為:在行人違反交通規則導致交通事故發生時,如果機動車方無違章行為,行人負全部責任。長期以來,大部分地區交通管理部門在處理交通事故時實行的是“嚴格責任規則”而新辦法用“過失責任”代替了嚴格責任。此新辦法引起了法學界“撞了白撞”的大討論。然而反對的呼聲居多,如著名法學家梁慧星教授就認為該辦法是反人道、反正義、反人權的,更進一步指出在交通事故處理上應該適用無過錯責任。
這場大討論引發了筆者的思考,如何衡量一個具體法律法規的合理性?在筆者看來,對該新辦法的反對意見多是基于把法律看作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或更傳統地說是從“公平”的角度判斷法律的合理性。依該標準,平均而言,行人是“窮人”、“弱者”,而司機是“富人”、“強者”,因此,無論司機有無過錯均讓其承擔責任是合理的。然而,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證效率,考慮如何使整個社會的成本最小。衡量一個法律是否合理的首要標準應該是效率標準而非分配標準。分配原則應該在效率原則下,如果離開了效率標準,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打個比方,如果單從分配標準出發,窮人盜竊富人的資產就不應被判有罪,弱者傷害強者也不應構成侵權行為。如果我們的制度設計完全遵照此標準,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就會降低,也不會有人愿做“富人”、“強者”;相反,依效率標準,任何盜竊行為、傷害行為均構成侵權,則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就會提高而努力積累財富。
我們假設交通規則本身是社會最優的,即,在雙方都嚴格遵守該規則的情況下,事故發生的概率處于社會最優水平。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社會最優水平并不是指事故發生概率最小,而是對于整個社會來說,經濟效率達到最大同時事故發生概率達到最小的邊際狀態。在此前提下可以有三種情況:第一,實行“無責任規則”,即在任何情況下司機均不承擔賠償責任,結果是司機沒有預防事故發生的積極性從而不遵守交通規則,行人有最大的積極性預防事故發生而過于小心謹慎甚至綠燈時也不敢過馬路,激勵機制沒有最優地分配責任承擔關系,所以是沒有效率的,不能達到社會最優狀態。第二,實行“無過失責任”,即在任何情況下司機均要承擔賠償責任,則司機有預防事故發生的最大積極性而行人則選擇最小的謹慎(因在發生交通事故的情況下行人無論如何也要承擔一定的人身損失),因此司機開車過于謹慎而放慢速度導致交通堵塞,行人卻亂闖馬路,這也不能達到最優化的效率。第三個規則就是實行“過失責任”,即只有當司機違章行人沒有違章時才由司機承擔全部責任,而當行人違章司機沒有違章時司機不承擔責任。這樣司機和行人都有積極性遵守交通規則,事故發生概率達到最優(注意是最優而非最小),則社會的效率也達到最優狀態。一個好的交通事故損失賠償的法律規則,應當能夠產生一種激勵,在這樣的激勵下,道路交通的參與人自愿投入適當的預防成本,使交通事故不發生或少發生。故此,沈陽市出臺的新辦法看似在人權保護上是一種“倒退”,實則可最大限度地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符合法律經濟學關于侵權法目的的闡釋,即為了促進防止侵權行為資源的高效率配置。判斷法律法規的合理性以效率為標準往往能夠最大地節約社會成本,在這個資源有限的世界中,實現真正的分配正義。
(三)言論自由的經濟學分析
波斯納認為,思想是一種商品。在一個自由的思想市場里面,各種思想會相互充分競爭,希望能獲得消費者(社會大眾)的購買(接受)。在這里,波斯納將市場的概念引入到思想領域,這是筆者下面討論各問題的邏輯起點。
1.言論自由的憲法保護的必要性
憲法為什么明確保護這一特殊市場(思想市場)而非其他市場呢?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主要有下列兩個原因。第一,對思想市場的管制會造成政府權力壟斷。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官員是公共利益代表的這種理想化認識與現實相距甚遠,行使經濟選擇權的人并非“經濟閹人”。我們沒有理由將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神造物。政府同樣也有缺陷,會犯錯誤,也常常會不顧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團自身的私利。這就是說政府也是一個經濟人,會有其特定的偏好。如果允許政府對思想市場隨意加以管制,最終的結果就是使輿論成為了政府宣傳的工具。只要一出現令政府反感的言論,政府處于本能就會對其進行壓制,將其排擠在思想市場之外,社會大眾所得到的就只剩下一些為政府所喜愛的言論。第二,思想市場的脆弱性。思想市場上有不少思想收益是外部性的,只要政府對這些思想(不受政府歡迎的)提高其進入市場的成本,那么其他的思想就極其容易替代這些不受歡迎的思想。正如波斯納在書中所舉的例子,投票本身是一種外在收益源,因為單一的投票根本不可能改變選舉,所以其對個人投票者的預期價值(即使相對于很小的投票時間成本而言)是很小的。由于投票幾乎沒有私人價值,所以我們就不應該希望人們對了解候選人和有關問題進行大量的投資。憲政的本意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行政權力,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如果憲法不對言論自由作出堅實的保護的話,憲法就難以真正達到憲政的目的。
2.媒體責任的歸責原則
隱私權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在隱私權和言論自由權發生沖突的時候如何取舍呢?尤其是擔負著傳播各種信息的義務的大眾傳媒,在報道發生失實之時,其責任應該如何分擔呢?媒體,作為一個經濟人,也會對外界的激勵或抵制因素作出反應,而成本與收益效應對媒體的行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成本高于收益,那么媒體便不會報道這一消息;尤其是當報道的消息極有可能會引發訴訟而法律又傾向于保護對方的時候,媒體是更加不愿意冒這樣的風險。如果一個記者得到一則重要的內幕新聞而搶先獨家報道,他的報紙將取得較高的銷售收入。但這只是這一新聞對公眾所產生的價值的一部分,因為所有競爭性報紙都將在稍后刊載這一新聞。由此可見,這一記者和雇傭他的報紙的總收益會遠遠低于這則新聞的社會總收益。但是如果記者和雇傭他的報紙預期,這則新聞的公布,將會令其承擔訴訟的風險,他就不一定會公布這則新聞,即使這則新聞對社會公眾有很大的好處。獲得一部分收益,但是要承擔所有的風險,任何一個理性人都不會作出這樣的行為。鼓勵報紙公開這一則新聞的一種方法就是降低公開成本;而其手段就是使報紙沒必要對新聞的真實性作全面、徹底的調查,但在它對公開假誹謗負有嚴格責任或過失責任的情況下,它就不得不做這種調查。因此在沒有證明媒體知道消息的虛假性或放任對其真實性不作辨別的情況下,媒體不應當負相應的責任。
3.言論自由的底線
可能是因為歷史的慣性,中國人對“言論”這個詞顯得特別敏感。因而對于言論自由的內涵和外延并不會太關注,對言論自由的限度更加沒有一個清晰的標準。古語云:“刑之不知,威不可測。”正是人們不知道言論自由的底線在哪里,所以人們在發表言論時,尤其是政治言論,顯得非常謹慎。就如我們在聽一些思想活躍的學者做講座時,講完某個尖銳的問題時,總會加上一句“純屬學術討論”之類的不痛不癢的話。一個教授尚且如此,一般的社會大眾又會如何呢?這就反映出言論自由在現實中并沒有得到切實的保障,而要真正保障言論自由,筆者認為,言論自由的限度必須要劃分明確,否則,言論自由只是空話。
法律經濟學為這一標準的劃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這里我們要引入一條有用的公式:漢德的過失公式B<PL.漢德公式是在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訴卡羅爾拖輪公司一案中由法官漢德(LearnedHand)提出的.B<PL(B表示預防成本,P表示損失概率,L表示損失金額),即只有在潛在的致害者預防未來事故的成本小于預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預期事故損失時,他才負過失侵權責任。也就是說,預防成本超過事故成本時,致害者就不承擔過失侵權責任。而在這里,漢德公式的意義是:B為政府干預行為所造成的思想減少的成本,P為講話人所慫恿的犯罪行為實現的幾率,L為犯罪行為確實實施后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如果B低于PL,那么政府對講話人所采取的干預措施就是有效的,講話人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然而,這只是靜態的分析,并沒有考慮到將來的風險。如果想客觀地評價講話人的講話是否應該為政府所壓制,即政府是否有正當理由對言論采取措施,我們不得不引用另外一個公式,即丹尼斯公式。如果i是未來危害現值的貼現率,n是危害發生距今的年數,那么B<PL就變成了B<P?L/(1+i)n.貼現率越高,危害就越遠,公式右邊的數字越小,壓制的理由就越小。這個公式表明,不是任何有害的、具有煽動性的言論都應該受到壓制。因為言論所造成的損失,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如言論本身的惡性程度,發表言論的時間和場合,言論的煽動效果等。例如同樣是散播暴動言論,如果在公開場合和在私人場所是完全不一樣的,因此我們必須要加以區別。只有充分考慮到這些情況,才能明確言論自由的底線。
三、結語
作為新興的法學理論,波斯納的經濟分析法學雖有其學說固有的缺陷,然而不能掩蓋該學說的積極因素。其強調從資源、效用、效率等經濟觀點分析法律,彌補了傳統上只片面關注生產關系與法律的關系的局限。同時,該學說以定量分析為方法補充了習慣上的定性分析的不足,對某些特殊的法律部門和制度(如合同法、公司法等)的經濟分析極具參考價值,為法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尤其在當今中國的大背景之下,“效率”仍然是主旋律,減少法律制度運行中產生的成本(浪費)和最大限度增加社會財富同樣重要。因此,將經濟因素作為重要的因素考慮到法律制度中,是勢在必行的。
注釋:
1、沈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P353。
2、王成著《侵權損害賠償的經濟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P24。
3、王文宇著《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P15。
4、王成著《侵權損害賠償的經濟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P12。
5、理查德·A·波斯納(RichardA.Posner)著《法律的經濟分析》蔣兆康譯林毅夫中文版譯者序言2000ChinaYouthReadingsNet.
參考文獻:
1、德·A·波斯納(RichardA.Posner)著《法律的經濟分析》蔣兆康譯林毅夫中文版譯者序言2000ChinaYouthReadingsNet.
2、沈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3、王成著《侵權損害賠償的經濟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王文宇著《民商法理論與經濟分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5、時顯群著《波斯納法律經濟學探究》原載于《云南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6、王哲郭義貴著《效益與公平之間-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學思想分析》原載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第3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