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法律論證的效力來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析法律論證的效力來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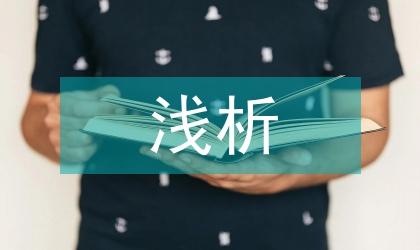
可以從司法判決的思維過程中來發現效力論的依據,實質上,我們清晰地知道演繹性證明是做出法律判決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法律論證方式。但是現在,可以把問題轉向,什么使得演繹性證明成為可能這一問題上。或者用凱爾森的話說,在具體的案件中,當需要演繹性證明來論證結論時,這種論證賴以存在的前提是什么?這樣的問題看似簡單,實質上意義重大。法官在審理案件時,發現案件事實與法律事實恰合,就邏輯推導出相應的法律結論。所以,實際上我們都不由自主地預想或者假定,每一個法官的職責就是適用法律。這種看法是從司法的功能或者法官的工作性質角度來說的。這種描述又引出一個相對次要的假設,這個假設是,法官一定能辨別出所有的規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然有一些既定的法治標準要求遵守。到了這里,可以看到筆者所要論述的主題核心所在,法律實證主義法律理論的中心原則,也是許多自熱法學派學者所堅持的,每一個法律制度都是由可憑借通常的承認標準加以辨別的一系列規則構成的,至少,法律制度中有一部分規則是這樣的。①至于承認標準是由什么構成的,主要依賴于那個法律體系的法官們接受什么標準,他們的責任就是通過這些標準去適用辨認出的規則。哈特②和約瑟夫•拉茲③都曾經提出過這一理論。但是,麥考密克明顯的注意到這一理論中存在循環論證的嫌隙。他提出,如果這個時候,我們提問“:在現在的英格蘭、蘇格蘭或者威爾士這些地方的法官是誰?”我們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套復雜的,哈特稱之為“裁判規則”的規范體系,例如《蘇格蘭最高民事法院法》或者《最高法院司法條例》等。法官之所以是法官,乃是因為法律規范授權他們成為法官,而那些使他們成為法官的規則以及其他一些規則之所以成為法律,乃是因為法官們承認他們是法律。這種論證是不折不扣的循環論證。法官并非像他們自己所說的那樣是由法律授權的自足機構,他們是由一個廣大的社區通過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在這個社區內,法院作為對立性利益的仲裁者,強化著自身的正統性和權威性。法院發出的指令之所以能夠得到執行,首先依賴的是接受指令者對法院權威的認同,其次,依賴的是掌握某種程度的集體性強制力量的官員們對司法權威的認同,后者一般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較晚階段逐步形成的。最終,麥考密克認為,賦予法院正統性和權威性的那個大社區不必然是某個整齊劃一的“國王共同體”。這個大社區也許并不比由那些權力集團或者強大的統治階級掌控下的區域更大,在那些有權力集團統治的區域,統治者可以通過控制暴力和散布恐怖等方式,在他們劃定的整個王國共同體內維持足夠的秩序。當爭議無法在人們之間自行解決或者經由他們的朋友解決時,必然需要法官而且法官必須承載一種為社會所承認的職能。④而這一職能依賴于古老傳統中傳承下來的平等和公道觀念,而不是求助于這樣那樣的“規則”。這樣一來,必將存在一些社會性的公認的裁判標準,且只有當那些被稱為法官的人們也認為法典規則由他們以命令的形式推行時,這些社會性的標準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另外,至少要在那些邊緣性的案件中,法官必須對裁判標準的精確含義作出說明。
現代法治體系中,我們法院里的法官其無可推卸的責任是在所經手的案件裁判中適用相關和恰當的法律規范。這已經成為一項規范。實際上,他是我們社會絕大多數人意志的體現。這種對法官權威的共同認同,確立和維系著法官的正當性和權威性,當他們依照職權發出命令時,該命令必須得到遵守,必要的時候可以強制執行。任命法官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他在履行司法職責時必須適用在法律上有效的規則,這表明了審判活動與立法活動的關系———因為立法活動是制定有效法律規范最為典型的程序。立法機關通過制度性規則建立機構并確認其成員的資格,還要根據權威性規則授予他們立法的權力,通過實施正式確立的程序規則,立法機構能夠使之成為有效的法律規則。⑤這樣司法機構和立法機構之間的核心關系就是,后者決定前者所負義務的內容,而前者在履行那一義務時也不得不劃定后者權能的范圍。而且,由此,也得以證立立法是法律的唯一源泉,而立法權和立法程序是有章可循的,如此一來筆者便得出了有效性的精確標準,也使有效的法律與非正當成立的法律區分開來。麥考密克將立法活動視為制定有效法律規則的最為典型的程序的態度,乃是不折不扣的現代觀點。但是緊接著,麥考密克又分析了詹姆士•斯戴爾爵士和十八世紀中葉的蘇格蘭的埃爾斯金和英格蘭的布萊克斯通的關于理性立法至上的態度,⑥也分析了約翰•奧斯汀有條件的實證主義和邊沁的徹底實證主義與約翰•埃爾斯金在《原則與制度》一書中的所秉持的自然法古老的理性理念的重合之處。⑦最終麥考密克得出了哲學上的轉向同時帶動分析了政治學轉向,理論層面的變化,也意味著必須要對法律之淵源進行重新闡述。如果所有的法律都是立法的產物,那么判例法也是立法的產物,法官就是它的立法者。邊沁和奧斯汀在這一問題上立場鮮明,與埃爾斯金態度相左,后者否定了特定先例的拘束力,布萊克斯通在這一問題上則模棱兩可。⑧麥考密克進一步論證了先例的法律拘束力淵源,他認為正如實證主義者所評價的那樣,運用先例越來越被認為是一種委任立法,判決理由受到挑戰,習慣法開始隱退讓位于私人契約,衡平法成為司法造法的代名詞。但是實質上,它們只是一些實質合理的規則,并且是基于作者個人的認識提出的。
哈貝馬斯在闡述效力的前提時,首先對法律的本源進行了洗禮,他認為法律本身是一個身兼二職的東西,它既是知識系統,又是行動系統;它不僅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規范語句和規范詮釋的文本,也可以被理解為建制,也就是一套行動規則。這樣的法律系統取消了法權人作為法律之承受者角色的確定判斷合法和不合法的權能。根據商談的過程,只要那些可能得到一切潛在的相關者同意的規范,才是可以主張有效性的。因此,在確保立法的程序正當外,我們所追求的政治權利必須以這樣一種方式來確保參與一切同立法有關的協商過程和決策過程,即使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行使對具有可批判性的有效性主張表示態度的交往自由。政治運用交往自由之獲得平等的法律保障,要求建立一種使商談原則得以運用的形成意見和意志的政治過程。⑨這樣一來,哈貝馬斯將效力論的前提歸納為行使政治權利程序的自由平等原則。它是與自然主義的去權威性不相同的。權力體系以平衡的方式確保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因此將事實性和有效性之間的張力變得可操作化。法律思維必須認識到事實性與規范性之間的鴻溝,而這樣的鴻溝在法律形式與商談原則的相互滲透中,得以化約。麥考密克所提出的將有效性留給立法者的主張,實質上也在商談論的程序中得以實現。因為商談的過程就使法律規則面對法律的承受者和法律的制定者。哈貝馬斯認為,法律的效力前提與合法律性是一個悖論,如果在這樣的前提下論證,我們只能把法律系統想象為一種回溯性地返回自身并賦予自身合法性的循環過程。人民自發性的政治熱情并不是要靠法律來強制的,這樣的自由意志來源于民眾對自由的主動性尋求,并在一個自由的政治文化的聯合體中得以維持和發展。⑩立法的合法化負擔不僅在于公民資格與商談性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的法律上建制化的程序。權利的合法化和立法過程的合法化是兩回事,一種統治秩序的合法化和政治統治之實施的合法化也是兩回事。法律與政治之間是一種構成性的關系,這種內在聯系具體而言就是,基本權利預設了一個制裁權威,一種為獲得對法律規范之尊重而運用合法暴力手段的組織所具有的制裁權威。國家作為制裁權威、組織權威和執行權威是必要的,是因為法律必須被實施,法律共同體不僅需要穩定認同的力量而且需要一個有組織的司法,因為政治的意志形成過程產生出一些必須被執行的綱領。這些不僅僅是對于權利體系的功能性補充,而且也是主觀權利之中包含的客觀法。以國家方式阻止起來的權力并不是從外部呈現在法律之下的,而是由法律預設的,以法律的形式建立的。所以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法律的效力性來源于程序性的民主商談。
最后,麥考密克得出了效力論的最終結論,在實證主義和自然法思想之間存在著一個相同的地方,即法律制度的形成是由一個共同的標準,這個標準即社會的認可,只要某個規則符合這個標準,這個標準它們作為該制度的有效規則的存在就是充分的,就是有效力的。哈貝馬斯進一步將權威寓于立法過程的商談,將法律規范的效力性前提證立為商談主體間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協商一致。法律與權力本是同源的理論徹底打破了事實性與規范性之間的鴻溝,也使效力論的前提得以證立。(本文作者:張蕾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