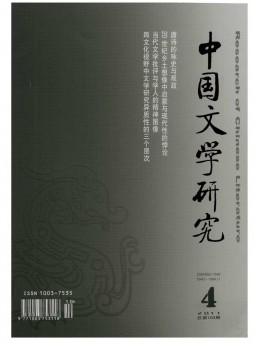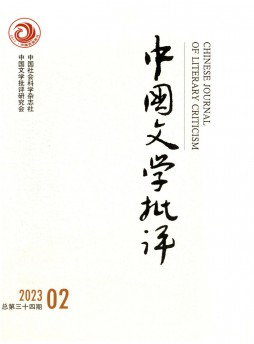中國文學趣味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文學趣味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文學趣味是審美主體在文學審美活動中的審美傾向性,對某些審美對象或對象的某些方面的特有的喜好和偏愛。”審美主體的生活經歷和文化修養不同,生理氣質和性格愛好的差異,使得人們對于文學作品的欣賞必然各有所偏好,不可能等同劃一。”對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之類鴻篇巨著的欣賞,對短小凝煉的作品如泰戈爾的《飛鳥集》等抒情詩的欣賞;還有其他不同類別的作品,欣賞者眼光都是不同的。審美趣味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漸進產生的,是人通過社會實踐產生的一種審美能力。年齡較大的人,受傳統教育較深,他們長期受古詩詞的熏陶,必然更喜歡格律詩、古典戲曲,他們覺得這類作品的韻昧悠長,意境深遠,正是悠長深遠的文學趣味。年紀較輕的人則對此類作品沒有那么感興趣,他們更多地接觸了西方文學,對現代主義的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認為意識流小說,荒誕派戲劇、朦朧詩才夠味,才能傳達他們的心聲,青年一代對文學趣味的發掘是與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產生的現代意識相聯系的。在廣大的讀者群中,盡管人們趣味各異,但是一個時代的文學欣賞和審美趣味還是可以被引導改變。文學評論家不停留在個人的興趣愛好上,將自己的審美趣味摒除,對審美客體進行公正的判斷,以引導廣大讀者進入更高的審美層次,獲得更多的高雅趣味為責任。因此,文學的審美趣味在引導下也具有一定的傾向性。區別于一般讀者的評論家們,必須在對作家及其作品充分理解的基礎上,以自己的審美理想來解釋作品,使作品獲得升華,使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涌現出來的一些非自覺的東西變成自覺的東西,即原來作家未意識到或未充分意識到的東西上升為自覺的充分意識到的東西,這時評論家完成了藝術再創造的任務,也將趣味深入發掘出來,滲入欣賞者心中。對于唐代詩人杜牧《江南春》一詩的欣賞,歷代詩評家褒貶不一。近代詩評家認為這首詩是詩人運用典型化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山重水復、柳暗花明、色調錯綜、層次豐富。認為前兩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寫了江南春明媚的一面,后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詩人特意把金碧輝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掩映于迷蒙的煙雨之中,這就增加了一種朦朧迷離的色彩,這樣明朗與朦朧相映襯,就使得這幅“江南春”圖畫更美麗、更富有層次了。一般讀者欣賞到此,一般的審美趣味似乎已經把握在手了,而精心的詩評家們卻別開生面,以自己審美理想的光束照射這首絕句,發現了詩的異彩。認為后兩句是對南朝統治者一面向人民無窮榨取、一面瘋狂佞佛的冷嘲,問“至今還剩下多少掩映于煙雨之中?”又說:“歷朝的封建統治者都逃不了覆亡的命運;然而,千里鶯啼,紅綠相映,江山依舊健在。水村山郭,酒旗搖風,人民也依舊頑強地生活下去。詩題叫作《江南春絕句》,也值得我們尋味。”[1]這就是升華的結晶:江南春的“春”真正內涵是:江山永在,人民永在,反動統治者必朽!這種理解中透露出欣賞者的信念和追求,實際上是欣賞者的理想信念在詩中找到了回響,于是欣賞者就借詩發揮了。這就是評論家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礎上,再把自己的獨特的審美理想投放到作品中去,從而使作品的境界獲得升華,發掘出一些作家本人未必自覺意識到的審美趣味,這正是評論家對趣味引導的責任所在。引導者用自己的審美理想照亮作品,升華作品;在審美過程中不斷地對自己的審美理想進行反思,并把新獲得的更高層次的審美理想投放到已有的審美理想中去,使自己的審美理想得到新的組合和升華。引導者在對一般趣味的理解不滿足中不斷地進行調整、組合、升華,才會使自己的審美理想不斷地飛升,越來越接近于藝術的圣境,才能讓讀者群接受趣味的異彩,獲得趣味的理想境界。
一、自然之趣的再現
趣味是藝術的本質和作用[2],是藝術的靈魂。梁啟超曾經說,文學、音樂和美術是專門從事磨礪感覺器官以誘發趣味機緣、增強生命趣味的三種利器。又將審美趣味產生的源泉歸結為三派,其中一派就是描寫自然之美。自然之趣的發微正是源于藝術的本質與作用。藝術因最能導人游于理想而予人趣味,對日常內在心理和微妙情感生動的表現是藝術給我們自然趣味的深刻根源之一。日常習見的事,現實生活中體驗的喜、怒、哀、樂等心態,活躍在紙上,惟妙惟肖,撥動讀者的心弦,使讀者把心的微妙之門打開獲得愉快。這其實就是由情感宣泄、心理共鳴而引發的暢快,稱之為“心態之抽出與印契”。對現在環境不滿,是人類普遍心理。肉體上的生活即使被現實環境所捆綁,精神卻渴望超越現實界闖入理想界以享受自由的快樂。“超越現實界,闖入理想界去,便是那人的自由天地。我們欲求趣味,這又是一條路。”[3]藝術中有不寫現實而純憑理想構造的,而且藝術所構的理想境界形形色色、優美高尚、富有魔力,能引導讀者跟著它闖進一個超越的自由天地。另外藝術給人以再現自然的趣味。欣賞自然之美,領略出水流花放、云卷月明等美境,就“可以把一天的疲勞忽然恢復,把多少時的煩惱丟在九霄云外”。若把美境印在腦里頭,令它不時復現,也同樣令人心爽神暢,這種“對境之賞會與復現”,是藝術喚起人自然之趣、世界賦予人類自然之趣的一種重要方式。[4]人與自然之間有著近似本能的情感關系,這種本源性的和諧使得人與自然之間有著天然的親近關系,在自然中感到歡欣舒暢。人類不管從事哪種卑下的職業,身處于多畝煩勞的境界,總有機會和自然之美相接觸。這就是說,我們不必整天閑游于山水名勝,為與自然接觸做專程的旅游觀光,就在奔波忙碌的日常生活行程中,隨時都可能得著親近自然的機會,而對自然之趣的欣賞,文學便是一種很好的媒介。只要心存天然之趣,善于隨處撿拾自然之趣,逢春便是春。梁啟超對于自然之趣的捕捉尤為突出。他在氣勢雄壯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在“戊戌政變”后逃往日本的太平洋途中,情激昂、神飛揚,樂觀精進地欣賞著“海云極目何茫茫”、“大風泱泱,大潮滂滂”的太平洋壯景。在為發起倒袁運動而匿蹤南下的冒險途中,梁啟超竟將偷渡當作清游,在《從軍日記》中寫道:“余起,張目推篷,喜欲起舞。境之幽奇,蓋我生所未見也。”一戰后赴歐考察航海南洋時,梁啟超更是隨時享受著與自然富有靈性的親和交融,“在舟中日日和那無限的空際相對,幾片白云,自由舒卷,找不出他的來由和去處。晚上滿天的星,在極靜的境界里頭,兀自不歇的閃動。天風海濤,奏那微妙的音樂,侑我清睡。”[5]文學自然之趣是在文學審美活動中敏銳觀察體驗,發自于本心的對自然的熱愛。抓住俗務奔趨中遭遇幽奇山水的時空境遇,在辛苦勞頓中也能隨時隨地享受人生佳趣。既不是不得志時的寄情山水,也不是不問世事的高蹈世外,而是出于他對人生遭際的事物、對人生到場之事物濃厚的興趣,出于隨處俯拾生命佳趣的天真爛漫情懷,出于對自然萬象的生動性、豐富性、淳樸性的天然喜愛。自然之趣的趣味論張揚的藝術人生并不表現為對現實和功利的純粹超越和解脫,而恰恰是對生活的熱情投入、對生活的迷戀和擁抱。自然無所為的生活狀態是為了更自由更愉悅更有興趣地去從事必然內含功利性的生存活動,從而進入自由創進因而活出樂趣的樂生境界。在文學活動的審美中,趣味既出乎其外又入乎其中,既空靈且充實的和諧生活,才是真正現實的自然之趣。
二、高雅情趣的提升
趣味是生活的原動力,“又有高等和下等趣味的分別”。[6]所謂高等趣味就是審美趣味。文學藝術的本質作用就在于以審美趣味來恢復人的審美本能,以維持和增進人的生活健康。從藝術表現上看,重視文學的藝術性,文學作品才能給人以高雅的審美情趣。高雅情趣的提升在文學作品中尤其體現在戲劇文學的藝術表現上。在各種藝術里,一部作品由受歡迎以至被遺棄,其變遷之急劇,恐怕也沒有甚于戲劇的。戲劇作品憑借著某一時期技術性的發展給觀眾以遞進的時代刺激和快感,作品主題不夠深刻也會經不起時間的淘汰。要使一部戲歷久不衰,那就“必須使作品先成為文學”,歸根到底,戲劇的文學性是重中之重。看好的劇本在舞臺上作有效的表演,那才是最理想的事。“劇本的寫作是創造,演員的藝術是再創造”。高雅情趣的不斷提升就要在這一創造的過程中完成。要培養高尚的趣味,發揮善的美的情趣,壓伏、淘汰和鏟除低級的、丑惡的情趣,推動人類的進步,趣味教育最好的工具就是藝術。早期新月派熱衷于文藝美的探討和交流,梁實秋認為“戲劇藝術是最高的藝術”,鑒賞戲劇“需要有極深的想象力”。他對“劇本第一”的堅持,實際上就是對戲劇文學藝術性第一的堅持。深邃的理解人生,通過對文學作品藝術性的宣揚,表達了高雅的審美情趣。劇場的舞臺藝術與題材結構的文本藝術,兩者絕不能混為一談。古希臘戲劇之所以取得成就,原因之一在于觀眾品位高,歌德戲劇作品排演的失敗,是因為沒有合適的觀眾。一部偉大的作品并不是只供少數人鑒賞,應該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供大多數人提升高雅趣味的目的。戲劇作為詩化的藝術形式,前途的關鍵在詩人的掌握里,也在觀眾的理解里。“我們不必著急、不必心焦,只需靜心的等著,好像漫漫的長夜里我們等著天明一般的等著真正戲劇詩人的出現”,在文學審美的過程中,期待觀眾高雅趣味的提升。高雅情趣并不是和高高在上、奢侈享樂、脫離社會實際等形象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高雅的情趣在左翼文藝中被泛化為貴族化的審美傾向,一直是詬誣的重點,無論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魯迅,還是建國后的無產階級文學,由于階級觀念的過分強調,貴族化的審美傾向長期以來成為我們唾棄的對象。而對于高雅審美趣味的積極意義,我們的認識顯然不夠充分。這種追求高雅的審美情趣、講求內容充實、格調清新的藝術化的超越性美學精神,是克服非文學化傾向的關鍵因素,不僅對左翼文學創作中的簡單化、模式化是一種有力的反駁,而且有效地抵制了文學的庸俗化和粗鄙化。文學的貴族化標榜文學藝術的純正性和藝術性,從發展的角度來看,貴族化不是一個與平民化相對立的概念,而是是一種自覺的、反映社會的高雅審美趣味的美學追求,是多種文藝美學中的一種審美意識形態。對審美意識中高雅趣味的認同,必然將對整個社會文化品味的提高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這也正是以戲劇文學為例探討高雅趣味審美傾向的最終目的。
三、悲趣傳統的形成
悲觀主義思想觀念在傳統文化中有著悠久的歷史。莊子對人生如夢的感嘆,對不合理現實社會的厭棄與退避早已成為傳統詩文吟詠的主題。在中國的傳統哲學中,莊子的悲觀主義哲學對現實人生、對人的生存境遇有著深刻的悲劇意識。“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知北游》),充溢著對生命的偶然性、有限性以及人生終日勞苦而意義何在的悲哀與困惑。在《德充符》、《人間世》、《知北游》中更有對人類生存境遇的悲劇性的覺悟“人之生也,與憂懼生”。他竭力用齊萬物、一死生的“天人合一”觀念來彌合這種深沉的悲劇感,用“心齋”“坐忘”實現對人生悲劇現實的審美超越,金圣嘆的以審美求解脫思想可以說正是莊子以“忘”為標志的審美超越精神在戲曲批評領域內的回應與承續。佛家的色空觀進入文藝領域后在客觀上對寫實的創作精神起到了推動作用,彌補了莊子的“忘”對人生悲劇現實的回避。無論是肯定欲望亦或是放縱欲望以達到對世俗禮教的反抗,為文人帶來的均是無法排解的痛苦。因此,欲望、痛苦與解脫逐漸成為文藝審美觀照的對象,人生境遇、生命本質等人生根本問題也日益成為文人思索的時代問題。悲觀主義審美趣味在中國文學領域內的形成是時代社會政治與各個時代文藝思潮共同作用的一個過程,在戲曲領域中以悲為趣的傳統是中國文學以悲為趣傳統的縮照。“先秦悲哀原則,類比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悲劇詩學。兩者都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紀左右。”[7]悲樂并傳也像《淮南鴻烈》、《聲無哀樂論》這些相關的美學著作所論,可以看作是在音樂客體本身不變的情況下,由欣賞主體自身的情感波動來比附或想象客體的相應存在狀態。元代曲學家周德清《中原音韻》中,對十七宮調中與悲怨有關的調性也作了論列:“南呂宮感嘆傷悲正宮惆悵雄壯”“,商角悲傷宛轉商調凄愴怨慕”,“角調嗚咽悠揚宮調典雅沉重”等,從音韻上對悲進行了明確的總結。作為基本存在方式,悲哀原則以時間、空間和一定的度量,形成悲而有時、有地和有節的外部規定性。其內在根源乃是主體人格情感三大依據,即由人生的悲哀導致惻隱之心的形成,由道德的悲哀導致是非羞惡感的形成,由理想的悲哀導致浩然之氣的養護。[8]明代后期社會的黑暗與動蕩現實對文人生存境遇以及文化心理帶來了巨大威脅與悲觀幻滅感,益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悲苦的情緒在文藝領域內蔓延,個性解放和獨抒性靈造就了中晚明文人的狂狷與放蕩。人們在關注人尤其是個體的生存境遇的同時,也感受到了與傳統、世俗的激烈對抗所造成的心靈分裂與痛苦。這種痛苦在戲曲創作中的表現,自湯顯祖開始至清初南北孔創作中悲觀主義傾向的日趨增強,而詩文領域內,從公安派提倡性靈到竟陵派漸漸轉向蒼涼、孤峭的藝術風格同樣體現出悲觀主義人生觀的滲透并漸占主流的發展趨勢。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與文藝思潮的浸染下,悲觀主義向戲曲批評領域內滲透也就不足為奇了。悲劇中審美快感的獲得,并非單純因為善惡有報的因果論,以悲為趣還在于悲劇角色的相互轉換。廣為人知的戲曲人物陳世美就是一個真正的悲劇角色,無論是從人生痛苦本質的認識上,還是對人的欲望與解脫的關注上,其高中狀元到最終徹底的追悔,個人結局的轉換,“終身之咎,真是古寺晨鐘,發人深省。”
傳統的文藝批評主要集中在作品的風教、載道等社會政治功用方面,即使追求純粹審美境界的意境論等也往往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了物我合一,神與境合等情景關系上。中國的文藝創作觀念繼承了審美超越等觀念。悲劇在從人本出發,通過文藝來對人生本質和存在價值的探尋中,追問人生痛苦的根源。可以說,沒有這種悲觀主義審美趣味對戲曲批評的介入,對中國文學的介入,就沒有悲觀哲學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融入。古典悲劇思想的形成和古代悲劇性文學杰作的誕生都將是難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