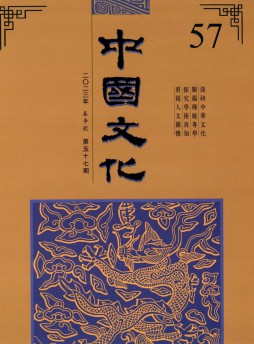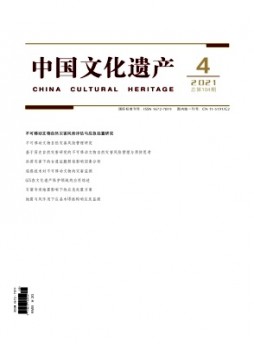中國(guó)文化女權(quán)主義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中國(guó)文化女權(quán)主義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馬克辛•洪•金斯頓(MarineHongKinston)(又名湯亭亭)出生于1940年,是美國(guó)第二代著名華裔女作家。1976年她的處女作《女勇士)(TheWomanWarrior)一經(jīng)發(fā)表,立刻好評(píng)如潮,在評(píng)論界和讀者中引起強(qiáng)烈的反響,并獲全美圖書(shū)評(píng)論界qE/J,說(shuō)類獎(jiǎng)。她本人則榮膺美國(guó)克林頓總統(tǒng)夫婦頒發(fā)的1997年“國(guó)家人文獎(jiǎng)”。此項(xiàng)大獎(jiǎng)僅授予10人,金斯頓是惟一的獲獎(jiǎng)亞裔。在《女勇士:}中,金斯頓毫無(wú)拘束地運(yùn)用現(xiàn)實(shí)與想象、事實(shí)與虛構(gòu)相互糅合的第一人稱敘事手法,向讀者展示了一個(gè)具有兩種文化背景,受到兩種民族精神影響的小女孩的成長(zhǎng)與反思。<女勇士》是本世紀(jì)六、七十年代美國(guó)民權(quán)和女權(quán)運(yùn)動(dòng)發(fā)展的產(chǎn)物,帶有強(qiáng)烈的個(gè)人色彩,它試圖驅(qū)除困擾作者本人乃至所有美籍華人和其他婦女的一些人為的鬼魂。小說(shuō)在讀者中備受青睞,很大程度源于書(shū)中所展現(xiàn)的神秘而新奇的中國(guó)文化,這與美國(guó)讀者眼中的“他者”形象一致。實(shí)際上,任何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有一點(diǎn)點(diǎn)常識(shí)的人都會(huì)輕易地在這部作品中發(fā)現(xiàn)與傳統(tǒng)文化版本完全不同甚至相左的“文化片段”。另一位美國(guó)華裔著名作家趙健秀就曾毫不客氣地公開(kāi)指責(zé)金斯頓、譚恩美等華裔女性作家的小說(shuō)完全是為了迎合白人社會(huì)而把華裔男性塑造成厭女主義者的滯定性形象,他說(shuō):“這些作品中所描述的中國(guó)和美國(guó)華裔完全是白人種族主義者想象的產(chǎn)物,它們都不是事實(shí),不是中國(guó)文化,更不是中國(guó)或美國(guó)華裔的文化傳統(tǒng)。”然而事實(shí)上,金斯頓本人卻非常美國(guó)化,她一再辯稱自己是“華裔美國(guó)人”(ChineseAmeri-c明),而非“美籍中國(guó)人”(AmericanChinese),并對(duì)一切中國(guó)事物持公開(kāi)批判的態(tài)度:“我真不明白他們是怎么將傳統(tǒng)文化延續(xù)了五千年的,也許他們根本沒(méi)有繼承,只是各個(gè)時(shí)代的人編造的罷了。”…㈣跏所以盡管金斯頓在書(shū)中運(yùn)用了大量的中國(guó)傳說(shuō)和歷史故事,但她并非意在“文化”本身,如她本人所說(shuō):“我是在寫(xiě)美國(guó)……關(guān)于中國(guó)的部分,只是為了寫(xiě)我的華裔移民前輩而提供的一個(gè)背景而已。”【2】‘n∞’那么這些“支離破碎”的中國(guó)文化片段在這部作品中究竟意義何在呢?本文將以“文化”為切入點(diǎn),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fā),分析作者對(duì)三組女性命運(yùn)描寫(xiě)的不同處理,從三個(gè)方面論證《女勇士>中“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元素的意義所在。
一、“無(wú)名女子”與“木蘭”:構(gòu)建女性的主體地位不可否認(rèn),傳統(tǒng)文化與意識(shí)形態(tài)具有一種無(wú)形的力量,影響著人們的思維與行為模式。雖然世界各國(guó)文化迥異,然而我們卻驚訝地發(fā)現(xiàn)很多文化對(duì)婦女的社會(huì)角色和個(gè)性氣質(zhì)等方面的界定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很多性別主義者甚至還引經(jīng)據(jù)典地證明女人從屬地位的合理性。亞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都曾表示“女人是不完整的人”的觀點(diǎn),這樣的觀點(diǎn)似乎在向人們暗示著“女人有時(shí)并不屬于人類的組成部分”。基于這樣的從屬地位,在早期的文學(xué)作品中,婦女很少作為主體出現(xiàn)在某一文本中,且多以邪惡的、自私的等非理性形象出現(xiàn)在讀者面前。<女勇士>開(kāi)篇故事的主人公“無(wú)名女子”是一個(gè)讓家族蒙羞的人物,她的名字人們不愿提及,她的存在幾乎被人否定。在母親的講述中,這個(gè)女子的事例只是充當(dāng)了。我”在青春期到來(lái)時(shí)母親警告“我”要檢點(diǎn)自己行為的反面教材。然而,“我”卻不顧母親“保持沉默”的命令,不但將姑媽失身的事說(shuō)了出來(lái),并且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想象力,極盡其詳?shù)貙o(wú)名姑媽如何在那個(gè)久遠(yuǎn)的年代,在那片“我”從未踏足的土地上失身的原因——被人強(qiáng)奸或誘奸或與人通奸一刻畫(huà)得細(xì)致入微。存在主義者認(rèn)為:人只有在生命的過(guò)程中才能對(duì)“自我”進(jìn)行實(shí)現(xiàn)和把握,而這一過(guò)程同樣可以看成是一種敘述文本。通過(guò)金斯頓的想象性重構(gòu)——“我姑姑纏著我。她的鬼魂附在我的身上……我正在講她的故事¨jJm”,“無(wú)名女子”得以重獲聲音,并在這一新的文本中獲得重生,從而在男性強(qiáng)勢(shì)話語(yǔ)的語(yǔ)境下建構(gòu)起以這樣一個(gè)被男權(quán)社會(huì)所不齒的女性形象為主體的“自我”身份。與“無(wú)名女子”不同,作品中的另一個(gè)人物“花木蘭”是一個(gè)家喻戶曉的人物,她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的故事更是代代傳唱。對(duì)于大多數(shù)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知之甚少的北美讀者而言,中國(guó)女性一直有著溫婉善良,多愁善感甚至憂郁多病的刻板形象。然而金斯頓卻將這一橫槍立馬,上陣殺敵,極富正義感和傳奇色彩的“女勇士”形象置于文本的中心位置,這對(duì)于顛覆殖民話語(yǔ)下的“傳統(tǒng)中國(guó)”形象有著積極的意義。在母親講述的故事中,“我”——一個(gè)在現(xiàn)實(shí)美國(guó)社會(huì)中受人輕視、缺乏自信、倍感孤獨(dú)的華裔小女孩,和“花木蘭”的形象合為一體,“我感到在聽(tīng)母親講故事的時(shí)候,自己也有使不完的力氣……她把花木蘭的歌教給了我。我長(zhǎng)大了一定要當(dāng)女中豪杰州n7)。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手法,將這一傳奇人物鮮活地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同時(shí)表達(dá)了敘述者對(duì)舊“自我”消解、對(duì)新“自我”重建的渴望,在解構(gòu)中國(guó)傳統(tǒng)中很多諸如“女不如男”的文化觀念的同時(shí),建構(gòu)新的華裔女性形象,建立新的華人敘述傳統(tǒng)和風(fēng)格。
二、“木蘭”與“木蘭”:彰顯女性的權(quán)威在這部作品中,金斯頓煞費(fèi)苦心、頗費(fèi)筆墨地塑造人物花木蘭與<木蘭辭)中那個(gè)孝順懂事的木蘭形象大相徑庭。其實(shí)在《女勇士)中木蘭的名字被拼成了FaMulan,而非HuaMulan。很多人解釋說(shuō)這是因?yàn)楣适碌闹v述者“我”的母親祖籍廣東,鄉(xiāng)音難改的緣故,但這也似乎是作者有意無(wú)意地向讀者暗示,其實(shí)她筆下的這個(gè)。木蘭”是完全不同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的那個(gè)“木蘭”的,她更象一個(gè)復(fù)仇者,一個(gè)反叛者,是一個(gè)有著中國(guó)面孔的美國(guó)式的女革命者。在作品中,作者充分發(fā)揮豐富的文學(xué)想象,將“我”刻畫(huà)成一名花木蘭式的女勇士,采用白描手法詳盡地?cái)⑹隽恕拔摇笔侨绾螐囊粋€(gè)七歲的小姑娘,經(jīng)過(guò)十五年的習(xí)武磨練,成為身懷絕技的女俠客,又是如何替父出征。而后營(yíng)房生子。一直到凱旋而歸,成為真正的女勇士的。在這一章,作者將該作品這一顯著的寫(xiě)作特色:“移植與變形東西方神話”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并選取了大量的168中國(guó)文化碎片,如。岳母刺字”、“盂姜女哭長(zhǎng)城”,。綠林好漢”、“末代農(nóng)民起義”、“打土豪、分田地、報(bào)家仇”、“娘子軍”以及“魯濱遜漂流記”和“愛(ài)麗絲漫游仙境”這些與花木蘭毫不相干的細(xì)節(jié),全部賦予“我”一人身上,使情節(jié)更加撲朔迷離,極大地增強(qiáng)了作品的可讀性。然而作者的目的并不僅限于此,這只不過(guò)是作者為了達(dá)到其宣揚(yáng)其女權(quán)主義思想這一特定目的而刻意采取的一種敘事手段或策略。在<木蘭辭>中,讀者很難想象木蘭在十年的戰(zhàn)斗生活中是如何隱藏自己的女性身份(包括更衣、就寢、沐浴、排泄及行經(jīng)等)的,女性的特征被中性化,甚至男性化了。法國(guó)女權(quán)主義理論家伊麗加萊(Lacelrigaray)認(rèn)為中性化是身份的喪失,而這種中性化如果有可能普遍實(shí)行的話,將意味著人類的滅亡,這是在召喚一種“種族滅絕”(geno-cide)H](Ⅲ-91)。對(duì)于兩性生理差異的強(qiáng)調(diào)西方女權(quán)主義觀點(diǎn)經(jīng)歷了三個(gè)演化階段:從主張消除兩性差異到譴責(zé)和排斥男性生理特征再到“女性優(yōu)越論”,即贊美女性的生理特征,主張女性的生理優(yōu)越和道德優(yōu)越。而《女勇士>中的花木蘭形象恰好是對(duì)這一論點(diǎn)極佳的詮釋。金斯頓沒(méi)有也無(wú)意于隱藏“我”的女性身份,反而贊美女性氣質(zhì)中的獨(dú)特之處,如婦女的重情感可避免人與人之間的暴力沖突,“我的軍隊(duì)從不強(qiáng)奸婦女,只是在富庶之地征些軍糧。我們所到之處,秩序井然”[3】(麒’;在戰(zhàn)斗中智勝多于力取,“我的第一個(gè)對(duì)手竟然是個(gè)巨人……我開(kāi)始將視線落到他下部致命之處……先一劍剁下他的一條腿。當(dāng)他蹣跚不穩(wěn)地向我走來(lái)時(shí),我又砍下了他的腦袋。竹【3](暇。35’而如懷孕、分娩等女性特征也賦予了“我”更多的戰(zhàn)斗力量。金斯頓在作品中刻畫(huà)的男性人物,與書(shū)中眾多勇敢、堅(jiān)強(qiáng)、威嚴(yán)的女性人物相比,顯得懦弱、丑惡、貪婪且衰老無(wú)力。無(wú)名姑媽的情人在村民圍攻襲擊“我”家時(shí),非但沒(méi)有挺身而出承擔(dān)責(zé)任,甚至有可能混在憤怒的村民中參與了這場(chǎng)襲擊,成為謀殺“我”姑媽的舊中國(guó)禮教的幫兇;肥頭大耳的財(cái)主靠賄賂官差逃脫了兵役,并常扮作土匪搶劫自己的村民;至于“我”的丈夫,則被作者設(shè)計(jì)成一個(gè)招之即來(lái),揮之即去且毫無(wú)主見(jiàn)的奴仆。與此相似的是,在作者的敘述中也很少涉及父親的形象,這些男性人物不僅面目模糊不清,而且毫無(wú)個(gè)性,好似女性人物的附屬品。作品的這一藝術(shù)處理與女權(quán)主義批評(píng)發(fā)展的趨勢(shì)相一致:女性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女人,她不僅享有男性同樣的權(quán)利,而且優(yōu)于男性,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本身并未被推翻,而是女性權(quán)力代替了男性權(quán)力,導(dǎo)致主體位置和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改變和置換"】(脫)。西蒙•波伏瓦(SimonedeBeauvoir)在她的女權(quán)主義寶典《第二性>(TheSecond融)(1949年)中指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是社會(huì)強(qiáng)加在兩性身上的一些約定俗成的東西造就了兩性之間的性格差異,而這些約定俗成的東西本身就是需要質(zhì)疑的。“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辯我是雄雌?”當(dāng)兩性被置于一個(gè)特定環(huán)境中時(shí),兩性之問(wèn)的差異是很難分辨的,因而正是社會(huì)對(duì)兩性的不同要求強(qiáng)化了這種差異,而并非性別本身。<女勇士)用自己獨(dú)特的方式,努力消解這種不合理的對(duì)性別差異的強(qiáng)調(diào)。通過(guò)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進(jìn)行合并與移植,如移植“岳母刺字”的故事,用金斯頓自己的話說(shuō)是“必須借用男子漢的能力和理想,去增加女人的力量,這樣她才變得強(qiáng)大”[’1‘一…,以達(dá)到作者喚起廣大婦女女權(quán)意識(shí)的同時(shí),構(gòu)建新女權(quán)主義的目的。
爭(zhēng)取女性的寫(xiě)作權(quán)和話語(yǔ)權(quán),使女性真正成為話語(yǔ)的主體,是西方女權(quán)主義運(yùn)動(dòng)的核心內(nèi)容之一。生活在男性中心社會(huì)秩序下的很多婦女都有著相同的病癥:“失語(yǔ)癥”,她們習(xí)慣對(duì)任何事物、任何事件保持沉默。我的“無(wú)名姑媽”因?yàn)榕c人發(fā)生婚外兩性關(guān)系而懷有身孕,因而受到保守的族人的處罰。最后自殺身亡,她在失去做母親和生存的權(quán)利的同時(shí)。也失去了為自己辮白的機(jī)會(huì)。“我”的姨媽月蘭可以說(shuō)是一個(gè)雙重的局外人,她被男性社會(huì)和美國(guó)主流文化社會(huì)所排斥,從來(lái)沒(méi)有對(duì)任何人傾訴過(guò)離婚后的孤獨(dú)與落寞。在“我”兒時(shí)的記憶中,曾被母親割掉舌筋,“我”以為母親希望我少說(shuō)話,因?yàn)橹袊?guó)人說(shuō)“長(zhǎng)舌婦是非多”。于是“我”開(kāi)始沉默,羞于開(kāi)口,盡管“正常華人婦女的聲音粗壯有威"‘”…,而我們卻要細(xì)聲細(xì)氣,以顯示我們的“美國(guó)女性氣”。有一次“我”在華人學(xué)校的女廁所對(duì)著一個(gè)總是沉默不語(yǔ)的女孩子大叫:“而你,你是棵植物,知道嗎?如果你不說(shuō)話,你就只能是植物。如果你不說(shuō)話,就沒(méi)有個(gè)性。你沒(méi)有個(gè)性,就不會(huì)有頭腦……說(shuō)話,快說(shuō)話…”㈣那個(gè)小女孩有著中國(guó)女孩的完美形象——安靜、干凈,黑黑的劉海兒,粉粉的臉蛋兒,小小的牙齒,穿著自己縫制的平平的棉布裙,其實(shí)正是敘述者本人的鏡象,它反射出“我”對(duì)軟弱和沉默的恐懼。折磨小女孩的舉動(dòng)恰恰顯示了敘述者童年時(shí)期的不安感和自我厭惡的情緒,然而她對(duì)其鏡象挑釁性的攻擊并沒(méi)有讓女孩開(kāi)口講話,反而讓敘述者本人患病臥床長(zhǎng)達(dá)18個(gè)月,這似乎也向讀者暗示,敘述者根本沒(méi)有戰(zhàn)勝自己,也沒(méi)有克服自己的“失語(yǔ)癥”。終于有一次,因?yàn)檎`以為母親要把“我”嫁給一個(gè)大塊頭,在和母親的爭(zhēng)吵中,“我”一下子說(shuō)出了lO件或12件最難啟齒的事情,母親卻告訴“我”:“我割你舌筋是為了讓你多說(shuō)話,而不是少說(shuō)話”,從此“我”的失語(yǔ)癥不治而愈。素有“三曹七子一蔡”之譽(yù)的文學(xué)女性蔡琰,創(chuàng)作了我國(guó)文學(xué)史上第一首自傳體五言長(zhǎng)篇敘事詩(shī),其文學(xué)成就甚至得到了男權(quán)意識(shí)極強(qiáng)的封建中國(guó)社會(huì)的認(rèn)可,成為文學(xué)婦女的典范。而蔡琰與作者本人的經(jīng)歷又有著驚人的相似。隨著父權(quán)制的建立,男性將自己定義為“自我”(self)。而將女性定義為“他者”(other)。女性在喪失了政治權(quán)、經(jīng)濟(jì)權(quán)、生存權(quán),甚至冠名權(quán)的同時(shí)也被剝奪了寫(xiě)作權(quán)和話語(yǔ)權(quán)。婦女文化水平低,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不僅被認(rèn)為是荒唐的,甚至是叛逆的,這一行為本身就是對(duì)滲透著男性權(quán)威的父權(quán)制的挑戰(zhàn)與反叛。所以,在試圖打破“菲勒斯中心”(phal]ocentre)秩序的同時(shí),如何構(gòu)建女性的主體身份,即思維主體、審美主體和話語(yǔ)主體,顯得尤為重要。可以說(shuō),作者巧妙地隱身于蔡琰身后,借助蔡琰的笛聲訴說(shuō)自己在既失去原有的文化根基,又無(wú)法完全進(jìn)入主流文化的尷尬與不安。其一,蔡琰被困匈奴,努力適應(yīng)當(dāng)?shù)厣睿?chuàng)作出舉世聞名的“胡笳十八拍”,正是作者努力想進(jìn)入主流社會(huì)并在文學(xué)領(lǐng)域中有所建樹(shù)的真實(shí)內(nèi)心寫(xiě)照;其二,蔡琰棄子返鄉(xiāng),從一種悲劇跌入另一種悲劇中,如同作者在文化夾縫中尋求自我身份認(rèn)同,并極力擺脫“他者”的邊緣狀態(tài)。蔡琰與金斯頓本人生活經(jīng)歷的對(duì)比,既確立了女性的評(píng)判權(quán)利,又肯定了女性的話語(yǔ)權(quán),是女性強(qiáng)烈的自我解放意識(shí)與性別覺(jué)悟的體現(xiàn)與折射。
結(jié)語(yǔ)
在金斯頓的潛意識(shí)里,就象無(wú)法擺脫她黑眼睛黃皮膚的相貌特征一樣,她無(wú)法擺脫中國(guó)文化對(duì)她的影響,而兩種傳統(tǒng)與文化的矛盾與沖突在《女勇士>中也隨處可見(jiàn)。作者成功地選取了中國(guó)文化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事例與片段,對(duì)其進(jìn)行了藝術(shù)的加工與再創(chuàng)作。一方面看似講述中國(guó)文化,實(shí)則宣揚(yáng)美國(guó)文化。譬如,花木蘭在沙場(chǎng)屢立戰(zhàn)功,體現(xiàn)的就是一種典型的美國(guó)式奮斗精神,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與個(gè)性而非中國(guó)文化中的服從和服務(wù)意識(shí)。再如,作品的副標(biāo)題<一段與鬼為伍的女孩的童年回憶>(MemoirsofaGirlhoodamongGhosts),看似講述來(lái)自中國(guó)的鬼魅故事,實(shí)則講述華裔乃至所有美國(guó)非主流社會(huì)的“他者”們的緊張與不安;另一方面,“中國(guó)文化”已成為一種表象,一種載體。“文化”這一概念已經(jīng)遠(yuǎn)遠(yuǎn)超越了其本身的內(nèi)涵,被政治化了。伊麗加萊曾提出,性別主義是種族主義的無(wú)意識(shí)形式,兩性關(guān)系是政治性的。作為華裔女性,金斯頓通過(guò)這些看似互不關(guān)聯(lián)的以中國(guó)為背景的故事材料,利用“文化”這把利劍,指向一切男權(quán)主義和種族主義。痛快淋漓地宣泄了自己的女權(quán)主義思想,使這部作品不僅極富藝術(shù)價(jià)值和美學(xué)價(jià)值,更賦予其極強(qiáng)的思想性、戰(zhàn)斗性和政治性,這無(wú)疑給七十年代的女權(quán)主義運(yùn)動(dòng)注射了一針強(qiáng)心劑,為構(gòu)建新女權(quán)主義作出了積極的貢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