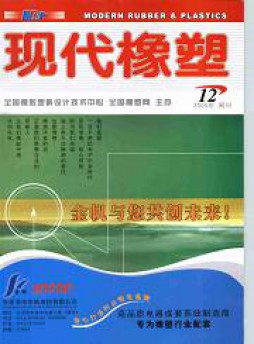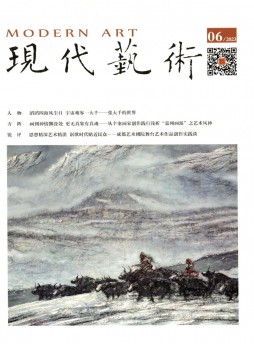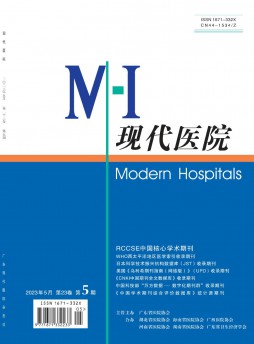現代古箏藝術發展路徑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現代古箏藝術發展路徑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五十年代——古箏藝術為發展奠定基礎
曹正曾談到歷史上“揚琴抑箏”,“重雅輕俗”的傾向。實際上,“雅俗”區別與社會地位的區別息息相關。琴人皆為“士”即封建社會的知識階層,他們文化水平高,他們的音樂也就“雅”了。為廣大群眾所喜愛的箏樂就被稱為“俗”了。藝術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是中國共產黨文藝政策的重要內容,古箏在新中國獲得新生乃歷史之必然。早在建國前的東北魯迅藝術學院時期,山東魚臺人張哲鳴就在此傳授箏藝。曹正于1950年應聘到該校,在更名后的東北音樂專科學校(沈陽音樂學院前身)設立古箏專業。1953年經曹正舉薦,山東趙玉齋到東北音專任教。此后全國高等音樂院校才相繼設立古箏專業。1953年河南派曹東扶應音樂研究所之邀,赴京演奏錄音,1954年到河南師專教授古箏。1955年中央音樂學院邀山東張為昭到校教授古箏。1956年再聘曹東扶執教。1956年浙江王巽之在上海音樂學院主持古箏教學。1956年潮州派蘇文賢到沈陽音樂學院任教。1958年后受聘廣州音專。1958年山東金灼南在南京藝術學院教授古箏,后來定聘山東藝術學院。1959年客家派箏人羅九香到天津音樂學院任教。1960年曹東扶去四川音樂學院執教。曹正于1964年從沈陽調入中國音樂學院任教。另有潮州派箏人郭鷹,山東派箏人高自成先后于1952年、1955年進入上海民族樂團、總政歌舞團任專職古箏演員。郭鷹同時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沈陽、西安各音樂院校兼職教學。高自成于1957年調西安音樂學院任教。至此,古箏藝術已全方位地進入專業音樂行列。民間箏人進入高校后,他們深感自身有待進一步提高。在這方面,趙玉齋是有代表性的,他以極大的毅力勤奮學習,將師傅口傳的箏曲、擂琴曲兩百余首整理成譜,同時學習音樂理論和西洋樂器。他學習鋼琴的請求得到李劫夫校長的支持。
他發現鋼琴的演奏原理與古箏相似,試將鋼琴的一些演奏技巧用于古箏演奏,將山東箏曲《老八板》改編成《四段錦》:在這首樂曲中采用了鋼琴的和音方法,初試成功。他在《慶豐年》的創作中,又采用了左右手交替和多聲部演奏手法。全國音協主席呂驥給予了高度評價。音樂評論家李凌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古箏演奏革新者》的文章,認為“《慶豐年》的誕生,結束了古箏單手演奏的歷史。為古箏演奏藝術的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后來,趙玉齋、曹正、高自成、韓廷貴等箏人都先后晉升為教授。民間箏人沒有“文人相輕”的習慣。高校的學術空氣,促進了全國性的箏藝交流。各校或相互兼課,或相互借調。為箏藝熱情奔走的曹正是個典型,幾乎各地都有他的弟子。1956年9月潮州派箏人蘇文賢到沈陽音樂院講學,把南派箏藝帶到北方。他與趙玉齋共同編輯有南北兩派樂曲的箏曲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蘇文賢向趙玉齋學習新的演奏技術。傳為南北交流的佳話。這一時期中,有幾次重要的藝術活動,對古箏藝術的發展具有巨大的影響。
1、1956年第一屆全國音樂周,出席人數達3500人。歷時月余。在音樂周期間,趙玉齋演出了《慶豐年》,高自成改編的山東箏曲《高山流水》獲創作演奏一等獎。曹正、曹東扶、羅九香、劉天一、蘇文賢等都參加了演出。總政歌舞團到中南海獻演,演出結束后,等中央領導接見演員。握著高自成的手親切地說:“中國的民族音樂內容很豐富,要做好繼承發揚工作,要古為今用。”通過他們精湛的演奏,加深了人們對古箏的理解,對各高校紛紛設置古箏專業不無影響。
2、1960年2月,中國音協邀請山東派箏家趙玉齋、高自成,廣東漢樂客家箏人羅九香,河南派箏家曹東扶等五人在中央音樂學院舉行專場音樂會。呂驥邀請時在北京的音樂界知名人士觀摩。演出后,由音樂史家楊蔭瀏主持座談,大家一致認為:“真是一次古箏名家大會師”。中國音協將這次演出、座談情況進行了報道,影響巨大。
3、1961年8月,在西安召開的高等音樂院校古箏教材會議,討論了各校的古箏教材,交流了教學經驗,進行了學術研究。會期15天。全國箏家大都到會。有廣東音專的羅九香、蘇文賢:沈陽音樂院的曹正、趙玉齋;四川音樂院的曹東扶;上海音樂院的王巽之:河南藝院的王省吾:西安音樂院的高自成、周延甲。山東藝術學院的金灼南因病未到會,送來教材。會議由曹正主持。會議對古箏教學的高、中、初級教材進行了規范:對彈奏指法進行了審定,進行了演出交流活動。人們發現山東、河南兩省地域相聯,民情相似,箏曲風格相近。后來,兩派箏家聯合編創了十首曲子,定名《魯、豫大板套曲》。演奏時采用兩臺箏,一臺奏山東樂曲,另一臺奏河南樂曲。兩臺箏演奏的復調音樂,是一次成功的創新。可惜樂曲沒有保留下來。會議期間,上海音樂學院的王巽之帶來古箏教程以及浙派箏曲與演奏技法。得到與會者的贊許。對于用五線譜記譜的做法,也得到了代表們的肯定。其后三十年,閻愛華編著的第一部《線譜古箏教程》問世。王巽之在教材建設、教學研究和實踐、嚴謹的治學態度、高水平的教學質量等方面,起了示范作用。老一輩的古箏藝術家,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引下,做了大量踏實的基本建設工作,為古箏藝術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成果在60年代以后逐步顯現出來。
二、六十年代初——第一批高校培養的古箏人才走向社會
經過五十年代的耕耘,在六十年代前后,各高校古箏畢業生,先后走向社會,至“”前夕,各校培養出的古箏藝術專門人材約百余人。他們較全面地掌握了中外音樂文化,特別是他們綜合各派箏藝的優點,形成了各自的風格。他們一部分到專業演出團體,一部分留校,一部分到群眾文化團體。從此,古箏藝術在更高層次上返回民間。“”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階段。在這階段中,高校停止招生,到處組織文藝宣傳隊,軍隊大招文藝兵,音樂上有一技之長的年輕人大都被吸收進去,在此導向下,孩子們的家長紛紛謀師求教,廣大古箏彈奏者大都參與了傳播箏藝。雖然多數專業演出團體停止業務活動,但還有些演奏家繼續演出活動,不僅鋼琴家殷承宗、二胡演奏家閔惠芬在公演,剛進入專業團體的古箏演奏家項斯華、張燕燕等也都在從事演奏活動,王昌元的《戰臺風》幾乎天天廣播。高校恢復招生是1973年開始的,活躍在城鄉的文藝骨干,于是有機會進入高校。他們經過系統學習,80年代初相繼登上音樂舞臺。如果把50年代從事箏藝的人作為第一代,60年代的高校畢業生中的箏人作為第二代,那么,80年代的高校畢業生就是第三代箏人。其中已有人獲得碩士學位。
三、八十年代學箏人數迅速增多九十年代古箏熱潮逐步形成
第二代箏人,二十年后,已在影響一方。北京的邱大成、李婉芬,沈陽的尹其穎、閻俐,西安的周延甲,四川的何成育,廣東的陳安華,武漢的丁伯荃,福建的焦金海,浙江的姜寶海、王剛強,南京的涂永梅,上海的何寶泉、孫文妍,以及專業演出團體中的潘妙興、郭雪君、李賢德、王昌元、項斯華、范上娥、王莉、張燕燕、金振瑤等,都已成為各地古箏名家。有人說,五十年代全國箏人不過千人,時過半個世紀,學箏人數已有幾十萬人。隨著教育改革和向素質教育轉變,學校中音樂課比重增強,對古箏的需求不斷增大,傳授箏藝的部門大量出現,高校及附中、附小,普遍增加了招生名額,培養了一批少年兒童,他們在各種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群眾性古箏普及教育蓬勃發展。1992年由上海東方古箏研究會創始的古箏考級活動,逐漸推向了全國。確切的學箏人數很難統計,從每年考級人數連續成倍增長來看,學箏熱潮令人振奮。箏藝社團如雨后春筍,紛紛建立。1980年12月,由曹正倡議,首建“北京古箏研究會”,并親任會長。還聘郭鷹、丁鳴任顧問,會員幾乎遍及全國。90年代初,會員達百余人,其理事遍及海內外。1983年徐州復建1947年曹正在徐州創建的“彭城箏社”,后改名為“徐州古箏研究會”。沛縣組建“大風箏社”。
1988年西安由高自成、周延甲倡議,組建了“西安秦箏學會”。出版了學會會刊《秦箏》,對交流信息起了積極作用。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在豫、魯、浙、粵等地相繼建立了古箏研究學會。山東在箏樂之鄉的鄆城創建了“齊魯古箏樂館”,旨在從兒童開始培養古箏藝術接班人。隨后,在山東音協指導下,成立了山東古箏研究會。在姜寶海、王剛強等人努力下,建立了杭州“武林箏社”及“武林箏研究室”。96年成立“浙江省古箏研究會”。河南由梁毅夫與曹東扶的女兒曹桂芬為核心,建立了“中州古箏學會”。廣東以陳安華為首建立了“廣東漢樂古箏會”。潮州、澄海地區成立了“澄海潮樂研究會”,于1993年專門舉辦了“澄海縣,93中國古箏,潮樂藝術節”,并出了會議專刊。在趙玉齋率領下建立的“東北地區,北國古箏學會”其實更早一些。并于1991年將開展群眾性古箏學習活動較好的朝陽市命名為“古箏名城”。還舉行了“中國古箏藝術研討會”。歷史名城揚州市在古箏家張弓的努力下,成為了古箏藝術普及較早的地區,并有南方古箏之鄉的美稱。作為潮州派和浙派活動中心的上海,成立了“東方古箏研究會”,南京建立了“金陵古梅箏館”和“南京少兒古箏協會”。湖北建立了“楚天箏會”。臺灣以古箏前輩梁在平為會長建立了“臺北古箏研究會”等等。對指導古箏普及活動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改革開放的二十余年間,對古箏藝術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幾件事,應特別予以說明。
1、北京古箏研究會自1980年成立以來,在20余年中,對全國古箏藝術活動起了聯絡樞紐和指導中心的作用。全國各地古箏社團的組織活動都與他們的熱情幫助相關。首倡古箏藝術“要從娃娃抓起”,對普及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1992年上海成立“東方古箏研究會”,名譽會長為上海音樂學院江明院長,會長為上海音樂學院何寶泉教授,會員基本上都是專業演奏家、教育家、理論家和作曲家,還有海外港臺的古箏家。研究方向著重于提高。首屆年會充分體現了這一點——研究了高校的四年制教學大綱:對箏曲創作及演奏技法進行了學術探討:首次擬定古箏考級章程。實踐證明,普及與提高是相互促進的。
2、揚州自1986至2000年連續舉辦四屆“中國古箏學術交流會”,對一種民族樂器進行如此大規模、長時間的持續投入,為歷史上所少有。第二屆交流會還專門就“現代箏曲創作”進行了研討,對新作品的不斷涌現,起了促進作用。
3、1991年7月在遼寧朝陽市召開的“中國古箏家、傳統箏曲交流研究會”,出席三百多人,以“敬業樂群,敬老尊賢、尊師重藝、獎掖后昆”為指導思想,提出“茫茫九派流中國,天下箏人是一家”。給趙玉齋、高自成、臺灣梁在平、馬來西亞陳雷士等人頒發“榮譽證書”。對有成就的年輕人授予“表揚證書”。
4、1993年的“中國古箏、潮樂藝術研討會”,全國箏界名家大都應邀出席。潮州、澄海是著名的僑鄉,潮箏、潮樂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東南亞流行很廣。應邀出席的海外華僑及港臺地區的箏人頗多,對擴大對外交流,把古箏推向世界有其特殊的作用。全國各地乃至世界性古箏比賽評獎活動、考級活動等都對形成古箏熱起了推動作用。所有以上活動都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和關懷下,在中國音協的指導和文化部門密切合作下進行的。中國音協的老領導呂驥、孫慎、文化部老領導周巍峙、音協書記馮光鈺等大都親自到會指導,熱情支持。
四、曲目創作與演奏技術的快速發展
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古箏演奏基本上是左手以潤飾為主,取音為輔。右手以取音為主,潤飾為輔。演奏技術相對穩定。從新中國成立,才進入了新的階段。箏人進入高校,加速了箏人自身知識更新的進程。前述之趙玉齋《慶豐年》首開先河。王巽之在《將軍令》一曲中,創造了左手快四點的密集彈奏和右手長搖的手法,將右手彈出之音,從點發展成線。曹東扶《鬧元宵》采用了大幅度的急速劃弦,連續性托、劈及密搖相結合的技法,與左手豫派箏的滑音、大顫融會貫通。
70年代,出現了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戰臺風》用左手拇、食指捻壓弦,右手搖指的扣搖手法以及快速點彈與掃搖手法的結合,使風聲、雨聲、勞動號子聲此起彼伏連成一片,進而使用刮奏手法從箏碼右邊轉到箏碼左邊的無序音高上,在協和與不協和的音響之間相互交替,引起聽眾的強烈共鳴。《雪山春曉》在委婉動聽的藏族音調中,運用了右手長搖結合左手大琶音分解和弦的手法,將冰雪融化,萬物復蘇的自然景觀與人民群眾喜迎新春的嶄新面貌展現了出來。表現龍梅、玉榮兩位小英雄的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幾乎匯集了以上所述各時期的古箏演奏技法,如表現流水動感的雙手連貫琶音:左手按吟、右手長搖的馬頭琴的歌唱;左手的歡快節奏與右手活潑流暢的快四點旋律相結合;運用掃搖、快四點、雙手連抹等技法表現暴風雨的來臨。
80年代的新作《侗族舞曲》、《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天京抒懷》、《木卡姆散序與舞曲》、《茉莉芬芳》、等都對古箏的表現能力有所豐富。練習曲也在向科學化發展,如《肖邦黑鍵練習曲》。快速演奏指法以及四指輪彈和以手腕為主的懸樁長搖法用于《井崗山上太陽紅》、《打虎上山》中,得到了令人振奮的效果。
90年代以來,古箏創作迎來了百花爭艷的春天。《黔中賦》的演奏以運用扎樁搖和懸樁搖的交替手法而成為亮點。加上左手輕壓規定音區的琴碼右側弦,右手同時向上劃弦的手法,栩栩如生地表現出木葉舞歡快、活潑富有節奏感的打擊樂聲和濃郁的民族風情。在這時期中,作曲家們參與箏曲創作,增強了創新力度,他們突破傳統五聲性調式的局限,吸收了日本琉球調式、都節調式的色彩,借鑒了梅西安人工調式的經驗,自行設計了許多新的調式,甚至創造了全新的“下方小三度加上方小二度”的調式色彩,每個八度分為三個環節,每個環節是一個大三度音程,在每個環節上都可以演奏同主音大小調的調式。新的調式色彩和多調性連環疊置的定弦方法,促進了演奏技法的變革。如《幻想曲》(王建民曲)、《箜篌引》(莊曜曲)、《溟山》(王中山曲)等。在這些箏曲的定弦中,就為轉調準備了條件。不同音區還采用不同音列,使不同音區演奏不同的調式色彩成為可能,既有對傳統調式色彩的偏離,又有對傳統調式色彩的回歸。音程的變化又為新的音樂語言的誕生創造了條件。在不斷達到過去做不到的創作意向的同時,人們逐步認識到,新的調式色彩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同時期內,更多的還是用五聲音階定弦法創作的箏曲,如《秦桑曲》、《臨安遺恨》、《鐵馬吟》等等。《秦桑曲》把握住了陜西派古箏善抒情的特點,充分發揮了“碗碗腔”音樂纏綿細膩、委婉迷人的表現力。以密集的搖指奏出自由的引子,在思念性的中板部分,采用秦箏傳統的左手大指和中指、名指交替按滑箏弦的手法,恰到好處地奏出了帶“徵調”的變徵和清角,生動地體現了秦地風格。二拍子與三拍子的交替出現,頗富詠嘆性質,如泣如訴,親切感人,細膩而生動地揭示了懷念親人的復雜心情,樂曲后半段的快板,清晰利索,激情滿懷,一氣呵成。結束部分,左手連續上行琶音的五聲音階模進,橫跨三個八度的寬闊音域,配合右手持續而清亮的高音搖指,由慢而快,彈奏起來有相當的難度。大有“一聲長在耳,百恨重經心”之感。《香山射鼓》取材于與唐代大曲有淵源關系的西安古(鼓)樂,以《柳青娘》為基調,與《月兒高》、《香山射鼓》等四首曲牌聯綴而成,描繪了幽靜的山谷,高聳的廟宇,虔誠的祈禱,深情的低唱的音響畫面。技法上保持了秦箏傳統,也吸收了潮州箏特有的“勾搭”技巧。在長音搖奏由ff的強度漸弱到ppp時,作了一個短暫的休止,似乎尋求“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效果。此曲在快速的雙手演奏中,嘎然而止,好像仿效“珠聯千拍碎,刀截一聲終”的唐代復終止式。《臨安遺恨》寫的是岳飛被害這一千古遺恨,以宏大的結構,強烈的戲劇性沖突與細膩的音樂語言,顯示了古箏這一古老樂器的超常的表現力。在箏與鋼琴的配合中,通過悲憤與哀怨,激情與溫柔,跌宕起伏的對比,將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有情有義。對命運的悲嘆,對人生的領悟,對奸臣的憤慨,對戎馬生涯的向往,對親人的思念,對人民的魚水之情,這一切綜合而成的崇高意境深深地凈化著聽眾的靈魂。《鐵馬吟》一曲更多地運用了魯派的傳統技法。風格剛健而含蓄內在。豐富的內涵耐人尋味。
古箏重奏作品的增多,說明人們注意到發揮古箏在群體中的表現力。古箏琵琶二重奏《大浪淘沙》、《水鄉高歌》、《春江花月夜》、:古箏與高胡二重奏《漁舟唱晚》:古箏高胡三重奏《豐收之歌》:古箏二重奏《滿江紅》;古箏與蝶式箏二重奏《春之海》;古箏四重奏《采蘑菇的小姑娘》、《步步高》、箏合奏《豐收鑼鼓》、《瑤族舞曲》、《伊犁河畔》、《百花引》、《拔根蘆柴花》等等,基本上都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建國以來的創作曲目,大體分屬三個時期,50年代為第一時期、60-70年代為第二時期,80年代以后為第三時期。作者大體分屬三種類型,一是老一輩古箏家,二是后來培養的古箏家,這兩類作者的作品,傳統性強,有創新,創新程度似有局限。第三類是專業作曲家,其作品最有創新力度。時代性強,也有傳統韻味不足之嫌。2000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龍音杯”中國民族樂器(古箏)國際比賽后,北京《音樂周報》11月16日發表題為《箏韻新聲,人才輩出》的述評:“近年來古箏演奏藝術的進步,尤其是技巧發展迅速,演奏人才輩出,新作品層出不窮。”“箏界的演奏技術,演奏技巧已進入全新階段”,“技高一籌的青年專業組,大多數選擇的是90年代至今,以快速為表現手段的新音樂風格的作品。這使得演奏新作品的選手成為快速技巧能力的比賽,”“當代箏曲的優美音色和個性特色,應該如何發展?箏曲的發展自50年代以來,一直走的是創新、發展的道路,而傳統箏曲在傳承與流派梳理方面的工作則較少。”文章確實切中肯綮。古箏藝術半個世紀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確實也該冷靜地思考一些前進中產生的問題。
五、結束語
半個世紀的經驗值得深思。成績是巨大的。古箏藝術有了很大提高,“古箏”不“古”是一大好事。古箏在為新時代服務,古老的藝術煥發了青春。古箏在提高指導下已相當普及。半個世紀來,前進步伐之大,超越過去二十個世紀。一批箏家走出國門,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挪威、阿聯酋、日本、馬來西亞、泰國等國,以及臺灣省、香港、澳門特區等地都有相當數量的古箏演奏家和愛好者。我們完全可以說,古箏藝術已經立于世界之林。值得思考的是,是否“有所得,也有所失”?“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是指導古箏藝術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半個世紀以來古箏藝術的成就,就是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取得的。成績是全體箏人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新作品是推動古箏藝術進步的動力。正是新作品促進了演奏技術的發展。如果說,我們還有不能令人滿意之處,那既不是迷失了方向,也不是少花了力氣。我以為,主要在于,對于創作古箏新作品這一任務而言,我們先天不足,而時間還沒容許我們彌補這一不足。如果說,老一輩古箏家缺乏世界音樂文化的素養,年青一代所缺乏的卻正是老一代所擅長的。老一輩努力于學習新東西,這正啟示我們,新的一代同樣需要學習,以進一步完善知識結構,充實藝術生命的活力。如果說“新創作不容許對于傳統的偏離”。那就是說,其前提就是不許創新。這顯然是不能接受的觀點。創新必然是對于傳統的偏離。如果說“新作品的作者不注意在傳統基礎上的創新”。那也不符合事實。新的作品分明在尋求向傳統回歸。
我們的作者群明白,揚棄并不是丟掉而已,它包含著保留傳統的精華,使之呈螺旋形上升的進步。傳統必須發展,不發展的東西就要死亡,發展就不能不有所偏離。無偏離也就無發展。哲學上經常討論誰是第一性的,誰是第二性的問題。究竟傳統性與時代性二者,誰是第一性的呢?我以為,第一性的,起決定性作用的,應該是時代性,時代是物質的客觀存在,應該是第一性的。考慮一切問題都應以此為出發點。毫無疑問,我們是為現代人民服務的。傳統的韻味一定會有所失。一點不失,既不可能,也不應該。老腔老調的《將軍令》不可能反映今天人民軍隊的精神面貌。“古為今用”絕不僅是聆聽古曲而已。作品與時代同步是不容回避的要求。我們確實對傳統掌握得還不夠深透,還需要深入鉆研。不僅如此,我們的音樂語言也還不夠豐富。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中說過:“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得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第二,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份。……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掌握音樂語言與掌握文學語言在原理上應該是一致的。如果說,“在廣泛深入地學習古今中外文化成果的基礎上,才能創造更新更美的文化。”這是一條規律。那么,只要我們堅持下苦功夫,向群眾、向外國人、向古人學習音樂語言,古箏藝術一定能實現“鳳凰涅”式的新生——它的古老軀體將在火焰中化為永恒的歷史記憶,新的鳳凰將在火焰中誕生。
擴展閱讀
- 1現代德育
- 2市場營銷現代到后現代
- 3將現代因素融入戲曲現代戲
- 4現代文化
- 5傳統與現代抉擇
- 6劇院現代轉換
- 7中國現代幽默喜劇
- 8現代后殖民文化
- 9現代廣告招貼設計
- 10現代家具實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