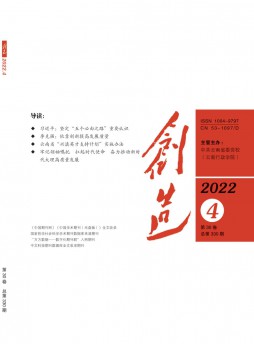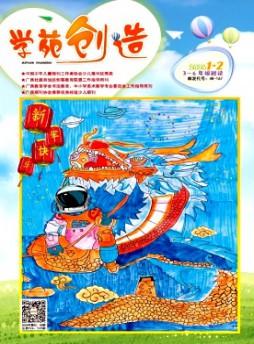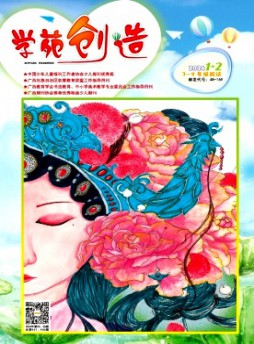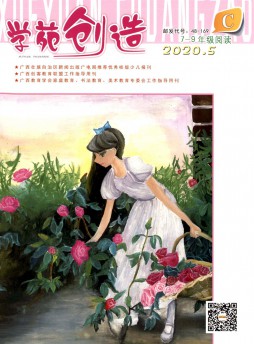創(chuàng)造社的顛覆策略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創(chuàng)造社的顛覆策略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在20世紀(jì)20年代的中國(guó)文壇,創(chuàng)造社在文學(xué)研究會(huì)和鴛鴦蝴蝶派的夾縫中異軍突起,并對(duì)20年代的中國(guó)文壇產(chǎn)生了持續(xù)的影響,使中國(guó)新文學(xué)史因此不得不劃一時(shí)代。歷來(lái)對(duì)創(chuàng)造社在文壇的興起不乏論述,但尚不夠系統(tǒng),我們借鑒布爾迪厄的社會(huì)學(xué)理論,從結(jié)構(gòu)動(dòng)力學(xué)的角度對(duì)其進(jìn)行全面的解讀,認(rèn)為:晚清至20世紀(jì)20年代,大眾傳媒的發(fā)展、獨(dú)立作家群的產(chǎn)生及現(xiàn)代讀者群的擴(kuò)大使上海等沿海城市形成了相對(duì)獨(dú)立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創(chuàng)造社進(jìn)入由鴛鴦蝴蝶派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所控制的這一場(chǎng)域,采取了顛覆策略而在文壇異軍突起。創(chuàng)造社采取這一策略,是因?yàn)樗麄儞碛挟愘|(zhì)的高勢(shì)能的文化資本和不斷擴(kuò)大的社會(huì)資本等符號(hào)資本。創(chuàng)造社的進(jìn)入策略和擁有的符號(hào)資本使其表現(xiàn)出區(qū)別于其他社團(tuán)作家的指導(dǎo)習(xí)性、反抗習(xí)性和自由習(xí)性,這些習(xí)性使其在文壇爆發(fā)出巨大能量的同時(shí),又面臨著內(nèi)部和外部的雙重危機(jī)。
一
法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布爾迪厄?qū)?chǎng)域“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guān)系的一個(gè)網(wǎng)絡(luò)或一個(gè)構(gòu)型。正是在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強(qiáng)加于占據(jù)特定位置的行動(dòng)者或機(jī)構(gòu)之上的決定性因素之中,這些位置得到了客觀的界定,其根據(jù)是這些位置在不同類型的權(quán)力(或資本)的分配結(jié)構(gòu)中實(shí)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他位置之間的客觀關(guān)系”[1]55。從這一定義可以看出,布爾迪厄的場(chǎng)域概念是由參與各方共同構(gòu)成的一個(g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空間,參與各方在場(chǎng)域中的位置與他所占有的資本具有對(duì)等關(guān)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對(duì)獨(dú)立性。場(chǎng)域可分為政治場(chǎng)域、經(jīng)濟(jì)場(chǎng)域、文學(xué)場(chǎng)域等,其中,文學(xué)場(chǎng)域在中國(guó)漫長(zhǎng)的封建社會(huì)中,由于受政治控制、經(jīng)濟(jì)發(fā)展遲緩及文人依附心態(tài)的影響,總體上看并未獲得獨(dú)立的地位。但晚清至20世紀(jì)20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的沿海城市的都市化進(jìn)程不斷加快,大眾傳媒的發(fā)展、獨(dú)立作家群的產(chǎn)生及現(xiàn)代讀者群的擴(kuò)大這三方的共同作用,使這一地區(qū)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逐漸發(fā)展成為相對(duì)獨(dú)立的結(jié)構(gòu)空間,成為創(chuàng)造社20年代進(jìn)入文壇的社會(huì)背景。
大眾傳媒的發(fā)展得益于現(xiàn)代出版業(yè)的繁榮和印刷術(shù)的進(jìn)步。19世紀(jì)90年代以后,中國(guó)開始興起辦報(bào)的高潮,而“小說(shuō)與報(bào)紙的銷路大有關(guān)系,往往一種情節(jié)曲折,文筆優(yōu)美的小說(shuō),可以抓住了報(bào)紙的讀者”[2]311,故各大報(bào)紙紛紛創(chuàng)辦副刊。與此同時(shí),各種供娛樂、休閑的報(bào)刊特別是文藝報(bào)刊開始興起。據(jù)調(diào)查,在1872年至1897年這25年間,總共只出現(xiàn)了5種文學(xué)期刊,從1902年到1909年,則有20種,而從1910年到1921年間,文學(xué)期刊則發(fā)展為52種[3]552。到20世紀(jì)20年代,新文學(xué)期刊已能夠與通俗文學(xué)期刊分庭抗禮。在此期間,中國(guó)的印刷技術(shù)也在不斷進(jìn)步,此時(shí)已不低于外國(guó)。如《新小說(shuō)》1902年創(chuàng)刊時(shí)在日本橫濱印刷,1903年時(shí)第2卷轉(zhuǎn)到上海廣智書局承印,其印刷水平并不低于第1卷[3]520。
獨(dú)立作家群的產(chǎn)生與當(dāng)時(shí)的政治狀況和稿酬制度緊密相關(guān)。清末至20世紀(jì)20年代的作家大致由兩類人群組成:一類是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受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最后一批知識(shí)分子。1905年,清朝政府廢除了科舉制度,迫使這一部分讀書人轉(zhuǎn)向以做編輯或?qū)懽g小說(shuō)來(lái)謀生。另一類是由國(guó)內(nèi)各新式學(xué)堂畢業(yè)的學(xué)生和大量留學(xué)歐美、日本的回國(guó)學(xué)生組成的中國(guó)第一批新型知識(shí)分子,他們面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政治動(dòng)亂和軍閥混戰(zhàn),感到在政治上沒有前途或進(jìn)入政治無(wú)望,遂憑借自己受新式教育所獲得的知識(shí)和寫作才能在傳媒、教育、文化、出版界占據(jù)一席之地。稿酬制度的建立則為這些新舊知識(shí)分子提供了相當(dāng)?shù)慕?jīng)濟(jì)基礎(chǔ),使他們成為社會(huì)上“賣文為生”的自謀職業(yè)者。如1910年《小說(shuō)月報(bào)》的刊例中明確規(guī)定了小說(shuō)稿酬的標(biāo)準(zhǔn):“投稿中選的,分四等酬謝: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兩元,來(lái)稿不合,立即退還。”[3]556于是一批以編輯創(chuàng)作為生的職業(yè)作家脫穎而出。茅盾回憶他在商務(wù)印書館工作時(shí)的1918年—1919年“月薪五十元”,平均每月還有40元稿酬收入[4]166。
現(xiàn)代讀者群的擴(kuò)大是指隨著上海等沿海城市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城市市民階層開始成為一個(gè)獨(dú)立的消費(fèi)群體。以上海為例,上海市民中的職員和知識(shí)分子構(gòu)成了文化消費(fèi)者的主要群體。在抗戰(zhàn)前,上海的職員群體已達(dá)40萬(wàn)人之多[5]127,這一群體的收入就總體來(lái)看可維持一個(gè)中等水平的小康生活。經(jīng)濟(jì)收入的保證和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使他們有相應(yīng)的文化需要。據(jù)調(diào)查,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人比較愿意接受新文學(xué),而受教育水平不高和受舊式教育的人比較喜歡通俗文學(xué)[2]301。知識(shí)分子中的學(xué)生群體構(gòu)成了最大的文化消費(fèi)群體。科舉制度廢除后,各級(jí)各類新式學(xué)校興起,到20世紀(jì)20年代在上海受過現(xiàn)代教育的學(xué)生已有幾十萬(wàn)人之多。這批學(xué)生群體受現(xiàn)代教育內(nèi)容的影響,愿意接受各種現(xiàn)代文化,葉靈鳳在《記<洪水>和出版部的誕生》中談到,一般訂閱或函購(gòu)書籍的人“多數(shù)是大學(xué)生、中學(xué)教員以及高年級(jí)的中學(xué)生”[2]301。
大眾傳媒為作家的寫作提供了廣闊的發(fā)表園地,又根據(jù)傳媒周期性出版的特點(diǎn)對(duì)其寫作產(chǎn)生某種壓力和動(dòng)力;作家依靠大眾傳媒提供的稿酬成為專職或兼職的自由撰稿人,又根據(jù)讀者的反饋不斷滿足其消費(fèi)需要;讀者為各種大眾傳媒提供了巨大的消費(fèi)群體,又通過反饋對(duì)作家和大眾傳媒提出各種消費(fèi)要求。這種作家、媒體和讀者三方的雙向互動(dòng),基本上按照商品生產(chǎn)、流通和交換的規(guī)律來(lái)經(jīng)營(yíng)文學(xué)場(chǎng)域,使中國(guó)以上海為中心的沿海城市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形成了一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的文化產(chǎn)業(yè)鏈條,從其他場(chǎng)域特別是政治場(chǎng)域的依附關(guān)系中解放出來(lái),并在互動(dòng)中不斷發(fā)展。
二
到20世紀(jì)20年代,在上海文學(xué)場(chǎng)域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是鴛鴦蝴蝶派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兩派。鴛鴦蝴蝶派以市場(chǎng)運(yùn)作為基礎(chǔ),以游戲休閑為旨?xì)w,受到了不斷發(fā)展壯大的上海市民群體的歡迎。茅盾接編《小說(shuō)月報(bào)》后,為文學(xué)研究會(huì)提出與鴛鴦蝴蝶派針鋒相對(duì)的主張:“將文藝當(dāng)作高興時(shí)的游戲或失意時(shí)的消遣的時(shí)候,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xué)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6]67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成員都受過現(xiàn)代中西方教育,且延攬了不少南北作家名流,又適逢“五四”運(yùn)動(dòng)的高潮過后青年重又陷入失望與苦悶之時(shí),故受到青年們的熱烈歡迎。據(jù)當(dāng)時(shí)的文學(xué)青年陳翔鶴回憶:“所謂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的惟一新文藝刊物,而同時(shí)也極在大中學(xué)生中流行的,恐怕便要算《小說(shuō)月報(bào)》一種了。”[7]129
鴛鴦蝴蝶派根基深厚,文學(xué)研究會(huì)已在文壇站穩(wěn)腳跟,創(chuàng)造社要想進(jìn)入文學(xué)場(chǎng)域這一結(jié)構(gòu)空間,就不能不采取一定的“策略”。布爾迪厄認(rèn)為:“策略”是指在某一場(chǎng)域中參與者為了爭(zhēng)奪場(chǎng)域中的地位,獲得“物質(zhì)和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有意無(wú)意的行為[8]78。參與者進(jìn)入場(chǎng)域的策略大致包括3種不同類型:保守、繼承和顛覆。保守的策略常常被那些在場(chǎng)域中占據(jù)支配地位的人或團(tuán)體所采用,如鴛鴦蝴蝶派。繼承的策略嘗試獲得進(jìn)入場(chǎng)域中的支配地位的準(zhǔn)入權(quán),常被那些新參加的成員采用,如文學(xué)研究會(huì)。而顛覆的策略是“通過挑戰(zhàn)統(tǒng)治者界定場(chǎng)域標(biāo)準(zhǔn)的合法性而采取的多少有些激進(jìn)的決裂形式”,“常被那些不那么企望從統(tǒng)治群體中獲得什么的人采用”[8]145,如創(chuàng)造社。創(chuàng)造社的顛覆策略包括“挑戰(zhàn)”策略和“區(qū)分”策略。
創(chuàng)造社的“挑戰(zhàn)”策略表現(xiàn)為對(duì)文學(xué)場(chǎng)域的其他社團(tuán)或?qū)W者的有形無(wú)形的“標(biāo)準(zhǔn)”、“權(quán)威”的強(qiáng)烈反叛。例如,前期創(chuàng)造社的“挑戰(zhàn)”首先表現(xiàn)為創(chuàng)造社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一起抨擊鴛鴦蝴蝶派,使其處于被動(dòng)地位。為了在文學(xué)場(chǎng)域站穩(wěn)腳跟,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茅盾、葉圣陶、鄭振鐸等對(duì)鴛鴦蝴蝶派的游戲消遣的文學(xué)觀、封建的“節(jié)”“孝”觀進(jìn)行了猛烈的抨擊,創(chuàng)造社則不斷與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批判相呼應(yīng)。郭沫若呼應(yīng)鄭振鐸的觀點(diǎn)時(shí)說(shuō):“先生攻擊《禮拜六》那一類的文丐是我所愿盡力聲援的……我不久也要助戰(zhàn)了。”[6]72其次表現(xiàn)為對(duì)文學(xué)研究會(huì)或其他學(xué)者名人不斷“發(fā)難”。茅盾回憶創(chuàng)造社曾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打了4個(gè)回合,依次是關(guān)于文藝觀點(diǎn)、關(guān)于如何介紹歐洲文學(xué)、對(duì)創(chuàng)作的評(píng)論、關(guān)于翻譯問題[4]234。從創(chuàng)造社與文學(xué)研究會(huì)論戰(zhàn)的情況看,皆以前者發(fā)難,后者答辯;前者謾罵多,說(shuō)理少為特點(diǎn),可見創(chuàng)造社“奮然興起”之“叛徒”姿態(tài)。創(chuàng)造社還和徐志摩、胡適等就創(chuàng)造社的人“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膿糜爛的創(chuàng)傷”、翻譯問題、郭沫若詩(shī)中的“淚浪滔滔”進(jìn)行論辯。
“區(qū)分”策略就是參與者試圖對(duì)文學(xué)場(chǎng)域進(jìn)行重新命名,以證明自身獨(dú)一無(wú)二的合法性,從而起到“打壓”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的目的。前期創(chuàng)造社的“區(qū)分”策略表現(xiàn)為提倡“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這一藝術(shù)主張來(lái)源于日本自然主義文學(xué),但我們也可以將其看做一種證明自身合法性的“區(qū)分”策略。為此,他們?cè)凇都兾膶W(xué)季刊<創(chuàng)造>出版預(yù)告》中打出了自己的旗號(hào):“自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發(fā)生后,我國(guó)新文藝為一二偶像所壟斷,以致藝術(shù)之新興氣運(yùn),澌滅將盡。創(chuàng)造社同人奮然興起打破社會(huì)因襲,主張藝術(shù)獨(dú)立,愿與天下之無(wú)名作家共興起而造成中國(guó)未來(lái)之國(guó)民文學(xué)。”[9]464“打破社會(huì)因襲,主張藝術(shù)獨(dú)立”正見其對(duì)文學(xué)場(chǎng)域重新“命名”的決心。隨著朱鏡我、李初梨、彭康、李鐵聲和馮乃超等留日學(xué)生回國(guó)的加入,后期創(chuàng)造社轉(zhuǎn)而提倡“表同情于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社會(huì)主義的寫實(shí)主義的文學(xué)”,并斷言“這決不是一種由于外界因素的強(qiáng)行介入所導(dǎo)致的歷史偶發(fā)事件,而是中國(guó)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其本身就客觀存在著這樣一種內(nèi)在要求”。由此他們要將刊物和文章當(dāng)作另一種戰(zhàn)斗的工具:“本志以后不再以純文藝的雜志自稱,卻以戰(zhàn)斗的陣營(yíng)自負(fù)。”[7]255這些文學(xué)理論表現(xiàn)得不容對(duì)手置喙,可見其“命名”口氣。
多年以后,郭沫若在回顧前期創(chuàng)造社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論辯時(shí)坦承:“文學(xué)研究會(huì)和創(chuàng)造社并沒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謂人生派和藝術(shù)派只是斗爭(zhēng)上使用的幌子。……在我們現(xiàn)在看來(lái),那時(shí)候的無(wú)聊的對(duì)立只是在封建社會(huì)中培養(yǎng)成的舊式的文人相輕,更具體地說(shuō),便是行幫意識(shí)的表現(xiàn)而已。”[7]132郭沫若的這段回顧其實(shí)可用在創(chuàng)造社所采取的所有“挑戰(zhàn)”和“區(qū)分”策略。“挑戰(zhàn)”策略就是從反面否定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的觀點(diǎn),從而為創(chuàng)造社進(jìn)入中國(guó)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開拓生存空間;“區(qū)分”策略就是從正面證明自己的文學(xué)觀點(diǎn)的正確,使競(jìng)爭(zhēng)對(duì)手的文學(xué)觀點(diǎn)貶值。總之,創(chuàng)造社的“挑戰(zhàn)”和“區(qū)分”策略等顛覆策略,其目的就是為了在當(dāng)時(shí)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獲得一席之地。
三
創(chuàng)造社的顛覆策略使其在文壇異軍突起,受到了青年讀者的熱烈歡迎。史蟫在評(píng)價(jià)創(chuàng)造社聲名鵲起時(shí)分析:“郁達(dá)夫張資平等充滿浪漫氣息的戀愛小說(shuō),可謂投其所好,遂都表示熱烈的歡迎,同時(shí)他們也歡迎郭沫若王獨(dú)清的熱情橫溢的詩(shī)歌,成仿吾的大膽潑辣的批評(píng),創(chuàng)造社擁有這許多受青年歡迎的作家,所以他們的聲勢(shì)凌駕同時(shí)的各種文學(xué)團(tuán)體以上,實(shí)在也是無(wú)怪其然的。”[10]
其實(shí),創(chuàng)造社只是由一批留學(xué)日本的青年文學(xué)愛好者組成的一個(gè)文學(xué)社團(tuán),最初除郭沫若在國(guó)內(nèi)文壇名聲較大之外,其他皆為無(wú)名小輩。那么,為什么恰恰是創(chuàng)造社而不是國(guó)內(nèi)其他社團(tuán)能夠在鴛鴦蝴蝶派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所構(gòu)成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中殺出一條血路來(lái)呢?我們這里借用布爾迪厄?qū)Y本的論述進(jìn)行分析。布爾迪厄的資本是指“積累性的勞動(dòng),這種勞動(dòng)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礎(chǔ)上被行動(dòng)者或行動(dòng)者小團(tuán)體占有時(shí),這種勞動(dòng)就使得他們能夠以具體化的形式或活的勞動(dòng)形式占有社會(huì)資源”[11]189。布爾迪厄創(chuàng)造性地將馬克思物質(zhì)化的“資本”延伸到文化符號(hào)領(lǐng)域,指出資本包括經(jīng)濟(jì)資本、社會(huì)資本和文化資本等多種形態(tài)。社會(huì)資本以社會(huì)聲望、頭銜為符號(hào),以社會(huì)規(guī)約為制度化形式。文化教育資本以作品、文憑、學(xué)銜為符號(hào),以學(xué)位為制度化形式[1]43。社會(huì)資本和文化資本雖由經(jīng)濟(jì)資本轉(zhuǎn)化而來(lái),但已擺脫了赤裸裸的利益形式,從而為占有符號(hào)權(quán)力獲得合法化根據(jù)。創(chuàng)造社正是由于擁有不同于國(guó)內(nèi)知識(shí)界的異質(zhì)的高勢(shì)能的文化資本和不斷擴(kuò)大的社會(huì)資本,才能在文壇異軍突起。
創(chuàng)造社的文化資本表現(xiàn)在3個(gè)方面:一是創(chuàng)造社成員具有留學(xué)生的背景。創(chuàng)造社是清一色的留日學(xué)生團(tuán)體:“這個(gè)團(tuán)體的初期的主要分子郭、郁、成,對(duì)于《新青年》時(shí)代一批啟蒙家如陳、胡、劉、錢、周,都沒有師生或朋友的關(guān)系。他們當(dāng)時(shí)都還在日本留學(xué)。”[12]181同時(shí)創(chuàng)造社成員在日本留學(xué)時(shí)都很年輕,留學(xué)時(shí)間相當(dāng)長(zhǎng),深受日本青年個(gè)性解放精神的影響,這種個(gè)性解放精神表現(xiàn)為脫離或逃避現(xiàn)存的統(tǒng)治體制,回歸感性的近代的自我。創(chuàng)造社成員和國(guó)內(nèi)名家學(xué)者沒有人際關(guān)系的瓜葛使他們能對(duì)國(guó)內(nèi)文壇進(jìn)行“自由”的批判,而他們所受的日本個(gè)性解放精神的影響則加強(qiáng)了這種批判精神。二是創(chuàng)造社具有日本“大高系統(tǒng)”的優(yōu)越感。創(chuàng)造社的成員大部分是日本舊制高等學(xué)校和帝國(guó)大學(xué)的“大高系統(tǒng)”的畢業(yè)生,他們對(duì)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普遍具有優(yōu)越感。伊藤虎丸認(rèn)為:“不論是早期的‘藝術(shù)派’或‘浪漫派’時(shí)代,也不論是后來(lái)的倡導(dǎo)‘革命文學(xué)’的時(shí)代,共同具有的那種啟蒙者的姿態(tài)和‘指導(dǎo)者’的意識(shí),我想和這‘大高同學(xué)’的優(yōu)越感不無(wú)關(guān)系。”[12]199因此,前后期創(chuàng)造社都認(rèn)為他們提倡的文學(xué)是相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的“高勢(shì)能”的文學(xué)。三是創(chuàng)造社對(duì)于日本文學(xué)的創(chuàng)造性學(xué)習(xí)。前期創(chuàng)造社成員留日期間,受日本文學(xué)自然主義理論的熏染,發(fā)表在《創(chuàng)造季刊》上的小說(shuō),許多是學(xué)習(xí)這種自然主義理論和當(dāng)時(shí)的日本短篇小說(shuō)的形式。后期創(chuàng)造社提倡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革命文學(xué),也是受日本當(dāng)時(shí)風(fēng)行的“左”傾教條主義福本主義的影響。對(duì)日本文學(xué)的創(chuàng)造性學(xué)習(xí)使創(chuàng)造社的文學(xué)觀點(diǎn)和作品表現(xiàn)出異國(guó)文學(xué)的特質(zhì)和與世界文學(xué)接軌的趨勢(shì),這種開放的、新穎的文學(xué)觀點(diǎn)和作品給中國(guó)的文學(xué)讀者以耳目一新之感。
創(chuàng)造社成員在國(guó)內(nèi)并無(wú)多少社會(huì)資本,但是創(chuàng)造社通過凝聚文學(xué)青年和建立社會(huì)關(guān)系使其社會(huì)資本不斷增加。首先,前期創(chuàng)造社作家在國(guó)內(nèi)聲名鵲起,在其周圍凝聚了一批青年。郭沫若、郁達(dá)夫、成仿吾、張資平等前期創(chuàng)造社的核心成員幾乎一夜成名,從而使創(chuàng)造社迅速成為一個(g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心,一批與創(chuàng)造社核心成員保持或緊密或松散關(guān)系的文學(xué)青年集聚在創(chuàng)造社核心成員周圍。成仿吾在《創(chuàng)造日》的《終刊感言》中說(shuō):“關(guān)于我們所選登的幾篇小說(shuō),我也可以保證它們是水平線以上的作品。幾個(gè)作者之中,尤以周全平與倪貽德二君最有望。”[9]492在《創(chuàng)造周報(bào)》的《一年的回顧》中成仿吾又深幸得到了幾個(gè)同心的朋友[9]481。另外,創(chuàng)造社成員通過同校、師生、同鄉(xiāng)、朋友、編寫等關(guān)系建立起一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前期創(chuàng)造社的核心成員郭沫若、郁達(dá)夫和成仿吾等都熱心對(duì)文學(xué)青年給予指導(dǎo)和扶持,周全平、鄧均吾、洪為法、葉靈鳳等在投稿過程中被發(fā)現(xiàn),許幸之在畫展上與郭沫若相識(shí),龔冰廬回憶他從事文藝工作是由郁達(dá)夫“拖出來(lái)的”。創(chuàng)造社還在留日學(xué)生中不斷獲得發(fā)展的力量,后期創(chuàng)造社隨著朱鏡我、李初梨、彭康、李鐵聲和馮乃超等留日學(xué)生回國(guó)的加入而成為創(chuàng)造社新的主要力量。創(chuàng)造社文學(xué)創(chuàng)作“眾星拱月”般的凝聚和網(wǎng)絡(luò)式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建立,充實(shí)了創(chuàng)造社的寫作力量,夯實(shí)了創(chuàng)造社的社會(huì)基礎(chǔ),擴(kuò)大了創(chuàng)造社的社會(huì)影響。
四
布爾迪厄認(rèn)為:“習(xí)性是指可轉(zhuǎn)換的傾向系統(tǒng),傾向于使被結(jié)構(gòu)的結(jié)構(gòu)發(fā)揮具有結(jié)構(gòu)能力的結(jié)構(gòu)的功能,也就是說(shuō),發(fā)揮產(chǎn)生與組織實(shí)踐與表述的原理的作用。”[8]116布爾迪厄的這一定義理論性較強(qiáng),他所要表達(dá)的意思實(shí)質(zhì)是:習(xí)性是一種集體性的、持久的規(guī)則行為的生成機(jī)制。它既是某一場(chǎng)域參與者的行為結(jié)果,又是一種存在的方式,一種習(xí)慣狀態(tài)。創(chuàng)造社進(jìn)入文壇的策略及所擁有的符號(hào)資本使其表現(xiàn)出與鴛鴦蝴蝶派作家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作家明顯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習(xí)慣狀態(tài)。鴛鴦蝴蝶派作家以滿足市民娛樂休閑的需要為宗旨,一些著名的鴛鴦蝴蝶派作家由于滿足了市場(chǎng)需要,生活過得優(yōu)裕自如,我們將他們稱之為“市場(chǎng)型知識(shí)分子”。文學(xué)研究會(huì)的主要成員大都在高校教育、文化、出版、傳媒等領(lǐng)域工作,他們?cè)趫?jiān)持現(xiàn)代人文理想時(shí)有一份普通但卻實(shí)實(shí)在在的工作崗位,故被一些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家稱為“崗位型知識(shí)分子”。而創(chuàng)造社作家在文壇所采取的策略以及所擁有的符號(hào)資本使其被稱為“流浪型知識(shí)分子”[7]290,他們表現(xiàn)出與鴛鴦蝴蝶派作家和文學(xué)研究會(huì)作家不同的指導(dǎo)習(xí)性、反抗習(xí)性和自由習(xí)性等特征。
指導(dǎo)習(xí)性是指創(chuàng)造社作家具有強(qiáng)烈的領(lǐng)導(dǎo)他人或文壇的意識(shí)。前期創(chuàng)作社作家標(biāo)榜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故他們既反對(duì)鴛鴦蝴蝶派作家的休閑娛樂主張,也反對(duì)文學(xué)研究會(huì)為人生而藝術(shù)的主張。可當(dāng)后期創(chuàng)造社作家轉(zhuǎn)向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革命文學(xué)時(shí),他們又聲稱這“是中國(guó)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其本身就客觀存在著這樣一種內(nèi)在要求”。這種不斷變化又始終認(rèn)為自己正確的文學(xué)主張當(dāng)時(shí)就引起了茅盾的譏諷:“想來(lái)大家也不會(huì)忘記今日之革命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在五六年前卻是出死力反對(duì)過文學(xué)的時(shí)代性和社會(huì)化的‘要人’。這就是當(dāng)時(shí)的創(chuàng)造社諸君。”[7]257反抗習(xí)性是指創(chuàng)造社作家與社會(huì)處于對(duì)立或沖突之中。這種反抗習(xí)性首先表現(xiàn)為創(chuàng)造社作家的獨(dú)身或家庭生活不和諧。前期創(chuàng)造社成員成仿吾、王獨(dú)清、鄭伯奇當(dāng)時(shí)都是獨(dú)身,成家的郭沫若感到自己不被安娜理解,郁達(dá)夫則稱原配妻子為“我的不得不愛的女人”。其次表現(xiàn)在創(chuàng)造社作家生活窘迫而鄙視金錢。前期創(chuàng)造社作家的生活仿佛“討口”一般,可郭沫若還是退還了四川紅十字會(huì)的高薪聘書。反抗習(xí)性還表現(xiàn)在創(chuàng)造社作家情緒無(wú)常。郭沫若和郁達(dá)夫曾因《創(chuàng)造》季刊只售出1500本而去借酒澆愁,兩人連吃了3家酒店,直到桌上酒壺林立,還自稱為“孤竹君二君子”。自由習(xí)性是指創(chuàng)造社作家個(gè)性強(qiáng)烈,不受外界環(huán)境或他人束縛。這首先表現(xiàn)在創(chuàng)造社作家和泰東書局的關(guān)系自由。創(chuàng)造社作家沒有泰東書局的報(bào)酬,也不受書局的拘束,寫作的態(tài)度自由,言論的膽量也大。其次表現(xiàn)在創(chuàng)造社作家人際關(guān)系自由。創(chuàng)造社作家是因志同道合而走在一起的,他們每個(gè)人并不受其他人制約。再次表現(xiàn)在追求個(gè)人感情的自由。郭沫若拋棄了原配妻子張瓊?cè)A,在日本和安娜自由同居。郁達(dá)夫本有妻室兒女,可又去追求年輕美貌的王映霞。
創(chuàng)造社作家的指導(dǎo)者習(xí)性、反抗習(xí)性和自由習(xí)性在當(dāng)時(shí)的文壇爆發(fā)出巨大的能量,產(chǎn)生了巨大的沖擊波的同時(shí),也使創(chuàng)造社面臨著內(nèi)部和外部的雙重危機(jī)。
創(chuàng)造社的內(nèi)部危機(jī)包括因創(chuàng)造社成員的情緒變化和人事變動(dòng)而產(chǎn)生的危機(jī)。情緒變化而產(chǎn)生的危機(jī)是指創(chuàng)造社文學(xué)的強(qiáng)烈情緒化色彩的難以持久。創(chuàng)造社作家的情緒不可能在某種文學(xué)主張上長(zhǎng)期處于亢奮狀態(tài),于是或者經(jīng)過一段時(shí)間的亢奮轉(zhuǎn)向疲軟,如郁達(dá)夫到北京和武漢之后感到所寫小說(shuō)都是“無(wú)聊的作品”;或者不斷轉(zhuǎn)移情緒熱點(diǎn),使情緒始終處于亢奮狀態(tài),如郭沫若由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轉(zhuǎn)而提倡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革命文學(xué)。人事變動(dòng)的危機(jī)是指創(chuàng)造社由于其成員的來(lái)去自由而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前期創(chuàng)造社由于郁達(dá)夫北上而離散;中后期創(chuàng)造社由于周全平的出走以及郁達(dá)夫的脫離,也給創(chuàng)造社帶來(lái)了巨大的內(nèi)耗和損失。
創(chuàng)造社的外部危機(jī)是指文學(xué)場(chǎng)域從根本上說(shuō)要受經(jīng)濟(jì)場(chǎng)域和政治場(chǎng)域的制約。布爾迪厄說(shuō):“文化生產(chǎn)場(chǎng)域在權(quán)力場(chǎng)域中占據(jù)的是一個(gè)被統(tǒng)治的地位。”[11]85首先,中國(guó)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受制于經(jīng)濟(jì)場(chǎng)域。創(chuàng)造社作家最初只是泰東書局沒有報(bào)酬的被雇傭者,后來(lái)創(chuàng)造社作家認(rèn)識(shí)到經(jīng)濟(jì)的重要性,從泰東書局獨(dú)立出來(lái)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出版部,但在國(guó)民黨政權(quán)的威脅和控制下,經(jīng)營(yíng)起伏不定,市場(chǎng)很快萎縮。其次,中國(guó)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更受控于政治場(chǎng)域。20世紀(jì)20年代的軍閥混戰(zhàn)使各派軍閥無(wú)暇他顧,上海的文化環(huán)境相對(duì)寬松,但隨著1927年作為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jí)代表的國(guó)民黨政權(quán)的建立和鞏固,其在文化領(lǐng)域的控制也一步步嚴(yán)厲,轉(zhuǎn)向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革命文學(xué)的創(chuàng)造社自然成為他們?nèi)【喌膶?duì)象。創(chuàng)造社的刊物不斷遭到查禁,直到1929年創(chuàng)造社創(chuàng)辦的主要刊物被查封,持續(xù)了近十年活動(dòng)的創(chuàng)造社終于被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