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劉震云小說的思想特質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析劉震云小說的思想特質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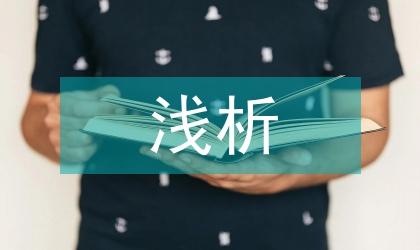
早期劉震云的小說如《一地雞毛》,通過對小林等青年功利的追求物質的現實表達不滿,從精神深處追溯根源,并使用反諷手法來對傳統崇高的追求消解,已初步表達了對知識分子的深深憂慮,并期望達到拯救的目的。在小說《手機》中,作者著力塑造了嚴守一和費墨兩個知識分子典型。與小林相比,他們世俗化趨向更為明顯,在市場經濟時代,他們已沒有了小林當初的被動與無奈,而是積極地融入,并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來滿足欲望。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欲望的沖擊下已蕩然無存。兩人有著主持人和大學教授的身份,可是滋長的欲望卻使他們丟失了精神信仰,變成了欲望的階下囚。作為主持人的嚴守一公共場合對于形象的維護與個人空間穿梭于女人之間的謊言形成了強烈的反諷,凸顯了知識分子在當代社會中道德修養的危機。
小說中,盡管嚴守一處處小心,但是還是被于文娟發現了問題,面對于文娟的質問,嚴守一非常惶恐,費盡心思周旋,卻又無法找到對策,小說生動地把他的尷尬比作吃苦瓜和含喉片:“晚飯吃了苦瓜,或是下午為了保護嗓子含了喉片,但它們都不是這苦法。”在費墨幫他圓謊后,他又說:“今天是我不對。晚上我沒跟費墨在一起。是一贊助商請我吃飯。吃過飯,又去洗桑拿。還有……還有小姐按摩。我想總不是好事,沒敢告訴你。”故作懊悔的辯解好不容易解決了問題,武月的一條短信又使事情真相大白。劇情各種偶然性因素的介入使故事高潮迭起,各種謊言的層遞出現,小說人物心理、動作的不斷變化,在謊言和真相之間,嚴守一丑陋、虛偽的靈魂躍然紙上,充分展現了劉震云的語言魅力。而在對人物的嘲諷過程之中,也隱含著作家對于知識分子在欲望面前的卑鄙行徑的強烈批判。
與嚴守一相比,費墨的故事則更發人深省,在所有人眼中,費墨都是被尊敬的形象:“嚴守一初見到他,馬上想起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老派知識分子。”[1]他不僅因為大學教師的身份具有很高的社會影響力,而且平時的做人、做事又獲得了家人、同事、朋友的高度評價。小說費墨面對金錢誘惑,仍然拒絕嚴守一的邀請,讓我們看到了傳統文人的高貴操守。但是當他與女研究生幽會的事被嚴守一無意撞見時,盡管他一再解釋,但是在事實面前,他苦心營造的美好形象瞬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猥瑣的偽君子形象,而他的名言“做人要厚道”,在形象發生變化后,就更凸顯了人物的道德虛偽性。知識分子具有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堅持自我不媚俗,崇高的精神追求在嚴守一和費墨身上出現了變異,主人公身上的欲望、庸俗、圓滑、卑鄙在作者反諷手法之中被無限的放大。對于這種選擇,李建軍認為,“他懷著一種近乎詛咒的惡意嘲弄一切,他通過對他者的嘲弄,體驗一種消極的快感”[2]。這種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劉震云肯定不僅僅是一種嘲弄,或是體驗快感,也不是簡單的表現對知識分子崇高的消解,而是在表達“五四”知識分子的啟蒙意識,通過喜劇方式去展示他深沉的思考。正如學者摩羅所說:“如果不這樣,他就不能表達他對這種日常生活及晦暗不明的人類存在的痛切。只有這樣寫他才能獲得最好的發泄。就像卓別林的電影一樣,用極度的夸張去嘲諷,卻讓你在笑聲中體會生活的艱辛。”[3]
眾所周知,在中國進入社會轉型期后,知識分子人文傳統精神遭受到世俗的嚴重沖擊,傳統知識分子一直致力于表現的崇高逐漸被戲弄、消解,如何堅守崇高,拒絕世俗成為今天知識分子苦苦思索的難題。劉震云在面對這個問題時并沒有逃避,而是勇敢的挑戰,希望作品能夠喚起知識分子的覺醒,通過社會的關注和自救來療傷,重塑當代知識分子階層的價值體系。恰如學者賀紹俊的觀點,“今天的知識分子,從社會擔當來說,不僅必須是一名拯救者,而且必須是一名自救者,甚至首先必須達成心靈的自我拯救才能去拯救別人。”[4]
“五四”時期,國民性是魯迅先生最早在小說中展示并被眾多作家所關注的問題,作品對歷史變革期國人在政治意識、自我意識、價值觀念和心理特征等幾個方面進行了強烈的揭示和批判,希望通過知識階層的啟蒙達到療救的目的。在當代作家中,劉震云是為數不多的始終關注國民性問題的作家之一,并對當代社會國人的心理和性格有著深沉的思考。從《新兵連》開始,其歷史小說和新寫實小說都在延續著前人的這種努力,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幅現代中國人的生存本相,愚昧、麻木、孱弱、喪失自我仍然是其小說重點表達的內容,通過對于國人無意識的對于權力的臣服和追求淋漓盡致地展現了當代社會“奴隸的痛苦與恥辱”。進入社會轉型期后,國民性存在背景發生轉化,對于經濟和物質的追求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小說《我叫劉躍進》中,劉震云通過對欲望的描寫展示了現代人陰暗的人性,建構起新的國民性批判體系。在小說中,作者圍繞劉躍進把人物設置成了狼和羊的生物關系,無論是高官、商人,還是竊賊、流浪漢,各種各樣的人和組織都被拉入這個關系網中。作品中的U盤象征著物欲,人性的陰暗在所有人物的爭奪之中著重被凸顯、放大,國人的種種劣根性表現在現代社會又一次重演,劉躍進被描寫成了當下社會的“阿Q”。在新的時代環境下塑造“阿Q”形象,劉震云的表現與魯迅和作家前期創作存在著明顯的變化。
對于主人公劉躍進的塑造,劉震云有意抹去了其階級屬性。傳統小說以階級來表現和深化主題,階級的介入使得人物具有典型性,表達的更多是階級共性。而在弱化權利意識,重點展示欲望的描寫中,劉躍進的故事僅僅是屬于其個人,是民工陣營的個體,不具有階級共性。這樣,小說的批判指向不會集中在社會矛盾上,主人公生存中遇到的困境才會成為人們思考的重點,進而去反思人性中存在的種種弊病。雖然小說在講述劉躍進的故事時僅僅把它當作一個個體,但是他的性格卻具有普遍性。考察他故事中的每一個情節就會發現,其性格并沒有因為社會的進化而改變,仍然和魯迅筆下的“阿Q”保持著一致。小說中的劉躍進勤勞、善良、吃苦耐勞,盡管遭遇到妻子的背叛,但對生活仍然充滿了信心,相信日子會一天天好轉。忍辱負重帶大孩子,對待馬曼麗的問題上,盡管心存非分之想,更多的卻是同情和愛護。作者無意對這種美德進行渲染,而是著重表現、揭示和批判劉躍進性格中的劣根性,如:自私狹隘、目光短淺、愚昧麻木、愛慕虛榮、占小便宜等。妻子背叛之后的懊悔自責和得到6萬元欠條的狂喜得意形成鮮明的對比,在他看來,這種交換是賺錢的買賣,進而不知羞愧地向兒子炫耀,這和阿Q的自我欺騙,自我安慰沒什么不同。平時精打細算,采購蔬菜占小便宜、不愿意給兒子學費故意拖延,但沒想到調戲吳老三的媳婦卻賠3600元。作為一個小人物,生活中從來沒有人重視過他,于是就愚昧地和賣唱乞丐比身份,認為自己要高“半頭”,進而就如“阿Q”對待“小D”一般,讓賣唱乞丐為他唱《王二姐思夫》,臨走前還要喊上一句“看見沒有?那棟樓,就是我蓋的!”可以說,在展示劉躍進這些性格特征時,劉震云的寫作是和魯迅先生相通的,只是人物出現的場景不同而已。
當然,劉躍進和“阿Q”被異化的因素是不同的,“阿Q”是傳統社會普遍熱衷的權力,而劉躍進是物欲,是金錢。作品中,夫妻關系、父子關系、朋友關系都是靠金錢來維持。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鉤心斗角、相互欺騙。面對兒子,雖然完成了撫養其長大成人的義務,可當兒子提出要錢交學費時,居然懷疑兒子是欺騙自己,父子之情在這里蕩然無存,凸顯的是其自私、狹隘的性格特征。而在對待U盤的事情上,從一個受害者最終轉變為勒索者,面對金錢的誘惑表現得極為勇敢,讓讀者看到了他貪婪的本性。小說中大量偶然性情節的設置,使得小說結局出人意料,“狼”吃“羊”的生物鏈條被倒置,伴隨著“狼”的死亡、被捕,“羊”大獲全勝。這種喜劇的結尾方式是社會道義的勝利,也符合大多數讀者的愿望。但是故事僅僅是一個載體,作者重點給我們呈現的是現代人的普遍金錢欲望,人性的變異、國民性的弊端在跌宕起伏的劇情中發人深省,以期達到自我拯救和社會關注的目的,這是劉震云通過小說重點傳達給國人的。
作為從農村進入城市的作家,劉震云與魯迅一樣,在世俗化時代繼承并發展了魯迅對國民性的關注和表現,以當代文化來考察鄉村文化的問題,繼而把批判擴展到現代都市,對人性的異化進行無情的鞭撻。當很多作家受到影視的吸引發生轉向,為了市場和世俗選擇轉型時,盡管劉震云在形式上也有著蒙太奇、空間化的借鑒和探索,但小說的精神追求仍建立在意義的追尋上,具有深沉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追求,表現了其獨特的藝術個性。(本文作者:王坤單位:新鄉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