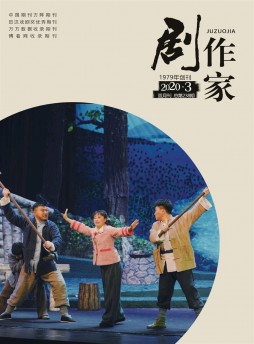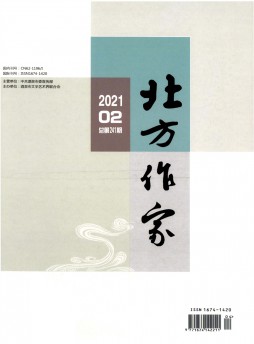作家書信中的文學(xué)批評思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作家書信中的文學(xué)批評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從內(nèi)容上看,沈從文書信中的文學(xué)批評活動主要包括對文學(xué)作品的分析,對作家的整體評價,對文藝思潮的分析,對文學(xué)史發(fā)展的觀點,對自己文學(xué)文本和創(chuàng)作觀念的解說,對自己文學(xué)史地位的不滿,對文學(xué)史研究狀況及成果的不滿,“”后對丁玲的反駁等。這些內(nèi)容構(gòu)成了沈從文與親友書信中的常見話題,也是沈從文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專門的評論活動之外表達自己觀點立場的主要方式。二現(xiàn)代階段(1929~1949)在將近20年時間里,沈從文在自己的書信中表達了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多個領(lǐng)域的關(guān)注,形成了鮮明的批評風(fēng)格,也印證了沈從文獨到的審美品位。在這個階段,沈從文在書信中較多談到自己的創(chuàng)作,包括作品解說、觀念闡述等方面。王際真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沈從文較為頻繁的寫信對象,兩人在書信往來中互相傾訴自己的困境,也互相鼓勵。沈從文于1930年元月18日在給王際真的復(fù)信中講述了自己的寫作狀態(tài):“昨夜因為斗氣,就寫了一萬七千字小說,這小說是今年第一篇,預(yù)計有一個禮拜寫好,當有六萬字左右。我今年當在大量生產(chǎn)下把我自己從困難中救出,不然明年恐怕轉(zhuǎn)鄉(xiāng)下也做不到。可惜的是生活總不許我在寫文章時多凝想一下,寫成后又缺少修改的暇裕,所以寫縱是寫,好是不容易的,這只有待一個機會去了。若果機會許可我從從容容寫文章又從從容容改,我一定做得出點比目下還好的文章來。”
迫于生活壓力,沈從文此時的寫作只能講求數(shù)量,故此自己也不滿意,明白地說“好是不容易的”,期待有“暇裕”可以從容寫作。1938年4月12日,沈從文從沅陵寫信給張兆和,談到了自己以往的小說和新的寫作計劃,“手邊有一本選集,一本《湘行散記》,一本《邊城》,一本《新與舊》,一本《廢郵存底》,象征卅年生命之沉淀。我預(yù)備寫一本大書,到昆明必可著手。”沈從文一向視小說為生命的記錄,從他認為自己的作品“象征卅年生命之沉淀”可見一斑。這部計劃中的“大書”就是長篇小說《長河》。在同年7月30日寫于昆明的信中,沈從文向張兆和介紹了《長河》的進度:“已夜十一點,我寫了《長河》五個頁子,寫一個鄉(xiāng)村秋天的種種。仿佛有各色的樹葉落在桌上紙上,有秋天陽光射在紙上。夜已沉靜,然而并不沉靜。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電閃極白,接著是一個比一個強的炸雷聲,在左邊右邊,各處響著。房子微微震動著。稍微有點疲倦,有點冷,有點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數(shù)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聽雷聲轟響所引起的情緒。同時也想起現(xiàn)代人在另外一種人為的巨雷響聲中所引起的情緒。我覺得很感動。唉,人生。
這洪大聲音,令人對歷史感到悲哀,因為它正在重造歷史。”這段告白可以提供理解《長河》的背景資料和作家的寫作狀態(tài)以及小說主題。沈從文對當時的文化環(huán)境非常敏感,在自己的書信中也反復(fù)提及,尤其是對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沈從文幾次出言批評。對于國民黨大肆屠殺進步作家,沈從文從文學(xué)發(fā)展的角度進行了抨擊。“年來政府對于左翼作家文藝政策看得太重,一捉到他們就殺(內(nèi)地因此殺掉的很多),其實是用不著這樣嚴厲的。另外一方面又似乎把文藝政策看得太輕,毫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把幾個較有名較有力的作家好好去培養(yǎng)起來,從作品上輸給年青人一個生活態(tài)度,一個結(jié)實自重耐勞勤學(xué)的為人態(tài)度,只知道用一些錢去辦一批刊物,卻不問刊物用處,兩方面實在皆作得極其愚蠢。”因丁玲被捕后胡適曾經(jīng)設(shè)法說項,沈從文寫信向胡適表達謝意。信中,沈從文對國民黨的文藝政策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評,對當時的文化環(huán)境也有極大抨擊。40年代,沈從文的作品常常被禁,沈從文也多有抗議。1943年元月13日,沈從文在信中概述了自己作品被刪和被禁的情況,并說由于這種刪改,小說的“精神早已失盡了”。對于文壇整體狀況,沈從文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與當時的主流觀點迥異。例如,1930年初,沈從文的筆友———最早向西方翻譯介紹《紅樓夢》的譯者———王際真向他表達了要翻譯介紹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的意思,沈從文當即回信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中國目下年青作家,說故事好文字好的,似乎還有幾個人,若是想選出說精致話做漂亮文章的可就難了。依我看,是郭沫若郁達夫都不行的,魯迅則近來不寫,冰心則永遠寫不出家庭親子愛以外。”
在這里,除了因魯迅沒有新作品而免于批評之外,沈從文直指郭沫若、郁達夫、冰心這些當時文壇巨匠的小說不夠格,認為只是“故事好文字好”還沒有達到自己理想中的“說精致話做漂亮文章”的程度,認為冰心的小說題材狹窄。這些觀點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更多的是出于自己文學(xué)觀念而對屬于異類的創(chuàng)作加以褊狹的否定。另外,在談到西方文學(xué)在中國的譯介時,沈從文也直截了當?shù)剡M行了總體否定。他有感于上海學(xué)生的讀書范圍小和盲目,于是談到文學(xué)譯介的局限:“在上海,近來是無數(shù)靠譯日本作品成偉人的。從前的周氏兄弟,郭沫若,現(xiàn)在的沈端先等,甚至于日本二流作品也轉(zhuǎn)販到中國來了,這原因一則是翻書人太多,其次則為譯者對文學(xué)的理解力,懂文學(xué)的不肯隨便翻,翻的人多數(shù)是不大懂的角色,所以現(xiàn)在譯品雜而且濫,呈空前混亂。書店則因為賤價原因,也不惜錢收買,所以譯著極多。”不得不說,這種觀點是過于偏激的,“不大懂的角色”,“譯品雜而且濫,呈空前混亂”等等判斷,用于全局可以,用于周氏兄弟則顯然有違事實。何況周氏兄弟的翻譯并不僅限于日本文學(xué),通過日文轉(zhuǎn)譯蘇俄、歐洲的作品和理論更多。
與魯迅之間,沈從文也并不總是采取反調(diào)的立場。值得一提的是,在對待梅蘭芳巡演美國的文化事件上,沈從文與魯迅不約而同采取了批評的立場。見諸魯迅雜文的對梅蘭芳的激烈批評人所共知,然而,沈從文的態(tài)度也并不稍顯緩和。沈從文勸說身在美國的王際真不要為梅蘭芳搖旗吶喊,并且言辭激烈地對梅蘭芳可能導(dǎo)致的西方對東方的誤解進行了分析。讓我們來談梅蘭芳吧。聽說張禹九同張仲述都幫了這旦角的忙,特意跑到紐約來做生意,我覺得不拘這事如何得美國人快樂,這快樂在我們總是一種羞辱。“東方趣味”有些事是對于民族人格不過問的,想不到這些有知識的人,還特意到紐約去介紹這趣味給美國人。你不要為那事做什么文章好一點,因為這件事在國內(nèi)較開明一點的年輕人,是一律加以反對,很對于這旦角藝術(shù)懷疑的。這段辛辣的文字不但略帶侮辱地將梅蘭芳直呼為“旦角”,而且對張禹九等絲毫沒有留情面。以沈從文與徐志摩的關(guān)系之深,按照常人的思路,沈從文該不會不對張禹九網(wǎng)開一面,可是率性淳樸的沈從文連這點“世故”爽性也拋掉了,對梅蘭芳訪美的動機、過程、結(jié)果都進行了全面的批評,甚至代表國內(nèi)的“較開明一點的年輕人”表態(tài)要“一律加以反對”,要懷疑旦角藝術(shù)本身。除了擔憂男扮女裝的旦角藝術(shù)給中國文化帶來誤解以外,沈從文也預(yù)見到了美國人欣賞梅蘭芳藝術(shù)時內(nèi)含的獵奇心理和潛藏的文化優(yōu)越感。這些分析在當時的文化環(huán)境中都是合理性大于偏誤的。沈從文與魯迅在這個問題上的近似立場也說明了兩人在思考中西文化大局時的清醒與深刻。在徐志摩去世之后,沈從文等人努力奔走欲成立以徐志摩命名的獎金基金,此事由沈從文來承擔有些勉為其難,于是沈從文一再向胡適求助。1936年3月31日,沈從文寫信給胡適,痛陳該獎金基金的必要性并吁請胡適設(shè)法周全。“我覺得關(guān)于中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獎金事,政府不注意到,如像中美基金會文化機關(guān)無論如何應(yīng)當提出幾萬塊錢來辦一辦。
事情很明顯,如今國內(nèi)大學(xué)少設(shè)一個文學(xué)講座,并不影響到這個學(xué)校分毫,如把這筆錢(一年五千)作為全中國新作家的獎金,影響可太大了。您不能給他們年青作家設(shè)設(shè)法,我覺得不大公平。對他們太疏忽,所謂新文學(xué)革命實近于有頭無尾。”同一封信里,沈從文還對疑似梁實秋批評林徽因的文章提出了質(zhì)疑:“《自由評論》有篇靈雨文章,說徽因一首詩不大容易懂(那意思是說不大通)。文章?lián)f是實秋寫的,若真是他寫的,您應(yīng)當勸他以后別寫這種文章。因為徽因的那首詩很明白,佩弦、孟實、公超、念生……大家都懂,都不覺得‘不通’,那文章卻實在寫的不大好。”
三“十七年”與“”時期(1949~1978)進入新舊中國轉(zhuǎn)換的歷史進程后,沈從文的命運開始急轉(zhuǎn)直下,外在環(huán)境的壓迫與壓抑日漸深沉。在這樣的處境中,沈從文書信中談及文學(xué)自身的文字日漸稀少,更多變成了對文化時局和文學(xué)發(fā)展的旁觀與質(zhì)疑,甚至反思反諷。在與親友的書信中,沈從文更多談及自己的心理磨難和生活困境,表達對自己“靠邊站”地位的不滿,同時也在無奈之中主動、真誠地希望改造自己以適應(yīng)新的社會、新的文學(xué)的要求。但是,他素來堅持的文學(xué)觀念和己執(zhí)拗頑固的個性又使他對自己的主動改造不斷反省。在這種多極分裂的精神格局中,沈從文對當時文壇的關(guān)注也在很多方面表現(xiàn)出了矛盾性的特征。
首先,對于當時主流的文學(xué)作品、文藝作品、文學(xué)批判運動,沈從文多有批評。沈從文比較關(guān)注對電影《武訓(xùn)傳》的批判。1951年,沈從文在一封一萬多字的信中談到了對這場批判運動的獨立思考。目前那么把《武訓(xùn)傳》提出來作全面學(xué)習(xí),領(lǐng)導(dǎo)方面自然是有計劃的大事。但是國家那么大的發(fā)展,文學(xué)思想上領(lǐng)導(dǎo),正可作正面的用鼓勵和幫助方法,和一個宏抱萬有的偉大涵容和理解態(tài)度,讓過去能用筆的將筆重新好好使用,準備用筆的都得到真正扶助和機會來用筆,才是辦法!如只把個武訓(xùn)來作長時期批評,武訓(xùn)這個人其實許多人就不知道,少數(shù)人提到他時還可能會說是魯迅的……一如托古射今,把現(xiàn)在人中有因種種原因工作一時和政治要求脫了節(jié)的情形,認為即是武訓(xùn)的再生,即動員一切可動員的來批判,還是主觀上有了錯誤的結(jié)果。因為這個時代哪里還會有武訓(xùn)?當時太平大國之革命,無從使武訓(xùn)參加,很自然。至于現(xiàn)在革命,哪是太平天國可比?革命者還自信不過似的比作太平天國,已不大近情,如再把時下人來比武訓(xùn),未免更遠了。因為事情明明白白,參加或擁護則活得事事如意,學(xué)武訓(xùn)則倒霉到死,世界上還會有人學(xué)武訓(xùn)來尋倒霉?如果有人始終和社會發(fā)展要求有游離情形,求解決問題還是從理解入手。使過去武訓(xùn)追隨太平天國,是一種完全錯誤的推理。但使一個現(xiàn)代人信仰當前的黨的一切領(lǐng)導(dǎo),沒有絲毫困難。一檢查偏向,去主觀,再莫把自己當成太平天國的英雄,也莫把人當成武訓(xùn)來有意作踐,就什么都不同了。
這種分析當然是站在旁觀者清醒的文化立場進行的,具有極大的合理性,但是與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不合。這表明,沈從文對時局的認識是“淺”的,沒有完全估計到意識形態(tài)的強大力量。同時,也是“深”的,它超越了當時文學(xué)批評界的時代局限和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限,是極為深刻的思想洞見,也是其獨立不倚的文學(xué)立場的淋漓表現(xiàn)。對《紅旗譜》、《紅旗飄飄》、《謝瑤環(huán)》、《李家莊的變遷》等主流作品,沈從文在自己的書信中都進行程度不同的批評。1960年12月,沈從文看了電影《紅旗譜》之后在書信中表達了自己的不以為然。“昨天我去看《紅旗譜》電影,覺得我體力如果還能得用,把今年搞的張鼎和四哥材料寫出來,一定還可望比這個作品真實有力得多。因為對各階層的人物都有一定熟習(xí),且明白如何刻畫即可收生動活潑感人效果,又會不太費力即可將背景畫出來,給人一種真切深刻印象。體力如夠用,我一定還是完成它。而且一定會比《邊城》寫得好得多。我過去寫什么都是事先先有一種輪廓,從輪廓就預(yù)先明白效果好壞。”
雖然沒有直接評價《紅旗譜》,但是通過沈從文對自己預(yù)期中以張鼎和為原型的小說的期待,可以反面看到沈從文對《紅旗譜》藝術(shù)上的否定。有時,這種否定更直接,有如下兩例。其一,1962年沈從文在江西瑞金看到田漢《謝瑤環(huán)》的演出,“滿座興奮,因為有‘女扮男裝’,有‘英雄打抱不平’,有‘官家少爺仗勢欺人,終于被巡按私訪查明,斬以尚方寶劍’。一切舊套子,內(nèi)容十分庸俗,但是在賣票上十分成功。也極自然,由北京到瑞金,看舊戲,才過癮,還有億萬群眾也。要群眾,或要有戲可演,都得遵循這一條路,這個方面想改良恐不是三五年事。”對田漢劇作“一切舊套子,內(nèi)容十分庸俗”的批評形諸筆端。其二,在此前1961年的一封信中,沈從文談到了《戰(zhàn)爭與和平》的偉大,稱其“又有趣又生動,真是偉大創(chuàng)造的心”,接著筆鋒一轉(zhuǎn)聯(lián)想到《紅旗飄飄》,“我們《紅旗飄飄》文章有的是不同動人事件,可是很多卻寫得并不動人,且多相同,重點放在戰(zhàn)斗過程上,表現(xiàn)方法又彼此受影響,十分近似,———不會寫!”這里評價《紅旗飄飄》中的作品把原本動人的不同故事寫得雷同,講述故事的方法又彼此雷同,總體的評價是“不會寫”。這與當時主流文藝界的觀點簡直就是唱對臺戲了。
其次,沈從文對老舍等主流作家多有批評。雖然老舍的寫作遭到了壓制,但是其處境畢竟比完全不能發(fā)聲的沈從文好得多。于是,在沈從文書信中,老舍成了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被批評的對象。50年代初,沈從文敏銳地覺察到當時文壇的呆滯,一些在他看來藝術(shù)質(zhì)量非常低劣的作品反而流行受追捧,尤其是“可以自由出版”,自己的作品反而徹底消失,這是讓他耿耿于懷、難以放下的。他對當時文壇的判斷是“巴金或張?zhí)煲怼⒉茇鹊仁侄即糇×耍灰粋€老舍成為人物,領(lǐng)導(dǎo)北京市文壇。事情如到只有領(lǐng)導(dǎo)者一人露面,不曾見更多年老的恢復(fù)用筆,年青的新成就不斷產(chǎn)生,領(lǐng)導(dǎo)方式還有問題,待改善,是顯明的”。這樣的領(lǐng)導(dǎo)方式,在沈從文看來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時代十分活潑,文壇實在太呆板”,換言之文壇脫離了時代。1951年年底,沈從文再次提到了老舍,這次是由于老舍因劇作《龍須溝》獲得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藝術(shù)家”的稱號,沈從文雖然肯定了獲獎的合理性,但是卻也指出:“其實還必須設(shè)很多獎來鼓勵各方面工作有貢獻的人,才合道理。戲劇不過是萬千種工作之一種而已。另外還有許多事情,在摸索中發(fā)展,有許多人不自私地在犧牲自己而努力,成績是一時看不出,將來卻重要的。”
到了1965年,沈從文更是因為汪曾祺打抱不平而直接批評老舍:“一個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還不知道他會寫小說(而且比老舍還寫得好得多),幸而轉(zhuǎn)到京劇團,改寫《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會寫文章。類此事或許還不少的。”除了為年輕人不得重視而抱不平的公心可以理解外,沈從文對老舍的批評有些師出無名。且不說汪曾祺小說寫得是否比老舍好,也不說汪曾祺《沙家浜》藝術(shù)成就多高,單說汪曾祺的會寫小說不為人所知恐怕主要與當時汪曾祺沒有作品發(fā)表有關(guān),雖然汪曾祺40年代就有小說集問世,但當時的影響力有限,過了二十多年沒人知曉也可以理解,這與汪曾祺是否在老舍手下工作,老舍是否應(yīng)該知道汪曾祺會寫小說實在是沒有多大關(guān)系的。將汪曾祺的沒有文名歸于老舍的壓制,實在是沈從文的一廂情愿和過于隨意。
再次,沈從文始終在自己的邊緣處境和融入主流的努力以及對這種努力的自我批判中艱難掙扎,始終沒有找到讓自己心安的文壇位置。早在1946年,沈從文就曾預(yù)感到自己的處境不妙,自己的“游離于現(xiàn)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為一種無益之業(yè)了”。有感于自己的處境,沈從文轉(zhuǎn)而抱怨時代環(huán)境使得自己“本可以帶著更年青的一群形成一種健康風(fēng)氣,結(jié)果卻必然在一種厭倦情緒中,一切萎縮。事到末后,寂寞死去。身與名沒,草草完事”。“寂寞死去”、“草草完事”云云雖則過于悲觀,卻也多少預(yù)示了自己此后的命運。頗為吊詭的是,前引的“游離于現(xiàn)代以外”句成為沈從文在“”中的罪證,專案組在抄家中讀到本封書信時特意用紅色下劃線將其標出。1949年4月,沈從文在同一封信里表現(xiàn)出了極端矛盾的狀態(tài),在讀到《人民日報》副刊上的幾篇主流作品之后,沈從文在自我反思的同時歡欣鼓舞,說這些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把我過去對于文學(xué)觀點完全摧毀了。無保留地摧毀了,擱筆是必然的,必須的”。進而又表達了自己不能適應(yīng)新形勢的遺憾,“從這幾篇文章中,讓我仿佛看到一個新國家的長成,作家應(yīng)當用一個什么態(tài)度來服務(wù)。這一點證明了延安文藝座談記錄實在是一個歷史文件,因為它不僅確定了作家的位置和責(zé)任,還決定了作家在這個位置上必然完成的任務(wù)。這一個歷史文件,將決定近五十年作家與國家新的關(guān)系的。上期有蕭參著《堅決執(zhí)行文藝為工農(nóng)兵的方針》一文,可惜沒有見到。從推想說,一定是對當前和未來能完全配合得極密切的。”自己也想“配合”卻無從“配合”,只好“游離”,這種復(fù)雜心境接下來就急轉(zhuǎn),變成自怨自艾:“唉,可惜這么一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我竟無從參預(yù)。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還可從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卻出于環(huán)境上性格上的客觀的限制,終必犧牲于時代過程中。二十年寫文章得罪人多矣。”
“寫文章得罪人多矣”確是重要原因,但未必是最重要的原因。根本原因其實是沈從文的文學(xué)觀念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巨大裂隙,這種裂隙使得他無從、無由、無法進入主流文學(xué)的視界,自覺的邊緣化和被動的邊緣化結(jié)合起來,沈從文“無從參預(yù)”“這么一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就是注定的了。當然,最能反映這種復(fù)雜心態(tài)的是《五月卅下十點北平宿舍》這篇已經(jīng)被文學(xué)史家充分注意到的書信,“我在搜尋喪失了的我”,“我在毀滅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處?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著了什么事?想不清楚。”在一個轟轟烈烈的大時代里迷失自我意味著對環(huán)境的質(zhì)疑,也更意味著對自我的進一步放逐。于是,自己是否瘋狂已經(jīng)關(guān)系到作家的生死,“我沒有瘋!可是,為什么家庭還照舊,我卻如此孤立無援無助的存在。為什么?究竟為什么?你回答我。”
當然沒有人能回答,當一個作家自絕于外在環(huán)境也被外在環(huán)境拒斥的時候,只有內(nèi)心的聲音能成為自己的友伴和支柱,當這種聲音堅強的時候,自我也能支撐自己,當這種聲音微弱的時候,自我也就隨著崩塌了。在沈從文的書信寫作生涯中,從1949年到“”結(jié)束,是最為密集的階段,沈從文以書信的形式痛陳自己的精神之痛,常向親友傾訴自己的內(nèi)心困頓。但是,在這些書信中,沈從文較少談及文學(xué)了,更沒有余裕去讀解自己中意的文學(xué)作品。他始終難以理解也難以釋懷的是自己的邊緣處境。卷帙浩繁的書信和為數(shù)不多的文學(xué)批評活動真實體現(xiàn)了沈從文在30年間的精神歷程和苦難狀貌,為文學(xué)史留下了珍貴的原始記錄。
四最后十年(1978~1988)“”后,隨著文化環(huán)境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巨大變化,沈從文的處境慢慢轉(zhuǎn)變,但是仍然處于邊緣的位置,直到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和金介甫的沈從文研究在國內(nèi)的傳播,這種境況稍微好轉(zhuǎn)。當然,沈從文再次聲名鵲起受寵于文壇是90年代之后了,沈從文自己沒有看到,即使看到也不知會作何種感想了。在沈從文最后10年的生命歷程中,他始終對自己的文壇處境念念不忘,對新時期之初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將自己有意無意遺忘非常不滿,對這種不滿的一再言說成為這10年中沈從文書信的一大主題。逐漸進入老境的沈從文絮絮叨叨不依不饒地訴說著自己的委屈,渴望被認同又對自己的不認同持著驕傲的姿態(tài)。同時,80年代初的筆墨官司也是他書信中的一個重要主題。這兩個主題與此前沈從文書信的一貫主旨其實是一以貫之的,都是對自我主體地位的確認和憂慮,都是自我身份認同中的矛盾與焦躁。換言之,貫穿沈從文一生的主題就是尋找自我定位,尋找自己在世間的準確位置,可是,他始終沒有找到答案,這種掙扎也就伴隨他走過了全部歲月。盡管偏于主觀、近于絮叨,但是這些晚年書信呈現(xiàn)出來的沈從文形象值得文學(xué)史研究給予充分注意。
第一,關(guān)于沈從文與丁玲的陳年恩怨。沈從文與丁玲一度相幫相攜共闖上海文壇,但是在丁玲1933年被捕之后,尤其是1935年出獄去延安之后,沈從文與丁玲的關(guān)系迅速惡化,50年代初雖有交往卻逐漸形同陌路。“”后彼此關(guān)系劍拔弩張,一度硝煙彌漫、嗆聲不斷,成為80年代文壇的一道別樣風(fēng)景。沈從文在這個階段的書信中不停地對丁玲從各個角度進行全方位的反擊,這種反唇相譏甚至掩蓋了沈從文個性中的柔和敦厚,呈現(xiàn)出了他個性中的硬質(zhì)一面。大致從1980年4月6日開始,沈從文開始在書信中對丁玲進行言辭激烈的批評,用了各種筆法。第二天4月7日,沈從文更是寫了萬字長信,繼續(xù)反擊“丁老太太”。10月14日的信中,沈從文甚至奉勸一位保存了自己《記丁玲》一文的朋友,“為你安全計,似以即早焚毀為得計合理。因為這是經(jīng)過丁玲本人判定為某某市儈寫的一本最拙劣的小說。丁玲女士是我們新中國最最偉大(同時也將是世界最偉大)的女作家,我由于無知,竟在四十多年前作品中,把這么一個偉大作家‘低估’或‘丑化’了,所以即從小說角度而言,也應(yīng)當算是最拙劣不過的。絕不宜流傳下去,十分顯明。為酬答你的好意,愿意你明白情形,希望把偶然留在手邊的那本書,即早毀去,免在另外一時受連累,出現(xiàn)意外麻煩,招架不住。承認現(xiàn)實并沉默接受,才符合‘明哲保身’之道!”
晚年的沈從文筆致漸趨老辣,這種語調(diào)里面除了被歷來壓抑而扭曲的心理之外,更多的是對丁玲的怨恨。這種怨恨讓晚年的沈從文刻骨銘心,形諸文字就變成了這種極度的反諷。這封信的附筆怨恨色彩更加濃厚,趨于憤怒、自虐和失去理性了。照抄如下:我本質(zhì)說來,實在材具平庸,思想極端保守落后,文字也半通不通,不過因緣時會,堅持不懈,從學(xué)習(xí)試探中,寫了幾十本不三不四的作品,并沒有任何值得贊美處。虛名過實,必致奇災(zāi)異難,居然能活到如今,已夠算得幸運了。所以放棄了空頭作家的名分,轉(zhuǎn)到歷史博物館工作,也只希望達到一個“及格說明員”的程度,事實上,學(xué)了三十年,也并未及格!外面說的我又專什么什么,都不足信。寫作上還一敗涂地,哪里會又來冒充什么專家?第二,關(guān)于自己的文學(xué)史地位等問題。新時期以來,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編寫在不斷調(diào)整,很多原來被淹沒的作家重新浮出歷史地表。但是沈從文的地位并沒有得到多少提高,這使得沈從文非常不解和苦悶。這個問題,他在信件中多次提及。1979年6月7日,沈從文在家信中說:“科學(xué)院文學(xué)所最近在云南開個什么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研究會,為一些五四以來有貢獻作家‘平反’或‘翻案’事,從簡報中,見到有由陳獨秀、胡適之到瞿秋白、艾青等等一系列名字。把我也放在其中,可惜太晚了點,而我的書也燒得太早、太徹底。一群搞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的假權(quán)威,只知為當權(quán)的人瞎捧,而把我貶得一文不值。國外印象卻正好相反。油菜花伯伯第二次來北京說,國外討厭宣傳品,花錢再多,印得再好,還是不買賬。在美、日我有讀者,若能用個‘回憶錄’方式寫寫昆明那八年,寄美國他可為花幾百美金用四號字印出來,肯定會成功,因為有的是讀者!日本且會即刻有人譯過去。”
有感于自己在國內(nèi)文壇的地位,沈從文對于自己在國外的知名度頗為看重,而且由此質(zhì)疑當時的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界和學(xué)者們,對他們多有微詞。同時,沈從文還對自己的書屢次被禁毀難以釋懷,尤其是《記丁玲》一書。1980年4月7日,沈從文在信中不厭其煩地敘述了自己這本書的命運:“其實這本書早已并我所有同樣不三不四、拙劣不堪作品,于解放前即受禁止,五二年且已和別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即紙型也不保存。臺灣方面亦于五三年用明令禁止,焚禁后且永遠不許重印,至今尚未解禁。唯一在香港有復(fù)印本,但從無什么人提過這本書,原因是否把她‘舉得過高’?不得而知。全部書被禁焚,我也早即料到,所以認為‘合情合理’,從不灰心喪氣……”1980年8月23日,沈從文在信中批評了前一年出版的九院校本《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且言辭十分激烈:“你應(yīng)當明白,直到去年用九大院校語文教師名分合編的《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教材,內(nèi)中廿五個年在四十五左右的教師,沒有一個人讀過我的作品,教材目錄上本來并沒有我的姓名,只臨時找個什么人看了一二復(fù)印選本,說了幾句不痛不癢的贊美后,末后便依舊采用四十年前什么‘權(quán)威批評家’老腔調(diào),胡罵我一頓完事。這種教材居然能通過印行,即可知是得上面同意允許,且得到南方什么主管的‘長’支持的。你如今若冒冒失失自出心裁,說出些真話,危險是顯明的,意見也顯明會觸犯那九大院校教師,肯定會在另一時受迫害譴責(zé)的。望牢牢記著此事。”
同樣的意思,沈從文曾經(jīng)于同年9月初的另一封信里再次重申。一方面,沈從文耿耿于自己在文學(xué)史上沒有地位,另一方面他又為安全計一再勸阻青年學(xué)者對自己進行重新評價,阻止別人抬高自己的文學(xué)史地位。其中的委曲與掙扎反映了沈從文受到迫害的深廣,也反映了其性格心理中的扭曲與變形。能說明這個問題的還有他對凌宇的沈從文研究的態(tài)度和對學(xué)界將其視作“小京派頭頭”的警惕與反感。值得一提的是,沈從文細心地計算著那些沒有機會看、有機會也不看或者根本沒聽說的自己名字與作品的學(xué)者的年齡,在80年代初的幾封信里分別用40、45、50歲等年齡來鎖定這個群體,可謂處心積慮了。
第三,關(guān)于夏志清、司馬長風(fēng)、金介甫、凌宇的沈從文研究。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最早對沈從文的小說創(chuàng)作做出較高評價,因此也成為沈從文研究某種意義上的一個起點,沈從文對此非常重視,將其視作自己在國外的學(xué)術(shù)名聲的明證。對于金介甫的沈從文研究,沈從文則給予很多幫助,提供材料,幫助聯(lián)系實地采訪等,也曾經(jīng)把金介甫介紹給朱光潛等。可是,當凌宇打算對自己寫作的沈從文傳記進行國際性的宣傳時,沈從文堅決制止了。“勸阻別人對自己的宣揚,盡力制止人們?yōu)樗Q不平,給‘沈從文熱’降溫,是他晚年書信一個持續(xù)特點。”甚至沈從文生前寫下的最后文字也是這個內(nèi)容。
第四,關(guān)于蘇雪林、張愛玲、魯迅等。在1980年4月上旬的一封信中,沈從文澄清了收信人問到的幾個問題,其中之一與蘇雪林有關(guān),言辭一樣激烈。蘇雪林文章不足稱引。那是在武大教“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作的講義。這是個神經(jīng)質(zhì)老姑娘,對人好壞全憑感情用事!當時一面罵我,一面把魯迅捧上了天。而次一年,卻又用“快郵代電”方式,散發(fā)了一份申討文,羅列魯迅“十大罪狀”,申討魯迅。忽然而天,忽然而地,令人不好招架。對我的批評,也近于“信口開河”。當時或稍后,即作了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隨同逃到廣州,又轉(zhuǎn)入天主堂作修女。現(xiàn)在若還活著,大致是在法國天主堂作修女了。上海人(萬象書局開始)盜印一折八扣書時,搞了我一個選集,為哄騙讀者,把她批評附上。從此以后,許多人寫現(xiàn)代文學(xué)史,都引用這個材料,左的也引。可想不到這個“不安定靈魂”,既是國民黨立法委員,又討伐過魯迅。而到抗戰(zhàn),我上武漢暫住在東湖時,她卻通過凌叔華,一再向我表示對我的歉意,說當時并不曾見過我全部作品。我卻付之一笑,走開了。關(guān)于張愛玲,沈從文為了澄清張兆和與張愛玲并無關(guān)系曾經(jīng)稍加說明。“你問的張愛玲,我和家中人均未認識。張家在合肥是個大族,‘和’字輩弟兄姐妹多達百十人,有大半就未見過。抗戰(zhàn)八年中,我一家大小四人,在昆明鄉(xiāng)下住了八年,復(fù)員后才返回北京。”關(guān)于魯迅,沈從文則是感嘆其書印刷數(shù)量之多,自己的書全數(shù)焚毀的不同命運。1982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同時出版沈從文的作品選集,沈從文在給參與編輯的凌宇的信中,有這么一段話:“印數(shù)不及萬本,我倒以為‘過時的舊作’,供參考用也很夠了。如像魯迅先生集子,以十萬計的印行。一面邀集大幾十個國家友好人士來祝壽,場面鋪排之大為歷史少有。另一面,琉璃廠和西單書攤上都廉價處理,《二心集》只一毛多一本,影印書信只一元一冊,未免令人短氣。”
這種話語方式近似于無理取鬧了。第五,關(guān)于古華《芙蓉鎮(zhèn)》、張潔《沉重的翅膀》等。沈從文晚年非常看重《芙蓉鎮(zhèn)》這部長篇小說,幾次在書信中盛贊。1981年10月31日,沈從文致信古華談到《芙蓉鎮(zhèn)》并作出高度評價。在同一封信中,沈從文有很大保留地談到了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沈從文的晚年是在焦躁不安的心理狀態(tài)中度過的,內(nèi)心充滿了種種矛盾,反映在書信中則表現(xiàn)為對自己文學(xué)史地位的過于在意和對丁玲的尖銳抨擊。其中的文學(xué)評論活動帶上了意氣用事的成分。縱觀沈從文書信中的文學(xué)批評活動,我們可以看到,沈從文充分利用了書信這一介質(zhì)并將其特性發(fā)揮得淋漓盡致,使其成為一個有效的文學(xué)批評手段,這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是不多見的。簡單概括,沈從文書信中的文學(xué)評論有如下特點。其一,注重審美觀照。除個別情況外,沈從文堅持以審美標準對待文學(xué)作品,在審視文學(xué)文本時注重對語言、形式和歷史內(nèi)涵的分析。其二,具有抒情性。沈從文將書信寫作看作文學(xué)寫作的基本訓(xùn)練手段,看重其文學(xué)功能,而且自己最早發(fā)表的作品就是書信體,一生中也多用書信體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可以說,書信體小說和書信往來一起構(gòu)成沈從文文學(xué)生活的重要部分。在這些小說與書信中,沈從文擅長抒發(fā)自己內(nèi)心的真情實感,娓娓道來,毫不矯飾。其三,主觀性。在某些情況中,尤其是涉及到與別人的論爭或者自己的文學(xué)史地位的時候,沈從文書信中的文學(xué)批評就陷入主觀,很多時候使用諷刺,剖白自己的同時也盡力嘲諷對方。從書信的角度觀察沈從文的文學(xué)批評活動,有利于了解沈從文的文學(xué)觀、批評觀、文學(xué)史觀,也有利于接近一個更加真實全面的沈從文。當然,以上的論述只是接近了沈從文的書信世界而已,遠遠不夠深入。
作者:劉永春單位:魯東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