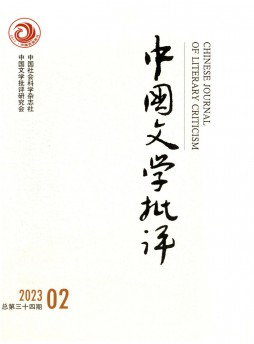文學(xué)批評的時間性與角力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文學(xué)批評的時間性與角力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在該書中,楊經(jīng)建從20世紀(jì)90年代的歷史文化語境入手論述小說創(chuàng)作,其中關(guān)于90年代文學(xué)的“新狀態(tài)”概念,顯然是他出于有效地考察當(dāng)代文學(xué)特質(zhì)而提出的。在他看來,以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各方面的現(xiàn)代化追求事實(shí)上已經(jīng)將當(dāng)代中國帶到了一個新的“時空維度”,在與西方接軌的過程中,消費(fèi)主義文化業(yè)已深深地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觀念、風(fēng)格上打上了烙印,20世紀(jì)90年代中國文學(xué)的審美出現(xiàn)了時尚化、休閑化、形象化的特點(diǎn)。進(jìn)而,楊經(jīng)建對這一時期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精神向度進(jìn)行了簡明扼要的概括,將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各異、流派紛呈的作家進(jìn)行了精神上的劃分———新理性主義、新本土主義、新民粹主義、新現(xiàn)實(shí)主義、新表現(xiàn)主義,從宏觀上把握了該時期中國文學(xué)與前27年以及80年代文學(xué)精神品格的本質(zhì)區(qū)別,不論是堅(jiān)持藝術(shù)信仰和精神操守的新理性主義,還是意義的空缺與意義的過剩奇妙地共存的新表現(xiàn)主義,它們都與此前文學(xué)作為政治的傳聲筒或政治理念的映射有了根本的不同:市場體制的到來固然攜帶著難以預(yù)料的對文學(xué)世俗化的誘惑與刺激,但同時文學(xué)卻擁有了一改過去受制于國家政權(quán)和意識形態(tài)的局面,具備了多樣發(fā)展的可能性。楊經(jīng)建對世紀(jì)末文學(xué)所作的精神劃分,彰顯出濃郁的理論意味和宏觀的學(xué)術(shù)視野,無疑有助于廓清眾說紛紜的當(dāng)代小說現(xiàn)狀,直接觸及小說所承載的時代精神與文化品味,在一種整體的觀照中梳理出這一階段文學(xué)清晰的脈絡(luò)。楊經(jīng)建的文學(xué)批評具有強(qiáng)烈的存在主義色彩,這種批評底色并不是到其專著《存在與虛無———20世紀(jì)中國存在主義文學(xué)論辯》寫作、出版時才表現(xiàn)出來,而是在其文學(xué)批評的初期便具備了此特質(zhì)。
存在主義式的文學(xué)批評直抵文學(xué)內(nèi)核,規(guī)避了文學(xué)細(xì)枝末節(jié)的遮蔽,顯示出大氣磅礴的思維智慧。正是立足于存在主義的立場,楊經(jīng)建從數(shù)千年潛移默化的家族宗法傳統(tǒng)造就的中國家族小說的繁榮中,從《金瓶梅》、《紅樓夢》一直延綿到《四世同堂》、《白鹿原》等優(yōu)秀家族長篇的文學(xué)實(shí)踐中,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中國家族文化母題的諸多共性。在他看來,“在人類的天生的‘?dāng)⑹聞訖C(jī)’的鼓動和作用下,將潛在人類意識中的那些基本情結(jié)外化、升華為敘事文學(xué)所要講述的內(nèi)容,換言之,生命、死亡、愛欲、家族成為敘事文學(xué)古老而穩(wěn)定的創(chuàng)作母題,也是理所當(dāng)然的。”進(jìn)而將中國百余年來的家族小說視為一種文化母題,它有著自己的敘事規(guī)范、結(jié)構(gòu)功能和模式,是人類基本精神、民族風(fēng)情在小說中的必然反映與遺存,是人類情感集體無意識的象征,“它充分體現(xiàn)了人類藝術(shù)的歷時態(tài)與共時態(tài)的一體兩面的本色”。楊經(jīng)建敏銳地感覺到,家族小說在當(dāng)代中國的發(fā)展必然會朝著城鎮(zhèn)、都市、個人體驗(yàn)的層面推進(jìn)和衍變,其中蘊(yùn)含著一種獨(dú)有的沉重、悲愴美感,其根源在于“知識分子文人在種種劇烈撞擊中出現(xiàn)的‘憂新’和‘患舊’的精神敏感病”。
同樣基于存在主義的文學(xué)批評立場,楊經(jīng)建對于人們所熟知的王國維的“三重境界說”也提出了讓人耳目一新的論斷。他認(rèn)為,王國維身處在生存論的精神困境中,因而借助詩學(xué)的方式傳達(dá)著一種人生態(tài)度和生活方式,即“人生困境與終極憂患與其說是在有我之境中的種種人生的苦惱與選擇,不如說是人處于有我之境中卻要去追求與實(shí)現(xiàn)無我之境的困惑”。于是,王國維的三重境界在存在主義視野下得到了重新理解:“其中的第一境乃俗境,人在俗境中卻想超越此俗境去追求理想之真境,故有‘望盡天涯路’之嘆;第二境乃處于真境中的人,然而因?yàn)樗皇橙碎g煙火了未免過于寂寞凄涼,所以只能是‘為伊消得人憔悴’;到了第三境,人終于豁然大悟:真正的勝境并非要完全脫離俗諦,原來在俗諦中也能實(shí)現(xiàn)真諦,這就是‘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以前之所以沒有發(fā)現(xiàn)俗諦中也能實(shí)現(xiàn)真諦是因?yàn)闆]有真諦照耀之光,只有真諦之光的燭照才能使人擺脫異化現(xiàn)實(shí)的束縛進(jìn)入自由的理想境界。如果轉(zhuǎn)用存在主義的話語表述則是,通過現(xiàn)象學(xué)的還原使作為‘此在’的人進(jìn)入本真生存的狀態(tài),人脫去生存的蔽障從‘此在’入手探詢生命的本源,從而進(jìn)入藝術(shù)的極度陶醉的境界———澄明之境。”
同時,在談到傳統(tǒng)社會與現(xiàn)代社會的藝術(shù)審美偏向時,楊經(jīng)建發(fā)現(xiàn)了一個饒有意味的現(xiàn)象:“步入現(xiàn)代性進(jìn)程的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卻延續(xù)了傳統(tǒng)社會中藝術(shù)審美偏向于維系社會協(xié)調(diào)、團(tuán)結(jié)的理性功能而喪失了現(xiàn)代文學(xué)自由的品格和突破現(xiàn)實(shí)局限的非理性功能,尤其是,當(dāng)‘現(xiàn)代性’的理性精神逐漸被置于中國式政治革命運(yùn)動所導(dǎo)致的單一狹窄的工具理性、實(shí)用理性運(yùn)行軌跡后。”這樣切中肯啟糸的凝練表述,在楊經(jīng)建的文學(xué)批評中并不鮮見,讀來饒有趣味,這與他對于存在主義哲學(xué)著作的喜愛、對于存在主義文學(xué)作品的熟讀以及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積累的豐富閱歷、人生經(jīng)驗(yàn)密不可分。
楊經(jīng)建的學(xué)術(shù)批評智慧和發(fā)現(xiàn)還遠(yuǎn)不止于此。他對于哲學(xué)、社會學(xué)、人類學(xué)、文化學(xué)以及中西文學(xué)保持著長期的廣泛涉獵和研究,因而在分析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與文化現(xiàn)象時常常能夠發(fā)人所未發(fā)。從過去一直到現(xiàn)在,很多研究者尤其是同屬于文學(xué)學(xué)科內(nèi)的研究者,都認(rèn)為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研究只停留在概括和分析的層次,沒有掌握綜合批評或跨學(xué)科研究的能力,因而缺乏學(xué)理內(nèi)涵。而楊經(jīng)建既對西方文化與文學(xué)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又廣泛涉獵古今中外的其它學(xué)科的知識,并且能夠很好地綜合、化用,因而在解決文學(xué)與文化現(xiàn)象時能夠獨(dú)具匠心。
只有以敏銳的目光定位好用力的方位,以長期的才學(xué)沉淀與縝密思維、生命意識相結(jié)合,批評家才有可能發(fā)現(xiàn)他人所不能發(fā)現(xiàn)的真知。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xué)自20世紀(jì)80年代后期出現(xiàn),到20世紀(jì)90年代無疑已經(jīng)發(fā)展為一個影響范圍相當(dāng)廣泛的文學(xué)思潮和現(xiàn)象,充盈的女性意識和女性話語日益成為眾多女性作家的基本“話份”和權(quán)利。楊經(jīng)建先生在書中巧妙地運(yùn)用了“女性主義文學(xué)”概念,從而避免了“女性文學(xué)”與“女權(quán)主義文學(xué)”這些概念的無謂糾纏,認(rèn)為女性主義文學(xué)“主要是以女性主體意識為本位的,以文學(xué)為切入點(diǎn)的藝術(shù)審美建構(gòu)現(xiàn)象”,并且業(yè)已轉(zhuǎn)入到自律性存在的狀態(tài)和階段。他從“五四”時期冰心、蕭紅、丁玲等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一直聯(lián)系到80年代以來的張潔、鐵凝、殘雪,勾勒出女性主義文學(xué)所經(jīng)歷的對自我、自我價值的認(rèn)識過程以及商業(yè)文化進(jìn)程中造成的女性文學(xué)發(fā)展存在著的“新的裂隙、誘惑與可能”。
楊經(jīng)建先生關(guān)注著女性文學(xué)產(chǎn)生、發(fā)展的宏觀語境,并真正觸及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女性解放的內(nèi)涵———“除了政治、經(jīng)濟(jì)等等的社會民權(quán)運(yùn)動外,必須伴之以意識和文化的變革”;在對“私語性”寫作的分析中,論者深入到女性作家的精神成長履跡中,由“房間”意象指涉到女性作家對私人經(jīng)驗(yàn)、隱秘心理的大膽揭示與解構(gòu)男性話語霸權(quán)的微妙關(guān)系,思考著當(dāng)代中國女性在市場經(jīng)濟(jì)并非完全“自由競爭”態(tài)勢下再次滑向社會邊緣的危險性和窘迫性,面對著她們可能存在著的寫作經(jīng)驗(yàn)的復(fù)制與話語空間日益狹窄的缺陷,論者也就如何避免女性主義文學(xué)重新陷入到被傳統(tǒng)男性社會“窺視”陷阱中去提出了自己的新見。楊經(jīng)建的學(xué)術(shù)視野開闊,又不失對于文學(xué)細(xì)節(jié)的感悟,這是他在長期的文學(xué)閱讀和理論研究基礎(chǔ)上形成的根底。沒有長期積累的學(xué)術(shù)觀察力、豐厚的學(xué)養(yǎng)、跨越的思維、活躍的生命感知力,是難于達(dá)到的如此警覺、睿智的批評深度的。楊經(jīng)建的文學(xué)批評深入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發(fā)生現(xiàn)場,既有對文學(xué)現(xiàn)象條分縷析的解讀,又有對文學(xué)思潮及其產(chǎn)生根源的透徹剖析,通過對宏大歷史文化語境的分析來考察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發(fā)生、發(fā)展特質(zhì)。他以簡明扼要的方式,將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各異、流派紛呈的作家進(jìn)行了精神上的整體歸類,直接觸及當(dāng)代文學(xué)所承載的時代精神與文化品味,在一種整體的觀照中梳理出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內(nèi)在脈絡(luò)。
楊經(jīng)建非常擅長把握行進(jìn)中的文學(xué)現(xiàn)象和思想命脈,對于當(dāng)前的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特質(zhì)也有著正確的理解。在他看來,目前一個新的城市文化語境和社會文化背景已經(jīng)形成,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逐漸地改變著過去以農(nóng)業(yè)文明為核心的中國社會軸心。楊經(jīng)建從中國古代不能產(chǎn)生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學(xué)入手,對城市以經(jīng)濟(jì)交往為中心的性質(zhì)進(jìn)行了分析,廓清了城市文學(xué)概念的基本要素。因此,他將王朔視為20世紀(jì)90年代城市小說的第一人,究其原因則是王朔的小說符合了城市化時代的商業(yè)性文化要素的需要。楊經(jīng)建十分贊同用“bus”這個比喻來喻指城市小說的精神要旨與世俗準(zhǔn)則,認(rèn)為判別一種文化具有生命力與否的標(biāo)志就在于它對人的同化能力的強(qiáng)弱。同時,在對“城市民謠”體小說的審視中,楊經(jīng)建將自己的思維觸角延伸到了城鎮(zhèn)民間社會、淳樸真摯的小城故事中去,展現(xiàn)了這類小說對自然審美理想的追求和知足常樂的生存方式;論及市情商態(tài)小說時,作者以都市商業(yè)文明景觀下的生存境況為基本考察點(diǎn),將張欣、王剛、邱華棟、何頓以及賈平凹等作家統(tǒng)統(tǒng)歸于此類;在談到賈平凹引起巨大爭議的《廢都》時,論者獨(dú)具匠心地分析了小說中“四大閑人”的城市中產(chǎn)階級身份和精神追求,凸現(xiàn)了由政治中心向市場中心轉(zhuǎn)變過程中傳統(tǒng)文人的無奈,并對中產(chǎn)階級的心理狀態(tài)、人生態(tài)度和生存方式、價值追求進(jìn)行了精辟的論述,從另外的一個側(cè)面揭示了某類可能的真實(shí)存在。
在文學(xué)批評過程中,楊經(jīng)建將自己的生命體驗(yàn)和研究對象融為一體,從彼之時代、學(xué)說以及人性、人情之常理出發(fā),由人及己,將人生經(jīng)驗(yàn)、生命感受和文學(xué)問題完美地融合。正是因?yàn)槿绱耍x楊經(jīng)建的批評文章使人常有如沐春風(fēng)卻又有恍然大悟之感。這既是思維之奇,也是創(chuàng)新之妙。楊經(jīng)建的文學(xué)批評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所折射出來的精神品味與時代意旨,并由此為切入點(diǎn)將自己潛心研究的文學(xué)現(xiàn)象進(jìn)行了宏觀掃描,體現(xiàn)出厚重的學(xué)術(shù)品質(zhì)和寬闊的研究視野。楊經(jīng)建對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與文化現(xiàn)象進(jìn)行審視時,不僅思考著當(dāng)代小說發(fā)展的趨勢和可能,而且對當(dāng)代知識分子如何尋找安身立命的精神資源、如何在市場擠兌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無形壓迫下尋找新的出路作了諸多的反思。基于這一立場,他在肯定20世紀(jì)90年代城市小說繁榮必然性的同時,也對其歷史理性精神的缺失表示了自己的憂慮;在審視“現(xiàn)實(shí)主義沖擊波”現(xiàn)象的時候,他也對其問題意識的淡薄與過度掛靠主流的缺陷進(jìn)行了批評。楊經(jīng)建的文學(xué)批評在對文學(xué)作品與文學(xué)現(xiàn)象進(jìn)行分析和歸納時,也具有直面當(dāng)下、燭照現(xiàn)實(shí)的探索力量和由此所帶來的精神愉悅,這種精神層面的努力在學(xué)術(shù)日益平面化、枯燥化的氛圍之中顯得尤其可貴。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他的文學(xué)批評看作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進(jìn)行文化價值重建的一次有益嘗試。
楊經(jīng)建的文學(xué)批評不僅具有可以感知的有血有肉的文本支撐和細(xì)讀,而且飽含深厚的社會文化底蘊(yùn)。他對文本的細(xì)讀與分析、感悟,為文學(xué)批評補(bǔ)充了來自細(xì)節(jié)的審美刺激和精神鼓動,它打開了研究者批評展開的感受力和心靈維度;而深厚的社會文化底蘊(yùn),則使他能夠超越一般文學(xué)批評的狹小天地,獲得思想力和觀察力的飛升。楊經(jīng)建將邏輯縝密、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術(shù)探究與人文精神的把握、評介融為一體,渾然天成,這種探索在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研究乃至知識分子身份確認(rèn)過程中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作者:龍其林單位:澳門大學(xué)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