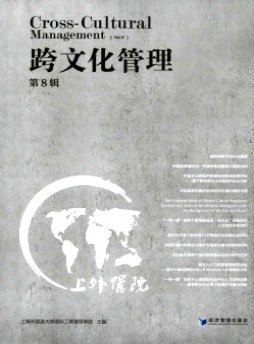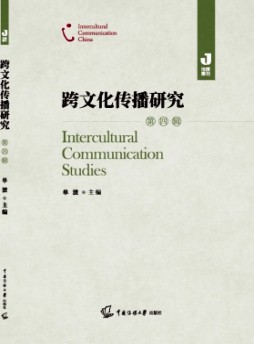跨文化對話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跨文化對話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日本著名學(xué)者伊藤虎丸先生的名著《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從探討亞洲不同于西方的近代(現(xiàn)代)性,或者說是從探討亞洲不同于西方的近代(現(xiàn)代)的獨特性的角度探討了魯迅的獨特價值,認(rèn)為魯迅的價值就在于他形成了一種“真正的個人主義”,即“個”的思想。這一思想主要是通過魯迅在日本留學(xué)而與西方近代相遇,特別是與尼采的個人主義相遇而形成的,并構(gòu)成了后來魯迅思想和文學(xué)的原型的“原魯迅”。魯迅1906年從仙臺來到東京從事《新生》文藝運動,所寫的幾篇評論奠定了后來魯迅的思想和文學(xué)的基本原型與框架。這的確是至論。不過伊藤虎丸的觀點仍然是建立在(西方)沖擊——(東方)回應(yīng)的框架上,雖然他強(qiáng)調(diào)了竹內(nèi)好先生提出的魯迅在接受西方文化時所堅持的“回心”/“抵抗”(堅守自我,與日本的“轉(zhuǎn)向”/成為一個“優(yōu)等生”相對)的文化態(tài)度,但是對于魯迅“個”的思想中主體所承傳的中國“固有文化血脈”仍然重視不夠;同時“西方”對于魯迅來說也是一個不斷擇取又不斷揚(yáng)棄,充滿多重復(fù)雜內(nèi)涵與向度的領(lǐng)域。也就是說,魯迅與西方近代的相遇經(jīng)歷了一個過程,這一過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接受西方(文化)與否定固有(文化)傳統(tǒng)的過程,而是一種復(fù)雜的中西跨文化的對話、交流、否定與融合的過程。正是在他對西方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雙重傳承與雙重超越中,才形成了這一“原魯迅”。
早在1898年魯迅到南京求學(xué)閱讀《天演論》時,他與西方近代的相遇便已經(jīng)開始了。自然與人類社會的“物競”、“天擇”,給他打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而“天道變化,不主故常”、“世道必進(jìn),后勝于今”的世界觀則使他開始沖破“天不變,道亦不變”循環(huán)的或輪回的歷史觀的束縛,從而逐步樹立起一種進(jìn)化論的世界觀;并且回應(yīng)著轟轟烈烈的變法維新思潮,把個人的郁積匯入到民族的郁積中,以一個“科學(xué)者”的形象投身于民族救亡與人民解放的時代大潮中。1902年到達(dá)日本后,無論是他于1903年開始在《浙江潮》上發(fā)表《中國地質(zhì)略論》、《說鉬》等科學(xué)論文和翻譯改寫法國儒勒·凡爾納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說,還是后來在宏文學(xué)院結(jié)業(yè)后,選擇醫(yī)學(xué)作為他的職業(yè),都是他的這一“科學(xué)者”志向的體現(xiàn)。然而魯迅并不是一個機(jī)械的唯科學(xué)(自然的進(jìn)化與物質(zhì)的進(jìn)步)主義者,他介紹這些科學(xué)知識的目的還在于使讀者“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bǔ)助文明……導(dǎo)中國人群以進(jìn)行”(P164)。也就是說他不是簡單地將自然科學(xué)作為一種知識來接受,而是同時作為一種倫理與思想來接受,已經(jīng)開始把科學(xué)知識與科學(xué)思想、自然現(xiàn)象與人類社會區(qū)別開來,在簡單的進(jìn)化決定論中看到了自然和社會進(jìn)步與演化中的復(fù)雜性。這樣一種獨特的文化視角與文化關(guān)懷,或許正印證了林毓生先生所說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重視“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P43)的傾向,也與當(dāng)時梁啟超所倡導(dǎo)的新民運動有關(guān)。
正是這種對自然與物質(zhì)的超越,使魯迅后來因著名的“幻燈片事件”而棄醫(yī)從文。1906年魯迅離開仙臺回到東京從事《新生》文藝運動。從仙臺到東京,不僅是魯迅從事文學(xué)事業(yè)的開始,而且標(biāo)志著從“科學(xué)者”魯迅向“文學(xué)者”魯迅的歷史的跨越,標(biāo)志著魯迅與西方相遇在揚(yáng)棄中的深化。在學(xué)習(xí)德文、俄文和哲學(xué)、歷史等學(xué)科的同時,魯迅博覽了大量的西方文學(xué)作品,特別是以英國拜倫為代表的摩羅詩人的作品和以德國施蒂納、尼采為代表的“新神思宗”哲學(xué)家的著作。正是受這些思想的影響,使“魯迅的進(jìn)化論,并不是把人類的歷史把握為人作為生物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過程,而是把握為作為‘人格’的人的精神的進(jìn)化過程”(P32)。雖然《新生》的流產(chǎn)給魯迅以“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P439)的悲哀。但是魯迅為這次文藝實踐所做的思考還是借《河南》雜志得到了一次噴發(fā)。他以“令飛”、“迅行”為筆名,發(fā)表了《人之歷史》、《科學(xué)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破惡聲論》等論文,展示了魯迅早期思想的深化。誠如伊藤虎丸所說:“這些文章是魯迅的文學(xué)原論,也是他青年思想的集成,從中已經(jīng)可以看出魯迅后來的思想框架。”(P8)
如果說《人之歷史》是前期科學(xué)思想的尾聲,那么《科學(xué)史教篇》則是從“科學(xué)與愛國”到文藝啟蒙的過渡。它不僅介紹和闡述了科學(xué)技術(shù)在改造自然和推動社會進(jìn)步方面的巨大作用,同時也指出了“所謂世界不直進(jìn),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萬狀,進(jìn)退久之而達(dá)水裔”(P28)的人類歷史演變規(guī)律;而且提出了“當(dāng)防社會入于偏”,如果“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xué),亦同趣于無有矣。故人群所當(dāng)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頓)已也,亦希詩人如狹斯丕爾(莎士比亞);不惟波爾,亦希畫師如洛菲羅(拉斐爾);既有康德,亦必有樂人如培得訶芬(貝多芬);既有達(dá)爾文,亦必有文人如嘉來勒(卡萊爾)。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見今日之文明者也”(P35)——已經(jīng)開始注意到實用科學(xué)(工具)理性對人性的扭曲,其結(jié)果不僅是造成人性的異化,科學(xué)也將被毀滅。因為在魯迅看來,科學(xué)本質(zhì)上是一種“人性之光”,并且“科學(xué)發(fā)見,常受超科學(xué)之力”,“本于圣覺”(靈感),“以知真理為惟一之儀的”。(P29-30)人類歷史上,精神與物質(zhì)的價值均有各自的適當(dāng)?shù)匚徊?yīng)相互平衡。因而面對“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shù)弗行”(P45)的所謂維新思潮,他特別批判了那些僅僅從表面拾西人(文明)牙慧的現(xiàn)象——“震他國之強(qiáng)大,栗然自危,興業(yè)振兵之說,日騰于口者,外狀固若成然覺矣,按其實則僅眩于當(dāng)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諦”(P33)。的確,如果僅僅考慮科學(xué)技術(shù)造成的經(jīng)濟(jì)與軍事實力,那就是并沒有得到西方科學(xué)思想的“真諦”。魯迅進(jìn)而對偏至的現(xiàn)代性的某些弊端進(jìn)行了反思與批判,其關(guān)注的中心話語已從“科學(xué)”轉(zhuǎn)向了“人”。
正是在以上的背景中,展開了魯迅以“立人”為中心的啟蒙思想綱領(lǐng)。在《文化偏至論》中,他以開闊的視野審視了(西方)人類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發(fā)展脈絡(luò),雖然“西方物質(zhì)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兩千余年之業(yè)績”,并且使“世界之情狀頓更,人民之事業(yè)益利”,但是如走向極端,片面地追求物質(zhì)功利,便會走向偏至。(P49)“諸凡事物,無不質(zhì)化,靈明日益虧蝕,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zhì)是趨,而主觀之內(nèi)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nèi),取其質(zhì),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jìn)步以停,于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于黯淡。”(P54)同樣,“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以法國大革命為頂點的歐洲“革命”,雖然掙脫了封建專制的束縛,但是走向極端,也會發(fā)生弊病。民主如果演變成“以多數(shù)臨天下而暴獨特者”(P49),就會變成新的專制;“平等”如果變成“夷隆實陷”,“使天下人人歸于一致”,就必然扼殺“個人特殊之性”,并降低社會發(fā)展水平,“精神益趨于固陋”。(P51-52)因而又有施蒂納、尼采等出來倡導(dǎo)“非物質(zhì)”、“重個人”的新神思宗學(xué)說出現(xiàn)。“知精神現(xiàn)象實人類生活之極顛,非發(fā)揮其輝光,于人生為無當(dāng);而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P55)所以“歐美之強(qiáng)”,其“根柢在人”(P58)。
以這樣一種“人學(xué)”視點,魯迅反觀了我國當(dāng)時的現(xiàn)代化方案,批判了唯西方物質(zhì)是趨的“輇才小慧之徒,于是競言武事”(金鐵/洋務(wù)論)傾向和惑言“眾治”的“制造商估立憲國會”(國會論)傾向,皆非“根本之圖”。(P46)前者正是洋務(wù)運動以來,僅僅眩惑于西方的強(qiáng)大而迷失于甲兵武器的物質(zhì)之中的洋務(wù)思潮。“雖兜牟深隱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祿之色,固灼然現(xiàn)于外矣!”(P46)而后者則是以康梁為代表的立憲國會的維新思潮。雖然康梁所倡導(dǎo)的立憲國會不失為中國走向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一種形式,但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由于封建宗法專制秩序及其意識形態(tài)的長期禁錮,缺乏西方在市場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上的個人主義思想的洗禮[“個人一語,入中國未三四年,號稱識時之士,多引以為大詬,茍被其謚,與民賊同。”(P51)],因而這種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很容易演變成“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制乃尤烈于暴君”(P46)的惡劣傾向。雖然如前所述,魯迅對國民性的思考和“立人”的思想都受到梁啟超“新民”說的影響,但是梁啟超所倡導(dǎo)的新民運動核心在于建構(gòu)現(xiàn)代國民的意識,而這種意識是以個人對于群體、國家、民族的義務(wù)的國民公德為本位的,也就是他所說的“自由云者,團(tuán)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P223)。而沒有個人之自由的自由,一方面會壓抑堅守獨立的個體的創(chuàng)造性,降低社會發(fā)展水平;另一方面則可能造成一種披著“民主”外衣的新形式的專制與極權(quán),因而只能是一種偽自由。“凡個人者,即社會之一分子,夷隆實陷,是為指歸,使天下人人歸于一致,社會之內(nèi),蕩無高卑。此其為理想誠美矣,顧于個人殊特之性,視之蔑如,既不加之別分,且欲致之滅絕。更舉黮暗,則流弊所至,將使文化之純粹者,精神益趨于固陋,頹波日逝,纖屑靡存焉。蓋所謂平社會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進(jìn)步水平以下。況人群之內(nèi),明哲非多,傖俗橫行,浩不可御,風(fēng)潮剝蝕,全體以淪于凡庸。非超越塵埃,解脫人事,或愚屯罔識,惟眾是從者,其能緘口而無言乎?”(P51-52)“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于興國究何與焉。”(P47)(辛亥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及其黑暗現(xiàn)實無疑印證了魯迅的判斷)——魯迅對梁啟超的超越,實際上是對一個時代的超越,誠如他在《文化偏至論》中引用尼采的話所說,“吾見放于父母之邦矣”(P50)。這種超前性既是他當(dāng)時倡導(dǎo)《新生》文藝運動流產(chǎn)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他五四時期崛起吶喊,就能橫空出世、磅礴古今的一個重要原因。
魯迅進(jìn)而提出了他的救國方案:“誠若為今立計,所當(dāng)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人既發(fā)揚(yáng)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P47)“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wù),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shù),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P58)“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zhuǎn)為人國。”(P57)“人”成為了魯迅思考的中心,而“立人”,也就是喚醒國人的覺悟,改造和提升他們的精神,促進(jìn)現(xiàn)代“個”體的自覺生成才是推進(jìn)民族現(xiàn)代進(jìn)程,建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關(guān)鍵[所謂“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P26)]。所以,這一時期,魯迅的文字中常常出現(xiàn)“個”、“個體”、“個人”、“己”、“自”、“自我”、“自性”、“獨”等概念。而“立人”的核心就是要確立個體的自主性與精神自由,也就是“聲發(fā)自心,朕歸于我”(P26),從各種束縛自我的“他者”的陰影中解放出來,從而擺脫被他者(天下/國家、社會、種族/民族、家族、父母、兄長、他人,等等)的奴役而進(jìn)入自我生命的自由狀態(tài)[“而人自始有己”(P26)]。對于中國社會來說,這更是走向歷史解放的第一步。
這一“個”的思想固然更多地來源于以尼采為代表的新神思宗的啟迪,但是盧卡契在談到世界文學(xué)的相互影響時曾經(jīng)指出:“任何一個真正深刻重大的影響是不可能由任何外國文學(xué)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關(guān)國家同時存在著一個極為類似的文學(xué)傾向——至少是潛在的傾向。這種潛在的傾向促成外國影響的成熟。因為真正的影響永遠(yuǎn)是一種潛力的解放。”(P452)文學(xué)是這樣,思想文化的相互影響也應(yīng)該是這樣。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便明確提出他立論的前提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nèi)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fù)古,別立新宗。”(P57)雖然魯迅在文章中主要是從“洞達(dá)世界之大勢,權(quán)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P59)而立論,對于“內(nèi)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未能詳盡展開,但是僅僅從魯迅這一時期文章中多使用的“自”、“自性”、“獨”等概念,我們便不難發(fā)現(xiàn),與他這時期所師從的章太炎所倡導(dǎo)的“依自不依他”的“自識宗”有一種前后相續(xù)的繼承關(guān)系。同時魯迅在遠(yuǎn)赴南京求學(xué)之前便已經(jīng)在故鄉(xiāng)紹興接受了固有文化血脈的熏陶。雖然在魯迅看來,中國文化的正統(tǒng)和主流是一種非個人的文化,“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擾亂)……有人攖人,或有人得攖者,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孫王千萬世,無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攖我,或有能攖人者,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寧蜷伏墮落而惡進(jìn)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P70)。“老子書五千語,要在不攖人心;以不攖人心故,則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無為之治;以無為之為化社會,而世即于太平”(P69)。一切平和,沉靜如死水。從而“本根剝喪,神氣旁皇”,“心奪于人,信不繇己”,“舉天下無違言,寂漠為政,天地閉矣”。(P25)因而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更主要的是熱情地介紹了西方從英國拜倫、雪萊,俄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到匈牙利的裴多菲等“摩羅詩人”——精神界之戰(zhàn)士,“起國人新生”,以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他還和周作人一起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
然而我們又必須看到,任何文化傳統(tǒng)都絕不是單純凝固的存在物,而是流動的、變化的、發(fā)展的、多元多向的。這不僅因為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新的成分加入(如中古時期的佛教、近代的西方文化),改變著它既有的秩序與結(jié)構(gòu);而且傳統(tǒng)本身也是包容多種因素和多元內(nèi)涵的矛盾綜合體,并且正是這種復(fù)雜的對立統(tǒng)一的矛盾運動推動著它的發(fā)展。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內(nèi)部也始終洶涌著一股追求民主與個性解放的異端文化思潮。魯迅“個”的思想也潛在地承繼著這一文化的血脈。中華文化是由多民族的文化融合而成的。在它遠(yuǎn)古的血液中流淌著來自東南沿海、更多受到海洋文化影響的越文化的因素。后來這種文化向度便作為一種“文化基因”而流淌在以江南為中心的越文化的涌流中,形成了一種不輕信、不盲從、反奴役、勇于質(zhì)疑、探索和創(chuàng)新的特立獨行的異端思想傳統(tǒng)。東漢時期的王充可稱是這一異端思潮的杰出代表,面對董仲舒所代表的天人感應(yīng)論、流行的讖緯學(xué)說及迷信觀念,他大膽地提出“嫉虛枉”的現(xiàn)實批判思想,并且在《問孔》、《刺孟》、《劈韓》等篇章中對先秦諸子也表現(xiàn)出了獨立思考與探索的理性精神。正是這一精神“下開魏晉。魏晉人在中國思想史上之獨特貢獻(xiàn),正為其能繼承王充,對鄒、董一派天人相應(yīng),五行生克,及神化圣人等跡近宗教的思想,再加以一番徹底的澄清”(P118)。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9](P30),“越名教而任自然”[10](P83),“剛腸嫉惡,輕肆直言”[9](P39),可以說是這一叛逆精神又一次的集中噴發(fā)。而特別是孕育了明清浪漫洪流的一代心學(xué)宗師王陽明所謂的“心即理”,“心外無理”的命題,開始將人們的思維本體從外在的理轉(zhuǎn)移到內(nèi)在的心上來,從而為沖破“滅人欲”的天理的束縛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武器與力量。應(yīng)和著當(dāng)時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市民社會的崛起,王學(xué)左派——泰州學(xué)派和李贄更是明確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11](P4)和“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12](P544),倡導(dǎo)“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12](P1),“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11](P97)。“非圣無法”,“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異位”。[13](P702)——實在是開啟了中國近代啟蒙思想的先河。雖然這一思想脈絡(luò)在滿清入主中原后遭到各個方面的非議與排擠,但是卻以各種變異的形式傳承了下來。從明清之際破天荒提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14](P2)的黃宗羲,到戴震對宋明禮教的控訴:“其所謂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15](P174)再到有清一代“但開風(fēng)氣不為師”的龔自珍、主張“六經(jīng)皆史”的章學(xué)誠和“自我橫沖的獨行孤見”(侯外廬語)的章太炎,幾乎構(gòu)成了一個前后貫通的精神譜系。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個”的思想與這一思想譜系的精神聯(lián)系。據(jù)周作人介紹,在他們家的藏書中,便包括了《王陽明全集》、《章氏遺書》(即《文史通義》)等書[16](P64),在祖父對子弟“自由讀書”的鼓勵下,喜愛廣泛閱讀的魯迅無疑也受到過這些思想的熏染。而他在“三味書屋”學(xué)習(xí)時的老師壽鏡吾先生也很喜愛魏晉文章而憎厭《近思錄》等程朱理學(xué)。[16](P126)或許正是這些影響使魯迅“決不跟著正宗派去跑,他不佩服唐朝的韓文公(韓愈),尤其是反對宋朝的朱文公(朱熹)”[16](P429)。實際上,這種異端思想傳統(tǒng)不僅僅在學(xué)術(shù)精英的思想間嬗變傳遞,也彌漫在民間,在下層知識分子乃至民眾中形成一種普遍的風(fēng)氣:“逆于時趨”,“辯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17](P332)即使社會底層如“土谷祠”的阿Q,對于未莊人普遍尊敬的“文童的爹爹”的趙太爺、錢太爺之流,也“在精神上獨不表格外的崇奉”。(《阿Q正傳》)所以在這樣一種文化搖籃中成長起來的魯迅“對于古來文化有一個特別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統(tǒng)’的東西,他都不看重,卻是另外去尋找出有價值的作品來看”[16](P435)。正是這種對個性自由的認(rèn)同與向往,對奴役和壓迫的厭惡與反抗,使他承接了中國民族文化傳統(tǒng)中爭取人的解放、反抗專制與精神奴役的思想血脈,并且在尼采等新神思宗的“個人主義”思想中獲得了共鳴與深化。所以我們反對簡單地將傳統(tǒng)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肯定與否定,必須看到它的復(fù)雜性與多樣性,魯迅之所以接受了西方以尼采為代表的新神思宗為代表的“個”的思想,是與我們文化傳統(tǒng)本身涌流著的這一思想暗流相應(yīng)合的。也可以說是在西方“個”的思想的啟迪下,才有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新構(gòu)造。雖然魯迅當(dāng)時還來不及對這一文化血脈進(jìn)行系統(tǒng)的理性梳理,但是在他后來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例如《狂人日記》中與“吃人的人”相對的“真的人”,與李贄的“童心說”所追求的“絕假純真”貫通著一種精神聯(lián)系;而在魯迅所塑造的“狂人家族”的形象譜系(如《長明燈》中的“瘋子”、《孤獨者》中的“魏連殳”等)中,也涌流著李贄等的狂悖之氣和“剛健不撓,飽誠守真”(P101)的摩羅詩人的精神血脈。在這種重新構(gòu)造中,魯迅在他的“原論”中還多次提到對遠(yuǎn)古先民(“樸素之民”)或“氣秉未失之農(nóng)人”之“白心”、“素心”的尋覓,以期重建民族文化的主體,也構(gòu)成了魯迅主體文化結(jié)構(gòu)的一個重要方面。伊藤先生已作了很好的闡述,限于篇幅,這里就不贅述了。當(dāng)然,從另外一種視角看,我們也可以說,魯迅“個”的思想是對“不攖人心”的傳統(tǒng)文化和“崇物質(zhì)”、“尚眾數(shù)”的西方偏至文化的超越。正是在這樣一種雙重傳承與雙重超越的跨文化的對話中誕生了“原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