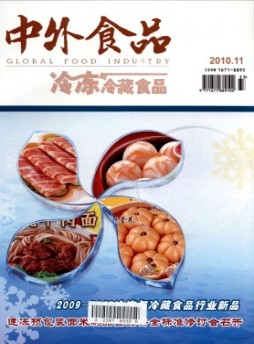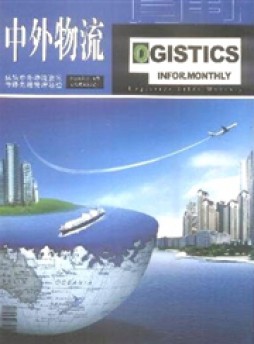中外體育文化傳播交流中的異化問題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中外體育文化傳播交流中的異化問題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采用批評話語分析方法,以中泰綜合格斗賽的中文媒體報(bào)道文本為素材,闡釋了中外體育文化尤其是武術(shù)和泰拳文化交流傳播的異化問題。研究認(rèn)為,將商業(yè)性綜合格斗賽上升為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對抗,能夠通過國族象征等層面使得觀眾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身份認(rèn)同感,且賽事中關(guān)于運(yùn)動員、賽制等充滿話題性的文本,亦能獲得更大的關(guān)注度。但實(shí)際上,一些虛假的“中華民族被挑釁”和“抵御外侮”言論被消費(fèi),而中外體育交流中的技戰(zhàn)術(shù)層面的美學(xué)價(jià)值并未得到有效挖掘,武術(shù)文化與泰拳文化交流所蘊(yùn)含的積極意義也被忽略。
關(guān)鍵詞:體育傳播;體育新聞;文化交流;民族認(rèn)同;異化
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體育文化傳播與媒介技術(shù)形態(tài)愈發(fā)多元化、動態(tài)化。體育媒介和體育傳播多樣化的結(jié)果,讓體育傳播傳遞出積極價(jià)值,但也呈現(xiàn)出娛樂化和媚俗化的導(dǎo)向,導(dǎo)致公共倫理、社會素養(yǎng)和游戲精神的消弭。這其中涉及到體育媒介與民族認(rèn)同的研究,是政治學(xué)、社會學(xué)和新聞傳播學(xué)等學(xué)科交叉形成的新的重要研究領(lǐng)域[1]。諸如奧運(yùn)火炬?zhèn)鬟f遭襲、劉翔退賽等大部分引起“圍觀”的體育新聞事件都裹挾著商業(yè)利益的炒作,但其迎合大眾何種心理需求,如何界定輿論關(guān)切和群體情緒宣泄的社會背景、如何厘清體育媒體文本和潛話語之所指,如何歸正體育賽事的惡意炒作及其宣傳信息的虛假夸大等問題都值得思考與探討。對類似體育傳播異化問題的認(rèn)識,不僅對中泰兩國文化友好交流十分重要,對中華傳統(tǒng)體育的跨文化傳播亦具有借鑒意義。基于此,本研究以“昆侖決”、“武林風(fēng)”等商業(yè)拳擊聯(lián)盟舉行的中泰綜合格斗競技項(xiàng)目相關(guān)新聞報(bào)道和社評為素材,采用批評話語分析方法[2],對上述媒體文本和訊息中所包含的身份認(rèn)同以及民族意識進(jìn)行了解讀,并闡釋了中泰體育文化———尤其是武術(shù)文化和泰拳文化交流傳播的異化問題。本研究所取文本對象來自新華社、人民日報(bào)和中國日報(bào)等傳統(tǒng)媒體,還包括新浪體育、騰訊體育等新媒體。
1中泰體育文化傳播的批評話語分析
跨文化傳播研究領(lǐng)域主要包括不同文化間的傳播(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多文化間傳播(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國際傳播等范疇[3]。成功的體育文化國際傳播都是主動調(diào)適自己以適應(yīng)外部環(huán)境的結(jié)果。強(qiáng)有力的推動者能夠促進(jìn)體育文化國際傳播,體育文化國際傳播有必要充分利用國際舞臺的影響力[4]。中泰體育交流是兩國文化與社會交往中的重要內(nèi)容,最早可以追溯至1921年,中華總商會籌辦中泰高手比武,上海精武會教練陳子正與泰國拳師乃央相互切磋技藝。2015年是新中國與泰國建交40周年,泰國在中國舉辦40場系列慶典活動,拳王爭霸賽、KO爭霸賽、正宗泰拳賽等綜合格斗類賽事,都是兩國建交慶典活動的組成部分,這些賽事不僅吸引了體育迷的關(guān)注,還形成了階段性的媒體聚焦。其中,2009年12月中泰搏擊爭霸賽的相關(guān)新聞報(bào)道和評論,不僅在網(wǎng)絡(luò)媒體和社交平臺廣為流傳,還被全國多地傳統(tǒng)媒體轉(zhuǎn)載。
1.1“搏擊即戰(zhàn)爭”的批評話語分析
這些比賽通常以“中國功夫vs.泰國泰拳”作為體育新聞的關(guān)鍵詞進(jìn)行編碼,而在國際體育文化跨國傳播中,部分國內(nèi)媒體報(bào)道會利用國家主義、民族認(rèn)同等方面的潛話語,來幫助新聞報(bào)道或評論獲得更多的關(guān)注。以2015年新聞報(bào)道為例:“中泰拳王K-O爭霸賽落下帷幕,中國隊(duì)以8:0全勝泰國隊(duì)。最近,應(yīng)世界職業(yè)泰拳聯(lián)盟的要求和賽事組委會提議,中泰雙方代表約定于7月5日再戰(zhàn)廣州,屆時(shí)泰國將派出更具實(shí)力選手‘一雪前恥’……在新聞會上,中泰雙方代表舉行了戰(zhàn)書簽約儀式。”可以看出,“中泰對決”、“戰(zhàn)書”、“再戰(zhàn)”等文本,將中泰綜合格斗賽事演繹成為一場“虛擬”或“微縮”的戰(zhàn)爭,這種文本的編碼充分展現(xiàn)了搏擊的特征———強(qiáng)烈的對抗性和斗爭性。被譽(yù)為“西方兵圣”的德國軍事理論家、軍事歷史學(xué)家克勞賽維茨曾經(jīng)闡釋“搏擊與戰(zhàn)爭”的關(guān)系:“我不打算一開始就給戰(zhàn)爭下一個(gè)冗長的政論式的定義,只打算談戰(zhàn)爭的要素———搏斗。戰(zhàn)爭無非是擴(kuò)大了的搏斗。如果我們想要把構(gòu)成戰(zhàn)爭的無數(shù)個(gè)搏斗作為一個(gè)統(tǒng)一體來考慮,那么最好想象一下兩個(gè)人搏斗的情況。每一方都力圖用體力迫使對方服從自己的意志;它們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對方,使對方不能做任何的抵抗。因此,戰(zhàn)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5]搏擊作為一種運(yùn)動項(xiàng)目,在競技過程中能夠充分模擬出戰(zhàn)爭的各種要素,可以稱之為“一種擬態(tài)的戰(zhàn)爭”。雖然兩者都追求勝利,但戰(zhàn)爭強(qiáng)調(diào)“對抗”與“結(jié)果”,體育則強(qiáng)調(diào)“交流”與“過程”,這也是兩者本質(zhì)的區(qū)別。綜合格斗比賽本質(zhì)上是具有交流技藝、商業(yè)展演性質(zhì)的體育賽事,將其等同于“模擬戰(zhàn)爭”并不恰當(dāng)。例如“武術(shù)”、“功夫”、“泰拳”等代表著各自文化傳統(tǒng)的符號,都被借用來闡釋民族間的沖突和對抗,在上文相關(guān)報(bào)道中,泰拳運(yùn)動員被構(gòu)建成一個(gè)想象的“入侵者”,并在搏擊賽事中成為“戰(zhàn)爭”的主導(dǎo)者———此外,從“泰拳最強(qiáng)五天王組團(tuán)向中國武林挑戰(zhàn)”、“泰拳王叫囂秒殺中國功夫中泰爭霸戰(zhàn)重慶擺擂”、“泰拳王嘲諷少林要在李小龍故鄉(xiāng)打敗中國”、“泰拳白蓮斬來華復(fù)仇威風(fēng)少俠領(lǐng)銜昆侖決”等新聞的標(biāo)題中,都可以看出,中方隊(duì)員、泰方隊(duì)員通常被新聞文本分別建構(gòu)成“防守者”和“進(jìn)攻者”的角色。
1.2“我弱敵強(qiáng)”的批評話語分析
在文化學(xué)層面上看,無論是中華武術(shù)還是泰國拳術(shù),都具有濃厚的人文精神,以制服對手為主,護(hù)人護(hù)己。但泰拳的文化理念還具有一種“用強(qiáng)烈的取勝欲望換取生存權(quán)利”的意識,即便致殘、致死亦被早期的賽場文化所默許[6]。這一點(diǎn)在具體技術(shù)上也有所顯示,劉創(chuàng)、鄭國華、黃文英(2010)通過信息技術(shù)研究了第5屆國際武術(shù)搏擊王爭霸賽,對武術(shù)和泰拳的技術(shù)進(jìn)行比較分析,結(jié)果顯示中國武術(shù)在腿法、拳法和組合動作中優(yōu)勢明顯。泰拳在摔法、膝/肘技術(shù)中優(yōu)勢明顯。而在國際拳擊賽場,膝/肘技術(shù)通常被認(rèn)為具有較大的危險(xiǎn)性[7]。中文媒體文本會強(qiáng)調(diào)外來挑戰(zhàn)者的強(qiáng)大,如采用泰拳規(guī)則,讓泰拳成為進(jìn)攻方,或者說是占利者(至少是規(guī)則的占利者)。這種中方隊(duì)員處于下風(fēng)、“以弱打強(qiáng)”、但依然“斗志昂揚(yáng)”的狀況,與我國近代史的被動戰(zhàn)爭狀況不無二致。報(bào)道文本描繪的中方隊(duì)員所處場景,并隱含賽事是在一場“非公平競爭”的情況下展開的,能夠獲得長期受到屈辱歷史教育的觀眾認(rèn)同,實(shí)現(xiàn)球迷、運(yùn)動員之間的共情。此外,媒體文本還嘗試附加給泰拳選手更多的“強(qiáng)勢”,譬如“泰拳王雅桑克萊說:中國功夫與泰拳,就象是蚊子與大象打架,蚊子專門抓住大象的弱點(diǎn)———不與大象直接對抗,專門往大象身上叮,只要大象身上一動,蚊子就跑了,這是弱者的表現(xiàn)。雖然大象打不著蚊子,但畢竟蚊子還是弱者……”(新浪體育,2014年08月15日)。這其中,“蚊子”和“大象”的比喻,明顯帶有對抗性質(zhì),而且充滿了歧視意味,這種由媒體自造的報(bào)道文本,不僅對泰拳文化進(jìn)行了構(gòu)陷,而且解構(gòu)掉了泰拳選手的運(yùn)動家精神。
1.3文本構(gòu)建“身份認(rèn)同”的批評話語分析
認(rèn)同(Identity)是一個(gè)反思性的自我意識概念,是“對模式無區(qū)別于其他所有事物的認(rèn)可,這包括在其自身統(tǒng)一性中的所有內(nèi)部變化和多樣性。該事物被視為保持相同或具有相同”。認(rèn)同是生成性的、歷史性的,是社會互動的產(chǎn)物,人們通過社會交往,對自己的地位、形象、角色、他者關(guān)系等進(jìn)行明確判定。隨著社會交往“差序”漣漪,自我認(rèn)同逐漸上升到群體認(rèn)同、民族認(rèn)同或國家認(rèn)同,進(jìn)而形成自我意識、集體意識、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8]。“外來挑戰(zhàn)者”———泰國泰拳選手強(qiáng)大并進(jìn)攻性十足,“防守者”中國搏擊運(yùn)動員處于劣勢但“斗志昂揚(yáng)”并且敢于“硬碰硬”地對戰(zhàn),可以明顯地看出嫁接中華民族近代歷史進(jìn)程的痕跡。這種嫁接一方面引發(fā)觀眾的危機(jī)感、焦慮與創(chuàng)傷,使得觀眾的情緒處于積極與敏感的位置,并試圖誘導(dǎo)其通過購票觀看中方選手取勝,來滿足國家與民族認(rèn)同感,平復(fù)個(gè)人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這種嫁接將中泰搏擊對抗作為“近現(xiàn)代中國戰(zhàn)爭史”的重新演繹———擂臺成為戰(zhàn)場,運(yùn)動員代表國家,鼓勵(lì)新聞傳播信息的接收者前來觀看一場“擬劇化”的表演。這些錯(cuò)誤的信息通過臆想的重新拼貼,形成了新的敘事空間。約翰•菲斯克認(rèn)為在這個(gè)傳播框架中,個(gè)人、民族與民族被緊緊聯(lián)結(jié)在一起,抽象的文化皈依被納入到這場濃縮的儀式(RitualCondensation)中[9]。“……在全場觀眾山呼海嘯般的助威聲中,楊建平以矯健的身姿飛身躍過圍繩,登上擂臺,引起現(xiàn)場觀眾又一次分貝更高的喝彩聲…‘中華戰(zhàn)虎’榮歸故里,不負(fù)眾望,再度以一場蕩氣回腸的‘完美絕殺’盡情演繹中國武術(shù)源遠(yuǎn)流長的俠者風(fēng)范…”但“所有的符號都是不好的符號”[10],這種新的象征物或符號將體育傳播的客體、主體都感染成另外一種傳播非善的客體與主體,并進(jìn)行重新編碼和敘事,惡、對抗、戰(zhàn)爭和“文化優(yōu)劣論”成為新的敘事空間中的關(guān)鍵詞。例如“昆侖決”搏擊商業(yè)組織的定位,十分明顯地揭示了這種重新編碼過的、新的敘事:“……對于一個(gè)國家和民族而言,尚武意識往往是實(shí)現(xiàn)國家意志、凈化民族品質(zhì)的有力武器。因此,尚武意識的強(qiáng)弱,也就成了衡量民族興衰成敗的重要指數(shù)。然而,自明清以降,尚武之風(fēng)漸弱,文弱奢華之氣上行,以致社會靡靡無向上奮發(fā)之力。到了近代,更是受制于以前來華拜服的‘夷狄’,列強(qiáng)欺凌,大片河山更是淪于日本鐵蹄之下長達(dá)八年之久,究其原因就是武風(fēng)不勝,文弱化的中國猶若破碎的玩偶只能任人擺布…正是一代代國人秉承尚武精神,挺起中華民族的脊梁,我們的民族才得以重新站立,國家才得以重新富強(qiáng)。然而,安逸使人忘憂,三十余年的國富民安使得國人忘記了尚武以自強(qiáng),精武以內(nèi)剛……”
2“國族象征”外衣的商業(yè)展演與國族象征失魅危險(xiǎn)
觀賞競技體育具有情緒和情感宣泄的功能。我國職業(yè)體育的觀眾并不滿足于從激烈的身體對抗中獲得一定的美感,體驗(yàn)像觀看電影、戲劇一樣的陶醉感,而是將民族意識、地域意識和個(gè)人意識作為出發(fā)點(diǎn),尋求一種勝利或失敗的刺激。并在觀賽的緊張與松弛、狂歡與悲憤中,宣泄過剩的精力,重塑心理秩序。綜合國力尚未強(qiáng)盛的國家,急于從競技體育中尋覓突破口,是個(gè)體或社會在多元競爭力上的目標(biāo)偏移,借以實(shí)現(xiàn)自身競爭力的強(qiáng)大,祛除自卑感和弱小感[11]。無論被動參與或主觀惡意,新聞媒介為了擴(kuò)大自身的影響力,扭曲事件本身所蘊(yùn)涵的積極作用,改弦易轍,將更吸引注意力的“壞新聞”作為主要賣點(diǎn),這種報(bào)道基調(diào)將消弭體育文化跨國傳播中的賽場表現(xiàn)、競賽精神和體育倫理。從體育傳播的背景上來講,賽事轉(zhuǎn)播報(bào)道并不是體育新聞傳播的唯一內(nèi)容,但它卻一直是大部分體育報(bào)道的最基礎(chǔ)的內(nèi)容。體育傳播首先以競技體育的賽事信息傳達(dá)為主,著力體現(xiàn)經(jīng)濟(jì)體育的“力與美”之本質(zhì)[12]。由于我國目前的搏擊競技賽事,既沒有西方職業(yè)拳擊的流暢感,也無自由搏擊的肉搏畫面,更缺乏西方職業(yè)摔跤手的身體魅力,亦無鐵籠搏擊賽的極端嗜血性、暴力性和殘忍性刺激,這樣的比賽由于缺少和諧化、舞蹈化、自然神教化的國學(xué)文化支撐,顯得觀賞性缺失[13]。通常認(rèn)為,體育在國家認(rèn)同形成與強(qiáng)化中的正面作用是,通過體育比賽展示國家的優(yōu)越地位,增強(qiáng)國民的凝聚力;利用體育來尋求認(rèn)同和合法性;提高公民的認(rèn)同感、歸屬感、團(tuán)結(jié)感[14]。消極作用則表現(xiàn)為過度將民族悲愴情感和民族振興寄托在一場賽事的勝負(fù)之上,難以培養(yǎng)真正的運(yùn)動球迷,形成現(xiàn)代化、商業(yè)化的職業(yè)體育模式[15]。體育賽場根本不需要國家榮耀、民族氣節(jié)和文化優(yōu)越性彰顯之沉重,需要的僅僅是對體育比賽本身的欣賞和對選手個(gè)人魅力的崇拜。在經(jīng)歷民族精神蕩滌、移位、毀壞后的治療性、安撫性和重建性程序之后,中國將會表現(xiàn)出對競技成績理性而淡然的態(tài)度,成為更具游戲精神、生活情趣與審美能力的中國人。中國體育應(yīng)該從展示“頑強(qiáng)拼搏、敢于超越自我、挑戰(zhàn)強(qiáng)手的良好的精神風(fēng)貌和自信、自強(qiáng)的民族精神”,轉(zhuǎn)向納入“親和、開放、寬容、友善”等新元素,重新塑造友好交往的態(tài)度、并回到對運(yùn)動員競技技術(shù)本身的關(guān)注上[16]。尤其是對綜合格斗類搏擊比賽來講,其技戰(zhàn)術(shù)精彩與否,這是最簡單、最直接也是最本質(zhì)的理解方式,不應(yīng)賦予其太多特殊的含義。
3亟待重塑體育文化附魅的中外搏擊賽事
文化和種族再無優(yōu)劣之分,所有的體育運(yùn)動也都無需扮演在19世紀(jì)末和20世紀(jì)初的角色———戰(zhàn)爭的替代品———進(jìn)行區(qū)域文化生態(tài)侵略(EcologicalInva-sion)以及彰顯霸權(quán),擾亂了正常與友好交流的宗旨,把賽事變成民族情緒宣泄的工具。將自己的文化看做是“理所當(dāng)然的”,在其他群體、種族、民族和文化面前充滿優(yōu)越感,并對異文化充滿歧視與敵意。這種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思想,為不同體育文化間交流的帶來嚴(yán)重障礙[17]。“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guān)系。尤其是在文化場域,強(qiáng)調(diào)“文化的沖突”、“自我中心論”或“主—客”模式,都不合時(shí)宜。正如巴赫金(1998)所揭示的,尊重差異性、理解差異性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對話,才能將走向割裂的、浮于表層的中泰體育文化交流推向更深層次:“我們給別人的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來的新問題,我們在別人文化中尋找我們的問題的新解釋。”只有這種“外位性”,能夠讓雙方在對話和交鋒中彰顯自己的深層次底蘊(yùn),也能讓不同的文化在對話和交鋒中相互得到豐富與充實(shí)[18]。在社會轉(zhuǎn)型期,無論是媒體事件還是文化沖突,都能在短時(shí)間內(nèi)激化情緒,引發(fā)輿論效應(yīng),這種傳播機(jī)制出于利益目的被商業(yè)機(jī)構(gòu)運(yùn)用,成為事件擴(kuò)大化的推手。事件本身所蘊(yùn)涵的積極社會價(jià)值被忽略[19]。體育文化傳播中,需要規(guī)避剛性廣告的弊端、放棄惡意營銷的思維,在塑造良好印象和公共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促進(jìn)正態(tài)、積極中外文化交流模式的形成[20]。同時(shí),公共關(guān)系在體育組織中比其他任何領(lǐng)域中更重要,體育被賦予了強(qiáng)烈的公共利益和媒體利益,許多細(xì)微的問題在體育領(lǐng)域完全可能成為危機(jī)。中泰綜合格斗類賽事本身具有文化體驗(yàn)的性質(zhì),比賽本身承載著雙邊交流、培養(yǎng)觀眾公民意識和休閑生活方式的責(zé)任。此外,體育新聞媒介還需對自身主導(dǎo)的傳播內(nèi)容和效果進(jìn)行技術(shù)和價(jià)值觀升級,在中泰體育交流乃至體育文化國際傳播中發(fā)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xiàn):
[1]董進(jìn)霞,陸地,李璐玚.全球化世界中的體育與國家認(rèn)同、倫敦奧運(yùn)及女子體育———國際體育社會學(xué)協(xié)會主席Pike女士、副主席Jackson先生學(xué)術(shù)訪談錄[J].體育與科學(xué),2014(1):86-90,96.
[3]陳國明.跨文化交際學(xué)[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9:12.
[4]史友寬.體育文化國際傳播的實(shí)踐考察與理念探索[D].鄭州:河南大學(xué)博士研究生論文,2013.
[5]克勞賽維茨.戰(zhàn)爭論[M].盛峰峻,譯.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14:3-4.
[6]靳衛(wèi)平,馮幼軍,錢茹.中泰武術(shù)格斗理念比較研究[J].體育文化導(dǎo)刊,2012(1):107-110.
[7]劉創(chuàng),鄭國華,黃文英.“第5屆國際武術(shù)搏擊王爭霸賽”中、泰技術(shù)分析[J].中國體育科技,2010(5):74-77.
[8]葉虎.大眾文化與媒介傳播[M].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2008:340-364.
[9]約翰•菲斯克.關(guān)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詞典[M].李彬,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245.
[10]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M].楊德睿,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195-230.
[11]路云亭.重估中國體育傳播的文化價(jià)值[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3:前言.
[12]王大中,杜紙紅,陳鵬.體育傳播———運(yùn)動、媒介與社會[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xué)出版社,2006:115.
[13]路云亭.武術(shù)的異化———央視《武林大會》對原生態(tài)武術(shù)文化的拯救[J].搏擊:武術(shù)科學(xué),2013(3):1-4,9.
[14]易劍東.體育媒體公關(guān):美國經(jīng)驗(yàn)與中國借鑒[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4:19.
[15]潘一禾.超越文化差異:跨文化交流的案例與探討[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1:125.
[16]李春華,劉紅霞.媒介體育與國家認(rèn)同———國外相關(guān)研究綜述[J].北京體育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7(4):467-469.
[17]趙均,許婕.全球主義、國家主義與中國競技體育[J].體育學(xué)刊,2009(3):15-18.
[18]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M].白春仁,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70-371.
[19]方潔.被裹挾與被規(guī)制:從新媒體與大眾媒體的框架建構(gòu)看新媒介事件的消解[J].國際新聞界,2014(11):6-18.
[20]斯托爾特,迪特莫,布蘭韋爾.體育公共關(guān)系———組織傳播管理[M].易劍東,王曉禹,謝敏,譯.沈陽:遼寧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08.
作者:任慧濤1;陳穎2;張俊濤3 單位:1.泉州師范學(xué)院,2.華僑大學(xué)體育學(xué)院,3.福建師范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