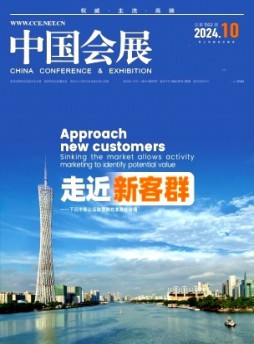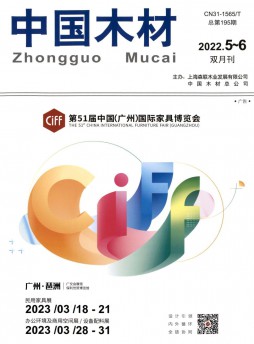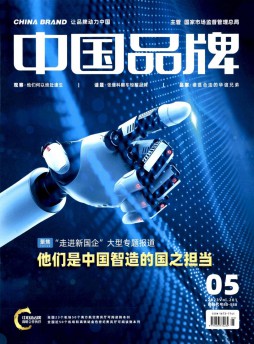中國生肖起源與演變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生肖起源與演變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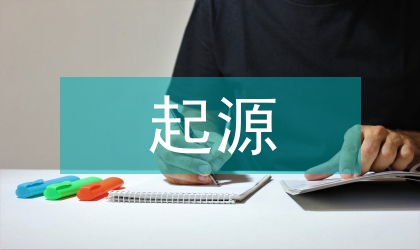
十二生肖是記人的生年屬相的,亦稱十二屬相,用以紀年、紀月、紀日或紀時辰時,則稱十二獸歷。十二生肖(獸歷)廣泛流行于亞洲諸民族及東歐和北非的某些國家之中,幾乎是一個具有世界性的民俗事象。
十二生肖(獸歷)的構成及順序,各個民族或國家不盡相同。現今漢、回、藏、哈尼、畬、拉祜、納西、阿爾泰語系諸民族以及朝鮮、韓國、日本的十二生肖(獸歷),在構成及順序上完全一致,為: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豬。有些民族的十二生肖(獸歷)因地區不同而有別,如黎族大多數地區的十二生肖(獸歷)與前相同,而毛道黎族則以“蟲”代“虎”,以“貓”代“兔”,以“魚”代“蛇”,以“肉”代“馬”,以“人”代“羊”;大部分地區彝族的十二生肖(獸歷)與前相同,而云南哀牢山彝族的十二生肖(獸歷)名稱及順序為:虎、兔、穿山甲(龍)、蛇、馬、羊、猴、雞、狗、豬、鼠、牛。除有一處不同(現也有以“龍”代“穿山甲”的說法)外,排序亦與前有異。哀牢山彝族之所以以“虎”為先,據說是因為其自認為是虎的子孫,尊母虎為其始相。每三年舉行一次的祭神大典,要選在虎月(首月)的第一個虎日,在當地的母虎神廟舉行。家家門上且都要繪以虎形,以示對虎的尊崇。正為此,才有了這樣的排序。如若將其按序前推或后移,仍與前同。而桂西彝族的十二生肖(獸歷)則為:龍、鳳、馬、蟻、人、雞、狗、豬、雀、牛、虎、蛇;德宏地區傣族的十二生肖(獸歷)與前相同,而西雙版納地區的傣族又改“豬”為“象”,改“龍”為“蛟”或“大蛇”,改“羊”為“蟻”。
此外,有些國家十二生肖(獸歷)的名稱亦與前頗有不同,如越南以“貓”替換了“兔”;印度的為:鼠、牛、獅、兔、龍、蛇、馬、羊、猴、金翅鳥、狗、豬;古巴比倫的為:牡牛、山羊、獅、驢、蜣螂、蛇、犬、貓、鱷、紅鶴、猿、鷹;埃及與希臘的與古巴比倫的基本相同,只是以“蟹”取代了“蜣螂”[1]。其“獅”、“蛇”的排序與印度的相同,且均是以“紅鶴”代替了“金翅鳥”[2]。其他民族或國家的十二生肖(獸歷)位于其“獅”這一序位的為“虎”,位于其“紅鶴”序位的為“雞”。也即是說,位于前一序位的均為猛獸,而位于后一序位的均為禽類。由此推測,全世界的十二生肖(獸歷)當有著同一起源。
十二生肖當起源于十二獸歷,由來甚為古遠。從地域上看,埃及、巴比倫、印度及中國等四個亞非文明古國恰好均在其流行的范圍之內。其流傳的區域雖廣達亞、歐、非大陸,但主要集中于亞洲。由此,我們有理由推斷,這一文化當起源于亞洲的某一民族,其后始逐步擴散,而先后為這一廣大地區的諸多民族所接受。然而,最初究竟為哪個民族所創,至今卻仍是個不解之迷。
一
關于十二生肖(獸歷)的始創者,目前有三種觀點較為流行[3],即:“突厥語民族始創說”、“漢族始創說”和“印度始創說”。
突厥語民族普遍使用十二獸歷。約刻寫于8世紀的《回紇毗伽可汗碑》上便有“羊年”、“猴年”、“豬年”、“兔年”的記載。此外,在《闕特勤碑》、《翁金碑》等碑文中亦同樣使用了十二獸歷[4]。敦煌、吐魯番出土的13世紀前后的回鶻文文獻及兩地諸多洞窟內的回鶻文題記亦均采用的是十二獸歷紀年。考古人員在西伯利亞及中亞地區,也曾多次發掘出刻有十二生肖動物圖案的文物[5]。
關于十二獸歷的起源,成書于11世紀的《突厥語大詞典》中記述了這樣一個傳說[6]:
某一突厥可汗想研究發生于若干年前的一次戰爭,但卻在弄清那次戰爭發生的年代時出了差錯。為此,該可汗與其部民開會商議,他說:“我們在弄清這段歷史時怎樣出錯,我們的后代子孫亦同樣會出錯。所以我們根據十二個月份和天空黃道十二宮(座)[7]給每一年份確定一個名稱吧!以后年份就以十二年為一周期來計算。這在我們中間要成為一個永久的歷法。”部民們贊同可汗的建議,說:“就照此計算。”可汗為此而出獵,下令將所有的野生動物向伊犁河驅趕。
這是一條很大的河。部民們追獵著將動物趕向伊犁河,有好些動物跳進了河中。其中有十二種動物游過了河,于是遂以這十二種動物之名作為十二年份的名稱了。老鼠率先過河,因此,以鼠名作為第一年的名稱,稱作鼠年。其后過河的被依次作為其余各年的名稱。分別為:牛年、虎年、兔年、龍年[8]、蛇年、馬年、羊年、猴年、雞年、狗年、豬年。豬年過后,復從鼠年開始計算。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即《突厥語大詞典》的作者——引譯者)稱,本書完成之年為(回歷)466年(公元1073年——引譯者)元月,業已進入蛇年。過了這一年就進入(回歷)467年即馬年了。年份就按我們所指出的這種順序計算。
突厥人推測,這一紀年的每一年都各具特色。如依他們的觀點,牛年戰爭頻仍,因為牛常互相頂架;雞年食物充足,但人們的憂慮會增多,因為雞的食物是谷粒,雞為覓食會亂刨揚垃圾;龍年雨水多,糧食豐收,因為龍在水中生活;豬年多雪酷寒,流言蜚語多。突厥人就是這樣,相信每年都必然有某種現象出現。
此外,該詞條中還說:“突厥人沒有每周七天的名稱,因為‘星期’(七曜)這個概念是有伊斯蘭教以后才知悉的。”并稱當時“城里人采用阿拉伯語的月份名稱。過游牧生活的非穆斯林突厥人將一年分為四季,每三個月以一個名稱來稱呼。用這種方法來表示一年的流逝,如將舊歷新年后的第一個月稱為‘奧厄拉克月’(Oʁlaqaj,意譯為‘山羊羔月’——引譯者);后一月稱‘烏魯厄奧厄拉克月’(Uluʁoʁ1aqaj,意譯為‘大山羊羔月’——引譯者),因為該月山羊羔要長大了;再后一個月稱‘烏魯厄月’(U1uʁaj,意譯為‘大月’——引譯者),因為該月時值仲夏,田野長滿了飼草。因而,牲畜易上膘,乳汁會增多,毋需辛勤勞作。”
據這一記載可知,突厥人雖以十二獸歷紀年,但紀月仍是采用與其畜牧文化相適應的牲畜名稱來命名的。然而,十二獸歷是否如《突厥語大詞典》所言,果真為突厥人始創,卻令人懷疑。首先,按其所稱,鼠之所以被列于首位,是由于鼠在十二種動物中率先游過了伊犁河。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且從這一傳說中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廣泛流傳于漢民族中的十二生肖動物賽跑,以名次先后排序的傳說(回、滿、錫伯等民族中亦有同樣的傳說,當均源于漢族)。其次,龍(nag)并非現實生活中的動物,且nag一詞本身即源于梵語。雞、豬等動物多為定居的農耕民族所飼養,而從歷史上來看,突厥人主要從事游牧業,向農耕經濟轉化則是較晚的事。古代突厥人的生活區域亦未曾見有過猴子的記載,連其biʧin/beʧin(猴子)一詞亦是借用于其他語言的(說詳后文)。再者,考古發現的許多刻有十二生肖動物圖案的文物上,同時還刻有漢字,證明是源于漢族的。更重要的是,《突厥語大詞典》為11世紀的作品,而其他突厥語碑銘文獻也早不過8世紀。顯然不能以此來論證十二生肖(獸歷)的起源問題。謂十二生肖(獸歷)為突厥語民族始創之論據明顯不足[9]。
那么,這一文化是否為漢族始創呢?眾所周知,干支紀年是華夏民族的傳統方法。“干”,又稱“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支”,又稱“地支”、“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傳“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尚書正義》說:“二人皆黃帝之臣。蓋黃帝以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此說固不可信,但甲骨文及殷墟出土的玉質干支表殘片等文物證明,商代肯定已有六十干支了[10]。殷商時,干支只用作紀日。春秋時,始用干支紀月。干支紀年法,《史記·歷書》載之。有人據《隋書·律歷志》引《竹書紀年》中的“堯元年景子”一句認為,戰國時已有干支紀年。“景子”也即是“丙子”,因唐高祖的父親名“暋保病皶”音的字皆改為“景”所致。前些年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數種帛書中都包括有干支紀年表,證明西漢初年便已使用。據此看來,稱戰國時已有干支紀年是可信的。在用干支紀年以前,華夏民族使用的是“歲星紀年法”和“太歲紀年法”。“歲星”指木星,“太歲”是假想的運行速度和木星平均速度(一年走十二分之一周天,即一辰)相等而運動方向相反的天體。設想它們在黃道帶里每年經過一宮,約12年運行一周天,故而以其所在的方位來紀年。
干支紀時法,不知始于何代。《后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云:“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東觀漢記·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有“甲夜讀眾書,乙更盡乃寐”之句;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則進一步指出:“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由此可知,至遲在東漢時便將一夜分為五段。不過紀夜用“十干”,而推論節氣和日月交食都用“十二支”。這是因為古人把一晝夜分為百刻,所以用“十干”比較方便。后來把一晝夜分為“十二辰”,則以“十二地支”來表示“十二時辰”較方便。每辰等于兩小時,今日所稱“小時”等于古之半辰。一辰中前一小時為初,后一小時為正,故而又有子初、子正、丑初、丑正等稱法。
漢語傳世文獻對十二生肖(獸歷)的記錄,首見于東漢王充《論衡》一書之《物事篇》、《言毒篇》及《譏日篇》,但也只是借用來批駁五行相克之理的。清人趙翼的《陔馀叢考》卷三十四及梁章鉅《浪跡續談》卷七,“十二屬”條亦均稱其始于東漢,漢以前未有言之者。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中曾舉出《詩經·吉日》“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為例證,認為詩句中有以午為馬的含意,從而認為先秦已有生肖;清人萬希槐在《困學紀聞集證》中又補充了一些例證,但理由仍不夠充分,而未能引起重視。十二生肖的普遍使用,約為南北朝時期。《南齊書·五行志》中有關于屬相的記載,《周書·宇文護傳》記其母貽護書中有“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之謂,但也僅僅是幫助人們記其出生之年罷了。
1975年底,考古工作者曾于湖北云夢睡虎地11號秦墓發現秦簡中有兩種《日書》。整理時分別稱為《日書》甲種和乙種。《日書》甲種中有一章標題為《盜者》,是用來占卜盜者相貌特征的。其中提到了十二生肖,如:“子,鼠也。盜者兌口希須……”;“丑,牛也。盜者大鼻長頸……”。其順序及名稱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原簡漏抄生肖)、巳蟲、午鹿、未馬、申環(猿)、酉水(雉)、戌老羊、亥豕。據研究者稱,該《日書》成于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有的內容可追溯到戰國時的楚國,有的可追溯到秦國。《論衡·實知篇》稱:“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云夢,望祀虞舜于九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陜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瑯邪。自瑯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臺。”筆者推測,《日書》很可能是由秦國傳至楚國的。
無獨有偶,1986年4月,考古工作者又于甘肅天水市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1號秦墓中出土甲種《日書》73枚竹簡,乙種《日書》380枚竹簡。其甲種《日書》的內容亦是用來占卜盜者相貌特征、入盜方向及物品藏匿處所的。有關十二生肖的文字,分條書寫于第30~41簡。十二生肖的名稱及順序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蟲、巳雞、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豕。其中:“巳雞”與“酉雞”相重,疑為“巳蛇”之誤。據研究者稱,放馬灘墓地的時代,“上限至戰國晚期,下限在秦始皇三十年以前或稍早”,1號墓“下葬的絕對年代當在(始皇)八年九月至九年初”,而甲種《日書》的“成書和流行時間當在秦統一前[11]。
兩地出土的《日書》,可謂是世界范圍內迄今所知有關十二生肖(獸歷)最早的完整記錄。然而,若據此而稱其為華夏民族始創,仍有許多疑點:
(一)華夏民族既然已采用天干地支紀年、月、日等,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再創制出十二生肖(獸歷)來與十二地支相配。
(二)為何最初要采用兩套系統,以十干紀時,用十二地支來推論節氣和日月交食,而后來又改用十二地支紀時?
(三)十二生肖(獸歷)若果真為華夏民族始創,為何東漢以前的傳世文獻中不見記載?其普遍使用又為何在南北朝時期?
這些都是難以解答且又必須解答的問題。相反,種種跡象倒表明,極可能是域外文化采借的結果。
印度始創說系近些年提出的。其論據是有許多相關的記載見諸于文獻之中。據《阿婆縛紗》和《行林鈔》記載,十二生肖動物原是十二位神祗座下的十二神獸:招杜羅神將駕鼠;毗羯羅神將駕牛;宮毗羅神將駕獅;伐折羅神將駕兔;迷企羅神將駕龍;安底羅神將駕蛇;安彌羅神將駕馬;珊底羅神將駕羊;因達羅神將駕猴;婆夷羅神將駕金翅鳥;摩虎羅神將駕狗;直達羅神將駕豬。另在許多佛經中亦有相關的記載,如《大集經》卷二三,《虛空目分中凈目品》五稱,十二生肖原是分別住于四海山中主十二時辰的十二種動物,各應其所主之時辰而巡行人世,為:子鼠、丑牛、寅虎(原文為獅)、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豬。
據《藥師本愿功德經》等所說,則系東方藥師佛之眷屬,為晝夜十二時之護法神將,其名為:毗羯羅大將(子時)、招杜羅大將(丑時)、真達羅大將(寅日寸)、摩虎羅大將(卯時)、婆夷羅大將(辰時)、因達羅大將(巳時)、珊底羅大將(午時)、額儞羅大將(未時)、安底羅大將(申時)、迷企羅大將(酉時)、伐折羅大將(戌時)、宮毗羅大將(亥時)。稱其為十二佛、菩薩之化身,各自頭戴表其所值時辰的鼠、牛、虎等冠。這十二神獸的名稱及排序均與現代印度的十二獸歷相同,因而認為,十二獸歷當即是由這十二神獸演變而來的,而世界其他民族的十二生肖(獸歷)則是在印度十二獸歷的基礎上進一步演變的結果。
然而,如若對這一觀點作進一步地考察,便會發現其中亦有許多可疑之處。從起源上看,十二生肖(獸歷)的形成與十二辰密切相關,而十二辰的確定又源于天文學。所謂十二辰者,系指自子至亥十二時。《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上古時,于天文學貢獻最大者為古巴倫人。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十二辰“導源于古代巴比倫之十二宮,其朔乃黃道周天之十二星座”[12],我國“十二辰之輸入或制定,即當在殷商一代”[13]。也即是說,就連華夏民族傳統的“歲星紀年法”和“太歲紀年法”亦是導源于此。而印度的天文學,據古印度天文學家伐羅訶密希羅(約505年)稱,亦是從“夜伐那人”(即西方人)那里傳來的[14]。由此看來,十二生肖(獸歷)的“印度始創說”亦難以成立。
二
據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古巴比倫人當為十二獸歷的始創者,古西北印度人是其改造者,而華夏民族則是十二生肖的改造者及這一文化的重要傳播者。
生活于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人,至晚在公元前20世紀以前,便已開始使用楔形文字。由于農業生產需要確定季節;古代宗教希求觀測天象,領會神的意志并預卜未來(占星術)而推動了其天文學的發展。古巴比倫人對太陽和月球的運動記錄了許多數據,并算出了它們的位置和虧蝕時間。他們知道太陽年但用陰歷作日歷,一年十二個月中有的是29天,有的是30天,并在19年里再插進7個月,使235個陰歷月等于19個太陽年。而我國古代的天文學理論因導源于此,亦與之完全相同。如《淮南子·天文訓》稱:“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甚至連古代所使用的“攝提格”、“單閼”等年名,經郭沫若先生考證,亦為其音譯借詞。十二獸歷當即是于這一時期為古巴比倫人所創制出來的。之后,隨著文化的交往而西傳至希臘、埃及等地,并被進行了些許改造(如將蜣螂改為當地人所熟知的蟹);東向則傳至印度及我國中原地區,進而演變為印度的十二獸歷和我國的十二地支。
古代印度,至晚于公元前9世紀便開始了與巴比倫、埃及、錫蘭等地的對外貿易。巴比倫人的天文學知識(包括十二獸歷)亦隨之傳至印度。公元前374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曾率步兵三萬,騎兵五千東侵,先征服了小亞細亞諸希臘城邦,繼而征服埃及、兩河流域和波斯全境。公元前327年占領了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25年至巴比倫,并定都于此。通過這次東征,亞歷山大建立了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這在客觀上亦促進了十二獸歷的傳播。古代印度的民間,流傳著許多寓言、童話。各類動物在這些寓言、童話中非但具有靈性,且會人語。十二獸歷進入印度后,在當地的文化環境中被進行了一番較徹底的本土化改造,除位列第三的獅子和位列第六的蛇之外,其余的獸名都被為當地人所熟知的獸名所替換,而鼠之所以被列在首位,則顯然與當地敬鼠習俗密切相關。
除了龍之外,其余的十一種動物均為印度所有。印度傳說中的龍雖和我國傳說中的龍一樣,是復合多種動物為一體且能興云作雨的神異動物,但也僅是釋迦牟尼所濟渡的“眾生”之一,并不象中國傳說中的龍那樣,尚具有至高無上不可冒犯的地位。此外,古代突厥語中的nag(龍)一詞,亦是通過焉耆-龜茲語借用于梵語之nāga的。與此相對,東部回鶻人則稱“龍”為lu或luu,系漢語“龍”之音譯借詞。古代突厥語的biʧin/beʧin(猴子)一詞,J·哈里甫及P·伯希和認為源于希臘語的πιθηχοs,G·J·蘭司鐵認為是從粟特語中借入的,同時他還將該詞同希臘語的πιθηυ進行了比較,Hanwoochoi則認為biʧin/beʧin是漢語“狒”與“申”的音譯,稱該詞“可能先由中古漢語借入粟特語或吐火羅語中,然后又通過這種語言進入突厥語和蒙古語中。因而這個詞的語言演變可以歸納為如下所示:突厥語bičin/bečin<粟特語或吐火羅語be:čin<中古漢語Pjwei+sien‘狒申’”[15]。這兩個突厥語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十二生肖是源于印度十二獸歷的,同時也意味著突厥語民族的十二生肖可能分別源于焉耆-龜茲語(亦可能是粟特語)和漢語,有著不同的途徑。
公元前324年,原在難陀王室中供職的旃陀羅笈多由于同國王發生沖突而避難于旁遮普。他趁亞歷山大入侵之機發動起義,并在反抗入侵者的斗爭中顛覆了那達·難陀的統治,建立起印度列國時代最強大的孔雀王朝。這位種姓下賤的月護大王,不但迅速統一了北印度,還很快奪回了由希臘人建立和鎮守的信德與旁遮普郡,全部控制了興都庫什以南健陀羅和古罽賓。從此,佛教勢力得以植根西北印度,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逐漸為中亞希臘化地區和塔里木盆地居民所接受和信奉。早在旃陀羅笈多舉事很久以前,僧侶們為弘揚佛教,就曾將原本流傳于民間的各類寓言、童話等改編為佛本生故事,用來宣傳佛教教義,故而其十二獸歷中的動物亦均見于佛本生故事之中。
古巴比倫的天文學及與之相關的十二獸歷東傳到我國中原地區后,其黃道十二宮被稱作“十二次”,十二宮名稱則演變為“十二次”名稱(如稱摩羯宮為星紀等)。與古巴比倫人在星占術中將黃道十二宮用作天空分野的區劃系統一樣,“十二次”亦同樣在星占術中被用作天空分野的區劃系統。古巴比倫的十二獸歷則演變為十二地支,與華夏民族傳統的十干相配合用于紀年、紀月、紀日。此外,尚用于音律(十二律)及度量的制定[16]。
在印度和中國這兩個東方文明古國之間,雖橫亙有所謂“峻極于天”的喀喇昆侖山和喜馬拉雅山,但也決不是“天乃為之闕,便不能相聞問”。郭沫若、岑仲勉、張星烺、季羨林等著名學者早就指出,遠在上古時代,印度與中國之間便有著密切的文化交往關系。孔雀王朝開國功臣喬底利耶的《政事論》,稍晚時成書的,匯編了印度宗教、哲學和法律等內容的《摩奴法典》以及著名史詩《摩訶婆羅多》和波彌爾的《梵文語法》諸書,均記有印中古代通商貿易的內容。前述之《放》簡《日書》及《睡》簡《日書》中的十二生肖當即是旃陀羅笈多創建孔雀王朝之前或其執政期間傳入我國的。不過,從其均用于占卜吉兇的內容及排序第三之獸名均為虎而非獅子的情況來看,似乎并非直接源于印度。這一變化可能是在中亞古罽賓等地區或塔里木盆地操印歐語的古代民族中形成的,并沿著“絲綢之路”而傳到我國內地。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中原地區的人不熟悉獅子這種猛獸,而將其比附為虎了。
戰國時期的《日書》能分別在甘肅天水放馬灘及湖北云夢睡虎地兩地發現,絕不是偶然的。它不僅昭示著兩地之間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內所具有的文化聯系,而且亦有助于我們認識十二生肖文化的東漸過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雒(洛)邑(今河南省洛陽市洛水北岸)后,自豐鎬(今陜西長安縣)以西盡為戎人所據。周平王因秦襄公護駕東遷有功,而“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17]”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用戎臣由余之謀,攻戎王,滅十二戎國,占地千里,稱霸西垂,奠定了華戎雜處的分布格局,進一步密切了不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戰國時期,“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18]。秦文化在這一時期,受到了西戎文化的強烈影響。十二生肖當即是于這一時期通過西戎的中介而進入秦文化之中的。
《日書》是日者以時辰推斷吉兇的占卜用書。張守節《史記正義》稱日者“言辭最鄙陋”,說明“它主要流傳于社會基層,而低級官吏似亦精通此道”[19]。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秦將白起攻取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并于楚地設置南郡。《睡》簡《日書》寫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的情況表明,該《日書》極可能是南征秦軍中的某一將領(墓主?)由秦地攜往楚地的。《睡》簡《日書》與《放》簡《日書》中十二生肖的些微差異,當是這一文化在秦地流傳過程中的自然變異。鑒此,本文不贊同將《睡》簡《日書》看作是“一個秦楚文化的混血兒”或“純楚《日書》”,將《放》簡《日書》看作是“純秦《日書》”的觀點[20],而認為無論《睡》簡《日書》或是《放》簡《日書》均系域外文化與秦文化的“混血兒”。
從兩地《日書》的內容來看,十二生肖(獸歷)與十二地支配合使用,當是用以紀時的(前人因無緣得見兩地《日書》,而誤認為十二辰紀時之制始于漢代[21])。其有關簡文,先是確定失盜的時辰,而后則指出于該時辰行竊者的肖相,并據此進一步推斷出盜者的相貌特征、入盜方向及藏匿地點等。如《放》簡甲種《日書》第32簡的簡文為:“寅,虎矣。以亡。盜從東方入。有從之臧山谷中。其為人,方顏然,扁然。名曰輒,曰耳,曰志,曰聲。賤人矣。得。”兩地《日書》中的地支與生肖均以主謂結構組句(如《放》簡稱:“子,鼠矣。”《睡》簡稱:“子,鼠也。”),后項顯然是對前項的解釋。其本身就意味著生肖在當時還是一種為常人所不熟悉的文化,僅為日者等少數人所了解。
東漢時,外來的佛教文化主要為五行家所用。《漢書·藝文志》載,五行家有“《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稱十二時各有其神主之。此說與十二生肖(獸歷)密切相關,明顯源于佛經。清·梁章鉅《浪跡續談》卷七“十二屬”條稱:“《法苑珠林》引《大集經》言其所由來曰:‘閻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獸,并是菩薩化導,人道初生,當菩薩住窟,即屬此獸神護持,得益,故漢地十二辰依此行也。”東漢以后,伴隨著佛教在中原地區的傳布,十二生肖(獸歷)才為更多的人所了解。及至南北朝時期,由于佛教的勃興和普及,十二生肖方普遍使用。
三
十二獸歷傳入我國后,以紀時發其端,后又發展為紀日(至少在西域地區是如此)。1904年,德國探險隊曾在高昌古城獲得一份用粟特語寫成的日歷。該歷所記各日,用粟特語、漢語、突厥語稱呼。每日先用粟特語七曜日的名稱,次譯漢語甲、乙、丙、丁等十二干之音,后更以粟特語之鼠、牛、虎、兔等配成十二獸名。在其上的第二日用粟特語譯出漢語之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名,且以紅字記之。這一日歷反映了當時高昌地區融多種文化為一體的狀況。通過這一日歷,我們至少可獲得如下兩個頗有價值的信息:
其一,抄寫者及使用者是操粟特語的居民。粟特人亦使用與漢族等相同的十二生肖或獸歷(其第三位為“虎”而非“獅”)。若將這種相同的情況解釋為是粟特人意譯漢語的,倒不如說在一定程度上昭示著粟特人早在漢族人之前就已使用十二獸歷了——以粟特語譯寫漢語“十干”(注意:非“十二支”)及五行之名的形式表明,該日歷書寫時,當地或內地的漢族居民仍習慣于使用天干紀日。
其二,十二獸歷在西域地區除用于紀年外,尚用于紀日。無獨有偶,樓蘭古城出土的第565號佉盧文木簡“歷書”[22]亦證實了這一點。與此相應,前述之《放》簡《日書》及《睡》簡《日書》亦均是紀日的。這亦從一個側面暗示著漢族的十二生肖是由西域的十二獸歷演變而來的。
兩地《日書》的內容均表明,最初人們以為于某時行竊的人,其相貌、習性也必肖某物。及到后來,由于用其紀年,又認為出生于某年的人便肖某物,如子年出生的肖鼠,丑年出生的肖牛等。生肖及生肖觀念的形成,無疑與十二獸歷初入中國便用于占卜的用途密切相關。可以說,十二生肖是十二獸歷傳入中國后,同華夏文化相結合的產物。考古發掘表明,至遲在隋代的墓葬中就有了隨葬的獸首人身生肖俑。到了唐代,此種習俗更為盛行,甚至連邊疆地區也不例外。
1972年,考古人員曾在吐魯番阿斯塔那的唐代墓葬中發現兩尊泥塑的獸首人身生肖俑。一為豬首人身,一為雞首人身[23]。五代時,蜀主王建因屬兔,甚至連其謚寶璽紐的龍頭也改刻成了兔首。反映了唐五代時,人們尊崇屬相動物的心理。
源遠流長的十二生肖,既然廣泛影響著古代的民俗,因而文人們亦常將其作為創作詩文的題材。迄今所知最早將十二生肖用于詩作的為南朝梁陳時人沈炯。其所作《十二屬詩》為:
鼠跡生塵案,牛羊暮下來。
虎嘯坐空谷,兔月向窗開。
龍隰遠青翠,蛇柳近徘徊。
馬蘭方遠摘,羊負始春裁。
猴栗羞芬果,雞砧引清杯。
狗其懷物外,豬蠢窅悠哉。
約自宋代開始,十二生肖詩代有人作,就連大名鼎鼎的朱熹,也有此類詩作:
晝聞空簞嚙饑鼠,曉駕羸牛耕廢圃。
時才虎圈聽豪夸,舊業兔園嗟莽鹵。
君看蟄龍臥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
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從容。
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鹍雞鳴角角。
客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豬肉。
又如元·劉因的《十二辰詩》:
饑鷹嚇鼠驚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
江山虎踞千里來,才辨荊州兔穴爾。
魚龍入水浩無涯,幻境等是杯中蛇。
馬耳秋風去無跡,羊腸蜀道早還家。
何必高門沐猴舞,豚柵雞棲皆樂土。
柴門狗吠報鄰翁,約買神豬謝春雨。
再如明·胡儼的《十二辰詩》:
鼷鼠飲河河不干,牛女長年相見難。
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
驪龍有珠常不睡,畫蛇添足適為累。
老馬何曾有角生,羝羊觸藩徒忿嚏。
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雞空自老林丘。
舞陽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
此類詩作的共同特點是多以十二句構篇,每句中含一生肖動物,類似于文字游戲,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古人的生活情趣。
清代的乾隆皇帝頗有文采,他曾以析字的技法創作過一首詞。其中巧妙地融進了十二地支諸字。作品形象地刻畫了少男少女卿卿我我的熱戀情景,讀來頗有情趣。因十二地支與十二生肖(獸歷)密切相關,故一并錄來以相參印。其詞為:
好良宵,正與女娘偕,佳人抽身去得快。扭著她,卻把那手推開。演出那百般態,珠淚兒點滴落窗臺。柳腰斜依欄桿外,又將那木槿花兒抓下來。振精神,步香階,即時不見那秀才。已還書齋。許訂佳期,毀前言,又把相思害。朱簾半卷莫聊奈,金釵懶向頭上戴。神前伐示,永合偕。酒醉心狂,莫點水來解。荷戈人小腳兒,欣然肯招,刻骨銘心,何嘗又把刀兒帶。
“好良宵,正與女娘偕,佳人抽身去得快”一句中的“好”字去掉“佳人”(女)后,就是個“子”字。“扭著她”的“扭”字卻把那手(扌)推開,剩下的就是個“丑”字。“演出那百般態,珠淚兒點滴落窗臺”中的“演”字去掉“珠淚兒”(氵)就是個“寅”字。“柳腰斜依欄桿外,又將那木槿花兒抓下來”中的“柳”字去掉“木槿花兒”(木)后就是個“卯”字。“振精神,步香階,即時不見那秀才”’中的“振”字沒有了“秀才”(扌)就是個“辰”字。“已還書齋”中的“已”字,關起門來就是個“巳”字。“許訂佳期,毀前言,又把相思害”中的“許”字“毀前言”(讠)后就是個“午”字。“朱簾半卷莫聊奈,金釵懶向頭上戴”中的“朱”若不戴頭上的“金釵”(丿)就是個“未”字。“神前伐示,永合偕”中的“神”字伐去“示”(礻)后便是“申”字。“酒醉心狂,莫點水來解”中的“酒”字沒有了“水”(氵),就是個“酉”字。“荷戈人小腳兒,欣然肯招”中的“荷戈人”(人、戈)按《說文》的解釋,“人”持“戈”為“戍”(守邊也,從人持戈)。而“人”字的“小腳兒”若再“招”起來,也就是“戌”字了。“刻骨銘心,何嘗又把刀兒帶”中的“刻”字若沒有了“刀”(刂),就是個“亥”字。
全詞構思巧妙,不但有人有物,有情有景,悱惻纏綿,銘心刻骨,且以離合、會意兩種技法暗示出了子、丑、寅、卯、申、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充分展示了漢字文化的藝術魅力,堪稱奇文絕技。
約自宋代開始,在人們的觀念中又進而將生肖與一個人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形成了許多生肖禁忌。北宋徽宗時,因其屬狗,曾詔令天下禁止殺狗。太學生們曾氣憤地質問:“神宗皇帝(徽宗之父)生于戊子年,肖生為鼠。為何當時不禁養貓?”元代的仁宗皇帝因屬相為雞,也曾頒布過不許在大都(北京)城內外倒提雞的禁令。明代的武宗皇帝因屬豬,還曾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詔令全國“嚴禁畜豬”,違者充軍,以至于次年清明皇家備辦祭祖三牲時,竟找不到一頭豬了。
生肖禁忌還表現在婚配方面,其肇因則是源于五行相克的屬相相克觀念。凡有婚嫁,必得先批“八字”,看二人命中是否相合。由此,甚而還產生了諸如“豬猴不到頭,白馬怕青牛;金雞怕玉犬,龍兔淚交流;蛇虎一刀錯,羊鼠一旦休”以及“古來白馬犯青牛,羊鼠相交一旦休,猛虎見蛇如刀錯,兔兒遇龍淚交流;金雞玉犬莫相見,亥豬從來怕猿猴”之類的婚配禁忌歌。屬相相克觀念,可謂是漢族生肖文化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它對周邊民族亦或多或少地產生過影響。此外,生肖禁忌還表現為語言上的避忌,如不說屬蛇而雅稱之為“屬小龍”,日本人諱稱“豬年”為“野豬年”,而回族人則諱稱屬豬的為“屬亥的”。
生肖文化在民間習俗的其他方面亦有所體現。“十二歲生日”、“本年禳解”(又稱“本年禳驗”)及“十二和尚”、“十二生肖歌”等均是其不同的表現形式。
“十二歲生日”和“本年禳解”為漢族及部分少數民族中的壽誕風俗。前者指男孩滿12歲即十二生肖滿一巡之日,家人為其“扎紅”、“剃跳姑圈”并置辦酒席,招待前來道喜的親戚、鄰里的活動。屆時,族中長輩及親友均要贈予男孩禮物或錢帛若干,以為可乞福、避災。此俗主要流行于內蒙古東部漢族和部分少數民族之中。后者主要指年過半百的老人逢自己所隸屬肖值年(即“本年”或稱“本命年”)的元日所舉行的禳解活動。民間認為,人到本年,災殃必多。進行禳解,才能逢兇化吉。其禳解之法是于生肖值年的元日舉行慶壽活動,由晚輩向老人敬獻紅色襯褲、紅布或紅綾褲帶,且于即日穿上或系上,認為如此即可禳解災殃。此俗主要流行于河湟地區。其他地區的漢族亦有此俗,所不同的是,一般不舉行什么儀式,也不僅限于老人。大多是于本年在腕上系一條紅絲帶,或換用一條紅褲帶,或貼身穿一件紅肚兜,或穿一件紅褲頭,以禳解災殃。
“十二和尚”是舊時流行于內蒙古土默特等地蒙古族民間的一種象征著吉祥的發式。兒童長到12歲時,家人要為其舉行儀式,并送至寺廟去“還愿”,祈求佛爺保佑,從此開始留發辮,取名“十二和尚”。屆時,親友鄰居也都要前來祝賀。
“十二生肖歌”為畬族的傳統歌,流行于浙江地區。一般于盤歌會或婚嫁時長夜對歌中演唱。其內容為描述十二生肖的形象、特點以及與人類的關系,各地唱詞大同小異。“十二生肖歌”多在盤歌結束前演唱,作為收底,故又有“歌底”之稱。其最后一段四句,俗稱“歌盤”,唱畢,表示歌會宣告結束。
十二生肖文化在我國扎下根后,又以內地為中心向周邊擴散,往東傳至朝鮮半島和日本;往北傳至阿爾泰語系各游牧民族,并隨著部落(族)的遷徙及西往的軍旅、商賈、流民、僧侶等而西傳至中亞、西亞和東歐;西南傳至吐蕃;向南則傳至我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越南等地。在向南傳播的過程中,又進而嬗變為各類獨具特色的構成形式。
四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十二生肖源于十二獸歷,十二獸歷的形成則與古巴比倫人天文學中的黃道周天之十二星座等密切相關。也即是說,十二獸歷為古巴比倫人首創。十二獸歷一俟形成,便分別沿東西兩個方向擴散:西向以次傳至希臘、埃及;東向則傳至印度和我國內地。希臘、埃及的文化由于和巴比倫文化有著許多的共同之處,故而十二獸歷僅出現了若干微小的變化。十二獸歷傳至印度后,由于處于文化差異較大的環境中而被進行了一番較徹底的本土化改造,賦予了許多本土文化特點。古巴比倫人的天文學(星歷)知識早在公元前19~18世紀便已傳至我國內地,殷人稱之為“十二辰”或“十二支”,但僅用于推算節氣和日月交食,并與傳統的“十干”相結合用于紀年。而與此相關的十二獸歷卻因無用武之地而湮沒不彰。此后,經印度改造后的十二獸歷約于公元前3世紀初,又沿“絲綢之路”傳到了我國內地,嬗變為十二生肖,進而隨著佛教的興盛而得到了普及。同時亦賦予了許多新的文化內涵。此后,又以中原地區為中心進一步傳播、擴散至周邊地區的民族和國家。[1]據郭沫若:《釋支干》(原作于1929年,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一卷,科學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一文所引資料稱,希臘十二獸歷中位列第八的為“鼠”,印度十二獸歷中位列第六的為“毒蛇”,位列第九的為“獼猴”,位列第十的為“雞”。
[2]同上注。
[3]郭沫若先生在其《釋支干》一文中,曾“疑中央亞細亞古族之稍落后者,如月氏、康居之類仿十二宮象之意而為之,故向四周傳播也”,但未詳論,響應者亦寥寥。另,幾乎每個使用十二生肖(獸歷)的民族中,都有關于其起源的傳說。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論及。
[4]參見[法]勒內·吉羅著,耿昇譯:《東突厥汗國碑銘考釋》,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84年內部鉛印本,第12~13頁,第15頁。該書作者稱,這是受漢文化的影響所致。
[5]參見蘇北海:《哈薩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83頁。
[6]《Tyrkitïl1ardïwanï》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449~452頁。
[7]“宮”(座)一詞,《Tyrkitïl1ardïwanï》作burʤ;黃啟輝:《土漢字典》(正中書局印行,1976)作burʧ,釋為“十二生肖(宮)圖”;《漢維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釋為“天干”,均不妥。
[8]《Dïwanuluʁatittyrk》原寫做nagjï1ï。g與k在阿拉伯文中不加區分,因而《Tyrkitïl1ardïwanï》翻譯者據突厥語構詞習慣,將其轉寫為nakjï1ï,釋為lɛhɛŋjï1ï(鯊魚年),又括注為“tïmsahjï1ï(鱷魚年),皆誤。按,nag一詞系從焉耆-龜茲語中借用的,而焉耆-龜茲語之nag又源于梵語的nāga,兼有“鱷魚”和“龍”二意,此處實應釋為“龍”。近些年來出版的許多論著,甚至于工具書都因此而誤認為突厥語諸民族是以“鱷魚”或“魚”代替了“龍”。具有代表性的如:《維吾爾族簡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94頁稱:“與漢族12生肖不同的是他們以鱷魚代替了龍。”《中國商業文化大辭典》(中國發展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291頁,“十二生肖·屬相”條稱:“維吾爾族以魚代替龍”。筆者另撰有《〈突厥語詞典〉詮釋四題》一文,刊于《喀什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對此有專門考釋。
[9]此說由沙畹(chavannes)于1906年提出。其誤業經伯希和(P·pelliot)指出,但伯氏對其起源亦未加考證,只稱:“不論此十二屬之遠因何在,余頗疑突厥之記年方法乃假之于在突厥前稱霸之種族,顧突厥假用蠕蠕(Avars)之制不少,殆亦為承襲蠕蠕者也。”詳見伯希和:《中亞史地叢考》(NeufnotesSurdesquestionsd’Asiecentrale.〈T’oungPao,1928-9〉)一文,漢譯文見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一卷,五編,第113~118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11月重印版。
[10]參見《殷虛書契前編》三卷,二葉四片;李學勤:《干支紀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證》,刊于《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
[11]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2]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載《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二卷,科學出版社,1982年9月版。
[13]郭沫若:《釋支干》,載《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一卷,科學出版社,1982年9月版。
[14]陳昌曙、遠德玉主編:《自然科學發展簡史》,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58頁。
[15][安卡拉]Hanwoochoi著,北川譯:《關于古突厥語bičin/bečin的詞源問題》,原刊于《中亞雜志》1989年第3~4期218-222,漢譯文刊于《突厥語研究通訊》,1990年第2期。
[16]參見《淮南子》卷三,《天文訓》。
[17]《史記·秦本紀》。
[18]《史記·匈奴列傳》。
[19]黃留珠:《秦文化的南播》,載《秦漢史論叢》(第六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0]黃留珠:《秦文化的南播》,載《秦漢史論叢》(第六輯),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1]最早見諸于文獻的為《漢書·翼奉傳》及《漢書·五行志》。故而,趙翼《陔馀叢考》謂“一日十二時始干漢”;郭沫若先生在其《釋支干》一文中認為:“此乃漢武重通西域以后,受西方之影響而仿制者,其事或于十二肖獸之輸入同時也。”(引自《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一卷,科學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郭沫若此文作于1929年,在今天看來,稱其始于漢代,雖已不能成立,但謂其系“受西方之影響而仿制者。其事或與十二肖獸之輸入同時也”,卻是獨具慧眼,應予以肯定。
[22]穆舜英著:《神秘的古城樓蘭》,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21頁。從內容來看,該“歷書”亦具有占卜性質。
[23]張玲玲:《十二生肖與生肖俑》,載《新疆日報》,1990年9月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