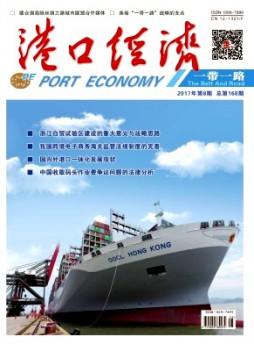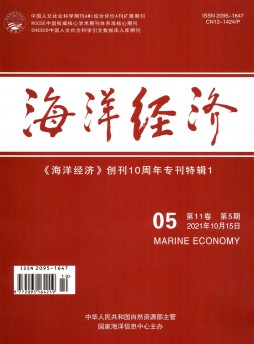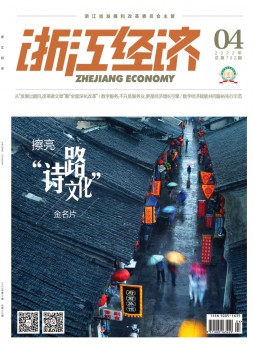經濟觀歷史演變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經濟觀歷史演變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的資本主義經濟觀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依據,運用對立統一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統一的方法,在長期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地位、作用和基本特征等進行分析和總結后所形成的一系列觀點和思想。資本主義經濟觀既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兩次理論飛躍的理論基礎和思想源泉,更是中國共產黨制定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基本理論依據。中國共產黨奮斗歷程表明,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的政策正確與否,是其政策正確與否的“晴雨表”。對資本主義經濟觀的歷史演變脈絡進行系統考察和科學評價,既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又有為中國社特色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理論參考和借鑒的現實意義。
一、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認識
“”前后的中國思想界在新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問題上,各種不同的文化派別幾乎都崇尚和標榜“社會主義”的思想。而當時的社會主義思潮是在對資本主義批判和改良基礎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受其影響,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919年8月在《社會問題》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即“勞動者把資本家推翻,由勞動[者]自己組織一切”[1]23。這種觀點雖然認識到了資產階級落后和反動的一面,卻沒有認識到資產階級也具有革命和進步的另一面,只是簡單地把馬克思社會主義中“推翻資本家”的觀點當作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全部。可以說,這是對資本主義整體認識的萌芽。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黨綱指出,“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2]5,到“六大”依然認為“中國受著資本主義發展之最厲害的壞處(平民群眾的無產階級化,破產失業廣大的貧困等等),但是沒有受著資本主義偉大的好處(生產力的增高)”[3]343。中共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這種認識必然影響到對資產階級的政策,必然導致黨在革命政策和策略方面忽視中間階級的結果。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在此階段也沒有擺脫全黨對資本主義經濟過左認識的影響。這一時期,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全面否定。1922年1月他在《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指出:“資本主義在中國越是發達,中國紛亂越是會延長期間。”[4]33這說明沒有認識到造成中國落后貧弱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經濟相對于資本主義經濟極端落后,也正因為其落后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和掠奪提供了機會和空間。二是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問題要靠社會主義革命。在《賠款與戰債》中指出,“把資本制度推倒”才是未來世界發展的根本[4]87。由此可以看出,只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方面,卻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經濟的工具理性特點。這既反映出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接受和認同,同時也反映出他對資本主義制度認識的局限性。這也說明在當時中國國情條件下,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無論在邏輯的系統性和完整性方面,還是在理論的深刻性和可行性方面,都處在感性階段,還沒有達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要求。
二、資本主義經濟觀的形成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進步性的錯誤認識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國內階級關系的錯誤認識和處理,“認為國民黨各派和各中間派別都是一樣的反革命,要求黨向他們一律進行‘決死斗爭’”[5]32。這是全黨在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錯誤認識基礎上對中國資產階級所做的判斷,直接造成黨在實踐中失去與中國資產階級中間派集聚政治資源的機會。二是對制訂蘇區建設和發展政策的錯誤指導。王明在1931年初提出“反對資產階級”等一系列“左”傾錯誤觀點和政策建議[6]139,給蘇區的鞏固和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在蘇區嚴酷的革命斗爭和建設實踐過程中,開始對“左”傾教條主義危害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并逐步擺脫“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形成了為土地革命服務的資本主義經濟觀。1931年在同中國托派進行論戰時指出:帝國主義國家“利用政治的與經濟的借款以及軍事失敗后的賠款,壟斷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取得了它們的勢力范圍,使各地的地主軍閥,以至資本家,變成了它們手中的工具”,得出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結論[4]178。此時雖然沒能區分民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界限,并提出利用資本主義的觀點,但他已經認識到是帝國主義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就從理論上說明了阻礙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是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這同當時中央“左”傾領導對待資本主義態度相比已表現出明顯的不同。隨著國民黨政府對蘇區經濟封鎖和對蘇區經濟建設實際認識的加深,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又有了新的看法。1933年4月,在《五一節與〈勞動法〉執行的檢閱》中批評了“把資本吃完了再說”[4]341的“左”傾政策。隨后又在《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中指出:“還不能不利用私人資本來發展蘇維埃的經濟。它甚至應該采取種種辦法,去鼓勵私人資本家的投資。”[4]344為此,提出“蘇維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貿易的自由,而且鼓勵商品的流通”[4]345-346的政策。從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否定轉變到“利用私人資本主義”,這不僅是他在理論認識上的質變和飛躍,也為全黨以后從認識上糾正“左”傾錯誤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前提。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對資本主義經濟又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這些認識集中體現在1934年1月發表的《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一文中,他指出:“像中國這樣的經濟,我們稱作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經濟,這種經濟決定了中國革命的任務與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中各階級的關系,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動力。”[4]481能夠在一年后的遵義會議上從“左”傾派別中分化出來,支持的正確路線,正是取決于他有這種轉變的自覺思想基礎,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前提,作為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才能在隨后的抗戰時期提出對待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的正確政策和策略。的資本主義經濟觀與蘇區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的有機結合,實現了蘇區經濟發展的理論創新。但是,的資本主義經濟觀還處于形成時期,理論內容方面尚不夠完善準確,只是探索了資本主義經濟與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關系,并沒有觸及對資本主義經濟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關系的認識,同時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地位、作用和基本特征也沒有進行充分的理論分析。對于這一問題,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給予解決的。
三、資本主義經濟觀的成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確立了建立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黨明確提出了“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用比較過去寬大的政策對待民族工商業資本家”,“歡迎華僑資本家到蘇區發展工商業”[7]213的政策,這標志著中共從整體上改變了以往對待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的政策,這與對中國社會經濟特征的分析是一致的。除此之外,之前對中國社會分析的理論框架,隨后也得到的借鑒。在1939年12月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部分“現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內容就借鑒了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基本分析[8]261。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隨著革命和建設實踐的發展,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也有了很大發展,并提出了許多理論觀點。這些對資本主義經濟認識的理論觀點,標志著的資本主義經濟觀已經成熟。這可以從之后提出“關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建議”都被中共中央接受并形成全黨的政策得到證明。首先,發展新式資本主義。1942年10月,在《發展新式資本主義》一文中開創性地提出“發展新式資本主義”的理論見解。認為,“發展新式資本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全部方向和內容,也是將來社會主義的前提”,“將來社會主義又要靠發展新式資本主義發展做基礎”,“只有走過新式資本主義的第一步,才能走社會主義的第二步”[9]184-186。1944年3月,指出:“現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10]110顯然,吸收了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觀點。其次,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五種成分。在主持東北合江省工作期間,從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視角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基本上“由五種經濟成分所構成,這就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凡國營經濟及合作社經濟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相當的發展,在生產與交換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設與積極意義”[11]29,39。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五種經濟成分”的觀點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被全黨接受并采納,成為指導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方針政策。最后,發展國家資本主義。1948年明確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從國家需要出發,吸引私人資本來為國家服務,并把私人資本置于國家的管理與監督之下,使之成為國民經濟建設計劃的有機的一部分”[11]38。隨即“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式”被全黨接受,并成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政策。新中國建立后,“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工商業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形式,這充分體現出對資本主義經濟分析研究的前瞻性和時效性。相對于形成時期而言,資本主義經濟觀成熟時期的理論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創新。對中國官僚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的區別,對資本主義經濟與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關系,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地位、作用和基本特征都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理論概括,使他的資本主義經濟觀進一步完善,并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理論體系。從中也可以看出理論上的進步與思想的成熟是同步的。在思想方法上,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從教條主義的誤區中擺脫出來,科學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獨立地提出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在理論內容上,他提出的“發展新式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等開創性理論觀點,豐富和發展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理論;在政策服務和建議上,他提出的“支持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理論觀點,也成為后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四、資本主義經濟觀的發展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經濟觀主要是以探索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為主旨的;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的資本主義經濟觀必然要承擔起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問題的重任。如果說資本主義經濟觀在革命時期解決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那么在建設時期,他的資本主義經濟觀所關注的則是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觀的理論品質和發展歸宿。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觀的發展主要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提出“利用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的中間環節”的觀點。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面對在所有制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和經濟建設中出現的“左”傾錯誤,他對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角度闡述社會化大生產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同點,提出“利用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的中間環節”的觀點[11]410。按照他的這種對資本主義經濟觀的理解,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要建立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之上;二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和理論分析是為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這就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觀在新時期的理論形態,使得他的資本主義經濟觀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其次,提出“保護個體所有制發展”的觀點。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提出:“現在在農村里,個人所有的東西比消費品還多一些,如自留地、小農具。至于消費品個人所有制,到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存在的。”[11]335這是針對“”期間的“共產風”“大鍋飯”等問題提出的政策建議。現在看來,在我國當時農業生產力發展條件下,農村的生產經營和分配方式最合適的就是維持小生產者的經營方式。這與改革開放以來對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調整是一致的。再次,提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完全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某些方式和條件”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同之處就是生產的社會化特征,這種共同特征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某些方式和條件。1961年8月,指出:“只要說明《資本論》的范疇在社會主義起了根本的質的變化之后,這些范疇的充分運用,不但無害,而且有利。因為這些范疇雖然表現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性,但也表現出一切社會化生產的共同性。”[11]376-377這表現出對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創新性認識,即資本主義經濟的某些方式和手段可以為社會主義建設所利用。最后,提出“發展集貿市場,改善市場管理”的建議。
1962年7月,針對集市貿易等問題,提出發展集貿市場,改善市場管理的建議,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要保持集市貿易的經常化和固定化;二是要規范商業流通秩序,建立小商小販登記和相應的稅收制度;三是國家要保持市場工農業產品的供求平衡;四是國家要運用貨幣和政策手段調節市場。指出,如果采取以上辦法,“今后我國市場和物價的發展趨勢,大體可以預測如下:隨著國家財政情況的好轉,工農業產品的增多,通貨膨脹的消除,市場物價會逐漸下降”[11]437。國家開放市場,并允許小商小販合法進入市場,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對政策禁區的一次沖擊,在今天看來,無疑是協調工農業關系、促進生產發展的有效措施。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為工具,分析資本主義經濟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關系,形成了自己的資本主義經濟觀。對資本主義經濟認識,始終堅持生產力是最終決定性因素的方法論;對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權關系的認識,始終都是根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兩重性來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對政權建設的作用;對不同經濟成分相互關系的認識,認為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最終消滅資本主義經濟。他的這些理論觀點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理論指導,許多觀點在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