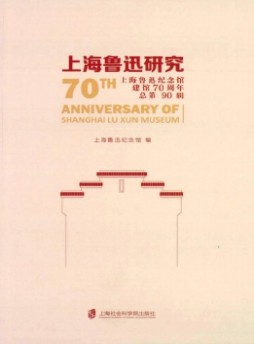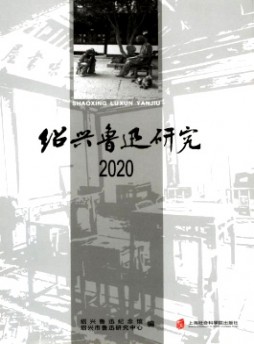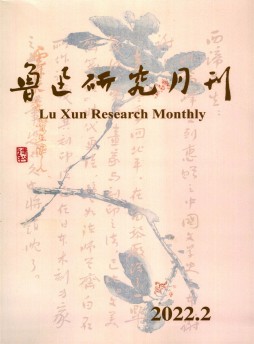魯迅小說與我國古典文學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魯迅小說與我國古典文學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魯迅小說的研究幾乎與魯迅小說的創作是同步的,但總的來說,在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的研究中,學者多注意的是其思想意蘊以及與國外的關系,而少論及與中國文學傳統的關系。因此,魯迅小說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關系的研究并沒有顯出思想研究那樣的明顯分期,而是大致呈現出比較薄弱的狀態。大體說來,可以將之分為三個時期:建國前、開放前和開放后。
建國前:精當的直感
對于魯迅小說的研究,建國前尤其是魯迅去世以前的研究多為一種直觀的解讀,可以說并沒有真正關注到其與古典傳統的關系,而是從其作品中直觀地感覺到傳統的影子,所以論述中多點到為止,而少展開論述和深入挖掘。后期受泛化以后的馬列學說影響,獲得了社會解析的角度,但同時也減弱甚至喪失了其他角度所可能達到的高度。這些角度包括考察與古典文學傳統的關系。例如魯迅小說的重要批評者茅盾,其1923年發表的《讀〈吶喊〉》肯定魯迅小說的新形式成為著名論點,但卻只字未提新形式的任何淵源。在二十多年后即1948年9月寫的《論魯迅的小說》這樣一篇綜論中,也只有這樣一句:“中國古文化的傳統如果也還有什么曾在前期的魯迅思想中占了相當比重的,恐怕是莊子思想。”[1]這一論述既未正面涉及文學傳統,更是立足于否定傳統思想將魯迅所受的古典傳統影響描述得模模糊糊。而且,從作者的語氣可以看出,他并無意于挖掘魯迅小說中所蘊涵的古典傳統,而更多的是有意避開這一問題。這一立場和思路深深地影響了后世,成為魯迅小說與中國古典傳統關系不清的重要原因。
對魯迅小說持否定態度的成仿吾等人也同樣如此。他于1924年在《創造季刊》發表的《〈吶喊〉的評論》中這樣提到魯迅小說:“除了那篇《故鄉》之外,我好象覺得我所讀的是半世紀前或一世紀以前的作品。”[2]在這里,立足于否定魯迅小說而將之比為古典作品,但又顯然沒有深入細致地考察,所以只是“好象覺得”,而沒有說出魯迅小說與古典作品的相似甚或相同之處。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成仿吾對魯迅小說中外國文學的影響則認識得清楚得多。同樣在這篇文章中,有這樣的論斷:“前期的幾篇,可以概括為自然主義的作品。”[3]雖然他同樣沒有做任何闡釋分析,但毫無疑問,他對魯迅小說中外國文學的影響做了定性,卻對中國傳統的影子辨認不清。最早對魯迅小說進行評說的傅斯年在他第一次評論魯迅小說時就敏銳地感到魯迅小說和古典文學傳統的關系。傅斯年將《狂人日記》論定為“以寫實的筆法來達到寄托的旨趣。”[4]這里,“寫實筆法”和“寄托旨趣”顯然是古典文學評論的范疇和術語。用這一范疇和術語來直觀地界定魯迅的《狂人日記》,正是體現了魯迅小說中一目了然的與古典文學的關系。而此后魯迅批評的重要人物李長之雖然以精神分析著稱于當時后世,但他在評價魯迅小說的藝術價值和不足時,顯然采用的不是西方的人物論、情節論、環境論等等理論,而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的品評文章的方式。在《魯迅批判》第三部分“魯迅作品之藝術的考察”中,李長之不但一再強調魯迅小說的抒情性(即使他并沒指出這一特點與長于抒情的中國古典文學的關系),而且他分析魯迅小說的優劣時完全用的是古典文學的視角和術語。他評價魯迅小說好壞在于完整與否,這與古典文學中講究神完氣足可以說一脈相承。而是否完整,也主要是從文筆情韻和節奏來看。他認為好的作品中,“《風波》以從容勝,《離婚》以凝練勝”;“《阿Q正傳》的風格之有似乎《風波》……也就仍是從容”;“講祥林嫂的故事的《祝福》”,“文字特別有一種舒暢之感”;《傷逝》則是“比較更純粹的抒情文字”。而他認為壞的作品,或者是因為落單,或者是因為沉悶無生氣,或者是因為結局太潦草……這種批評方式本身昭示著魯迅小說與古典文學傳統血肉相關的內在聯系。[5]
但最早對魯迅小說與古典文學傳統的關系有著相當的自覺的卻是寫過著名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周作人。他在1923年以仲密的筆名發表于《〈晨報〉副刊》的《自己的園地•阿Q正傳》中首先對這一小說進行了基本的界定:“《阿Q正傳》是一篇諷刺小說,……是古典的寫實的作品。”[6]接下來周作人對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比較了《阿Q正傳》與《鏡花緣》、《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古典小說的異同。“《阿Q正傳》里的諷刺在中國歷代文學中最為少見,因為他多是反語(Irony),便是所謂冷的諷刺——冷嘲。中國近代小說只有《鏡花緣》與《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點相近。《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多是熱罵,性質很是不同,雖然這些也是屬于諷刺小說的范圍之內的。”[6]在將《阿Q正傳》放在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中進行考察之后,周作人判定:“《阿Q正傳》的筆法的來源,據我所知道是從外國短篇小說而來的。其中以俄國的果戈理與波蘭的顯克微支最為顯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鷗外兩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響。”[6]但是,周作人在做了這樣的判定后,又筆鋒一轉,這樣說道:“但是國民性真是奇妙的東西,這篇小說里收納這許多外國的分子,但其結果,對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陸的迫壓的氣氛而沒有那‘笑中的淚’,對于日本有了他的東方的奇異的花樣而沒有那‘徘味’。……多理性而少情熱,多憎而少愛,這個結果便造成了satyiio,satire(山靈的諷刺),在這一點上卻與‘英國狂生’斯威夫德有點相近了。”[6]周作人在具體分析了魯迅小說與國外小說諷刺藝術的不同之后,對阿Q這一形象做了一個著名的總結:“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實社會里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6]雖然他沒對這一形象的文學傳統做深入辨析,但從“傳統的結晶”這一基本論斷,可以見到一向關注中國新文學源流的周作人的真知灼見。
郭沫若的《莊子與魯迅》和許壽裳的《屈原與魯迅》可以說是專門論及魯迅與傳統文學關系的文章,雖然并非專門著力于魯迅小說。郭文寫于1940年。但他寫這篇文章的緣起卻是“年青一代的人要讀魯迅的作品恐怕沒有注解不行了”,[7]寫成這篇小文只是希望“對于將來的注釋或一般讀者,能夠提供若干的參考”,[7]所以全文主要是列舉了許多魯迅作品中得之于莊子的語匯、句法、故事等等,從而證明魯迅受莊子的影響頗多,卻沒對莊子的影響做深入探討。不過,郭文仍然有兩個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一是他在文中首先提到的對魯迅文章始終如一的直觀感覺。“我在日本初讀的時候,感覺著魯迅頗受莊子的影響,在最近的復讀上,這感覺又加深了一層。因為魯迅愛用莊子所獨有的詞匯,愛引莊子的話,愛取《莊子》書中的故事為題材而從事創作,在文辭上贊美過莊子,在思想上不免有多少莊子的反映,無論是順是逆。”[7]從這段描述中可知,郭沫若是自始至終深切地感覺到莊子對魯迅的影響,這和魯迅后來自己所說的中些莊子的毒是一致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郭沫若對魯迅文中錯引莊子語匯做了獨到的具有深遠意義的分析,盡管只是淺嘗輒止。他認為:“把他早年的文字和晚年的文字并起來看,可以知道魯迅在早年實在是熟讀《莊子》的人,所以詞匯和語法,都留下了顯明的痕跡。但到晚年來,盡力想從古人的影響之下擺脫出來《,莊子》是丟生了。因早年熟讀,所以有不少辭句活在記憶里,但晚年丟生,所以有些實在不免‘記的不真確’。”[7]這里雖然只論及莊子的熟與生、顯與隱,但卻觸及到一個關于文學接受當中潛移默化還是主動追求的問題。新文學作家們往往在年少時都練就傳統文學的童子功,但他們卻往往主動取法西方。這是兩種不同的接受狀態,也將帶來不同的接受效果。主動取法容易痕跡宛然,卻難免未融化吸收;潛移默化雖然無跡可求,卻是揮之不去,令人一望便知而又難以言傳。這是追溯文學淵源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往往為人忽略,郭沫若此處也并未將之上升為一個值得考察的重要問題,而且后來者也鮮有涉及于此。許壽裳的《屈原與魯迅》本是《亡友魯迅印象記》中的一節,主要是仿照郭沫若將魯迅舊詩中得之于屈原的詞句“很粗略地摘一點出來”。[8]不過,作為與魯迅比較親近的朋友,他提到魯迅喜好屈原的一些旁證,比之郭沫若完全從文本中得的印象更為豐富。馮雪峰曾經和魯迅談到過當時的文學批評應求出和中國文學史的聯系,而在他那篇得到魯迅肯定并修改的《關于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給捷克譯者寫的幾句話》中,馮雪峰論及魯迅和中國文學史上的文學家在精神上的聯系。作者認為:“中國舊有的好的文學傳統及豐富的中國歷史演變的教訓,也深刻地影響著魯迅的文學與思想。他的文學事業,有著明顯的深刻的中國特色,特別是他的散文的形式與氣質。其次,在文學者的人格與人事關系的一點上,魯迅是和中國文學史上的壯烈不朽的屈原、陶潛、杜甫等,連成一個精神上的系統。這些大詩人,都是有著偉大的人格和深刻的社會熱情的人,魯迅在思想上當然是新的,不同的,但作為一個中國文學者,在對于社會的熱情,及其不屈不撓的精神,顯示了中國民族與文化的可尊敬的一方面,魯迅是繼承了他們的一脈的。”[9]比之周作人單純從文學藝術手法和形象傳統來論述魯迅和古典文學傳統的關系,馮雪峰從人格和精神的角度來論述,應該說更進了一步。雖然他時時不忘魯迅的新思想,而且也更多地從魯迅散文來論述,但精神氣質和人格,無疑會影響到一個作家創作的各個方面,而論者在論述時,也必然從其作品整體中才能審視和把握其精神和人格。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魯迅自己的態度。魯迅自己說過的“全仗著先前所看的百十來篇外國小說開始創作”一再被人引用,但人們卻往往忘記和忽略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追溯了自己小說的外國文學淵源后緊接著的一段話:“以后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畫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10]這里,有著高度自覺的魯迅非常明確地說明自己后來的創作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但論者或許處于前面所說的心態往往對這一說明置之不理,仿佛魯迅終身都受著外國作家非常深入的影響,甚至只是外國作品的模仿者。
在孫伏園寫的《魯迅先生二三事》中,曾經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劉半農贈送過魯迅一副聯語:“托尼學說,魏晉文章”,“當時的朋友都認為這副聯語很恰當,魯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對。”[11]這里,將魯迅文學作品比擬為“魏晉文章”,不單明白地點出了魯迅文學作品和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關系,而且更是明確地指出了在復雜豐富的文學傳統中魯迅的選擇,盡管也許這里更多地是指魯迅的雜文而不是小說,盡管聯語只有極其精練的八個字,但毫無疑問,冉紅音:魯迅小說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研究綜述精練的論斷往往直指要害,而且肯定包含了魯迅的所有創作。魯迅并不反對,可以說是比較明確地承認了當時朋友認為很恰當的說法。也更加見出魯迅小說和文學傳統的關系非同小可。但是,新文學創造的追求和革命的追求使魯迅小說與傳統的關系要么被視而不見,要么見而不說,即使說了,也只心有戚戚而絕不多說,這有待于新文學確立之后以及革命任務完成之后才能充分展開。
開放前:范式的確立
新中國建立后,對魯迅小說和古典文學傳統關系的研究脫離了直觀感性的論斷,而著力于從魯迅對中國文學傳統的接受及其自身所受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來論述。確立這一范式的是本來致力于研究古典文學的王瑤先生。他的《魯迅對于中國文學遺產的態度和他所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完成于1950年4月5日。在這篇影響很大的論文中,作者一開篇就下了一個基本的論斷:“誠如馮雪峰先生所說,魯迅的文學思想并非中國傳統文學所培養成的;但也如他死后上海群眾用寫著‘民族魂’字樣的旗子給他蓋棺一樣,他的思想和作品同時又無不浸潤著中國民族的長久的優秀的戰斗傳統。”[12“]從他自己思想發展和所受的影響上,從他的作品的某些風格和表現方式上,都可以看出傳統文學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和影響。這些影響所給予魯迅的,也并不是在他思想或作品中的不重要部分,或比較消極方面的部分;反之,幾乎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和形成他創作的特色中,中國傳統文學的影響都占著很大的因素,而且是和整個的魯迅精神分不開的。”[12]在這里,由于時代使然,王瑤將魯迅所受的中國古典文學傳統論定為“戰斗傳統”,雖然有些失之簡單,但他第一次正面地充分地肯定了魯迅和傳統文學的關系,并且較為周詳地從“進”和“出”兩個角度來論述這一問題。“進”是指魯迅對傳統文學的接受,“出”是指傳統文學影響魯迅后在其作品中的傳承和表現。在作了這樣的基本判斷后,王瑤從以下六個方面展開了論述:一、關于接受文學遺產;二、讀什么書,如何讀法;三、魏晉文章;四、小說手法;五、雜文特色;六、研究和創作的一致。王瑤首先肯定了魯迅對傳統文學遺產“占有和挑選”的態度,其目的雖然主要是為被推翻的舊文學尋找其在新文民辦高等教育研究學中的合法性,但這一態度的辨析也側面說明了魯迅古文修養的全面深厚和文學眼光的敏銳獨到,對于達到文學自覺以后的魯迅與古典文學傳統的關系,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在為舊文學的影響確定了合法性后,王瑤考察了魯迅讀書的經歷、范圍和方法,指出魯迅從小所培養的對于歷史尤其是野史筆記的興趣以及他廣泛的涉獵范圍和不囿于經的讀書態度,并進而辨析出在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中,對魯迅影響最深的是魏晉文章,是莊子、屈原、嵇康和阮籍等人。他們影響魯迅的,主要是“憤世的解放要求和懷疑的個人精神”和“剛健不撓的反抗舊俗精神”,也有“清峻通脫的文風”。并進而指認出魯迅“小說雜文的簡勁樸實”和“魏晉風格有一脈相通之處”。[13]可以看出,王文通過豐富的文化習染過程的考察,將魯迅對古典文學傳統的接受和選擇落到了實處,夯實了魯迅作品和古典文學的關系的基礎,并詳實地分辨出魯迅所受傳統文學影響的側重點。在考察了文學接受根源之后,王文考察了魯迅的小說和雜文創作,將古典文學在魯迅小說和雜文中的表現揭示了出來,并將魯迅的古典文學研究作為佐證,從而揭示出魯迅小說創作中簡潔的語言、白描手法和諷刺藝術等顯著特色都得之于古典文學傳統的滋養。而王瑤1956年發表在《文藝報》上的文章《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與此文觀點、思路基本一致,只是更集中于魯迅作品中古典文學的滋養。以后論者大致不出這三個方面:影響的發生、影響的表現和魯迅的文藝觀。
但是,王瑤的論述首先因其背景而難免言之不盡,時時提防著可能襲來的打擊而預先左支右擋。比如,作者不時地分辨著消極和積極等似乎是當時必須涉及的問題。同時,接受遺產這一立場也常常使其關系變得簡單化,似乎就是批判地“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其論述范圍也因而變得狹窄,與魯迅本身的狀態有一定距離。其后論文多沿此路而行,但基本上是在此范圍內作細部論述,這些細部論述數量眾多,但由于歷史的原因,成果多集中于小說筆法上,而對精神聯系多曲解附會,而且小說筆法也多集中于諷刺藝術、白描手法、寫意手法以及語言的簡潔上。許懷中的《魯迅與中國古典小說》是一本研究魯迅與古典文學傳統關系頗為重要的專著,這本書長于魯迅對待中國古典小說的論述,用了絕大多數篇幅詳細論述了魯迅的古典小說研究工作以及魯迅對古典小說的發現、看法和貢獻,但魯迅小說創作和古典小說關系的論述則明顯不足。雖然作者在序論中也承認“在魯迅的全部創作實踐中,無不浸潤著中國古典小說的滋養,也無不牽連著與中國古典小說家連結的絲縷。中國古典小說是構成魯迅創作特色和民族風格的重要因素。”[14]但作者“研究魯迅與中國小說的關系”,出發點在于“不但有助于了解魯迅的思想和創作,看出他對我國文化遺產的態度,而且將幫助我們更好地批判繼承我國古典文學遺產,發展社會主義的新文藝。”[14]也就是說,他并沒有與這一問題正面相遇,而是將這一問題的考察作為工具,所以不但未能達到王瑤的高度,而且因為特殊歷史風云之后所蒙的煙塵,比附之處不少。
著名學者楊義的《魯迅小說綜論》將魯迅小說放到古今中外的歷史體系中進行考察,較為深入地論述了魯迅小說與中外文學的聯系,是王瑤以后最為重要的關注這一問題的論著。雖然全書總共只有四章,但他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來論述魯迅小說與本國文學的關系,足見楊義對這一問題的重視。他沿襲王瑤而又有所發展,這種發展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論述更為充分細致。楊義不但充分肯定了魯迅小說和傳統文學藝術的血肉相連的關系,并且進一步論述了魯迅對民族文化承傳和擇取的特點。楊義認為:“他(指魯迅)的小說藝術和我國的傳統的文學藝術有著血肉相關、氣脈貫通的歷史聯系,具有獨特而鮮明的民族氣派和民族風格。外采現代小說的格式,內保民族文學的氣質,融合成高度獨創的藝術肌體,這是魯迅小說的顯著的美學特征。”[15]“他對這種民族血脈的承傳和擇取,所表現的特點一是‘博’,二是‘通’。在古代詩歌方面,他對屈原、陶潛、李賀、李商隱、龔自珍都有濃厚的興趣。在古代散文方面,他對莊子、嵇康以及近代的梁啟超、章太炎都有足夠的重視。在小說方面,他的修養更是堪稱獨步,對唐人傳奇以至《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紅樓夢》都有深刻而獨到的體會。在美術方面,在自漢代石刻、六朝造像、唐代佛畫、明人版畫、清代小說插圖,直到近代的陳衡恪、齊白石的寫意畫,有著廣泛的愛好和傾注極大的熱情。他的眼光絕不拘囿于某一個朝代,某幾個名人,不局限于某一個藝術品種,某幾部名作,而是對于眾多朝代、眾多作品、眾多流派博取廣搜,研究它們的精神氣質,揣摩它們的辭采筆法,探究它們的源流升降,從中加以分析比較,捕捉住我們民族文學藝術的‘血脈’,心神所注,往往能見人所未見,道人所未道。而且他能夠觸類旁通,化為自己的血肉。”[16]二是論述古典文學傳統的影響采用了人格養成的角度,比之王瑤更深入推進了一層。“文如其人”雖然不是將文和人進行簡單地對應,但毫無疑問,誠如魯迅所說:“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17]人格和文學的關系不但在古代早就被認識到,魯迅本身也高度重視文章和人格的關系。如果說王瑤主要是從文學習染及偏好來論述魯迅所受古典文學傳統最鮮明的影響,楊義則更著力于發掘魯迅融會貫通古典文學甚至是古典文化中的各種因素而表現出的鮮明的民族氣派和風格。他從精神氣質上進行了挖掘,從人格形成的角度深入論述了魯迅所受古典文學文化傳統的內在影響。楊義認為:“魯迅小說的人物大都十分平凡,情節也并不怪誕和驚險,但卻有著猶如英雄史詩一般搏擊人心的力量,有著一種不可抗拒的崇高美。把一種向前的力和詩情的美結合起來,這是魯迅小說‘總而持之,條而貫之’的內在格調。這種成功與小說內蘊的作家的人格美密切聯系。作家的人格美,是魯迅小說的崇高的力量的基本條件之一……這種人格美又和我國歷史上一批優秀作家的高尚人格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8]很顯然,楊義更強調魯迅接受傳統文學影響時的吸收狀態以及傳統文學對魯迅精神氣質形成所起的作用,將王瑤只粗略提到的問題進行了詳細論述,不但遠溯出歷史上優秀文學家的人格影響,同時發現近代章太炎較為直接的人格影響和浙西文化等地方文化的浸潤,從而將魯迅與傳統文學的關系研究推進了一步。其三,楊義較為細致地論述了魯迅在創作小說時自覺的革新意識及其革新成果,比之只指認其歷史影響更進一步,在歷史的鏈條中考察了推陳出新的過程,從而也真正將融會貫通落到了實處。不過,楊義在改革開放初期進行的這項研究,難免帶上時代的烙印,革命論和階級論仍然是權威性的話語,成為他研究魯迅小說和中外文學關系的基礎和出發點,所以仍然難免歸結到革命現實主義這一簡單機械的概念上去。
開放后:薄弱的多向
80年代以來,隨著整個學術界的活力恢復,魯迅研究也獲得了很多突破和重大進展。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打破了原有的研究系統,富有開拓之功。從那以后,魯迅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漸漸變得多元、豐富,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近來有學者對魯迅研究進行總結,葉世祥從研究方式的角度將之歸納為四種研究范式,王家平則從研究范疇的角度清理出六大研究系統。這種歸納和清理工作都顯示著新時期以來魯迅研究的進展和開拓。在眾多的研究中,最有成績的是承接思想革命而來的對思想、精神、心靈、心理等等的深入探索和研究。汪暉的《反抗絕望》、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是其中的代表。文本重讀雖然涉及到了多方面的內容,但主要也在這一方面。同時,形式研究得到了重視,而在眾多的形式研究中,多數學者集中于敘事學的研究。葉世祥的《魯迅小說的形式意義》則是形式研究方面的第一本專著,較為全面地論述了魯迅小說的形式問題。
但是,在眾多的突破和探討中,魯迅小說與古典文學傳統關系的清理則相對薄弱,與考據之學等同為薄弱環節。即使是在1986年興起的文化熱潮中,曾經召開過“魯迅與中外文化研討會”,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可謂已成顯學,這一問題也成為熱點,大批的論文和專著在此時面世,但和其他文化研究一樣,貼文化標簽者多,內容堅實,分析透辟者少,而且力作中如林非的《魯迅與中國文化》、陳方競的《魯迅與浙東文化》等也大都致力于分析其思想意識,而對文學傳統往往淺嘗輒止,或者順帶一筆。專門論述很少,細致深入的剖析更少。除了相對而言關注較少外,這一問題的研究所以為薄弱環節,還表現在涉及這一問題的研究論文大多在低水平上重復,專著則幾乎沒有。究其原因,既與眾多學人認為魯迅研究已經飽和從而忙著開拓新的研究對象有關,也與研究思路的僵化有關。但另一方面,九十年代以來,作為整體的現代文學和古典文學傳統的關系漸漸引起人們的重視,出現了一些研究這一問題的專著和論文。有的立足于古典文學向現代文學的延伸,如董乃斌1994年發表在文學遺產的論文《現代小說觀念與中國古典小說》,有的則是現代文學向古典文學的溯源,如1996年發表于《魯迅研究月刊》第九期的《魯迅小說中“散文化”傾向形成的文化歷史背景》。其中比較重要的是方錫德著的《中國現代小說與文學傳統》和高旭東的《五四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高著完成于2000年,主要論述了五四文學對中國文學傳統的突破。雖然他基于五四文學是西方文學的一個支流的觀點,著重于五四文學相對古典文學的新變,而且五四文學這一概念的范疇也過于狹窄,同時,他在論述這一問題時,將諸如魯迅、周作人這樣的大家經常置之不顧,但他將五四文學放到中外古今的大文化背景中,從中外文學的沖突矛盾中來進行考察,這一路向毫無疑問是有啟發意義的。出版于1992年《中國現代小說與文學傳統》的啟發意義則更直接明顯。這本著作是第一次較為全面系統地探討中國現代小說與古代文學的關系的專著。作者顯然對于現代小說與文學傳統關系的復雜性和內在性有著較為充分的自覺和反省。因此他考察了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現代作家接受古典文學的不同狀態,恰當地概括為民族文學傳統的自然流露、文人文學傳統的主動探索和民間文學傳統的自覺接受,而在他重點探討文人文學傳統時著力于發憤精神、史傳意識、抒情風貌、意境美感和白話文體幾方面,也是極有見地的。但是,這樣的總體研究以其宏闊見長,卻難以細致具體,魯迅研究領域一方面由于重精神、心靈向度的挖掘而忽略其他,另一方面也由于魯迅研究的充分而常常讓后來者望而止步。所以,盡管方錫德早在十年前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值得深入的維度,但一直后繼乏人。近年鮮有關于魯迅小說和古典文學傳統關系的力作問世。
相對而言,孫昌熙的《魯迅“小說史學”初探》和何錫章的《魯迅讀書生涯》雖然并不是自覺地直接地研究這一問題的著作,但卻從外圍為深入研究這一問題的復雜性打下了基礎。孫著出版于1988年,可以說是多年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教學的結晶。其中三章雖然是其所帶研究生碩士論文的精華部分,但大部分為其親筆所寫,而且其研究生的碩士論文在題目選擇、研究思路和寫作框架等方面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說是孫自己的。該著雖然重點在魯迅“小說史學”的建立及其形態,但魯迅對待古典小說的民辦高等教育研究理性態度及其小說史觀念本身與他的創作有著極為緊密的關系,而且,作者注意到了不同作品與魯迅關系的差別,因此仍然有其積極意義。何錫章的《魯迅讀書生涯》是中國名人讀書生涯系列叢書中的一種,本意是通過名人的讀書來教導后學,雖然并非新見疊出,但卻因其關注的全面而提供了更多的材料,比之簡單論述魯迅與某一種文化傳統的關系更具有比較和系統的意義。
但是,總的說來,這一時期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是薄弱的,但這種薄弱并非研究已經成熟的表現。相反,關于這一課題,還有不少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首先是接受狀態沒有得到認真清理。雖然早在建國之初,王瑤一直強調現代文學中的外來影響是自覺追求的,而民族傳統則是自然形成的,[19]但他并沒有深入探究自然形成的民族傳統在魯迅小說中的表現形態。一般說來,自然形成的影響一望即知,卻無跡可求,自覺追求的影響則往往還沒能夠融合無間,所以痕跡宛然,卻又難免生硬。而且,在自覺追求外來影響時,一定會和自身傳統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一個聯系就是將外來因素內化即中國化。同時,在接受狀態中,年齡的因素一直受到忽視,但實際上,年少時吸納共鳴和成年以后批判比較的讀書狀態對人的影響是很不一樣的。現代文學眾多作家接受國學往往在年少時,接受西學則往往在成年以后,因此,國學的影響往往潛移默化深潛血液,不招即來卻揮之不去。作家的精神結構與其創作中對文學傳統的接受也有著密切的關系,近年學者們在魯迅精神結構的探討中取得的學術成果堪稱斐然,這為魯迅小說創作中文學傳統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這方面的研究卻比較欠缺。其次,由于學制的關系,過去的學者考慮影響魯迅的文學傳統時,往往條塊分割,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者著力于發掘魯迅小說中的外國文學因素,有著較為深厚的中國文學背景的學者則強調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兩方面對話很少。這一傾向也表現在整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內。將現代文學當成西方文學的一支和將現代文學當成是古典文學的繼承這兩種觀點的對立局面的形成,與這一情況不無關系。在魯迅小說中,中外文學因素關系極為復雜,交錯、對立、相通、互補、沖突、包含、轉化等等狀態此起彼伏,糾結纏繞,是一個極難厘清的問題。這需要相當的學養方能從事這一研究,就目前的學術體制而言,要進行這一問題的探討,只怕尚需時日。其三,古典文學傳統的獨特性沒有得到充分重視。誠然,古典文學傳統和思想傳統、哲學傳統、文化傳統有著很密切的關系,但文學傳統有其自身的獨特性。文學傳統研究固然應該以其他傳統的研究為背景,但更應該側重于文學傳統的獨特范疇諸如意蘊、形象、語言、氣質和手法的研究。
當前的文學研究中,現代性是一個熱點。關注現代性,自然以古典文學為參照。從前面的論述可知,現代文學研究一直對中國古典文學傳統有意無意地忽視。這種忽視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為現代文學主動地取法西方的態度使得研究者多注意與西方文學的關系。二是因為批判繼承文化遺產的論斷借助權力的作用成了難以撼動的權威,并且將魯迅的雜感《拿來主義》當成理性論斷加以佐證,從而使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關系研究處于一種時時涉及,卻難以深入的格局。相對而言,后者對于研究現代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的關系更是一個障礙,因為它給人一種假象:似乎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系研究得挺充分的,但都不外是在“批判繼承傳統”這一范圍中打轉,仿佛傳統成了一個死的對象,等著現代人用更具真理性的眼光來審視、批判、辨別和吸取。這樣一來,不但古典文學傳統成了被剝離的空殼,而且很難真正辯清現代文學的生長及其狀態。現代文學的主要文學形式是小說,研究現代小說和古典小說乃至古典文學的關系,應該是現代文學和古典文學關系研究中的重中之重。魯迅不單是現代文學中的小說大家,更是對文學傳統有著充分自覺的第一人。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第一部國人寫的中國小說史,至今無人能出其范圍。因此,研究魯迅小說和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關系,無疑具有經典個案的意義。將這一意義發掘出來,不論對于魯迅研究,還是現代文學研究,還是古典文學研究甚至外國文學的研究,都應該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