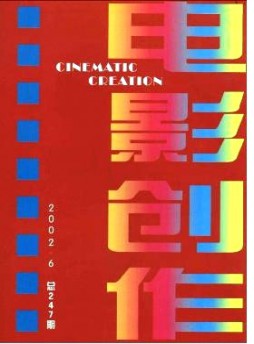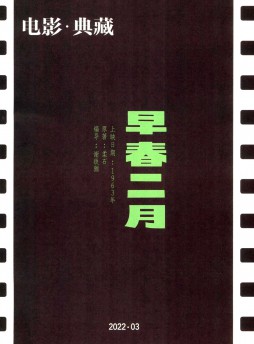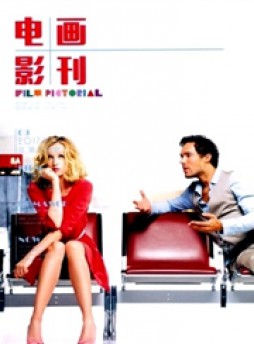電影與戲劇的語用功能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電影與戲劇的語用功能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為一種時空復合、視聽兼收的藝術,電影借助于影像藝術獨特的符號系統,不可避免地具有敘事性。在語言交際能力方面,此處所指的電影語言就是:“電影藝術家用以與觀眾交流的、表達其本人對客觀世界看法與主張的語言工具。”林賽認為:電影與建筑、雕塑、詩歌一樣,以不同形式表述人類對審美感受的共同體驗。閔斯特堡則提出:電影觀眾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擺脫了現實生活中時間與空間對思維的束縛,自由地運用想象力,建構另一個世界。倪祥保認為:明暗、光影、色彩、景別、景深角度、鏡頭、速度、人稱與意謂等是重要的電影敘事符碼。在著名符號學家羅蘭•巴特看來,電影則是一種“綜合系統”,電影語言系統比自然語言和文字系統更加復雜,是聲音與連續性影像形成的聯合體。在電影語言學家眼中,蒙太奇、長鏡頭、意識流是電影語言的三種基本手段。而戲劇的語用表達符碼在T•考弗臧看來則可分為語言、語調、表情、動作、調度、化妝、發型、服裝、小道具、裝置、照明、音樂及音響效果等十三種。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曾就戲劇做了大量論述。亞里士多德把戲劇看作一種表演文本,既有文字敘事的共同點,又有表演自身的特點。葉長海在《中國戲劇學史稿》中提出將劇本、演員和觀眾看作戲劇的三個核心要素,提倡將關于演員的研究納入舞臺藝術研究,以強調演員表演對于展現故事的重要作用;而有些研究者則將目光投向了戲劇觀眾,將觀眾觀看的行為比作讀者的閱讀行為。從這個角度來看,觀眾欣賞戲劇的過程實際上是觀眾與導演、演員的交際過程,由此便產生了交際行為中的語用活動。就敘事學與戲劇的關系而言,學者們較多關注戲劇文本對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劇情發展的建構。例如在展現人物性格的敘事方法方面,荒誕派戲劇比較偏愛使用表現人物外部活動的手法。在《等待戈多》中,第一幕描寫了兩位主人公弗拉基米爾和愛斯特拉岡在一條荒蕪的小路上等待一個叫戈多的人。第二幕開場時兩人依舊等待如初。因為劇本無法像小說那樣對人物心理活動進行詳細的說明,這一劇本敘事的限制性反而被貝克特利用來有力地表現出單調、重復的人物外部行為上,成功地表達了對人類存在的意義的探索。
在符碼的語用敘事方面,電影與戲劇存在諸多差異。由于戲劇僅以舞臺這一有限的空間為演出陣地,其敘事功能受語用符碼數量的限制,不得不采用隱喻等方式將舞臺上無法直接布景表達的信息傳遞給觀眾,有時會因為觀眾的理解能力等因素的影響,直接造成演員與觀眾交際的語用失誤。在時間符碼表達層面,戲劇故事情節中的時間表達受舞臺上的表演時間及道具效果所限,角色行為不可能達到變換自如,時間的變換只能靠相關舞臺道具與布景的變換并通過類比、隱喻等方式來擴充觀眾的想象空間,以有限手段表現無限情節,這也正是戲劇舞臺敘事藝術的魅力所在。正是在這樣一種智力較量層面的間接交際,才使得戲劇語用功能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同戲劇敘事藝術相比,電影則通過鏡頭語言的變換及蒙太奇手段人為地制造出多個時空,從而實現猶如乘坐時間機器般地隨意進行時空穿梭。借助于高科技手段,電影的時空限制遠遠少于戲劇,可以隨意采取倒敘、插敘等手法,來去自如,貫古通今。在敘事結構方面,對于戲劇而言,其基本結構單位是“幕”。對于電影而言,鏡頭則是其基本敘事單位。電影語言就是由無數鏡頭詞匯的無縫組接完成的動態話語。在交際對象方面,無論電影還是戲劇都是編劇與導演指揮演職人員與觀眾的對話,只不過在這個交際行為過程中,又將涉及許許多多的更加細致、直接的交際行為。比如導演與編劇就劇情所進行的探討、與演員們的溝通,指揮,等等。只不過有區別的是,一旦演員們已經進入表演環節,對戲劇這種藝術形式來說,整個與觀眾的交際行為是完全不可逆的,是即時發生的。也就是說,戲劇表演過程中,在劇場里,舞臺上的演員們一旦進入角色,即已經開始了和觀眾的交流,而且在這個特殊的單方面的交流過程中(單方面是指:觀眾一般情況下不可以像真正的自然對話那樣有打斷對方或插話行為,亦即不會有多重話論的產生,除非發生由于對演出不滿而中途離開劇場或“喝倒彩”這種發泄不滿或抗議的情況,即出現單方面終止交際行為的語用效果),演員只是按照導演的指示,直線般地按時間順序持續表演,宛如某個人自言自語說著單口相聲或唱著獨角戲一般。可以說,沒有任何兩場演出會是完全相同的。這一點與電影拍攝過程中導演可以反復讓演員不斷重復表演同一場戲(只要他感到不滿意)是完全不同的。
在《等待戈多》的戲劇版演出過程中,劇中人物流浪漢愛斯特拉岡不僅要和弗拉基米爾(劇中另一人物)進行對話,還要通過他們二人的交流表演活動,與在場欣賞戲劇演出的觀眾進行交流,只因為他們是實時的舞臺演出,面對的是緊密關注劇情發展的觀眾。貝克特主張:“只有沒有情節、沒有動作的藝術才算得上真正的藝術。”這一指導思想在演出過程中得到了極大的體現。無論劇中演員的互動表演是否成功,他們與觀眾的交流卻立竿見影。有的觀眾在演出過程中毅然退場,有的則觀賞得津津有味。整個語用符碼的傳遞鏈條由以下環節構成:(荒誕的)現實社會、作者(承認社會的荒誕性)、演員(身體力行地表演著“荒誕”)、觀眾(觀看“荒誕”,接受“荒誕)。在上文中,現實世界的荒誕性及其存在性在作者的大腦中得到了極大的展現。作者必須通過演員的演出這一途徑與觀眾進行互動并最終取得理想交際結果,從而使自己對社會的個人看法得到重大普及。因此,戲劇演出過程中編劇、演員與觀眾的交流會有多重“話論”的出現。當演員進行表演時,觀眾可能會因為對演出的不滿產生抵制情緒并毫不掩飾表現出來,從而對演員直接產生回應,在這種情況下,演員的演出情緒會受到負面影響。在不同場次的演出實踐中,受交際對象雙方頻繁更換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地點、不同場次的演出可能會由不同的演員承擔,而觀眾也會有所不同。在電影版《等待戈多》中,導演將和演員進行多次的交流,向其提供解讀劇本、熟悉臺詞的機會與可能,這就構成了電影中敘事結構的主要思路與環節。相關符碼的表意順序如下:(荒誕的)現實社會、導演(承認社會的荒誕性)、演員(身體力行地與導演進行驗證)、導演(承認社會的荒誕性)、觀眾們(觀看“荒誕”,接受“荒誕),最后引起共鳴。演員的演出可以一遍又一遍不間斷反復進行,直到導演滿意為止。這里便涉及多重話輪的使用。可以說,在導演與觀眾進行交流、演員與觀眾進行交流之前,導演將和演員進行多次反復溝通。而在演出過程中,整個銀幕的世界的那一部分不會受到任何觀眾由于對于電影內容滿意與否的干擾,無論觀眾如何反應,影片的播放進程始終不會被打斷。也就是說,電影攝制過程中出現的反復糾錯并不會出現在與觀眾的互動環節中。整個演出就是線性的單項信息傳遞過程。只有在電影播放完畢,觀眾的評論才會以另一種形式與演員們進行慰問評價。
無論是電影,還是戲劇,都是對客觀世界的反映。在傳遞信息的過程中,交際由此產生。相對而言,電影語言比戲劇語言在語用表達方面有更多可展現的內容、有更多可以借用的語言形式,等等。戲劇版《等待戈多》中,演員不得不借用舞臺道具的符碼隱喻來進行深層次目的性文本的表達,而電影版《等待戈多》中靜態的畫面則留給了觀眾更多的淡定、從容與思考。真實的小樹梢幾片綠葉的突然出現、燈光的時明時暗對時間變化的暗示都賦予了電影強大的符碼表意功能。電影攝制過程中,演員不必擔心如戲劇般的實時演出的緊張感,而只需要容忍與承受來自導演的壓力便可以使自己在最終的電影演出中定格。戲劇看起來似乎遠不止那么簡單。戲劇演出過程中沒有人能在觀眾的眾目睽睽之下敢于轉而求詢于導演,而只能無助地注重演出的各個細節。因此,電影的言語語用表達就好像有人喜歡多次反復修改稿件的寫作方式,而戲劇語言的語用表達則如同參加考試一般需要勇敢者一氣呵成。(本文作者:孫宇、王天昊單位: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人文學院)
擴展閱讀
- 1電影文化
- 2電影傳播
- 3電影現狀
- 4電影發展戰略電視電影
- 5深究傳統電影以及數碼電影結合
- 6電影海報設計
- 7電影類型思索
- 8電影文化闡釋
- 9英語電影欣賞設計
- 10電影中服裝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