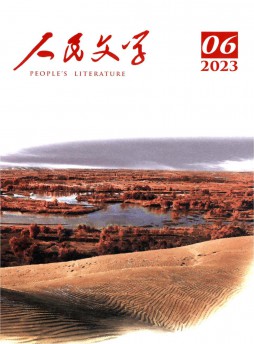人民文學的觀念嬗變與當代價值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人民文學的觀念嬗變與當代價值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人民文學”作為一個新的文藝范疇,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文藝觀的理論創新,是有別于“五四”時期“人的文學”的新的創作導向。通過對“人民”這一概念的歷史考察,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人民文學觀的生成和發展,進一步揭橥人民文學觀的當代價值。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的提出,對于文學創作有著指導性的作用,它的價值不僅在于滿足了文藝發展的需求,更在于對現實、社會、人的發展的推動作用。
“人民文學”作為一個新的文藝范疇,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文藝觀的理論創新,是有別于“五四”時期“人的文學”的新的創作導向。“人民文學”是立足于大眾,面向社會、群體的藝術概念,自提出至今,這一命題不斷得到豐富、發展的同時,卻少有學者對其由來作真正溯本清源的探析。筆者認為,真正廓清“人民文學”的生成、建構及發展脈絡,只著眼于1949年至今的這一段時期遠遠不夠。“人民文學”的核心詞匯是人民,簡單的講,就是人民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問題;再者就是“人民的文學”,人民作為一個修飾語,屬于變量,“人民”一詞的內涵發生變化,“人民文學”的內涵亦有所變化。因此,要探討“人民文學”觀念的發展,首先要厘清“人民”這一概念的生成及發展。
一、中國視野下“人民”概念的歷史考察
“人民”一詞古已有之。在中國古籍中,“人民”一詞的出現不會晚于編纂《詩經》的時代,“質爾人民,謹爾侯度”(《詩經·抑》),[1](P435)其大意是:對待百姓有禮儀,謹遵法度講道理。這首詩是衛武公為諷刺周王室而作,同時也為自戒而作。這里的“人民”是一國之民眾、百姓。在《周禮》中“人民”一詞出現了3次,如“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輿其人民之數”(《周禮·大司徒》)、“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周禮·秋官司寇》)、“分其人民以居之”(《周禮·天官冢宰》)。[2](P148)此處的“人民”指平民、庶民,即這一方土地的人。在《管子》一書中,“人民”一詞多次出現,如:“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管子·侈靡》)、“其治人民也”(《管子·正世》)、“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管子·七法》)、“城域大而人民寡者”(《管子·八關》)、“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谷菽粟泉金”(《管子·輕重丁》)、“其人民習戰斗之道”(《管子·輕重戊》)。[3](P107)此書中“人民”出現6次,表達之意并不一致。《韓非子》出現過2次,如“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韓非子·五蠹》)[4](P698)在先秦之后,“人民”一詞出現的仍不多,在二十四史中,也只是在少數著作中鮮有出現,如,“人民和順”“人民蕃息”(《后漢書》),“人民怨嗟”“人民相食”(《魏書》),其使用意義也是指平民百姓。經上考證,“人民”一詞在我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出現,只是并未廣泛使用。近代以后,“人民”這一概念開始廣泛使用,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近代學術期刊,如“人民皆有戰心”(《萬國公報(上海)》)、“合天下城鎮之人民戶口而論”(《中西聞見錄》)、“論中西人民智愚”(《寰宇瑣記》)等[5](P93)經常使用“人民”這一概念。晚清開明人士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多次使用“人民”這一概念,“中國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地廣產豐”[6](P431),“各部落人民”、“本州人民”、“本地人民”等均出自《海國圖志》一書,這個時候,“人民”的內涵逐漸清晰化了,但也是沿襲了中國傳統文化“人民”的內涵,主要是指政治范疇意義的某一方土地上除君王官僚以外的社會多數成員。隨著洋務運動的孕育和發展,資產階級維新派受西方“人民主權”思想的影響,逐漸走出了中國傳統“人民”概念的困囿,嚴復認為“華人素斥西洋為夷狄,而不知此中人民,居民相與之誠”。西方無論君民都屬于人民,人民的不同群體間能做到誠、篤、愛與信等。[7](P141)梁啟超進一步認為“天下未有無人民而可稱之為國家者,亦未有無政府之為國家者,政府與人民,皆構造國家之要具也”[8](P138),梁啟超認識到人民的主體特性及重要性,這是中國“人民”思想的一大進步。孫中山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將“人民”的概念具體化“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9](P249)
孫中山站在時代的角度,從國家的生存狀態出發,將“人民”這一內涵具體化為民族之統一。1912年,“人民”一詞正式出現在我國第一部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下簡稱《約法》)中,該《約法》同時使用“國民”和“人民”兩個概念,在陳述主權時用的是“國民”,“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在規范權利的時候,用的是“人民”。第二章的標題為“人民”,內容皆為人民權利的規定,共計11條(第5條~第15條),其中第15條規定限制人民權利的條件。[10](P139)至此,“人民”一詞的內涵又發生轉變,“人民”不僅是作為國家的主體構成,而且還代表著個體,擁有屬于個人的權利,這其中隱含著普及性的意義。“人民”一詞作為政治范疇在不斷深化。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由西方語言轉譯成中國語言時,“人民”一詞最初沒有找到合適的與之對應的中國詞匯。雖然中國語言中的“民”義大致相若,但單純用“民”替代,又不能鮮明地表達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民”的基本含義,即社會最底層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者身份。因此,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民”字加上一個限制的前綴,庶民、平民、民眾之類的詞語頻率較高地出現在他們所撰寫的文章里。[11](P14)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為歡呼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所撰寫的演講稿就叫《庶民的勝利》。1928年“人民”一詞出現在的《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人民群眾的力量”、“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系”,“人民”一詞最終由作了權威的定義。新中國成立前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一文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12](P493)“人民”的概念第一次有了明晰的內涵指稱,從時代、國情的高度確定了“人民”內涵的真實具體性。之后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講到:“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人民的敵人。”[13](P205)在《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的講話》中再一次肯定了“人民”這一概念,“人民是什么?在現階段,人民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14](P386)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時期,“人民”的概念被賦予鮮明的階級性和現實性,區分人民的關鍵在于個人的階級屬性,確立了人民的對立面是敵人。到了新時期,“人民”由被動的客體性轉向能動的主體,鄧小平把人民視為真正的歷史創造者,社會實踐的主體,并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強調“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15](P23)在為人民服務的實踐中,把人民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與歸宿點,做到還權于民。此后,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使人民成為一切工作的中心所在,為我們從更高更深的層次理解人民地位、人民關系指明了方向。“人民”的內涵在觀照集體性的同時也指向了個體。
二、人民文學觀的引入和發展
對“人民”概念進行歷史的考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人民文學”。關于這一觀念的內涵,仍需用歷史的眼光去考察。早在19世紀40年代,恩格斯就提出過“文藝為什么人”這一問題,并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文藝應當“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16](P224)。19世紀80年代,恩格斯又進一步鼓勵作家,要努力表現工人階級的反抗和斗爭,他指出:“工人階級對他們四周的壓迫環境所進行的叛逆的反抗,他們為恢復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劇烈的努力———半自覺的或自覺的,都屬于歷史,因而也應該在現實主義領域內占有自己的地位。”[17](P462)后來,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寫道:“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的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18](P375)對于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來說,寫作是無產階級總的事業中的一部分,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是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寫作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決定著寫作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重大發展。列寧在與德國女革命家蔡特金的談話中說:“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18](P392)革命先驅們早已為無產階級文學確立了黨性原則。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學”,希望從文學上起首,提倡一點人道主義思想,這里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19](P6)人間本位主義平衡了利己與利他之間的關系,即“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對于“人的本質”的重新發現,是中國文學發展歷程中的一次上升與飛躍。在周作人的文藝思想中,人的文學的特性就是理想的“平民文學”。“平民文學決不單是通俗文學。因為平民文學不是專做給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平民文學所說,近在研究全體的人的生活。”[19](P14)平民文學的文學精神的基本特質就是“普遍”與“真摯”,普遍,即是說,不必記英雄豪杰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真摯,即是說,應以真摯的文本,記錄真摯的思想與事實,須以真為主,美在其中。周作人以“平民文學”來宣揚“人的文學”的“普遍”特性,告訴國人:人類每位成員本無貴賤之分,而是具有共同的、普遍的情感。“人的文學”是關于“人”這一現代主體的知識建構,宣揚人的解放、人的個性自由,是文學現代化的重要標志。20世紀二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被全面引入后,以階級性取代人性的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概念開始出現。[20](P44)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在我們,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21](P45)這里的“人民”,就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在此明確指出,第一是為工人,第二是為農民,第三是為革命戰斗的主力,即兵士,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為什么人的問題,作為根本問題、原則問題,在這次講話中被提出并確定。這次講話從根本上解決了文藝為群眾與如何為群眾的問題,規定了文藝服務的對象群體,同時暗示了文藝的內容與形式的要求。由此,人民文學觀念確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周揚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對的文藝思想進行了論證,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序言》中講到:“貫穿全書的一個中心思想是,文藝從群眾中來,必須到群眾中去。”[22](P48)馬克思主義者一貫認為,一切文化,包括藝術與文學,都是群眾的勞動所創造的。而群眾的精神生活由于長期被壓抑、束縛,文藝到群眾去,對于群眾是一種需求和解放。序言中,周揚指出了“大眾化”的問題,這就將文學與人民的關系從淺層形式上升到了本質內容,真正的“大眾化”是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情緒與工農兵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在文藝作品中體現工農兵的思想感情,真正的做到藝術性與大眾性的統一。1949年8月4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發表了一則消息:《全國文協出版“人民文學”》,[23](P2)《人民文學》同年10月25日正式出刊,本人應《人民文學》第一任主編茅盾的“請示”,為《人民文學》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23](P5)“人民文學”作為觀念擁有了自己的實踐園地。鄧小平在《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1979)中提出:“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
文藝創作必須充分表現我們人民的優秀品質,贊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在同各種敵人和各種困難的斗爭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24](P181)要求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從人民生活中汲取材料,表現人民的優秀品質,創造生動感人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同時他還講到“要教育人民,必須自己先受教育。要給人民以營養,必須自己先吸收營養。由誰來教育文藝工作者,給他們以營養呢?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只能是:人民。”[24](P183)人民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文藝的創作來源于生活,離開了人民,文藝創作就變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這深刻地反映了在文學藝術領域,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時代賦予文藝的歷史使命,也是根本的發展方向。1996年,《在中國文聯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對文藝工作做了一系列指示,并充分肯定:“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決定著我國文藝的性質和方向,為我國文藝的發展和繁榮開辟了無比廣闊的前景,”[25]強調:“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遠同人民在一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藝術之樹才能常青。”《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以下簡稱《講話》)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進一步確定了人民文學觀的根本屬性,為廣大文藝工作者提供了正確的理論指導。并對此作了三方面論述:一是人民需要文藝;二是文藝需要人民;三是文藝要熱愛人民。文藝是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人民是文藝表現的主體,同時也是文藝審美的鑒賞者和評判者。重視文藝與人民的密切聯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一以貫之的重要特點。的講話將文藝與人民的關系擴大到文藝創作各個方面和文藝工作各個環節,這是對人民文學觀與時俱進的理論豐富。“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文藝思想的許多內容都具有新涵義、新特征,具有劃時代意義。首先,這是對于延安講話中提到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以及新時期以后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的轉化,文藝與人民之間的關系由服務與被服務轉化為統一關系,使人民真正成為文藝的中心,融入到文學活動的各個領域。其次,《講話》中提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這是對鄧小平提出的“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這一思想的深化,明確的將社會主義文藝定性為人民的文藝。第三,《講話》中提出“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作品的鑒賞家和評判者”,肯定人民群眾在文藝的創作與生產中的地位與重要性。第四,“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突破了傳統文學的“四要素”說。在《講話》中并沒有局限于這“四要素”,而是提出了文學的另一個要素———“人民”,這一要素處于其他要素的中心,形成了新的圍繞“人民”而展開文學活動的“五要素”說[26](P168),這是極具重要意義的理論突破,也為人民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
三、“人民文學”的當代價值
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韋勒克曾指出:“文學的本質正是價值。”[27](P58)“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28](P406)文學作為人類的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形式,其起源、生成和發展的客觀存在是與作為意識的文學觀共生的。并非僅僅是文學觀產生于文學實踐之后,或文學實踐決定了文學觀,而是在主客體的雙向互動關系中文學觀決定了文學行為和活動的性質及其價值取向,從而生產出文學,決定了文學的價值和意義。[29](P198)文學作為黨和國家事業的一部分,一貫受到黨的領導人的高度重視,鄧小平、等繼承和發展了的文藝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人民文學作為觀念形態被建構起來,對于文學創作有著指導性的作用,它的價值不僅在于滿足了文藝發展的需求,更在于對現實、社會、人的發展的推動作用。當代文藝創作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整體上呈現出數量與質量失衡,致使社會精神文明建設走向滑坡。當我們享受著文化開放帶來的快感時,精神逐漸趨于單薄、扁平化,文藝的發展在走向多元的同時,也走向了無中心、無導向,這時就需要有積極的理論引導。在《講話》中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給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方向,為精神文明建設樹立了新路標。當下的文藝是不斷整合生成的文化場域,新奇的事物不定時地沖擊人類的視覺神經,在這樣的一個場域中,文學創作應當堅持人民意識。人民意識并不是說抽象地寫人性,宣傳普世價值,而是貼近現實,深入民心,在生活中找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文學家們應當找到自己對生活、對人民的主觀態度,把這些態度體現在作品的形式、內容和語言中。文學創作應當具有文學的精神內核。什么是精神內核呢?在筆者看來,主要是指思想情感。文學作為一種審美的藝術,最終的“消費者”是人民,文學的思想情感應該具有人民性。人民性首要地體現在:作家必須把所提出的主要問題和對問題的解釋放在人民的立場上,要從這個立場來觀察生活,協助人們去爭取自由的戰爭。但是人民所爭取的自由首先是人的自由。[30](P152)對人民負責的文藝工作者,應當始終不渝地面向廣大群眾,認真嚴肅地考慮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糧貢獻給人民。在消費主義甚囂塵上,身體和欲望被不斷編碼,崇高和理想等精神價值逐漸解體,歷史的宏大敘事漸行漸遠的“小眾”時代,底層文學和底層寫作的出現帶給人們沉甸甸的思考。[31](P99)底層寫作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轉向。例如,遲子建的《花牤子的春天》,主要描寫底層人的生活狀態,代表底層人發聲。總之,農村人外出打工的題材寫作,通過作品呈現出來,使得大家去關注這樣一個底層群體(農民、城市打工者),這就屬于人民文學。
文學應當肩負國家形象建構的使命。國家形象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它既包括物質基礎、政治理念,還包括文化理念和民族精神。其實一國的國家形象是各構成要素相互作用和整合的結果,是一種綜合體現,只是有時在一定的歷史或特定時期某一要素占據主導而表現為國際社會所認知的某一國家形象。[32](P35)基于這樣的認識,文學作品中的國家形象建構,主要與作家的政治立場、思想觀念有關,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文學作品只寫正面形象,不揭露問題,關鍵是要看該民族在面對問題的時所體現出的精神氣質。比如《保衛延安》中解放戰爭中的英雄人物,《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地下黨工作者的生活等,這些作品體現出來的是我國民族的精神氣質,面對困難迎刃而上、面對窘境永不言說的民族精神。這就將國家形象具體的呈現并傳播出來,這也屬于人民文學。文學對于女性群體的關注,如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記》;文學對于新農民形象的呈現,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文學對于普通小市民生活狀態的描摹,如劉震云的《一地雞毛》等等,這些文學作品都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對現實生活的關照,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極具代表意義的典型,這也是人民文學。人民是一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的物質創造者。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要求文學作品從創作到鑒賞之間的每個環節都要以人民為中心,但并不是說,人民文學就要忽視個體,摒棄個體的主體性表達。人民文學與人的文學,在理論基礎上具有可通約性———人的主體性。人民文學作為無產階級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是以人民為本位的文學觀念,它以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本位的主體性理論為基礎,建構了人民主體地位的文化理論。[20](P44)這里的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是“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文學中“人”與“人民”并非對立范疇,而是從個別到一般的思維方式,文學就是要立足于個別來尋求一般,正如上文中提到的“典型”。人民文學只有在融入“個體、生命”等要素之后,才能夠保持精神的純粹,匯入持久的文化消費活動中,否則就只有改變內容去吸引口味更迭的人群。“以人民為中心”是文藝工作者集體的價值取向、整體定位,在符合這個維度的情況下,文學亦不能放棄對個體主體性的表達。“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是強調把人類大愛放到個人情懷之上,其本質并非排斥個人,而是要把“人民”放在“人”的前面,這種人民本位的文藝思想是符合我國傳統文藝價值觀的,也是文藝的終極職責所在。
作者:張園園單位:江西師范大學
- 上一篇:如何引導學生創編幼兒文學范文
- 下一篇:專業期刊數字優先出版的困境及出路范文
擴展閱讀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人民調解工作計劃
- 2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
- 3人民幣國際化論文
- 4人民幣匯率論文
- 5人民調解工作思路
- 6人民幣升值論文
- 7人民幣結算論文
- 8人民防線宣傳工作計劃
- 9人民銀行匯報材料
- 10人民幣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