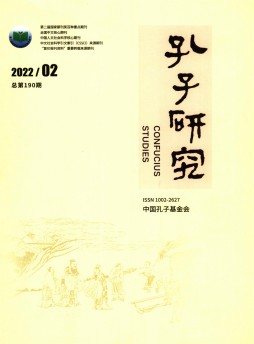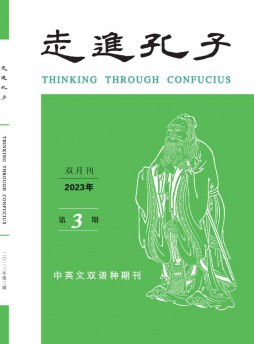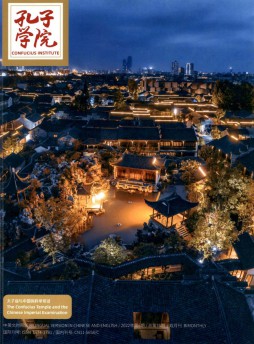孔子對請求學農的批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孔子對請求學農的批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孔子學院》2017年第5期
【摘要】《論語》中記載的樊遲因為請求學農而受到孔子批評的故事古往今來一直耐人尋味。探究孔子批評樊遲的原因并做出客觀評價,對于發掘儒家人格目標和價值追求的思想財富具有積極意義。孔子批評樊遲的原因主要包括重義輕利的傾向、求賤棄貴的嫌疑、違背中庸的錯誤和舍本逐末等四個方面問題。這種批評有重視道德意識和人文精神的優點,但也有輕視改造自然和個性發展的不足。今人必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從中獲得更多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孔子;樊遲;批評;原因;評價
《論語•子路》中記載了孔子的弟子樊遲向老師請求學種糧食和白菜,卻遭到孔子的拒絕并被批評為小人的故事,它也是《論語》里流傳最廣,人們最為津津樂道的孔子與其弟子間的故事之一。古往今來,孔子對樊遲的批評曾被視為志當存高遠的生動詮釋,也曾被看作是輕蔑勞動者的反面教材。探究孔子批評樊遲的原因并對這種批評做出客觀的評價,對于后人全面看待孔子乃至儒家的人格目標和價值追求,從而吸取其中的精華并摒棄其中的糟粕,具有積極的作用。
一、孔子批評樊遲請求學農的原因
樊遲是孔門弟子七十二賢人中的重要人物,《論語》中他曾數次向孔子問“仁”和“知”,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1]和“仁”就是“愛人”(《論語•顏淵》)著名觀點都曾出現在他對樊遲的回答中。[2]然而當樊遲請教如何種地時,他卻受到了批評。具體來講,孔子批評樊遲學農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因:第一,樊遲有重利輕義的傾向。孔子斥責樊遲是“小人”,那么“君子”和“小人”有何區別?至少在他的思想中,首要的一定是道德水準的高下,一定是義利觀的對立。孔子認為,君子應該擔憂的不是物質利益的增加,而是道德水平的提升,不是個人的貧富安危,而是大道的興衰行廢。仁德甚至是高于生命的,當二者產生沖突之時,君子理當毫不猶豫地犧牲生命來捍衛仁德。在論語中,孔子反復強調君子和小人在義利之選擇上的尖銳對立:“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3]“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4]即使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5]“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的評價中沒有明確提出他們各自以何為好,[6]但君子之所以能和睦相處而又堅持原則而小人不能,仍是因為在其心目中道義的標尺始終如一而小人卻只計較個人之得失。
以孔子之見,君子從不違背道義,即使是窮困潦倒、顛沛流離也堅定不移,“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仍然“不改其樂”(《論語•雍也》)的顏回便是典范。[7]農業生產活動是與人們的物質利益息息相關的,是可以直接滿足穿衣吃飯這樣的最基本的物質需求的,人出于滿足物質需求而從事農業生產,而人的功利欲望也很可能在農業生產中被進一步激發。樊遲不同老師探討道德修養或者社會治理方面的問題,而是想要請教農業技能,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還不能充分做到“義以為上”(《論語•陽貨》),[8]他就重義輕利而言功夫還不到家。“學稼”、“學圃”或許沒有“八佾舞于庭”(《論語•八佾》)那么不可容忍,[9]但畢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孔子看到的是樊遲在守衛道德底線,[10]追求道德目標的過程中有所動搖的意志,這位嚴師也因此而批評了他的學生。第二,樊遲有求賤棄貴的嫌疑。這里的“賤”與“貴”是就“禮”的體系中的社會地位而言。孔子大力弘揚“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在道德水平和人格層次上的意義,但他的本意并非將這方面的意義和它們原初的地位高下和身份貴賤上的涵義完全割裂開來,而是要求將前者作為后者的支撐和依據。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復周禮的權威,熱切渴望把按照周禮的規定已經混亂和顛倒的名分重新修正過來,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他認為關鍵就是讓社會的統治者和權力的掌控者擁有道德,由此他甚至把政治的實質就視作為政者崇高的道德水準,“政者,正也”(《論語•顏淵》),[11]“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論語•子路》)。[12]
培養一批既有高尚的德行又有高貴的地位的君子來對政局和社會施加積極的影響,可以說既是孔子的教育宗旨,又是孔子的政治目標,為此他本人也是率先垂范,即使屢受挫折,依舊矢志不移。為了使自己這塊美玉能遇到一位識貨的買主從而賣出一個滿意的價錢,孔子甚至曾想接受叛亂者的聘請,在他看來真正精神高潔的君子是不會被污染的,倘若可以將自己的德行推廣開來,反而可以使骯臟的政治環境得到凈化,這也正符合“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的道理。[13]巧合的是,孔子在樊遲問仁時還向他直接傳授這一道理。雖然農業生產活動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但農業生產者古時的社會地位是比較低下的,“古凡習稼事者皆稱小人”,[14]身為孔門弟子,樊遲不專心于思考如何從政為官,不專心于尋找施展政治才能的機會,不專心于謀求與君子的道德水平相符合的高貴體面的社會地位,卻想要學習身份卑微的糧農和菜農最為精通的事情,這當然是與孔子的教育宗旨南轅北轍的。既然如此,樊遲受到孔子的批評也就不足為奇。第三,樊遲有違反中庸的錯誤。孔子果真認識不到農業生產活動對社會的意義嗎?答案是否定的。在回應子貢問政時,他明確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作為治理好一個國家需要滿足的條件,[15]盡管不是最為重要的條件,但位居次席也足見孔子對于糧食充足的重視,“足食”和“民信”在多數情況下也是可以兩立的,而充足的糧食當然要從農業生產中來。孔子本人也曾擔任過負責畜牧業的小吏,并在此期間使牲畜興旺繁殖。[16]由此可見,孔子所否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農業生產活動本身。
“仁”、“禮”和“中庸”都是孔子的哲學思想的重要范疇,其中“中庸”是孔子基本的方法論原則,他曾盛贊“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17]明確認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思想的核心精神是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遵循合理而適當的尺度,既避免超過,又避免不及,沒有偏向,不走極端。仁是禮的內在要求,禮是仁的外在規范。沒有仁的內在要求,禮會流于形式,沒有禮的外在規范,仁會失去保證。要想讓仁和禮都實現理想的效果,二者不可偏廢,而中庸之道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便是妥善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以中庸原則來審視樊遲,一位君子如果既可以在“禮”的規定下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又可以承擔起“仁”的使命讓老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他無疑是合格的,但如果他置“禮”所規定的位置于不顧,親自去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則是不合乎中庸之道的。由此可見,孔子反對的主要是樊遲違背中庸之道的行事方法,他認為君子在自己的官位上推行德治,才是真正明智和可取的。第四,樊遲有舍本逐末的問題。既要有合乎“仁”的德行,又要有合乎“禮”的位置,還要有合乎“中庸”的方法,那么最終的目標又是什么呢?對此孔子表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論語•衛靈公》),[19]君子的視野絕不局限于一城一池的范圍,君子的任務也絕不束縛于一時一事的解決。
禮崩樂壞,天下大亂,需要君子挺身而出,勇挑重擔;仁義衰落,天命不彰,需要君子英勇無畏,力挽狂瀾。君子的根本使命就是讓仁義之道弘揚于天下,為了擔負起這一神圣的使命,君子必須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并自覺修煉與之相適應的能力,惟其如此,他們才真正“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論語•泰伯》)。[20]子貢是孔子最為出色的學生之一,但在孔子看來他充其量只是一個祭祀用的胡璉,只是一個比較貴重的“器”,[21]而“君子”是“不器”(《論語•為政》)的,[22]由此可見對于君子應該樹立遠大的志向他有著多么高的要求。學種地當然也有其價值,可它與孔子的要求相比顯然還有著非常明顯的差距,只是一個細枝末節而已。對于樊遲舍本逐末,志向不足的問題,后世的評論者也是多有批評: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引用楊時的評論說“樊遲游圣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詞而辟之可也”,還說孔子之所以在拒絕了他之后還把道理明確地講出來,是因為怕他真的去找老農和老圃,如此“則其失愈遠矣”;[23]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亦評價道:“若士之為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當志于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向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哉!”[24]本末倒置,胸無遠志也是孔子批評樊遲的重要原因。綜上所述,樊遲請求學習種地存在重義輕利、求賤棄貴、違背中庸、舍本逐末等問題或者說是苗頭,不管從“仁”的精神還是“禮”的規定,從個人修養還是社會理想來講,都與孔子的要求南轅北轍,他正是因此而受到了孔子的批評。
二、孔子批評樊遲請求學農的評價
1、孔子批評樊遲請求學農的積極影響
明確了孔子批評樊遲的具體原因之后,便是如何看待和評價這種批評的問題。從積極的作用來看,首先,這種批評具有道德意識的提升意義。能夠生存是人從事實踐,創造歷史的基本前提,以生存為核心的功利性需求便成為人的第一需求,但人不只有功利性需求,人還可以超越功利性需求而產生更高的其他層面的需求,包括道德需求。由于個人具體情況的差異,不同的人突破功利型需求的限制而具有道德意識的程度也是不同的,這其中最值得尊重和敬佩的就是基本的功利性需求尚未得到保證卻仍然毫不動搖地追求更高的道德水平的人。即使達到了某一更高的道德水平,也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要想守住這一彌足珍貴的成果,還必須與固有的功利欲望展開激烈而長久的斗爭。古往今來,真正的“君子儒”能夠熱情高揚“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的大學之道,[25]能夠牢固樹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集•張子語錄•語錄中》)的遠大理想,[26]能夠時刻具有“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陽明全集•卷三•語錄三•傳習錄下》)的省察意識,[27]沒有對功利需求的超越和與功利欲望的斗爭,都是不可想象的。孔子批評樊遲,就是希望他在對功利需求的超越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在與功利欲望的斗爭中保持堅定的信念,在道德品格歷練的征程中保持高昂的斗志。從人的全面進步和協調發展的角度看,強調道德意識的儒家當然有其局限,但無可否認的是,強調道德意識也是儒家思想成為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的重要原因。
鼓吹功利欲望的思想雖有可取之處,但其終究不太可能成為一個民族的薪火相傳的精神傳統的主流,就中華民族精神傳統的形成來講,圣人倡導道義至上無疑是功不可沒的。其次,這種批評具有人文精神的弘揚意義。孔子主要是出于對道德的嚴格要求和殷切期望而批評樊遲的,而之所以重視道德不僅是為了把君子和小人區分開來,也是為了在人與低等動物之間劃出界限。人要想獲得真正屬于人的自由,首先要自覺其為人,之所以稱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為一場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據著非凡地位的思想解放運動,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的價值在其中得到了空前的凸顯,而先秦諸子實現這一點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一種是把人從宗教神學下解放出來,另一種就是把人從低等生命中拔升出來。而在儒家那里,把人從低等生命中拔升出來的基本依據就是人向善的趨向,就是人的道德自覺。孔子指出,與犬馬相比,人的孝道不在于能養父母,而在于在養父母的同時還能產生對父母的敬意,這就明確把道德視為人與動物相異的本性,這一觀點也為后世儒者所繼承并不斷強化。道德不是人與動物區別的全部,也不是人與動物根本意義上的不同,但因為道德既是社會關系的產物,又是人能動地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價值評價的結果,所以它仍是人超越于動物最重要的地方之一。當然需要強調的是,動物是無所謂事實與價值,物質與精神的矛盾的,無論就身份之貴賤還是道德之高下,小人也絕不等同于動物,君子與小人的差別也絕不等同于人與低等動物的差別,但人的本質終究是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提升的,從這個角度上說君子的人格比小人更加完善。孔子要求樊遲在“成人”的漫漫征途上更上一層樓,對于人的自覺和進一步發展來說,也無疑可以提供強勁的推動力。
2、孔子批評樊遲請求學農的消極影響
從消極的作用來看,第一,這種批評輕視了改造自然的意義。孔子批評樊遲“學稼”、“學圃”是否一定意味著孔子輕視農業生產和勞動人民,可能還存在一定的爭議,但在孔子乃至儒家思想的價值取向中修身和治國的分量重于務農應該沒有明顯的疑問。從儒家所描繪的君子理應致力于的宏偉藍圖來看,務農的確不值得投入大量的熱情和精力,可如果換一個角度,結論就未必如此了。從事農業生產屬于人類改造自然界的活動,改造自然是人類獲取物質生活資料以滿足最基本的生活條件的必要途徑,是人類實踐活動的基本形式,一切更高層次的實踐活動都必須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生產力是社會運行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而生產力的實質就是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與西方傳統哲學更多地以認識和改造自然界為宗旨不同,中國傳統哲學主要是面向人和社會自身的,它本質上不是以本體論和認識論為特色的哲學,而是價值哲學。[28]這一特點使我們榮耀地成為了一個重人文精神,重道德修養,重價值追求的民族,但也讓我們遺憾地成為了一個輕規律掌握,輕技術進步,輕真理探索的民族,而中國傳統哲學經驗領域與超驗領域密切結合,不善區分的思維方式也妨礙了我們從理論的高度認識務農乃至改造自然的重大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果要追究這種遺憾最早從哪里產生,反對學農的孔子自然是要承擔一定的責任的。雖然他和后世的儒者都不否認物質生產活動的價值,但在他們那里這種活動更多地還只是一種必經的事實,對其價值的承認帶有較強的被動性,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輕視改造自然的意義也就順理成章了。
第二,這種批評禁錮了人的個性的發展。孔子及儒家高度重視道德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但道德提升和人格完善是否只有“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這一種模式,[29]又究竟該如何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質,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事實上,人們在完善自己的人格,實現自己的價值的過程中需要遵循共同的原則,守住共同的底線,但人更需要在此前提下努力打造自身的特色,彰顯自身的個性,如果特色和個性不能充分發展,自由就不過是海市蜃樓而已。在人向自由邁進的過程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在不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前提下,允許人們根據自己的愛好和意愿進行獨立自主的選擇;其次,不管一個人做出了怎樣的選擇,他都有必要進一步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質,但提升的方式仍必須充分尊重其獨立自主的權利,必須嚴格遵守道德靠人的自覺性來維持和提升的本質規定。只有做到了這兩點,才能既保證人的個性的發展,又推動人的道德的進步。以此來審視孔子對樊遲的批評,就第一點來講,學農并不是一個會對他人和社會造成損害的選擇,孔子卻表示反對;就第二點來說,即使樊遲的道德境界的確還有待提高,孔子的批評就尊重其獨立自主和道德自覺而言也顯得有些過激。對于儒學束縛人的個性發展的問題,楊國榮先生曾評論道:“孔子以圣人、君子為普遍的人格模式,似乎未能注意到人格的多樣化問題,這種思維取向在理論上與‘克己復禮’(將自我納入禮所要求的普遍模式)相一致,它或多或少使其人格理論呈現出某種負面意義。”[30]這種負面意義的不斷加重,也是儒學后來墜入“以理殺人”(《孟子字義疏證•與某書》)的深淵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31]
三、結語
科技進步與人文繁榮,個性張揚與道德約束間的矛盾都是人類社會特別是現代社會的發展歷程中十分突出的矛盾,盡管時空有別,但孔子對樊遲的批評仍可以為我們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提供可貴的啟示。我們需要繼承孔子乃至儒家對人文精神和道德水平的重視,但也要克服他們輕視科技提升和個性發展的不足。相信隨著對儒家價值追求和人格目標的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可以從中收獲到更多的精神財富!
作者:王彥凱 單位: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