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guān)婦女解放的社會學(xué)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有關(guān)婦女解放的社會學(xué)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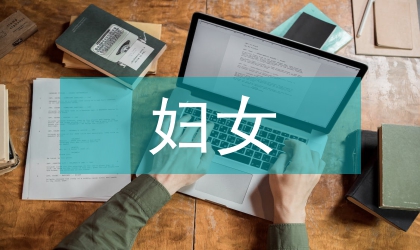
國內(nèi)學(xué)者在婦女解放領(lǐng)域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鄭也夫從男性的視角出發(fā),認(rèn)為男女社會地位的差異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生物性與社會權(quán)力奪取的之間的一致性,力量和金錢在權(quán)力奪取中越重要,男性社會地位就越高,智力和知識在權(quán)力奪取中越重要,女性社會地位就也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專橫而缺乏理性的男性意識形態(tài),即將男女的差異評判為一種對立的二元劃分,男性的特征被認(rèn)為是優(yōu)越的,男性的統(tǒng)治被認(rèn)為是無可厚非的。據(jù)此,他認(rèn)為,我國在智力與經(jīng)濟(jì)對權(quán)力與生產(chǎn)的決定作用上,在社會物質(zhì)財富上都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發(fā)達(dá)國家,婦女的解放是動用行政力量造就的,是一種非自然的結(jié)果,是超前的,而這種超前的運動的后果便是“使中國社會失去了男子漢,也失去了自己的女性”。而市場經(jīng)濟(jì)使得女性重新被排擠出市場,是一種優(yōu)勝劣汰的自然選擇,是遵循合理高效原則的結(jié)果[2]。劉伯紅則站在完全相對的立場上,對鄭也夫的觀點進(jìn)行了批判。她認(rèn)為,新中國的婦女解放歷程并不完全是行政力量推動的結(jié)果,更大程度上是女性意識的蘇醒,是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賦予人主體意識和婦女接受教育、價值觀念發(fā)生變化的產(chǎn)物,這種趨勢的出現(xiàn)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另外,她認(rèn)為,市場經(jīng)濟(jì)并不是自由公平的,而是建立在社會性別分工不平等的基礎(chǔ)之上的,政府應(yīng)當(dāng)采取適當(dāng)?shù)男姓侄芜M(jìn)行干預(yù),是強(qiáng)固社會公允,克服社會不平等,補(bǔ)償因市場而造成的失衡,是保證女性在就業(yè)市場中的“機(jī)會公平”[3]。
孫立平在解決中國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中,提出減少婦女就業(yè)的數(shù)量的建議,他認(rèn)為,我國正處于一種后工業(yè)化階段,一方面,家務(wù)勞動沒有實現(xiàn)社會化,另一方面,又要求男人全心全意的在外面工作,婦女的普遍就業(yè)實質(zhì)上是打亂了社會中的角色分工,結(jié)果是造成社會功能的紊亂以及其他種種問題[4]。這種觀點同樣體現(xiàn)了當(dāng)代中國男性知識分子重建社會性別等級秩序的要求。西方的女權(quán)主義者通常對中國的兩性平等持一種懷疑的態(tài)度。由于20實際80年代中國的發(fā)展模式基本是政治性的,婦女解放運動的過程其實是不加批判的將男性標(biāo)準(zhǔn)普遍化為婦女解放的手段與目標(biāo)。DeliaDevin進(jìn)一步分析了中國婦女解放的兩面性,認(rèn)為在“”期間的平等浪潮中,往往簡單的否定兩性之間的差異,拒絕承認(rèn)存在所謂的“女性特征”,而在另一些時候,又接受男女存在的差異,并試圖使這些特征得到更高的評價[5]。通過對有關(guān)中國婦女解放進(jìn)程的文獻(xiàn)綜述,我們不難看出,由于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是政府強(qiáng)制力推動的一種男性中心和國家主義的,所以男女只實現(xiàn)了形式上的比較平等,并沒有實現(xiàn)實質(zhì)意義上的平等,女性不是解放的主體,而是工具性的客體,婦女解放總是被置于國家富強(qiáng)和名族昌盛的大背景之下,是“被解放”而不是主動“解放自己”。而學(xué)者討論的問題多集中在婦女解放在經(jīng)濟(jì)層面的作用,國家強(qiáng)制力推動下的婦女解放是否有意義,并沒有從根源上解釋男女為何不平等,能否平等,如何平等的問題。
二、從性別社會學(xué)的角度談男女平等
首先,性別社會學(xué)的發(fā)展是建立在一種性別建構(gòu)主義的基礎(chǔ)之上的,即是對生物決定論與性別本質(zhì)主義的批判,它認(rèn)為,在生物性上男女兩性的差異并不是造成男女社會性別差異的原因,更不是導(dǎo)致男女不平等的原因,相反,這種社會性別之間的差異是行動者互動的結(jié)果,并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發(fā)生變化。需要說明的是,行動者之間的這種互動并不是平等的,在一定場域中,優(yōu)勢地位的占有者通常會為了自身的地位及利益,利用自己所持有的話語權(quán)力,創(chuàng)造一種看似合理的分類體系,這種分類體系在不斷內(nèi)化的過程中形成一種不證自明的觀點,反過來再指導(dǎo)人的行為。建構(gòu)主義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一種“意識”的作用。
我們肯定男女的sex在生物概念上是不同的,但這種不同僅表現(xiàn)在染色體、荷爾蒙、基因、生殖器等客觀存在上,這些客觀因素并不是兩個完全極端的呈現(xiàn),而只是或多或少的差別。只有當(dāng)這種客觀存在經(jīng)過不斷的社會實踐、社會評價、社會所固有的兩性觀念以及什么構(gòu)成男女兩性特征的文化與理解才形塑了個人的性別認(rèn)同,也就是說,是社會將男女建構(gòu)成為差異的、不平等的,而這種建構(gòu)的社會性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實質(zhì)是壓抑了生物性別,將原本或多或少的客觀存在的生物因素生硬的壓制到兩個極端的男女范疇中。AnneFausto-sterling就從生物學(xué)的角度,分析了每個個體在染色體、荷爾蒙、基因、生殖器等生物性客觀存在上,常常并不是互相對應(yīng)的,提出了一種序列狀態(tài)呈現(xiàn)的性的觀點,認(rèn)為在一定意義上人人都是雌雄同體,去除了男女的二元對立性。指出對性別的社會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人的生物性[6]。
后現(xiàn)代女性主義認(rèn)為,男女差異是被社會建構(gòu)的。從微觀的角度來講,我們對于“什么是一個合格的男人或者女人”的認(rèn)知是在社會環(huán)境中生成的,從出生到死亡,不同的社會評價、社會判斷不斷影響著我們的認(rèn)知。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創(chuàng)造和表現(xiàn)自己的性別,以變得越來越像個“合格”的男人或女人,以獲得群體的認(rèn)同。從宏觀的角度來講,性別的具體內(nèi)涵與文化意義是會隨著生產(chǎn)方式,社會結(jié)構(gòu)的變化而變化的。正如JaneF.Collier在對一個西班牙的村莊的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對女性的社會評判標(biāo)準(zhǔn)是隨著生產(chǎn)方式的變化而變化的,在農(nóng)業(yè)社會,女性的地位取決于孩子,女性貞操決定著家族的完整與孩子的合法繼承權(quán),所以穿著保守、身形臃腫、勤勞家務(wù)是這一時期女性的特征。進(jìn)入工業(yè)社會之后,個人職業(yè)、收入、社會地位由自己的能力決定,女性的女性特質(zhì)就成為其資本,女性的地位決定于她嫁什么人,所以這時身材妖嬈、穿著入時、參加社交活動成為女性的特征[7]。所以,就我國婦女解放運動時期對“女性特性”的贊揚(yáng)也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了特定的目的,是意識形態(tài)下對個體的建構(gòu)。中國的婦女解放進(jìn)程中,往往簡單的否定兩性之間的差異,拒絕承認(rèn)“女性特征”或者對“女性特征”給予更高的評價,這種看似合理的兩個極端男性中心的宣傳手段,是由于沒有性別差異的社會建構(gòu)概念,即sex和gender的區(qū)別。產(chǎn)生了兩方面的消極作用,一方面,在男性統(tǒng)治、男性認(rèn)同與男性思維模式的作用下簡單的將女性特質(zhì)等同于男性特質(zhì),否認(rèn)男女之間存在差異,女性獨特的個性及需要就被抹殺了,男女平等的本質(zhì)是兩性間的義務(wù)平等而不是權(quán)利平等;另一方面,基于本質(zhì)主義的對于女性特質(zhì)的解釋,強(qiáng)調(diào)女性與生俱來的關(guān)懷、哺育、溫柔(這種文化普世主義的解讀忽視了女性特增是立足于特定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受制于經(jīng)濟(jì)、政治制度的),實際上對婦女在就業(yè)和工資中的地下地位、對雇主決定把婦女排除在勞動力之外提供了合法性。這就是為什么雖然婦女解放運動形勢高昂,卻并沒有真正從實質(zhì)上改變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所在。
所以我們應(yīng)該明確,男女在生理上有差異,但男女的社會差異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社會化過程中被不斷建構(gòu)的,所以這種差異并不應(yīng)該導(dǎo)致不平等,要想實現(xiàn)平等,就要對這種差異進(jìn)行解構(gòu),從女性自身出發(fā),將女性當(dāng)做有血有肉有不同生活經(jīng)驗的獨特個體進(jìn)行研究,而不是將其置于宏大的社會事實背后。對于男女的平等問題,筆者認(rèn)為這種平等首先應(yīng)該是觀念上的,女性有其獨特的經(jīng)歷、感受,這種感受是應(yīng)該被社會所聽到的,女性要有創(chuàng)造自己的一套話語方式,可以有權(quán)力用自己的話語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在政策層面,應(yīng)該給予女性選擇的機(jī)會,而不是將女性作為客體、作為他者來幫她們做選擇。
作者:張光單位:北京師范大學(xué)哲學(xué)與社會學(xué)學(xué)院
- 上一篇: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管理探討范文
- 下一篇:SSK的理論來源及發(fā)展困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