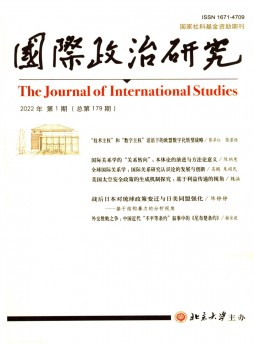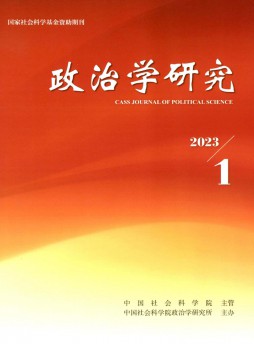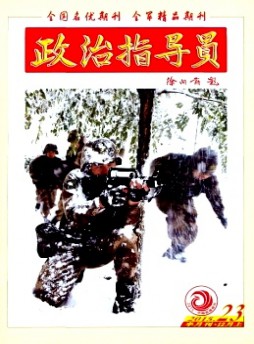政治動因的消費行為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政治動因的消費行為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炫耀性消費與符號性消費中的“身份政治”
“只要花費是滿足基本需要的,就不是消費主義。當為了滿足更高需求時,就是消費主義。”〔6〕消費主義范疇中的奢侈性、浪費性消費,一是為了物質(zhì)享受,二是為了炫耀。這兩種追求既可以獨立地存在于消費活動中,也可能統(tǒng)一于消費活動中。之所以有炫耀性消費,“因為這是財力實力的明證。財力實力是值得尊敬的或尊榮的,因為分析到最后,它展現(xiàn)了成功和優(yōu)越的力量。”〔7〕“消費社會學之父”凡勃倫(ThorsteinB.Veblen)進一步指出:“財富或權(quán)力必須提出證據(jù),因為唯有取得證據(jù)才享有尊榮。財富的證據(jù)不僅僅讓別人對自己的權(quán)勢產(chǎn)生深刻的印象,以及讓自己對權(quán)勢的意識保持活力和警覺,并且在營造和維系本身的自我滿足方面的功能也不遑多讓。”〔8〕為顯示地位和優(yōu)越性的消費必然是奢侈性的,而為了維護消費地位及其優(yōu)越感,消費又必然是競爭性和攀比性的。炫耀性消費,成為影響他人的工具之一,是權(quán)力塑造和練習的過程———消費已經(jīng)政治化了,或者說,這種消費行為的動因是政治性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歐美消費文化生態(tài)發(fā)生了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電視的高度發(fā)展,其后是互聯(lián)網(wǎng)的迅猛擴張。這些科技的新發(fā)展極大地拓寬了人們的眼界,人們可以也愿意越過周圍的人群,注目遠處絢麗夢幻的生活景象。電視、電影、廣告、時尚雜志的發(fā)展相互促進,它們既是消費品,也是消費的推動者,它們“不僅培養(yǎng)了消費主義,而且還和消費主義一道發(fā)展”。〔9〕電視、電影、廣告、時尚雜志等,呈現(xiàn)的是有錢人的生活,它們對于人們消費模式的描述常常是極度夸張和極端扭曲的,宏大、豪華、奢侈、時尚等成為成功的符號,成為人生的目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電視、電影、廣告、時尚雜志等成為消費主義的創(chuàng)造者,所有這些又被互聯(lián)網(wǎng)所放大。由此,歐美消費進入了新的消費文化時期,朱麗葉•朔爾(Juli-etSchor)把它稱為“新消費主義”。
和消費主義一樣,新消費主義在物質(zhì)層面追求奢侈、豪華、貴重;和消費主義不同的是,新消費主義為了展示審美情趣和消費技能,對“時尚”和“品位”有著迫切的追求。究其原因,新消費主義已經(jīng)超越物質(zhì)和生理享受層面,在社會和政治層面規(guī)劃和設(shè)計消費策略。新消費主義更加注重通過消費來定位身份,身份政治的需求和動機更加迫切而明顯。從社會狀況看,“在較早的年代,社會地位是由一個人的出身、歷史和階級決定的,消費在決定社會地位中只不過起到一種次要的作用。”〔11〕城市化的發(fā)展、熟人關(guān)系的劇減、現(xiàn)代政治文化的教育,所有這些使得傳統(tǒng)的標示身份的方式已不被認可,占有財富本身在陌生人關(guān)系中也難以有效地標示出身份,只有其直觀的動態(tài)的使用和消費才是方便快捷的標示社會地位和個人身份的有效方式。“實際上,當一個人的出身、歷史和階級在社會里不再那么重要的時候,身份就更是一種流動資本,消費也就變得更加重要了。”〔12〕在流動的社會中,消費作為身份象征性、符號性的意義更進一步凸現(xiàn)出來。這種定位于“身份政治”的新消費主義的消費“更具有侵略性,已不再是防御性的”。
在新消費主義氛圍下,消費作為文化資本決定了消費者的品味和喜好。品味成了一種階級地位的象征、一種階級的標志。〔14〕權(quán)力地位是相對而言的,由此,定位于身份政治的新消費主義與消費主義一樣,也是競爭性、攀比性的消費,持續(xù)地處在消費物品有和無、消費品味高和低的不斷競爭與追逐中。在朱麗葉•朔爾看來,與過去攀比性消費不同,新消費主義的攀比性消費在可攀比的范圍上擴大了:電視提供了眾多樣本,街坊鄰居已不再是參照樣本;以前的攀比主要在鄰里之間,現(xiàn)在工作單位已成為消費攀比之風的沃土。這種攀比性消費常常是和經(jīng)濟地位遠遠比自己高的人進行比較,以爭取實現(xiàn)更高級的富豪式的生活。〔15〕在凡勃倫看來,炫耀性消費是財力實力的明證。〔16〕這一論述可以看作是對傳統(tǒng)消費主義的經(jīng)典總結(jié)。新消費主義則不僅意在展示財富的多寡,也要表明消費技能的高下,并力圖表現(xiàn)審美情趣的優(yōu)劣。布迪厄(PierreBourdi-eu)認為,在現(xiàn)代社會,消費“品位”是社會分層的重要依據(jù),是社會“區(qū)隔”的文化資本。〔17〕這一論斷可以當作是對新消費主義的扼要概括。消費主義主要展示“硬實力”,新消費主義則同時要展示“軟實力”。如果說凡勃倫闡述了消費主義關(guān)于“硬實力”的身份政治機理的話,布迪厄則在新消費主義層面上論及了關(guān)于“軟實力”的身份政治機理。“消費符號具有區(qū)分社會層次、鞏固社會差異的作用,現(xiàn)代人被符號的社會區(qū)分所控制而竭力勞動。”
新消費主義的競爭性攀比性,使得后來者不斷進行補償性消費,以便彌補消費競爭不足或在消費競爭中取勝,努力保持品味差距和社會距離。這就需要保持高收入水平,加大文化與象征符號的資本投入,花大量的時間鑒別服務(wù)與產(chǎn)品,于是,新消費主義者成為“被蹂躪的有閑階級”。〔19〕一些學者直接在政治層面上對“品味”加以解釋。如丹尼爾•米勒(DanielMiller)寫道:“品位主要被看作‘階級偏見’的原因,‘階級偏見’被定義為少數(shù)中產(chǎn)階級和上流社會對于粗俗的玩笑、廉價的商品、工人復(fù)制品或沒有風格的商品的感受,以及被輕視的工人階級對于狂妄的、冷酷的、墮落的中產(chǎn)階級和上流社會的感受。”〔20〕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Skidelsky)也認為,社會不平等是引發(fā)消費品味和刺激凡勃倫式競爭的動因。〔21〕米勒和許多學者都認識到消費差異和消費競爭是政治經(jīng)濟的結(jié)果,但米勒與大多數(shù)學者不一樣的地方在于,他還把政治經(jīng)濟看作是消費的后果。
消費品味及其競爭,源自于社會政治經(jīng)濟的不平等,又反過來導(dǎo)致政治經(jīng)濟的進一步差異和不平等。相較于大眾奢侈消費的身份政治,奢侈性的公款消費則更直接地體現(xiàn)出消費與身份政治之間的關(guān)系。奢侈性的公款消費,首先是權(quán)力自身的消費,是不適當?shù)乩脵?quán)力的過程。其次,它也是權(quán)力展示的過程,高檔的消費場所、昂貴的消費物品、繁雜的消費程序,無不是權(quán)力展示過程的一部分。為了展示權(quán)力,它還模仿最具權(quán)力象征性的消費,如建辦公大樓模仿天安門和白宮,就是權(quán)力最為癲狂的想象。公款消費的消費物品和消費場所,已經(jīng)具有權(quán)力符號的意義———“豐裕的物質(zhì)消費表征著權(quán)力和官位。”〔23〕再次,它還是權(quán)力再生產(chǎn)的過程,通過消費來建立或鞏固各種關(guān)系,并把這些關(guān)系轉(zhuǎn)化為職場的權(quán)力資源。正如保羅•霍普(PaulHopper)所言,炫耀性消費,是一種地位競爭,這種消費文化展示了社會不平等,可能引起社會不安。〔24〕奢侈性的公款消費,更是撕裂了社會和政治關(guān)系。可以說,公款奢侈性消費反映著一定的政治關(guān)系,也影響著政治關(guān)系;既是權(quán)力的結(jié)果,也是權(quán)力的原因。正因為如此,在政治學層面展開消費行為政治動因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明顯的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
二、大眾日常消費行為中的政治意蘊
消費行為的政治動因,不僅表現(xiàn)在奢侈消費中對身份政治的追求,也表現(xiàn)在日常消費中政治感知對消費決策的影響。業(yè)已形成的道德倫理、價值觀和政治意識會滲透到購物過程中,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是否要購買某些產(chǎn)品和服務(wù)。例如,購買綠色產(chǎn)品需要多花費用,為了家人的健康,人們常常愿意這樣做;而為了盡到減少碳排放的公共責任,人們是否愿意多花費用,則是很不確定的。因此,是否購買綠色產(chǎn)品,是否采用減少碳排放的消費方式,這不僅是表達愛意的問題,也是關(guān)于公民公共責任的政治問題。“有許多人樂意假裝是生活的旁觀者,而不是負有責任的參與者,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毫無愧疚地進行消費了。”人們的公共責任意識沒有被激發(fā)出來,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其中政治公平是主要原因。在丹尼爾•米勒看來,從市場機制入手來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純屬胡扯,因為市場機制會加劇這種招致大量消費和欲望的不平等因素;而且這也不是貪婪的問題,而是因為單純的不公平。發(fā)展中國家的人們在達到發(fā)達國家的消費水平之前是不會抑制消費的。〔26〕米勒還認為,社會不公的加劇會導(dǎo)致人們之間信任的缺失,而人們之間信任的缺失又會導(dǎo)致他們不愿參與公共活動。
由此看來,綠色消費問題最終是個政治問題。自由是人們追求的目標。在物質(zhì)豐裕社會,或者說消費社會,消費者自然把消費活動和消費選擇作為自由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作為自由的象征。汽車的暢銷不僅僅在于產(chǎn)品自身的功能以及產(chǎn)品的社會地位的符號意義,也在于汽車所賦予的自由的感覺和聯(lián)想。個體自由是連接共同生活與社會生活的中心環(huán)節(jié),長期以來,“這種中心性的位置的確立原本來自市場領(lǐng)域和權(quán)力領(lǐng)域,近來已經(jīng)轉(zhuǎn)入了消費領(lǐng)域。”從社會結(jié)構(gòu)看,消費自由“以高效的市場存在為基礎(chǔ),而反過來它又是確保市場存在的條件。”個體消費自由是以物質(zhì)豐富為基礎(chǔ)的,受到市場機制的鼓勵,并由此受到政府的保護。從個人的欲求上看,“消費不僅僅是一個個人選擇和自我表達的過程。……比起勞動,消費才是創(chuàng)造自己專屬生活的主要方式。……對他們來說,勞動并不是價值的根本來源,消費才擁有更為合適的基礎(chǔ),因為消費不像勞動那樣使他們感到被動和壓抑。”消費具有令人愉悅的屬性,消費的感受是獨自不可轉(zhuǎn)讓的,消費創(chuàng)造了專屬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消費自由最為符合人性的自然追求,在消費社會,“個體自由首先作為消費者的自由”。這也就不難理解,在消費社會,“大多數(shù)成員的個人自由是以消費自由的形式出現(xiàn)的”。正是基于對消費行為的研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Bauman)對自由做出了后現(xiàn)代的新解釋:“自由只有作為一種社會關(guān)系時方能存在。自由不是一種所有權(quán)或個人對自身的占有,而是一種與個體間的某種差異相關(guān)的屬性。”
這種差異是“由他人意志決定行為與由自身意志決定其行為之間的差異”。也正是由于消費自由,使得消費社會具有了明顯的差異性。鮑曼從消費者日常生活入手,以微觀敘事的方式展現(xiàn)了消費者的情感、欲望及消費行為的政治涵義和政治影響,解構(gòu)了以宏大敘事、崇尚理性、國家中心、一元化為特征的現(xiàn)代政治,展現(xiàn)了消費社會由于消費行為而帶來的豐富的差異性。當然,鮑曼也告誡,消費自由并不是絕對的自由,政治無所不在,只要消費自由不損害國家利益,政治就以隱匿的方式存在。自由不僅表現(xiàn)在主動選擇的積極自由,也包括免于控制的消極自由。消極意義上的消費自由,主要表現(xiàn)為購物的熱情與流連忘返,因為在消費社會中,“……消費市場是消費者逃避官僚政治壓抑的唯一場所”。也如馬丁•帕維斯(MartinPurvis)所言,消費是集體逃離生產(chǎn)競爭的工具。〔37〕大型購物中心也正是從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兩個方面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一方面,眾多的商品供開放式自由挑選;另一方面,刻意營造輕松愉快的氣氛,甚至預(yù)留交往和聊天的空間,使購物中心切實地成為釋放壓力的場所。對有些消費者而言,大型購物中心主要作為休閑放松的場所,購買一點商品只是對商家的一種補償。于是,商業(yè)和政治就這樣通過消費結(jié)合在一起。在理查德•桑內(nèi)特(RichardSennett)看來,對自我消費激情有兩種解釋:其一是“時尚驅(qū)動說”,即認為廣告和大眾傳媒業(yè)學會了如何塑造欲望,以促使人們對他們擁有的東西感到不滿;其二是“有預(yù)謀的廢棄說”,認為廠家可以不把商品制造得經(jīng)久耐用,以促使公眾購買新的東西。這兩種解釋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們都假定消費者扮演的是被動的角色,消費者只是廣告的“玩偶”或者廢品的“囚徒”。而事實上,消費者能夠以更為主動的方式參與到自我消費的激情中去。〔38〕消費者在體驗產(chǎn)品功能的同時,往往賦予了商品以某種特定的想像,如酒和性感、珠寶和高貴、香水和魅力等等聯(lián)結(jié)到了一起,從而挖掘出產(chǎn)品的新功能;消費者也會在高度同質(zhì)化的商品中尋找細微的差異,并從中獲得樂趣;最能調(diào)動起消費激情的,則是邀請消費者參與完善“半成品”產(chǎn)品,因為使用那些業(yè)已完善的耐用的產(chǎn)品很可能已沒有了激情。消費者的想像和參與,既與知識興趣有關(guān),也與公民意識有關(guān),即便是以國家理論為研究中心的政治學也不能否認其政治隱喻,而政治社會學理所當然地把這些視為自己的研究內(nèi)容。
購物消費,不僅會涉及道德操守和價值觀問題,也會涉及政治利益的考量,涉及政治情感和政治情緒的表達。在購物消費過程中,一旦“這是誰生產(chǎn)的?”“這是哪里生產(chǎn)的?”“我的購物消費對誰有利?”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影響消費選擇時,那么這已不是在包裝審美、產(chǎn)品功能及性價比上進行權(quán)衡,而是在政治上進行考量。消費的區(qū)域主義、消費愛國主義(或者消費民族主義)就是這類政治考量的突出表現(xiàn)。而回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節(jié)日消費(如春節(jié)、清明節(jié)消費等),追捧西方文化的節(jié)日消費(如圣誕節(jié)、情人節(jié)消費等),以及它們之間的并存、競爭,都充滿了政治意蘊。英語“boycott”一詞,一般譯為“聯(lián)合抵制”。在英語世界中,最近生造出一個新詞“buycott”,與“boy-cott”相對,對此國內(nèi)尚無相應(yīng)的翻譯。根據(jù)維基詞典,“buycott”的定義為:1.Noun.Theoppositeofaboycott:deliberatelypurchasingacompany'soracountry'sproductsinsupportoftheirpolicies,ortocounteraboycott.2.Verb.Tosupport(acompany,country,etc.)bybuyingitsprod-ucts.〔39〕“buycott”是通過購買行為表達對國家或企業(yè)的支持,或是對抵制的“反抵制”。根據(jù)“buycott”一詞的涵義,可以譯為“支持性購買”;考慮到和“boycott”一詞相對,也可以譯為“聯(lián)合購買”、“聯(lián)合支持”。當然,在具體使用中可以根據(jù)語境對“buycott”的翻譯做些調(diào)整。這一語言現(xiàn)象表明,歐美國家消費者常常把消費作為政治表達和政治參與的形式,而大量的消費運動則更是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獨是英語世界的國家,其他國家,包括中國,許多消費行為也內(nèi)涵了政治訴求。
三、消費行為政治動因的研究與消費問題的治理
福蘭克•莫爾特(FrankJ.Molter)認為,自凡勃倫的名著《有閑階級》(1899)出版以來,社會學關(guān)于消費研究的重大成績就是把消費看作是各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一部分;但比起消費自身的權(quán)力動力學來說,相當多的研究更關(guān)心外在于消費的權(quán)威對消費的影響,而不是深入到消費的具體細節(jié)中分析消費的權(quán)力模式。福柯(MichelFou-cault)關(guān)于權(quán)力具體性的話語模式則提供了另一個有用的理論框架,即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并不是與其他類型的關(guān)系(如經(jīng)濟發(fā)展、知識經(jīng)濟、性關(guān)系等)截然分開的,而是存在于后者之中。消費領(lǐng)域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不僅僅是其他網(wǎng)絡(luò)的投影,而是與其他領(lǐng)域緊密相連的,它是由知識和策略的共同作用,社會聯(lián)盟和社會運動、抵抗和經(jīng)驗形式等相互交織而形成的。
從消費行為的政治動因進行分析,消費政治首先是微觀的,但進而可能成為群體性的,甚至是規(guī)模性的政治運動,從而深刻地影響著國家政治。我們已經(jīng)熟知國家政治對微觀消費政治的影響,而對消費行為的政治動因的研究,則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彌漫于日常生活中的微觀政治對宏觀政治的影響,并感受到這些彌漫力量聚集后產(chǎn)生的重要的社會建構(gòu)作用。如上所述,在物質(zhì)豐裕社會中,消費行為的動因很多,消費已經(jīng)不再是僅僅滿足生理需求。消費行為的動因往往是復(fù)合的。消費行為的生理的和經(jīng)濟的動因常常是直接的、顯性的,而其社會的和政治的動因卻是隱性的、深層次的。消費行為的政治學研究,主要不是以國家機構(gòu)為中心,主要是以公民個人及其行為為中心逐步展開。“消費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了家庭生活和更為廣泛的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秩序包括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和世界觀。”在政治影響滲透于每個生活角落的時代,政治影響消費,消費過程也往往內(nèi)涵政治意蘊,消費行為的政治學研究已不可或缺。當然,消費行為的政治學解讀不僅要結(jié)合公民的政治意愿、意識形態(tài)、政治情感、價值觀偏好等,更要結(jié)合其所嵌入的社會結(jié)構(gòu)、客觀情境和文化背景,將消費行為放到一定的經(jīng)濟政治社會環(huán)境下進行解讀。
長期以來,我們在思想教育、工程技術(shù)和市場機制層面展開消費問題的治理研究,力圖實現(xiàn)綠色消費、適度消費,但效果甚微,其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消費問題背后的政治動因有所忽視。消費行為動因的政治學研究,拓寬了分析問題的視野,掘進了問題剖析的深度,可以為消費問題的治理提供重要的思想啟迪和理論支持。例如,近年來國內(nèi)一些名牌嬰兒奶粉出現(xiàn)質(zhì)量問題,消費者紛紛高價購買“洋奶粉”;盡管媒體爆出有些“洋奶粉”的國產(chǎn)背景,這種購買熱情仍然不減,繼續(xù)橫掃香港奶粉市場。可見,這已不是單純的產(chǎn)品質(zhì)量問題,其深層原因在于對大陸奶粉生產(chǎn)、尤其是政府監(jiān)管的不信任,這是一種政治表達,是用“鈔票投票”的行為。在香港政府做出限購奶粉的規(guī)定之后,許多大陸游客加入了代購奶粉的行列,相當部分代購者的目的主要不是從中賺取二三十元錢,而是表達對限購政策的不滿。如果說購買“洋奶粉”源自于風險政治的話,那么代購“洋奶粉”則已經(jīng)發(fā)展為消費政治。奶粉的風險政治主要訴求的是食品安全,而奶粉的消費政治則是企圖對限購政策施加影響。事件的原因和訴求有所不同,那么治理的方略也就應(yīng)該有所不同。顯然,只有找準問題的根源,采用有針對性的治理方略,才能獲得良效。
作者:范廣垠童星單位:山東大學(威海)法學院副教授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 上一篇:女大學生消費行為論文范文
- 下一篇:網(wǎng)絡(luò)游戲消費行為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