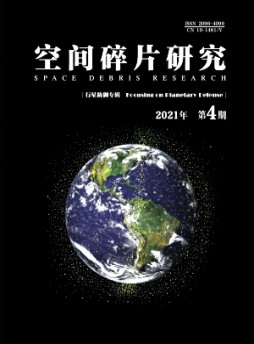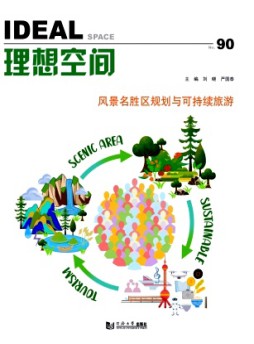空間特征的旅游經濟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空間特征的旅游經濟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方法筆者首先運用ArcGIS軟件分析旅游業發展的空間特征,然后運用空間探索性分析方法揭示各省域間旅游經濟的空間關系。空間探索性分析(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ysis,ES-DA)是一種分析空間相連關系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基于樣本數據驅動的分析,在沒有先驗的理論假設下,通過作圖、制表、方程擬合、計算特征量等手段來了解被觀察單元在空間分布、空間結構以及空間相互影響方面的特征;它的優點在于可將具有相同或相異屬性值的地區以圖像化的形式展示出來,并把空間關系分為空間全局自相關和空間局部相關兩個部分,來揭示空間效應中的空間依賴性和異質性。常用測度空間關系的指數有Geary’指數和Morans’I指數,筆者采用Morans’I指數,取值在[-1,1]之間,若Morans’I指數為負,說明相似的地區在空間上呈離散狀,若為正則呈集聚狀,若為0,則不存在空間相關關系。
2.數據筆者采用旅游總收入作為度量旅游業發展水平的指標。文中數據來自國家旅游局網站、國家統計局網站、四川省旅游局網站、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庫各省市統計年鑒(2000~2012年)、《四川省旅游統計便覽》、《浙江旅游統計便覽》、《湖北省統計便覽》。入境旅游收入根據當期年末美元與人民幣兌換匯率進行了換算。
3.旅游業空間特征分析(1)旅游經濟空間差異顯著,發展水平由東部沿海向西北內陸遞減;總體聚集與分散、多中心,局部“中心-外圍”特點突出筆者運用ArcGIS軟件繪制出2000~2012年間各省旅游總收入均值的5級分布圖(如圖1所示),顯見,我國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顯著。總體上,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分布符合“騰沖-黑河”人口地理分界線,以東為高發展區,以西為低發展區,大致呈由東及西階梯狀分布。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省區市由南到北為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山東、北京;第二級由東到西為遼寧、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第三級由東到西為河北、山西、安徽、陜西、云南;第四級由東到西為黑龍江、吉林、江西、重慶、貴州、廣西;發展水平最低的由南到北為海南、西藏、青海、寧夏、甘肅、內蒙古、新疆。就全國而言,旅游經濟的空間分布既有集聚、規則的分布,也有隨機分布。集聚分布表現為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省份聚集在東部沿海,最低的省份則集聚在西北部;發展水平相近的省份在空間上相鄰,如第四級發展水平的黑龍江與吉林相鄰、重慶與貴州、廣西相鄰;規則分布表現為東、中、西部雖呈梯度遞減、但東部、西部區內仍然存在旅游經濟發展高低相間分布;隨機分布則表現在“騰沖-黑河”以東地區,多種分布方式共同存在。由此可見,旅游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多分布在東部,但西部的四川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旅游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多分布在西部,東部的海南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從描述性分析可知,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多樣性,空間特征顯著,聚集與分散同時存在。無論是高發展水平區,還是中、低發展水平區,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省區皆存在空間相鄰的現狀;局部既有發展的“中心”也有發展的“凹點”。(2)旅游經濟發展存在較強的空間依賴性,空間集群呈增強-降低趨勢空間全局自相關揭示的是旅游經濟的空間依賴性。根據2000~2012年旅游總收入、以邊和點相鄰作為空間鏈接關系(將廣西、廣東作為海南鄰居),運用GeoDa軟件計算出其全局Morans’I指數(見表1)。2000~2012年間,指數值皆為正值,即我國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關系,意味著在此期間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省份在空間上表現為集聚狀態;其空間相關水平呈現先急劇增強后又有所下降但呈現出較為平緩的趨勢。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聚集程度在2005年達到最高(0.3123),最低的是2000年(0.2091)。可見,我國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強的空間全局自相關,即存在很強的空間依賴性。(3)相鄰省份的空間關系顯著與不顯著的數量各占1/2筆者根據旅游總收入繪制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局部空間分析(如圖2所示)。局部空間分析旨在了解某一省份與其相鄰省份之間的關系,揭示的是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異質性特征,其分布模式分為4類:高-高、低-低、高-低、低-高。高-高、低-低相關模式指的是某一省份的鄰省具有同樣的特征,為正相關,表示空間集聚;高-低、低-高相關模式指的是某一省份的鄰省與其特征相反,為負相關,表示空間離群。圖2顯示,旅游經濟空間關系的空間聚集與“中心-外圍”特征同存;同時,我國部分省區市與其相鄰省份空間關聯性不顯著,部分省份的局部空間關系明顯。旅游經濟發展水平高-高相關的省份有上海、江蘇,低-低相關的省區從東到西有甘肅、新疆;這說明高發展水平省集聚在東部,低水平發展省集聚在西北;高-低相關的省區僅有四川;低-高相關的省區有安徽、福建,“中心-外圍”特點突出,四川省是西部旅游經濟的發達地區,安徽、福建是東部地區的欠發達地區;也就是說,四川是西部旅游經濟發展的極點,安徽、福建是東部的塌陷點。
二、旅游經濟空間溢出效應計量分析
旅游經濟發展的空間特征表明,相鄰省份的旅游經濟間存在較強的空間依賴性,這從描述性角度說明,2000~2011年旅游經濟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其溢出效應的大小則要通過定量分析而得。
1.計量模型構建本文旨在分析政府主導模式下旅游經濟發展是否可以持續的問題,且從旅游經濟系統本身入手。旅游經濟系統包含了旅游需求、旅游供給兩個方面,具體而言,需求主要指的是可支配收入以及閑暇時間,而2000年以來,閑暇時間并未大量增加。因此,此處的旅游需求主要是指可支配收入;供給主要指旅游資源、旅游接待設施。相關研究結果認為,旅游資源稟賦、交通可達性、區位、基礎設施、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等均可對旅游業發展產生影響。產業發展環境反映了政府主導模式的具體內涵,其間主要是制度環境。因此,筆者構建空間面板回歸模型考察旅游需求、旅游供給與產業發展環境對旅游經濟發展的影響。其中,Y是各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D是各省的旅游消費需求,S是各省的旅游供給,P是各省的旅游發展環境,ρ表示空間溢出效應,ω表示空間相關關系,Xi,t為一組控制變量,μi為空間隨機項。
2.變量說明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用各省區的國內旅游收入表示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原因在于入境旅游收入受區位和開放程度的影響(廣東、上海、北京作為我國重要入境口岸,入境旅游收入遠高于內陸地區),為了剔除由于入境旅游與國內旅游的結構差異所導致的不一致,筆者未將各省的旅游總收入作為衡量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度量指標。旅游產業發展環境:由兩個方面構成,(1)旅游交通:交通被譽為旅游業三大支柱,對旅游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旅游經濟的特點之一是旅游消費者(即旅游者)的空間轉移,便捷的交通為旅游者空間轉移提供良好的服務,促進旅游經濟的發展。由本地交通密度即鐵路、公路的營業里程除以國土面積表示。(2)稅收:用稅收占旅游企業營業收入的比例代表政府對旅游企業發展的相關政策變量。稅收比例越低說明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反之則反。旅游需求:旅游者出游主要受閑暇時間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約束,因休假制度的限制,大部分旅游者的閑暇時間是確定的,受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約束更強。由于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數據獲取存在困難,本文將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衡量旅游消費的指標。旅游供給:由旅游景區點表示,旅游景區點是旅游業的發展基礎,是吸引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因素。我國存在多種旅游資源評價體系,分別由國務院不同部門進行評價。為了保持評價體系的一致性和避免重復,筆者選擇4A級景區和5A級景區作為旅游資源的變量,未將遺產類景區納入分析,原因在于遺產類景區包含在5A級景區內。由于A級景區體系始于2001年,2000年旅游資源的數據則由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世界遺產、優秀旅游城市加總而得。旅游接待設施為旅游者提供服務的,它依托旅游景區點的吸引力而存在,因此,未采用旅游接待設施作為旅游供給的變量。控制變量:對外開放水平,由外資酒店固定資產投入與酒店固定資產投入的比例表示,表示政府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對產業的管制狀態;由于對外開放水平部分省份部分年度的值為0,參照劉衛東等的做法,將其賦予一個很小的值10-8;各省區人口總數,用于人口規模對旅游出游率的影響。為了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筆者利用各個省份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收入進行了折算。
3.模型估計與結果分析面板模型的回歸估計包括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兩方面。由于本文是對我國大陸所有省份旅游經濟中的本地消費傾向進行分析,所考察的截面單位是總體的所有單位;同時,旅游經濟的兩大特點即旅游產品的不可轉移和旅游消費者的空間移動,各個地區的地理特定效應對于旅游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采用地區固定效應回歸模型更加合適。對模型進行空間效應檢驗可知,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依賴性是通過空間誤差沖擊所致(見表2),應選擇模型(2),并對模型(2)進行估計,結果見表3。表3中列出空間誤差模型、空間滯后模型和無空間效應項時的估計結果,筆者主要以空間誤差模型估計結果進行分析,將后兩者的估計結果作為模型和變量參數是否穩健的參考。從3個模型估計結果來看,模型與變量參數在統計上具有穩健意義,但變量參數的大小存在差異。(1)旅游需求旅游需求對旅游經濟發展的彈性系數為1.36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國內旅游需求在2000年以來的旅游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旅游業是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這個角度而言,旅游經濟的發展水平與旅游需求的大小相關;按照國際經驗,在人均GDP為1000美元時,旅游需求開始增長,尤其是國內旅游;為2000美元時,國內旅游進一步發展,出境旅游增長;5000美元時則出現城市的度假旅游。2000年以來我國旅游業的發展也佐證了這一發展途徑。如2006年人均GDP2070美元,同年,我國國內旅游人次13.94億人次,達到國民平均每人出游一次的規模,標志我國進入大眾旅游時期;2011年人均GDP5450美元,這意味著旅游需求進一步增加。(2)旅游產業發展環境旅游交通對旅游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彈性系數為0.451,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旅游經濟的旅游產品的不可轉移和旅游消費者的空間移動兩大特點決定了交通在產業發展過程的重要作用。交通作為旅游業發展的三大支柱之一,承載了游客從客源地到目的地往還的運輸任務,是客流流向的主導力量之一,這樣的矛盾現象集中體現在黃金周出游現象中。雖然有研究表明,交通對旅游業的發展影響不顯著,原因可能在于所采用的計量模型有差別所致。產業發展環境的另一變量稅負的估計系數在統計上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現階段旅游經濟發展并未受到政府的制度環境的影響。(3)旅游供給表示旅游供給的變量旅游資源對旅游經濟的估計系數不顯著。旅游資源作為旅游業的基礎之一,主要指的是旅游資源對游客的吸引力,旅游的基本內涵是“愉悅”和“異地”(與居住地相異),只要能夠對游客構成吸引力的客觀事物皆可稱之為“旅游資源”,從旅游的基本意義來講,旅游資源具有廣義性,這也許是以星級旅游景區、國家風景名勝區、歷史文化名城、優秀旅游城市等國家評定的旅游資源級別、數量來分析旅游資源對旅游經濟發展影響不顯著的原因。(4)旅游經濟空間溢出效應旅游經濟從描述性分析中可知旅游經濟存在較強的空間依賴性,計量結果說明,空間依賴性達到0.449,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旅游經濟發展存在較強的空間相互作用,這種作用是正向而有益的,即相鄰空間的省份(本文指的是邊界相鄰的省份)在旅游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這種作用可以理解為空間示范作用,即一省的旅游經濟發展可以帶動相鄰省份旅游經濟的發展,其促進程度為47.4%,這也就解釋了旅游經濟相似水平發展的省份為什么在空間上出現集聚的原因。
三、結論與建議
盡管旅游業是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日本的經驗表明,旅游業可以反哺經濟,在國家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扮演調結構、促增長的杠桿角色,反過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同時,它又具有重要的社會作用,可以調節人的身心,降低現代社會帶給個人的負面影響,因此,發展旅游業對經濟轉型時期的我國來說意義重大。“黃金周”以來,旅游經濟呈現出“東高西低”、相似發展水平空間聚集、局部“中心-外圍”特點突出的空間特征,且存在較強的空間依賴性(即空間集群),在時間上體現出“增強-降低”的趨勢;旅游需求、產業的發展環境以及旅游經濟的空間溢出效應是形成這一空間特點的重要原因。2000年以來,旅游經濟發展的事實說明政府主導旅游經濟發展的有效性,而不斷增長的旅游需求是保證政府主導旅游經濟發展模式的關鍵點;另外,政府為產業經濟發展所提供的基礎環境也是旅游經濟能夠發展的重要保障。筆者認為,政府主導的旅游經濟發展模式在這一階段取得了較好成績,若要繼續以此模式發展旅游經濟,必須處理好3種關系,即:旅游需求、旅游需求的地區差異與旅游業發展、相鄰省份旅游經濟發展、產業發展環境的關系。具體而言,根據旅游經濟發展的特點,中央政府則要掌握旅游需求的規律,合理引導旅游產業的發展與空間布局;地方政府則要因地制宜,考慮本省旅游需求以及相鄰省份的旅游經濟發展程度,考慮相鄰區域的合作,開發本地和相鄰省域的旅游消費,低水平省份可以借助相鄰高水平省份相關經驗,如可采取“鄰里模仿”等策略拓展現有的發展方式和路徑。而高發展水平的省份則要考慮鄰近低發展省份的影響,在旅游業發展過程保持既有的發展政策之外,還需加強與鄰近省份邊界區的合作和競爭并繼續保持領先發展。不論哪級政府,均要保障旅游經濟的發展環境。
作者:向藝鄭林王成璋單位:西南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四川工商職業技術學院西南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