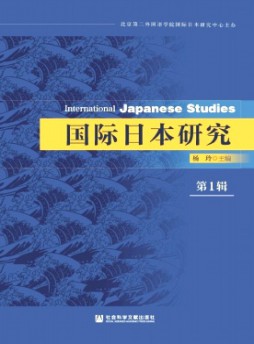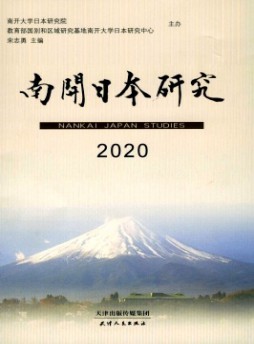日本病奇跡到沒落警示上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日本病奇跡到沒落警示上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時間:2003-4-22作者:鐘偉巴曙松趙曉高輝清
在東亞奇跡遭受金融危機的重創之后,人們開始重新反思所謂“東亞模式”,激烈批評者稱此模式不過是裙帶資本主義(CronyCapitalism)的拙劣復制品,熱烈鼓吹者則堅持“東亞奇跡既非虛構,亦未終結”,在亞洲仍為自身的成就和挫敗頗感茫茫然之際,美國“新經濟”已經締造了驚人景氣,歐盟11國也進行了人類有史以來發行區域貨幣的嘗試,所謂“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這樣的論斷再度顯得遙不可及。一種稱之為“日本病”的東西正使得亞洲經濟黯淡起來。
日本病給我們的啟示,也許在于作為“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如果政府以為其有能力看到,并且試圖“駕馭市場”,“增強市場”,就可能遭受市場的嘲弄;如果后來者只是看到可以模仿可以引進的“后發優勢”,忽視了重模仿輕創新而隱含的“后發劣勢”,甚至忽視了民眾進行創新的深厚力量,就可能陷入集體的失敗;如果把一切可能付出深刻代價的改革回避掉,甚至進而將這種回避上升到“特殊論”、“特色論”的高度,那么市場可能將不是特色的特色沖刷干凈,畢竟市場機制有其內在的邏輯統一性,而不是任由政府打扮的小姑娘。
也許,身患“日本病”的不僅僅是日本……
一、深陷泥淖的日本經濟:百年趕超似終結十年未曾磨一劍
從平庸到精彩而復歸平庸的日本經濟。從戰后至今,日本經濟增長大致可以分為3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1970年以前,為騰飛時期;第二階段是1970年到1990年,為快速增長時期;第三階段是1990年以后,為明顯衰退時期。前兩個階段是讓日本感到非常自豪的階段,而后一階段則是使其非常沮喪的階段。從這三個階段看,表現出明顯新生、成熟和衰敗的生命周期特征。有生則有死,有興必有衰,本來萬事萬物皆如此,也沒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是由于日本經濟在每個發展階段的特征都表現得非常突出,前后差別形成鮮明對比,這就使得日本經濟的發展歷史顯得不尋常了。
在二戰之后,出于圍攻紅色世界的需要,日本受到了與同為戰敗國德國不一樣的待遇,美國不僅讓日本政府繼續留任,而且在經濟上對其大力扶植。一方面,允許日本隔離于世界市場之外,通產省可以像在保育箱中一樣扶持日本工業企業,先是通過數以億計的貸款和稅收優惠政策促進重工業,如鋼鐵、造船和汽車制造業的發展,后來又把范圍擴展到計算機和生物技術領域。另一方面,西方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技術援助。從1951年到1984年,日本公司簽署了約4.2萬項引進西方技術的協議。日本僅花了170億美元的微小代價就買到了通過高科技時代的通行證。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日本經濟出現騰飛之勢。1960年,日本政府曾提出要在十年間讓GDP翻一番,而到70年實際上增長了2倍。
經過幾十年的快速增長,日本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趨勢似乎不可阻擋,日本人對自己的信心也空前高漲。當時,有個在金融和商業圈人士里很流行的笑話。一架飛機在中途發動機出了問題,上面有三名乘客。飛行員最后對乘客說:“對不起,發動機故障嚴重我們已不能繼續飛了。請寫遺囑吧。”三位乘客分別是一個法國人、一個美國人和一個日本人。法國人說:“我想唱馬賽曲”。日本乘客是位商人,說:“我想教你們一堂日本管理課。”那美國人說:“我在聽他講課前就想死掉。”
從泡沫破裂到“失落的十年”的日本經濟。進入9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信心似乎沒法太充足了。如果從1992算起,日本經濟在增長率為0.5%以下的低增長區間運行已經超過8個年頭,甚至有人把整個90年代稱為日本“失落的十年”。盡管1996財年,日本經濟略有好轉,但進入1997年后,日本反而陷入更深的經濟衰退,實際GDP連續三年下降,產出周期、收入和支出都進入下降軌道,產出缺口不斷擴大。針對經濟持續下滑的困難局面,日本管理當局祭出了以財政投入拉動經濟的著數。最近幾年,日本不斷出臺大型“景氣對策”,加大財政投入。僅以1998年一年為例,日本政府就兩度出臺財政刺激計劃,金額合計達40萬億日元,約為GDP的8%,致使政府赤字將擴大到GDP的10%,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比率超過100%。幾乎每個新的景氣對策都只是一只強心劑,推動日本經濟出現短暫的景氣恢復,效力十分有限,無法從本質上扭轉日本經濟的頹勢。1999年到2000年上半年,日本經濟出現了小幅上升的良好趨勢,曾使人們對日本經濟的復蘇產生了較大的期望。但從最近的數據看,這種期望看來又要落空。表1、90年代以來世界、美國和日本經濟的增長
項目/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世界GDP
2.2
1.8
2.7
2.7
4
3.7
4.3
4.2
2.5
3
3.5
美國GDP
1.8
-0.5
3
2.7
4
2.7
3.6
4.4
4.4
4.2
5.2
日本GDP
5.1
3.8
1
0.3
0.6
1.5
5.1
1.6
-2.5
0.2
1.4
資料來源:國家信息中心
據統計,2000年第三季度日本GDP增長按可比方法計算較上季度下降了0.3%,年率下降1.1%,這是三個季度以來的首次負增長;10月份工業總產值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5%,比一致預期數要低1個百分點;11月份東京消費者價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創下了連續第15個月走低的新紀錄;12月企業景氣季報"短觀"又顯示,大型制造業企業景氣判斷指數為正10,與9月報告持平,低于分析師預期的正11。面對這些數據,日本央行總裁速水優12月15日表示,日本經濟復蘇已經停滯。受其影響,美元對日元匯率在年低創出全年新高。沉疴難起和欲進趑趄的日本經濟。由于日本經濟新病舊傷一起迸發,上世紀90年代以來幾乎進入長期的休克狀態。慣于制訂產業政策的日本政府,由于再也制定不出新的、有前景的產業政策,迫不得已,只好放棄以產業發展為主導的調控政策,自1998年開始改用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國內需求。從財政政策看,日本政府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實施包括削減稅收、加大公共工程投入、實施信貸保證等一攬子振興經濟的計劃。但這些措施卻沒能刺激消費的增長,反而使預算赤字和公共債務加大。日本目前國債高達5.5萬億美元,是國內生產總值的1.3倍。從貨幣政策看,日本出臺了“零利率政策”,并且持續多年,直到去年才被取消。但在投資乏力、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人口老齡化現象嚴重的情況下,其效果也一直不明顯,除了形成一種所謂的新型“流動資金陷井”(即,有錢人更多地以現金的方式保存他們的錢,并放在保險柜里而不是銀行賬戶里。據一個研究所估計,這部分錢總計有13萬億日元(1250億美元)之多)和造成M1增多之外,其他方面并沒有任何顯著影響。現在日本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幾乎都用到了極限,真不知道下一步日本政府還能有什么招?!
如果從明治維新算起,日本在趕超西方列強方面已經付出了超過百年的努力,而在80年的幾乎成功的事后重新急劇滑落;自泡沫經濟破裂以來,日本為擺脫不景氣的尷尬更是十多年來殫精竭慮,而至今似乎仍欲進而趑趄。目前國際經濟界正在喪失對日本經濟復蘇的期待和耐心。經濟悲觀主義四處彌漫。據悉,美國中央情報局在2000年底的預測報告中曾經指出,日本在2015年將失去亞洲經濟大國地位。日本經濟似乎已經身染沉疾,欲振乏力。
二、“騎馭市場”的日本病:集體的失敗精神的荒蕪
我們已經熟知多種經濟發展病癥,例如“英國病”、“荷蘭病”等待,折射出不思設備和技術更新、躺在資本輸出的好處以及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對一國經濟所可能帶來的傷害。而日本病,則似乎是鮮為人知的疑難雜癥,但卻來勢洶洶,并可能使亞洲經濟的前景變得黯淡起來。日本病的病癥之一是過度重視后發優勢(BackwardnessAdvantages)。在西歐產生現代工業文明以來的幾個世紀中,亞洲一直處于世界體系的邊緣、半邊緣狀態,因此亞洲國家和地區幾乎毫無例外地有一種緊迫感,即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試圖通過植入西方市場經濟的架構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現代化。這種思使得亞洲國家不必要象歐美先行者那樣,經過無數次市場的起落和崩潰、無數爾虞我詐的案例及其處理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場運作框架,通過“后發優勢”亞洲國家可以迅速追趕上先行者。充分利用“后發優勢”,迅速趕上先行者,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這種趕超變成了急功近利,那么就必將是充滿崎嶇坎坷的道路。1801-1851年,當英國從簡·奧斯汀筆下的農業國轉變為查爾斯·狄更斯筆下的工業國時,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3%,英國完成人類近代史上的工業化花費了一個世紀的時間。1870-1913年,美國實現類似的轉變時,其人均GDP年增長率為2.2%。而美國從“爆發戶”真正成為一流強國也經歷了百年滄桑。1953-1973年,日本創造出人均GDP8%的年增長率,號稱為“陽光下的新事物”,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一個經濟曾經達到過如此高的增長率,但至今仍難說日本和美國等已經并肩前行。可見趕超的艱辛。歐美國家花費了數個世紀才使得人均收入超過了2000美元,而很多亞洲國家用了不足50年時間就達到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這種思路也有致命缺陷:1、“拿來”會產生排異反應,西方市場架構中的契約、信用和個人負責精神碰到“亞洲價值觀”就變形,從而導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業銀行制蛻變為日本銀企勾結的主銀行制;西方股份制蛻變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制等等,這些變形都被掩蓋在“具有本國特色”的借口之下。2、“拿來”會使亞洲缺乏創意,模仿和學習西方較之獨立摸索當然省事,但習慣于此則可能產生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等方面的貧乏,換言之,因為你有了游泳教練并學會了游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沒有留意原本可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3、趕超到接近先行者時,作為后來者突然會陷入到“無航標”的茫然之中。這在80年代的日本尤為突出,當年美、歐、日幾成三足鼎立之勢時,日本迅速地迷失在無榜樣的困惑中。亞洲國家在看到所謂“后發優勢”的同時,是否可以時刻提醒自己這其實就隱含著“后發劣勢”(BackwardnessDisadvantages)呢?
日本病的病癥之二是突出產業政策。歐美市場經濟的制度架構有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兩方面,宏觀層面大致是政府對有關競爭、行業準入等法律框架的完善,提供適當的公共產品以彌補市場失靈(MarketExternality);微觀層面則是私人部門進行交易的秩序。但日本在兩者間插入了一個中觀的東西:產業政策,即政府可以引導資源注入特定的產業部門,迅速造就所謂的“支柱產業”。盡管產業政策(IndustryPolicy)已經被視為20世紀經濟學的十大誤區之一,但日本等亞洲國家至今仍對此津津樂道。產業政策在亞洲垂而不死折射出市場機制始終在亞洲得不到根本尊重。1、如果產業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也就是說政府有預見未來新興產業的方向,此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嚴格優于市場機制,市場經濟就是多余的,如果產業政策是失敗的,那么政府就沒有任何必要搞產業政策。2、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展本身就表明,市場機制是“看不見的手”。我們似乎始終不能理解風險的本質乃是事先的不確定性。曾有這樣的笑話,說既然股票等證券資產的總體收益率比銀行貸款還高3個百分點,那么只要從銀行貸款炒股票不就可以進行套利了嗎?這種說法顯然忽視了這3個點的利差是高風險下集體理性的事后結果,?魑鎏逋蹲收叩耐蹲始瓤贍芑窶姆嵋部贍芮慵業床2嫡叩幕拿砸睬∏≡謨謖鍪恿誦灤瞬檔撓肯鄭撬餃瞬棵旁謁鋅贍艿姆較蚪懈髦中問醬蔥潞螅謔諧』頻拇蟪逼踩ナО苷咦慵5摹笆潞蟆苯峁7不即瞬≈⒌難侵薰遙謨屑?裳睦投薌拖蜃時久薌筒瞪妒蓖潛冉銑曬Φ模俾蹕蚣際躉蛑睹薌筒凳北閌腫鬮藪搿U貧┎嫡咭竦貿曬Ρ匭氪嬖諞慌馴恢っ魘淺曬Α⒍一勾笥蟹⒄骨巴鏡牟怠R簿褪撬擔謖廡┎抵幸延辛順曬Φ南刃姓擼⑼ü塹氖導っ髁蘇廡┎稻哂薪蝦玫姆⒄骨熬啊2嫡咚鸕淖饔鎂褪撬跣『笮姓哂胂刃姓叩牟罹唷R壞┱廡┎底呦蛄松鬧盞悖蚨雜Φ牟嫡咭簿筒黃鶉魏巫饔昧恕R蚨攬坎嫡呃捶⒄咕夢薹ǔ講檔納芷詮媛傘S紗絲蠢矗嫡咧荒苤卸唐讜縈茫豢勺鑫て詰牧⒐盡?/P>當一個故事尚未開始時,誰知道其結局?當一種產業政策被執行時,卻誰都不為其失敗負責,至今沒有誰為日本80年代中后期大力扶持模擬技術、忽視即將到來的數字時代的失敗負責,更沒有誰為締造了當年韓國經濟奇跡的、而今資不抵債的超級財閥的崩潰負責。
日本病的病癥之三是政府隱含擔保和企業預算軟約束。所謂隱含擔保(ImplicitGovernmentalGuarantee)是指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放貸損失提供不言自明的擔保,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得益于金融機構大量的資金扶持,至今一些日本的金融元老,不僅沒有考慮政府指定銀行向某些產業優先貸款的作法本身,使得銀行業幾乎淪為“第二財政”,并導致銀行貸款質量的持續惡化。反而認為,低利率有助于銀行緩解其支付存款利息的壓力;甚或認為如果日本政府當年如果能拿出10萬億日元來借助銀行,就不會象今天這樣需要至少支付50萬億日元來實施“金融大爆炸法案”(TheBigBang)了。所謂預算軟約束(SoftBudgetConstraint),按照短缺經濟學之父科爾奈的總結,大體含有兩個特點,一是事后政企間可就財務狀況重新協商,就是企業賠了掙了都可以和政府再商量;二是政企之間有密切的行政聯系,就是企業領導階層兼有行政領導色彩。既然大藏省的官員退休后到企業人職被稱為“神仙下凡”,既然部分企業可以源源不斷地得到主銀行的融資,既然銀行也在政府隱含擔保下不擔心死無葬身之地,那么非常自然地,政府、銀行和企業通過隱含擔保和預算軟約束被捆綁在一起,俱榮俱損??nbsp;目前,日本金融系統不良貸款已超過全部銀行貸款總額的5%,無抵押物清償的不良貸款估計達20萬億日元。日本政府曾提出60萬億日元(GDP的12%)拯救銀行計劃,其中,17萬億日元用于保護存款人,18萬億日元用于接管和使無清償力的銀行國有化,25萬億日元用于有清償力的銀行的注資。其效果如何還有待觀察。而曾經顯赫的日本公司則利潤連續下降。很多公司面臨壓縮開支和根據終身就業體制保障勞動力利益的兩難境地。盡管法定就業合同通常是一年期,但傳統的年功序列制使得多數雇員無合同或假定為終身雇傭,這樣企業很難在經濟衰退時期解雇其雇員;交叉持股更使得日本企業破產而死比半死不活地生存更為困難!類似的現象在東亞其它國家乃至中國難道不存在?由是觀之,亞洲金融危機暴露的并不是金融問題,而是政府管理的問題;反觀兩年來險象環生的亞洲經濟,危機給我們的最大教訓恰恰是我們也許根本沒有從中得到教訓!日本病的病癥之四是“駕馭市場”的偏頗。“日本病”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是政府對“看不見的手”和對個人創新的懷疑,是借用傳統文化和道德回避市場機制可能帶來的深層次微觀基礎的演化。對待市場機制,無非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較為放任的市場,政府只是彌補市場的外部性;一種是較為自負的態度,相信政府的自覺決策能夠較之市場的自發演進更為有效,而日本乃至亞洲恰恰就是后者。我們傾向于相信,政府有能力預見市場的意愿和方向,政府可以在配置資源(如果不是在企業層面,至少是在產業層面)發揮主角的作用。即利用人類已有的經濟學知識,政府可以“駕馭市場”或者“增進市場”(Market-enhancing)。換言之,我們希望免費享用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的好處,但不想付出交織的繁榮(投資加速或曰重復投資)和衰退(企業的兼并和重組)的代價。我們希望亞洲經濟可以和歐美媲美,但卻生怕淹沒在金錢的之中,這一切如日本金融學家竹內宏所聲稱的那樣:老一代精英以其勤勉、集體至上和拋棄個人私利造就了戰后的新日本,而現在的精英們卻深信新古典經濟學,毫無羞恥感,為了私利私欲而葬送了整個國家。不幸的是亞洲的竹內宏們沒有看到:純柏拉圖式的集體模仿、集體創新制在造就日本奇跡的同時也將“日本病”深植其中。最悲劇性的現象并不是新精英們的個人主義,而是沒有政府官員、銀行或企業,必須為10年之久的泡沫經濟負責,似乎也沒有亞洲各國政府官員為本國遭受的危機負責;而是裙帶風盛行、貪污腐化驚人幕布后的精神荒蕪。日本病使得我再度想起這樣一句話:如果你讓它負起各種各?娜吭鶉危敲唇峁∏∈峭耆桓涸鶉巍?/font>相關性:畢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