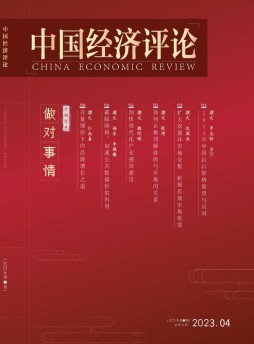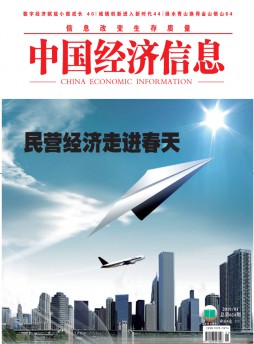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實現(xiàn)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實現(xiàn)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本文從分析中國經(jīng)濟體制現(xiàn)階段的三大矛盾出發(fā),概括性地提出了“公共尺度體制”、“公共財政體制”、“公共政府體制”的改革大目標,對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終極形態(tài)作了前瞻性探索,并按“三大體制”的要求,提倡應裁藩、分流、定分、厘標、退市,以此作為逼近改革終極目標的主要途徑。
歷經(jīng)30年改革,中國經(jīng)濟體制已與傳統(tǒng)計劃經(jīng)濟迥然有別,伴隨而來的不僅是超長期的快速經(jīng)濟發(fā)展,而且有社會演進、政治文明的巨大躍遷。作為一個跨世紀的龐大社會工程,改革總有它的最終目標,這個未經(jīng)詳細詮釋的終極目標及其實現(xiàn)途徑,事實上已伴隨中國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而逐漸浮出水面。我們需要的是進一步從理論和系統(tǒng)的制度層面對這一問題加以考察,以期指導后續(xù)依然奮進的偉大變革。
一、改革相與伴生的績效與矛盾
中國的體制改革是先農(nóng)村后城市、先投資后物價、先沿海后內地、先特區(qū)試驗后面上推廣而逐步發(fā)展起來的,而改革的總體目標也歷經(jīng)了一個逐步識別的過程。最初的目標是“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然后是“發(fā)展社會主義商品經(jīng)濟”,直至黨的十四大,肯定了改革的大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其后的各次黨代會又圍繞著這個大目標展開了各個階段改革戰(zhàn)略和主要任務的闡述和部署。
顯然,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走的是一條試錯型的漸進式道路。從一個社會整體制度創(chuàng)新的角度來看,漸進式道路的改革成本是最小的,而其收益則隨改革政策的投入呈逐漸遞增之勢。首先,改革從舊體制顯著的弊端入手,可收到即期的改革成效。無論是農(nóng)村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投資的“撥改貸”,還是企業(yè)的“放權讓利”、物價的“逐步放開”。中國經(jīng)濟改革總是從束縛經(jīng)濟發(fā)展最顯著的矛盾人手而逐步解套的。結果不但維系了現(xiàn)實經(jīng)濟發(fā)展進程不致中斷,而且漸次排除了發(fā)展障礙。使發(fā)展和改革能相得益彰:再次,由表及里的漸進性改革使得發(fā)展?jié)摿θ找嬉栽龃蟮膽B(tài)勢釋放出來。這里最為典型的是市場的開放與培育,亦即從消費品市場到生產(chǎn)資料市場,到勞動市場、資本市場。市場疆域的逐步擴大和體系的配套式推進。極大地消除了舊體制的掣肘,使得經(jīng)濟發(fā)展的潛力累積性地爆發(fā)出來。這是中國經(jīng)濟30年持續(xù)以9.5%以上的高速推進。且至今尚未出現(xiàn)拐點的根本原因。
矛盾與績效是伴生的。任何改革都有它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因為作為一種利益關系的大調整,改革會形成新的利益關系,一旦當新的利益既得者處于改革主導地位即制度供給人的地位時,改革便會依利益既得者的意志來安排,從而會出現(xiàn)路徑依賴而偏離改革的最終目標。特別是漸進式改革。這一問題更為嚴重。因為漸進式改革是分階段、分步驟甚至分區(qū)域來實施的。在每個階段、步驟、或先行改革的區(qū)域中,都會使某些社會成員從中獲益,且這種利益是受新制度的保護和鼓勵的,從而這些利益既得者便會竭力維護“半生不熟”的過渡性體制,或只愿將這種體制推向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從而使得改革出現(xiàn)鎖定效應,或者偏離正確的目標,這兩種傾向都會使改革很難繼續(xù)下去。
中國的改革在大的方面并未出現(xiàn)鎖定效應,是因為中央政府本身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且它作為改革的主要制度供給人始終在探索和堅持改革的目標。然而這并不能完全排除漸進式改革中的固有矛盾和利益關系的掣肘,這里主要有:
第一,企業(yè)化進程中的“雙軌制”。企業(yè)的市場化改革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至關重要的微觀基礎,它包括兩個相互支撐的戰(zhàn)略任務:一是市場化取向的國企改革;二是大力培育民營企業(yè)。這兩大任務最終必須殊途同歸才能達成市場化的目標。這個目標我們叫它為“多元一軌制”。也即是說,市場化的企業(yè),其產(chǎn)權主體可以是多元化的。這種多元化包括同一企業(yè)內部產(chǎn)權的多元化(股份制),以及不同企業(yè)產(chǎn)權形式的多元化(獨資或合資等),但不論企業(yè)的產(chǎn)權結構如何不同,各類企業(yè)的利益分配與調節(jié)都只能走市場這個唯一的軌道。這種“多元一軌制”是對企業(yè)改革完成形態(tài)的一個概括,它允許有分階段、分步驟的中間形態(tài)的存在。但如果這些中間形態(tài)不是朝著“多元一軌制”的最終目標邁進而是有悖于這個目標,則可判斷企業(yè)改革出現(xiàn)鎖定效應。
從現(xiàn)實進程來看,民營企業(yè)發(fā)展的制度柵欄幾經(jīng)拆除,已經(jīng)成為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國企改革則經(jīng)“退出式”改制和股份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實現(xiàn)了與市場的對接。但問題仍然集中在國有控股企業(yè),這部分企業(yè)在公司化外殼下,依然享有來自政府“欽許”的諸多壟斷利益,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賴市場競爭的利益分配,特別是緊缺要素和技術力量的供給。這事實上仍是一種雙軌制,即普通企業(yè)的要素供給完全走市場軌,而國有控股企業(yè)則可在關鍵部分走政府軌,其結果不但阻礙了統(tǒng)一市場的形成,而且使得市場的價值標準發(fā)生奇變。更應擔憂的是,一旦國有控股企業(yè)從這種雙軌制中獲得源源不斷的壟斷收益,便可依托利益相關部門的行政力量來固化既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后續(xù)的改革進退維艱。
第二,公共資源的部門化。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無論怎樣闡釋,市場化總是其基礎和主要內涵。這里包括兩層內容:一是“私人物品”或競爭性物品應全部由市場配置,且通過統(tǒng)一的價格尺度調節(jié);二是“公共物品”在可以采取“排他裝置”的條件下由市場配置,完全不能排他的物品由政府提供。但不論是否排他,公共物品都必須有切實的制度保障使其為社會成員所共享。現(xiàn)代產(chǎn)權理論的這個解釋,是對市場化社會的一個普適性說明。
若按這一理論辨析,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嚴格意義上完成了三分之一。即競爭性行業(yè)(等價于“私人物品”)只是部分實行了市場化,該行業(yè)中國有控股企業(yè)離市場化尚有不小的差距。至于公共物品在配置方式上并未向市場化邁出切實的步伐。這個辨識的依據(jù)在于,掌握著公共權力的各類行政部門,按改革完成形態(tài)的社會結構來考察,它們是超然于市場之外的沒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市場管理和公共物品的供給部門。然而。現(xiàn)階段公共物品沿襲計劃經(jīng)濟的配置方式由相關行政部門掌握,而這些行政部門在公共財政體制缺失及市場尋租的刺激下。逐步生發(fā)出強烈的部門利益沖動,并將其主管的公共資源(等價于“公共物品”)以行政審批的形式不同程度地與部門利益掛鉤,不少人甚至以此謀取個人私利。“管土地的吃土地”,“管水的吃水”、“管電的吃電”、“管交通的吃交通”。最后發(fā)展到任何公共資源及公共權力都可用來牟取部門和個人利益,直至“買官賣官”。公共物品配置的這種畸型化,不但減少了資源配置的效率,滋生了腐敗,而且會使改革成本居高不下,甚至會使改革歸于流產(chǎn)。
第三,地方政府強烈的市場參與沖動。政府是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制度供給人,然而市場化取向的改革目標恰恰是要將很大一部分權力逐步從政府手上轉向企業(yè)、市場和社會。隨著改革的推進,政府與市場在權力配置上應是一個此長彼消的矯正過程,保證這個過程的正常進行,需要政府有一種高度自覺的“自我犧牲”精神。但是在漸進式改革中,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要兼顧發(fā)展的任務,在財政“分灶吃飯”體制下,后者出于“保財政,保吃飯、保政績”的壓力,不能不披掛上陣,大搞招商引資和直接參與市場活動。地方政府這種強烈的市場參與沖動,是中國經(jīng)濟30年發(fā)展長盛不衰的一個重要動力源。但它至少在三個方面阻礙了市場化的進程,甚至可能使改革出現(xiàn)鎖定效應。其一,政府參與市場競爭,必然會把行政指令和行政科展活動帶進市場,從而割裂了市場價值鏈的傳導機制,在市場發(fā)育不全的狀況下,這種現(xiàn)象及其危害更為嚴重;其二,地方政府的利益沖動強化了既有的行政區(qū)域的分割,導致大小不等的疊層式的行政壁壘,結果便是統(tǒng)一市場的形成更為艱難,產(chǎn)業(yè)整合及資源大范圍的合理配置不能實現(xiàn);其三,由于地方政府直接參與市場活動,并普遍以遠低于市場正常價格的優(yōu)惠政策出讓資源以吸引投資,使得大量市場價格信號失真,導致資源環(huán)境的全局性緊張,使后續(xù)改革可操作的空間更為狹小了。
二、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
上述三大矛盾是在漸進式改革中逐步出現(xiàn)的,解決這些矛盾不是退回去搞計劃經(jīng)濟,而只有按市場化改革取向加以消除。這樣,改革的終極目標事實上便隨這些矛盾的解決而凸顯出來。這里涉及到對改革最終目標的辨識問題。理論界不少人依據(jù)國有企業(yè)的股份制改造和非國有經(jīng)濟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斷言“混合經(jīng)濟體制”已形成。該體制“尊重財產(chǎn)、尊重人權,尊重契約”,體現(xiàn)了法治社會的精神。這樣便在事實上將“混合經(jīng)濟體制”看作了改革的理想目標。應該說,“混合經(jīng)濟體制”只是對目前雙軌制的一個準確概括,但這種體制恰恰是漸進式改革推進到中間階段的產(chǎn)物,它不是改革的終極目標。具有極大的不穩(wěn)定性和暫駐性。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其主攻方向可用下述三大目標來概括:
一是“公共尺度體制”。競爭性資源的價格是公共的,而消費是排他的,這類資源必須也只能由市場配置,否則便會偏離效率目標。回歸到現(xiàn)實經(jīng)濟中來說,也就是一切競爭性的部門和行業(yè),不論它們的產(chǎn)權結構如何不同,其利益分配都必須走市場競爭的軌道,服從市場公共價值尺度的調節(jié)。對此,可簡稱為“公共尺度體制”。公共尺度體制顯然不是雙軌的,而是一軌式的。它是解決中國經(jīng)濟深層矛盾的唯一出路。首先,“公共尺度體制”解決資源環(huán)境的低效利用。資源的低代價、高消耗是發(fā)展“兩型社會”的最大困擾,不少人認為這一問題是市場經(jīng)濟造成的。恰恰相反,資源利用的低代價、高消耗恰恰是違市場而動的結果。以土地而言,近年來各地土地批租十分迅猛,但地價從不受市場價格的制約,地方政府爭相以低廉的價格出讓土地以吸引投資,由此損失的地價達數(shù)十萬億元之巨。不僅如此,在市場不起作用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也會失效,因為地方政府的數(shù)量擴張沖動在強大利益的誘惑下是很難抑制的。我們忽視了市場經(jīng)濟的效率原則總是從資源的稀缺性出發(fā)的,稀缺程度越高。使用資源的責任主體付出的代價越高,這樣便形成了一種維系資源可持續(xù)的自我矯正機制。不以市場價格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尺度,我們的資源和環(huán)境利用的代價只能由全社會和歷史來買單。而這種局面一旦沿存下去,整個發(fā)展都可能歸于崩潰。其次,“公共尺度體制”解決企業(yè)運行的雙軌制矛盾。盡管傳統(tǒng)意義的國有企業(yè)已不復存在。但國有控股企業(yè)仍然享有大量非市場競爭的壟斷收益。其關鍵是稀缺要素的供給還享受政府“父愛主義”保護。這樣,只要某一要素供給不走市場軌,便會通過一系列傳導機制引起整個市場價值標準的畸變。這就是為什么時下的眾多非國有企業(yè)都樂于鉆營政府門路而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場競爭上的原因。于是。價值標準的不一導致企業(yè)行為的不一,統(tǒng)一市場的生成和資源合乎效率的配置都只能假以時日了。建立“公共尺度體制”,關鍵是國有控股企業(yè)的要素供給應完全走市場軌。這與削弱國有經(jīng)濟的控制力完全是兩碼事,它只要求放棄國有經(jīng)濟的傾斜優(yōu)惠政策,切斷其源于行政口徑的要素供給渠道,將其真正地推向市場。如此,不僅有利于統(tǒng)一市場的生成。且會使國有經(jīng)濟的控制力進一步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