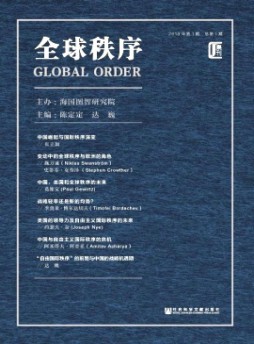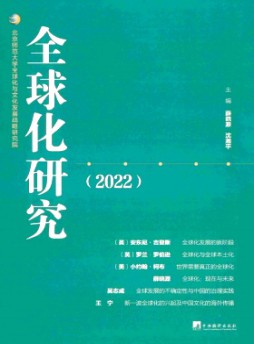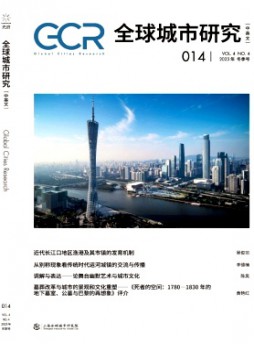全球價值鏈對制造業地位的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全球價值鏈對制造業地位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統計研究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方法、指標和數據
附加值貿易以垂直專業化為基礎,通過放松在計算時存在的兩個關鍵假設③,形成了更加完善的貿易統計框架。
(一)總出口的價值增值分解Koopman等基于對總出口的價值增值分解,通過分離國內價值增值和國外價值增值中的“純粹重復計算部分并界定其來源,進一步完善了增加值貿易統計框架,明確了總值貿易統計和附加值貿易統計的對應關系,成為增加值貿易的“集大成之作”。本文將借用該方法對我國出口進行價值增值分解,并測度出我國制造業各行業出口中包含的國內價值增值以及國外價值增值,為衡量我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參與程度和國際地位奠定數據基礎。現將該方法介紹如下:假設存在G個國家和N個部門,所有產品既可被用作中間品也可用作最終產品被本國和外國消耗④。因此,產品市場的出清意味著一國產出滿足。 其中,xs和xr分別表示s國和r國的總產出;表示s國產品生產過程中所需消耗的本國產品;表示r國產品生產過程中所需消耗的s國產品,也即r國產品對s國中間品的直接消耗系數;yss表示s國對本國產品的最終需求,ysr表示r國對s國產品的最終需求。因此,式(1)中等號右邊的前兩項加總表示的是s國產出中以中間品形式滿足本國和外國生產的部分,而后兩項加總表示的則是s國產出中用于滿足本國和外國最終需求的部分。將式(1)整理,并改寫成矩陣形式,得到:需要明確的是,出口中價值增值分解與附加值出口盡管相關但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附加值出口是指直接或間接包含在另一國最終消費中的一國價值增值;而出口中的價值增值是指包含在總值貿易中的不同來源價值增值。可見,盡管二者測度的都是生產國生產要素創造的價值,但是出口中的國內成分不受消耗地點的影響,而附加值貿易則取決于一國出口如何被進口國使用。綜合上述分析,最終可將一國出口分解為五個部分。其中,表示被包含在最終產品和服務出口中直接被進口方吸收的r國國內價值增值;表示包含在出口中間品中用于進口國生產國內需求產品的r國國內價值增值;表示包含在出口中間品中,供進口國生產向第三國出口產品的r國國內價值增值,也即r間接附加值出口;表示r國出口給進口方用來生產回流本國產品的中間品中含有的國內價值增值;表示出口中包含的國外價值增值。的加總等于各國附加值總出口。的加總則為一國出口中包含的國內價值增值,其中表示各國的直接國內價值增值出口,也即包含在本國最終產品出口中的國內價值增值的加總表示包含在一國中間品出口中的國內價值增值;表示回流的國內價值增值。
(二)指標基于貿易價值增值分解框架,等構建指標分別衡量一國在特定部門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以及一國對全球生產網絡的參與程度。反映一國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程度指標如下:其中,i表示產業,r表示國家,表示r國i部門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程度,IVir表示r國i部門間接附加值出口,該指標衡量的是有多少價值增值被包含在r國i部門的中間品出口中經一國加工后又出口給第三國,也即別國出口中包含的本國價值增值;FVir則表示一國出口中包含的國外價值增值;Eir表示r國i部門總出口。該指標越大,表明一國i部門參與國際價值鏈的程度越高。又考慮到即使兩國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相同,兩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也會存在差異,Koopman等進一步構建了反映一國國際分工地位的指標:該指標的基本思想是,一國特定產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國際分工地位反映在該產業作為中間品出口方與作為中間品進口方的相對重要性。如果一國處于上游環節,它會通過向其他國家提供原材料或者中間品,參與國際生產。對于這樣的國家,其間接價值增值占總出口的比例就會高于國外價值增值的比例。相反,如果一國處于生產的下游環節,就會使用大量來自別國的中間品來生產最終產品,此時IV會小于FV。該指標越大,表明一國在國際生產鏈上所處的位置就越高;該指標越小,則表明一國在國際價值鏈上的位置越靠近下游。
(三)數據本文中涉及的投入產出數據和貿易數據均來自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中的世界投入產出表①。WIOTs時間涵蓋1995—2009年,涉及的地區包括27個歐盟成員國②、其他13個主要國家(或地區)③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在內的41個經濟體,涵蓋的部門共35個,其中包括生產行為產品分類標準下的16個生產部門和19個服務部門。本文考察的制造業涉及以下13個行業:紡織原料及其制品,皮革、皮革制品和鞋類,木材及其制品,紙漿、紙制品和印刷出版,煤炭、煉油和核燃料,化學原料及其制品,橡膠和塑料制品,其他非金屬礦物,基礎金屬和合金,機械,電子和光學儀器,運輸設備(,其他制造業及回收。2013年1月16日,OECD和WTO基于WIOD數據正式聯合對外附加值貿易數據④,該數據庫提供了41個經濟體附加值貿易的相關數據,為本文涉及的國際比較問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該數據的劣勢在于在分行業附加值貿易數據上,并沒有逐一匯報WIOD中13個制造業部門的附加值貿易數據,而是將13個部門匯總成8個部門⑤,因此本文將利用WIOD數據對特定部門的附加值貿易自行計算。
二、中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與國際分工地位
(一)中國制造業出口中的國內價值增值1.制造業整體的國內價值增值。2000—2008年,中國出口中的國內價值增值比例下降明顯,從78.8%下降到66.7%。但2008年與2005年相比,國內價值增值在我國出口中下降的趨勢得到了扭轉。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國制造業國際分工地位經歷了“V”型的發展軌跡。然而,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出口國內價值增值比例仍然相對較低,甚至比墨西哥、印尼、印度等國還要低。相應地,中國出口中的國外價值增值比例由2000年的21.2%提高到2008年的33.3%。這表明,隨著對全球價值鏈的充分融入,中國出口對進口中間品的依賴程度逐漸提高。2.細分產業的國內價值增值。1995—2009年,中國制造業出口中大部分行業的國內價值增值比例有較明顯的下降,其中煤炭、煉油和核燃料、基礎金屬和合金、機械)、電子和光學儀器以及運輸設備)等行業下降得尤為明顯。而紡織原料及其制品和皮革、皮革制品和鞋類行業是唯一兩個國內價值增值比例提升的行業。究其原因,和其他行業相比,這兩個行業大部分生產過程是勞動密集型的,因此中國憑借廉價的勞動力能夠完成該類出口產品出口中大部分的價值增值。另一方面,加工貿易向一般貿易的轉型也是導致上述部門國內價值增值比例提高的重要因素。以紡織服裝及紡織制品和皮革制品為例,加工貿易占兩個部門出口的比重分別從2006年的29.4%和36.9%,降低到了2011年的19.4%和22.8%①。為進一步比較中國制造業出口中國內價值增值情況,本文選取了2000年和2009年中國與代表性國家及地區②在代表性③制造業中的國內價值增值比例中加以研究。結果顯示,日美兩個發達國家在代表性制造業出口中的國內價值增值比例明顯高于其他經濟體。這表明發達國家仍處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上游,這一點在國際生產分割程度高的行業,電子和光學儀器)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表明在國際生產分割程度高的行業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分出上下游的分工格局十分明顯。
(二)中國制造業國際分工地位④本文對2000年和2009年中國制造業各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參與程度進行了測度和比較,并分解了間接附加值出口和出口中國外價值增對全球價值鏈分工參與程度的貢獻。結果顯示,大部分中國制造業對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參與程度逐漸提高,其中煤炭、煉油和核燃料,基礎金屬和合金,化學原料及其制品以及紙漿、紙制品和印刷出版等行業是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程度最高的行業,其主要因素是間接附加值出口占總出口比例的提升。而機械,電子和光學儀器,運輸設備行業參與國際分工程度的提高則主要源于這些行業生產中投入的進口中間品比例的提升。與上述行業不同,中國紡織原料及其制品以及皮革、皮革制品和鞋類行業的國際分工參與程度出現了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進口中間品比例的下降,也即出口中國內價值增值比例的提升。這一點與上一部分中兩個行業國內增加值比例提升相呼應。同樣地,本文對2000年和2009年中國制造業各行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也進行了測度和比較。結果顯示,中國制造業整體處在下游位置,但表現出微弱的上升趨勢(國際分工地位指數由-0.05提升到-0.02)。從制造業各行業來看,在中國制造業出口的主導行業中,除了運輸設備行業外,其他所有行業都處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下游。而且對于電子和光學產品、機械以及運輸設備等技術水平較高的產品,我國出現了明顯下游化趨勢。與之相反,中國傳統的出口優勢產品,紡織服裝以及皮革鞋類的國際分工地位穩步提升,逐漸靠近上游位置。在其他資源型(煤炭煉油、木材、橡膠等)制造業部門中,中國則處在國際價值鏈分工中的上游位置,而且上游化趨勢明顯。但這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資源型行業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意味著中國越來越多地扮演原材料提供者的角色,其代價是大量的資源輸出和環境污染。
(三)中國制造業融入全球價值鏈的路徑分析上述分析表明,中國不同類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路徑是截然不同的。由于行業的技術層次決定了生產的國際分割程度,本文根據技術層次⑤的不同對不同制造業部門融入價值鏈分工的路徑進行考察。結果顯示,不同技術層次部門,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路徑存在巨大差異:對于低技術部門,全球價值鏈分工參與度與國際分工地位之間出現了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意味著紡織、鞋類等行業更多地通過扮演中間品提供者的角色來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促進了上述行業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對于中低技術部門,全球價值鏈分工參與度與國際分工地位之間出現了不太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中國的中低技術行業更多地是通過依賴進口中間品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中高技術部門和高技術部門迅速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過程中,國際分工地位不斷下降,且技術密集度越高,下降得越明顯。這意味著越是高技術部門,我國越會通過從事加工裝配等下游環節參加國際分工,面臨的“鎖定”風險越大。上述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由我國制造業各行業參與國際分工模式的差異造成的。首先,對于電子和光學制品、運輸設備等中高技術產品,由于其生產模塊化程度較高、生產環節較多,所以成為價值鏈分割程度較高的行業。對于該類產品國際分工的參與,中國主要憑借豐裕的勞動力要素專業化從事加工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同時也是下游的生產環節,因而導致出口中包含了大量來自其他國家的價值增值。同時又由于我國在技術水平的差距,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掌控研發環節,向其他國家提供包含核心技術的中間品,最終導致了我國在該類制造業的國際分工中處于下游地位。而在此過程中,外資企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出于降低生產成本的考慮,在華外資企業通過整合母公司生產性資產與中國勞動力要素,成為聯結中國與全球價值鏈的紐帶,同時導致加工貿易成為我國參與該類行業國際分工的主要模式。以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例,2007年該行業出口中有88.3%是加工出口,其中的93.4%由外資企業完成①。因此,提高我國在高技術行業技術密集環節的研發能力,掌握核心競爭力,是我國在參與國際分工的同時提升國際分工地位的關鍵。其次,對于紡織服裝、皮革鞋類、木材、紙張等低技術行業,由于生產的國際化程度較低,加工貿易并不是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主要方式。同時,上述行業生產過程的相對集中,意味著哪些國家的要素豐裕度與上述行業核心增值環節的要素密集度相契合,哪些國家就將獲得上述行業出口中的大部分價值增值。這意味著,中國作為勞動力豐裕的國家,可以通過參與價值鏈分工獲得上述勞動密集型行業生產過程的絕大部分價值增值,并通過貿易方式的轉型升級,實現國際分工地位的逐漸攀升。最后,對于煤炭煉油、橡膠、非金屬礦物等行業,其生產具有明顯的資源導向性,而且通常作為原材料用于生產滿足消費需求的產品,因此融入價值鏈分工對我國上述行業分工地位的影響并不明確。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中國在上述行業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它意味著資源的大量流出。
三、結論性評述
本文運用附加值貿易框架,對我國制造業各行業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路徑進行了刻畫,得出了以下結論:首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國際分工地位出現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形發展軌跡,但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制造業整體仍處在下游地位,這主要體現在國內價值增值比例在我國出口中占比較低;其次,對于紡織、鞋類等技術水平低的行業,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帶來的間接附加值出口提升,導致我國在上述行業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逐漸提升,而對于機械、電子、運輸設備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以加工貿易為主,且明顯處在下游環節,并存在被鎖定在低端環節的風險;最后,參與國際分工模式的差異是導致不同行業融入全球價值鏈路徑出現分化的根本原因,對于紡織服裝、鞋類等勞動密集型行業,我國憑借勞動力優勢完成了大部分價值增值,導致我國該行業的國際分工地位逐漸上升,對于國際生產分割程度較高的高技術行業(比如機械、電子和運輸行業),在外資企業主導下,我國以加工貿易方式融入全球價值鏈,被鎖定在加工裝配等下游環節。因此,融入全球價值鏈在使我國對外貿易迅猛發展的同時,也使我國制造業尤其是中高技術部門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價值鏈參與度和國內增加值比例兩個維度將發展中國家全球價值鏈的發展路徑概括為:融入、升級、準備、競爭、反轉和蛙跳。而目前最適合我國的發展路徑是“升級”,也即在充分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前提下,通過提高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需要指出的是,限于世界投入產出表沒有區分進口中間品的最終用途(用于生產本國消費產品還是用于出口),本文的測算結果沒有考慮加工貿易與國內消費品在進口中間品投入密集度的差異,存在高估我國出口中國內價值增值比例的可能。可以預期,考慮加工貿易后,加工占比較大行業(比如電子和運輸設備等)的國際分工地位還要下降,將進一步驗證本文的結論。而考慮加工貿易和服務業對中國制造業的國際分工地位的影響是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作者:王嵐單位: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國際貿易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