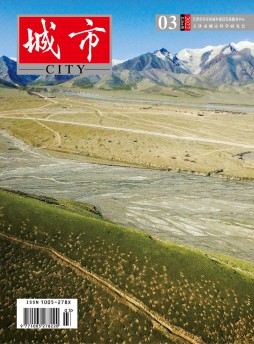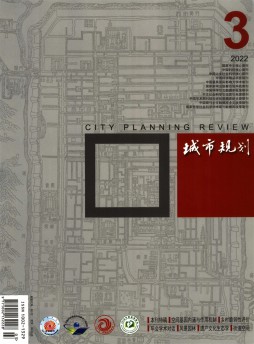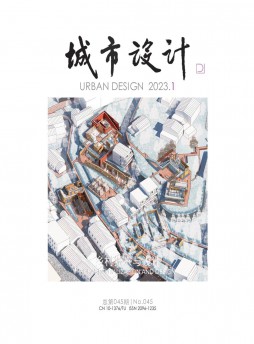城市與小城鎮的決定因素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城市與小城鎮的決定因素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統計科學與實踐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實證分析
1.指標選取。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變遷過程,諸多因素對這一過程產生影響。陳洋等(2007)認為城市化進程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并且兩者的關系日益密切。而經濟的開放、外商直接投資等,同樣也促使了人口的集聚和經濟體制的[1]改革,帶動了農村城市化過程。現有文獻中關于城市化影響因素研究較成熟,歸納起來這些因素主要有: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總量、產業結構、交通狀況、經濟對外開放度以及政府政策和公共產品供給等。
2.模型構建。根據影響城市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及選取的量化指標,構建江蘇省城市化計量模型。模型分析的時間跨度為1978年至2012年,數據來源為各年份的《江蘇統計年鑒》。其中,Z取rat_cit和rat_tow,即城市人口比率和城鎮人口i比率;c為各變量的系數;gdp為地區生產總值;peop是地區i總人口數變量;ter_stru反映產業結構變量,包含第三產業的產值結構ter_pro和就業結構ter_emp;open是經濟的開發程度的衡量,包含貿易總額變量trad和使用外商投資總額fdi變量;comm反映的是區域內交通狀況變量,以公路通車里程指標測度;gov是政府能動性變量,包含城市公共產品供給和戶籍制度兩方面。城市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由城市公交車輛數量bus變量、城市公交營運線路長度busline變量、城市實有道路長citroad變量共同衡量。江蘇在1998年和2002年頒發《江蘇省縣以下地區戶籍管理規定》和《關于進一步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因此使用虛擬變量d1和d2捕捉戶籍制度對城市化進程的影響。為降低和消除變量的異方差性,對除城市人口比率、城鎮人口比率以及產業結構和虛擬變量的其他宏觀變量取自然對數。在回歸前為防止偽回歸,需檢驗變量的平穩性。表1是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的結果,顯示各變量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一階單整,表明可建立線性回歸方程。表2是計量方程的回歸結果。以城市人口比率rat_cit為被解釋變量,a1模型中包含所有解釋變量,a2為剔除不顯著或顯著性不高變量后的模型。同理,以城鎮人口比率rat_tow為解釋變量,b1中包含所有解釋變量,b2為剔除不顯著或顯著性不高變量后的模型。
二、主要結論及解釋
1.模型結果表明,江蘇第三產業發展水平、進出口貿易、地區交通狀況以及城市基礎設施等對城市人口比率起著促進作用,而總人口數量抑制城市化進程。該結論與陳洋等[1,2](2007)、Krugman(1991)等研究結論較為一致。第三產業發展、進出口貿易增長能帶來就業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時也給生產經營和生活提供更多產品和服務,使得城市的吸引力變強,加大城市對農村人口轉移的拉力效應,城市化水平提高。交通網絡發達,能減小勞動力、原材料、中間投入產品的流動難度,降低運輸和通勤成本,加快了要素和產品向城市集中。另外,城市道路、城市交通狀況的改善,使得原本城郊邊遠地區成為可居住、可生產經營的地區,城市生活、經濟活動的范圍拓展,提高了城市可承載的人口數量。控制其他變量,總人口與城市化水平負相關,但影響不顯著。人口總量越多,需轉移的農村人口越多,實現高階段的城市化需要的時間越長,城市人口比率提高越緩慢。
2.國民生產總值及FDI對城市化水平的反作用效應。一般研究表明隨著人均GDP水平的增長,城市化率趨于上升[3](HollisCheneryandMoisesSyrquin,1975)。本文在引入產業結構、交通以及城市基礎建設等變量后,江蘇的國民經濟規模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其原因在于江蘇的產業選擇和收入分配格局。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主導了江蘇經濟的發展,但相對于服務業,第二產業資本密集程度高,勞動力需求相對較少,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份額越大,服務業比重越小,就業擴張的限制就愈強。因此,依靠以資本密集型產業帶動的經濟增長,并不能推進城市化進程。另外,占經濟相當比重的房地產及相關行業的發展,在帶來國民生產總值增加的同時,也抬升了房價,提高了城鎮、城市的生活、生產經營成本,抑制了城鎮、城市潛在遷入個人和企業,或將一部分主體擠出城鎮、城市范圍。國內大多數研究(陸銘等,2004)證明FDI對城市化有著[4]促進作用。但本文結果顯示FDI對江蘇城市化有抑制作用。相對于本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知識技術、資本要素的密集度高,勞動力需求相對較低,在市場份額一定條件下FDI增加勢必擠出勞動要素。因此,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FDI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相對降低勞動力需求作用就越明顯,對城市化的抑制效應也就越顯著。
3.戶籍管理政策取向不同,對城市化進程的作用也不同。1998年江蘇出臺《江蘇縣以下地區戶籍管理規定》,提出“實際居住在城鎮建成區內,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生活來源的非城鎮常住戶口公民”在符合有關規定條件下可以轉為常住戶口。該文件在給一部分人“放行”的同時,也對大多數的流動人口設立了進入門檻。加上當時的人口管理和城鎮相關配套遠未成熟,對人口遷移的促進作用不明顯。2002年江蘇省提出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打破城鄉分割戶籍管理二元結構,下放戶口審批權限,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體制。因此,在準遷范圍和入戶條件上有了顯著的放寬,尤其在投資和人才引進上,給予了較大的優惠政策。對于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具體準入條件上,文件規定由各省轄市人民政府研究確定,一定程度上給地市級政府調控城市規模法律支持。模型也證實了這點,虛擬變量d2系數表明2002年戶籍改革對城鎮人口比率的提升效果高于城市人口比率。
4.城鎮人口比率受政府因素影響較大,而城市人口比率受市場機制影響更明顯模型b2中政府對公路網絡以及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極大的促進了人口向城鎮轉移,而模型a2中決定城市人口比率的主導因素是經濟規模、第三產業發展水平以及進出口貿易額。
三、啟示
小城鎮和城市作為城市化的兩種不同的空間載體有著各自的優勢。以分散的小城鎮為載體進行的人口城鄉轉移,其成本相對較低,且見效快,但由于其經濟集聚效益不明顯,難以支撐起高端的產業結構,加上受土地、環境等資源約束,弊端日益凸顯。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在資源配置效率上有著明顯的優勢,但對于人口眾多的國度或地區,單純以大、中城市作為城市化的空間載體,將潛存“城市病”風險,有些城市已經出現交通擁擠、社會治安、生活成本高昂等諸多的城市問題。但目前江蘇各城市人口密度遠未達到發達城市水平,考慮到未來技術進步、城市管理水平提升等,江蘇大、中城市在城市化進程中有著極大的發展空間。汽車、地鐵、城際列車等新型交通網絡和交通工具的應用,新型住宅建筑材料和建筑技術的改進,以及物聯網等信息技術對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等,都使得城市空間更傾向于節約和高效,帶來城市容量的突變。時下,江蘇與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動車、高鐵開通,使得各種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流動,經濟活動也將在更廣的區域中重新排布,這必將帶來新一輪的城市化范圍的大延展、城市化空間形態的大變遷。最佳的城市化空間形態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自身系統的累進在動態中趨于均衡。因此,實現江蘇城市化空間形態優化均衡,必須在尊重和應用經濟規律、市場機制對城市發展的主導作用的同時,發揮政府對城市化能動性干預,雙管齊下、優勢互補,以推動城市化向更高階段演進。
作者:張瑜單位:國家統計局江蘇調查總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