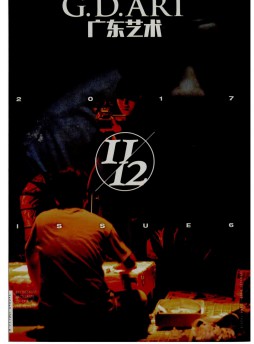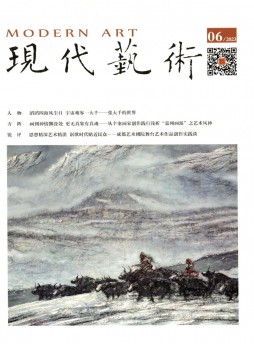藝術與哲學關系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藝術與哲學關系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葉燮 《原詩》 研究綜述
清代文論家葉燮的《原詩》,體系完整,論述精到,是繼劉勰《文心雕龍》之后的又一座文學理論高峰。自其問世之后,研究者代不乏人,產生了較大影響。聲名較著者,國內有朱東潤、郭紹虞、霍松林、蔣凡等人,國外有日本的青木正兒、德國的卜松山等人。以上學者功底深厚,分別從文學、史學、哲學(美學)等領域切入,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就,為后世了解和進一步研究《原詩》提供了學習的范式。
自21世紀以來,學術界對《原詩》的研究更加細化,同時,由于西方文論的深刻影響,“中西比較”或“以西釋中”的方法被引入,從而出現了新的研究熱點。總體來看,新世紀以來的《原詩》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
一、關于《原詩》文學流變思想的研究
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以蘇州大學李曉峰的博士論文(2006)為代表。該文認為,葉燮的文學史觀十分明確和準確,是建立在對詩歌流變進行仔細考察的基礎上的,并認同詩歌處在永不停歇的發展運動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一認識決定了葉燮文學史觀的發展性和開放性。該文肯定葉燮文學流變的開明性,認為他打破了封閉的詩歌史,為詩歌史走向開放提供了新鮮血液。很顯然,這種認識對我們分析葉燮的文學史觀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與此相類似的論文還有馬瑩的《葉燮詩學思想基本特質的再檢討》(云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劉瀏的《變而不失其正――葉燮論綱》(《華僑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白春香的《葉燮以“變”為核心的辯證的理性主義詩學觀》(《晉中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楊暉的《正變思想研究的追溯與反思》(《河南科技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等。
除此之外,具有創新性的論文還有李曉峰的《葉燮的矛盾性和現代性的方法論生成》(《社會科學輯刊》2006年第3期),該文對“理、事、情”從客觀到主觀進行了描述,并且將“現代性”引入到《原詩》的研究中,她認為《原詩》的現代性表現在葉燮學科意識的獨立、文學流變觀的開明、批評意識的創新以及強烈的反傳統的意識中,應該說,這一論斷頗有見地。
二、關于《原詩》美學思想的研究
美學思想研究已經成為《原詩》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集中體現葉燮美學思想的,主要是創作論部分。劉曉春《葉燮美學思想研究》(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一文對《原詩》的審美主客體以及主客體之間的關系作了較全面的論述,該文認為,葉燮詩學觀中的審美主客體主要有4種關系:“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的對應關系、“含蓄無垠”的認識關系、“倘恍以為情”的體驗關系、“虛實相生”的創造關系。
李曉峰《葉燮研究》認為葉燮的主客體關系論是葉燮詩學思想的核心部分,“情”是主客體發生關系的關鍵所在,在人、物由分離到合二為一的過程中,達到了情理交融的審美境界,從而消解了簡單意義上的“情”“理”相對的看法。該文還將“法”這一理論貫穿其中,認為“法”是將“理、事、情”聯系起來的重要樞紐,這樣就將主客體關系論和創作聯系了起來。
此外,劉曉春《論葉燮對審美主客體關系的分析》(《山東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張兆勇和張彩云的《論葉燮美學思想》(《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2年第4期)、王向榮的《葉燮原詩的“中和”之美》(《哈爾濱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等文章都對《原詩》的審美思想作了分析。但就總體來看,這些論述都沒有超越前輩學者的研究。
三、關于《原詩》與其他理論著作詩學觀的比較研究
近年來,有學者將《原詩》與其他文論著作進行了比較,這其中也包含了與西方文論著作的比較。洪濤的《、心物接觸論的比較――并略論西方文論的相關議題》(《聊城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主要圍繞著“觸”“迎”“合”這三個方面,將《姜齋詩話》與《原詩》進行了比較,在比較的過程中,借助了美國文論家艾布拉姆斯的文學“四要素”概念,論述兩部作品在不同層面顯現的優缺點。王向榮的《“詩性言說”與“思性言說”――與比較研究》(《綏化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以《文賦》和《原詩》為例,分析了中國文論中的兩種言說方式,比較了兩者的長處,指出這兩種言說方式各自存在的意義。
方漢文的《清葉燮之“理”與柏拉圖的“理念”(Idea)》(《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通過對中西文論中關鍵詞“理”的解讀來分析和比較中西方文化與思想觀念的差異。靳希的《從與看如何正視古典文學――以葉燮與布瓦洛為例》(《芒種》2013年第21期)從批評態度、理論主張等方面對東西方的文論進行了比較分析。此外,白春香的《葉燮的詩歌審美思想與俄國形式主義詩學之比較》(《延安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殷晶波《兩種美學追尋的碰撞――試比較賀拉斯與葉燮的美學思想》(《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等都運用了比較分析的方法,闡述了中西文論的相通之處,但個別論文對于西方文論的理解不夠透徹,導致相關分析不能切中肯綮。
四、關于《原詩》創作理論及其影響的研究
葉燮認為寫詩有“法”,這種“法”就是要恰當地表現“理”,確切地表述“事”,真實地表達“情”。張紅玉的《論葉燮中的“法”》(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對葉燮的“活法”與“死法”進行了認真分析,論述了“法”與“理、事、情”“才、膽、識、力”以及“胸襟”之間的關系,認為“法”是貫穿其中的重要因素。“法”作為《原詩》中一個重要的理論范疇,對這一理論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原詩》的創作理論。張紅玉在論文中還論述了《原詩》的“活法”理論對葉燮弟子及曹雪芹《紅樓夢》詩歌創作理論的影響。
劉曉龍《試論葉燮對詩歌理論的影響》(《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4年第15期)一文從五個方面論述了葉燮理論對《紅樓夢》詩歌批評理論的影響,這五個方面分別為:詩歌創作無定法,詩歌內容與形式,主客體的“理、事、情”,詩歌貴在創新,詩人要有形象思維。該文分析了葉燮詩歌創作理論對《紅樓夢》詩歌理論的影響,雖然有證據不充足之處,但對拓展我們的研究視野仍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劉靜的《沈德潛、薛雪對葉燮詩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內蒙古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從《原詩》的源流分析、創作方法解讀以及影響接受等方面,較為詳盡地分析了葉燮理論對其學生的影響以及學生對他的繼承與發展。
五、關于《原詩》批評觀的研究
葉燮《原詩》的批評觀已經成為研究《原詩》的一個重要方面。鄧心強的《論葉燮詩學批評的突出表征》(《玉林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認為,《原詩》的批評思想既有對傳統儒家思想的繼承,又有創新,具有一定的現代性。文章從“破”與“立”的角度,運用“點線面”相結合的方法,分析了葉燮的批評觀。樊藍燕《葉燮理論的“破”與“立”》(《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12年第14期)從“破”與“立”兩個方面論述了《原詩》對詩歌、詩人、批評家的批評。劉鐵男的《葉燮批評論中對歷代詩學詩歌的批評》(《平原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從葉燮對歷代詩學和詩歌的批評兩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除此之外,《原詩》理論建構的一大特色是大量采用比喻的修辭手法,對于這一點,研究者關注較少。據潘鏈鈺的《葉燮比喻修辭的藝術特征》(《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統計,《原詩》使用比喻的地方多達19處,在全文中所占比例將近十分之一,可見葉燮對于比喻手法的鐘愛。該文從葉燮所處的時代背景、學習態度以及特有的思維方式入手,分析了葉燮大量使用比喻的原因,指出使用這一修辭手法的作用。
綜上所述,21世紀以來,對葉燮《原詩》研究的領域雖然有所拓展,研究也有細化的傾向,但總體來說,成果并不突出,尤其是對葉燮詩學思想與西方詩學思想的對比研究不夠深入,仍存在較大的研究空間。
參考文獻:
[1]劉曉春.葉燮《原詩》美學思想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
[2]李曉峰.葉燮《原詩》的矛盾性和現代性的方法論生成[J].社會科學輯刊,2006,(3).
[3]李曉峰.《原詩》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4]馬瑩.葉燮《原詩》詩學思想基本特質的再檢討[D].昆明:云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第2篇
關鍵詞:丹納;三元素;認識
中圖分類號:J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4)26-0263-01
丹納生活在19世紀的歐洲,那時的歐洲正處于一個極度驕傲和膨脹的時期,究其原因在于,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隨著自然科學的巨大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歐洲人逐步擺脫了封建宗教思想禁錮的枷鎖,特別是在18世紀末期,資產階級啟蒙思想迅速發展,影響到整個歐洲。歐洲在自然科學和民主制度的影響下,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物質也變得豐富無比,這讓歐洲人對自然科學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丹納自然深受19世紀自然科學界的影響,特別是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無論物質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都可以解釋;一切事物的產生、發展、演變、消滅,都有規律可循。因此,丹納的治學方法是從事實出發,不從主義出發;不是提出教訓而是探求、證明規律。同時,他還深受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和法國哲學家孔德的影響。孔德認為,理性已經滲入到自然科學的每個角落,很自然的也進入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所以,孔德第一次把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納人到觀察科學的范疇,把觀察的方法引入人文社會科學之中。在這種學術環境的影響下,丹納提出了一個重要理論―“種族、時代、環境”三元素說,強調了三元素對文學藝術的決定性影響。具體而言:丹納在《藝術哲學》中以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繪畫、尼德蘭繪畫和古希臘的雕塑為例,以藝術發展史實為依據,強調了種族、環境、時代等三個元素對精神文化的制約作用,并認為在三個元素中,種族是“內部動力”,環境是“外部壓力”,時代則是“后天動力”,這三種力量合起來共同促進了精神文化的全面發展。
丹納“三元素”理論的形成是有歷史淵源的。早在18世紀初,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孟德斯鳩就認為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政治文化不僅和居民的宗教、癖性、財富、人口、貿易、風俗習慣等有關,而且同氣候、地理條件及農、獵、牧等各種生活方式也有極大關系。史達爾夫人承襲了孟德斯鳩的這種觀點,她在《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論文學》和《論德國》中進一步認為不同的自然環境決定了不同的精神風貌。不僅如此,、社會制度、風俗習慣也都不同程度地左右著文學藝術的發展。史達爾夫人的這種觀點為丹納的“三元素說”開辟了道路。除此之外,對丹納影響較大的還有黑格爾。黑格爾雖然是從“絕對理念”出發研究美和藝術,但他關于環境、沖突、性格以及古希臘神話的分析,都給予時代、環境、民族等因素以極大的重視。可以說,丹納是把孟德斯鳩的地理說、史達爾夫人的文學與社會關系的研究、黑格爾理念演化論和文化人類學的實證研究綜合起來,提出種族、環境、時代三元素理論的,并形成了一個較為嚴密、完整的學說。我們從丹納的“三元素說”可以看到民族特性對藝術家和作家的人生態度、理想、性格、情感等方面的持久性的影響,也可以看到環境、社會意識、時代精神對文化藝術發展的決定性作用。所以,丹納在《藝術哲學》中,從三元素理論出發,詳細論證了他的看法:因為種族的不同,造成日耳曼民族的藝術與拉丁民族的藝術不同,前者更渾樸,后者則更精致;因為自然環境的不同,所以意大利繪畫多表現理想的優美的人體,而尼德蘭繪畫多表現現實的甚至是丑陋的人體;因為時代不同,所以古希臘人能夠創造出簡單而靜穆的偉大作品,而現代人只能創作出孤獨、苦悶、掙扎的藝術。在當時很多的文藝研究主要從既有觀念出發,或僅僅圍繞作品情節、人物進行研究,經常把人物孤立于其所生活的環境,不能從更廣泛的社會、歷史角度去考察的背景下,丹納提出的“三元素說”無疑是開了一代風氣之先河,極具啟發性,并為以后的實證主義藝術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丹納《藝術哲學》中所講的“種族、環境、時代”中的具體內涵,是復雜多樣的:“種族”,在丹納那兒可以是“人種”,有時也指為“民族”、甚至“宗族”或藝術家群;“環境”,既指地理環境、氣候條件,有時也偶然地含有社會環境的意思;“時代”的內容就更為廣泛,精神、制度、政治、文化、生產條件,甚至包括對經濟狀況的某種程度上的分析。這就明顯地告訴我們,丹納的“三元素”說與孟德斯鳩、史達爾夫人、圣?佩韋乃至孔德,都有著實質性的不同。他賦予這些概念以物質的實在性和具體性,而這是前人所不能企及的。但與此同時,丹納把藝術的產生與發展以及藝術的本質,最終歸結到“種族、環境、時代”三元素之上,使他所具有的唯物論的觀點不能繼續發展而走向唯物史觀,并最終走進唯心主義的死胡同里。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丹納《藝術哲學》中唯物論與唯心論同時并存,并不時地發生矛盾,而這恰恰反應出丹納世界觀中正確與錯誤之間的經常不斷的矛盾。
參考文獻:
[1]李學智.丹納中的地理環境與社會生活[J].史學理論研究,1994(04).
[2]丹納.藝術哲學[M].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10).
第3篇
作者簡介:王永祥(1967― ),男,漢,江蘇大豐人,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在讀博士。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美學,文化學。)
中圖分類號:J01文獻標識碼:A
Bakhtin’s Dialogic Aesthetic Ideology
WANG Yong-xiang
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巴赫金(Mikhail Mikhaǐlovich Bakhtin,1895C1975)堪稱20世紀蘇聯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于20世紀60年代被發現后,其復調理論、對話理論、狂歡化理論等在歐美廣為流傳。他認為,如果將藝術的視野局限于藝術自身的領域內,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或藝術家本身的創造的自由,那么藝術就陷入嚴重的危機。巴赫金的哲學美學是一種交往性美學,即參與性或對話性美學。而巴赫金的對話性思想首先表現為一種關系論。
一、巴赫金的三種“關系”
在《1970年――1971年筆記》中,巴赫金[1](P.401)提及三種類型的關系:客體間的關系、主體和客體間的關系、主體間的關系。
巴赫金的“客體間的關系”包括“物體之間、物理現象之間、化學現象之間的關系,因果關系,數學關系,邏輯關系,語言學關系等等”[1]( P.401)。巴赫金非常強調主體在各種關系中的作用。如果說在客體間的關系中主體僅充當了“見證人和裁判官”角色,那么在第二和第三種關系中,主體則直接參與,成為真正的“當事人”。巴赫金的“主體與客體間的關系”相當于經典作家的人與事物的關系;人與客觀世界打交道的過程,即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在這種認識和實踐活動中,人與事物發生了聯系。一切事物的本質都存在于該事物與人的關系之中,其本質必須以人的本質為衡量尺度;而人在本質上是社會性的,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所以,在承認事物自然本質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注重事物的社會本質;在確定事物本質的時候,我們必須尋找事物與人之間普遍性的聯系,把那些非普遍性的聯系排除在外;即使是這一普遍性的聯系,也需要經過歷史的考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任何事物與人的本質關系都會發生變化。
巴赫金的“主體間的關系”包括“個人之間、個性之間的關系:表述之間的對話關系,倫理關系等等。屬于此類的還有一切人格化了的涵義聯系。意識之間、真理之間的關系,互相的影響,師徒關系,愛,恨,欺騙,友誼,尊敬,虔誠,信任,猜疑等等”[1]( P.401)。主體間的關系不同于主體與客體間的關系,不是我與他的關系,而是我與你的關系;要知道,在人與物的關系之中,“人以智力觀察物體,并表達對它的看法。這里只有一個主體――認識(觀照)和說話(表達)者。與他相對的只是不具聲音的物體。任何的認識客體(其中包括人)均可被當作物來感知和認識。但主體本身不可能作為物來感知和研究,因為他作為主體,不能既是主體而又不具聲音;所以,對他的認識只能是對話性的”[1]( P.379)。
巴赫金的三種關系恰好反映了西方哲學和美學發展的三個階段:客體性哲學/美學、主體性哲學/美學、主體間性哲學/美學。他對三種關系的區分旨在突出主體間的關系,對話性是其理論的核心。巴赫金為我們領悟和洞察世界指引了正確方向:對話。
二、哲學基礎與理論淵源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具有深厚的哲學淵源。巴赫金對主體的重視(或者說他的主體建構論)的理論來源是康德。他視康德哲學為哲學之主流。康德關于人的主體性的思想對巴赫金有重大影響:在《藝術與責任》、《論行為哲學》等文中,巴赫金把主體的建構看成一種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主體的建構是在我與他者的對話和交往中實現的。巴赫金的主體建構論強調人的主體性和個人的參與性;進行理論探討的時候,主體(人)是其出發點。當然,雖受康德哲學的影響,巴赫金的主體建構論所回應的問題是現代哲學所面臨的危機。
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的代表人物柯亨對巴赫金的影響尤其巨大,其著作(如《康德的經驗理論》)深受巴赫金的喜愛。柯亨強調倫理學的重要性,視其為哲學之中心。柯亨提出以哲學方式研究美學,主張“系統的美學概念產生于系統的哲學概念”。受德國古典哲學和柯亨的新康德主義的影響,巴赫金剛剛踏上學術之路,就特別重視倫理學,試圖建立一種倫理哲學;他發現,人類文化的三個領域(科學、藝術與生活)在多半情況下未能得到統一,他提出要克服藝術與生活之間由來已久的脫節,藝術與生活要相互承擔責任;而要“保證個人身上諸因素間的內在聯系”,只能“在個人身上獲得統一”,只能是“統一的責任”;還有,“藝術與生活不是一回事,但應在我身上統一起來,統一于我的統一的責任中”[2]( P.1C2)。
巴赫金于20世紀20年代上半葉撰寫的論著表現出他思考問題的顯著特征:美學的倫理化、哲學化思考,哲學、倫理學的美學化傾向。按劉康[3]( P.166)的分析,這一時期即可看作巴赫金哲學思想發展的第一階段:早期哲學美學階段。在這一時期,巴赫金的思想更多地體現了以柯亨為代表的新康德主義的馬堡學派的影響。
三、作者與主人公的對話、“我”與“你”的對話
巴赫金關于主體間性的美學命題可以概括為作者與主人公的對話、“我”與“你”的對話。其對話理論源于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研究和發現,源于他對復調小說理論的闡述。巴赫金認為,陀氏小說不同于以往的獨白小說,他的小說是一種復調小說。
在巴赫金看來,獨白小說類似于主調音樂。在獨白型構思中,主人公是封閉式的,其形象建立于作者的世界觀之中,獨白小說中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只是作者意識的一部分,主人公的聲音缺乏獨立性,只能對作為主旋律的作者聲音起烘托和陪襯作用。而陀氏的復調小說則類似于復調音樂。在這種小說中,作者與主人公分別唱著各自互不融合的聲部,主人公不再是作者聲音的傳聲筒,它們互相獨立。陀氏小說中的主人公是能夠直抒己見的主體,彼此之間形成良好的“和聲”關系。獨白小說中一切使主人公按照作者構思成為特定形象的東西,在復調小說中已不再作為完成主人公形象的形式起作用,而是作為主人公自我意識的材料加以利用。復調小說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了真正的復調,這些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于某個統一的事件之中。
對于陀氏來說,小說內部和外部的各成分之間的一切關系都具對話性,整個小說的結構就是一個“大型對話”結構。所謂大型對話,指的不是表現于布局結構上的、處于作者視野范圍之內的、客體性的人物對話,而是一種對話關系。
陀氏復調小說的獨特之處在于作者對主人公所取的不是高踞對話之上的立場,而是一種新的藝術立場,是認真實現了的對話立場。這樣,主人公便具有其內在自由、內在邏輯、獨立性、未完成性和未論定性。因此,在其復調小說中,主人公相互之間、作者與主人公之間均具有對話關系,這種對話不是文學中假定性的對話,而是嚴肅的、真正的對話,他的主人公不是描繪的客體,不是作者語言講述的對象,而是對話的對象。在藝術上,陀氏小說的大型對話是作為一個非封閉的整體構筑起來的。這種對話是未完成的對話,不同于獨白型小說中的客體性對話或完成了的對話的形象(或者說完成了的對話的記錄)。
大型對話和微型對話是巴赫金研究陀氏復調小說時提出的一對范疇,它們最終歸結于對話性原則;巴赫金發現,陀氏構建對話的原則到處都一樣,大型對話和微型對話之間具有相互依賴的關系。大型對話與微型對話又可相互轉化。一方面,當構成微型對話的、處于一個話語主體內部的兩個聲音進一步發展分裂為兩個話語主體的思想意識。另一方面,巴赫金提出的大型對話僅是一個相對概念;在小說文本內部,相對于微型對話而言,作者與主人公之間、主人公相互之間的形諸布局結構的對話關系是大型對話;而相對于陀氏整個文學創作來說,這種大型對話又成了小對話,或微型對話。與此同時,巴赫金與陀斯妥耶夫斯基以及其他文學創作者也展開了大型對話;在這種對話中,巴赫金尋覓到了隔世的知音――陀斯妥耶夫斯基。
巴赫金獨具慧眼地發現了歐洲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場革命,認為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如同歌德的普羅米修斯,認為他創造出來的不是無聲的奴隸,而是能和自己的創造者并肩而立的自由的人;因此,陀斯妥耶夫斯基顛覆了獨白小說的傳統,突破了獨白型的已經定型的歐洲小說模式,創造了一個文學藝術的復調世界。巴赫金的復調小說理論為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作品的工作起了巨大的拓展和推進作用,他的對話性思想開闊了美學、哲學、語言學等的思維空間,對當代美學和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研究都具有啟示意義。(責任編輯:高笑云)
參考文獻:
[1]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四卷)[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沈華柱.對話的妙悟――巴赫金語言哲學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
[2]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一卷)[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