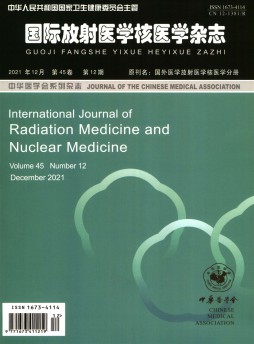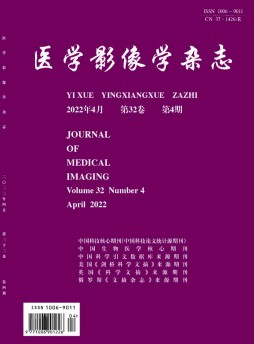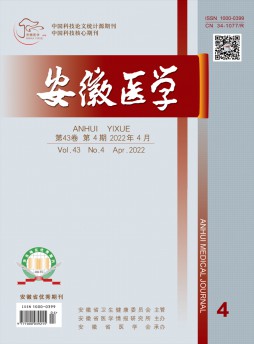醫學的哲學思考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醫學的哲學思考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有人認為中醫學因為未能全方位與現代科學技術緊密結合,發展緩慢,所以至今未能得到長足的發展,主張它應該與現代醫學相結合,還應該結合一切現代科學為我所用。初期看來,中醫尤其是中藥是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但是,我們從實際情況看到,中醫研究越來越標準化、客觀化,很多學科都從細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來研究中醫中藥,結果呢,一味中藥越提越純,臨床應用一看,結果卻不是這么一回事。事實上,中醫現代化已經走入了一個誤區。從SARS的爆發和控制過程可以看出,西藥所治療的病人死亡率明顯高于中藥,而且,中藥現代化研究的一些成果在SARS面前仍然束手無策,而我們控制SARS所使用的正是被認為不符合時展需要的中藥湯劑。
裘沛然教授指出:“中醫現代化,首先要知道幾千年來無數的大醫和先哲們嘔心瀝血的成果是什么,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談得到中醫的現代化。”而我們從事中醫現代化研究的,有幾個真正懂得中醫、了解中醫?所以中醫現代化只能是一種假的現代化,是“偽現代化”。“現在的政策導向是強調用現代科研方法研究中醫,其實就是用西醫替代中醫,美其名曰中醫現代化,實際上就是消滅中醫”(焦樹德教授語)。在這樣一種中醫現代化的指導思想下,談中醫的創新只能是一句空話。必須牢記的是:只有返本才能創新。事物需要發展,但是如果摒棄原來的基礎,只能算是一種新興事物罷了。中醫學只有在自身的準繩內發展,保持自身的特色,中醫現代化才能有真正有價值的成果。
中醫需要創新,它的現代化應該是繼承了五千年傳統的現代化,中醫一系列獨特的理論體系、醫學方法,并不是束縛中醫發展的絆羈,而是體現中醫特色的關鍵和根本,科學需要突破束縛,但是如果要打破中醫這些特征的話,那么現代化的中醫也就面目全非了。而中醫在幾千年來的發展過程中,本身就是在不斷的求創新、求發展的,從來就不是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的,歷代中醫各家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對中醫學的豐富和發展,重大創新歷代層出不窮。
不相信中醫獨立的學術地位,盲目崇拜西醫學方法,對中醫自身傳統的冷漠,導致中醫學術界目前的現狀,即:把盲目改造中醫傳統、簡單模仿西醫當成中醫現代化的方向。中醫的發展本身是在一個非常成熟的、完善的、符合客觀規律的理論框架之內的,這種發展可以是無限的,如果任意想突破這個框架,必然容易導致違背客觀規律。現在的大多數現代化研究只不過是對中醫藥的量化、標準化、客觀化的研究,進行微觀的分析,而這種研究成果實際上只不過是對中醫藥進行一次邏輯語言、數學語言的解釋而已,對中醫的實際內容沒有任何觸動,中醫藥的思維方式仍然沒有變化,只是某些形式和外在的東西有所變動,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變動可能對中醫的發展造成致命的打擊。
中醫對疾病的認識是通過“黑箱理論”來認識的,控制論認為:認識客觀,“黑箱理論”有兩種方法,即打開和不打開黑箱。中醫認為有諸內必形諸外,我們完全可以不通過打開黑箱的辦法研究中醫藥,而且取得相當大的發展(高國宇語)。中醫的很多理論是無法通過現代研究來證實的,如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現代研究無法證實它的存在,然而它在實際應用中卻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中醫理論是一種“哲理式”的思辯,實踐是一種“經驗式”的積累(王磊、常存庫語)。認識中醫必須先從中醫的哲學思維入手,中醫與西醫是截然不同的理論體系,如果一味地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研究中醫的本質、中醫疾病的本質及轉歸的機制,是行不通的。而且,現代研究也不過是一種思維方式,過分追求中醫藥的客觀化、標準化、量化只能把中醫引入死路。尤其是當代的“實驗陽性”理論根本改變了中醫以人為本的理念,試圖用臨床--動物實驗--臨床實驗--臨床的方法進行中醫藥的研究,是對中醫根本理論方式的漠視。歸根結底,中醫現代化應該尊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應先理解中醫、理解中醫的思維方式才能談發展。中醫幾千年來不斷的發展、壯大,以至今天獲得獨立的社會地位,都證明了一個哲學道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第2篇
關鍵詞:攝影;羅蘭•巴特;哲學思考;藝術創作
中圖分類號:J40-02 文獻標識碼: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Photography Art: On "La Chamber Claire" by Roland Barthes
SHAO Xin-yuan
攝影技術誕生至今已經有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這期間有無數的書籍介紹過攝影,其中羅蘭•巴特的《明室》卻給我們打開了另一扇窗。在《明室》中作者沒有關于光影、構圖、拍攝等任何攝影技巧的文字描述,而是以一種在我們看來近乎于“囈語”的獨白彌漫著全書。但在書中我們似乎觸摸到定格在真實影像背后的時間、記憶、地點,體驗了文字與語言符號所表述不了的樂趣。筆者認為,羅蘭•巴特在書中真正想表達的不是攝影本身,也不是形而下的技術,而是形而上的思考,是想表達一種觀念,一種由“攝影”闡發的態度,并想通過攝影讓觀者來討論“觀看”。我們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去觀看攝影、繪畫、文字與雕塑,以至于觀看歷史、當下和未來。也許這就是攝影的魅力所在,它留住一個個“不可能再觸摸到的真實”。在臺灣版《明室》的封底,羅蘭•巴特引用了一個典故,故事講述了藏傳佛教的祖師馬爾巴修得一門大法,叫“往生奪舍”,它可使靈魂脫出自己的身軀,進入另一具尸體,使之復活。他的兒子塔瑪多德跟隨父親修行,成為此法的獨門傳人。一次,塔瑪多德參加賽馬,墜落懸崖,馬爾巴得知噩耗,忙趕去看望兒子。弟子們想請師父行“往生奪舍”法,卻找不到合適的尸體。馬爾巴把兒子抱在懷里,哀痛不已。恰巧就在前幾天,有一對老人失去獨生子,馬爾巴前去以佛理相勸。說,得子喪子,如夢如幻,不要太過悲傷。看到馬爾巴悲痛的樣子,一名弟子對他說:您告訴我們,一切皆是幻象,令郎之死且不也是一種幻象?馬爾巴答道:你說得沒錯,但我兒子的死是一種超幻象。
這段文字與《明室》有什么聯系呢?當讀完全書我明白了,書中的寓意都包含在這個故事里。羅蘭•巴特在《明室》的開篇便舍棄了學術的立場,聲明只“以對我而言真正有存在意義的幾張照片作為研究的根據,完全不關文本總體,只談這些個體。”他甚至倡導開創一門個體的學問,不關乎普遍性的“知面”,只關注打動個人的“刺點”。“知面”(Studium)和“刺點”(Punctum)這兩個詞語貫穿書的始終,這是兩個拉丁語在詞典中也找不到確切的翻譯和中文解釋。所謂“知面”我的理解就是影像的表層,是一幅畫面所展示的眾所周知的描述,是廣義上的攝影,衍生開來就是各個學科、各個領域的普遍知識。而“刺點”則與個體息息相關,它只是關注個體本身的情感,在攝影的范疇里,是畫面里真正能夠擊中人的內心世界的元素。“知面”與“刺點”雖然彼此相互對立,但又并存于同一張照片中。羅蘭•巴特在思考“知面”與“刺點”時,訴諸這樣一種“面的延伸”與“點的穿透”的辯證解釋。其實他借用了伯格森與德勒茲“廣度•強度”的二元論。廣度是外在的、空間的、物質的;強度是內在的、時間的、精神的。在羅蘭•巴特看來“神情也許是某種精神方面的東西,一種把生命的價值神秘地反映到臉上去的東西”。如果用“刺點”理論來看《明室》,書中第一處打動我的是在閱讀完整個上篇晦澀深奧的理論之后,下篇開頭關于他的母親去世的那段文字。當讀完這段文字,我恍然大悟了,前面提及的馬爾巴的喪子在這里暗喻著羅蘭•巴特的喪母。讓羅蘭•巴特困惑的是在一堆母親的影像中,他無法尋找到與記憶里的形象相符的母親。每張照片都只是保留著母親的一個側面,一個局部,一個稍縱即逝的殘留。即使這些都是曾經的母親、曾經存在的母親。但都并不是母親的本質,“因為我錯失了她的生命本質,所以我錯失了全部的她。”羅蘭•巴特懷著對母親深深地思念,去追尋心中母親的影像,他走進了母親過世時住的那套房子。于是,影像穿越了時空,“在燈下一張張地看她的那些照片,跟她一點一點地上溯歷史,想到我曾經愛過的那張真實的臉。結果,我找到了。”死亡的陰霾被照片中的小女孩兒驅散,那是一幅幅完整的影像,它觸動了羅蘭•巴特,他說“我從中看到了不被家庭悲劇(父母離異)以及任何體系束縛的善良。”在照片中,羅蘭•巴特看到母親童年時代的善良與溫存,母親堅守著這些美好的品質,終其一生。在這里他找到了他心中的完整的母親。
書中還寫道:“總算這一回,攝影帶給我好像回想般斷定的感觸,正如普魯斯特曾體驗過的:一天普魯斯特低著頭脫鞋,腦海里突然閃現出他祖母的面龐,‘我第一次于無意中在記憶里重新見到了祖母,她那樣子完整而生動’”。在羅蘭•巴特看來“他拍攝了一張超等照片,其存在之久遠,超過了攝影技術本質所能合理保證的期限。”其他的照片,僅有類比而無真實。“ 不管照片給你看的是什么, 也不管它以什么樣的方式給你看, 照片永遠都是不可見的,我們看到的不是照片。”在這里,羅蘭•巴特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戲,而是道出了攝影作為藝術在精神層面上的“虛無”。這樣的論述總覺得似曾相識,也同樣適用于其他任何藝術門類,可以放進繪畫、雕塑、設計,可以放進古典主義,也可以放進后期印象派的筆端。只是在攝影中表現得比較明顯罷了――以其“可視” 表達它的“不可視”。作品中形象的部分只是作為媒介,或者是被作者用來轉述或實現其意圖的材料,它們除了作為意義或“無意義” 的方式、手段或線索之外, 并不指向“形象”本身。在羅蘭•巴特看來“攝影出自純粹的偶然并且只能如此(和文字相反,文字的東西可以因為一個字于無意之間起的作用,使一個描寫的句子變成一個發人深思的句子),攝影能立即把成為人種學知識素材的‘細節’顯現出來。”不管是照片,還是“一般圖像”,在細節方面,每個人觀看的角度不同,觸動觀者的細節不同,對同一張照片的解讀也就因人而異。當圖像給予觀眾不同的體驗和感受時,對于圖像的生理感應就很自然的上升為精神層面的感應,觀眾會對照片的世俗價值與精神價值進行判定。羅蘭•巴特希望看到的是,從生理感應上升到精神感應所產生的愉悅,而作品本身與現實產生的關聯性以及邏輯關系,則是更值得關注的。
從而羅蘭•巴特認為“攝影的真諦很簡單,很平常,沒有什么深奧的東西:‘這個東西存在過’”,按照現象學的說法,圖像是虛無的物體。“攝影對我來說成了一種奇怪的‘中間事物’,一種新形式的幻覺,在感覺這個層面上是假的,在時間這個層面上是真的,是一種有節制有分寸的幻覺,是‘可分的幻覺’。是一張實在的事物擦過不可思議的圖像。”
看到這里我迷惑了,既然這些都是虛無的,都是時光殘留的幻像,那么,這些影像是怎樣震顫我們的靈魂,甚至震撼一個時代的呢?難道我們都在被假象所欺騙?在全書的末尾,羅蘭•巴特給了我回答:“我明白了,在攝影、瘋狂和某種我不知其名的東西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扭結般的),我開始把這種東西稱的痛苦。”在人類所有領域到達一定的高度時,人們關注的問題則是心靈的回歸,回歸到最原始最本質的愛。且不說哲學的定義就是“愛,智慧”,就連當今前衛的物理學都試圖求證物質與人類情感之間神秘的聯系,攝影亦是如此。一個著名的攝影師曾經說過:“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喜歡,但我喜歡拍攝痛苦的主題,快樂永遠只是短暫的,只有痛苦才能穿越永恒。”因為愛所以痛苦,因為痛苦所以愛得更深。如果從這個層面理解,攝影的意義已經不在于影像本身,影像只是一個觸點,用于激活已成過去的潛藏于靈魂深處的愛以及追憶那段往事的痛苦,這樣的痛苦足以讓人沉溺。影像激起了我們對過去美好事物的懷念,那些稍縱即逝的美好時光因為影像重新浮現在眼前。但過去的終究已經成為過去,我們會很自然的面對正在發生的當下。更痛苦的事情隨之到來,對于當下,對于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在,每個人同樣是無能為力。一切體會到的,沒有體會到的美好生活都會成為過去,我們能做的只有再次記錄下眼前的瞬間,讓它定格在記憶中。在書中羅蘭•巴特還提出了另一個命題:憐憫。“我把所有那些曾經‘刺痛’過我的照片又重新集中回想了一遍……通過其中的每張照片,我都必然走得更遠,比被再現事物的不真實走得還要遠,我會發瘋似地進入照片的場景,進到圖像里面去,用雙臂去圍攏已經死去的和將要死去的東西,像尼采那樣――1889年1月3日,尼采哭著撲向一匹被殺死的馬,抱住馬脖子:由于憐憫,他瘋了。”就像巴爾馬對喪子的追憶一樣,羅蘭•巴特對已故母親的追憶也只是現實中愛與憐憫的形式,真正的愛深藏于心靈的深處。當然更多人心中的愛會因為現實的冷酷變得無情而僵硬。然而攝影師是敏感的,他們貪婪的享受著正在經歷的愛與歡樂。同樣是因為敏感,他們必須承受當愛逝去時的悲傷。痛苦的力量遠比愛帶來的精神愉悅更為強大,更為持久。影像的記錄是暫時的,也是無助的,但是攝影師必須拍攝。只有拍攝出力量足以強大的影像,才能蓋過時間流逝的悲傷。時間的逝去與影像的定格永遠是不能兩全的悖論,即使已經定格下的影像也有保存的期限。然而愛可以永恒,與愛伴隨的痛苦可以穿越一切。攝影師就是在這樣一個悖論中追問并無限逼近真理。同樣,這樣的追問也刺痛著所有看過這些影像的人。
《明室》出版不久,羅蘭•巴特就因車禍身亡,巴特的理論也到了“最后一個階段”。《明室》中充斥著極其主觀的姿態,“自我之古老的絕對權力”(尼采語)隨處可見。羅蘭•巴特把自己的經驗視為首位,并以此去定義攝影的本質,在哲學的高度關注攝影、闡釋攝影、洞察攝影,給我們留下了對攝影的哲學思考。
參考文獻:
第3篇
由于現代醫學根植于現代科技和思想文化,使人們從思想上更容易接受,而中醫學根植于中國古代文化,其思維并不具備完整的邏輯性,甚而很多理論是離散的,這能從《黃帝內經》的篇目題名和《傷寒雜病論》的條文看出來。中醫學的“望聞問切”及語言的模糊性使人難以直觀的理解,中醫學是整體地看待人與疾病及周圍環境包括四季氣候和人的思想情緒等。中醫學是一門實踐醫學,它與同時代的《老子》和《周易》有明顯的源流關系。《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認為“道是產生作為宇宙萬物統一體的原始混沌之氣,而在此統一體的基礎上產生出陰陽二氣,陰陽相互作用而產生出千差萬別的萬物。《周易‘系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認為陰陽對立而相互轉化,容忍人們對道的陰陽屬性有不同的認識和見解。”仁者見之謂之仁,知(智)者見之謂之知(智〉。“《內經丨陰陽應象大論》”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指出了疾病的本質是陰陽失調。能明其中奧妙者,往往一語中的,而不得要領陳述再多如墜五里云霧不知所云。
中醫學依照“道”的觀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對疾病的認識亦是如此,“道”是自然規律是天地萬物(宇宙包括人的生理病理)的本源,是可以由人的思維去認識,用人的語言表達描述,但用人的語言思維表達的“道”是不完整和有偏差的,當你描述的越多,越背離“道”的宗旨。當你試圖對某個具體事物下精確的定義做精辟的闡述,那么你就越背離了事物的本質,失卻了事物的本來面目。《周易·系辭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這器。“一陰一陽的道作為客觀規律,它是無形的東西。《老子》“道恒無名”,大凡有形的東西它就不是道,只能是具體的器物,大凡物就有二重性,一是可以看得到(包括儀器觀測)的物質實體,二是它有內在的運動規律,二者互相依存構成對立統一的體用表里。中醫學的整體觀也是試圖從總體上把握實在,力求最簡。《易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力求從宏觀上把握本質上的東西,而對具體的器物背后細微末節的是不予深究。中醫醫生對經典的誦讀記憶與理解,有類佛教的參禪,靠對經典的熟記于心、臨證自會有所領悟(直覺和悟性很重要)。本人曾治過一例難治性冠心病,男性40多歲,經某二甲醫院二次住院無效,后經某三甲醫院專家確診為特殊類型的心臟病無特效療法,囑休息靜養,遷延半年多,表現為惡寒特甚。雖盛夏酷暑,在室外陽光下尚可,一人室內即刻全身雞皮疙瘩,欲厚衣被,舌淡,脈緊。予以麻黃湯3劑,汗出病愈,后予調理脾胃補助正氣之劑3劑完全康復,病雖遷延但始終是太陽表證,如拘泥于冠心病活血化瘀那就誤人歧途了,隨訪十多年此人至今健康。五行學術并非機械唯物主義,這點本人在臨床有深刻體會。《傷寒雜病論》的外感三陰三陽六經傳變與雜病五行推衍是亙古真理。本人曾經治過一例較重的乙型肝炎患者,中年發妻暴斃,又經商蝕本,某三乙醫院要求立即住院,因經濟困頓轉求中醫。遵《金匱》治肝實脾之法,并明示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再用之,肝病很多是本虛標實。予茵陳術附湯加味。十劑藥后腹脹黃膽頓消,矢氣頻作,飲食倍增,精神有加,服至三十劑,各項化驗肝功正常,僅表面抗原陽性,后再服藥漸感藥后腰痛,頓悟脾過實能傷腎,誠至理明言,至今三年多,不時調3,基本健康,可從事體力勞動。中醫臨證用藥確如用兵打仗,藥不在多而在精,遇一青年婦女經常感冒,習慣輸液治療,效果并不好,自述沒精神,見此人體溫并不高,似欲昧狀,脈微細,此傷寒少陰證,與麻黃附子細辛湯二劑而愈。外感傷寒三陽病多見,而三陰病相對少見,為什么此人常感冒每次都大致如此,這使我悟到《內經·陰陽二十五人篇》五行之人各有不同,因體質差異而外感生病不同。臨證不可不細心玩味。還有一例是某男,50多歲,農民,勞累過度經常感冒,有時消化不好就自己服用酚酞片,后患一病深以為苦,在工作中時常有欲腹瀉大便感覺,且便意急迫,如廁慢時欲便褲內,而真正如廁下蹲則便意消失并不大便,一曰內頻繁發作,經兩家二甲醫院診治未能明確病因,經口服慶大霉素及諾氟沙星多次無效,歷時二年多不見好轉,此人不信中醫,后在萬般無奈之下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吃中藥,思忖似痢非痢,因于外感正氣不足,侵人大腸陽明之里脅迫津液瀉下,葛根黃芩黃連湯證也,后服藥三劑病若失。《傷寒雜病論》由于年代久遠有些古語需要反復玩味深刻理解,又如經文中“小便不利”與“淋病”絕不相同,尤其有些農村婦女語言表達描述不清,醫生再不細究就會辨證失誤。本人還曾治過兩例60多歲農村老年婦女,都是“小便不利”說成是淋證(老百姓俚語有的叫淋澀一例小便頻數,總覺尿不盡,以致夜不能安,但無尿痛,服用了多種抗菌素及石葦膠囊等無效,以為患了大病,就診于某三甲醫院,經輸頭孢菌素半個月無效,細尋病因乃半年前患感冒經一庸醫誤用下法,致體虛三個月后患此病癥,面色咣白,此中氣不中足中氣下陷,膀胱收縮無力下墜壓迫尿道也,予以補中益氣湯,重用黃芪二劑,不期第二天病人喜來,大笑不止,自以為是小學教師略通文理,不意大補之劑竟愈此疾。又一例尿道熱灼不適難受但不痛,小便不盡欲尿,經輸抗菌素及服用三金片20多盒無效,時值盛夏時年雨多,田間下蹲鋤草受濕氣交蒸,舌苔黃厚膩,予以五苓湯五劑而愈。這些實實在在的治法療效,皆為本人苦讀經典的臨床感悟。還有我上學時老師講過一病例,一個角膜潰瘍的病人經多方醫治效果不好,后找了一個老中醫看了后辨證下藥補中益氣湯,數劑痊愈,跟隨的學生問這是什么道理,老先生說我不懂什么深奧的道理,我只知道中醫治則”陷者升之“一語中的。中醫有些療效很難用現代醫學的生理生化得到驗證的。可惜這些藥方都不賺錢,不能產生經濟效益,而這些病都經過西醫治療,那些療法都大賺其錢,這恐怕也是中醫是日漸衰落的原因之一。
《醫學衷中參西錄》治癃閉方之對宣陽湯與濟陰湯交替應用的更是中醫陰陽互生的精髓與典范,值得一讀,能啟迪中醫的思維,耐何人多不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