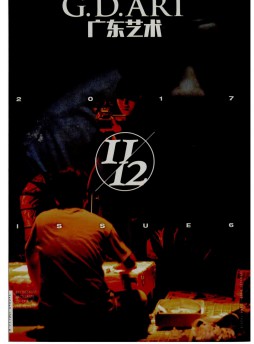藝術(shù)歌曲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藝術(shù)歌曲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lái)啟發(fā),助您在寫(xiě)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由《春天》《九月》《入睡之時(shí)》《在夕陽(yáng)中》4首歌組成,女高音聲部演唱,交響樂(lè)隊(duì)伴奏。《春天》完成于1948年7月,《九月》完成于1948年5月,《入睡之時(shí)》完成于1948年9月,《在夕陽(yáng)中》完成于1948年8月,4首歌曲的順序雖然與作者實(shí)際完成的時(shí)間相同,但整個(gè)主題的構(gòu)思是在同一時(shí)段內(nèi)進(jìn)行,作品中的歌曲順序是后來(lái)學(xué)者們的安排。《最后四首歌》創(chuàng)作于1946—1948年間,作曲家歷經(jīng)了漫長(zhǎng)而又騷動(dòng)的職業(yè)生涯,正值人生苦悶與晚年之秋。詩(shī)人艾辛多夫的同名詩(shī)歌《在夕陽(yáng)中》所描寫(xiě)的一對(duì)老人家面對(duì)近在眼前的死亡所表現(xiàn)的沉思與作曲家的個(gè)人處境形成強(qiáng)烈的共鳴,引發(fā)了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靈感。這是一部極具價(jià)值的音樂(lè)文獻(xiàn),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和寫(xiě)作手法在以往德、奧藝術(shù)歌曲的基礎(chǔ)上有了新的發(fā)展,可以說(shuō)這部作品完美地表達(dá)了作者對(duì)事物終結(jié)、生命即將消亡的哲理性思考。《最后四首歌》于1950年5月22日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lè)廳進(jìn)行了首次演出,擔(dān)任這首歌曲獨(dú)唱的是弗拉格施塔特•魏爾海姆,富特文格勒指揮愛(ài)樂(lè)樂(lè)團(tuán)伴奏。《最后四首歌》每首歌曲中至少都有一個(gè)“主導(dǎo)動(dòng)機(jī)”穿插在聲樂(lè)和樂(lè)隊(duì)的聲部中,其中由一個(gè)忐忑不安情緒的主導(dǎo)動(dòng)機(jī),把前三首歌曲聯(lián)系在一起,第四首歌是套曲的和總結(jié),通過(guò)前三個(gè)階段后,逐步地描繪出一個(gè)美滿而又靜止與安息的意境;同時(shí),套曲在4首樂(lè)曲的結(jié)束處,都運(yùn)用了施特勞斯最寵愛(ài)的法國(guó)號(hào)的獨(dú)奏旋律作為結(jié)束,使整部套曲在創(chuàng)作上既有統(tǒng)一又有對(duì)比。《最后四首歌》的調(diào)式、音色自然和諧,極富意象描繪功能;音樂(lè)織體和諧統(tǒng)一、清澈透明,表現(xiàn)了四季的更始復(fù)新、愛(ài)情、沉睡與死亡;管弦樂(lè)配器安排周密細(xì)致,特別是弦樂(lè)為女高音聲部提供了明晰的背景又與之有機(jī)融合在一起;為每首歌曲伴奏的管弦樂(lè)以縹緲不定、起伏錯(cuò)落的經(jīng)過(guò)句為背景,伴隨著節(jié)奏的徐緩急馳與對(duì)比,同整部作品一道,在夕陽(yáng)的余暉中、在懷舊的冥思中、在莊嚴(yán)的訣別中逐步消退。《最后四首歌》曲式結(jié)構(gòu)非常自由,兩段歌詞也會(huì)時(shí)常連接在一起,樂(lè)隊(duì)間奏時(shí)常在段落的中間部分穿插。歌曲樂(lè)句的長(zhǎng)度也有長(zhǎng)有短,長(zhǎng)短分布的情況也極不規(guī)則和極不均衡。從宏觀上來(lái)看,《最后四首歌》的序奏部分是第一首《春天》,第二首與第三首歌《九月》《入睡之時(shí)》是兩個(gè)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比較抒情性的段落,第四首《在夕陽(yáng)中》則是終曲。因此,演唱者在演唱時(shí)尤其要注意作品情感的整體性與一致性。
1.《春天》:選自海曼•赫瑟詩(shī)歌,Andante(行板),套曲的前奏曲。歌詞大意如下:在那陰暗潮濕的地方,我會(huì)經(jīng)常這樣夢(mèng)想著,你就是那些叢林與晴空的微風(fēng),你就是那些花朵的芬芳與嬌艷,是那雀鳥(niǎo)般的歌聲。在燦爛的盛裝中,你彰顯出了自己。在明亮的光輝的照耀下,你竟然奇跡般地來(lái)到我面前。我已經(jīng)認(rèn)出了那就是你,并在不斷地溫柔地向我招手。這時(shí)我的四肢都不由自主地激動(dòng)地顫抖。那是因?yàn)槲抑佬腋>鸵獊?lái)臨。這首《春天》一直貫穿著一種憂郁與不安的情緒和沉思與暗淡的音響,所喚起的是對(duì)春天的懷念。但是,聽(tīng)起來(lái)卻沒(méi)有春天的氣息,可以理解為作曲家暮年對(duì)春即將離去的感受。全曲開(kāi)頭部分的調(diào)中心不穩(wěn)定,沒(méi)有調(diào)號(hào)標(biāo)記。統(tǒng)一的和聲基礎(chǔ)為c小調(diào)的主和弦與降a小調(diào)的主和弦組成的琶音音型,通過(guò)這一推動(dòng)力的音型,給全曲奠定了比較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歌者演唱時(shí)可以自由地、瀟灑地縱情歌唱。歌曲第一、四行詩(shī)的最后一個(gè)字總共長(zhǎng)5小節(jié),作曲家在處理旋律與歌詞之間的關(guān)系上突破了傳統(tǒng)的處理方式,引導(dǎo)我們從整體的音響與聲部線條中去思考。歌曲中采用的主導(dǎo)動(dòng)機(jī)多次變型,調(diào)性復(fù)雜、變化音較多。這是一首調(diào)性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比較復(fù)雜,需要變化的音節(jié)比較多的現(xiàn)代藝術(shù)歌曲,所以歌唱者在演唱這首歌之前,一定要相當(dāng)熟悉這首歌的旋律,充分感受旋律的方向,使其成為一個(gè)完整的整體。再一個(gè)就是要嚴(yán)格按照節(jié)拍朗誦歌詞,發(fā)音一定要正確,這些都是歌唱前必須要做到的、不可缺少的預(yù)習(xí)工作。這首歌在演唱時(shí)可以較為自由地發(fā)揮想象,演唱者要從傳統(tǒng)的對(duì)稱(chēng)、呼應(yīng)等關(guān)系中解脫出來(lái)。歌曲的最后,歌聲在悠揚(yáng)的威尼斯船歌的伴奏下要與寬廣的音程一道,和著圓號(hào)的響應(yīng)完美地結(jié)束全曲。
2.《九月》:選自海曼•赫瑟詩(shī)歌,套曲的抒情樂(lè)章。歌詞大意如下:雨水是無(wú)情的,它冰冷地灑落在嬌艷的花朵上,就連花園都在悲傷。夏天的明媚陽(yáng)光也在不由自主地戰(zhàn)栗,非常安靜地走到了盡頭。金黃色的葉子無(wú)力地低著它的頭,就這樣從高大的洋槐樹(shù)上無(wú)奈地落下。夏日帶著驚奇的笑容,在那將近毀滅的夢(mèng)境中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耗盡自己。但它仍然逗留在玫瑰花叢中,慢慢地逝去。雙眼也慢慢地閉上了,因?yàn)樗α恕!毒旁隆穼⒃?shī)中金色樹(shù)葉的下落與滴雨渲染得栩栩如生,而晚夏后虛弱的微笑、“閉上了雙眼”的描寫(xiě)等都是對(duì)生命逐漸消失的一種象征,也是留給人們一種“一切即將終結(jié)”的印象。演唱者在演唱時(shí)一定要注意對(duì)歌中情緒的表達(dá),注意在較為穩(wěn)定的調(diào)性中平靜地歌唱,力求突出女聲部的歌唱性與抒情性特點(diǎn)。《九月》1—4小節(jié)樂(lè)隊(duì)部分中的裝飾音,高聲部中由三個(gè)音組成的和弦組,都是歌曲中最重要的主導(dǎo)動(dòng)機(jī)或音型組,以此貫穿全曲而引申到《入睡之時(shí)》中,這樣的效果是不僅旋律優(yōu)美動(dòng)聽(tīng)而且具有戲劇性。樂(lè)曲最末的圓號(hào)獨(dú)奏部分是全曲最的部分,曲中主導(dǎo)動(dòng)機(jī)最后由一支安慰性的獨(dú)奏圓號(hào)封住這朦朧的氣氛,求得與整部套曲的和諧與統(tǒng)一。
3.《入睡之時(shí)》:選自海曼•赫瑟詩(shī)歌,套曲的抒情樂(lè)章。《入睡之時(shí)》這首歌詞的形象鮮明、詩(shī)意濃厚。作曲家借描寫(xiě)孩童的天真暗示歷經(jīng)坎坷的自己,渴望、期待著卸掉所有的重?fù)?dān)去尋得安歇。歌聲在一聲疲憊的嘆息中進(jìn)入,刻畫(huà)的是一種精神恍惚的狀態(tài);隨后小提琴獨(dú)奏將人們帶到臨睡時(shí)刻,用動(dòng)人心弦的旋律來(lái)替代靈魂在太空中自由飛翔的情景,這是全曲情感最濃郁的部位,也是全曲的。歌者演唱時(shí)要唱出心靈隨著令人神往的歌聲而放飛的情景,唱出讓人感到片刻的安息、無(wú)比的滿足又不得不回到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矛盾心理。這里的心理表達(dá),要運(yùn)用稍有變化的音色,唱出矛盾的戲劇性,同時(shí)也要借助第二段與第三段歌之間的小提琴獨(dú)奏段落的抒情力量,唱出獨(dú)奏之后最為激動(dòng)人心的樂(lè)段。要注意旋律部位從降a與降g推至最高點(diǎn)降b的過(guò)程,這樣的旋律我們稱(chēng)為模進(jìn),它與下面聲部的和聲充分地結(jié)合在一起,構(gòu)成了全曲極為輝煌的。所以,演唱、演奏時(shí)更要注意用歌聲與樂(lè)聲互為表達(dá),藝術(shù)地再現(xiàn)歌曲的抒情性與交響性情景。
第2篇
聲音是歌曲感情表達(dá)的重要工具,不同風(fēng)格的歌曲需要依靠不同的音色來(lái)表現(xiàn)。舒伯特《致夜鶯》講述的是面對(duì)在懷抱里熟睡的愛(ài)人,看到窗外美好的花朵、草地,心中充滿無(wú)限歡喜,并將感情寄托在夜鶯,希望自己像夜鶯一樣輕聲歌唱,為愛(ài)人營(yíng)造安靜、甜蜜的睡眠。那么在這種感情渲染中,我們的歌唱注定不能像演唱歌劇那樣使用很輝煌、音量較大的音色,而是應(yīng)該跟隨歌曲的意境與旋律的發(fā)展隨時(shí)調(diào)整合適的音色。舒伯特《致夜鶯》前奏是在“p”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第一個(gè)樂(lè)句又是三拍子的弱起,音符屬于和弦音,那么在保持音準(zhǔn)的同時(shí),為了使人聲的加入不至于突兀,在演唱時(shí)力度也應(yīng)該使用“p”,第三個(gè)樂(lè)節(jié)歌詞是第二個(gè)樂(lè)節(jié)的重復(fù),那么在演唱時(shí)兩個(gè)樂(lè)節(jié)之間應(yīng)該在力度、感情上表現(xiàn)出對(duì)比。第二個(gè)樂(lè)句伴奏音型出現(xiàn)變化,節(jié)奏比第一樂(lè)句較為歡快,因此在演唱時(shí)音色要略微輕巧,頭聲加入多一些的共鳴,在音符上強(qiáng)調(diào)整體的顆粒型,以表現(xiàn)自己看到花朵、小草、愛(ài)人時(shí)的愉悅心情。第三個(gè)樂(lè)句是感情的抒發(fā),通過(guò)對(duì)夜鶯的寄語(yǔ)表達(dá)對(duì)愛(ài)人的憐愛(ài)之心,在這個(gè)樂(lè)句的前兩個(gè)樂(lè)節(jié)中嘗試氣聲的運(yùn)用會(huì)對(duì)歌曲感情起到良好的烘托作用。結(jié)合歌詞的描述,筆者認(rèn)為整首歌曲在演唱過(guò)程中音色不能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胸腔共鳴,聲音以輕巧、甜美為好。音量不宜過(guò)大。
二、氣息運(yùn)用
“誰(shuí)懂得了呼吸,誰(shuí)就懂得了歌唱”。可見(jiàn)氣息在歌唱中發(fā)揮的作用之大。舒伯特《致夜鶯》這首藝術(shù)歌曲整體速度規(guī)定為中板。那么在演唱時(shí)就不宜使用較快的速度,因此在演唱過(guò)程中一定要注意的氣息的延伸,“以氣帶聲”,給聽(tīng)者一種聲斷氣不斷的感覺(jué)。如第一個(gè)樂(lè)句中開(kāi)始的弱起,通過(guò)氣息的運(yùn)用帶動(dòng)聲帶的振動(dòng),這樣比直接發(fā)聲出來(lái)的效果要更柔和。第三個(gè)樂(lè)節(jié)最后一個(gè)小節(jié)是一拍的休止,那么最后一個(gè)音一定要延伸出去,這樣才能使旋律有繼續(xù)進(jìn)行的感覺(jué)。最后一個(gè)樂(lè)句更加強(qiáng)調(diào)氣息運(yùn)用的技巧,樂(lè)句中位于g2上的音延續(xù)四拍半,那么在這個(gè)樂(lè)句開(kāi)始演唱前,氣息準(zhǔn)備一定要充分,分配要合理,通過(guò)聲帶的規(guī)則振動(dòng)使氣息得到充分的運(yùn)用。除了氣息的延伸之外,偷氣也是本首歌曲演唱中不可獲取的技巧。這首歌曲雖然是中板,但是在樂(lè)節(jié)與樂(lè)節(jié)的銜接中并沒(méi)有設(shè)置休止供演唱者換氣,如第二個(gè)樂(lè)句第25個(gè)小節(jié)中,兩個(gè)音符鏈接非常緊湊,之后的樂(lè)節(jié)大約持續(xù)5個(gè)小節(jié),因此,偷氣的運(yùn)用就必不可少。在偷氣技巧運(yùn)用過(guò)程中,切忌明顯的偷氣動(dòng)作,這樣會(huì)破壞掉整個(gè)旋律的進(jìn)行,又強(qiáng)調(diào)偷氣的充分準(zhǔn)備,以免樂(lè)節(jié)過(guò)長(zhǎng)氣息運(yùn)用不足。
三、小結(jié)
第3篇
論文摘要:舒伯特藝術(shù)歌曲洋溢著溫馨、甜美,同時(shí)又感傷、優(yōu)郁,他的音樂(lè)賞心悅耳,旋律優(yōu)美,精雕細(xì)琢,充滿了純粹的美感。他第一次把歌曲創(chuàng)作提升到可與交響樂(lè)相提并論的歷史地位,奠定了浪漫主義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基礎(chǔ)。
十九世紀(jì)初,歐洲文學(xué)藝術(shù)普遍形成了一種新的潮流、新的風(fēng)格,音樂(lè)的發(fā)展也出現(xiàn)了不同的特點(diǎn)并產(chǎn)生了許多民族作曲家、音樂(lè)活動(dòng)家,像羅西尼、柏遼茲、舒伯特等等。他們一方面汲取浪漫主義思潮中有益的部分,另一方面,在民間藝術(shù)中尋取創(chuàng)作素材,在作品中重視和反映民族的特點(diǎn),用幻想的題材和形象來(lái)體現(xiàn)自己的愿望,并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做了許多革新,在主題的音調(diào)上加強(qiáng)了抒情的因素,在器樂(lè)作品主題中貫穿了歌曲的音調(diào),在聲樂(lè)作品器樂(lè)伴奏里也增加了詩(shī)意的形象刻畫(huà),在音調(diào)中突出了民族民間因素的聯(lián)系,加強(qiáng)和聲和調(diào)性關(guān)系的色彩變化。如三度的調(diào)性關(guān)系、同主音大小調(diào)的轉(zhuǎn)換等,特別是在創(chuàng)作手法和形式上做了大膽的革新,豐富和發(fā)展了古典的傳統(tǒng)。奧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則是這個(gè)時(shí)期浪漫主義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短暫的一生中,創(chuàng)作了六百三十四首藝術(shù)歌曲,八首交響曲,大量的弦樂(lè)四重奏,鋼琴奏鳴曲和為數(shù)不多的室內(nèi)樂(lè),此外還有多首彌撒曲和價(jià)值影響均不大的歌劇。
一、主要作品
舒伯特對(duì)藝術(shù)歌曲的創(chuàng)作靈感像泉水一樣,不停地噴涌。這和貝多芬有很大的不同,貝多芬的創(chuàng)作構(gòu)思十分辛苦,不斷琢磨和修飾且經(jīng)常改動(dòng),甚至放棄原來(lái)的計(jì)劃。舒伯特卻從不做長(zhǎng)時(shí)間的推敲,經(jīng)常是一揮而就,一氣呵成。傳說(shuō)他的那首著名的《聽(tīng)聽(tīng)!那云雀》就是在咖啡館內(nèi)的菜單上畫(huà)上五線譜寫(xiě)出來(lái)的,他的譜曲十分神速,據(jù)創(chuàng)作年度統(tǒng)計(jì),在1815年8月這一個(gè)月內(nèi),他一口氣寫(xiě)出了二十九首藝術(shù)歌曲,兩首交響曲,一首四重奏,四首奏鳴曲,兩首彌撒曲和五部歌劇。有朋友問(wèn)他是怎樣作曲的,他只是說(shuō):“我寫(xiě)完一首樂(lè)曲,就開(kāi)始寫(xiě)下一首。”然而,這決不是粗制濫造,每一首樂(lè)曲都是他心血的結(jié)晶,都產(chǎn)生自他的感時(shí)傷世的浪漫主義偉懷。他說(shuō)過(guò):“我的音樂(lè)是我的才能和悲慘境地的產(chǎn)物,世人最喜愛(ài)的,正是我以最大的痛苦寫(xiě)成的音樂(lè)。”
以下是在我國(guó)流行廣泛、燴炙人口的作品:
聲樂(lè)套曲《美麗的磨坊女》(1823年),這部聲樂(lè)套曲和另一部聲樂(lè)套曲(冬之旅》都是根據(jù)大詩(shī)人威廉?繆勒的名詩(shī)譜成。兩部套曲的創(chuàng)作相距四年,但其風(fēng)格氣質(zhì)和內(nèi)心感受卻有一脈相承的相似之處,像是姊妹篇,也具有很大的自傳性成份。
《美麗的磨坊女》是一部愛(ài)情悲歌,它的內(nèi)容大意是一位青年磨工偷偷愛(ài)上了磨坊主美麗的女兒,他每天向女孩傾訴他心里的秘密,把姑娘的名字刻在樹(shù)枝上,把鮮花種植在姑娘的窗前。然而姑娘讓一位英俊的獵手帶走了,痛苦的小磨工只能與奔流著的小河作伴,最后在碧澈的河水中埋葬了他痛苦的靈魂。
聲樂(lè)套曲《冬之旅》(1827年)是舒伯特去世前一年里的最后一部聲樂(lè)套曲。它的悲劇色彩比前一首強(qiáng)烈很多,在音樂(lè)手法上也有更多的變化和發(fā)展,描寫(xiě)一個(gè)在生活中備受折磨,經(jīng)歷了種種痛苦的流浪者,在漫漫的冬夜踏上凄涼的旅途,四周是一片黑暗與冷酷,他追憶著過(guò)去的幸福,明媚的春天,企圖作奮力的掙扎,然而現(xiàn)實(shí)無(wú)情,他萬(wàn)念俱灰,失去了一切希望。只有不斷地祈求死亡,以得到最后的解脫。整個(gè)套曲的基調(diào)是消沉的,舒伯特自己也稱(chēng)這些歌曲是“可怕的歌”。這部套曲共由二十四首小曲組成,它們的標(biāo)題是:晚安、風(fēng)標(biāo)、凍淚、凍僵,菩提樹(shù)、淚泉、在河上、回顧、鬼火、睡息、、孤獨(dú)、郵車(chē)、白發(fā)、烏鴉、最后的希望、在村中、風(fēng)雨的早晨、迷惘、路標(biāo)、旅店、勇氣、虛幻的太陽(yáng)、街頭藝人。從這些標(biāo)題中可以看出,這位冬日的流浪者的心境是多么的寂寞,生活是多么的坎坷。它的第五首菩提樹(shù)是我們最熟悉的一首,也是最具有代表性一首,他情景交融,委婉動(dòng)人,通過(guò)流浪者對(duì)家鄉(xiāng)屋前菩提樹(shù)的回憶,顯示了他對(duì)昔日的美好生活的眷戀和旅途寂寞憂傷心情的對(duì)照。音樂(lè)含蓄樸實(shí),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勻稱(chēng),常用同名大小調(diào)轉(zhuǎn)調(diào)的手法來(lái)對(duì)比不同的心情。
二、創(chuàng)作特征及藝術(shù)表現(xiàn)
號(hào)稱(chēng)“歌曲之王”的奧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在同時(shí)代的作曲家中其作品更為敏感和細(xì)膩。他的一生雖然沒(méi)有貝多芬的地位顯赫,但翻開(kāi)舒伯特創(chuàng)作的作品,就能摸索到他頭腦中大量美麗歌曲的源泉。舒伯特的藝術(shù)歌曲以優(yōu)美的旋律,樸素的織體,溫暖而富于色彩的和聲打動(dòng)人心,作品突出音樂(lè)性、家庭性、通俗性,音樂(lè)形象鮮明。尤為突出的是他作品中超越時(shí)代的和聲、開(kāi)放式的調(diào)式變異、一體化多層次的樂(lè)隊(duì)結(jié)構(gòu)和他無(wú)比非凡的奇思異想。在舒伯特的藝術(shù)歌曲中,不僅具有橫向、細(xì)膩、歌唱性的旋律,還伴有意想不到的,突如其來(lái)的和聲變化,而每一個(gè)和聲又暗示著聲部的不斷進(jìn)行,在看似平凡的外表下隱藏著一顆敏感、豐富、脆弱的心靈。
舒伯特善于在藝術(shù)歌曲的創(chuàng)作中經(jīng)常采用一種結(jié)構(gòu)形式—分節(jié)歌,即:詩(shī)歌的每一段或每一節(jié)都重復(fù)使用相同的旋律。如旋律輕松、歡暢的《野玫瑰》和在清澈小溪中暢游的《縛魚(yú)》及具有沉思般樂(lè)句所闡感又仿佛讓人進(jìn)人凝重的《小夜曲》等等。他善于沖破古典和聲的嚴(yán)格束縛,達(dá)到完全自由的和聲走向,沖出調(diào)式遠(yuǎn)近關(guān)系的限制,運(yùn)用多聲部、多線條的立體和聲與復(fù)調(diào)、技法來(lái)表現(xiàn)旋律色彩的不斷變化。從調(diào)式、聲音、和弦到節(jié)奏的不斷改變,達(dá)到音響色彩和諧而有規(guī)則的效果。這一切正是舒伯特音樂(lè)的強(qiáng)大藝術(shù)力量所在,這種強(qiáng)大的藝術(shù)力量能夠體現(xiàn)出作曲家內(nèi)心的祈求與掙扎。長(zhǎng)期緊迫的生活壓力和內(nèi)心孤獨(dú)感交織在一起,處處充滿了希望與絕望、黑暗與光明、生命與死亡的抗?fàn)帲瑥亩@得一種活下去的堅(jiān)強(qiáng)信念。舒伯特深信:一支動(dòng)人的曲調(diào)本身就蘊(yùn)藏著無(wú)窮的樂(lè)趣和魅力,它的經(jīng)常出現(xiàn)無(wú)疑會(huì)令聽(tīng)者感到無(wú)比親切和滿足。“舒伯特的音樂(lè)用平易近人的語(yǔ)言訴說(shuō)的不是后來(lái)浪漫主義者那種孤僻的主觀世界,而是大家所熟悉的普遍存在的事物”。在敘述事物時(shí),音調(diào)的直率和表現(xiàn)事物時(shí)音調(diào)的內(nèi)在氣質(zhì)正包含著今天音樂(lè)所有的品質(zhì)—和諧、美妙、高尚。
在舒伯特的藝術(shù)歌曲中,他不僅善于創(chuàng)作優(yōu)美的充滿內(nèi)在激情的旋律,而且還有意識(shí)地把和聲及器樂(lè)伴奏等其它音樂(lè)因素提高到詩(shī)和旋律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詩(shī)的旋律的主體周?chē)鷦?chuàng)造出一個(gè)均衡完整的音樂(lè)機(jī)體,使歌聲與器樂(lè)伴奏水融。他的藝術(shù)歌曲的伴奏,既不是象往昔的歌曲那樣只是簡(jiǎn)單的和聲上的輔助,也不是象現(xiàn)代某些作曲家那樣,只是從管弦樂(lè)的角度設(shè)想,把聲樂(lè)部分納人一個(gè)類(lèi)似交響樂(lè)那樣的結(jié)構(gòu)中。他在伴奏樂(lè)器上所作的感情烘托,色彩和氣氛刻劃,包括對(duì)大自然、對(duì)心理上的刻劃都是無(wú)以倫比的。“他的著名藝術(shù)歌曲《縛魚(yú)》伴奏中的魚(yú)躍與和聲;他的《小夜曲》伴奏中對(duì)六弦琴分解如弦的音響模擬;他為歌德敘事詩(shī)《魔王》中的音樂(lè)氣氛的心理描寫(xiě),都是十分卓越的”。比如:在歌曲《魔王》一開(kāi)始,鋼琴伴奏就以持續(xù)不斷的三連音和低音區(qū)簡(jiǎn)短的音階走向,既模仿了急促的馬蹄聲和呼嘯的風(fēng)聲,又渲染著毛骨驚然的陰森的氣氛,音樂(lè)形象極為鮮明。它至今仍然是歌曲伴奏上難以涉及的典范。貝多芬當(dāng)年也準(zhǔn)備為歌德的這首詩(shī)譜曲,留下了一份草稿,他對(duì)這首詩(shī)的戲劇性有深刻的理解,但是卻放過(guò)了歌德詩(shī)作中那種神奇的幻境。“舒伯特的《魔王》具有同樣的戲劇性,然而卻進(jìn)一步用奇幻的音樂(lè)手法來(lái)捕捉他的意境,表現(xiàn)出十分生動(dòng)的心理刻畫(huà)和氣氛刻畫(huà),產(chǎn)生出非常富于想象力的神秘幻覺(jué)。”岡他在古典主義沃土里培育出浪漫主義花朵,并使它具有強(qiáng)大的生命力,正如哈多爵士這樣評(píng)價(jià)舒伯特的藝術(shù)成就:“就樂(lè)思與體裁的明晰度而言,他不如莫扎特的成就;就音樂(lè)的結(jié)構(gòu)而言,他遠(yuǎn)遜于貝多芬;但就詩(shī)意的表現(xiàn)力及暗示力而言,卻是前兩者所不能及的”。的確,舒伯特的音樂(lè)既有浪漫主義的詩(shī)意,又有古典主義的光明。他是音樂(lè)史上浪漫與古典交替時(shí)期承上啟下的人物。從他明確的思維和采用風(fēng)俗色彩的寫(xiě)作手法來(lái)看,他屬于古典樂(lè)派的作曲家;但從他的處世態(tài)度、對(duì)大自然的特殊愛(ài)好、以及音樂(lè)的歌唱性、抒情性和富于多變的舞曲性來(lái)看,他屬于一個(gè)浪漫主義作曲家,他的交響性風(fēng)格繼承的是古典傳統(tǒng),但他的歌曲和鋼琴曲完全是浪漫主義的。
三、歷史貢獻(xiàn)
舒伯特在藝術(shù)歌曲的創(chuàng)作上確實(shí)有著杰出的貢獻(xiàn),他第一次把歌曲創(chuàng)作提升到可與交響樂(lè)相提并論的歷史地位,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杰出成就。在他創(chuàng)作的六百多首藝術(shù)歌曲中,其中有一百多首是以歌德的詩(shī)所譜寫(xiě),其余的則采用席勒、海涅、繆勒等著名詩(shī)人的詩(shī)歌。舒伯特在旋律寫(xiě)作上有著極高的才能,尤其是歌曲的創(chuàng)作,幾乎是不費(fèi)吹灰之力。他寫(xiě)歌曲總是那么輕而易舉,提起筆來(lái)不家思索。對(duì)于寫(xiě)成的東西,他從不再去反復(fù)推敲與修改,一切順其自然,水到渠成。在這一點(diǎn)上,他完全可與莫扎特相媲美。他常常手執(zhí)名家的詩(shī)集在室內(nèi)徘徊,然后突然伏案奮筆疾書(shū),短短的幾分鐘又一首傳世佳作誕生在人間。難怪有人說(shuō)他的歌曲不是“寫(xiě)出來(lái)”的,而是“生出來(lái)”的。
伴隨著法國(guó)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的爆發(fā),浪漫主義思潮隨之席卷了整個(gè)歐州。他的實(shí)質(zhì)是理想主義,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目的就是為了抒發(fā)具有個(gè)性的作曲家本人的思想感情。這種感情是復(fù)雜多樣的,對(duì)美好生活的憧憬,對(duì)大自然的贊美,找不到出路的困惑及逃避現(xiàn)實(shí)的自我陶醉等等。
為了表達(dá)如此豐富復(fù)雜的思想感情,古典時(shí)期樸素的功能和聲語(yǔ)言顯然是難以勝任了。正是由于這樣的表現(xiàn)要求,在浪漫主義初期的作品中,半音化和聲,遠(yuǎn)關(guān)系轉(zhuǎn)調(diào),各種變音及不協(xié)和和弦的使用開(kāi)始頻繁起來(lái)。作為在創(chuàng)作上承前啟后的過(guò)渡,舒伯特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某些浪漫派和聲的端倪。他和其他浪漫主義藝術(shù)家一樣打破古典的規(guī)矩、追求個(gè)性、自由和熱情。其中,副三和弦的連續(xù)進(jìn)行及副屬和弦的廣泛應(yīng)用是一個(gè)重要的標(biāo)志。這些不穩(wěn)定和弦的使用,正是作曲家刻畫(huà)心理變化的手段,和聲—這一重要的音樂(lè)表現(xiàn)方式,在此已雖然不像古典時(shí)期僅為加強(qiáng)和聲動(dòng)力而用,他已作為一種純粹的表現(xiàn)因素,恰當(dāng)?shù)睾嫱谐鍪娌匾庥麅A吐的復(fù)雜情緒,極大地豐富了樂(lè)曲的抒情性。我們可以從舒伯特的作品中看出浪漫主義藝術(shù)家的這一追求,是他奠定了浪漫主義音樂(lè)創(chuàng)作的基礎(chǔ)。“他的音樂(lè)所表現(xiàn)出的隨意性、自發(fā)性和意料不到的魅力都成了浪漫主義藝術(shù)的要素。因此無(wú)論是以統(tǒng)一為主題,還是以變化為主體,在舒伯特的藝術(shù)歌曲中都為更好的抒發(fā)豐富多彩的內(nèi)在情感,都以“抒情”為最終的主旨和目的。他還十分巧妙地把抒情性和戲劇性的情緒安排在一個(gè)緊密的結(jié)構(gòu)空間里,從民間音樂(lè)史詩(shī)的寶庫(kù)里吸取養(yǎng)料,繼承前人的高超技巧對(duì)它們進(jìn)行梳理、提煉、概括和集中,創(chuàng)造性地將濃郁的個(gè)人情感和崇高的社會(huì)精神水融為一體,既表現(xiàn)了歌曲中難以表達(dá)的思想內(nèi)涵,又保留了富有個(gè)人特征的抒情風(fēng)格,他遵循古典主義時(shí)期崇尚理性的美學(xué)原則,要求創(chuàng)作的規(guī)范化和程式化及作品形式上的完美統(tǒng)一。在這種美學(xué)思想的指導(dǎo)下,古典時(shí)期的音樂(lè)掘棄華麗與復(fù)雜的技巧,和聲上以嚴(yán)格的功能邏輯為組織手段,這種音樂(lè)也可歸納為以大小調(diào)自然音樂(lè)為主體,以嚴(yán)格、簡(jiǎn)單、質(zhì)樸的功能邏輯為基礎(chǔ)的主調(diào)音樂(lè)。這一特征在舒伯特的許多作品中都有所發(fā)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