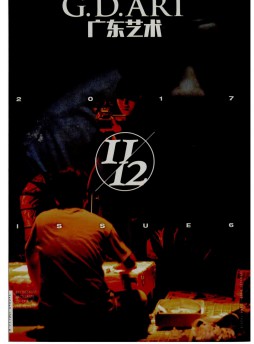藝術生活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yōu)質藝術生活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京劇服飾來源于生活服飾
宋元雜劇時,隨著創(chuàng)作題材的日益豐富,角色分工更細化,根據劇中人物身份、境遇,穿戴的服飾增多,戲曲服飾的類型特征更趨明顯。“嘗見元劇本,有于卷首列所用部色名目,并署其冠服,器械,曰:某人冠某冠,服某服,最詳。”道士穿“道士裝”,文人穿“儒服”,官員穿“衣冠”,宦官穿“黃衣”等等;對各角色的服飾顏色也有了規(guī)定性,如“裝孤”一般穿紅袍,副末、副凈多穿黃色或白色衫等。明傳奇興盛,尤其是明后期“昆山腔”盛行,戲衣樣式和名稱有了不小的變動,在戲曲服飾發(fā)展歷史上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它吸收使用明代生活常服來扮演角色,至清中葉,圖案更加五彩繽紛,服飾顏色由只有五色到出現上五色、下五色,清代舞臺上還用全堂色,如喜慶場面用紅色,稱“紅全堂”;喪祭場面用白色,稱“白全堂”;宮廷場面用黃色,稱“黃全堂”。明清以來的服飾從歷史和現實生活服飾中擇取了某些式樣加工提煉,根據劇中人物的官職、身份地位,日益規(guī)范化和程式化。隨著徽班進京,京劇形成,京劇服飾受時代影響,在清康、乾年間和慈禧時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通過演員的著裝來實現角色的轉換,通過衣著打扮來推動演員進入角色,“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從而將歌舞表現得形神兼?zhèn)洌铎`活現。作為一門欣賞藝術,從生活服飾中的實用到夸張美化、增加舞臺演出效果,戲曲服飾最終形成。
(二)京劇服飾是生活服飾的抽象提煉
京劇服飾來源于封建時代的生活服飾并受到封建社會各種觀念的影響和限制。等級制度要求全體社會成員根據自己再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來穿戴,京劇服飾就是按照生活中不同等級的人物身份來設計,始終無法擺脫等級觀念的約束,可以說,京劇服飾從形成時期就是生活服飾的仿制品。如:上五色黃紅綠白黑,一般用于社會地位較高的人物;下五色粉藍紫香湖,一般用于社會地位較低者。再如:圖案中的蟒紋,來自于皇帝龍袍上的龍紋,象征尊貴、權威;“補子”圖紋來自于明清時代的“補服”,平民百姓的“素布素衣”,落魄書生、窮人的“補納服”,仙凡僧尼的水田紋樣,道士的八卦圖紋等等,都來自于生活服飾。京劇服飾中的配飾也來自于生活服飾,如“大靠”,從生活中的鎧甲演變而成;“水袖”,從水衣演變而來;“玉帶”,從生活中的腰帶發(fā)展而來等等。
二、人們的想象成全京劇服飾的寫意性
第2篇
從《黑暗中的舞者》獲獎,《老頭》、《江湖》、《北京彈匠》、《鐵路沿線》、《北京風很大》等作品走向國際開始,DV就不再平靜了,“一夜之間都成了革命黨”①,人人說DV,人人玩DV。DV到底帶來的是什么,取代電影的技術手段,粗糙不堪的畫面對電影造成的傷害,“影像不能承受DV之輕”②,還是賈樟柯呼吁的“反對歧視DV”③的另一種發(fā)展?審美需求,是人的最高需求,DV最后的發(fā)展必然是走向藝術的殿堂。藝術的生活化,生活的藝術化,是人類藝術和人類生活的極致,藝術從勞動脫離開始就渴望回歸生活,DV在某些特性上表現出來了這一藝術發(fā)展的趨勢,本文主要就DV客體的生活化,關注的題材從宏觀的歷史轉向日常化的生活圖景,民間普通百姓的生活,小人物的命運;DV主體的多元化,越來越多的人擁有自己的影像話語權力和自由,“革命”和“歷史”的官方宏大敘事轉為坦率的個人化的語言;美來源于人在本質力量對象化過程中反觀自身,受眾期待在DV作品中看到自己的生活,直觀自身,另一方面僅僅生活在其中也不能使他們滿足,在欣賞別人的鏡頭同時也拿起DV,對自我的生活表達,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客體、主體及受眾在生活中是融合的,DV在走進生活,走近我們,慢慢消解著藝術和生活的壁壘,DV藝術在走向生活,生活在DV鏡頭中變?yōu)樗囆g,生活,是DV藝術的起點,也是終點。
ABSTRUCT
Since《dancerinthedark》obtainawardsofCannesin2000,and《oldman》,《LakesandRivers》,《ballcraftsmanofBeijing》,《heavywindinBeijing》DVworksmovetowardsworld,DVhavebeennolongercalm,and"becomeRevolutionaryPartyawholenight",EverybodysaysDV,everybodyplaysDV.WhatDVbringtousonearth:itreplacesthetechnologicalmeansoffilm,"injurywhofilmleadstothefact"coarsepicturethatcan''''tbear,"imagecan''''tbearDVlight",merchant"objecttodiscriminatingagainstDV"byZhangKeJiaonethatcallupon,anotherkindofdevelopment?Aestheticdemandisthepeople''''ssupremedemand;DV''''slastdevelopmentmustbetheartpalace.Thelifenessofart,lifeartup,andmankindlifesendhumanartsverymuch,Artwisheagerlytoreturntolifesincebreakawayfromit,DVshowthetrendsofdevelopmentatcharacteristics.ThistextismainlyonthelifenessofDVobject,thedailylifeviewthatthesubjectmatterpaidcloseattentiontochangesdirectionfromhistoryofthemacroscopic,Thelifeofordinarycommonpeople,thesmallpotato''''sdestiny;ThepluralismofDVsubject,moreandmorepersonshaveone''''sownimagewordspowerandfreedom,Themightynarrationofofficialsidewith"history"of"revolution"istransferredtoacandidindividualizedlanguage;Gracefulstemsfrompeopleandreviewsoneselfinthecourseofessentialstrengthtargetindividualityisexpectedtoseeone''''sownlifeinDVworks,theyarenotsatisfiedlivinginit,alsopickupDVtoo,Expressingself-life,sotheobject,subjectandmerginginlifemainlyinasense,DViscomingintolife,walkingclosetous,andclearingupthebarriersofartandlifeslowly,DVartismovingtowardslife,livesandturnintoart,lifeinDV''''slens,ItisastartingpointofDVart,theterminalpointtoo.
關鍵詞
DV藝術的生活化生活的藝術化自我關照
導論DV之美在何方?
眼下,DV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詞,網站,流行雜志報刊,大學校園內也流行著“今天你DV了嗎?”的問候語。這里所說的DV已經突破了digitalvideo(數碼攝像機或數碼影像)的原始定義,已經具有了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在內的廣泛含義,甚至還是一種時尚和潮流的代稱,內涵上呈現出思想的異質性和藝術的前衛(wèi)性的意識精神領域。“DV是一種生存狀態(tài),是對生活原生態(tài)的接近真實的記錄。DV讓人們找回對生活久違了的天真和熱情,讓人們換一個視角去觀察習以為常的一切;DV是一種權力,是將用影像表達自己的權利從少數壟斷者手中歸還給大眾的一把利劍……”、①
1996年,DV攝像機在日本問世,最初被用來拍攝家庭影像。但是短短的幾年間,隨著機身性能的改進以及電腦配套設備的開發(fā)與研制,“能輕巧、價廉、自由地干事”、②,DV機已經成為當前個人影像制作甚至專業(yè)媒體都非常喜愛的一種攝像設備,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選擇DV進行自己的影像表達。“Dogme95”宣言的提出者之一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vonTrier)的《黑暗中的舞者》(DancerintheDark),獲得第五十三屆戛納電影節(jié)最佳影片金棕櫚獎,DV在中國也有著迅速而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甚至要比國外的DV制作更有熱情。DV傳入中國以來產生了不少的優(yōu)秀作品,比如:《老頭》、《江湖》、《北京彈匠》、《鐵路沿線》、《北京風很大》、《雪落伊犁》……在觀影群體中都是盡人皆知的代表作品。而青年導演賈樟柯用DV攝像機拍攝的電影《任逍遙》則入圍第55屆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jié),獲得很高的國際聲譽,成為中國DV影像的驕傲。
DV一詞被炒得沸沸揚揚,DV的輕便和便宜使傳媒家電化,DV成為人們觀察生活,體驗生活,表達思想的一種方式,代表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DV等數字藝術的發(fā)展在對傳統(tǒng)藝術沖擊的同時,也受到各方面的質疑,尤其是在審美價值上頗有爭議。DV給了人們影像權利的同時也破壞了影像藝術的高貴和經典,“每個人都是一位藝術家”③,開機關機太容易了,影像能否承受DV之輕?“首屆獨立影像節(jié)”也被形容為“考驗觀眾體能的‘視聽盛宴’”,④沒有審美的愉悅可言,DV到底是以怎樣的一種身份介入影像藝術之流的,DV的美在何方?
藝術的本質在于展現生命力。生活是最大的藝術之源,美正是來源于生活中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作為民間影像的力量,DV比任何其他影像藝術更接近生活。DV在誕生初期只是為了提高家庭錄像的聲畫質量,當DV成為人們的家用品也就是最大程度的回歸民間,承擔起反映民間的使命,甚至會在不自覺中最大限度的貼近生活的真實。DV的藝術性固然來源于對膠片電影在表現手法上的繼承和發(fā)展,然而其技術的特性與獨立性使其藝術性也具有特殊性。DV在技術層面上的輕便和經濟層面上的便宜促進了DV創(chuàng)作主體的下移,人們都不滿足僅僅生活在其中,都有了自我表達的欲望,創(chuàng)作主體多元化的同時,創(chuàng)作的內容更加平民化生活化,DV在本質上更傾向于民間,傾向于生活。
DV記錄著蕓蕓眾生的常態(tài)生活:《鐵路沿線》的流浪漢,《高樓下面》的外地打工者,《老頭》中的遲暮者……平常的人倫親情和家常里短無不感動著我們,無論是在DV鏡頭后面,還是鏡頭里面,我們看到的都是生命力的展現,都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到處都是美的展示。DV的美,正是在于對生活的回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實現了人類的假說:藝術的生活化,生活的藝術化。
DV,能承受生活之輕
美無處不在,只是缺少發(fā)現美的眼睛。DV這只眼睛,發(fā)現了更多樸實無華的東西,讓生活中更為感人,更為真實的東西,無論丑,還是美,都坦然的呈現在鏡頭中。DV的平民化從純粹個人的角度對普通人喜怒哀樂的表達、對底層老百姓命運的關注、對人的個體或群的原生狀態(tài)的真實記錄,正是DV創(chuàng)作與生俱來的特點。因此,如果你在一個凌亂不堪的菜市、一個灰塵彌漫的建筑工地或一個破敗清冷的老街看到手持DV拍攝的人,你完全無須詫異,因為他就正是在以DV人的獨到視角,去捕捉周遭生活最平常、最質樸、最細小的片段。如西南師范大學學生創(chuàng)作的《最后的鐵匠鋪》,它所抓取的就是渝北靜觀場里的一家小打鐵鋪,那里曾是打鐵很發(fā)達的地方,后來因為農業(yè)機械化的發(fā)展,鐵器在生產生活中逐漸淡出,不少打鐵鋪都歇業(yè)了,這對父子卻在他們長期的作息慣性里,維持著冷清的鋪面。從中,我們看到的是新舊生活交替過程的一個縮影。類似的又如美視學院的《棒棒軍》,在紀實反映重慶“棒棒”①在城市邊緣不乏困苦的掙扎時,也折射出他們離開故鄉(xiāng)和土地流向城市的希望與夢想。在這里,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生活狀態(tài)與我們這個大都市的發(fā)展變化形成了寓意豐富的對比。《歌者》也是這樣一部反映平常及社會邊緣人生活狀態(tài)的DV作品。該片導演兼編劇鄭正運用電影的方式和手段,將眼光投向重慶民間的“死人板板”②樂隊,講述了一個女子到外地尋找失蹤幾年的丈夫,為生存進了一個喪事樂隊。在對找到丈夫已經絕望時,她愛上了樂隊的組織人,卻又在一次演出中,意外發(fā)現死者正是她要尋找的丈夫。片中對小人物命運的表現,凸顯出一種平民化的審美視角。楊天乙則是看到城墻根下的老頭好玩,于是動了要拍攝的想法,《老頭》中展現的是一群地道的北京老人,他們操著純正的京腔,在墻根下曬著太陽,天南海北地聊著。他們中有的已經口齒不清了,但是他們在人生的最后階段依然顯出輕松自然,就連身邊的老哥哥去了,他們談論起來似乎也要像老北京喊臺一樣的叫上一聲“好”。這一切自然地從影片中流露出來,像是一杯滾茶在慢慢地往下沉,緩慢而有節(jié)奏。一切就如生活一般親切自然。《北京彈匠》的導演朱傳明,是在偶然的機會里結識了一位來北京彈棉絮謀生的湖南農民,從而引發(fā)了他拍攝此人生活際遇的想法;《鐵道沿線》的導演杜海濱(朱的同班同學)則是在他家鄉(xiāng)寶雞的火車站附近發(fā)現了一群以揀垃圾、拾破爛為生的來自中國各地的流浪漢,于是力圖切入并記錄這群被視為“賤民”的人真實的生存狀況,DV用鏡頭關注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一部影片最重要的部分應該是人的生活,而不應該是劇情,脫離生活的劇情是經不起琢磨的,而我之所以喜歡紀錄片也正是出于對這方面的偏愛。人類的行為標示著一切,如果你用心觀察,你會發(fā)現許許多多生活的細節(jié),而正是這些細節(jié)組成了我們復雜的生活,并暗示著已經發(fā)生和將要發(fā)生的一切。”①
在DV作品中,拍攝者不僅僅通過鏡頭來觀察生活,而且是切身體驗著鏡頭下的生活,與其說他們在拍別人的故事,不如說他們拍的就是自己用心去感受到的生活。盛志名他拍《心-心》時說:“當我回到北京的時候,是冬天,特別累,就開始玩兒,到酒吧之類的地方。玩兒的過程中,就看到我電影里那些小女孩的形象。有一天我從酒吧出來看到三個女孩兒暈在地上,就送她們到另外一個地方,然后就跟她們認識了。她們的生活給我的觸動特別大。我覺得我是真實地把她們的生活放在那里了,我沒想作任何的遮蔽。這可能和我對生活的認識有關,我沒看到那么殘酷的東西,我覺得大多數人的生活沒那么傳奇。”②蕭狼在《苦樂打工妹》的創(chuàng)作手記中寫到:“我是在農村長大的,應該說小時侯也吃過不少苦;貧農的階級成分的原因吧,長這么大的20多年里,我接觸得比較多的是人文關懷者們所謂的‘弱勢群體’,我們宿舍樓旁的小炒部的那些打工妹于我畢竟是親切的,我們之間有共同話語;我想這是我們能夠溝通,因而我能順利完成這個小片子最重要的原因。她們對于拍攝、采訪、DV、紀錄片等等這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也并沒有去想她們會從自己日常看到的電視屏幕中出現;所以面對著攝像機,她們真是不會做秀,一切反而都如平常一樣自然。在很短的時間里,我們成了真正的朋友。我也在凌晨4點起床,看她們做包子、煎雞蛋;然后我可以安心地去睡覺,讓她們午餐前給我打電話起來繼續(xù)拍攝——拍攝成了我們共同的工作。”③與其說是共同的工作,不如說是一種生活。杜海濱在《高樓下面》接近片尾的部分,出現了全片中惟一一個使用三角架拍攝的段落:除夕之夜的地下室的宿舍,一個中全景的畫面,阿毅蹲在地上剝蔥和蒜;此時作者從畫面右側出現,和阿毅一起剝蒜、洗菜,他離開、又回來,準備他們的年夜飯……當作者從攝像機背后走出來,他使自己也成為一個被拍攝者。吳文光在拍完《江湖》后,對“遠大歌舞團”④的關注也沒有結束,他有時仍然會出現在那個在窮鄉(xiāng)僻壤流動演出的歌舞大棚里。雖然大棚的演員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在他們當中,這個“戴眼鏡、肯幫忙、還給他們做飯吃的吳老師”⑤已經成為了傳奇人物。這次經驗似乎完全改變了吳文光以往的拍攝立場,他在一次訪談中說道:“我是在一種悲喜交加的感情中拍片,我甚至覺得不是在拍一種另外的生活,而是我以什么眼光看他們,甚至我是在拍攝自己的生活,是在拍我自己的自傳。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這種感覺真好,也許我沒有達到,但是的確拍他們就是拍我自己。我不能確定拍了這個團就像拍了全中國的團,但是我能確定拍的是我的生活。”①仲華也說道:“幾年前我曾經在武警部隊里當兵,做了好幾年的電影放映員,所以《今年冬天》有種半自傳的意味。再回到部隊拍這個片子,這是我呆過很多年的地方,這是我的地方,電影中四個不同的方式也是在完成一種電影的形象。使館的鏡頭能看出來,那幾乎是一個鏡頭一氣貫成,那里邊是我呆過很多年的地方,那兒的一切我都非常熟悉。”②把家用攝像機對準被遮蔽的現實與生活的時候,對準可能要遺忘的過去的時候,可能就完全是出于一種感性沖動,和一種對同類人的理解。朱傳明在創(chuàng)作手記中說到:“我常常被生活中這樣的場面感動:火車站疲憊而臥的人群,集市上擁擠的人流,馬路邊吆喝生意的攤販,建筑工地腳手架上的民工……他們的呼吸象暗流一樣洶涌,被裹脅而去。”③而楊天乙與她所拍攝的老頭之間,也產生了“他們成了我的生活,而我成了他們的念想”④那樣親密的關系。DV拍攝者以一種人文關懷的心態(tài)為底層吶喊。生活中的輕賤無所遮蔽地坦露在DV的鏡頭中,故事、演員、導演都來自生活,最后構成同一個藝術。
DV,能承受藝術之重
DV作為藝術的革新工具不僅在于拍攝客體的草根化,更在于創(chuàng)作主體的身份出現了多元化的可能,DV的出現,打破了“業(yè)內人士”和主流媒體的設備優(yōu)勢,模糊了昂貴的“專業(yè)影像”與便宜的“家庭錄像”之間原本不可逾越的品質差異,從而賦予了更多普通人以真正意義上影像創(chuàng)作的權利。因為DV使用的低成本,因為其主要使用者是社會各階層的普通百姓和愛好者,所以從DV問世至今,它一直都體現出很平民化的色彩。曾在峨影廠執(zhí)導多年、后又到西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任教的余紀教授告訴記者,“以前搞電影電視的,的確多多少少都有些‘貴族感’。由于它很強的藝術性和專業(yè)色彩,對普通老百姓來說,甚至它整個的攝制生產過程都顯得較為‘神秘’。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DV越來越普及,使得老百姓用影像的形式來自由表達自我成為可能。DV作為一種新興的話語權力的載體,正在被泛化和更多地采用,并影響和改變著我們這個社會這個時代。”⑤重大美視電影學院副院長唐澤芊教授對此也有深刻體會:“藝術領域的影像創(chuàng)作,離不開相應的技術裝備。隨著科技、經濟的發(fā)展,后期制作功能的簡便化,使原來停留在專業(yè)領域的影視藝術走入了尋常家庭。就像卡拉OK一樣,影像藝術正在成為一種家庭化的藝術,平民化的藝術。”①DV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自由,一種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自由,DV具有配合先進的剪輯器材進行非線性剪輯的優(yōu)點,并且采用了數碼信號的方式把作品傳到網上,“DV最主要的優(yōu)勢對我而言在于真正的低成本,你不需要在創(chuàng)作前就擔心市場,擔心錢怎樣收回,擔心制片人給你壓力,哪怕作品賣不了,也不會使我債臺高筑,創(chuàng)作進入真正自由狀態(tài)”②,技術的發(fā)展從形式上改變了藝術的發(fā)生,技術門檻的降低和操作的私人化使越來越多的人擁有影像話語的權利和自由。
DV不僅僅是一種設備,而是一種新的對待電影和對待生活的方式。當代中國比較著名的DV導演,除了吳文光以外,其余幾部DV作品的導演全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而且都是第一次拍攝紀錄片,這些年輕作者的創(chuàng)作初衷大都介乎自發(fā)與自覺之間,沒有誰在拍攝之前就對紀錄片的本體或價值有一個明晰的認識,但每個人在舉起攝像機的時候,都滿懷著真誠表達的強烈愿望。吳文光認為自己是使用先拍后制作的工作方式“拍的時候完全不知道這東西拍來干什么,以后有什么用,只是覺得非常有意思,不去制作一個驚人的作品,它是一個更私人的東西,它想表達什么東西,想說明什么東西,它肯定是屬于我的,DV代表了一種真正個人的表達方式。”③“DV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作者的自來水筆,影像技術的進步可以使更多的人擁有一種表達自己的手段,一種語言。”④DV承受生活之輕的同時,也承擔起藝術的重。創(chuàng)作客體下移的同時,創(chuàng)作主體的下移,創(chuàng)作的自由和私人化使藝術更有活力。雖不說人人可以玩DV,但至少它已不再是主流的特權。DV家電化的趨勢,使DV藝術成為一種生活態(tài)度,DV著,藝術著,生活著。
影視是一門高深的藝術,如果你拍一部電影,必須有專業(yè)知識,必須有設備,更主要是最好有個幾百萬,看《英雄》就可以知道了,光那些著名的演員的出場費就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擔的,DV就完全不同,當然你也可以象《黑暗中的舞者》一樣,動用100臺DV,但那畢竟不是我們要走的路,真正的DV,有一個DV,有一腔對生活的熱情,有一幫朋友就可以。“DV影像工作站”⑤第三期的推薦作品是楊天乙的《老頭》,這部片子至今讓人們津津樂道的是,這是一個之前跟影視毫無關系的女孩;第一次拿起DV機;第一次拍攝紀錄片;耗時過兩年;一切自費;拍攝的是一群被忽略的北京退休老頭,雖然有點粗糙但不失原創(chuàng)性和藝術性。清華同學自編自導的《清華夜話》畫面的晃動,聲音的生硬也無損于大家對它興趣,它是那樣的生動活潑,蕩漾著對生活積極的熱情。蕭狼在拍攝《苦樂打工妹》時,他鏡頭中的主人公甚至搶過攝像機拍起他來,讓他說他的故事。拍攝的對象和主體都已經融入到生活融入到拍攝的快樂中去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對生活的理解。2009年9月起,云南省德欽縣的幾位藏族農民在一家基金會的資助下,拍攝了《冰川》、《茨中圣誕夜》、《酒》、《黑陶》等幾部DV紀錄片,這個“社區(qū)影視教育”項目負責人郭凈博士在項目宗旨中寫道:“照相機,攝像機和電腦變得如此便宜,促使普通人產生了自己制作影像的欲望,當城市里的年輕人到茶館為朋友的第一部短片助興,當鄉(xiāng)下的制陶師傅開始用攝像機機錄村民選舉的場景時。多樣化的聲音便在影像中出現了。”①從專業(yè)的角度而言,最近的DV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視聽方面的缺陷,但這些新紀錄片人卻以影片內容的真實性與原創(chuàng)力震動了國際影壇:楊天乙的《老頭》獲2000年法國真實電影節(jié)的評委會獎,朱傳明的《北京彈匠》獲去年日本山形紀錄片電影節(jié)“亞洲新潮流獎”,而雎安奇的《北京的風很大》則在澳大利亞國際獨立電影節(jié)上獲得了“最高喝彩紀錄片獎”。這些獎項不僅僅是對這幾位紀錄片導演的褒獎,更重要的是,它傳遞了這樣一種信息:一個普通人可以通過他的才華、毅力、對生活的熱愛以及簡陋的攝影器材,成為一位“真正”的紀錄片導演。因此DV更深刻的力量是一種對普通民眾的影像啟蒙,是販夫走卒(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掌握并運用的記錄工具,是無數雙眼睛對我們這個社會的多元觀察和描繪,DV帶來了“民間影像”的燦爛前程。DV也不會因為其承受生活之輕而損害電影藝術的重,相反,越是民間的越是藝術的,越是生活的越是深刻的。DV是最具平民意識的,一切平民化的東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們對這個世界保持經常觀察,表達思考的習慣,每個人的眼睛都會更銳利,感覺更靈敏,思想會更開放,藝術也將更具生命力。
審美的生活化
DV從一種技術手段開始對藝術創(chuàng)作主體起了深遠的影響,進而對藝術內容的生活化起了催化作用,如果說技術帶來的藝術的生活化是一種外在的手段,那么審美情趣的生活化則是藝術生活化的本源。
美來源于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說來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②,面對“人化的自然”③,人們“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④因此受眾在藝術批評和欣賞中,有一個“期待視野”⑤,他們期待藝術對生活的親近,真實成為中外視覺藝術作品接收和欣賞的衡量標準。它是在人類幾千年欣賞描寫現實的文藝作品的過程中和幾十年接收寫實風格的影視作品過程中形成的,從柏拉圖“模仿乃是藝術之根本特性”⑥起,至中國“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偽”⑦,無不要求藝術的真實性,惟有真實才能引起受眾的真正共鳴,受眾也才能透過藝術作品反觀自身。受眾代表的就是生活,DV反映的也是生活,受眾的生活又呈現出藝術的狀態(tài),我們在看DV的同時我們也就是在看自己。當我們看到《不快樂的不止一個》家庭問題,《心-心》中的絕望中的希望,《苦樂打工妹》的艱辛又充實的日子,《清華夜話》中的學生生活,我們本能地感到親近,立刻意識到,這就是我們周圍的生活,這就是我們自己的生活。這些鏡頭真實記錄的酸甜苦辣就是我們自己的酸甜苦辣。巴贊、古拉考爾多次指出,紀實電影與真實的生活有一種親近性,正是電影與觀眾的親近性引起了觀眾對電影的親近性。DV更是如此,它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題材對生活的貼近。在權威調查機構AC尼爾森調查中發(fā)現觀眾喜歡收看的紀錄片類型的節(jié)目卻是《生活空間》這樣的節(jié)目和一些專題片,顯然“講述老百姓的故事”是很多觀眾關心的話題。人們期待紀實性的作品,是因為人們希望看到自身。“紀錄片,尤其是更多的民間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者的角度可能是相對小眾的私密的,但他們所揭示出的空間,卻是大眾共通的。”①京華時報記者在北京電影學院等藝術院校和北工大等非藝術院校的學生會均進行了調查,學生們對紀錄片顯示出的極大熱情,讓記者很是意外,其中的幾部紀錄片是學生們屢屢提起的,比如講述了關于農民巡回演出的《江湖》;講述了一群遲暮老人生活故事的《老頭》;還有彈棉花的農村青年在都市中的遭遇和生活的《北京彈匠》等。吳文光講,“雖然乍一看,這些拍攝對象都不是社會的主流,但從片子中,大家能看出許多人性中相同的東西,而這些恰巧是普通人不愿顯露的,卻是人人都有的,大家喜歡的原因就是這種大眾化激起了心底的共鳴。”、②學者黃集偉認為:“文字閱讀中,那種以虛構為能事的傳奇已是最靠不住的東西,‘非虛構’的加入,正顯出了無上魅力,開始成為我們閱讀生活中的核心期待。”③文字如是,影像豈不一樣,DV中真實的生活,讓我們更大程度的反觀自身,藝術的生活,美的生活產生了。
僅僅生活其中,僅僅觀看他人或者自己的生活也不能使我們滿足,我們又有自我表達的渴望,于是在欣賞別人的作品,別人的故事同時,我們也拿起了DV拍攝自己和周圍人的生活,于是有了《清華夜話》,我們一邊臥談,一邊拍攝,一邊看著我們的DV哈哈大笑;于是有了《冰川》、《茨中圣誕夜》、《酒》、《黑陶》,我們在生活的同時把它記錄下來,同時我們又成為自己第一個觀眾。創(chuàng)作與審美在生活中融為一體。藝術的審美,得到的是一種共鳴。導演的思維,對象的生活喚起了審美主體的某種相似經歷的記憶,看到的是自己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因此藝術更真實更具感染力;當審美主體成為創(chuàng)作主體兼創(chuàng)作客體的時候,這種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也就更為深刻,前者是反觀自身,后者是直面人生。審美的需求也促使藝術創(chuàng)作的生活化。藝術的生活化,民間化,從內容上改變了藝術的發(fā)生,生活主體的藝術化從形式上改變了藝術生成;DV改變了藝術,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導演、演員、還有我們都生活在這個社會,我們都在別人的故事中演著自己的故事。今天我出現在你的鏡頭中,也許明天你將會在我的鏡頭里,“我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我,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④,DV溝通了藝術和生活,溝通了你和我。我們期待著在DV中的我們,以此反觀現實中的我們。
美在生活
“人是詩意的棲居的”①,生活和藝術本不可分割,人類走了一個循環(huán),藝術自從勞動中生活中脫離開始就有一種回歸的沖動,這也是紀錄片的經久不衰的原因。在工業(yè)化的現代,人們更渴望一種高科技高情感完美結合的生活,DV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工具,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希望。與其把DV當作一種媒介,一種設備,不如把它當作一種生活態(tài)度,DV并不同于過去的“作者電影”②,它不僅僅是“個人的表達”③,它還是一種個人的生活。真正跟DV態(tài)度有親緣關系的是維爾托夫的“帶攝影機的人”④。DV不僅使制作電影成為了一種個人的事情,它的欣賞也是成為個人的事情:我們在自己家里觀看DV作品,我們把DV作品裝在上衣口袋里隨身攜帶,贈送朋友,……DV,代表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獨立的藝術生活。或者說DV就是生活本身.它是生活中的一個全新的要素,一種生活習慣或習俗;它在我們的手上,在我們的生存之中;在它的面前,生活沒有一個外面,它無法從外面來觀照生活;它就在生活的里面,是我們個人生活和身體的一個組成部分,面對它,我們就是在直面我們自身。
席勒在《美育書簡》中談到:“人對美只應是游戲,而且只應對美游戲。…………唯有當他是充分意義的人的時候,他才能游戲,唯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⑤如果說DV產品的產生和發(fā)展從技術上促使藝術回歸生活,人的審美情趣則從人的本性上要求藝術回歸生活。美是自由的,就像我們的生活一樣自由,DV給我們自由藝術自由表達的權利。藝術更重要的是參與性和互動性,游戲的藝術不僅僅是自由的,更是積極的。我們都在參與這個美的游戲,游戲中處處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生活中處處展現著人的生命力,在對象化的現實中我們反觀自身,在富有生命力的生活中我們關照自我,從而得到審美的愉悅。“美在生活”⑥,藝術在生活,美和自由不可分,藝術和生活也不可分的,DV在走進生活融入生活的同時,也就從藝術起點回歸到藝術的終極。回歸是人們的審美理想,只有在生活中藝術,在藝術中觀照生活,這才是完整的人。
參考書目
《電影觀眾學》章柏青張衛(wèi)著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6
《西方文論概要》楊慧林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7
《西方文藝理論》張秉真章安祺楊慧林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第3篇
關鍵詞:中國早期;儀式生活;舞蹈藝術
舞蹈是一門古老的身體語言藝術,具有悠久的傳統(tǒng)。從其產生看,其產生在尚沒有文字的遠古時代,是伴隨先民圖騰崇拜和祭祀活動的需要而產生的。早期舞蹈往往在祭祀性場合表演,成為先民祭告神靈、傳達神意、表達情感的一種重要方式。現存各民族民間舞蹈中,有許多舞蹈就具有濃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極強的儀式性特點,這是各民族早期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在舞蹈中的遺存。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進步,舞蹈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性質也不斷地發(fā)生變化,成為一種具有極強審美價值的欣賞性藝術,具有娛樂、表演、抒情等多種藝術特性,但是這些特性都是從舞蹈最早存在的儀式性中漸漸衍生出來的。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舞蹈的根本屬性是儀式性。
一、何謂儀式
郭于華在其《儀式與社會變遷》一書中說:“儀式,通常是指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特征的由文化傳統(tǒng)所規(guī)定的一整套行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動。這類活動經常被功能性地解釋為在特定群體或文化中溝通(人與神之間、人與人之間)、過度(社會類別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強化秩序及整合社會的方式。”紀蘭慰認為“儀式就是通過一定的時間、地點、對象、形式再現社會習俗(生活)的一個過程;通過歲歲重復、交替的程式化、制度化的儀式行為,實現某一時刻儀式所意味著的一切。”前者主要從儀式的社會功能角度對其進行定義的,后者主要從儀式的過程性角度定義的。雖然側重點不同,但皆揭示了儀式的基本內涵,即儀式的程式化、制度性和象征性。《說文》曰:“儀,度也。從人,義聲。”墨子·天志》:“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又《說文》曰:“式,法也,從工,弋聲。”《詩·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傳:“式,法也。”可見,“儀”和“式”的本義皆是法度、準則、規(guī)矩的意思。中國古代“禮儀”連稱,其實就是指各種禮俗儀式,這是古代早期儀式的主要內涵。儀式行為者往往通過姿勢、舞蹈、吟唱、演奏等表演性活動和對象、場景等實物性安排營造一個有意義的儀式情境,并從這種情境中重溫和體驗這些意義帶給他們的心靈慰藉和精神需求。因此,一個儀式,就是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是一個用感性手段作為意義符號的象征體系。所以,象征人類學家特納認為,和動物的儀式化相比,人類儀式的原理是象征性的,儀式中的象征符號具有組合和重組的類似語言的能力,儀式就是“一個符號的聚合體。”儀式符號大致有:(1)語言形式的符號,如頌辭、詩文、韻白、咒語以及歌詞等;(2)物件形式的符號,如道具、服飾、用品、繪畫、塑像、樂器等;(3)行為形式的符號,如行動、姿勢、手勢、舞蹈、歌唱行為、演奏行為以及儀式角色的扮演等;(4)聲音形式的符號,如呼叫聲、吶喊聲、吟誦聲、歌唱聲、響器敲擊聲、舞蹈節(jié)奏聲、音樂演奏聲等。可見,舞蹈是儀式符號中比較重要的一種,它既可充當行為形式符號,還可充當聲音形式的符號。
二、先秦儀式的文化內涵與社會生活
中國上古時期的各種社會實踐活動是以禮俗儀式為核心展開的。“禮”之本義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為祭神的宗教儀式,再而后才泛指人類社會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行為儀式。《說文解字·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所謂“豊”,《說文》曰:“行禮之器,從豆,象形。”可見,禮是淵源于上古巫祝事神活動的。孔子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引)可見,禮俗儀式在早期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歷代王朝建國之初最重大的文化舉措莫過于制禮作樂,也說明禮樂在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從本質上說,禮是為了從自我約束的層面讓人們去自覺遵守社會道德,從制度的層面來維護社會等級。而禮的外在形式則是儀式,即通過各種儀式行為和過程規(guī)范社會的各種秩序,再現禮的精神內核。祭天祭祖、歲時祭典和其他政治儀式決定著國家的政治秩序;禮儀中的等級規(guī)則決定了集體內部的交往秩序;生老病死,婚喪嫁娶儀式及其他各種人生禮儀和節(jié)日慶典儀式決定著人們的生活秩序;春祈秋報及其相關節(jié)候性祭典與各類生產儀式,構成了農業(yè)社會中的經濟秩序。由此可見,儀式是上古時期生產生活各領域的中介環(huán)節(jié),也是社會秩序的表征性符號和文化事項的聯結點。它表征著上古時期整個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節(jié)奏。儀式在社會生活中的功能,一方面,體現為儀式使生產生活的各方面有秩序地開展;另一方面,儀式還承載著集體意識如生命觀、死亡觀、倫理觀、禁忌觀等民族文化的深層心理內涵。三、中國早期的儀式及其類型
意大利學者維柯《新科學》認為每個民族的誕生和發(fā)展中大致經歷了互為銜接的三個時代,即神的時代、英雄時代、人的時代,我國早期先民的認知觀念和儀式活動也可從維柯所分的這三個時代進行分析。
所謂神的時代即人類的史前社會。從現存文獻記載和考古學成果證明,中國早期的儀式活動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的山頂洞人。山頂洞人已經有鬼魂崇拜觀念和與此相關的喪葬巫術儀式,新石器的仰韶時代已經有社祭的考古遺存,龍山時代已經有祭祖的考古遺存。夏朝之前的顓頊、堯、舜、禹等方國時期,從大量而成套的祭祀儀器的出土可見,此期已經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的祭祀禮儀。這些禮儀是原始宗教的產物,是在先民自然崇拜、圖騰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等原始的支配下進行的。早期先民對這些看不見的力量或以臣服與膜拜的方式進行祭祀,或借助某種神力進行干預、制服以達到目的,于是產生了巫術思維和巫術儀式。
所謂英雄時代即夏商時期。這時候的祭祀儀式是圍繞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進行的。夏禹治理水患當為中華民族英雄崇拜觀念最早的表現。他死后被奉為社神,人們制禮作樂歌頌其功德,《大夏》樂舞就是為祭祀夏禹而作的。當然,大禹還具有祖靈的性質。商代祖先崇拜觀念占據主導,現存甲骨卜辭中有相當數量是商人祭祀鬼神的記錄。《禮記·表記》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所尊之神,除自然神、英雄神以外,還主要是祖先神。甲骨文中“帝”、“上帝”等字樣,不是后來抽象意義上的帝,而與“祖”的意義是相同的。《大濩》樂舞就是表彰商湯滅夏之功的祭祀儀式樂舞。
所謂人的時代,即西周及以后的祖神分離和以德配天的祭祀儀式。西周重人事而輕神事。其宗族崇拜觀念強調道德教化和政治秩序,傾向于人事和倫理的經營。其祭祀儀式無論祭祖還是祭天,都有意識突出禮儀制度的性質,其《大武》、《大象》樂舞,是這種觀念在意識音樂中的體現。
以上勾勒了中國古代早期儀式發(fā)展的基本面貌和特點。下文對中國早期的儀式類型作簡要勾勒。
1、巫術儀式
巫術是人類童年時期,對人自身和人以外的自然的認識還處于蒙昧狀態(tài)時對神秘的異己力量有所感受和體驗的時候,自然產生的言辭和行為,并使其固定化的結果。原始時代的人們相信人與自然存在著的某些神秘聯系的觀念,幻想人可以通過某種特殊的方式影響自然和他人,于是產生了巫術。巫術儀式一般包括巫術行為和與此相關的一整套巫術觀念。通常形式是通過一定的儀式表演來利用和操縱某種對象影響人類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滿足一定的目的。巫術的儀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種據認為賦有巫術魔力的實物和咒語。中國大約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隨著氏族社會圖騰崇拜的出現,也出現了相關的神話和巫術。中國早期巫術涉及古人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除個體巫術外,還有公共巫術,如禳災巫術有《山海經》中的驅旱魃巫術,《呂氏春秋》中的湯禱桑林的止旱求雨巫術;順祝巫術有《呂氏春秋》祈求農業(yè)豐收的“葛天氏之樂”;詛咒巫術有《尚書·牧誓》中的克敵巫術等。2、占卜儀式
占卜儀式起源于原始范疇中的前兆迷信。史前的先民們相信事物發(fā)展的趨勢與一些特定的事象諸如氣候、天象、夢境、卜兆等出現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這樣便產生了根據特定事象推知事情結果的占卜儀式。主要有龜卜、筮占、謠占、夢占等儀式。《史記·龜策列傳》曰:“聞古五帝三王,發(fā)動舉事,必先決蓍龜。……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涂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禮記·表記》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西南各少數民族現在還保留著一些古老而原始的占卜儀式。如藏族、云南羌族、四川彝族、貴州苗族、湘西土家族等皆有各種占卜儀式。
3、祭祀儀式
史前社會的祭祀儀式種類繁多,說明祭祀儀式在中國早期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祭祀儀式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儀式當屬蠟祭、社祭與祖祭。張光直先生認為:“仰韶時期農村里最要緊的儀式是祈豐收,拜土地;在他們儀式用的器皿上畫幾個象征繁殖力的女子性器的紋樣,正說明我們祖先祭祀時的虔誠,并吐露作為這片誠心之原動力的耕作生活之艱苦。這就是后來的蠟祭。所祭之神有八種,又稱八蠟,是在十二月時索求四方百物之神而祭之,以求得農業(yè)豐收。社祭是對社神的崇拜儀式,源于史前時期對土地的崇拜,后來演變?yōu)槿烁窕耐恋厣耢`崇拜。而且,社神具有自然神、農業(yè)神與部族神混合的特征。祭祖儀式最早可能在龍山期新石器時代就產生了。在仰韶村(龍山時期)出土的陶祖,很象一尊男性性器模型,據張光直先生推斷,這是中國史上拜“祖”的最早實證。他認為:“中國古代的‘祖’字,本來是個性器的圖畫,亦即祖先牌位的原形。
4、儺儀式
“儺”據說產生于黃帝時,儺祭開始時只限于宮廷,謂“大儺”、“國儺”。逐漸遍及于鄉(xiāng)村,謂“鄉(xiāng)人儺”。殷商時起就可見此宗教儀式,周代舉行最為盛大。傳說方相氏可以驅鬼逐疫,最遲在漢代,驅儺已與蠟祭發(fā)生聯系,在蠟祭前一日,宮廷中要舉行大儺。《后漢書·禮儀志》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記載。舉行儺祭時,巫師就要裝扮成方相氏,身上穿著熊皮,頭戴留有四只眼睛的面具,一邊開路,一邊喊:“儺!”率領十二個戴著面具、裝扮成各種野獸的人--戴面具所具有的戲劇性已為人們所公認,后跟一百多個扎紅頭巾、穿黑衣服、手執(zhí)撥浪鼓的少年兒童,到宮室、房舍、各處跳躍、呼喊,并合唱祭歌《趕鬼歌》以驅逐“疫鬼”,最后,把鬼趕到河里,把火炬丟進水里,表示鬼全部被河水逐走了——人們歌唱、舞蹈、打斗,場面甚為壯觀,也極其富于戲劇性。據《論語·鄉(xiāng)黨》記載,每逢年三十孔子老家舉行儺祭儀式時,孔子就“朝服而立阼階,觀鄉(xiāng)人儺”。
5、人生儀式
人生是人的一生從一個階段過度到另一階段的重要標志,通過儀式強化人生轉折時期的標志,表明先民對人生的獨特理解和對生命的珍愛。有誕生儀式、冠禮、葬禮等。其中,冠禮最重要。冠禮源于氏族社會的“成丁禮”或“入社式”。
以上僅簡要羅列了中國早期社會儀式生活的發(fā)展演進和最為重要的幾類儀式生活。
可見,上述儀式內容已經涉及到早期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體現了先民的生活內容,也反映了先民的思維觀念,而這些儀式大多數都要借助樂舞的形式進行。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舞蹈藝術是伴隨著早期先民的各種儀式而產生的藝術形式,其直接目的是為先民的儀式活動服務的,也是整套儀式活動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正如張本楠先生所說:“原始宗教儀式的進行過程就是原始舞蹈的創(chuàng)作和表演過程,原始宗教儀式的發(fā)展歷史就是原始舞蹈的發(fā)展歷史。無妨說,原始舞蹈就是宗教儀式。”
參考文獻:
郭于華:《儀式與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紀蘭慰:《論民俗舞蹈的儀式》,民族藝術研究1999年版。
薛藝兵:《儀式音樂的符號特征》,中國音樂學,2003年第2期。
《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
張光直:《仰韶文化的巫覡資料》、《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三聯書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