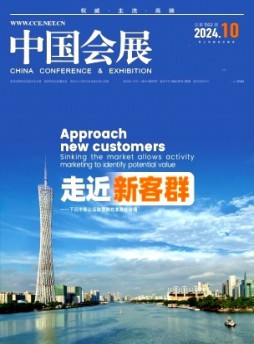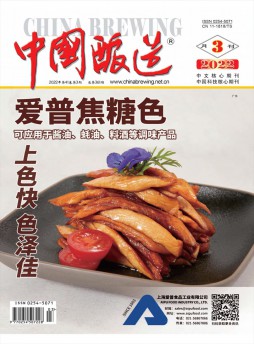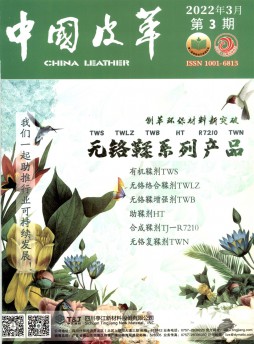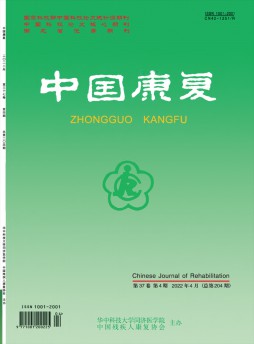中國哲學性與情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哲學性與情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中,西方哲學著重強調一種認知關系,把人視為認知主體,把世界理解成認知活動的客體,并由此在精神與物質之間做出嚴格區分,形成主客兩分的思維定勢,從而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中國哲學則強調一種價值關系,自然不可能在精神與物質之間做出嚴格區分,相反卻把人的需要及其合理性始終作為哲學基本問題。因此,與西方哲
學相比,中國哲學基本問題應是情與性的關系。
一、中國哲學有基本問題嗎?
眾所周知,“哲學”這一名詞大約在1895年左右傳入中國,后經梁啟超等人的宣傳才成為中國學界所習見的名詞。這說明中國古代并沒有一門稱作“哲學”的學問。只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才模仿著西方哲學范式,“建構”了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從而奠定了中國哲學這門學科。這就引發一個問題:西方哲學范式的引進究竟只是改變了中國傳統哲學的詮釋方式,還是直接建立了中國哲學本身?關于該問題的討論,自胡適、馮友蘭兩位先生系統地創立了中國哲學學科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直至在當代引發了長達數年之久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大討論。從討論的結果看,學界目前基本形成這樣的共識:“西方哲學只是‘哲學’這一普遍概念的一個殊相,而不是哲學的標準。中國哲學的問題和范圍雖然與西方哲學有所不同,但這并不妨礙其為‘哲學’,這也恰恰體現了哲學是共相和殊相的統一。”①這就是說,中國哲學可以成立,但與西方哲學有著本質的差別。那么,本質差異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認為,哲學基本問題可以成為我們破解這一謎團的鎖鑰。
哲學基本問題的產生應屬于西方哲學的一個重大發現。恩格斯曾這樣評價近代西方哲學,他說:“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②又說:“只是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世紀
的長期冬眠中覺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的提出,才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③恩格斯的這兩句話必須放在
一起來理解:從第一句話看,“思維和存在的關系”似乎是一切哲學的基本問題,但結合第二句話的意思,我們應該可以肯定恩格斯總結的只是西方哲學的基本問題,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部哲學”。因此,我們不能把“思維和存在的關系”直接當作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由于長期受到“左”的思想影響,這一西方哲學基本問題卻一直被當作評判中國哲學派別乃至哲學家思想優劣的標準,唯物的就是革命進步的,唯心的就是反動落后的。這種簡單化的認識模式直接導致對中國古代思想認識的混亂。對于這一點,我們從以前學界對老子哲學性質的認定上就可以窺一斑而知豹了。任繼愈先生20世紀60年代主編的《中國哲學史》認為,老子是唯物主義哲學家。20世紀70年代著的《中國哲學史簡編》又認為,老子是唯心主義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則認為:“老子哲學究竟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按照這種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方法去追問,是不會真正有結果的。”①原因很簡單,就是把本不屬于自己的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來研究,這只能是捕風捉影。但是,既然西方哲學有著自己的基本問題,中國哲學也應有至今沒有“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的基本問題,如果我們還相信存有普遍意義的哲學概念的話。
二、對中國哲學基本問題各種觀點的反思與批判
一直以來,天人關系始終被大部分學者當作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而把天人關系視為中國哲學基本問題卻有著獨特的歷史背景。它的產生與西方哲學基本問題泛化有著直接聯系:“雖然我們不能把天與人同思維與存在這對范疇硬套,但是可以看出,先秦哲學家們對天人關系問題的思考,實際上都涉及到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亦即涉及到了世界的統一性在于物質還是在于精神的問題,以及思維與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問題。”②對這樣的問題,我們還是分析一下中國哲學中天與人概念的基本內涵。在一般意義上,中國古人所理解的天是宇宙的代名詞,如郭象在《莊子注》中所說:“天者,萬物之總名也。”③這似乎能與西方哲學中物質概念相對應,但實際上中國古人眼中的自然并不是毫無生命的機械之物,而是富有精神的。因此,它不僅有客觀自然的意思,也有命定與主宰的意思。如孔子一方面承認“天何言哉”的自然之天,又默認“天生德于予”的意志之天。應該說,天所具備的這兩層內涵一直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秉持的。至于人這一概念,就更不能簡單地理解成精神,因為關于人的形神關系一直是中國哲學爭論的一個焦點,它本身就反映了中國古人從不把人抽象地理解成精神存在物,而是形神兼備的統一體。基此,有些學者干脆拋開思維與存在關系的干擾,直接把天人關系理解成人與自然關系,并視之為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如宮哲兵先生說:“‘天人關系’問題不是思維與存在、精神與物質的問題,而是人類(社會)與自然宇宙的關系問題⋯⋯天人關系問題將始終是中國哲學的人生哲學、自然哲學的極其重要的問題。”④應該承認,這種理解要比以往認識前進了一大步。但以與自然關系為內核的天人關系是否就是中國哲學基本問題呢?我們還是反思一下哲學的基本含義。哲學是什么?雖然至今依然沒有一個定論,但并不意味一些基本內涵都不存在。孫正聿先生說:“哲學世界觀是關于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理論,因而也是人們理解和協調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理論。”⑤因此,人與自然的關系更應說是一切哲學共性問題,而不僅是中國哲學基本問
題。韋有多先生就說:“貫穿整個哲學發展史并成為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⑥
①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60.
②吳震.先秦“天人之辨”是否就是思維與存在關系的爭論[M]//夏乃儒.中國哲學三百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5.
③齊物論注[M]//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62.
④宮哲兵.中國古代哲學有沒有唯心主義[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6,(1):12.
⑤孫正聿.哲學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15.
⑥韋有多.哲學基本問題暨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演變[J].海南師院學報,1998,(3):77.
31
那么,以人與自然作為中國哲學基本問題就有泛化基本內涵,使之平庸化的危險。故而,有些學者又進一步以“天人合一”作為中國哲學基本問題,如李清良先生說:“‘天人合一’實是中國哲學對于人的存在境域、人的物性、存在價值取向、人生境界和超越維度以及認識方法與思維方式的高度綜合的規定。這些規定確定了中國哲學的基本走向,因此它才在中國哲學中居于核心地位,才是整個中國哲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命脈和基本的意義生長點。”①相對人與自然關系命題,“天人合一”自然更能體現中國哲學特質,也為許多中國哲學研究大家所認可。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其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說:“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徹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②張岱年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大綱》開篇也說:“中國哲學有一根本觀念,即天人合一。”③以此來看,“天人合一”作為中國哲學基本問題應是鐵板釘釘的結論。但是,在做出這樣結論之前,我們似乎需要分辨一下重要問題和基本問題的關系:首先,重要問題與基本問題有相統一的地方。重要的問題往往就是主要問題,解決了它,其他問題也就相應而亡,因此我們也經常把重要問題稱為基本問題。其次,重要問題與基本問題也有著許多相差異的地方。重要問題通常總是相對次要問題而言的,是指與其他問題相較出現的頻率比較高,具有代表性,因而表現出很強的歷史感,不同時代的重要問題可能不同,并且,基本上所有哲學家都會清醒地意識到它的存在,并當作祈盼解決的目標。而基本問題則必然具有超時代性,始終貫穿在哲學發展始終,而且不容易被直接發現,所以只是到了近代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才被西方哲學家當作基本問題清醒地意識到。
那么,“天人合一”應是中國哲學重要問題還是基本問題呢?我認為應該理解成重要問題,而不是基本問題。理由如下:
第一,“天人合一”思想不具備普遍性,不足以涵蓋中國哲學所有問題。夏甄陶先生說:“在天人關系存在和展開的歷程中,不可能在某一階段是單純的天人之分,也不可能在某一階段是單純的天人合一。所以,持天人合一觀點的人,不能排斥天人之分;持天人之分觀點的人,也不可能否認天人合一。”④這說明,“天人合一”與“天人相分”始終并存在所有思想家的思想之中。如北宋哲學家張載,雖明確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題,但他又強調,“若非有異則無合。”⑤因此,僅以“天人合一”來總結中國哲學思想,無疑是以偏概全。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雖然大部分哲學家都推崇“天人合一”,但也有一些思想家則突出強調“天人相分”,如荀子、王充、劉禹錫等。此外,“天人合一”理論無法表征中國佛教哲學的特質,因為,在佛教哲學中,天和人都屬于虛妄不實的塵俗之物,根本不是表述終極存在的基本范疇。
第二,“天人合一”內涵模糊,歧義輩出,不能讓人確切地把握。就目前研究狀況看,“天人合一”思想既有被理解成一種境界追求的意思,也有被當作承認自然界具有生命和內在自我價值的生態觀。更有甚者,則把它理解成一種政治信仰,如劉澤華指出,“天人合一”的源頭是“天王合一”,直到近代以前,“天王合一”始終是“天人合一”的中心⑥。究竟哪一種觀點,能真實地表達中國傳統哲學中“天人合一”的觀念,可能很難有最終結論。
第三,把“天人合一”當作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不符合關于哲學基本問題認識的邏輯特征。哲學基
本問題是哲學之“根”,規范著整個哲學傳統的精神特質,是不同哲學傳統相互區別的根本標準,因此必然
①李清良.天人合一與中國哲學基本問題[J].社會科學家,1998,(2):26.
②錢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J].中國文化,1991,(4):5.
③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27.
④夏甄陶.天人之分與天人合一[J].哲學研究,2002,(6):6.
⑤張載.正蒙·乾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4.
⑥劉澤華.天人合一與王權主義[J].天津社會科學,1998,(2):85.
32
是深埋在各種思想表象的底層。這就造成對哲學基本問題的清醒認識,只有到達一定發展階段才能隨著各種哲學矛盾內涵的揭露而被發現。而“天人合一”思想從先秦諸子哲學開始,就一直被當作主要問題被研究。如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①《易·系辭》又說:“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②先秦以后,中國哲學家更是非常自覺地把“天人合一”當作最重要的哲學問題。例如司馬遷把他的《史記》當作一部“究天人之際”的書;董仲舒答漢武帝策問時說,他講的學問是“天人相與之際”的學問;宋代哲學家邵雍更是說得直接:“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③,等等。因此,如果把“天人合一”當作中國哲學基本問題,這在嚴重缺乏哲學自醒意識的中國文化中,是很難想象,也不符合認識發展的邏輯順序,因為具備強烈哲學自醒意識,并在古希臘時期就把哲學當作一門單獨學科加以研究的西方文化傳統中,哲學基本問題只是到了近代才被自覺出來。
總而言之,目前關于中國哲學基本問題的探討,所形成的各種觀點總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點,所以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加以反思和探索。
三、性與情的關系才是中國哲學基本問題
在比較中西方文化差異時,梁漱溟先生說:“西洋偏長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國偏長于理性而短于理智。”④這里的“理性”和“理智”兩概念內涵迥異于現代語義,“前者為人情上的理,不妨簡稱‘情理’;后者為物觀上的理,不妨簡稱‘物理’”⑤。用現代話語表述,梁漱溟先生就是認為,西方文化重認知理性,而中國文化重情感之理。并且,他還對兩者內涵做了更細致的判別:“情理,離卻主觀好惡即無從認識;物理,則不離主觀好惡即無從認識。物理得自物觀觀測;觀測靠人的感覺和推理;人的感覺和推理,原是人類超脫于本能而冷靜下來的產物,亦必要屏除一切感情而后乃能盡其用。因此科學家都以冷靜著稱。但相反之中,仍有相同之點。即情理雖著見在感情上,卻必是無私的感情,同樣也是人類超脫本能而冷靜下來的產物。”⑥即是說,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中,西方哲學著重強調一種認知關系,把人視為認知主體,把世界理解成認知活動的客體,并由此在精神與物質之間做出嚴格區分,形成主客兩分的思維定勢,從而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中國哲學則強調一種價值關系,自然不可能在精神與物質之間做出嚴格區分,相反卻把人的需要及其合理性始終作為哲學基本問題。因此,與西方哲學相比,中國哲學基本問題應是情與理的關系。為了更符合傳統表述習慣,我把情與理的關系改譯成情與性的關系。
從詞源角度看,性之本字為生,原指生而即有的各種欲望和能力;情則衍生于性,是指人性感外物而有的欲望和要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⑦。隨著中國哲學的發展,性表征的內涵越來越獲得超越意義,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⑧。這就把性與天命連接了起來,從而為性拓展出超越本能的形上韻味。孟子“性善論”中的“惻隱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羞惡之心”就是沿著這條思路產生的,即認為人不僅有來自本能的生命之情,而且有超越生命本能的道德之性。這就形成了
性與情的矛盾關系,于是在兩者之間就產生了誰主誰次、是分是合等問題。不同的回答代表著不同哲學派
①劉俊田等.四書全譯·盡心上[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604.
②徐芹庭.細說易經六十四卦·系辭上[M].北京:中國書店,1999:348.
③邵雍.皇極經世·觀物外篇[M].四部叢刊本.
④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8-149.
⑤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49.
⑥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50.
⑦孔穎達.禮記正義·樂記[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105.
⑧劉俊田等.四書全譯·中庸[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31.
33
別的基本性質。
儒家一直把情作為構建思想的立足點,如孔子的仁學就奠基在人對父母的孝敬之情上;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道始于情”一言就更表達得直接。并且,在儒家看來,性也是情,孟子所言的性之“四端”其實就是情感,只不過相對于自私的生理之情,這種情具有無私性和超越性。因此,儒家在性情關系上傾向于統一角度的理解。當然,儒家并不是直接融合了性情,相反在性情統一的基調下,它積極地探索兩者本質的區別。孟子說:“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知之于賢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①就是說,口目耳鼻四肢之類的生理欲望(情)和仁義禮智之類的道德之性雖都本屬于人,但君子把前者稱為命,后者稱為性。在孟子看來,命是一種“求無益于得也”②的外在必然力量,因而充滿盲目性;性則是“求有益于得也”③內在于人的必然力量,故而能把握,是人之尊嚴的終極依據。這就在價值等級序列上形成了落差,在兩者發生沖突時,孟子主張“舍生取義”。時至兩漢,性對情的價值優位作用逐漸被絕對化,例如董仲舒說:“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④又說:“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尊陰卑》)從表面看,這種“性善情惡”論徹底割裂了儒家一貫的性情統一觀點,但實際上并沒有,如《白虎通德論·性情》篇說:“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⑤正因此,儒家一方面強調性情相合,一方面又主張性對情的控制。這種認識最終成熟于由張載提出、朱熹系統演繹的“心統性情”思想中。朱熹說:“心統性情,蓋好善而惡惡,情也;而其所以為善而惡惡,性之節也。且如見惡而怒,見善而喜,這便是情之所發。至于喜其所當喜,而喜不過;怒其所當怒,而怒不過。以至哀樂愛惡欲皆能中節而無過,這便是性。”⑥就是說,性情都本具人心之中,情是表達人對物愛惡的欲望要求,性則是體現在情中的節度;而心則是由性情渾然一體過渡到“性其情”的橋梁,因為心有靈明知覺能力,“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⑦。因此,儒家既注重世俗生活,又強調以超越意義的倫理精神規范人的行為,從而形成“極高明而道中庸”⑧的人生態度。新晨
道家對性情關系的認識迥異于儒家。在老子哲學中,道家就以道為核心把“天之道”與“人之道”在價值范疇內對立起來,“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⑨。莊子也說:“何謂
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λυ因此,道家把由道而來的德或稱性,與
由人而來的情絕對對立起來:“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益生也。’”λϖ因此,道家主張“無欲”,要
求人徹底地從人的情欲中解放出來,回歸到“無待”的道德狀態。這就最終演化成道家消解自我意識的“坐忘”、“心齋”的思想。“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
①劉俊田等.四書全譯·盡心下[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613.
②劉俊田等.四書全譯·盡心上[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605.
③劉俊田等.四書全譯·盡心上[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607.
④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深察名號[M].北京:中華書局,1996:196.
⑤班固.白虎通德論[M].四部叢刊本.
⑥黎靖德.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94.2514.
⑦朱熹.四書集注·大學章句·補格物傳[M].上海:上海書店,1987:8.
⑧劉俊田等.四書全譯·中庸[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65.
⑨沙少海等.老子全譯·第七十七章[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278.
λυ楊柳橋.莊子譯估·在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40.
λϖ楊柳橋.莊子譯估·德充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10.
34
矣。’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謂
‘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后也。’”①可見,道家不僅否定了一般意義的情欲,而且連儒家標榜為性的仁義禮智也被排除了。而對待性情的這種態度,直接導致了道家消極避世的人生理念。
性情關系同樣是佛教哲學的基本問題。呂渟先生說:“印度佛學在原始的階段,即為確定實踐的依據,提出‘心性清凈’這一原則性的說法。⋯⋯人心之終于能擺脫煩惱的束縛,足見其自性(本質)不與煩惱同類,當然是清凈的。———這樣就構成了以明凈為心性的思想。”②又說:“這種思想通過印度的部派佛學、大乘佛學等階段,即逐漸有了發展。⋯⋯不過,以為人心自性不與煩惱同類的那一基本觀點是始終未曾改變的。③即是說,清凈的本性與無明貪念是佛教確立自我解脫和“人生即苦”思想的基礎。佛法東傳以后,中國化佛教更是談心性道德蔚然成風。但與印度佛教把性情決然對立情況不同的是,中國化佛教一直致力于調和清凈之性與無明之情的關系,如天臺宗的“性具善惡”和“貪欲即道”理論就是這種努力的結晶。禪宗更是把這種傾向發揮極致,如惠能說:“世人性自本凈,萬法從自性生”④。這就把佛性清凈轉化成人性本凈,而人性自不可免有情有欲,因此導致禪宗一改以往佛教出世修行的特點,主張不離人世生活的當下解脫。正由于這種認識,中國化佛教表現出很強烈的關注世俗生活的態度,而這是中印佛教精神的最根本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