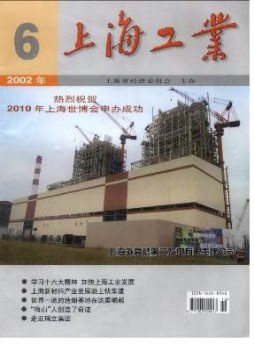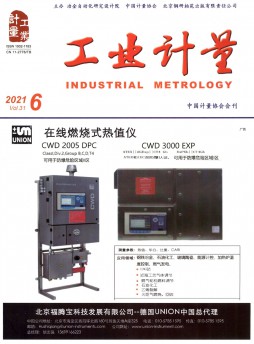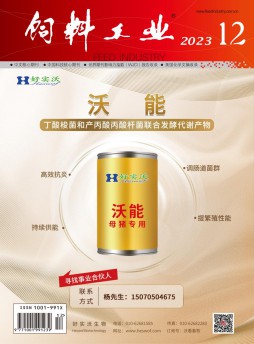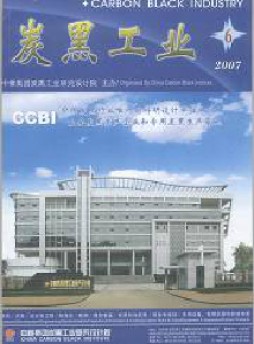工業協同管理本質及特性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工業協同管理本質及特性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研究21世紀工業領域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必須重視基于共生理念基礎上的工業生態協同管理。工業生態協同管理,既是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工業領域得以實施的必要條件,也是工業企業順應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必然途徑。有關它的討論,對我國工業企業界具有一定的重要參考價值。
一、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的基本含義
工業生態協同管理,是基于生態共生理念和前提,基于哈肯所說的協同學方法論基礎上,對工業企業自身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生產經營方式進行突破性轉變(與新老自由主義理論要求不同的轉變),進而實現工業企業綠色化調整,以防止庇古福利經濟學派所說的“負外部性”抑或“外部不經濟”的產生,并使之能夠行之有效地實現資源生態合理性優化配置的管理運作方式。這種方式,是在對經濟-社會-生態復合目標系統整體關系的全面認知,并對現存工業體系進行實質性相關改進或變革基礎上實現的。二、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的主要理論依據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的主要理論依據包括共生理念、協同學方法論、工業代謝理論和工業生態學等。在此僅就共生理念及協同學方法論的一些基本觀點進行討論。
(一)共生理念的形成背景及其對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的影響
對共生理念的研究,不只限于生態學領域,經濟學、政治學、以“超循環論方法”研究的進化論以及協同學等學科對之都有涉及。在經濟學范疇,美國學者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的《看得見的手》一書,似乎較有助于對企業共生理念形成的了解,但是它依然是以“經濟人假設前提”為特征討論問題的,所以理論上并不會對“外部性”內容有實質性解決。在環境倫理學領域,20世紀40年代,美國學者利奧波德在其“土地倫理學”中就有述及并強調。他指出:“事物在各種相互依存的個體向相互合作的模式發展的意向中,是有其根源的。生態學家把它稱為共生現象,政治學和經濟學則是提高了共生現象。在這種共生現象中,原有的自由競爭的一部分被帶有倫理意義的各種協調方式所取代了。”[1]而在以“超循環論方法”研究的進化論理論中,對共生概念的強調則更為突出。德國生物學家和系統科學家M•艾根20世紀70年代對此也有研究。艾根對共生問題的探討是針對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極端片面性展開的,他把達爾文進化論適當地引入分子進化的研究過程,同時進行必要的修正與補充。
在達爾文的理論中,自然界競爭和選擇的必然結果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這一思想在社會領域的代表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白哲特和薩姆納。而達爾文主義在經濟領域又直接影響到了古典經濟學派及其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直到今天,許多從事市場經營和企業管理的人員依然深受其影響。當然,這種影響無疑也來源于當今世界所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在此前提下,正像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他們“深深地陷入了這個競爭的旋渦不能自拔:如果你想生存下來,就必須擊敗對手,你必須在生存競爭中不停的斗爭,因為最大的成功者也就是最僥幸的‘幸存者’”。[2]這正是對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特征的陳述,是對今天“新自由主義”的風行及其本質的形象刻畫,也是對“新自由主義”適者生存理論實質的深刻揭示。
在可持續性發展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選擇的今天,世界各國都在對自由市場經濟及工業革命的嚴重弊端進行反思,而艾根則對達爾文的進化論從根本上做了批判性的改造。艾根認為,進化過程,不僅存在“競爭”與“選擇”,同時還存在另外一種進化的發展形式———共生。他指出:“進化過程無數復制和突變步驟造成大量分支的結果。這包括同源的競爭者之間的選擇,但也有躲入小環境中造成的隔離,還有十分溫和的選擇壓力下形成的互容或共生。”[3]因此,艾根在其《準物種模型》一文中,批評了達爾文的理論,他說:“達爾文自然選擇原理并非公理性的,而是從自我復制的物理條件中衍生出來的。”[4]
艾根援引了古恩特•斯登在《黃金時代的到來》中的話進一步批評指出,“如眾所周知,適者生存不是別的,只是同義反復:能夠生存的生存下來了,在這里,‘不適者’所代表的不是一個客觀的科學的價值判斷,而是主觀的價值判斷。”[5]
可見,無論是達爾文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還是那些奉行達爾文主義的自由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在工業革命以來,抑或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演進中,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的理論已經促成了許多社會問題的產生(比如1929年到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普遍出現的經濟危機,以及由新自由主義的推行導致的“拉美問題”,乃至當今世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它成了為強權政治、經濟掠奪、損人利己,甚至侵略戰爭辯護的理論。不僅如此,在自然生態領域,深受達爾文競爭理論激勵的無數極端自利的“經濟人”肇事者,其行為后果既造成了種種“外部不經濟”,也釀成了無數的生態災難和“公地悲劇”。不僅艾根的“超循環論”,就是在哈肯的“協同學”理論中,對達爾文的“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觀點同樣也有嚴厲的批評。哈肯在其專著《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不是最適者也能生存”一章中指出:“大自然設下無數的妙計,擊敗了適者生存這個論點”。值得注意的是,哈肯同樣也強調了“共生”概念。他說:“在激烈的生存斗爭中,一個特別有趣的例子是共生現象,其中不同的物種相互幫助,而且甚至只有這樣大家才可能生存。”[6]
但是,哈肯所說的共生,是指“種際”間的共生,在理論上,這與動物解放論者辛格提出的“種際公平”思想基本相似,區別前者是藉“共生”反映種際間的公平問題。艾根和哈肯對“共生”問題的研究,在理論上證明了這樣一個問題:競爭個體或群體,可通過彼此間的互利行為而存在。這一點對我們研究可持續發展管理來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極為重要。共生問題已經在世界范圍受到普遍重視,對它的研究將會引起我們觀念的深刻變化,并成為指導我們工作和實踐的一種新的理念。這種理念,不僅對糾正達爾文主義的偏頗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的研究不可或缺。研究工業生態協同管理,首先必須強調共生理念。只有基于共生理念基礎上的工業實踐活動,才能真正實現與自然生態總體平衡的協同或一致。
(二)協同學方法論與工業生態協同管理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的研究與實施過程,除了受共生理念的影響外,協同學方法論將發揮重要的作用。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盡管既不能脫離工業生態學及其物理基礎的相關研究成果,也不能脫離對自然生態系統關系的整體認知,但在工業領域若要全面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協同學方法論的指導將不可或缺。即使對研究工業生態物理基礎的工業生曄楓,馬青華:當代工業管理的協同學本質及其特征態學連同工業代謝理論來說,協同學方法同樣至關重要。
“協同學”是系統科學范疇的一個分支,為德國學者哈肯所創,其基本含義正如哈肯本人所解釋的,乃是“協調合作之學”。它指系統之中各子系統的動態協調與合作。協同使得系統具有整體性和穩定性,同時也反映出系統演化中的確定性與目的性。由于系統的協同作用,經協調后的各種矛盾達到整體統一,并將其整體功能加以放大,從而產生互補效應,使系統整體功能大于各個組成部分功能之和。協同學還研究大量子系統構成的宏觀行為,故僅從微觀層次的參量中難以了解這些宏觀量。在系統的演化中,并非所有參量對宏觀層次的各種表現發揮相同作用,只有系統協調合作時產生的序參量才具有決定意義。所謂序參量,就是指在系統相變過程中,能夠標識從無序到有序的狀態參量。它用系統宏觀量來表征,并決定系統的整體行為和特征。在協同學中,序參量是一個最基本的概念,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可刻畫支配系統演化的基本量度。
協同學對于研究工業生態協同管理大有裨益。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的基本宗旨,就是要通過協同學協調合作之方法,使現存工業經濟體系擺脫傳統經濟理論的桎梏,從而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總體平衡相一致。傳統的工業經濟體系,導致了自然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衡。這種情況如果說是因其僅僅側重遵從經濟規律而忽略自然生態系統的客觀要求所致,那么工業生態協同管理則必須以此為戒。現存的工業體系只有藉協同學方法論將之融入自然生態系統時,才能真正實現工業生態協同管理。工業生態協同管理不僅要遵循經濟規律,而且要遵循自然法則。工業生態協同管理同樣是一種新的相變過程,一種能夠標識從無序到有序的狀態參量,它將以一種新的序參量支配我們時代的工業整體行為和過程。
三、對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研究內容的大體劃分
任何劃分都以一定的標準來進行,對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研究內容的劃分也不例外,依據一定標準對其劃分,便于我們區分它所研究對象的不同特征。
(一)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的劃分內容
在此,我們將以企業自身的協同運作和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協同運作為標準進行大體劃分,以便厘清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的內外差別。這一陳述的另外方式便是:以一個或若干工業行為主體為劃分標準,可分為“工業內生態協同管理”和“工業外生態協同管理”兩個方面。
1.工業內生態協同管理這是指工業經濟行為主體以生態環境保護為目標,以綠色化科技創新為支撐,對工業企業自身各個生產環節進行系統改造或調整的一種管理。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相一致或與生態系統總體平衡協同是這種管理的基本特征。我國魯北化工集團,以生態環境保護為目標,以綠色化科技進步為支撐,對其內部進行了系統變革,創建了磷銨、硫酸、水泥聯合生產的工業生態鏈就是典型的內生態協同管理案例。這是我國第一套磷銨、硫酸、水泥聯合生產裝置。其工藝流程是:用生產磷銨所排放的廢渣(磷石膏)制成硫酸,進而聯產水泥;硫酸再返回運用于生產磷銨,以致整個生產過程無廢料排出,使自然資源得以充分和高效利用,真正達到了“因子x”理論現共時態的整體要求。它既解決了傳統磷銨生產廢渣占地和污染環境的世界性難題,又有了生產硫酸和水泥的新的原料來源。[7]魯北化工企業集團充分實現了內生態協同管理。
2.工業外生態協同管理若干不同工業企業行為主體之間,以生態環境保護或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為目標,相互間進行優勢互補或資源生態合理性優化配置,從而在整體上與自然生態系統平衡相適應的叫工業外生態協同管理。丹麥卡倫堡工業生態園區,就是典型的工業外生態協同管理案例。該園區是由若干各不相同的工業企業,即斯塔朵爾煉油廠、阿斯耐斯瓦爾蓋發電廠、挪伏•挪爾迪斯克生物工程公司及吉普洛克石膏材料公司等等所組成的工業生態共生體。卡倫堡共生體的協同運作方式是:用煉油廠排出的水冷卻電廠的發電組;電廠的廢蒸汽又供給煉油廠、生物工程公司發酵池及市政分區采暖;電廠在其機組上安裝了脫硫裝置,使燃燒氣體中的硫與石灰產生化學反應,生成的硫酸鈣(石膏)供應石膏材料廠,從而使材料廠不再進口西班牙的天然石膏。這既節省了自然資源,又利用了廢棄物。此外,煉油廠的多余燃氣又可作為燃料供應電廠和石膏材料廠之用等等。[8]正是這樣,卡倫堡共生體通過不同企業間的協同運作,使每個企業均毫無例外地實現了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優化結果。
(二)魯北化工集團與卡倫堡可產生的效益情況
無論魯北化工集團的內生態協同管理,還是卡倫堡工業共生園區的外生態協同管理,均已改變了以往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工業化發展理念。共生理念和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的運作方式,使得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明顯可見。以魯北化工集團為例,其經驗倘若推及全國,則每年可節約磷石膏廢渣堆建費6000萬元,節省800萬噸水泥的石灰石礦山建設費21億元,節省生產600萬噸硫酸的硫鐵礦礦山建設費30億元。[7]此外,該集團的內生態協同管理運作方式尚可避免產生污染環境的廢棄物。卡倫堡的效益狀況也表明,它們每年可節約45000噸石油,15000噸煤炭,50000立方米水;溫室氣體排放也有所減少,每年可少排175000噸二氧化碳和10200噸二氧化硫;廢棄物重復利用情況是:每年可利用130000噸煤炭、4500噸硫、90000噸石膏、1440噸氮、600噸磷等等。[8]這些情況都說明,假如全世界的所有工業企業都能真正實現工業生態協同管理,那么,“因子10(Factor10)”(資源能源利用效率必須在1990年的基礎上擴大10倍才能滿足人類目前可持續發展要求)的近期目標將由設想變為現實,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無疑是現實可行的。
四、研究工業生態協同管理的現實意義
研究工業生態協同管理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現實意義。首先,對于所有工業企業來講,只要把順應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自身的奮斗目標,則共生理念和工業企業協同管理就是必須的。因為,共生理念將導致傳統“經濟人觀念”的改變,而工業生態協同管理則會有助于對企業進行生態合理性的變革。故此,它們都是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的必要條件,對于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來說,無疑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其次,研究工業生態協同管理,對于當前我國企業戰略重組,協同應對市場經濟的各種挑戰,突破發達國家苛刻的貿易堡壘,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內生態協同管理,可使企業挖掘自身潛力、積極創新、降低成本、提高資源利用率,并使其生存能力大為增強。外生態協同管理,則可增強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力,使每個企業都能節約自然資源,成本代價也會大為降低,因而它可從整體上增強國際競爭能力。再次,工業生態協同管理可使由于結構調整或市場競爭原因導致的弱勢企業找到新的生存契機。在共生理念基礎上的工業生態協同管理,將使不同的企業形成優勢互補,不僅“強強聯合”得以生存,而且“強弱聯合”,乃至“弱弱聯合”亦可在協同運作方式基礎上共生。顯然,這將從根本上糾正那種片面的、“經濟人”式的所謂“強強聯合”的理論弊端。
總之,工業生態協同管理,是對傳統工業管理學的一種理論上的變革和揚棄。傳統的工業管理學并不足以實現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理論上的改進,因為它是以西方市場經濟管理學的“經濟人假設”為前提的。這種理論,除了滿足“經濟人自身利潤最大化”的要求外,其管理行為的“負外部性”結果,并不被納入認識視野。因此,對它來說,除了更有效地促使“經濟人組織”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以外,就是造成十分嚴重的“外部不經濟”。“外部不經濟”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以及在“新自由主義風行”的當今世界,所有“經濟人式企業管理”的最顯著特征。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地球生態家園才出現了許多的災難性結果抑或“公地悲劇”。而傳統的管理學理論從來沒有對其理論后果負任何責任。今天我們對傳統管理理論的批判性分析,正是要對之有清醒的認識。毋庸置疑,只有基于共生理念和原則基礎上的工業生態協同管理,方有助于對“經濟人行為”的“負外部性結果”進行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