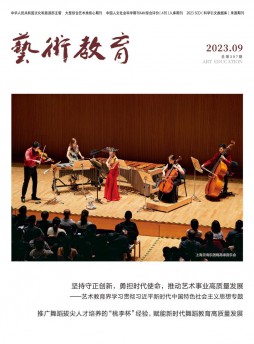教育公平視角的民族英語教育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教育公平視角的民族英語教育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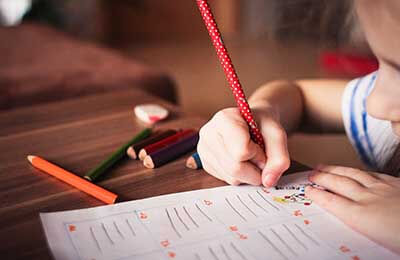
一、過度的語言課程在遮蔽或架空民族教育的內涵和功能
20世紀70年代末,英語作為第一外語,逐漸進入全國的大、中、小學課堂。1984年,在國家政策和教育改革的雙重影響下,英語正式列入高考主科,此后幾十年里,英語成為必不可少的考試科目,從小到大,從中、高考到雅思、托福、四六級,每個中國學生都要經歷無數次英語考試。英語本應是溝通外界的橋梁,卻成為應試教育的沉重負擔。直到最近英語高考改革方案的提出,才使得“英語熱”有了降溫的趨勢。2013年10月,山東省教育局公布的2014年普通高校考試招生工作實施方案中提出,不再將英語聽力成績納入高考成績中;北京市在2016年將中考語文卷總分值由120分增加到150分,英語卷總分值由120分減至100分。我國長期以來實施的英語教育只以語言輸入為主,脫離學生經驗與真實生活,孤立而被動地強調語言技能訓練。此次英語教育政策的重大調整實質上反映了對傳統的、應試的、功利的、受技術理性支配的教育理念的批判,對回歸教育為本的、解放性的、實踐性的教學理念的反思與重建。盡管社會各界對英語教育改革持不同意見和態度,但這次改革毫無疑問將成為我國教育教學改革中的一次“大手術”。
對少數民族教育的認識,有幾種誤區一直存在。首先,將“少數民族教育”等同于“少數民族語言教育”,認為少數民族學生學業成就的標志就是學好語言課程,尤其是漢語和英語,認為少數民族學校的教育教學活動就是以學習語言為主。其次,把“少數民族雙語教育”或“三語教育”理解為“專門的語言教育”,認為“雙語教育”或“三語教育”的重要標志就是學習正確發音、積累詞匯、學習各種句式,強調專門的語言技能訓練,以量化形式作為教學質量的衡量標準。這些誤區導致民族教育在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忽視了學科知識與語言學習的平衡關系,也忽視了語言學習與文化理解的相互關系。內蒙古三語教學的實踐證明,比兩種語言學習付出成倍辛勞的三種語言學習過程,只能培養極少部分三語能力均衡的少數民族學生,對于大多數學生而言,語言學習并沒有成為教育和發展認知的有效資源。過重的語言學習負擔使學生失去了學習其他科學知識和發展個人興趣的時間與精力。內蒙古的蒙古族小學在開設英語課程之前,蒙古語文與漢語周課時數就已經占周總課時數大約30%。隨著英語課程的增設,三種語言的周課時累計數已達到總周課時數的37%,其語言課程比重比同年級(小學三年級)漢族小學的30%、香港小學的27.5%、美國小學的20%、日本小學的18.5%高出很多。
內蒙古民族學校高中階段“三語實驗班”的語言課程中,英語課時數占總課時數的19%,漢語課時數占總課數時的14%,而蒙古語課時數比例下降到7%。這種為保證漢語與英語課程的數量及質量而忽視母語教育的現象在內蒙古的各級民族學校普遍存在。“三語實驗班”與普通班課程設置的最大區別在于英語課時數及蒙古語課時數的不同。這些課時數的變化不只是量的變化,其背后隱藏的實質是民族教育的潛在危機。不可否認,“三語實驗班”的課程設置能夠幫助極少部分三語能力均衡的民族學生在高考和就業中處于有利地位,從而提高他們的社會競爭力。然而對于大多數學生而言,一方面語言教育的過度重視影響了學生的學科均衡發展,占據了學生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另一方面在語言教育教學中過度重視英語而忽視母語的現象會削弱他們的社會競爭力,使民族學生最終成為三種語言哪樣都不精的“語言中間人”,甚至是“文化中間人”,從而很難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生存發展,逐漸走向教育的邊緣,進一步加深教育不公平。這不僅違背了語言教學的規律,也違背了人的發展規律,更重要的是遮蔽或架空了民族教育的實質內涵與功能。對少數民族成員而言,獲得實用的語言技能無疑是等同于獲得個人及所屬社會發展的重要機遇。在我國,漢語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們之間交流的重要工具,英語則是通往世界的重要工具。然而,只專注于實用語言對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會導致少數民族失去自己的語言文化,甚至失去認同感的危機。
二、以漢語為媒介語的英語教學可能導致更嚴重的教育不公平
媒介語指教學過程中傳遞知識的中介語言,既不同于學習者的母語,也不同于目標語的中間過渡性質的語言。任何一種語言都負載著其民族的思維方式、思想情感、傳承者民族綿延不息的文化。因此,任何多民族,多語言國家都會在教育發展中遇到教師用何種語言教學,教材用何種語言編寫等難題。究竟哪種語言適合在課堂上使用的爭論一直沒有定論,因為這是一個涉及文化、種族、權利和身份的較量。1970年美國公立學校的中國學生反對在教育上受到起點不公平的教育方式,而控告舊金山聯合區域學校。這場震撼全美、影響深遠,從而促進雙語教育在全美蓬勃發展的“勞控告尼克爾斯訴訟案”(Lauv.Nichols),雙方爭論的焦點并不是中國學生因為校方沒有為其開設相應的課程而導致他們學習困擾這個事實,而是當使用中國學生不了解的語言來指導學習時,中國學生是否得到公平教育的機會。控告方認為盡管校方為中國學生提供了與其他學生相同的設備、書本、老師和課程,但這不等于公平待遇。事實證明,中國學生相對于英語語系的學生獲益較少。最終最高法院要求學校當局推行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雙語教育和雙文化教育。世界很多國家,少數民族教育質量低下一直是不爭的事實[2]。在中國,少數民族學生的英語學業成就一直低于漢族學生。國內很多相關研究有效地論證過媒介語言的選擇是影響少數民族英語學習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克勇(2007)、張宏偉(2013)關于少數民族大學生英語學習策略的研究以及馬麗范(2006)、蔣燕(2013)、龔江平(2009)、烏力吉(2006)關于青海、貴州、西藏、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學生英語學習障礙的相關研究等。內蒙古的蒙古族學校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同時加授漢語和英語課程(有些學校在二年級時加授漢語,三年級時加授英語)。其中,第三語言英語的學習是在“三語教育”體制下,以第二語言為媒介語展開的。語言學家JamesCommins提出:人的兩種形態的語言能力,分別是一般生活的語言能力BICS(BasicInterpersonalCommunicativeskills)和認知學習的語言能力CALP(CognitiveAcademicLanguageProficiency)。用JamesCommins的理論分析我國少數民族學生英語學業成績低下的原因就會發現,長期以來我們對不同學習階段不同少數民族學習者的漢語水平缺乏正確客觀的評估,盲目認為少數民族學生可以用漢語交流(BICS)就可以用漢語授課(CALP)。除此之外,在教學中少數民族兒童認知能力發展的最大困難,是母語表征的感性經驗和認知結構在以漢語為中介的教學過程中難以被感知,少數民族生活、生產的世界,他們的歷史、文化和語言的特征很難在教學中呈現顯性化[2]。少數民族學生學習第二語言或第三語言,并不是要放棄第一語言,而是要多具備一種語言表達能力,多一種溝通的頻道。目前的民族學校英語課程如果以漢語作為媒介語,我們不免擔憂其他科目是否也有可能逐漸轉向漢語授課。那么,不久的將來,作為民族教育核心的民族語言可能就會被抽離,民族學校承載民族文化、傳遞民族文化的功能也會隨之消失。民族最重要的內涵是尊嚴平等和文化公平傳承,失去本民族文化傳承的最重要的場所,被文化邊緣化的少數民族學生將成為現代教育的最大犧牲品,教育差距將進一步擴大。
三、對策及建議
(一)探索少數民族英語教育自身規律,以多學科理論指導三語教學少數民族英語教育能否取得成效的必要前提是當前實施的民族教育是否遵循三語教育教學的規律、少數民族學生的認知發展規律以及少數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顯然,只用語言學理論去解決少數民族英語教育問題過于片面、狹窄。這里至少提出了教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視角。我國著名的蒙古語學者清格爾泰經過研究認為:現行的蒙古文字是一種純粹的拼音字,它在拼音的方法上與西歐以及世界各主要拼音文字沒有什么不同。不但如此,從它的淵源關系來說,他也是從世界各主要拼音文字的共同祖先腓尼基字母演變而來的。母語與目的語如果具有同源關系、相近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語言特征,就會促進目的語的學習,形成“正遷移”。相反,母語與目的語間的差異將阻礙目的語的學習,形成“負遷移”。因此,以蒙語為母語的學生學習英語比漢族學生占優勢[3]。該理論突破語言學單一的視角,從語言與社會、歷史、文化的關系深刻論證了蒙古族學生學習英語的優勢所在。同時,這也說明蒙古族學生用母語學習英語比用漢語等媒介語言學習英語更有優勢,為民族學校選用何種語言教授英語這一問題提供可參考的理論依據。縱觀國內關于少數民族雙語或三語教育相關的研究,基本限于現狀的描寫或經驗分析,缺乏理論支撐以及地方性特征對教學模式、課程結構、師資配備、教材選用等方面充分的分析和考量。除此之外,雙語或三語教育的研究依然局限在語言學本體研究或語言教育技術等狹窄領域里,這使得少數民族學校在使用何種語言教學、使用何種語言編寫的教材、第二語言或第三語言課程從哪個年級開始設置較為科學、語言之間的遷移等問題上爭論不休,各持己見。筆者認為,解決上述問題的瓶頸在于跳出語言教育的范疇,從歷史、文化、社會,甚至更廣泛的領域中去審視和思考問題,解決內蒙古民族教育問題就必須遵循并揭示蒙古族教育在課程特征、語言價值和文化追求方面特殊的、復雜的發展規律,同時深刻了解與分析內蒙古蒙古族當今所處社會狀況以及整體的教育狀態。
(二)尊重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特征,科學設置三語教育課程框架制定宏觀的學術標準和測試手段時,充分認識到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特征,給予各民族地區更多靈活性和自主權。同時,各民族地區可出臺特殊政策與富有競爭能力的獎勵基金而不是補助金的方式,鼓勵并幫助民族學校建設適合當地民族學生特點要求的學科與課程。少數民族學校可以根據這些學科學習以及學校活動來配置國家課程、地方課程、校本課程的比例,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權去改變課程結構,以滿足不同區域和不同背景的少數民族學生的需要。在具體的教學科目設計上,改變當前過度強調語言課程的狹義的教學傾向和忽視科學、社會、藝術等更廣泛的教育目的,同時增加了解人和社會的生命教育課程。如香港小學的多元智能課、多元學習活動課、視覺藝術課等,日本小學的生活課、家庭課、社會課等,美國小學的環境教育、反教育、多元文化和多種族教育等值得借鑒。語言課程應該注重培養學生學習語言的興趣及良好的學習態度與方法,強化“文化”的語言教育,而不是重“語”輕“文”的教學觀念。除此之外,在課程體系中安排適當的生活實踐課程。比如,西部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工作中,內蒙古的有些地區過多地撤并牧區學校,片面推行“學校進城”,致使蒙古族兒童遠離牧區環境和母文化。合并后的城鎮蒙古族學校課程往往很少涉及牧區文化、生產和生活方式相關內容。這使很多不能繼續升學的來自牧區的蒙古族學生成為文化“邊緣人”,從而擴大了教育差距。
因此建議把鄉土教材的開發及其教師隊伍培養納入國家和地方教育公共資源分配中,國家和地方財政明確承擔鄉土教材的開發、印刷及人才培訓等方面的資金。在教材建設中,也要杜絕全盤搬用漢語教材的做法,充分考量以少數民族語言為母語的學生把漢語當作第二語言進行學習的特點和規律。教育要適應社會經濟的需要,滿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需要,不僅追求公平的發展,也要追求有質量的發展。少數民族學生有著獨特文化中的行為規范和價值體系,尊重少數民族學生的民族文化與傳統,了解他們的學習能力與需求,才能解決民族教育中的實際問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公平。
作者:塔娜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公共外語教育學院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
擴展閱讀
- 1創業教育實踐教育
- 2教育策略教育統計運用
- 3合唱教育與藝術教育
- 4中職教育中的感恩教育
- 5教育傳統與教育創新
- 6教育局教育計劃
- 7教育思想
- 8教育目
- 9藝術教育
- 10教育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