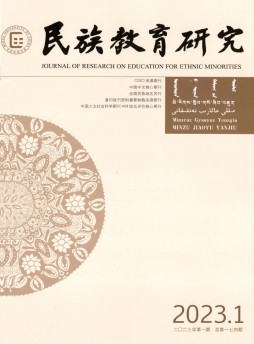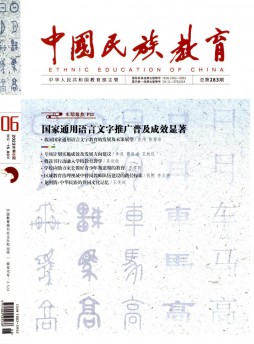民族教育共同體的價值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族教育共同體的價值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教育意圖在民間的貫徹
本文將援引火塘文化,即以實體范疇的民族所獨自擁有的特殊的教育方式為例,在于說明教育共同體的意圖如何在民間得以行之有效地貫徹。在此引述的火塘文化,產生于火被引進到人類的居室之后所形成的火塘。這個例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追蹤原始教育的意味,實際是在作民族教育發生學的探究。將野火從荒野的熊熊烈火引進人類的居室空間,的確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它在方寸之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靈性世界,從而被賦予更多的人文色彩。
在此無意去做人類學意義上的民俗追蹤,而是著重在火塘所蘊含的教育內涵上,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復雜多元的人類社會生活的綜合性文化象征實體如何擔待起教育共同體的責任。火塘首先是少數民族家居生活的中心,同時兼具社會性活動的中心。祭神、祭祖在這里展開,民族音樂在這里吟唱,美德故事在這里宣講,它將神性、靈性與溫暖的氣氛融合在一起,將民族成員吸引到火塘前。摩梭人的成年禮在火塘邊舉行,而且巫師和老人必須吟唱這樣的祝吉歌:“小樹苗變成大樹了,小孩子變成大人了。今天是吉祥的日子,阿鐵日爾穿上了褲子。祝他像天邊的大雁,能活一百歲,祝他像海里的野鴨,能活一千歲。在家能犁地,出門能攆山,戰場上英勇殺敵,戰無不勝。刀子是你的伙伴,讓他陪伴著你,戰勝虎豹,趕走魔鬼。”
這是一個典型的具有教化意味的場景,它由普通的家庭成員和成年禮這樣一種獨特的教育活動結成特殊的教育共同體,這個教育共同體的倫理特質不只是顯現為倫理性的實體,而且還顯示出它是造就倫理性的實體。它授人道德知識,完成倫理使命,成就教育權威。再以納西族、景頗族在火塘邊傾訴哀思、頌揚故人的《雞鳴祭歌》、《挽歌》為例:“雞叫了,云中的白鶴已醒來,它們抖一抖潔白的翅膀,搖一搖美麗的尾羽,向高空雙雙飛去了。阿爸阿媽呀,請你起來吧!雞叫了,碧海里的野鴨和鴛鴦已醒來,它們輕捷地在水中嬉戲,阿爸阿媽呀,請你起來吧,起來洗臉吧,起來喝茶吧!”“你先去了,不要悲傷,不要難過,萬物都會死的,星星也會落下,太陽會落山,月亮會落坡,牛老會縮角,你活在世上時,教會我們勞動生產,你的名字像金子一樣發光,你沒做完的事我們接著做。”
諸如此類的吟唱多使用比興的手法,它有文學活動的意味,但更多的是傳達教育共同體的意圖。正如歌詞中所吟唱道:“你活在世上時,教會我們勞動生產,你的名字像金子一樣發光,你沒有做完的事我們接著做。”這個圍繞火塘、基于家庭而生的教育共同體實際上就是一個鮮活的倫理實體,它在倫理精神的培育中具有根源性的意義。對此意義的審理還將引導我們做出家庭實乃倫理精神的根源的判斷。因此,由上述民族的教育場景可推知,無論是對于族類共同體的理想的實現,或是對于個體實現從現實世界向可能世界的轉換,教育共同體都有出色的表現和作為。
二、教育共同體的道德力
從倫理與教育的互生關系出發,可以考查教育共同體的道德力,即它對于個體上的道德牽引如何得以有效展開。高兆明指出共同體是黑格爾在事實上將之作為價值合理性的根據,并從共同體中尋求對倫理關系與倫理秩序的理解,甚至可以說共同體就是把握倫理關系與倫理秩序的鑰匙。因此,研究嘗試將所言及之民族倫理的主體———民族視作教育共同體,從而展開我們對于道德力的討論。民族是否堪稱我們在此所言之教育共同體呢?這首先要從我們已經放大了的教育共同體的定義來判定。教育共同體的多樣性在于生活領域、生活層次的多樣性。不同的生活領域、生活層次有不同的具體的教育共同體,在哪個特定領域與特定層次,它們都是合理的。顯然,民族是否堪任教育共同體的疑問,可由教育共同體的多樣性內涵來得以解答。
在此的求證得到解決以后,所要集中論證的是作為族類共同體的民族,如何展示自身最基礎、最普遍的社會關系,如何真資格地充當教育共同體的重任?試以苗族知識分子梁聚武先生關于禮俗的論述為例。他在回答“我們需要什么禮俗”中,反思了各民族的禮俗,指正了彼此的優劣。他對于喪葬,這樣評論道:“若把一具尸體放在家里,請道士,請陰陽,迎神點祖,鬧個不休,這樣一來,真是花錢不少,對于衛生方面,也是成了問題,影響自己,影響鄉里,影響社會,不能不說是一件應該特別注意的大事。”
他還認為,對于婚嫁喪葬,斥簡陋為不進化,而以多玩幾個花樣為文明。這樣的文明,不見得可能適應現代環境的需要。他還指出,不要完全站在個人的立場或家族、宗族的立場,而忽視了國家的民族的利益。梁先生在闡發這通議論的時候,抗日戰爭尚未勝利,但他作為民間知識分子,已在身體力行地大行教化之力,希望抗戰勝利之后,可以以各族的禮俗為基礎,形成“國族”的禮俗,做通盤的考慮。作為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梁先生的以上思想作為教育共同體的精神內核,一度影響了苗族的一代代青年。
此引述的用意在于真實地呈現民間禮俗所蘊蓄的德性力量,并較為充分地展示了它所完成的德性牽引。黑格爾說:“一個人必須做些什么,應該盡些什么義務,才能成為有德的人,這在倫理性的共同體中是容易談出的:他只須做在他的環境中所已指出的、明確的和他所熟知的事就行了。”
這個引述中的梁聚武先生所流露出的德性品質就來源于他所在的、所熟知的苗族社會。筆者更看重的是他從善的動機從何而來?其實,我們只需堅信:雖則個體因其有限的理性存在并不如像服從自然法則一般地必然恪守道德法則,但是只需個體自覺其為理性的存在,就必定會不囿于感性自然的束縛而依定言命令行事,而此道德法則直面一切理性存在而生的效力,就是道德力無疑。
而這個道德力原生于教育共同體,作用于道德個體,從外在于個體的異在,換化為內在于個體的德性,從而圓滿地完成教育共同體所要承擔的教育重任。
作者:毛越華單位:貴陽護理職業學院
- 上一篇:工程施工中管理部門的重要性范文
- 下一篇:民族教育的實踐與探微范文
擴展閱讀
- 1民族旅游與民族文化論文
- 2民族品牌戰略
- 3傳播民族志
- 4民族品牌戰略
- 5藝術民族性
- 6民族企業官商關系
- 7民族地區旅游
- 8民族主義情結
- 9民族科技提升近況評估
- 10民族文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