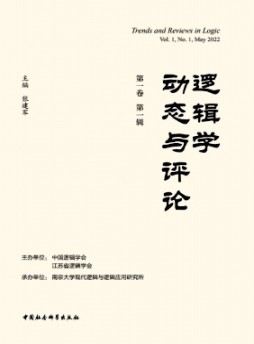邏輯學不連貫性問題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邏輯學不連貫性問題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邏輯學》系統連貫性的標準
正如上文所述,黑格爾關于《邏輯學》的構想是通過一個自身構建自身的“存有論核心”(selbstkonstruierenderOntologiekern)來引領思維的自身運動過程。那么,當其中個別環節之間出現了邏輯不連貫性問題時,一種有效的解決路徑應該首先假設《邏輯學》是一個完整的系統。而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其組成部分之間必須是相恰的,而各個組成部分自身也都是必要的。這對于展開為一個發展過程的《邏輯學》而言就意味著諸環節之間的連貫性以及各個環節自身的必要性。事實上,所謂的邏輯不連貫性問題也并不僅僅存在于有論和本質論之間。長久以來,學界也一直對其他環節之間的邏輯連貫性存在著爭議。例如,在有論的開端:一方面,作為《邏輯學》的第一個環節,“純粹的有”(reinesSein)是一個不可回溯的、絕對的存有論事實(SachverhaltderOntologie);而另一方面,它作為一個純粹的開端卻又能獨立地從自身給出新的環節,即“無”和“變”。然而,同時要將這兩個方面都包含在“純粹的有”這一環節中卻存在著很大的困難。
倘若將這一位于有論開端的邏輯不連貫性問題與之前的問題同時置于系統的語境下整體地考察,就不難發現:前者的問題在于,當一個環節作為一個無前提的開端時,其產生后續環節的能力無法與其純粹性相統一;而后者的困難則在于難以統一“本質”對先行環節的連續性與其相對于“有”的獨立性。換言之,所謂的邏輯不連貫性問題都根源于以下兩個方面之間的根本矛盾:《邏輯學》中思維自身運動過程的連貫性以及這一過程中各個階段的獨立性。這兩個方面構成了邏輯不連貫性問題,同時也就構成了任何一種對這一問題的有效的解決路徑都必須滿足的標準。在下文中,本文作者將基于這一標準,通過對現有解決路徑的系統性考察來反證同時滿足以上兩個有效性標準的必要性。1.第一種解決路徑:貫穿不同階段的基礎結構第一種解決路徑嘗試通過對《邏輯學》展開過程中個別階段的分析得出一個可以同樣應用于其他階段的基礎結構。倘若所有階段都是基于同一個結構構建的,那么,它們就可以被歸納并還原到這一基礎結構上,從而也就不存在所謂的邏輯不連貫性問題。簡言之,這種解決路徑將《邏輯學》中思維自身運動過程的連貫性置于個別階段的獨立性之前。其代表是ThomasKesselring對有論開端的重構。Kesselring的解決路徑的關鍵在于將有論的開端置于和本質論的開端的類比中,通過將本質論開端才出現的“外在的反思”(dieuβereReflexion)引入有論的開端來區分黑格爾所系統性地混淆的三個層次:“所思(Gedanke)的層次,思維本身的層次和黑格爾的表述以及對于這一表述的一般性理解的層次。”①“外在的反思”所對應的正是第三個層次。基于這一區分,Kesselring指出,作為《邏輯學》開端的任務,思維思維本身(dasDenkenalssolcheszudenken)毋寧是對前兩個層次的混淆。從第三個層次,即“外在的反思”的視角來看,這一混淆導致了第一個二律背反,即黑格爾所謂的“純粹的有”,因為對思維本身的思維本身也是一種主觀思維,在不考察理論前提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內在于理論本身表達出一個理論與其目標域之間的關系的”。②因此,要么思維本身,即“純粹的有”是無規定性的(unbestimmt),但無規定性本身也是一種規定;要么“有”是被規定的,而這又與其無規定性相矛盾。這一二律背反只有通過抽離思維思維本身的主觀思維,將無規定性視為沒有規定時才能被消解。而這一抽離又會導致第二個二律背反,即黑格爾所謂的“無”,因為對思維本身的抽離本身也是一種主觀思維。因此,要么沒有任何規定,即“無”,但沒有規定本身也是一種規定性;要么有規定性,而這又與沒有規定相矛盾。要消解這一二律背反就必須恢復主觀思維,將沒有規定視為無規定性。然而,這一恢復又會再次導致二律背反A。因此,兩個二律背反相互過渡到對方,它們共同構成了第三個二律背反,即黑格爾所謂的“變”。盡管Kesselring的解決路徑統一了“純粹的有”產生后續環節的能力與其純粹性兩個方面,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將“外在的反思”引入有論的開端使Kesselring能夠區分被黑格爾系統性地混淆的三個層次并統一“純粹的有”的兩個方面;否則,第一個層次和第二個層次是無法從自身內部加以區分的。然而,“外在的反思”是直到本質論才出現的環節,這一解決路徑無疑忽視了有論和本質論之間的根本性區別,取消了各自的獨立性,因為在有論中還未被思維反思的、主客體之間的“相異性”和本該在本質論的開端才出現的“外在的反思”被混淆了。首先,缺乏對這兩者的區分將使后續階段的獨立性和必要性陷入質疑:既然在有論開端就已經出現了“外在的反思”,那么,本質論的必要性何在?對此,Kesselring在文章中也同樣提出了疑問:“似乎并不需要本質論來厘清在有論開端被混淆的三個層次。”③然而,除了“為了貫徹辯證運動的三分法”這一牽強的理由之外,Kesselring始終都沒能對其解決路徑所帶來的問題做出充分的解釋。其次,就有論的開端本身而言,倘若單純地從“外在的反思”的視角來考察“直接性本身”(Unmit-telbarkeitalssolche),那么,后者也就不再是“直接性本身”了。假設Kesselring的解決路徑是可行的,那么,在有論中出現的毋寧就是反思的結果,即“被建立起來之有”(Gesetztsein)和“被事先建立起來之有”(Vorausgesetztsein)。而這兩者的含義與有論中的“直接性本身”的含義完全不同。正如Henrich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永遠無法揚棄作為《邏輯學》整體的開端的直接性,也永遠無法通過后續更加豐富的結構來充分地解釋它。”④因此,“任何一種基于《邏輯學》后續階段來尋找有論開端真正的核心和動力的路徑”⑤都是不允許的。類比于Kesselring的解決路徑,筆者還可以舉出許多類似的解決路徑,例如,基于概念論第一部分“第二章:判斷”的結構來重構有論的開端,或者將《邏輯學》的最后一章,即概念論第三部分“第三章:絕對理念”理解為所有在先行的階段中被遮蔽的原則的顯現,以此類推。但正如上文所述,所有這些路徑都將無一例外地陷入同樣的困境。2.第二種解決路徑:以個別階段的獨立性為前提和第一種解決路徑相反,第二種解決路徑將個別階段的獨立性作為前提,置于《邏輯學》中思維自身運動過程的連貫性之前。其代表是Henrich對本質論開端的重構。Henrich首先預設了有論和本質論結構上的不同。黑格爾在有論中用以展開思維自身運動的考察方式(Explikationsmittel)本身在本質論中成為了考察的對象。具體而言,在有論中,“現有的東西”(das,wasvorhandenist)①還只是被直接性地把握,是“作為對與他物關聯的否定的直接性”(U1)。在有論的結尾和本質論的開端,思維通過對作為U1的否定物的否定得以反思這一作為考察方式的“直接性本身”,而“直接性”也由此成為了“作為否定的自身關聯的直接性”(U2)。也就是說,“映象”(Schein)的直接性特征在否定的自身關聯,即“本質”中被重新發現了。Henrich稱之為“意義推移”(Be-deutungsverschiebung,U1→U2)。然而,被反思的“直接性”也就不再是“直接性本身”了,而是被反思的考察方式,即“否定的自身關聯”。也就是說,“映象”的規定性通過U1和U2之間結構的等同被轉移到“本質”的規定性中了。Henrich稱之為“意義等同”(Bedeutungsidentifikation,U1=U2)。這一被Henrich稱為“思想實驗”的解決路徑統一了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本質”避免了成為“被建立起來之有”建立的“本質”。相反,通過“意義等同”,它與“映象”共同構成了一個獨立的“本質結構”的兩個方面;否則,“我們就無法將‘本質’作為一個自身充分的思想進行概念地把握”。②另一方面,通過“意義推移”,“本質結構”也在保持獨立性的同時繼續作為“直接性結構”的后續概念而存在;否則,在這兩個結構之間就存在著斷裂,而“自身為自身奠基的思維自身發展也不再可能了”③(見表2)。盡管如此,這一解決路徑仍然會帶來新的問題。如上文所述,既然作為系統的《邏輯學》展開為一個發展過程,那么,它首先就必須是連貫的。而按照黑格爾的構想,它還是思維的自身運動過程。因此,這就必然地要求能夠從黑格爾在其開端預先設置的前提引出一種能夠貫穿有論、本質論和概念論的考察方式,使得其中每個階段都能獨立地從自身給出后續的階段,從而保證整個過程的邏輯連貫性。然而,黑格爾又同時堅持認為《邏輯學》在有論、本質論和概念論之間進行了方法的轉換。正因如此,Henrich對在思維自身運動過程的語境下保持邏輯連貫性的可能性提出了質疑:“從來沒有人能夠借助某種可以解開《邏輯學》秘密的關鍵得出一個可以為整個《邏輯學》的文本奠基并從而實現一種合理解釋的機制。”④在他看來,倘若嚴格地遵循黑格爾的構想,就會必然地陷入矛盾:要么堅持《邏輯學》三個部分之間方法的不同,那么,其展開過程就不能被視為思維的自身運動過程,因為不可能存在一種考察方式能夠獨立地從自身給出一種與其自身不同的考察方式,以此類推;要么將《邏輯學》視為思維的自身運動過程,那么也就無法進一步將這一過程作為整體來進行重構,因為“使《邏輯學》中每一個章節的考察方式都有效”⑤的條件是不盡相同的。在從有論向本質論的過渡中,前者的考察方式就成為了后者的考察內容,而后者又是基于另一種考察方式。因此,倘若要保證作為系統的《邏輯學》展開過程的連貫性,它就不能被理解為一個思維的自身運動過程。
Henrich將它理解為一個意義發展過程(Bedeutungsentwicklung),而這正是其解決路徑的前提。在這一前提下,他的目標并不是保證《邏輯學》展開過程的邏輯連貫性;相反,他僅僅是通過“意義推移”來保證考察內容之間的意義連貫性,進而保證作為系統的《邏輯學》展開過程的連貫性。誠然,黑格爾在《邏輯學》的第二版序言中仍然堅持有論和本質論之間方法的區別。然而,在有論的第二版(1832)①中卻出現了本質論第一版(1812/1813)的考察方式。根據Henrich的解決路徑,這一考察方式本該在本質論的開端才出現。因為黑格爾沒能完成本質論和概念論的第二版,學界也無從斷定他是否會在計劃中的本質論第二版中沿用其第一版的考察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本質論的第一版②中,黑格爾就已經將本質論中“直接性”與“自身反思”(Reflexion-in-sich)的關聯置于與有論中“有限物”(dasEndliche)和“無限物”(dasUnendliche)的關聯的類比中了。這說明,事實上早在寫作《邏輯學》第一版時,黑格爾就已經意識到了有論和本質論兩者考察方式的相似性。因此,本文作者有充分的理由推測:在完成了《邏輯學》第一版之后,黑格爾產生了對有論新的構想,即要在其中進一步貫徹《邏輯學》思維自身運動過程的邏輯連貫性,因而直接在第二版的有論中使用了本質論的考察方式。這僅僅是一種推測。但假如黑格爾真的計劃在本質論的第二版中沿用第一版的考察方式,那么,這就意味著在有論和本質論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邏輯連貫性。正如Henrich所言,這一結果對于其解決路徑而言則無疑是致命的,因為他首先預設了有論和本質論結構上的不同。因此,其解決路徑成功與否也就完全取決于推測是否成立,從而是有條件的了。Henrich堅持這一并不完善的解決路徑的原因在于黑格爾關于《邏輯學》的構想自身內部存在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兩個方面在他看來是無法調和的,以致于他必須另辟蹊徑。然而,這一路徑同樣面臨著與文本的矛盾。那么,Henrich所指出的矛盾的兩個方面是否確如他所言是不可調和的呢?是否存在一種解決路徑,能夠從黑格爾在《邏輯學》的開端預先設置的前提引出有論的考察方式,而這一考察方式又能夠獨立地從自身給出本質論的考察方式?倘若存在這一可能性,那么,就能夠在滿足有論和本質論之間方法的不同的同時保證作為思維自身運動過程的《邏輯學》的邏輯連貫性。相比Henrich的解決路徑,這一解決路徑不但獨立于推測結果,而且更加符合黑格爾關于《邏輯學》的構想。反觀Kesselring的解決路徑,雖然它導致了與作為系統的《邏輯學》的矛盾,卻從另一方面佐證了有論開端和本質論開端之間考察方式的相似性。引入“外在的反思”之所以能夠區分無法從自身內部加以區分的“所思”和“思維”兩個層次正是因為有論的開端也同樣包含著一個外在的維度。在下文中,本文作者將首先嘗試提出一種能夠同時滿足兩個有效性標準的、系統性的解決路徑。
二、位于有論開端的“存有論核心”的基礎結構
這一解決路徑以黑格爾所構想的、自身構建自身的“存有論核心”為基礎。在下文中,筆者將首先從對黑格爾對整個思辨哲學的目標設定及其關于《邏輯學》的構想的考察出發,再現黑格爾在有論開端預先設置的“存有論核心”的基礎結構。
(一)黑格爾關于《邏輯學》的構想在《邏輯學》的第一版序言中,黑格爾強調邏輯學要成為“構成真正的形而上學或純粹的思辨哲學”③的原則。而新的精神要在這一原則中“顯出痕跡”,④使得邏輯學能夠成為一門“科學”(Wissen-schaft)。他進一步地對所謂的“科學”進行了規定:“只能是在科學認識中運動著的內容的本性,同時,正是內容這種自己的反思,才建立并產生內容的規定本身。”①換言之,只有當內容的本質毋寧是被反思的內容,而反思也因此同時賦予了思維以實體性特征時,邏輯學才能成為一門“科學”。這一“主體的實體性特征”(SubstanzcharakterdesSubjektes)理論是黑格爾哲學革命的標志,是其“科學”以及思辨哲學真正的內容,也是他對《邏輯學》的目標設定,即將原有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合二為一,從而將原有的邏輯學發展為一種作為存有論的邏輯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黑格爾將《邏輯學》構想為一個從“現有的東西”出發的,并作為“認識的絕對方法”自身構建自身的發展過程。因此,“現有的東西”首先是一個發展過程的開端。又因為這一過程同時還是思維的自身運動過程,那么,作為一個自身運動過程的開端,它又必須是黑格爾在《邏輯學》開端預先設置的前提,一個包含之后任一階段成立所需要的所有前提的前提,一個能夠引領思維自身運動過程的前提。因此,一方面,它作為前提蘊含展開作為存有論的《邏輯學》的動力,是其“存有論核心”;另一方面,它又位于其開端,是這一“存有論核心”的基礎結構。
(二)作為有論開端的“現有的東西”就黑格爾的哲學科學體系而言,作為《邏輯學》中思維自身運動過程開端的“現有的東西”并不僅僅是一個絕對的存有論事實。它還是《邏輯學》所繼承的《精神現象學》的結果。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意識發展過程的開端設置的前提是主體和客體之間原初的、絕對的“相異性”。②在這一過程開始之前,主體和客體之間沒有任何關聯,主體還沒有反思到這一絕對形式的“相異性”(absolutfrmlicheAndersheit)。而當主體打破沉寂,開始整個哲學科學體系中的第一個主體活動時,它首先是意識活動。正如德文“意識”一詞的構詞方式所展現的那樣,主體首先是通過對對象的意識(be-wusst-)而“有”(sein)的。然而,此時還未意識到自身的主體毋寧是將自身作為對對象的確定性投射(hineinversetzen/projizieren)到對象中,從而主客體之間的“相異性”也被相應地轉換為對象和對對象的確定性之間的區別。換言之,主客體之間的“相異性”不再是絕對形式本身,而是作為內容的形式(AndersheitalsinhaltlicheForm)。在《精神現象學》的結尾,意識終于意識到對象毋寧是主體的所思,對象就是對對象的確定性,進而達到了絕對知識,即作為絕對形式的“相異性”,亦即思維本身。這一結果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所思被從思維中抽離,而剩下的思維本身成為了考察內容;另一方面,對象和對對象的確定性之間的區別被消解了,原本絕對形式的主客體之間的“相異性”也以新的形式,即作為所思和思維(dasDenkende)之間的“相異性”而再次出現(見表3)。筆者將這兩個方面分別稱為內容的方面和形式的方面。作為同一個結果的兩個方面,內容的方面首先作為形式的方面的原因過渡到后者:通過將所思從思維中抽離出去,思維得以和所思區分開來,而對象和對對象的確定性之間的區別也被所思和思維之間的“相異性”所取代。同樣,形式的方面也作為內容的方面的原因而過渡到前者:由于對象和對對象的確定性之間的區別被消解了,思維揚棄了對象和思維,并回到自身,將“現有的東西”,即思維本身作為考察內容。這兩個相互過渡到對方的方面正是黑格爾系統性地混淆三個層面的原因,因為,倘若對形式的反思只意味著堅持形式的方面,那么,被反思的形式就會像在《精神現象學》中發生的那樣再次被轉換為作為內容的形式,反之亦然。
真正對形式的反思必須是對相對于內容的形式的反思。換言之,真正對形式的反思也就同時包含著對與之相對的內容的反思。或者正如Kesselring所指出的那樣:“黑格爾在《邏輯學》開端所明確繼承的唯一前提就是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的非分離性(Ungetrenntkeit)和不可分離性(Untrenn-barkeit)。”①這也正是《邏輯學》思辨的方法之根本性地區別于《精神現象學》現象學的方法的地方。因此,當思維的自身運動從把握“現有的東西”這一任務出發時,它真正的出發點正是同時作為內容和形式的思維本身。內容的方面和形式的方面也分別作為“直接性的元素”和“相異性的元素”構成了“存有論核心”的基礎結構。作為基礎結構的元素,它們首先是不可回溯的(unhintergehbar),無法被通約的,因為內容和形式之間的區分是絕對的。同時,它們也不能被相互割裂開,因為兩者始終處在向對方的過渡中。在此基礎上,黑格爾開始了對“現有的東西”這一絕對的“存有論事實”的“科學”考察(wissenschaftlicheBetrachtung):第一步是基于“直接性的元素”從直接性視角的考察。而由于“直接性的元素”又同時過渡到“相異性的元素”,那么,第二步就是基于后者從“相異性視角”或者“第三視角”來進行考察,并揚棄之前的結果,以此類推。這樣一種對同一個“存有論事實”的考察視角的交替轉換正是“存有論核心”(selbstkonstruierenderOntologiekern)自身構建自身,并引領思維自身運動過程的動力所在(見表4)。以有論的開端為例,黑格爾正是通過這一視角的交替轉換來開啟思維的自身運動過程的:首先,從直接性視角來看,在思維面前的是被直接性地把握的思維本身。它是無規定性的“純粹的有”,即黑格爾的第一個環節。然而,從第三視角來看,“純粹的有”事實上是被思維的所思,其無規定性本身仍然是一種規定,那么被規定的思維本身也就不再是“純粹的有”了。因此,思維揚棄了它對思維本身的規定。沒有任何規定也就是“無”,即黑格爾的第二個環節。然而,從直接性視角來看,“無”事實上是思維的“無”,其本身仍然是一種規定性,那么進行規定的思維也就不再是“無”了。因此,思維又恢復了對思維本身的規定性,即“純粹的有”。所以,通過從第三視角向直接性視角的轉換,“無”過渡到了“純粹的有”。而通過從直接性視角向第三視角的轉換,“有”又將再次過渡到“無”。這兩個過程分別對應黑格爾所謂的“發生”和“消滅”,兩者共同構成了他的第三個環節,即“變”。可以看到,正是通過兩個視角的交替轉換,思維獲得了其自身運動的動力。在下文中,本文作者將基于這一“存有論核心”過程的基礎結構來重構本質論的開端,并驗證它“是否在每個階段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實現和保持了”。①
三、位于本質論開端的“存有論核心”的結構轉換
本質論的開端包括了本質論第一部分“第一章:映象”(DerSchein,下文簡稱第一章)的三節,即“本質的與非本質的”(A.DasWesentlicheunddasUnwesentliche)、“映像”(B.DerSchein)和“反思”(C.DieReflexion)。在下文中,本文作者將它們分別命名為階段1、階段2和階段3;每個階段又包括兩個環節,即環節1:直接性視角的考察和環節2:第三視角的考察。例如,第一節“本質的與非本質的”就由階段1的環節1(環節1.1)和環節2(環節1.2)構成,以此類推。
(一)“本質的與非本質的”倘若“相異性”在有論中還是直接性的,那么,它在本質論就被建立起來了(gesetzt),成為實在的(real)相異性了。存在謂詞(ist)在有論中還只是直接性的規定,作為不定式或者名詞的“有”(Sein)被思維投射到所思當中。此時,“存有論核心”的結構還是:es/Sein。第一節“本質的與非本質的”包括以下兩個環節。環節1.1(對應該節的第1段):從直接性視角來看,首先在思維面前的是通過對無差別的揚棄回到自身的“本質”。作為被揚棄的“有”,它單純地與自身相等同。環節1.1:Dasein(式1)對環節1.1的揚棄:然而,“本質”還同時處在與“直接性”的對立中:“有與本質以這種方式,一般相互作為他物而彼此相關”。那么,“本質”也就不再單純地與自身相等同了。作為“他物”,作為“另一規定了的實有”,②它揚棄了自身。環節1.2(對應該節的第2段至第3段):此時,思維終于反思到了第三視角。后者在有論中始終是隱含的,現在則開始作為“一種外在的建立”、“一種把實有的一部分從另一部分隔離出來而不觸及實有本身”、“一種歸入一個第三者的分離”以及“一種外在的觀點和考察”③而出現。“那個在此實有中的有”對于作為基礎的“實有”(Dasein)的層面而言是外在的,或者說,“本質”“只是就規定的(bestimmt)觀點對其他的自在自為之有而言”④才是“自在和自為之有”(Anundfürsichsein)。從第三視角來看,直接性視角的考察毋寧是對“實有”的規定,是作為名詞的否定(Negation)。通過這一否定,“有只會變為實有,實有只會變成一個他物”。向階段2的過渡(對應該節的最后一段):從直接性視角來看,第三視角的考察是作為動詞的否定(Negieren)。作為這一否定的結果,“有”“既是作為直接性的有,也是作為直接性的否定”。因此,它不再是直接性的了,而是“自在自為的、無的直接物”,①從而“揚棄自身而回歸到本質”。②這是“有”向“本質”的自身回歸(Sich-Zurückkehren)。它標志著“存有論核心”的結構轉換:es/Sein→esistes。③此時,主體終于通過思維對第三視角的反思作為“本質”出現了。與主體同時出現的還有它的存在謂詞(ist)。“有”不再是作為不定式或者名詞被投射到所思中的“有”了。相反,它是主體直接性的規定。
(二)“映象”第二節被黑格爾分為以下兩個環節。環節2.1(對應該節的第1段至第3段):從直接性視角來看,首先在思維面前的是通過對直接性的否定的揚棄而被把握為否定物(Negatives)的“有”。作為“非本質”(Unwesen)或者“映象”(Schein),它在其“無”(Nichtigkeit)中獲得其“有”:“有是映象。映象之有全在于有之被揚棄,在于有之虛無”。④在環節1.1中,“有”是對與他物的關聯的否定,并且被直接性地規定為另一個他物(einanderes)。與之相比,“有”在環節2.1中毋寧是否定的自身關聯,即“本質”的他物(dasanderedesWesens)。這一環節對應的正是Henrich所謂的“意義推移”(U1→U2),因為“映象”的直接性特征在“本質”中被重新發現了。對環節2.1的揚棄:然而,“映象”仍然擁有“一個直接性的前提,一個獨立于本質的方面”。那么,“映象”也就不再是直接性的規定性(Bestimmtheit)了。作為“本質”的規定性,或者更準確地說,作為“本質”的規定性的“無”(Nichtsein),它揚棄了自身。環節2.2(對應該節的第4段到第5段):通過對“映象”的揚棄,所思成為了思維的規定性。兩者相互構成了對方的“自在之有”(Ansichsein):“它的自在的虛無就是本質自身的否定的本性。但是,這個非有所包含的直接性和漠不相關性,就是本質自己的絕對的自在之有。”⑤在環節1.2中,否定是對另一個他物的直接性的否定。與之相比,否定在環節2.2中已不再是直接性的了,而是“本質”對其他物的否定。這一環節對應的正是Henrich所謂的“意義等同”(U1=U2),因為“映象”的規定性被轉移到“本質”的規定性里了。向階段3的過渡(對應該節的第6段至最后一段):從直接性視角來看,在“本質”中的“映象”仍然是“自在的映象,即本質自身的映象”。因此,“映象”不再是“本質”的規定性的“無”,而是揚棄自身,成為“在有之規定性中的本質自身”。⑥或者說,“本質”揚棄了“映象”,成為了單純地與自身相等同的否定性(Negativitt)。這是“本質”的自身運動,是“其在自身中的映現(dasScheinenseinerinsichselbst)”。①它標志著“存有論核心”的又一次結構轉換:esistes→esisteses。黑格爾用“一個外來語,即反思”②來命名這一新結構。
(三)“反思”第三節被黑格爾分為三個小節。環節3.1(對應該節“第一小節:建立的反思”(diesetzendeReflexion)的第1段至第5段上半部分):從直接性視角來看,首先在思維面前的是通過揚棄對“本質”自身規定性的否定而單純地與自身相等同的否定性。作為“被‘本質’建立起來之有”(dasvomWesenGesetztsein),它是在直接性中的“本質”,因為“當前并沒有一個他物,既沒有反思從那里出來,也沒有反思回到那里去的那樣一個他物”,而“直接性絕對只是作為這種關系,或說作為從一個否定物的回歸……作為規定性,或作為自身反思”。③在環節1.1中,“有”是對與他物的關聯的否定,并且被直接性地規定為另一個他物。在環節2.1中,“有”是否定的自身關聯,即“本質”的他物。與之相比,“有”在環節3.1中毋寧是“本質”本身,但是在“直接性”中的“本質”本身。正因如此,反思“本身是對對象性的反思性構建,是真正的、‘本質性的’建構反思”。④對環節3.1的揚棄:然而,“本質”同時又排斥自身,將自身推向“直接性”,并因此而揚棄自身。“作為否定物的揚棄”,它“是對它的他物的、即直接性的揚棄”。⑤或者說,它將自身揚棄為“直接性”,“是否定物本身的揚棄,是與自身的消融”,⑥是“本質”回到自身。那么,對立的“本質”也就不再保持在“直接性”中了。作為“被‘本質’所事先建立之有”(dasvomWesenVorausgesetztsein),它揚棄了自身。環節3.2(對應該節第一小節的第5段下半部分至第6段上半部分以及最后一段的下半部分至該節“第二小節:外在的反思”(dieuβereReflexion)的最后一段):通過對“本質”的揚棄,所思成為了“被思維所預先建立之有”(dasvomDenkendenVorausgesetztsein):反思“依據這種規定而具有一個事先建立,并且從直接物,即從自己的他物開始”。⑦在環節1.2中,否定是對另一個他物的直接性的否定。在環節2.2中,否定是否定性對其他物的否定。與之相比,否定在環節3.2中已不再是對他物的否定了,而是反思,即否定性對其自身的否定。向“第二章:本質性或反思規定(DieWesentheitenoderdieReflexionsbestimmungen)”的過渡(對應該節“第三小節:規定的反思”(diebestimmendeReflexion)):從直接性視角來看,“反思在直接物中所規定和建立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對直接物說來,便是外在的規定”,①而反思也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了“外在的反思”。然而,“外在的反思”并沒有單純地揚棄自身,而是與“建立的反思”一起被統一在“規定的反思”中。作為整個第一章的考察結果,“規定的反思”不僅是對兩者的統一,還同時是對直接性視角和第三視角的統一。它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外在的反思”是實在的反思,是“直接性”和反思的中項。通過“外在的反思”,“直接性”在“相異性”中被建立起來了,從而“相異性”通過被建立起來的“直接性”才自為地作為“相異性”被建立起來,并過渡到“直接性”中,揚棄自身。也就是說,所思被思維規定了;而這些規定對于所思而言卻是外在地被建立的。因此,第三視角的考察結果現在毋寧是對“被作為他物事先建立起來之有”的否定(NegierendesalsanderenVorausgesetztsein),也就同時是“自身反思”。簡言之,從第三視角來看,規定現在毋寧是“直接性”,但自身反思的“直接性”,即“反思規定”(Reflexionsbestimmungen)或“在相異性中的直接性”:DasSeinistReflexionsbestimmung。另一方面,“建立的反思”則是反思和“直接性”的中項。通過“建立的反思”,“相異性”在“直接性”中被建立起來了,從而“直接性”通過被建立起來的“相異性”才自為地作為“直接性”被建立起來,并過渡到“相異性”中,揚棄自身。也就是說,“有”對于思維而言是單純地與自身相等同的規定;而這些規定毋寧是被思維所事先建立的規定性:“反思從這個直接物開始映現,就像從一個異己之物開始映現那樣,而這個直接物也只是以反思開始才有的。”②因此,直接性視角的考察結果現在毋寧是“被作為單純地與自身相等同建立起來之有”(alseinfachmitsichgleicheGesetztsein),也就同時是回到“本質”。簡言之,從直接性視角來看,規定性現在毋寧是“相異性”,但是回到“本質”的“相異性”,即“本質性”(Wesenheiten)或“在直接性中的相異性”:DieBestimmtheitalsWesenheit。這兩個方面相互過渡到對方,構成了“本質”的自身運動,即“本質”的自身規定。正因如此,黑格爾將本質論第一部分第二章命名為“本質性或反思規定”。這一相互過渡是“一個理性本身基本的事實”,一個“所有理論不可回溯的開端”,而“關聯的起源在反思的自身關聯中”③被隱藏了。在這個意義上,本質論的第一個規定毋寧是“對同一性的規定,它是對《邏輯學》開端的‘純粹之有’的繼承”。④也許正是出于這個原因,黑格爾在《哲學全書綱要》版的《邏輯學》(1830)中也刪掉了原版本質論(1813)的第一章,而直接將第二章的第一個環節,即“同一性”作為新版本質論的開端。
四、結論
可以看到,一方面,第一章中思維自身運動過程的每一階段都是開始于從直接性視角的考察,最后通過對第三視角的考察的揚棄過渡到下一階段。因此,第一章的三節都是基于同一個“存在論核心”的基礎結構構建的。這一基礎結構貫穿了整個第一章(見表5)。另一方面,每一個階段在其自身內部都是一個獨立但又各不相同的結構。來自兩種視角的考察在三個階段中都以不同的方式相互關聯,并構成新的“存有論核心”的結構:es/Sein→esistes→esisteses。同時,同一種視角的考察在不同階段所獲得的結果也各不相同(見表6)。因此,在基于同一個“存在論核心”的基礎結構的同時,每個階段又保持了各自的獨立性。Henrich是通過其思想實驗來統一“本質”對先行環節的連續性與其相對于“有”的獨立性。然而,正如上文所述,這一解決路徑又會導致與文本的矛盾,其成立與否是有條件的。與之相比,在筆者的解釋框架內,思想實驗的兩個步驟,即“意義推移”和“意義等同”分別對應環節2.1和環節2.2,而這兩個環節又都是由先行的環節獨立地從自身給出的。自此,所謂的《邏輯學》邏輯不連貫性問題也就得到了系統性的解決。
作者:洪凱源 單位:德國波鴻大學黑格爾檔案館及德國古典哲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