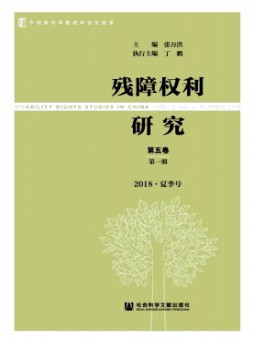權(quán)利憲法化憂患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權(quán)利憲法化憂患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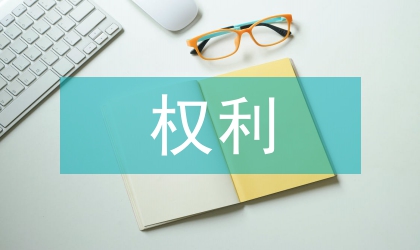
關(guān)鍵詞:人權(quán)入憲/社會權(quán)/違憲審查/憲政
內(nèi)容提要:本文對當前一些學者提出的“權(quán)利憲法化”主張進行了反思。權(quán)利憲法化的動機無可置疑,但它誤解了憲法的屬性,不但于事無補,而且貽害甚多。該主張對政治渠道的回避,使得我國本不完善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面臨進一步功能失調(diào)的危險,也忽視了社會組織在維護公民利益方面的功能,并且為清晰地理解權(quán)利體系設(shè)置了障礙。權(quán)利憲法化訴求增強了權(quán)利意識,卻貶低了民主過程,它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設(shè)想,但也容忍了問題的產(chǎn)生。
解決問題的辦法可能比問題本身還糟。
引論
近年來,呼吁社會保障權(quán)、環(huán)境權(quán)、受教育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知情權(quán)、住宅權(quán)等“入憲”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有些已經(jīng)拿到入場券,有些正在排隊,還有一些則正在不遺余力地尋找憲法依據(jù)。〔1〕持有這種主張的學者認為,權(quán)利入憲啟蒙了人民的權(quán)利觀念,劃定了公共權(quán)力的邊界,堪稱保障人權(quán)的“第一步”。即使那些謹慎的人們也不過認為,權(quán)利寫入憲法并不多浪費紙張——寫進去總比不寫好吧。
權(quán)利憲法化的現(xiàn)實背景有目共睹:一方面,中國當下公共權(quán)力侵權(quán)事件大量存在,而且與多年的經(jīng)濟總量膨脹并行的是民生保障相當不足;另一方面,“天賦人權(quán)”、“認真對待權(quán)利”、“為權(quán)利而斗爭”、“違憲審查”等現(xiàn)代法觀念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對處于制度轉(zhuǎn)型期的中國而言,權(quán)利憲法化似乎成了一個當然的選擇。的確,保障人權(quán)的努力從抽象層面無可置疑,它是立憲主義的核心價值,但如果我們誤解了實現(xiàn)權(quán)利的根本方式,對它的執(zhí)著就可能只是激起了人們的熱情,卻不能提供滿足熱情的手段。對于轉(zhuǎn)型期的中國而言,至少我們可以提問:如果此前發(fā)生的一些侵權(quán)事件不是因為沒有把權(quán)利寫入憲法,那么寫入憲法意義何在?這一疑問可以成為我們追問權(quán)利憲法化主張的第一步。
本文通過檢討內(nèi)在于權(quán)利憲法化理論的幾個具體命題來反思這一主張。這些命題可以歸納為:1.人權(quán)必須法律化或憲法化。2.就最為緊迫的社會權(quán)而言,只有憲法化才能回應當下緊迫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及環(huán)境權(quán)訴求。3.憲法權(quán)利需要普通法律將其“具體化”才能真正落實。4.為了使憲法權(quán)利所指明確,其清單越詳盡越好。5.違憲審查是落實權(quán)利的主要手段。本文第一至第五部分分別檢討了這些具體命題,第六部分討論了權(quán)利保障的可能路徑——政治過程。最后的結(jié)論是,就當前我國的情勢而論,權(quán)利憲法化主張雖源自良好的動機,卻采用了錯誤的手段,實現(xiàn)以社會權(quán)為中心的權(quán)利訴求的根本方式是推進對以公民參與和表達自由為核心的傳統(tǒng)公民權(quán)利和政治權(quán)利,這也是現(xiàn)代立憲主義的基本經(jīng)驗。
一、經(jīng)驗方面的疑問
“權(quán)利憲法化”將法治主義置于人權(quán)保障的核心地位,這種熱情源于一個根深蒂固的判斷:權(quán)利的享有始于法律的明確肯定。著名的“人權(quán)三形態(tài)說”對此提供了說明:“從應有權(quán)利轉(zhuǎn)化為法定權(quán)利,再從法定權(quán)利轉(zhuǎn)化為實有權(quán)利,這是人權(quán)在社會生活中得到實現(xiàn)的基本形式。”〔2〕有學者附和說,“將人權(quán)明確寫入憲法,明確規(guī)定基本人權(quán)原則,更有利于保障人權(quán)……因此要使人權(quán)從‘應有的人權(quán)’到‘法有的人權(quán)’再到‘實有的人權(quán)’。”〔3〕這種帶有濃厚實證主義色彩的理論所蘊含的邏輯是:法律(憲法)之外沒有權(quán)利,保障人權(quán)始于權(quán)利的法定化(憲法化)。
對此,一個來自經(jīng)驗方面的疑問是,為什么有些治理良好的國家(如加拿大、新西蘭)長期沒有權(quán)利法案,有的國家(如英國、以色列)甚至連一部剛性的成文憲法都沒有?如果憲法是保障人權(quán)的來源,這些國家的憲法性文件和不成文憲法慣例就不會如此瑣碎。這的確是少數(shù)國家的情況,但恐怕難以簡單地用“不具有代表性”來搪塞,它引領(lǐng)我們思考憲法規(guī)則的功能及其條件。另一方面,那些擁有成文憲法典和權(quán)利法案的國家,盡管憲法的形式與上述例子不同,保障權(quán)利的方式上卻完全一樣。權(quán)利法案并非與政治過程不同的、可任加取舍的維權(quán)渠道,它們密切相關(guān),如果沒有政治渠道起作用——甚至是過分的作用,莊嚴的憲法權(quán)利就會落空。阿奇博爾德·考克斯(ArchibaldCox)教授曾經(jīng)指出,美國黑人在二戰(zhàn)后之所以能夠獲得憲法平等保護,根本上是由選舉權(quán)和表達自由的擴大帶來的,正是這一政治過程為民權(quán)運動提供了有效的訴求途徑。〔4〕同樣,在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早期的英國,正是選舉權(quán)和表達自由促進了政治過程,成為公民獲得諸如改善勞動條件等內(nèi)容的社會和經(jīng)濟權(quán)利的途徑。〔5〕另外,一個并非不重要的事實是,1787年的美國聯(lián)邦立憲者們對“權(quán)利法案”并不熱衷,它是后來以修正案的形式附加上去的。漢密爾頓在《聯(lián)邦黨人文集》第84篇中指出,權(quán)利法案不僅多余,而且有害,由于無法窮盡列舉的那些自由,反而有可能成為政府侵害的對象。〔6〕立憲者們相信,政府的政治過程才是保障公民權(quán)利的有效渠道。
德國《魏瑪憲法》通常被視為社會權(quán)憲法化的經(jīng)典文本,并成為我國學者建議效法的對象。有人指出,“1919年德國魏瑪憲法對社會權(quán)的確立及其司法效力功不可沒。魏瑪憲法以其社會權(quán)條款數(shù)量之龐大、社會權(quán)種類之完備、性質(zhì)之明顯而成為20世紀憲法之典范”〔7〕。這一理解并不正確,魏瑪憲法的失敗也部分地歸因于社會權(quán)入憲。由于當時的社會主導的聯(lián)合政府將大量社會權(quán)——諸如健康權(quán)、受教育權(quán)、工作權(quán)、住宅權(quán)、社會保障權(quán)等——寫入憲法,但又無法提供充足的財政保障和有效的司法救濟,并抑制了立法機構(gòu)對此類事項的審議和決策權(quán)力,其引發(fā)的憲法危機加劇了魏瑪政府的垮臺。這也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作為對社會國理念的回應,德國魏瑪憲法并沒有處理好傳統(tǒng)自由權(quán)利與新興社會權(quán)的關(guān)系,為日后的納粹上臺埋下了禍根”〔8〕。
社會權(quán)為什么從社會人的善良期待變成了促使政府垮臺的一個原因?〔9〕盡管我們可以懷疑這一因素在1919至1933年間的德國所起的作用大小,但社會權(quán)本身的一般特征不可忽視。首先,社會權(quán)是一種強烈依賴政府稅收汲取和再分配能力的“積極”權(quán)利,若要滿足它,政府需要積極擴張權(quán)力。它勢必挑戰(zhàn)“有限政府”傳統(tǒng),并引發(fā)了政治哲學上的不安。其次,社會權(quán)具有不可訴訟性,如果此類權(quán)利既宣告于憲法,又無法通過訴訟渠道獲得保障,它就會挑戰(zhàn)政府的正當性,事實上,在當時因戰(zhàn)敗而財政捉襟見肘的德國,這一危機被無情放大了。第三,社會權(quán)只能是“綱領(lǐng)性”的,它是政府努力的目標,而不是需要即刻履行的強制義務。盡管關(guān)于社會權(quán)上述特征的看法在學界仍存爭論,但一個無法反駁的的事實是,二戰(zhàn)之后的德國基本法是把魏瑪憲法當做一個教訓來對待的,它一方面重申基本人權(quán)的價值,把大量表達自由和人格權(quán)寫入憲法,一方面又堅定地把社會權(quán)拒之門外,交給日常的政治過程處理。立憲者認為,受到來自選舉和表達自由形成的政治壓力的督促,民選的國會代表和政府自然有動力根據(jù)財政狀況不失時機地改善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措施。相反,把社會寫入憲法倒使得政治部門(國會、政府)的審議功能遭到削弱。
二、政治審議、非政府組織與社會權(quán)
成文憲法的生命立基于一個教條——憲法先于并高于立法機關(guān),因此凡屬憲法權(quán)利范圍的事項,立法機關(guān)的政治審議范圍需要保持克制。換言之,憲法權(quán)利的功能在于防止立法機關(guān)憑借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規(guī)則侵害個人權(quán)利。但是同時,立法機關(guān)保持著對非憲法權(quán)利和利益的審議權(quán)力。因此,不能把所有利益訴求都納入憲法規(guī)范,否則立法機關(guān)的審議范圍會受到過度限制。這樣就容易理解,為什么西方國家憲法中通常只包含有限的公民權(quán)利和政治權(quán)利,并以消極權(quán)利和自由為主要內(nèi)容。人們通常認為,這只是人權(quán)觀的不同造成的,它們只是選擇了與我們不同的方式而已。但更準確的理解在于,將本質(zhì)上積極能動的社會權(quán)排除在憲法權(quán)利法案之外并非貶低其重要性,而是認為它們應該通過政治審議過程加以實現(xiàn),或部分地交給非政府組織去消化處理。與此同時,他們相信公民政治權(quán)利并非與社會權(quán)不同的利益訴求,而是社會權(quán)的根本實現(xiàn)方式。
因此,“權(quán)利憲法化”訴求主張將社會權(quán)寫入憲法,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它會抑制日常政治過程的審議范圍,并凸顯政府的強制性義務。這一訴求在本質(zhì)上有助于強化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再分配權(quán)力。社會權(quán)入憲增加了需要全國性政府來提供的再分配事項。經(jīng)常發(fā)生的情況是,對社會權(quán)的高度關(guān)注由于不僅涉及單純的生存保障,而且涉及政治穩(wěn)定的大局,會大大激勵中央政府強化稅收汲取和財政再分配的動機和能力。令人不安的是,它所帶來的公共權(quán)力日益膨脹的趨勢,又會對傳統(tǒng)的消極自由構(gòu)成威脅,旨在保障人權(quán)的力量,因此可能成為威脅人權(quán)的力量。這就使我們?nèi)菀桌斫猓瑸槭裁闯墒斓姆ㄖ螄彝ǔI髦貙Υ鐣?quán)入憲問題了。由于公民無法通過日常政治過程傳達利益訴求的種類和強度,社會權(quán)的憲法化會對民意機關(guān)產(chǎn)生釜底抽薪的作用。具體到我國的情況,它直接導致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本不寬泛的政治審議范圍更趨萎縮。
權(quán)利憲法化越多,政治過程的裁量范圍越小,人民代表大會的地位就越不重要,這與我國多年來一直試圖強化人大政治審議功能的改革取向明顯不符。在政治體系內(nèi)部,這種危險集中表現(xiàn)于縱向的分級政治安排活力不足。大量權(quán)利憲法化不僅在國家層面導致人大政治審議空間縮小,在地方人大層面也會導致同樣的結(jié)果。某種利益訴求一旦變身為“憲法權(quán)利”,就“一個都不能少”,而且需要在全國統(tǒng)一實施,這樣的話,地區(qū)間在財政支付能力上的差異勢必引發(fā)平等問題。而社會權(quán)利從其對財政的依附上看,必然是要受各地經(jīng)濟狀況制約的。因此,憲法化后的社會權(quán)實現(xiàn)狀況,最好的情況是造成地區(qū)差別,最壞的情況則是由于地方抵制中央集權(quán)趨勢而使得權(quán)利無法落實。如果政府試圖通過強化中央財政來統(tǒng)一解決,它就必然忽視地方特殊性和能動性;而如果中央政府不這么做,社會權(quán)的實現(xiàn)水準將可能由支付能力最弱的地方?jīng)Q定。權(quán)利意識被調(diào)動起來了,保障權(quán)利能力的不足也顯露出來。如果將下列事實考慮進來,情況就更加嚴重:當下中國的社會權(quán)訴求大多是由于各級人大審議和監(jiān)督功能的失靈引發(fā)的。一方面,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單純追求經(jīng)濟績效的沖動造成了大量民生問題;另一方面,由于政治過程無法滿足社會保障方面的訴求,反過來激勵了對社會權(quán)入憲和中央政府再分配能力的強烈渴望。由此也可以發(fā)現(xiàn),權(quán)利憲法化實則源于政治過程堵塞之后對中央政府的“路徑依賴”。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難道政府是社會權(quán)訴求的唯一承載者嗎?
社會權(quán)入憲訴求也會導致社會組織相應功能的弱化。社會權(quán)所代表的那些利益訴求,本來可以通過非政府組織部分地予以滿足。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公益慈善社團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重要力量”。〔10〕在許多國家,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險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非政府組織提供的,法律通過稅收優(yōu)惠鼓勵捐款流向慈善團體。這一途徑不但提高了社會的自我組織能力和財富使用效率,而且減少了政府承受的政治壓力。但是在我國,有目共睹的困境是,一方面來自政府的民生保障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對非政府組織提供的法律支持又十分有限,由于不能得到足夠的社會捐款,它們的救濟功能難以發(fā)揮。〔11〕于是,球踢給了政府。政府的權(quán)威增強了,責任也在不斷增加,承受的政治風險亦悄然累積。
對環(huán)境權(quán)的理解,既可遵循上述道理,又引領(lǐng)我們把視角轉(zhuǎn)向由于憲法權(quán)利種類太多引發(fā)的技術(shù)性難題。憲法權(quán)利的事項并非越多越好。當生存權(quán)、發(fā)展權(quán)、社會保障權(quán)、環(huán)境權(quán)等一股腦地涌入成文憲法時,權(quán)利體系內(nèi)部的沖突也越來越大。正如有學者正確指出的,“若在憲法中明確規(guī)定了環(huán)境權(quán)的至上的優(yōu)勢地位,并且假設(shè)在現(xiàn)實中得到充分貫徹,那么是否意味著發(fā)展權(quán)必須止步于環(huán)境權(quán)?”〔12〕困境源于對環(huán)境權(quán)屬性的誤解。臺灣學者葉俊榮指出,環(huán)境利益固然是政府應予妥善考慮的要素,但從資源的有效利用著眼,該利益只是國家所應追求利益中的一環(huán)(雖然是很重要的一環(huán))。環(huán)境對其他同等重要的利益(例如經(jīng)濟的持續(xù)發(fā)展、社會安全、消費者保護或勞工安全衛(wèi)生)均會產(chǎn)生深遠影響。而其中環(huán)境保護與經(jīng)濟發(fā)展之間的關(guān)系是時常處于緊張狀態(tài)的。由于環(huán)境資源注定是稀缺的,政府在做資源分配時經(jīng)常面臨“要環(huán)境”還是“要發(fā)展”的現(xiàn)實選擇。〔13〕這就意味著,憲法上的環(huán)境權(quán)可能引發(fā)理論混亂和權(quán)利概念沖突,并進一步帶來嚴重的執(zhí)法和司法難題。
三、把憲法權(quán)利“具體化”?
社會權(quán)入憲后再由普通立法“具體化”,是與權(quán)利憲法化訴求伴而行的主張。例如有學者主張:“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一般只規(guī)定國家和社會生活最根本的原則,這種原則性的規(guī)定,往往由普通法律加以具體化;而普通法律的規(guī)定有時還需要次級的法規(guī)、規(guī)章再進一步具體化;只有在具有可操作性的規(guī)范產(chǎn)生后,憲法的規(guī)范才可能變成現(xiàn)實的力量。”〔14〕還有的學者說:“有些憲法條款雖對一些權(quán)利有所規(guī)定,但這些條款卻無法得到間接實施,更不可能直接實施。如在憲法中明確規(guī)定公民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然而,對公民的這一權(quán)利具體應該如何實現(xiàn)以及怎樣對其保護,卻沒有法律進行進一步規(guī)定,造成了事實上公民的這些權(quán)利在很多情況下是形同虛設(shè)的,須進一步制定《新聞法》、《出版法》等下位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成為公民真正能夠切實享有的權(quán)利”〔15〕。
對此,已有學者做過有價值的反思:“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人權(quán)方面是不能由下位法來具體化的。那種呼吁我國抓緊制定結(jié)社法、新聞法、宗教自由法的人都是建立在這樣的錯誤觀念基礎(chǔ)之上的。其實,要是真的有了這些法律,人權(quán)的保障也就到了危險的境地。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世界各國基本上都沒有這些人權(quán)方面的國會立法。”〔16〕根本的癥結(jié)在于,“具體化”主張誤解了現(xiàn)代立憲主義和憲法權(quán)利的本質(zhì)。如前所述,之所以把某些權(quán)利寫入憲法,恰恰是為了防止普通法律通過具體化方式加以限縮、侵害。作為民主制之核心的“多數(shù)決”原則,產(chǎn)生了托克維爾所描述的那種“多數(shù)派專制”風險,立憲主義正是通過確立成文憲法的至上性,對民主過程構(gòu)成了建設(shè)性約束。它的一項基本訴求是:即使是多數(shù)派的意志,也不能為所欲為。作為現(xiàn)代成文憲法之起源的美國聯(lián)邦憲法,開創(chuàng)的正是這樣一種傳統(tǒng),立憲主義的那些關(guān)鍵性設(shè)置——司法審查、權(quán)利法案、行政否決權(quán)、議會內(nèi)部的兩院分權(quán)等——都是為了防范那個野心勃勃的立法機關(guān)而設(shè)立的。〔17〕
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對成文憲法與民治政府之間的這一緊張關(guān)系做出過說明,立法機關(guān)正是由于“有人民做后盾”而成了立憲主義的防范對象。同樣,由于立法機關(guān)的民主化產(chǎn)生的關(guān)注多數(shù)派利益的本能,決定了幾乎所有“具體化”的法律都或多或少地旨在限制憲法權(quán)利。在限制表達自由和選舉權(quán)利上,民主政府具有利益。我國憲法規(guī)定的表達自由經(jīng)《集會游行示威法》具體化后的結(jié)果是:它的實施需要取決于縣級公安機關(guān)的行政許可。〔18〕無論哪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喜歡公民用表達自由來制造麻煩,政府對“麻煩”的顧慮不一定源于對公民權(quán)利的漠視,更多的可能是由于對公共利益富有責任而容易忽視個人訴求。而立憲的本意恰恰針對這一情況。美國聯(lián)邦憲法第一修正案規(guī)定:國會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減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削減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愿伸冤之權(quán)力。”(著重號為引者所加)。之所以用否定性措辭,目的就是防止立法機關(guān)假借“公共利益”之名制定限制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具體法律,而權(quán)利法案之所以把一些(刑事)訴訟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法不溯及既往、禁止強迫自證其罪等——規(guī)定下來,也同樣是為了防范國會立法對其加以侵害。舉其中一例,我國不少學者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理解為,只要是有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就是“正當法律程序”,殊不知,這項憲法要求恰恰是用來衡量國會的刑事程序立法是否“正當”的一個標準。〔19〕“具體化”思維之誤,由此可見一斑。
簡言之,憲法權(quán)利與非憲法權(quán)利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前者處于政治審議過程之外,后者處于政治審議過程之內(nèi),法律將人權(quán)“具體化”,恰恰是成文憲法所警惕的。“人權(quán)三形態(tài)說”的法實證主義和權(quán)利入憲論的“具體化”主張,都削弱了憲法同下位法之間的建設(shè)性緊張關(guān)系,它的善良意愿帶來的可能是憲法權(quán)利被“抽象地肯定而被具體地否定”。的確,作為我國立法機關(guān)的人民代表大會從來都沒有讓人有值得警惕的感覺,而多年來我們努力的方向正是強化人大的政治功能而不是約束它。但是,這恰恰是其沒有發(fā)揮應有的政治審議和監(jiān)督功能的表現(xiàn),否則人們就不會期待它從“橡皮圖章”變成“木頭圖章”了。這似乎是一個令人頗感吊詭的結(jié)論,難道我們要有意使人大像別國那樣非得有“多數(shù)派專制”風險才行嗎?不能為惡的權(quán)力也不能行善,如果人大不能發(fā)揮其作為政治審議機構(gòu)的功能,它固然不能造成“多數(shù)派專制”的風險,但也同樣無法體現(xiàn)公眾的意愿。本文主張將社會權(quán)訴求回歸人大和政府的日常政治審議,既是基于優(yōu)化政治過程效能的考慮,也是因為確信社會權(quán)利益的實現(xiàn)寄予此一渠道將更為有效。在中國所處的特殊情勢之下,通過強化以人大為中心的政治審議過程來,既可以有效減少侵權(quán)事件的發(fā)生,又能制度性地促進政府關(guān)注社會權(quán)訴求,避免把改善民生僅僅作為防止社會失序的功利主義回應。
此外,“具體化”主張為消極的立法不作為和積極的立法侵權(quán)帶來了風險。如果社會權(quán)只有憲法化才能得到保障,侵權(quán)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歸因于沒有憲法化,那就無異于把問題歸咎于作為立憲者的人民自身。權(quán)利入憲需要等待,而等待過程可能是不可容忍的漫長。即使社會權(quán)成功入憲,財政支付能力不足總可以成為拖延兌現(xiàn)權(quán)利的口實,“具體化”因而又必然讓位于“綱領(lǐng)性”主張,憲法就只是一個指導下位立法的大綱——它無須對政府課以強制性義務。在這方面,實證主義立場所主張的法的規(guī)范性特征又被悄然舍棄了。成文憲法的“高級法”預設(shè)一旦遭到拒絕,憲法規(guī)范喪失評價基準地位,權(quán)利憲法化就只是滿足了學者的自尊,卻成為公民手中一張精美的空頭支票。當“綱領(lǐng)性”與“具體化”奇異地結(jié)合在一起,將立法保障的責任留待未來時,公共機構(gòu)事實上的怠惰和侵權(quán)行為反而成為可以原諒的事情了。如此選擇性地接受實證主義觀點,后果如何可想而知。事實已經(jīng)做出了回答:我們以前所經(jīng)歷的許多權(quán)利侵害,并非因為憲法權(quán)利的缺失。僅就最遭詬病的強制拆遷帶來的權(quán)利侵害而言,不也大量發(fā)生于2004年憲法修正案重申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之后嗎?
四、列出權(quán)利清單?
下面的討論將稍稍偏離社會權(quán)這一主題,但所涉及的原理仍一以貫之。
在權(quán)利入憲論的諸多主張中,一個同樣令人擔憂的傾向是為憲法權(quán)利開列“清單”:“吃早餐的權(quán)利”還嫌不夠,也需要將“吃面包的權(quán)利”和“吃饅頭的權(quán)利”等次級項目明確列出。實證主義立場視之為邏輯上的當然之舉:既然保障權(quán)利始于權(quán)利憲法化,權(quán)利的條款就應越細越好,以免在實踐中產(chǎn)生歧義。有學者主張,憲法規(guī)定的言論、集會、結(jié)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監(jiān)督政府的權(quán)利,必須輔之以知情權(quán)、參與權(quán)、表達權(quán)等明確入憲。“知情權(quán)作為一項新興的權(quán)利,已成為當今民主憲政國家的基本人權(quán)之一,在當代中國知情權(quán)也備受關(guān)注。但是知情權(quán)卻在被視為人權(quán)保障書的憲法中難尋蹤影,直接影響了對知情權(quán)的保護力度,將知情權(quán)在我國憲法中加以明確規(guī)定已具備了充分的理論基礎(chǔ)和現(xiàn)實條件。”〔20〕“知情權(quán)的入憲途徑……(有)兩條可行的做法:一是直接啟動修憲程序,將知情權(quán)寫入憲法;二是通過憲法解釋,使知情權(quán)獲得憲法性權(quán)利的地位。”〔21〕
“清單”論也表現(xiàn)為為某些權(quán)利尋找“憲法依據(jù)”的主張。“信訪權(quán)”可能是一個典型的例子。〔22〕持此觀點的學者把信訪權(quán)同憲法第41條聯(lián)系起來,〔23〕似乎如果不指出這種聯(lián)系,侵權(quán)行為的發(fā)生就可以歸因于憲法文本自身的缺陷而不是其他,甚至暗示侵權(quán)情有可原。但是,當前上訪所面臨的困境是由于缺乏憲法根據(jù)嗎?一個簡單的事實就可以說明“上訪權(quán)”的存在意味著什么——在那些政治過程(選舉制度和表達自由)有效運作的國家,上訪既不存在也無必要。由于受到日常民意約束的官員,民治政府有足夠的動力回應公民的訴求,并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或“萌芽狀態(tài)”。說到底,上訪是正常的政治渠道堵塞的結(jié)果,矛盾和訴求從體制外尋求突破,顯示的不是憲法文本性制度的知識性缺陷,而是促使其運轉(zhuǎn)的動力不足。
對憲法權(quán)利清單的迷戀,還表現(xiàn)為追求權(quán)利主體的細化。例如由于城鄉(xiāng)二元格局、社會保障權(quán)不平等、農(nóng)民工權(quán)益受損等問題的存在,農(nóng)民權(quán)益的衰微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有人據(jù)此提出了“農(nóng)民權(quán)利”概念,甚至主張出臺一部“農(nóng)民權(quán)利保護法”。〔24〕的確,有些權(quán)利的主體需要特定化,例如對婦女、兒童、外國人某些權(quán)利的保護,但其必要性在于普通立法無法涵蓋這些特殊主體的某些利益。“農(nóng)民權(quán)利”則不然,它的狀況不佳是由于一般的公民權(quán)利沒有得到落實的結(jié)果——由于缺少有效地表達渠道,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和社會利益主張無法充分實現(xiàn)。但是,善意的想法是多余的嗎?為農(nóng)民單獨立法難道不更有助于對其權(quán)利保障嗎?問題很簡單:權(quán)利主體的特定化削弱了一般性的“公民權(quán)利”共識,它不但增大了立法者的思維負擔,也給司法部門解釋權(quán)利制造了更多的含混。根本的問題在于,“農(nóng)民權(quán)利”訴求轉(zhuǎn)移了人們的視線,忽視了他們權(quán)益受損系源于政治參與渠道堵塞這一基本事實。如果一般性的公民權(quán)利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到底列舉出多少主體才能最終解決問題?
“清單”論錯誤地把問題歸結(jié)為“法律不健全”以及憲法文本的技術(shù)性缺陷,而這恰恰是對憲法權(quán)利和自由價值的貶損。如果把知情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當做手段性權(quán)利列入憲法權(quán)利清單,那么其他手段就可能由于沒有明確寫入而變得無需保護。要知道,“自由”的特征恰恰在于無法一一列舉。因此“清單”論不但難以厘清憲法權(quán)利的含義,反而背離了這一目的,它無可避免地使憲法權(quán)利陷入更加含混的境地。對此,彼得·奧德舒克(PeterOrdeshook)已經(jīng)指出了:
“為了避免實施中的模棱兩可,這項憲法想做的太多,簡直成了判斷政府侵犯人們生活方面的文件。在試圖避免這種不民主的結(jié)果以及防范各種潛在的專斷時,不可避免地就會試圖增加進一步的禁令,行政命令、立法命令以及大量的權(quán)利訓誡。但這樣做只會使問題更加復雜化,因為它只給我們期待實施的文件又增加了一頁。第二個以及相關(guān)的錯誤是對文字的濫用。契約式憲法的具體內(nèi)容只能用文字加以明確;不幸的是,這僅僅為更為模棱兩可得條文大開方便之門。對于條文中所使用的每一個單詞,我們必須用十個單詞來詮釋,而其中的每一個詞有需要用另外十個單詞來修飾。”〔25〕
清單論的危險還在于,它試圖一廂情愿、一勞永逸地設(shè)定權(quán)利的含義和邊界。但這一“哲學王”式的抱負既是不必要的,也不可能成功。正如德沃金所說的,權(quán)利在有一個確定的核心的同時,也可以有一個變動的邊緣。〔26〕在一個民主社會,權(quán)利的邊界可以根據(jù)情勢有所變動,它并不依賴于成文法的明確界定。以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對憲法的理解為例,之所以存在司法能動主義與消極主義的對峙和交替,恰恰是因為存在一個有效運轉(zhuǎn)的政治審議過程。當一些問題需要由議會政治過程去決定時,天平向司法消極主義傾斜;當問題需由獨立的法院去決定時,司法能動主義就會獲得更多的同情。二十世紀
五、六十年代的沃倫法院時期,社會支持法院推動平等權(quán)運動,司法能動主義大行其道;
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國社會漸趨穩(wěn)定,法院的能動角色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懷疑,強調(diào)公民政治參與的“新共和主義”抬頭,以國會為中心的政治過程被重新看重,馬克·圖什奈特(MarkTushnet)甚至提出“將憲法從法院手中拿走”〔27〕。司法審查雖常常與政治民主針鋒相對,二者卻也總是相伴而生,前者實為后者的“保健措施”,此為立憲主義的要義。總之,對憲法權(quán)利清單的迷戀,同樣顯示了我國當前在權(quán)利保障上由于政治渠道的堵塞而形成的不可救藥的路徑依賴——依賴立法專家的智慧明確法律權(quán)利的含義。
“清單”論的目的毋庸置疑,但與其說它提供了保障權(quán)利的希望,毋寧說把權(quán)利保障推向了一條不歸路:到底這份清單有多長,才能窮盡憲法權(quán)利的子項目呢?或許可以說,它本身就印證了權(quán)利保障面臨的困境,這何嘗不是權(quán)利沒有得到實施和保障的結(jié)果帶來的無奈反應呢?公民權(quán)利的含義本來可以在公共討論、政治過程和司法適用中界定得足夠清楚。
五、用違憲審查保障人權(quán)?
對完美憲法文本的渴望,很容易激起人們對違憲審查的青睞,盡管這一制度在西方并不以完美的憲法文本為前提。在我國,“孫志剛案”等一系列惡性事件的發(fā)生,使得學者們更加迫不及待地把違憲審查同人權(quán)保障聯(lián)系起來。問題被歸咎于缺乏明確宣告的權(quán)利法案,違憲審查也成了保障人權(quán)的不二法門。“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刻不容緩”〔28〕,而且成了“公民基本權(quán)利保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29〕。
但是,一個也許會令權(quán)利憲法化論者們無法接受的事實是,違憲審查本不是用來保障人權(quán)的。〔30〕那個讓我們耳熟能詳?shù)膭?chuàng)設(shè)了司法審查權(quán)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31〕,或許最能揭示違憲審查與人權(quán)保障的真實面相:馬歇爾大法官正是通過犧牲馬伯里的個人權(quán)利——擔任治安法官的機會——來確認違憲審查權(quán)的。有西方學者已經(jīng)指出了,沒有司法審查制度的國家,在憲法權(quán)利的保障方面并不次于、甚至好于有嚴格違憲審查制度的國家。〔32〕了解一下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歷史會發(fā)現(xiàn),它在保障人權(quán)方面的記錄并不都是光彩的。要不是坦尼法院時代最高法院反復確認奴隸制的合憲性,斷絕了通過司法渠道廢除奴隸制的可能性,也許南北戰(zhàn)爭就不會發(fā)生。〔33〕從1885年到1935年間,美國的州和聯(lián)邦法院撤銷了150多部勞動立法。〔34〕公眾在立法機關(guān)得到支持的權(quán)利,在法院卻遭到反對。在新政時代,最高法院拒絕禁止童工、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和改善工人勞動條件的立法;〔35〕二戰(zhàn)以后,最高法院與激進的國會勢力沆瀣一氣,加入了對共產(chǎn)黨的政治迫害隊伍。
的確,法院也利用違憲審查權(quán)推進人權(quán)保障,但實際上,當今世界上那些運作良好的違憲審查機構(gòu)——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德國憲法法院、法國的憲法委員會,都是為了劃定權(quán)利的具體邊界,而不是在原則上重申基本人權(quán)這一價值。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紐約時報訴薩利文案、米蘭達訴亞歷桑那州案、羅伊訴韋德案、得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等〔36〕一系列為我國學者津津樂道的憲法案例中,聯(lián)邦最高法院都被認為是在用司法審查來維護人權(quán)。但是試想:法院做出相反的判決就是在侵害人權(quán)嗎?在這些案例中,受到審查的國會立法和政府行為并非因為明目張膽地否定人權(quán)而被宣告無效。可以說,類似于孫志剛案之類的赤裸裸地侵權(quán)案例,在民主體制中根本不會進入最高法院的審查范圍,有效運轉(zhuǎn)的基層政治過程提供了足夠的機會預防和解決這類事件。
至少美國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權(quán)利法案和司法審查是為了防范民主過程的危險而設(shè)置的,它是民主政治的減肥藥,旨在促進民主肌體的健康;它警惕政治過程,但如果離開了政治過程也無法發(fā)揮作用。回到我國的情況,如果我們還沒有胖起來,減肥藥的必要性何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尚有待發(fā)揮其應有的政治審議、監(jiān)控公共權(quán)力的功能,表達自由的實現(xiàn)也還任重道遠。而且,恰恰是以各級人大為中心的政治過程的失靈——公民無法通過周期性的選舉制度和日常性的表達自由向政府傳導訴愿,引發(fā)了大量的侵權(quán)事件,并使得思想界慌不擇路地將壓力傳導至“法治”渠道——權(quán)利法定化、憲法化以及憲法監(jiān)督制度。“國情論”出人意料地在這一問題上嘎然而止,主張大膽引入西方制度。個中原因可能是,相比于改善政治過程,違憲審查所代表的“法治”路徑既冠冕堂皇又政治正確。在這條道路上,人們癡迷于以違憲審查為核心的憲法機制,幻想其神奇功效可以不依賴政治過程就能解決源源不斷的侵權(quán)問題,而這是何等的誤解!
六、憲法陀螺的動力
作為一個西方舶來品,“人權(quán)”思想三十年來在中國的發(fā)展是具有高度選擇性的。聯(lián)合國于1948年頒布的《世界人權(quán)宣言》,既是人權(quán)在抽象層面上成為各國普適價值的一個標志,也是人權(quán)學說的具體主張發(fā)生分裂的一個開端。一些國家強調(diào)傳統(tǒng)的公民權(quán)利和政治權(quán)利,一些國家則對社會權(quán)情有獨鐘。傳統(tǒng)人權(quán)學說在為中國人權(quán)理論提供思想資源的同時,也構(gòu)成了批判和審視的對象。在“特殊國情論”、“東方價值觀”、“中國模式說”等命題的支持下,中國人權(quán)研究整體上呈現(xiàn)出懷疑、疏遠甚至否定傳統(tǒng)人權(quán)學說的趨勢,在人權(quán)的普遍性、人權(quán)主體論、人權(quán)的內(nèi)容、保障方式等諸多具體方面提出了嚴峻挑戰(zhàn)。〔37〕“權(quán)利憲法化”的是與非,可以置于這一大背景下來加以檢討。
“權(quán)利憲法化”最為關(guān)注的是種種“社會權(quán)”——生存權(quán)、發(fā)展權(quán)、環(huán)境權(quán)、受教育權(quán)等,它善意而積極地回應了當代中國對相關(guān)社會問題的不安,其權(quán)利啟蒙意義不容置疑,但內(nèi)在的邏輯也令人擔憂。“三代人權(quán)”理論是這種選擇性賦權(quán)的理論基礎(chǔ)。〔38〕將人權(quán)以“代(generation)”來指稱,無論是在英文還是中文里,都意味著老的勢將死去,新的才值得歡呼。第一代人權(quán)所表征的公民權(quán)利和政治權(quán)利,盡管也是我們的“憲法權(quán)利”,卻被認為應由“新人權(quán)”取而代之。在權(quán)利憲法化論者看來,三代人權(quán)保障的利益截然不同,因此可以任加取舍。這樣,雖然同屬憲法權(quán)利,命運卻截然不同,傳統(tǒng)的公民和政治權(quán)利在“具體化”和“清單化”的主張下遭受了貶抑:既然中國社會面臨的緊迫需求是改善社會保險、社會保障和環(huán)境問題,突出其憲法地位便是理所當然的了。
即使是當下主張監(jiān)督權(quán)、知情權(quán)這些意在強化公民政治權(quán)利的主張,也與傳統(tǒng)憲法權(quán)利的基本要求有所不同,它在政治和司法過程之外界定含義的要求本身,就顯示了與傳統(tǒng)公民權(quán)利中的表達自由劃清界限的內(nèi)在沖動。如果像有些學者所主張的,所有憲法權(quán)利的含義都要由法學家去界定、立法者去描述、執(zhí)法者去落實,公民對這些權(quán)利和自由進行理解的余地就會越來越小,理解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弱。當然,這可能是一些學者始料未及且不愿意看到的結(jié)果。
“權(quán)利憲法化”訴求誤解了傳統(tǒng)公民權(quán)利和政治權(quán)利的功能及其與社會性利益的關(guān)系。如前所述,在許多國家,保障公民社會性權(quán)利的主要方式還是政治渠道。其對傳統(tǒng)公民權(quán)利和政治權(quán)利的看法是:它們不僅是保持個人人格完整的“天賦權(quán)利”(自然法學說和康德主義),而且是促進公共生活健康的必要手段(功利主義)。拒絕第一代人權(quán),意味著在肯定第
二、三代人權(quán)的同時否定其必要的實現(xiàn)手段。羅伯特·達爾(RobertDahl)提醒我們不要誤解美國憲法體制的安排:“憲法規(guī)則并不是維持民主制的關(guān)鍵的、獨立的要素……憲法規(guī)則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有助于確定在政治競爭中哪些特定集團將獲益或受損……認為因為有憲法才民主顯然是倒果為因;相反,美國憲法之所以能夠維持,正是由于我們的社會實質(zhì)上是民主的。”〔39〕
如果把書面的憲法體制安排比喻為一個美麗的陀螺,那么使其運轉(zhuǎn)起來的力量卻來自于外部——公民自主性的和平等的參與。理查德·貝勒梅(RichardBellamy)說,“一個民主社會中為法律立憲主義者所期待的權(quán)利、平等對待,來自于政治性的憲法,它體現(xiàn)于民主本身。”〔40〕麥迪遜在《聯(lián)邦黨人文集》第51篇中也提示我們:憲法文本中的分權(quán)安排對于保障人民的自由來說只是“輔助性的預防措施”,而“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41〕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費城制憲會議形成的憲法文本的全部篇幅只是涉及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的設(shè)計而不包含權(quán)利條款,以及為什么被視為對憲法進行了經(jīng)典闡釋的《聯(lián)邦黨人文集》幾乎通篇都在不厭其煩地討論如何設(shè)計政治過程的細節(jié)了。
根本的問題不在于以違憲審查為標志的憲法規(guī)則如何完備,而是如何促使以公民參與為中心的政治過程能夠有效地構(gòu)造一個責任制政府。我們相信,如果對社會權(quán)的訴求能有向政府傳導壓力的制度性機會,侵權(quán)事件將在根本上減少,而不是僅通過違憲審查來從結(jié)果上消極回應如潮的侵權(quán)之訴。在這一點上,必須廓清現(xiàn)代立憲主義對政治過程的警惕和中國對政治過程的需要,二者并不沖突。違憲審查是以政治過程的充分運轉(zhuǎn)為前提的,它不只是憲法系統(tǒng)的終端,而必須首先依賴于政治過程對侵權(quán)事件的有力阻滯,只有當赤裸裸地侵權(quán)危險被化解于政治過程之內(nèi)時,審查機構(gòu)才能憑借司法獨立氣定神閑地處理遺留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審查機構(gòu)既無需就范于政府對公共利益的訴求而忽視個人權(quán)利,也無需“見義勇為”式地討好大眾。我國當前面臨的情勢與此不同,我們一方面艷羨他國違憲審查機制之效能,另一方面卻忽視了此種效能之政治前提,其結(jié)果必然是,由于大量社會性訴求夾雜著正義激情涌入司法過程,法院的“隔離、中性化和冷卻功能”無處存身,它必須像政治部門一樣去機會主義地處理專業(yè)性極強的法律問題。這必然在根本上瓦解作為違憲審查機構(gòu)安身之本的獨立和超然品質(zhì)。這種風險是根本性的,它可能最終導致政治過程與司法過程的雙重失靈。因此對于中國來說,即使我們對違憲審查情有獨鐘,也必須首先將我們稀缺的注意力轉(zhuǎn)向政治過程的改善。
回過頭來,再從另一個角度理解為我國學者津津樂道的違憲審查制度。約翰·哈特·伊利的解釋是啟發(fā)性的:司法審查的功能不是要在政治過程之外提供保障權(quán)利的路徑,而是要疏通政治過程。它不關(guān)心社會權(quán)利,是因為相信那些利益的實現(xiàn)依賴一個設(shè)計良好的政治過程。伊利指出,違憲審查通過治理政治過程的失靈而獲得正當性。政治過程可能在兩種情況下失靈,“一種是在任者堵塞了政治變革的渠道以保證他們繼續(xù)在任,未當選者繼續(xù)落選;另一種是,盡管沒有人真正忽視一種意見或一個投票權(quán),但一個有影響的多數(shù)支持的代表會有計劃地損害少數(shù)群體的利益。”〔42〕伊利認為,法官因享有終身任職保障,遠離黨派之爭,能夠客觀地接觸和解決由于對民主的不信任產(chǎn)生的爭議,其方式就是通過捍衛(wèi)言論自由和為少數(shù)派找到合適的代表來疏通治道變革的渠道。〔43〕司法審查不只是法律性的,它也是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它是政治審議的重要參與者。由此可見,與當代如火如荼的違憲審查制度浪潮并存的現(xiàn)實是,“對政府行為的憲法約束在某種程度上正在被民主監(jiān)控所取代。同樣,對多數(shù)決定規(guī)則的實質(zhì)性憲法約束,已經(jīng)為程序性控制所取代。……如果法律是由按適當方式選出的國會制定,并通過適當?shù)膮⑴c程序加以執(zhí)行,那么,對憲法約束的需求就可能顯得不那么迫切了。”〔44〕原來,健康的政治過程的本身,能夠大大緩解對違憲審查制度和“權(quán)利憲法化”的需求壓力。
結(jié)論
公民權(quán)利的保障主要應該依賴政治過程:選舉壓力、表達自由以及由此形成的政府責任,而不是權(quán)利憲法化和違憲審查。對政治過程的憲法確認——周期性的選舉過程(有利于多數(shù)派)和日常性的表達自由(有利于少數(shù)派)——雖然并不直接提供利益,但它是公民主張利益的基本途徑。這一觀點比權(quán)利憲法化論者更多地注意到了消極權(quán)利和積極權(quán)利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傳統(tǒng)的公民權(quán)利和政治權(quán)利不僅是個人自由的保障,而且是公共生活的平臺,它們不是政府的對立面,它們就是政府本身。權(quán)利憲法化在道德上毋庸置疑,它回應了當前中國嚴峻的社會問題,也真切地表達了公民的訴求。遺憾的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可能比問題本身還糟,它把注意力從更為根本的權(quán)利保障渠道——政治渠道——上轉(zhuǎn)移開來,使得我國本不完善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面臨進一步功能失調(diào)的危險;它忽視了社會組織在維護公民利益方面的功能,并且為清晰地理解權(quán)利體系設(shè)置了障礙。我們在權(quán)利憲法化之路上高歌猛進,反映的是在民眾參與之路上的挫折與無奈;它增強了權(quán)利意識,卻貶低了民主過程;它提升了憲法的聲譽,卻誤解了憲法的功能;它大聲告訴人們要“為權(quán)利而斗爭”,卻忘記了應該首先減少侵權(quán)的發(fā)生;它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設(shè)想,但也容忍了問題的產(chǎn)生。
綜上,本文的規(guī)范性結(jié)論可以概括為:1.阻止憲法權(quán)利項目的擴張沖動,以防止其必然導致的含混、無效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對公共權(quán)力合法性的挑戰(zhàn);2.通過激活縱向的分級政治審議,把公民的社會性訴求分散到不同層級的政治單元,以通過各級人大的政治審議過程逐步解決;3.改善非政府組織發(fā)展的法律環(huán)境,削弱社會對中央政府再分配能力的強烈訴求,并弱化公共權(quán)力借滿足權(quán)利訴求之機形成的擴張沖動。4.把權(quán)利憲法化的熱情轉(zhuǎn)向推進同為憲法權(quán)利的選舉權(quán)和表達自由,將利益訴求逐步移入政治過程加以消化,以減少社會矛盾集中性地向執(zhí)政黨、中央政府和司法系統(tǒng)聚集。這些方式會對我們深化體制改革形成壓力,但可能仍是最安全和最具誘導性、漸進性的方式。
注釋:
〔1〕相關(guān)的討論可參見溫輝:《受教育權(quán)入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殷嘯虎:《保障人權(quán)寫入憲法體現(xiàn)了政治文明的進步》,載《檢察風云》2004年第7期;孫凌:《論住宅權(quán)在我國憲法規(guī)范上的證立——以未列舉憲法權(quán)利證立的論據(jù)、規(guī)范與方法為思路》,載《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09年第5期;杜承銘、朱孔武:《“信訪權(quán)”之憲法定位》,載《遼寧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2〕李步云:《人權(quán)的三種存在形態(tài)》,載《法學研究》1991年第4期。
〔3〕秦前紅、陳俊敏:《人權(quán)“入憲”的理性思考》,載《法學論壇》2004年第3期。
〔4〕參見[美]阿奇博爾德·考克斯:《法院與憲法》,田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5〕RichardBellamy,PoliticalConstitutionalism:ARepublicanDefenseoftheConstitutionalityofDemocracy,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p.34.
〔6〕參見[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lián)邦黨人文集》,程逢如、在漢、舒遜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84篇。
〔7〕龔向和:《社會權(quán)司法救濟之憲政分析》,載《現(xiàn)代法學》2005年第5期。《魏瑪憲法》第二篇“德國人民之基本權(quán)利及基本義務”在規(guī)定傳統(tǒng)的自由權(quán)的同時,規(guī)定了許多有關(guān)健康權(quán)、藝術(shù)科研權(quán)、受教育權(quán)、住宅權(quán)、工作權(quán)、社會保障權(quán)等社會權(quán)內(nèi)容的條款。
〔8〕聶鑫:《憲法基本權(quán)利的法律限制問題》,載《中外法學》2007年第1期。
〔9〕對德國魏瑪憲法失敗原因的反思是多方面的:總統(tǒng)緊急狀態(tài)權(quán)力、經(jīng)濟困難以及比例代表制等。尚未有學者把魏瑪憲法的失敗歸于社會權(quán)入憲這一原因的,本文在此提出這一問題是嘗試性的,僅作為支持論題的一個經(jīng)驗性證據(jù)。
〔10〕王利銳:《公益慈善社團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重要力量》,載《理論界》2006年第7期。不少學者指出,非政府組織的導入有助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在實踐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可以通過互補性合作來合理、充分地發(fā)揮它們的作用。可參見何曄、安建增、許琳:《供需分析與模式選擇:將NGO導入社會保障體系》,載《陜西省經(jīng)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11〕目前這一情況在兩個方面表現(xiàn)出來,一是非盈利性結(jié)社存在較大的法律障礙;二是由于對于捐贈者不能提供稅收優(yōu)待,社會組織由于缺少資金來源而供血不足。
〔12〕王文卿:《徘徊于理念與現(xiàn)實之間——“環(huán)境權(quán)入憲”的困境解讀》,載《法制與社會》2009年第4期。
〔13〕葉俊榮:《憲法位階的環(huán)境權(quán):從擁有環(huán)境到今與環(huán)境決策》,載《臺大法學論從》1990年第1期。
〔14〕周葉中主編:《憲法》(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61頁。類似的主張還可參見許博淵:《僅將人權(quán)寫入憲法是不夠的》,載《環(huán)球》2004年第7期。
〔15〕秦前紅、陳俊敏:《“人權(quán)”入憲的理性思考》,載《法學論壇》2004年第3期。
〔16〕王磊:《人權(quán)的憲法保護的幾個誤區(qū)》,載《法學家》2004年第4期。
〔17〕兩院制使得多數(shù)派意愿在轉(zhuǎn)化為法律時能夠自我約束;行政否決權(quán)和司法審查是對立法機關(guān)的外部約束;憲法權(quán)利法案則把一些重大的公民利益從立法審議過程中拿走,防止對其進行惡意的政治審議。《聯(lián)邦黨人文集》全書即對此所做的經(jīng)典說明。
〔18〕《集會游行示威法》(1989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0次會議通過)就有違反憲法的嫌疑,首先在制定機關(guān)方面,該法律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而不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涉及公民基本人權(quán)的內(nèi)容應當由全國人大來制定;其次,在內(nèi)容方面,該法共有36條,其中有10個“不得”,1個“不能”,7個“必須”,四種“不予許可”的情況,三種“應當予以制止”的情況,以及6條法律責任。相關(guān)討論參見王磊:《人權(quán)的憲法保護的幾個誤區(qū)》,載《法學家》2004年第4期。
〔19〕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可參見黃士元:《程序是否需要“法定”?》,載《中外法學》2006年第4期。
〔20〕徐璐:《知情權(quán)入憲之探討》,載《法制與社會》2007年第12期。
〔21〕趙方:《知情權(quán)入憲之途徑構(gòu)想》,載《法制與社會》2009年第11期。
〔22〕杜承銘、朱孔武:《信訪權(quán)之憲法地位》,載《遼寧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于建嶸:《保障信訪權(quán)是一項憲法原則》,載《學習時報》2005年1月31日。有人主張,上訪既然是憲法第41條保障的“憲法權(quán)利”,那么“逐級上訪”、“越級上訪”也是憲法權(quán)利,“上訪遣送”和“上訪拘留”是違憲的。參見劉大生:《上訪是公民的憲法權(quán)利》,載《紅旗文稿》2004年第2期。
〔23〕我國憲法第41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guān)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quán)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guān)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guān)國家機關(guān)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quán)利”,“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guān)國家機關(guān)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
〔24〕李國綱:《對<農(nóng)民工權(quán)利保護法>立法的思考》,載《云南財貿(mào)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25〕[美]奧德舒克:《立憲原則的比較研究》,載《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第128-129頁。
〔26〕[美]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quán)利》,信春鷹、吳玉章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
〔27〕MarkTushnet,TakingtheConstitutionAwayfromtheCourt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9.
〔28〕李步云:《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刻不容緩》,載《法制日報》2001年12月2日。
〔29〕周菁、王超:《憲法司法化散論》,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30〕參見姜峰:《違憲審查:一根救命的稻草?》,載《政法論壇》2010年第1期。
〔31〕Maburyv.Madison,1Cranch137(1803).
〔32〕〕WojciechSadurski,JudicialReviewandtheProtectionofConstitutionalRights,OxfordJournalofLegalStudies,Summer,2002.
〔33〕參見RobertH.Bork,TheTemptingofAmerica:ThePoliticalSeductionoftheLaw.NewYork:TheFreePress,1990.pp.28-30.
〔34〕JeremyWaldron,LawandDisagreemen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p.288.
〔35〕1916年國會通過禁止童工的法律,最高法院在1918年以5:4的比例判定其違反憲法,國會重又通過類似法律,結(jié)果1922年再次被否決。憲法修正案因為沒有達到2/3而沒有通過,但國會在1938年再次通過反童工立法,直到1941年,最高法院才認可它。參見:RobertDahl,DemocracyanditsCritics,NewHe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9,p.359,n.8.在洛徹那案中,最高法院以保護自由契約為名,推翻了國會制定的限制最長工作時間的立法。參見Lochnerv.NewYork198US45(1905).
〔36〕Brownv.BoardofEducationofTopeka,347U.S.483(1954);NewYorkTimesCo.v.Sullivan,376U.S.254(1964);Mirandav.Arizona,384U.S.436(1966);Roev.Wade,410U.S.113(1973);Texasv.Johnson,491U.S.397(1989).
〔37〕對當代中國人權(quán)理論的批判性反思,可參見姜峰:《多元世界中的人權(quán)觀念——自由主義人權(quán)理念之重申》,載徐顯明編:《人權(quán)研究》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8〕KarelVasak,"A30-YearStruggle:TheSustainedEffortstoGiveForceofLawtothe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inUnescoCourier.November,1977.Vasak把連帶權(quán)視為“第三代人權(quán)”,“三代人權(quán)”說就此成型:第一代人權(quán)即生命權(quán)和政治參與權(quán),第二代人權(quán)即經(jīng)濟、社會、文化權(quán)利,第三代人權(quán)即和平權(quán)和環(huán)境權(quán)等連帶權(quán)利。
〔39〕轉(zhuǎn)引自[美]奧德舒克:《立憲原則的比較研究》,載《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第95頁。
〔40〕RichardBellamy,PoliticalConstitutionalism:ARepublicanDefenseoftheConstitutionalityofDemocracy,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p.8.
〔41〕《聯(lián)邦黨人文集》第51篇,第264頁。
〔42〕[美]約翰·哈特·伊利:《民主與不信任》,朱忠
一、顧運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頁。
〔43〕參見《民主與不信任》第五章“清理治道變革的渠道”和第六章“有利于代表少數(shù)群體”。對這本著作的評論,可參見LaurenceTribe,“ThePuzzlingPersistenceofProcess-basedConstitutionalTheories,”89YaleLawJournal.1063(1980);朱中
一、顧運、楊海昆:中譯本代譯序“司法審查——從對民主的制度的不信任出發(fā)”;汪慶華:《對誰的不信任?——評Ely<民主與不信任>中譯本》,載《中外法學》2004年第5期。
〔44〕[美]約翰·埃爾斯特等編:《憲政與民主》導言,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