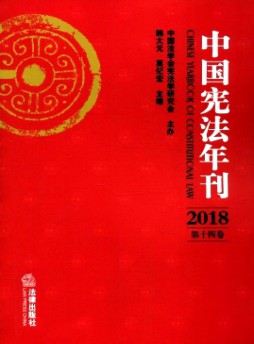憲法能力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憲法能力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關(guān)鍵詞:憲法能力/中國憲法/制度正義/社會團結(jié)
內(nèi)容提要:憲法能力意指作為一種規(guī)范的憲法在統(tǒng)攝政治資源、調(diào)控政治過程、規(guī)約政府行為以及導引社會價值等方面的資質(zhì)及其影響力。憲法的涵攝力、規(guī)約力和導向力構(gòu)成了憲法能力的三個核心要素;超驗、經(jīng)驗和理念構(gòu)成了憲法能力的三個基本淵源;制度正義導向力、法治政府型塑力和社會團結(jié)凝聚力分別構(gòu)成了憲法本源性能力、本能性能力和本質(zhì)性能力。面對其日益緊迫的時代使命,中國憲法的能力障礙也日益凸現(xiàn),憲法能力建設(shè)也因此而成為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課題。
在實體法學中,有責任能力之說,其中“能力”一詞意指一種“法律上的資格”;在程序法學中,有證據(jù)能力之說,其中的“能力”一詞意指證據(jù)的“證明力”或者“可采性”。本文之所謂憲法能力,意指作為一種規(guī)范的憲法在統(tǒng)攝政治資源、調(diào)控政治過程和規(guī)約政府行為以及導引社會價值等方面的資質(zhì)及其影響力。
一、憲法能力之解析
在何種意義上探討憲法能力?判斷憲法能力的基本立場是什么?以及構(gòu)成憲法能力的核心要素是什么?這是我們討論憲法能力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
(一)作為功能主義范疇的憲法能力
在這里,憲法能力是一個純粹的功能主義范疇。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功能主義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德和斯賓塞的著作中,后來的迪爾凱姆、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馬林諾夫斯基對其作了較為系統(tǒng)的闡述。功能主義將整個社會理解為一個功能性的系統(tǒng),組成系統(tǒng)的每一個部分都因其特定的功能而為系統(tǒng)的維持作出一定的貢獻——這個系統(tǒng)得以維續(xù)的基本條件就是組成系統(tǒng)的各部分之間在功能上保持協(xié)調(diào)或平衡。如果組成系統(tǒng)的某個部位在功能上出現(xiàn)故障或者發(fā)揮不能的時候,為維持這種功能上的平衡或者協(xié)調(diào),就有必要由另一個部分來代行這種功能,否則整個系統(tǒng)就將因為功能上的障礙而陷入失衡甚至崩潰的狀態(tài)。[1]122作為政治社會的有機組成分子,憲法是一種功能性存在——憲法因其功能而存在,而且憲法之存在是作為政治社會整體的一部分而發(fā)揮作用。易言之,憲法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其所在的政治社會整體對其有所需求。[2]111而社會整體之所以對憲法之存在有所需求,就在于憲法具備某種能力,而且這種能力為憲法所獨有,具有不可替代性。這就意味著,憲法因功能而存在,功能則由能力所決定。
(二)憲法能力的兩個判斷立場
立場決定判斷,對于同一種事物,站在不同的立場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jié)論。因為立場不同,意味著判斷者所處的語境與偏好有差異,正是這種差異,決定了判斷結(jié)論的差異甚至對立。長期以來,法學研究存在兩種基本立場:一是所謂應(yīng)然,意指在理想模型中事物應(yīng)該達到的狀態(tài);二是所謂實然,意指事物在現(xiàn)實條件下實際存在的狀況。
就其應(yīng)然立場而言,憲法既是國家政治資源配置的總方案,也是使政府服從規(guī)則控制的公共事業(yè),它的存在取決于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它具備充分的政治資源統(tǒng)攝能力、政治過程的調(diào)控能力和政治生活的導向能力——當我們不得不歷史性地將國家政治資源總體配置的機能交給憲法來完成的時候,我們事實上就承認了這么一個前提性假設(shè),即憲法對國家政治資源的統(tǒng)攝能力是充分的,而且憲法對政治資源的統(tǒng)攝狀態(tài)是完整的。唯其如此,憲法對于政治資源的總體配置才具有可能性和有效性。同理,當憲法不得不歷史性地承載著人們規(guī)控政府的愿望與訴求的時候,我們也在事實上預(yù)設(shè)了這樣一個邏輯前提,那就是憲法對于政治運作的規(guī)控能力是充分的,而且這種充分的規(guī)控能力之效力貫穿于政治運作的全過程。唯其如此,確保載滿人類塵世希望的國家政治之舟在憲政航道上的運行才成為可能。[3]45-53
然而,在其現(xiàn)實意義上,憲法之于國家政治資源的吸附并非像海綿吸水一般的徹底,其對政治資源的統(tǒng)攝因此也并非總是充分的。一旦憲法對資源的統(tǒng)攝存在缺漏,那些游弋于憲法之外的政治資源就很可能成為政治主持者或者參與者競相爭奪的目標,其結(jié)果不僅勢必打破依據(jù)憲法所構(gòu)設(shè)的政治資源配置上的平衡,而且也必對整個憲政秩序構(gòu)成挑戰(zhàn)和威脅。[4]與此相類似,由于政治運行的實際環(huán)境與理想模型相去甚遠,而且總是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tài),這就注定憲法對于政治運作過程的規(guī)控通常也是不充分的,而憲法規(guī)控的不充分性勢必催生政治過程或者政治領(lǐng)域的某些“憲法真空地帶”,這種“真空地帶”構(gòu)成了憲政大堤的“蟻穴”,除非存在某種補救機制,否則,這種“蟻穴”必將敗壞整個憲政體制的根基。[5]147在這個意義上說,憲法對于政治過程的實際規(guī)控能力是有限的,它必須借助于某種補救機制才能夠完整對政治的全過程實行有效規(guī)制的使命。
迄今為止的經(jīng)驗表明,應(yīng)然世界和實然世界總是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差異性,二者完全相同的情形幾乎是不可能的。同理,站在應(yīng)然或者實然的不同立場,我們看到的憲法能力是不同的,易言之,憲法的應(yīng)然能力和實然能力并非完全一致,相反二者往往存在著無法避免的差距。當然,立場是可以轉(zhuǎn)換的——盡管有其社會生活環(huán)境所決定的特定思維方式往往不具有可選擇性,但是由于生活場景的改變或者受使命感的驅(qū)使,不同立場的相互轉(zhuǎn)變是完全可能的。這就意味著,憲法能力始終只能是一個具有相對意義的概念——應(yīng)然的憲法能力只有相對于實然的憲法能力而言才具有現(xiàn)實的意義,正如同實然的憲法能力只有相對于應(yīng)然的憲法能力才具有真實的含義一樣;而憲法能力本身則只有相對于其他規(guī)則在相似的政治領(lǐng)域中的影響力而言,才具有真實的意義。
(三)憲法能力的三個基本要素
在其最一般的意義上而言,我以為涵攝力、規(guī)約力和導向力構(gòu)成了憲法能力的三個核心要素。
其一,憲法的涵攝力。所謂涵攝力是指憲法的包容力、感召力和整合力的總稱,它構(gòu)成了憲法能力的精神性要素。具體而言:
包容力是憲法的第一精神要件,它既是憲法作為一種文明之存在的標志,也是憲法之所以成其為憲法的基本因素——憲法盡管不能包羅萬象,但是憲法必須對人的多樣性和社會的多元化具有足夠包容力,從而使得所有人都能夠在憲法的框架內(nèi)找到自身應(yīng)有的位置。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的人必須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樣才能得到它所想要得到的東西,并躲開他不想得到的東西。[6]79
有包容力而后才有感召力。韋伯認為感召力是“歷史上的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力量,并且是對科層制的僵硬性的不可缺少的緩解劑”。[7]89據(jù)此,憲法的感召力實際上就是憲法影響和改變政府和社會心理和行為的一種品格,在一個缺乏憲法感召力的社會,公民的政治行為完全受制于個體理性的支配,并最終導致了集體的非理性,即不管“其他人會怎么做,我最好的選擇就是不合作(個體理性)”。如果所有的人都這么想,那么這個社會必因缺乏最低限度的向心力而瓦解。[8]117憲法的感召力是憲法信仰得以培植的基本條件。
社會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逐漸整合起來的一個有機體。這個被整合起來的有機體內(nèi)在地存在著某種分離的趨勢,所以社會整合是一個與社會同始同終的動態(tài)過程。在人類的早期,社會整合主要依存于圖騰和宗教的力量。正如同迪爾凱姆在論述宗教和圖騰的社會整合功能時所說那樣,一旦人民因為對同一種圖騰的崇拜而聚集在一起,一種熱情就通過他們的集體形成了,并且極快地在他們中間傳播而達到非常濃烈的程度。[9]176這就是圖騰的意義,它象征著集體的生活和群體的力量;它既是集體生活的產(chǎn)物,也加強集體生活所依賴的社會聯(lián)系。因為在這種群體所經(jīng)驗和感受的禮拜形式中,個體會明顯地發(fā)現(xiàn)他已被集體情感所淹沒,他們會自愿地放棄個人所有,把自己的生命依附于群體的使命。[10]69現(xiàn)代社會,社會資源以及個人注意力的整合則更多地依賴于憲法,正是借助于憲法的凝聚力,不管組成社會共同體的個人或者不同政治勢力通過什么樣的方式有意無意地瓦解著社會的固有秩序,也不管這個社會之外的勢力通過什么方式?jīng)_擊著社會的固有團結(jié),這個社會仍可以牢固地維持著其內(nèi)在的和合。[11]201
其二,憲法的規(guī)約力。規(guī)約力是憲法的規(guī)范力、執(zhí)行力和威懾力的總稱,它構(gòu)成了憲法能力的規(guī)范性要素。具體而言:
規(guī)范力意指憲法對權(quán)力秩序的型塑、調(diào)試和監(jiān)控的能力。在其現(xiàn)實性上,除非憲法具備了足夠的規(guī)范力,以至于不僅能夠有效地規(guī)范體制內(nèi)的各種權(quán)力及其運行,而且可以成功地將體制外的各種政治力量及其行為納入憲政軌道,否則,權(quán)力秩序就只能是一種幻影。[12]40-42一旦權(quán)力無秩序,我們就會生活在一個瘋狂混亂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我們會被反復(fù)無常的且完全失控的權(quán)力斗爭折騰得翻來覆去,無所適從;人類試圖過一種理性的、有意義和有目的的生活的一切努力,都將在這個混亂不堪的世界里化為烏有。[13]220-222在這個意義上說,權(quán)力秩序的存在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基本前提,而憲法則是權(quán)力秩序真正的構(gòu)筑者和維護者。
執(zhí)行力意指憲法本身所具有的將其價值與規(guī)范現(xiàn)實化的能力。執(zhí)行力不僅是實現(xiàn)立憲目標、達成憲法使命的重要保障,而且是一國憲法能力的最直觀的表現(xiàn)。在法律移植和憲法成文化已經(jīng)普遍的時代,各國憲法在文本上的差異日益縮小,并在規(guī)范上存在明顯的趨同性。其所差異者,主要體現(xiàn)在執(zhí)行力上。在這個意義上說,執(zhí)行力已經(jīng)成為判斷一國憲法優(yōu)劣的核心指標;沒有執(zhí)行力的憲法就是最無能的憲法,一部無能的憲法,既無力達至其規(guī)約政治之目標,也無力完成其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它的存在顯然只具有紙面的意義。因此,憲法的規(guī)范力固然是無比重要的,但是如果這種規(guī)范力缺乏有效的執(zhí)行力作為保障,那么再理想的規(guī)范力也只能徒具皮囊。
威懾力則是憲法控制政治沖突和化解政治對抗的能力,即面對處于對抗狀態(tài)的不同政治勢力,憲法借助于其規(guī)范力和執(zhí)行力迫使對立各方放棄對抗走向合作的能力。憲法威懾力通常是以“違憲脅迫”為條件的,只有在被威懾者對于“違憲”產(chǎn)生足夠敬畏的條件下,憲法威懾才可能成立。對于政治對抗者而言,除非他們充分認識到“違憲的代價大大超過對抗所可能獲得的政治效益”的條件下,放棄對抗才成為可能。因此,如何將政治沖突控制在有益的范圍之內(nèi),并促使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對立各方“放棄對抗意圖”,便成為拷問憲法能力的一道難題——如果說,沖突是政治生活的常態(tài),那么對立則是憲政秩序最危險的陰謀家。因此,除非憲法具備了足夠的威懾力,否則,政治沖突就勢必會僭越憲法界限,并演變?yōu)檎螌梗欢螌箘t在任何時代都是政治共同體的掘墓人(在現(xiàn)代社會,憲法的威懾力是形成國家政治共同體之向心力的基本要素。國家既統(tǒng)一又充滿民主氣氛和活力的狀態(tài)就是向心力與離心力達到相對平衡的狀態(tài);若離心力大于向心力,則國家難免遭遇分崩離析的命運;若向心力大于離心力,各種政治勢力將看到聯(lián)合的好處大于對抗分離的風險而著力于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
其三,憲法的導向力。導向力是憲法的指示力、引導力和教育力的總稱,它構(gòu)成了憲法能力的價值性要素。具體而言:
指示力是指憲法本身所固有的指示或者昭示政治者如何行為的能力。如果說憲法是政治的航標,是一種昭示社會如何行動才可以達至正義和自由的燈塔,那么指示力則是航標之所以成其為航標“光”,或者是燈塔之所以成其為燈塔的“電”,沒有“光”的航標和沒有電的燈塔一樣,充其量只是一個擺設(shè)。所以,在一個缺乏憲法指示力的社會,不僅政治將迷失方向,而且整個政治共同體都將在黑暗中遠離正義和自由。
引導力是憲法引領(lǐng)社會和國家朝著理想目標而合力前行的能力。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是應(yīng)該有理想的,而任何形式的國家理想都必須依靠于社會合力才可以實現(xiàn)——但社會合力的形成似乎又必須借助于共同理想的引導才可能獲得。[14]638因此,憲法承載著為一個國家構(gòu)設(shè)共同的生活愿景和范式的使命,同時還擔負著引領(lǐng)社會朝著這個共同理想邁進的責任。其中后者更為關(guān)鍵,只有在憲法具備了足夠的引導力的條件下,人們對于憲法理想的訴愿才有可能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的行動。
如果說,普通法律的實現(xiàn)總是以某種程度的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話,那么憲法的實現(xiàn)則總是以某種程度的憲法認同為基礎(chǔ)——在其終極意義上而言,憲法的實現(xiàn)是以政府和公民具備最低限度的憲法認同為必要條件的,而憲法認同的產(chǎn)生固然與一個民族的傳統(tǒng)價值觀密切相關(guān),但更為根本恐怕還在于憲法自身的教育能力。在一個憲法自身教育能力低下的社會,顯然是不可能產(chǎn)生良好的憲法認同。
二、憲法能力之淵源
憲法能力之淵源問題,在本質(zhì)上是一個與憲法本身之正當性密切相關(guān)的問題。自近代以來,憲法本身之正當性就已然成為西方社會探討憲政命題的一種基本思維范式。結(jié)合學界就憲法本身之正當性的研究成果,我以為憲法能力主要有三個基本淵源,即超驗性淵源、經(jīng)驗性淵源和理念性淵源。
(一)憲法能力的超驗性淵源
迄今為止,許多人都確信“憲法有一種先在給定的能力”,這種先在給定的能力就淵源于憲法本身的超驗性。比如美國學者弗里德里希就視基督教為西方憲法之正當性和憲法能力之基本淵源。在《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一書中,弗里德里希確信作為西方世界最大政治成就的立憲政治就“植根于基督教的信仰體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義的政治思想之中”。[15]1他認為西方立憲政治賴以存續(xù)的基督教傳統(tǒng)中的正義,是一種具有某些超驗的氣質(zhì)和力量——盡管它扎根于世俗社會,但由于其受到基督教的洗禮而獲得了神圣氣質(zhì),并借助于這種神圣性,而成為匡約世俗正義的戒尺——圣·奧古斯說,真正的正義應(yīng)該是完全超驗的合乎邏輯的宗教推斷的結(jié)果,只有虔誠的信徒借助于神的恩典才可能達到,而永遠不可能在世俗共同體中找到。人世間所可能存在的最好的法律也不過是這種超驗正義的啟示與殘片或鏡像而已。[15]9正是這種具有神圣氣質(zhì)的超驗正義鑄就了西方源遠流長的自然法傳統(tǒng),正是這種“作為上帝統(tǒng)治世界的永恒法的具體體現(xiàn)”之自然法,“規(guī)定了真正的立憲政府”,而這種由超驗氣質(zhì)的自然法所規(guī)定的立憲政府“有賴于一種對人類堅定不移的信念,即人是理性的和向善的,因此,他能有效地參與到該政治制度之中,并通過選舉那些為他們說話的人來參與制定法律”。[15]41
在這個意義上說,西方語境中憲法的神圣氣質(zhì)是與生俱來的,這種與生俱來的氣質(zhì)集中表現(xiàn)在其人權(quán)法案之中——在西方立憲政治的話語體系中,人權(quán)并非源于憲法亦不取決于憲法而存在,而是先于憲法和政府的存在,人們制定憲法和成立政府的目的正是為了保障人們“原則上在沒有任何形式的政府之前就享有權(quán)利;這些權(quán)利乃是造物主的賜予物”。[16]10
與其神圣氣質(zhì)相匹配的是憲法的超驗?zāi)芰Γ簯椃ú粌H承載著超驗正義匡約世俗世界的使命,而且也因此具備了引領(lǐng)世俗世界邁向理想境界的能力。這種能力之所以具有高于一切的效力,恰在于它是淵源于“上帝的命令”。憲法正是借助于“上帝”的命令,來統(tǒng)領(lǐng)人世間紛繁復(fù)雜的政治生活——或許現(xiàn)代立憲主義并不情愿承認憲法的這種引領(lǐng)凡俗政治的能力是一種超驗的能力,但除了“超驗”之外,我們還有什么更恰當?shù)姆绞絹黻U釋憲法的這種統(tǒng)領(lǐng)世俗政治的絕對權(quán)威呢?至于這種權(quán)威是來自于虛擬的上帝抑或是抽象的人民,實在并非是最為重要的。在這個意義上說,以上帝的名義立憲和以人民的名義立憲并沒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其目的無外乎要為憲法這種統(tǒng)領(lǐng)政治的能力或者權(quán)威設(shè)定一個至高無上的淵源。
(二)憲法能力的經(jīng)驗性淵源
憲法是經(jīng)驗的產(chǎn)物,憲法學是以經(jīng)驗為根據(jù)的學問——盡管在憲法的歷史演進過程之中,理性或者邏輯的作用不可或缺,但與其他在社會演進的所有部門一樣,“經(jīng)驗所起的作用大于邏輯”[17]714——憲法與社會、語言、文字一樣都是依據(jù)歷史的順序逐漸演化而來的,而不是由任何人設(shè)計出來的,因而它不能以邏輯推理的方式加以重構(gòu)。[18]憲法可以發(fā)現(xiàn)并記載一切,但卻不能憑空制造一切,那種希望制定一個詳盡無遺的憲政制度,創(chuàng)制出一個嶄新秩序的企圖是不符合現(xiàn)實的。
憲法作為一種規(guī)范,和所有其他行為規(guī)則一樣,是人們對于大多數(shù)難以測定的情勢所作的一種應(yīng)對或調(diào)適。正因為人們不知道某一特定行動所可能產(chǎn)生的全部后果,所以,憲法對于行動的引導能力才被認為是必不可缺的——這就決定:人們對于憲法的遵守是不以對遵守或違背憲法所帶來的任何性質(zhì)后果的認知為條件的(在這個意義上引申地說,任何對規(guī)則的遵守都不應(yīng)當以特定的功利為條件。當守法的動機受功利的支配,那么,當人們受到比守法更大的功利的誘惑的時候,任何法律都將威風掃地。江國華:《立法價值——從禁鞭令的“尷尬”說起》,載《法學評論》2005年第6期);如果人們在行動之前的確什么都知道,那么憲法的存在也就不是必不可缺的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伯爾曼說人類生活在這個星球上,就像白克特劇中那兩個站在樹下等待戈多的人——靠著無可言說的溝通,靠著某種雖可依憑,卻沒有把握會被遵從的規(guī)則。但是,這才是人類,生存于這顆星球上的人類,他所需要的新的法律將因先在概念和程序的重建而出現(xiàn)。[19]145-146
正因為憲法不是為了滿足那些可預(yù)見的特定需求而制定出來的,而是在一個優(yōu)勝劣汰的進化過程中存續(xù)下來的;人類理性固然是賦予憲法以具體形式的基本條件,但人類理性及其發(fā)揮作用的基礎(chǔ)仍然是經(jīng)驗——賦予憲法具體形式的人類理性及其知識形態(tài)大多并“不是作為對人們所必須準備應(yīng)對的某些可列舉的情勢的認識而存在,也不是作為對人們應(yīng)予解決的那類問題的重要性的認識而存在,更不是作為對這些問題得以發(fā)生的可能性的認識而存在,而是作為在某些類型的情勢中以某種特定方式行事的一種傾向而存在的。”[20]29因此,憲法與大多數(shù)行為規(guī)則一樣并不是經(jīng)由一個智識的過程而推演出來的,相反,人類智識本身也遵循著與憲法大致相似的進化歷程,而且這種進程顯然主要是一種經(jīng)驗的過程——誠如詹姆斯所強調(diào)的那樣:經(jīng)驗的基本屬性乃是他的連續(xù)性;它是思想或者意識的源泉。[21]83
正因為憲法是經(jīng)驗的產(chǎn)物,經(jīng)驗才構(gòu)成了憲法能力的基本淵源——憲法的基本能力正是在經(jīng)過反復(fù)試錯和經(jīng)驗過程逐漸積淀和錘煉而成的。這就意味著“像所有為一般目的服務(wù)的規(guī)則一樣,憲法之所以能夠有助于一般性目的的實現(xiàn),實是因為它適合于解決那些反復(fù)出現(xiàn)且難以對付的情形,從而有助于那些奉行憲法的政府和社會成員能夠更為有效地追求各自的目的。正如人們打造一把刀子或鍛造一把錘子一樣,人們之所以按照某種形式來制造它們,并不是因為它們可以被用來實現(xiàn)眼下的某個特定目的,而是因為它們被證明以這種形式而不是以其他形式才能在各種各樣的情形中發(fā)揮有益的作用。”[20]29
(三)憲法能力的理念性淵源
人類是有理性的,人類憑借其理性的力量,不僅成為改造自然的主導者,而且也成為社會制度建構(gòu)的推動者。正是在理性的支配之下,人類對其思想和意志在改造自然和社會方面的主導作用深信不疑——人類在大多數(shù)情形下,都對其理性在決定事物的價值、分辨意見真?zhèn)我约芭袛嘈袨橹斝缘牧α砍錆M信心。而且,即便是最純粹的經(jīng)驗主義者也不否認理性在社會制度建構(gòu)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迄今為止的經(jīng)驗表明,在人類社會的所有領(lǐng)域中,都存在理性作用的痕跡。即便是在深深扎根于傳統(tǒng)與環(huán)境之中、似乎最不會順從理性主義的政治領(lǐng)域中,也須臾離不開理性的建構(gòu)作用。
龐德說:“法是通過理性所組織和發(fā)展起來的經(jīng)驗。”[22]110盡管“人類僅僅憑借其非凡的理性就能夠設(shè)計出一整套完善無缺、運行良好的理想制度”的說法多少有些偏頗,但人類“借助于憲法這種方式來謀求一種理想生活境界”的過程卻一刻也不能有理性的缺席——事實上,憲法之于政治的意義恰在于為合理的政治行動創(chuàng)設(shè)一種藍圖,并為通向這個歷史性目標而設(shè)置一種可欲的軌道。[23]在這個意義上說,理性之于憲法及其能力的形成和演進過程實際上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因素,憲法能力與憲法本身不可避免地帶有建構(gòu)性特征。唯其如此,美國學者埃爾金等人才將憲法學解讀為“為美好的社會設(shè)計政治制度”的學說。[24]3也正是受建構(gòu)主義的啟示,人類通過對經(jīng)驗的總結(jié)和抽象,并借助于憲法這樣一種形式,來謀劃一種理想的政治圖景和社會境界——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在實施憲法之前,就已知憲法所能夠達到的目標;毋寧是要強調(diào)我們在行動之前,必須先審視這種行為與憲法所意欲達至的目標是否兼容。
憲法能力的理念性淵源表明,面對憲法,人盡管沒有隨心所欲的自由;但憲法能力的發(fā)揮程度在相當程度上卻取決于人為的努力程度。所以,我們所能夠做的不是任意給憲法設(shè)定人為的目標,而是努力創(chuàng)造和維護一種環(huán)境,從而使得憲法的這種客觀的能力能夠得到最大可能的發(fā)揮功效。
三、憲法之核心能力
從前文分析可知,憲法能力是一個總括性或綜合性范疇,構(gòu)成憲法能力這一范疇的要素具有多元性。在通常情況下,如果我們無法窮盡該范疇的一切要素,那么任何企圖通過列舉的方式對于一項具有多元性要素的范疇所進行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甚至會導致對所研究范疇本身的誤讀。對于憲法能力這樣一個范疇也是如此。因此,我們只能用概括的方式,從制度正義導向能力、政府法治構(gòu)造能力和社會團結(jié)凝聚能力等三個層面對憲法本源性能力、本能性能力和本質(zhì)性能力等進行闡述。
(一)憲法的本源性能力:制度正義導向力
所謂本源性能力一指憲法與生俱來的、并對憲法其他能力具有始源性意義的能力,這種能力集中表現(xiàn)為憲法的制度正義導向能力——源遠流長的正義原則和思想借助于成文憲法這種形式轉(zhuǎn)變?yōu)橹贫日x,正是這種制度正義導向能力決定了憲法作為一種規(guī)范在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應(yīng)當說,人類思想史上關(guān)于制度正義的思考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比如柏拉圖認為,國家的正義是指這樣一種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和各盡其責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安排中,具有“金”本質(zhì)和智慧品質(zhì)的哲學家充當國家統(tǒng)治者,具有“銀”本質(zhì)和勇敢品質(zhì)的人士充當國家輔助者和衛(wèi)士,具有“銅鐵”本質(zhì)和節(jié)制品質(zhì)的人士從事國家生產(chǎn)建設(shè)事業(yè)。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城邦的正義主要是指關(guān)于政體制度的正義,它主要體現(xiàn)為對城邦公職的分配、享有問題的處置上;但政體制度要表現(xiàn)為法律規(guī)定,政體制度的正義要借助于法律來實現(xiàn)——如果說柏拉圖對國家正義的論述拓展了人們對正義的思考范圍的話,那么亞里士多德對國家(城邦)正義的論述則啟迪了人們對法律正義的思考。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后,制度正義和法律正義問題便成為政治哲學和法律哲學領(lǐng)域中的一個歷久常新的課題。延至今日,人們對制度正義問題的思考漸次集中于對國家政體結(jié)構(gòu)正義的思考,而政體結(jié)構(gòu)形式是由憲法所規(guī)定的,因此,在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法律的正義,因而也是憲法的正義。
憲法的正義是一種屬人的正義,其核心在于借助于一套系統(tǒng)的制度安排,以確保包括生命權(quán)、財產(chǎn)權(quán)、自由權(quán)在內(nèi)的最低限度人權(quán)免于國家或政府專橫權(quán)力侵犯的同時,為人之基本權(quán)利的有效保障設(shè)置了嚴密的司法救濟機制。[25]133在這個意義上說,憲法正義是一種制度性政治正義,它以人的最低限度的人權(quán)為起點,以人權(quán)的制度性保障為旨歸;它既確立了政府正義的基本原則,即“只有當我們按照憲法來行使政治權(quán)力時才是恰當?shù)模蚨攀钦斢欣淼模覀兛梢院侠淼仄诖械墓癜凑諏λ麄儊碚f是合乎理性的和合理的可接受原則與理想來認可這一憲法的本質(zhì)內(nèi)容。”[26]230同時,也為個人價值的彰顯提供了一種反抗專斷性強制的正當性依據(jù),為自由社會奠定基礎(chǔ)——“區(qū)別一個自由的社會與一個不自由的社會的判準乃是,在自由的社會里,每個個人都擁有一個明確區(qū)別于公共領(lǐng)域的確獲承認的私域,而且在此一私域中,個人不能被政府或他人差來差去,而只能被期望服從那些平等適用于所有人的規(guī)則。”[27]264
作為制度正義導向的憲法,首先規(guī)定了國家的主要制度,所謂主要制度,即“政治結(jié)構(gòu)和主要的經(jīng)濟和社會安排”,它“確定著人們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前景即他們可能希望達到的狀態(tài)和成就;”[28]149其次它指引著制度的價值取向,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系統(tǒng)中,就是制度為誰服務(wù)的問題,羅爾斯認為,制度正義要符合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每個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yīng)有一種平等的權(quán)利;”第二個原則是“社會和經(jīng)濟的不平等應(yīng)這樣安排,使它們一方面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wù)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29]86其三它為如何實現(xiàn)制度正義預(yù)設(shè)了主要的原則和規(guī)范——比如在羅爾斯看來,為了確保制度的“正義結(jié)果”,制度不僅在安排上要有一些階段和序列,而且制度內(nèi)部之間的價值原則以及制度與程序之間,還存在一個孰先孰后的優(yōu)先規(guī)則,大致包括以下幾個層次的內(nèi)容:在制度與程序之間,前者優(yōu)先與后者;在制度正義兩原則中,自由優(yōu)先于平等;在利益分配上,正義優(yōu)先于效率和福利;在個體與制度的關(guān)系上,既要強調(diào)制度對個人的剛性約束,又須重視個人對制度的道義性服從。[30]7
(二)憲法的本能性能力:法治政府型塑力
憲法既無法忍受無政府狀態(tài),也無法容忍任何形式的專制;正如人本身既痛恨一切形式的奴役,又始終排斥非自由狀態(tài)一樣。這是由其本能所決定的——但凡世俗世界的存在,皆有其本能,憲法亦不例外。其中,構(gòu)建法治政府無疑是憲法最重要的本能,基于這種本能,憲法不僅具有排斥一切形式之專制政府的能力,而且具有型塑法治政府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政府的法治化程度及其構(gòu)造的科學性程度,是判斷其憲法能力發(fā)揮程度的基本標準。
在西方傳統(tǒng)中,法治的概念幾乎與其文明演進具有同樣久遠的歷史。早在古希臘時代,法律就被當作一種治國方法被提了出來。柏拉圖在其《法律篇》中明確指出“依法治國”是僅次優(yōu)于“哲學王治國”的理想政體。他說“如果有人根據(jù)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陽光來指導自己的行動,他們就用不著法律來支配自己,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識更有力量。理性不應(yīng)該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它應(yīng)該是萬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實,而且本質(zhì)上是自由的話。但是,現(xiàn)在找不到這樣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們必須作出第二種最佳的選擇,這就是法律和秩序。”[31]257柏拉圖之后的亞里士多德進一步闡發(fā)了“法治優(yōu)于一人之治”的觀點,因為“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tǒng)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較為優(yōu)良;”[32]137而感情用事恰正是由人類本性所決定,幾乎無人能夠避免,惟有最沒有感情的法治才可能將人類政治從感情用事的泥沼之中拯救出來。延至中世紀及其后,逐漸產(chǎn)生了這樣一種信念,那就是“不管法律是上帝的還是人定的,法律應(yīng)該統(tǒng)治世界;即使是政府也不能改變一個基本的法律。”此后,經(jīng)由啟蒙時代的演進,法治理論被認為是新政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
自有法治概念以來,我們就發(fā)現(xiàn)“法治”始終與政府的構(gòu)造形式和治理方式密切相關(guān);時至今日,我們在一切場合所探討的法治都與“政府是如何踐行這一立憲主義基本原則”密不可分。離開政府而談法治,與離開法律而談法治一樣,是同樣不可想象的事情。正因為法治與政府的關(guān)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至于當我們“弄清了法治是什么也就等于是弄清了法治政府是什么”。比如我們實際上完全可以將亞里士多德關(guān)于“法治”的二要素解讀為“法治政府”的二要素,即一個法治政府至少應(yīng)當滿足兩個基本要件,那就是“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yīng)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33]116
作為法治政府型塑者的憲法,首先規(guī)定了政府的構(gòu)造原則,即政府及其組織必須依憲法而設(shè)立,以確保政府的正當性和有效性;但凡依憲法而設(shè)立的政府及其組織,都排斥專斷的權(quán)力,其職能即在于“創(chuàng)造和維護一種環(huán)境,使得生活于其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夠過上有尊嚴的生活”[34]53——在這樣一個環(huán)境中“任何人不應(yīng)因為做法律未禁止的行為而受罰,任何人只能因為違法而不能因為其他而受處罰。”[35]76“使用絕對的專斷權(quán)力,或不以確定的、經(jīng)常有效的法律來進行統(tǒng)治,兩者都是與社會與政府的目的不相符合的。”[35]80其次,它確立了法律對于政府過程的剛性約束和對自由的絕對價值——“無論國家采取什么形式,統(tǒng)治者應(yīng)該以正式公布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臨時的命令和未定的決議來進行統(tǒng)治……政府所有的一切權(quán)力,既然只是為社會謀幸福,因而不應(yīng)該是專斷的和憑一時高興的,而是應(yīng)該根據(jù)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來行使;這樣,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們的責任并在法律范圍內(nèi)得到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統(tǒng)治者被限制在他們的適當范圍之內(nèi),不致為他們所擁有的權(quán)力所誘惑。”[35]85-86其三,它設(shè)置了政府行為的責任追究和矯正機制——“法律一經(jīng)制定,任何人也不能憑他自己的權(quán)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優(yōu)越為借口,放任自己的或任何下屬胡作非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會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35]69
(三)憲法的本質(zhì)性能力:社會團結(jié)凝聚力
社會團結(jié)凝聚能力:憲法是社會團結(jié)的象征。在一個倡導文明的時代,我們除了借助于憲法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來重塑被社會分工所破壞了的政治認同乃至整個社會團結(jié)——隨著社會分工的發(fā)展,職業(yè)活動越來越專門化的人們發(fā)現(xiàn)他們彼此之間在信仰、觀點和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變得越來越互不相同。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如何實現(xiàn)社會的整合,避免分裂?這就需要社會成員之間存在最低限度的價值認同,而憲法在建構(gòu)這種最低限度的價值認同上發(fā)揮著基礎(chǔ)性和根本性的作用。
根據(jù)迪爾克姆的觀點,集體意識和社會分工分別構(gòu)成了社會團結(jié)的精神基礎(chǔ)和物質(zhì)基礎(chǔ)。但是,集體意識和社會分工在機械團結(jié)和有機團結(jié)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機械團結(jié)的社會中,由于社會成員有著相同的信仰、觀點和價值觀,有著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集體意識彌漫于整個社會空間,涵蓋了個人意識的大部分,個人幾乎完全在共同情感的支配下,社會強制和禁令支配了社會生活中的大部分。因此,機械團結(jié)是以一種強烈的共同的“集體意識”為基礎(chǔ)的。但隨著社會分工的發(fā)展,共同的集體意識逐漸削弱,使個性的發(fā)展成為可能。職業(yè)活動越來越專門化的人們,發(fā)現(xiàn)他們彼此之間在信仰、觀點和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變得越來越互不相同。正是這種正在增長的異質(zhì)性促使社會從機械團結(jié)轉(zhuǎn)變?yōu)橛袡C團結(jié)——這種建立在社會分工和相互依賴基礎(chǔ)上的有機團結(jié),比主要建立在相似的價值觀和信仰等集體意識基礎(chǔ)上的機械團結(jié),能夠更徹底、更有效、更深刻地實現(xiàn)社會的整合。但是,倘若這種基于社會分工所帶來的角色之間的差異性繼續(xù)成為社會成員之間分化的催化因素,那么角色之間的認同與合作便無從談起。”[36]24倘若一個社會缺乏了這種結(jié)合或認同,那么其必須的和諧秩序及共同體的團結(jié)必將因此而瓦解。
迄今為止的經(jīng)驗表明,一個社會除非建構(gòu)起了最低限度的穩(wěn)定的政治認同,否則社會共同體必將因為政治認同上的混亂而分崩離析。亞里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人天然的就是終其一生都在尋找政治歸屬的動物。人對于社會的歸屬感幾乎就是源自于其對于政治的認同。所以,一個社會一旦出現(xiàn)政治認同上的危機,那么社會危機就成為不可避免。歷史上的許多社會危機大多與政治認同危機有關(guān)。當今中國的許多社會問題,亦大多與政治認同問題存在著或近或遠的聯(lián)系。[37]
在一個倡導政治文明的時代,憲法無疑是維續(xù)最低限度的社會的政治認同的核心力量——在其現(xiàn)實性上,政治認同是一個普適性的概念,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政治形式獲得人們認同的路徑也多具有相似之處:[38]64那就是一方面建構(gòu)一套價值符號系統(tǒng),來維護其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就是建立一套規(guī)范體系,以確保這種政治認同的可持續(xù)性。而憲法集這兩套系統(tǒng)于一身。
四、憲法能力建設(shè)
當今中國的社會轉(zhuǎn)型是一種典型的社會改良,是在保留原有的憲政體制下所進行的改革。這就注定在這場改革中憲法所承受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任何一項大的改革都涉及憲法問題,憲法承載著人們太多的期望。為確保憲法能夠盡可能的完成其歷史使命,有必要充分發(fā)掘憲法自身的固有能力,整肅制約憲法能力發(fā)揮的制度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推動憲法能力發(fā)揮到最佳狀態(tài)。此即所謂憲法能力建設(shè)。
(一)憲法能力建設(shè)何以必要:中國憲法能力障礙
從其應(yīng)然的立場而言,中國憲法應(yīng)當具有西方國家憲法大致相似的能力。但在實然的立場上,我們看到,中國憲法存在著嚴重的能力障礙,這些障礙制約了憲法能力的正常發(fā)揮,貶損了憲法應(yīng)有權(quán)威,并構(gòu)成了憲法能力建設(shè)必要性之所在。
其一是心理性障礙。心理性障礙原本是指作為主體的人面對環(huán)境中的變化和壓力所產(chǎn)生的一種心理異常反應(yīng)以及由此所引發(fā)的反常行為——人的心理活動是由各個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組成的,包括人的感知、記憶、思維、情感、意志以及人格特征等。[39]1279-1283心理活動是一個完整的整體,當心理活動的某一部分出現(xiàn)障礙或異常時,就可能引起整體的異常。我這里所謂“憲法能力的心理性障礙”意指作為主體的人在憲法的認知層面上所存在的心理性缺陷——對于憲法的心理性認同和積極性認可,是對憲法的支持性行為產(chǎn)生必要條件;一個社會除非具備對憲法的足以低限度的普遍認同,否則,再完美的憲法也注定是無能的。長久以來,我國公民對于憲法缺乏大致統(tǒng)一的心理認同:有些人對憲法中基于歷史原因所形成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不以為然,并因此拒絕承認憲法的規(guī)范性效力,或者對憲法心存抗拒心理;有些人以憲法某些倡導性條款的不可操作性為由,而懷疑憲法整體上的可使用性,并因此對憲法產(chǎn)生輕慢心理;有些人則以現(xiàn)行憲法與計劃經(jīng)濟聯(lián)結(jié)過于緊密為由,對憲法是否具有足夠的能力能夠引領(lǐng)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或者憲政,缺乏足夠信心。公民的這種在憲法認知上的心理性分歧,導致中國憲法長期缺乏大致統(tǒng)一的公民性支持,這是限縮其能力發(fā)揮的一種重要的心理障礙。如何化解這種心理障礙,型塑公民對于憲法的一致性認同,喚起人們對憲法的足夠信心,將構(gòu)成未來中國憲法學研究和憲政建設(shè)的重大課題。
其二是功能性障礙。憲法能力的發(fā)揮程度是與其功能配置密切相關(guān)的,不同國家的“憲法”之所以在能力的實際發(fā)揮上存在著巨大差異,大多與憲法功能配置上的差異有關(guān)。正如同外形相似的電腦之所以在能力上大相徑庭,大多由其功能性軟件配置不同所決定的一樣。這種功能配置上的差異或者缺陷所造成的憲法能力發(fā)揮障礙即我所謂之憲法能力的功能性障礙。毋庸諱言,由于其固有的時代局限性,我國現(xiàn)行憲法在功能配置方面的確存在著某些缺陷,比如至今我國憲法尚未有嚴格意義上憲法平等保護、糾正違憲等功能性配置。而這些缺陷,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我國憲法能力正常發(fā)揮的重要制約因素。如何矯正其功能缺陷,完善其功能配置,對中國憲法的發(fā)展和完善將具有戰(zhàn)略性意義。
其三是器質(zhì)性障礙。所謂憲法能力的器質(zhì)性障礙,有似于電腦的“硬件”故障。應(yīng)當說,現(xiàn)行憲法是在國家改革開放剛剛起步時制定出來的,受當時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諸方面的影響,特別是受到市場經(jīng)濟發(fā)育不完全的制約,憲法的某些條款存在著明顯的時代缺陷,實踐證明這種缺陷已經(jīng)成為中國憲法能力發(fā)揮的重大障礙。另一方面,在歷經(jīng)近30年的運行之后,現(xiàn)行憲法先后經(jīng)過四次部分修改,這些修正案極大地緩解了憲法的適應(yīng)性危機的同時,也對憲法文本的整體性造成了一定的損傷,甚至出現(xiàn)了條款之間的沖突和不協(xié)調(diào),這種憲法能力的器質(zhì)性障礙又易導致憲法能力的功能性障礙。這也是影響中國憲法能力發(fā)揮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如何彌補和修復(fù)這種器質(zhì)性缺陷和損傷,并盡可能地避免出現(xiàn)新的器質(zhì)性損傷,比如盡可能借助憲法解釋的方式而不是憲法修改的方式來化解憲法適應(yīng)性危機和彌補條款之間的歧義,勢必成為中國憲法學研究的熱點問題。
(二)憲法能力建設(shè)何以可能:建構(gòu)理性主義的地位
同所有的政府一樣,立憲政府必須要催生和建構(gòu)。[40]36而催生和建構(gòu)立憲政府則必須借助于一定的理論形式,缺乏一定的理論形式,一切形式的政治建構(gòu)都是盲目的;而任何被依憑為政治或者制度建構(gòu)的理論形式,都必將對政治實踐產(chǎn)生實質(zhì)性的影響——理性的建構(gòu)思想沒有理由不對政府產(chǎn)生影響,政府結(jié)構(gòu)的演進也沒有理由不對一定的理論形式產(chǎn)生依賴。[40]45迄今為止的經(jīng)驗表明,理論不僅是制度演進的引導者,而且也構(gòu)成了制度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大法官霍姆斯說:理論之于法律教條的意義,有似如建筑師之于建筑工匠的意義。[41]1在一個僅有工匠而缺乏建筑師的時代,或許也有建筑,但永遠不可能有建筑藝術(shù),正如同在沒有理論的社會或許也有法律,但永遠不可能有法治。
柏林說我們所擁有的信念不能被認為僅僅是某種主觀狀態(tài),而是構(gòu)筑我們行動的客觀力量。[42]1因此,只要人類沒有停止行動,思想就永遠在發(fā)揮著對行動的建構(gòu)性作用。因此,理性建構(gòu)主義并不像哈耶克所貶謫的那樣令人厭惡,它實際上是社會進步和制度變遷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中國這樣一個后發(fā)型的缺乏法治傳統(tǒng)的國家進行憲政建設(shè),建構(gòu)理性主義尤其不可或缺——西方憲政之所以“是一個沒有任何人能夠預(yù)期到的后果,”[43]378-381并不是完全不受理論指引的結(jié)果,相反,西方憲政的任何形式的演進都烙上了理性主義的痕跡。時至今日,歷經(jīng)數(shù)個世紀的磨礪和積淀,世界范圍內(nèi)的憲政理論體系已然建立,這不僅對中國憲政建設(shè)提供了經(jīng)驗示范,而且也為理性建構(gòu)主義切入中國憲政建設(shè)提供了范本和契機。[44]126
麥金太爾曾經(jīng)指出:理論就像地圖一樣,即便它不是那么完整或者準確,都是構(gòu)成行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指南,它的價值就在于“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避免適用它。”[45]32為此,我們有必要借助于理性建構(gòu)主義將立憲政治的理論模式和經(jīng)驗范本引入公眾認知和公共討論的領(lǐng)域,讓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都接受一次立憲思潮的洗禮,以型塑公眾對于憲政的理解和認識——這是促使中國憲政早日成熟的基本途徑。[23]
既然憲法本身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理性建構(gòu)主義作用的痕跡,那么借助于建構(gòu)理性主義的方法,將西方憲法在其歷史演進過程之中所積淀的能力通過一定的形式嫁接到中國憲法之中,當然也是可能的——能力的嫁接只為提升憲法自身對于政治過程的現(xiàn)實駕馭力量,它基本不涉及憲法意識形態(tài)問題。也就是說,能力是一種客觀的因素,它是推動立憲目的和宗旨現(xiàn)實化的基本力量,而不是改變憲法意識形態(tài)的因素。
(三)憲法能力建設(shè)何以進行
清理影響憲法能力發(fā)揮的各種障礙,是憲法能力建設(shè)的基本路徑。其中,清理影響憲法能力的功能性障礙可以稱之為憲法能力的“軟件”建設(shè),主要應(yīng)著重于憲法對于政治過程的引領(lǐng)能力和對國家政治資源的調(diào)控能力——憲法的政治引領(lǐng)能力是由其對政治資源的調(diào)控能力所決定的,而憲法的政治引領(lǐng)能力則是其政治資源調(diào)控能力的直接體現(xiàn)。
清理影響憲法能力的心理性障礙和器質(zhì)性障礙則是憲法能力的“硬件”建設(shè),主要應(yīng)著重于發(fā)揮憲法對公民憲法思維的培育能力,整肅影響憲法固有能力發(fā)揮的各種障礙——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心理性和器質(zhì)性障礙之修復(fù)外,還包括政治文化、制度環(huán)境等方面的整肅和建構(gòu)[46]386-387——如何清理憲法能力的心理障礙,在中國這樣沒有憲政根基的后法治國家是一個富有挑戰(zhàn)性的問題,其挑戰(zhàn)性不在于理論的艱深,而在于在現(xiàn)有的經(jīng)濟、文化、政治條件下人們從憲法文本和理論中能獲得多大程度的預(yù)期及在憲法框架內(nèi)如何實現(xiàn)預(yù)期。與此相對應(yīng),清理憲法的器質(zhì)性障礙必須通過完善憲法文本自身才能完成。憲法文本至少要滿足兩個條件才能發(fā)揮其應(yīng)有的效用:一是依憲政之邏輯憲法文本的所有條文應(yīng)無邏輯沖突,如憲法條文存在邏輯矛盾,憲法實施將無所適從,會導致憲法秩序的混亂,法律體系難以統(tǒng)一;二是憲法文本應(yīng)當大致和當前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和政治等條件相適應(yīng),不能過于落后,也不能過于超前,否則憲法的效用不能真正發(fā)揮,憲法必將威信掃地失信于民。憲法的制定和修改都是極富技術(shù)性的作業(yè),憲法文本內(nèi)容的取舍,條文間邏輯的安排,語言的運用表達等都應(yīng)相當?shù)目季俊椃ㄐ薷牡哪康氖鞘箲椃ㄟm應(yīng)發(fā)展變化了的社會,但憲法的修改不應(yīng)當損害憲法的整體性,應(yīng)保證已修改的條文和原有條文能和諧共生。
五、結(jié)語
憲法能力研究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課題。借助于憲法能力研究,不僅有望將長期以來被人為分裂的理性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憲政理論有機融合起來——在這兩種具有明顯對立性的憲法理論之間,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比“憲法能力”更為恰當?shù)穆?lián)結(jié)紐帶。因為憲法能力不僅是社會進化的產(chǎn)物,而且也與人之理性密不可分;憲法能力的形成過程不僅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而且也是人之理性發(fā)揮效用的過程。因此,憲法能力的大小,既受制于憲法自身及其所處之社會的發(fā)育水平,而且也決定于人之理性的發(fā)達和人為努力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說,憲法能力研究不僅將有效促使人們對于憲法之原理性反思,而且也勢必推動整個憲法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并能夠有效解決諸如中國之類后發(fā)型國家所推行的理性建構(gòu)主義憲政路徑的理論困境。
注釋:
[1]〔英〕拉德克利夫·布朗.社會人類學方法[M].夏建中,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2]JonElster(ed.),DeliberativeDemocrac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Spanishtranslationforthcoming).
[3]JeffreyL.Pasley,AndrewW.Robertson,andDavidWaldstreicher(ed.)BeyondtheFounders:NewApproachestothePoliticalHistoryoftheEarlyAmericanRepublic,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2004.
[4]江國華.權(quán)力秩序論[J].時代法學,2007,(2).
[5]WilliamWade,ConstitutionalFundamentals,LondonPress,1980.
[6]JürgenHabermas,Philosophical-PoliticalProfiles,Lawrence,FrederickG.(Trans),Cambridge,Mass.:MITPress,1983.
[7]〔德〕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楊富斌,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8]〔挪威〕斯坦因·U·拉爾森.政治哲學理論與方法[M]任曉,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9]〔法〕埃米爾·迪爾凱姆.論宗教[M].周秋良,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10]〔美〕哈奇.人與文化的理論[M].黃應(yīng)貴,等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
[11]〔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會結(jié)構(gòu)與功能[M]丁國勇,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12]AbrahamH.Maslow,MotivationandPersonality,NewYorkPress,1970.
[13]〔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14]JürgenHabermas,Philosophical-politicalProfiles,Lawrence,FrederickG.(Trans),Cambridge,Mass.:MITPress,1983.
[15]〔美〕卡爾·弗里德里希.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M].周勇,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
[16]〔美〕路易斯·亨金.憲政·民主·對外事務(wù)[M].鄧正來,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
[17]〔英〕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M].劉山,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6.
[18]李靜冰.盛行的經(jīng)濟立法觀在法理學上的檢討[J].法律科學,1995,(1).
[19]〔美〕哈羅德·J·伯爾曼.法律與宗教[M].梁治平,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
[20]〔英〕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
二、三卷)[M].鄧正來,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
[21]James,ThePrinciplesofPsychology,NewYorkPress,1890.
[22]〔美〕羅斯科·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wù)[M].沈宗靈,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4.
[23]高秦偉.憲政建構(gòu)的理性主義與經(jīng)驗主義[M].河北法學.2004,(8).
[24]〔美〕斯蒂芬·L·埃爾金,卡羅爾·愛德華·索烏坦.新憲政論——為美好社會設(shè)計政治制度[M].周葉謙,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
[25]C.J.Friedrich,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Politics,HarperandBrothersPress,1937.
[26]〔美〕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M].萬俊人,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0.
[27]〔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鄧正來,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
[28]HannahArendt,BetweenPastandFuture:EightExercisesinPoliticalThought,NewYork:theVikingPress,1968.
[29]QuentinSkinner,LibertybeforeLiberalis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
[30]〔美〕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31]PierreVidal-Naquet,TheBlackHunter:FormsofThoughandFormofSocietyintheGreekWorld,AndrewSzegedy-Maszak(Trans),Baltimor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6.
[32]〔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2.
[33]〔古希臘〕柏拉圖.法律篇[M].張智仁,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4]StephenL.Elkin,KarolEdwardSoltan(ed.)ANewConstitutionalism:DesigningPoliticalInstitutionsforaGoodSociet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9.
[35]〔英〕洛克.政府論[M].葉啟芳,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2.
[36]〔法〕迪爾凱姆.社會分工論[M].王力,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34.
[37]于建嶸.穩(wěn)固的政治認同是社會維系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基礎(chǔ)[J].中國改革論壇,2005,(2).
[38]K.C.Wheare,ModernConstitutions,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
[39]GregoryEM,CinnamonA.Stetler,RobertMC,ClinicalDepressionandInflammatoryRiskMarkersforCoronaryHeartDisease,theAmericanJournalofCardiology,2002,90:1279-1283.
[40]〔英〕馬丁·洛克林.公法與政治理論[M].鄭戈,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2.
[41]〔美〕愛德華·S·考文.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M].強世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6.
[42]I.Berlin,DoesPoliticalTheoryStillExist?,inP.LaslettandW.GRunciman(ed.),Philosophy,PoliticsandSociety(SecondSeries),OxfordPress,1962.
[43]杜維明.儒家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44]陳弘毅.法理學的世界[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45]AMacintyre,TheIndispensabilityofPoliticalTheory,inMillerandSiedentop(ed.),TheNatureofPoliticalTheory,OxfordPress,1983.
[46]Laski,AGrammarofPolitics,LondonPress,1925.
擴展閱讀
- 1憲法義務(wù)
- 2憲法能力
- 3憲法監(jiān)督模式
- 4美國憲法再讀
- 5憲法委員會到憲法法院
- 6憲法解釋之憲法文本
- 7憲法民生保障
- 8憲法司法適用
- 9憲法解釋
- 10公民憲法研究論文
推薦期刊
精品推薦
- 1憲法學教學論文
- 2憲法原則論文
- 3憲法學習計劃
- 4憲法學論文
- 5憲法宣誓制度
- 6憲法論文
- 7憲法基礎(chǔ)論文
- 8憲法教學論文
- 9憲法制定權(quán)論文
- 10憲法法學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