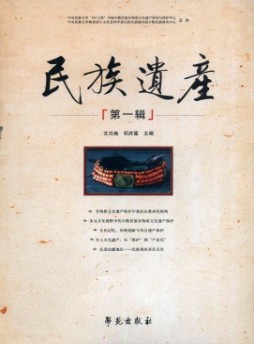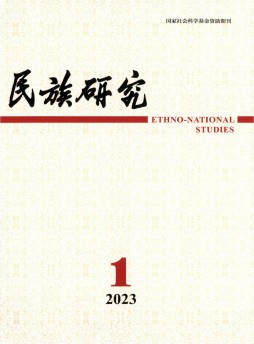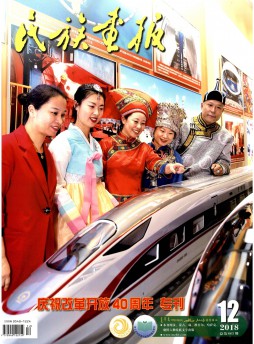民族文學生態探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族文學生態探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導言
時至今日,關于民族文學的定義似乎“一直是見智見仁,說法不一”,“關于作家的族屬問題,人們的意見似乎分歧不大。也就是說,首先要看作家是不是少數民族出身。如果是,就可以考慮將他的作品列入少數民族文學的范圍;如果不是,也就不去考慮了”。①那么,本文所討論的“珠三角少數民族文學”的歸屬范疇,自然就是以南方珠三角的少數民族作者創作的文學作品為探討對象。在我國南方民族文學的領域,少數民族如果說還是一個相對概念;那么,值得肯定的絕對概念無疑是如何回歸少數民族文學寫作的本質———民族文學的書寫也依然是安頓自我身心的產物。與漢民族相對比,他們似乎有著更多歌舞藝術的天賦與自在表達,擁有著比相對內斂的漢民族更直接和多樣的藝術載體的支撐,那么南方少數民族文學是否也應當呈現出與其歌舞風格一致的表情與節奏,有著江水入大海、林鳥夜歸巢一般的舒暢自如的面貌?南方民族文學如何反映時代變遷中的少數族群內心的喜悅與憂傷,傾聽他們生命燃燒時那噼里啪啦的聲音?如何成為南方少數民族心靈的活地圖與溫度計?如何真實呈現民族記憶里的殘酷與芬芳?如何真實展現現代國度里的民族特點以及人類共通的本性,還有與此相連的地域民族的發展問題?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民族文學應該展現的不再是《荷馬史詩》里那種馬背上的游牧民族征服異域、鏗鏘恢弘的一面;也不再是風情奇趣、引人入勝的離奇故事;更不是停留于表面形式上的民族團結所形成的種種夸飾性贊美文式。地處南方珠三角地區的民族文學,建立在中國民族文學近幾十年進步與變化的基礎之上,同時又是中國民族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以珠三角的中山民族作家群體為例,他們的創作中有對南方經濟社會以及原先生養他們的那片土地的觀察和對比,有草根生存的經驗提取,他們在作品中力圖做到有思想、有故事、有文化、有切入點,從而展現當代南方少數民族的生活畫卷,這樣的嘗試是有意義的。但在觀照各種文化融合的同時,厚重感、深層審視、文字修養其實正是珠三角少數民族創作中相對薄弱的。基于此,本文以兼具特殊性與同一性的作品為例,梳理出以下關于南方珠三角民族寫作的三個研究要點:1.南方民族寫作具有審美優勢。2.其中蘊含他鄉與故鄉的糾結。3.南方民族文化生態的現狀與問題綜述。如何協調與平衡這一個問題的三個方面,也就接通了當下南方民族文學在永恒的古老與創新的現實之間的涅槃生存之道。本文最終得出有關珠三角民族文學的三方面結論:1.異質文化的碰撞使這一地域的民族元素呈現出一種雜交優勢與生命力,具有先天的審美優勢。2.民族地域尋根的寫作可說是尋根文學的一種延伸,有傳承意義。3.該地區民族文學面對文化沖突的局限性及出路。而研究以上問題的背景與核心是:南方特殊的寫作語境使當地傳統資源、民族文化、外來文明之間有著最大程度的整合,不同文化接觸和文化沖突的頻繁發生,對自身文化的生存與發展的焦慮無法避免,形形色色的交往無論有無火花都昭示著異質文化的雙方或多方可以通過尋找相互之間的文化契合點,來達成更多合作與對話的空間與可能性。改革的移民浪潮改變了南方尤其是珠三角的文化生態圈,進而在民族融合中形成文化共同體。開放包容、和而不同,應當成為民族文學在改革開放的南方前沿最為突出的特點。
二、南方民族寫作的策略性標識
在談到語言的實質時,卡西爾認為是“隱喻”,海德格爾認為是“詩”,正是這種“隱喻”或“詩”的品格,使作品變得意味深長,語詞如花,使一切被敘述地域如花般綻放,使地域性、民族性寫作蒙上了詩性的色彩。民族生活一經敘述,就像被施了魔法般,有了一種神奇的美。很多少數民族作品充分展現了這種書寫的魔力,使自己生活的周遭與現實變成“語言的烏托邦”。“一個無與倫比的異族美人有時并不完全基于自身那種原生態的美麗,往往因為有傳說、有典故、有敘述而成為經典,正如海倫的美是因為后世人對特洛伊戰爭的反復描述。一個地方,一個民族,同樣也會因世人的反復吟詠而附麗了許多額外的內容。”①在南方這片沃土之上,民族書寫為民族地域蒙上了魔幻的色彩;民族書寫使民族身份凸顯、民族文化進步、民族生活喜悅;民族書寫使民族之魂變得柔軟而安詳。遙遠而美麗的《荷馬史詩》《吉賽爾》《圖蘭朵》,在西方古老的民族文學里頌贊的自然是古老的愛情,所有民族的作品也無一例外,情感被反復吟唱,是因為在現代塵囂中它日顯蒼白和荒謬,雖然它一直存在著,卻只在民間的歌聲中才表現出分量。是什么聲音在高高低低地牽引著,讓人不能心如止水?是什么聲音在不動聲色地蔓延著,將率真質樸放回情感中去———“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我愿拋棄了財產,跟她去放羊,我愿她拿著細細的皮鞭,不斷輕輕地打在我身上。”這一刻,情愛因為沒有文明教化的打擾而變得美不勝收、自然而然。又譬如舞蹈這種藝術形式,近乎于人類集體無意識的身體扭動,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與天賦,可一個漢族人通常會羞于用舞蹈來表達思想感情,古老的舞蹈本能深藏于他們的體內而不自知。而在少數民族的生活中,一切似乎都還是那么隨性而自在———我舞蹈,因為我憂傷;我歌唱,因為我喜悅———這樣簡單而又純粹的生趣與美感,是被現代人日益疏離與陌生著的,這種差異性恰巧成就了民族文學獨具的美感。正是“珠三角”“少數”“民族”三個關鍵詞的組合,賦予了珠三角少數民族及其文學以陌生與魅力的特權。在珠三角特殊的寫作語境中,傳統資源與外來文化有著最大程度的整合,沿海地區所謂的海洋文明“賴以維系的物質基礎始終牽引著文化緯度的世俗性”。①在此基礎之上,一種世俗情懷與利益追求為導向的文化心理與創作心態,勢必影響著整個南方文化大系統內的方方面面,甚至成為詮釋該地區創作的一個標向。
在此背景下,聚居于此的各民族對日顯保守的農業文明及傳統文化精神內涵的反觀,對精神家園的浪漫描述與追尋,無疑使南方文學中的民族元素具有先天優勢,使南方民族文學作品更容易脫穎而出。在南方的都市里,少數族群這生命的歌、古老的唱本是各民族與生俱來的生命狀態,如今蛻變為陌生,而這份陌生仍然以頑強的生命力石破天驚地存活于姿態萬千的當代生活里,形成一種距離產生美的創作優勢。現居廣東中山市的土家族作家譚功才,以其出生地為藍本創作的《鮑坪》,在其個人的文學創作生涯中引起了最大程度的社會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這之前他的個人寫作基本沒有對自我的民族身份做過如此集中的民族抒寫。《鮑坪》分別從地理、人物、風俗、風物四個方面來描摹故鄉鮑坪的人情風物,表達了作者對于土家族故土的懷念之情。《鮑坪》的創作意義、寫作手法和內容的匹配都基于作者對自我民族身份的正確定位,一個作家的成功不僅僅依靠筆力,風格、特點、方向形成合力,亦即綜合表現力,對于作家的創作前途也能形成決定性影響。《鮑坪》被關注,因為這是一部帶著溫度和厚度的反映鄉愁的作品,更因為這是一部恩施土家族的豐富人情志。于南方詭譎多變的文學市場,個人寫作的策略性規劃就更為重要。正如孔雀舞之于楊麗萍的意義,文學作品的辨識度是文學作品成功的重要元素之一,對少數民族作品而言,甚至更為重要。“對于中國少數民族作家來說,他們有先天的、得天獨厚的民族文學土壤和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立足于自己民族的社會生活,再現獨特的民族生活畫卷,反映民族的風土人情,展示傳統與現代、人與自然之間的融合與矛盾,這些應該是少數民族作家的獨到之處和作品理想的追求。”②南方珠三角民族文學同樣浸洇在古老先祖圖騰與靈魂的沃土之中,具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素材與先天優勢,如能將目光與關注鋪展開來,深入挖掘本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民族情感的最深處,以自身最為熟悉的生活開發文學寫作的根據地,直至形成個人寫作的生態鏈,而不只是私人意義上的地方志、風物志,這才是具有流動感的民族生命寫作,這才是一個民族抒寫者永恒的精神退守之地。
三、他鄉與故鄉的平衡
與對話說到一個民族抒寫者永恒的精神退守之地,就順理成章地引發了“他鄉與故鄉”的問題。文學界普遍可見的一種現象:寫作者常年飄泊在外,已經無法分清故鄉與他鄉,社會的變遷、時代的更迭,使得一大批各個年齡層的作家淪為無根、無鄉愁的作家;從而形成了一種無根、無鄉愁的文字書寫;再從而形成對于這種“無根文學”的現象探討。這類文字及作家的都市化寫作本身沒有問題,也不乏力作,問題是他們偶爾為之的鄉愁令人起疑———當他們為現代文明的物欲所累他們就還鄉,返回生命的原點、精神的家園,留下一些原鄉人的感慨;一旦離開那片故土,那中的一條船便隨之隱沒。這種情況當然還包括了不少著名作家。那么讀者會問:既然如此眷戀精神原鄉,為何離開,又何來感慨?不如逍遙自在,常居舊地?如此功利的懷鄉之情豈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顯得惺惺作態?這樣的質疑雖略顯簡單粗暴,但也表明了他鄉與故鄉之間這種雙重人格之糾結,在珠三角民族文學的發展中應該說表現得更為明顯與強烈。其實無論身在他鄉的少數民族作者,還是長居少數民族地區的作家,他們都面臨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歸根結底,“無根”也不是完全的無根,總歸是有出處的人,就免不了在作品中露出蛛絲馬跡。現居中山的苗族作家楊彥華認為自己是基本沒有鄉愁的寫作,其小說《女神之死》中的巴人“當初從中原和江漢平原逃離”,最后在楚國戰敗后回到夷水,及其間出現的江陵等背景,讓讀者很容易聯想到她的湖北故土,遑論小說中的生活方式與習俗,僅字里行間那種突如其來的巴楚幽默都帶有其出生地的氣息。
四、珠三角民族文化生態的演變與走向
在地域與時代交織而成的文學坐標之上,開放包容、和而不同成為民族文學在改革開放的南方前沿最為突出的特點。僅以珠三角核心地帶之一的中山為例,一座900年前以“香山”命名的城市,改革之初被稱為珠三角經濟發展“四小虎”的僑鄉,與港澳毗鄰,如今當地的文化生態圈卻被改革的移民浪潮改變了,進而在民族融合中形成文化共同體。難以想見,就在此地,文學創作的少數民族作者業已聚合成為初具規模的團隊,包括譚功才(土家族)、劉春潮(白族)、楊彥華(苗族)、楊昌祥(苗族)、黃祖悅(土家族)、田夫(苗族)、李緒恒(土家族)、黃建(土家族)、喬明杰(土家族)、劉作術(土家族)、邱運來(土家族)在內的一個陣容龐大、創作活躍的民族作家群,在各具特色的同時又具有一些共同的寫作特征,同時也映照出珠三角地區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一些總體特征與演變。其一,異質文化的碰撞使這一地域的民族元素呈現出一種雜交優勢與生命力,具有先天的審美優勢。聚居本地的各民族及其傳統文化,以誠信義氣、務實求利、生而平等的性格,將對日顯保守的農業文明及傳統文化精神內涵的反觀,融入到南方文學的創作中。中山整個少數民族的創作群體,嘗試著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途徑,多方位地去豐滿中山與他們的故土,契合了他鄉與故鄉面對經濟高速發展下的不安與矛盾,以及經歷糾結后的和美與發展。現居中山的“60后”苗族作家楊昌祥,也有著類似于譚功才在《鮑坪》中對湖北清江老家的不舍,例如他寫傳統節慶的溫熱在一個少年心底留下的永遠的沉淀。相映成趣的是,在隨筆《馬,永不停蹄》中,楊昌祥又仿如物換星移的大時代背景下的一粒微塵,不再如兒時故土那般地篤定悠長,取而代之的是飄移過程中人之常情的心理變化、兩種生活境遇的交接、隱約的不安與期待。這些文字光影中的他鄉與故鄉,記錄了城市與鄉村的滄桑變化,塑造了多面形象,使得中山等珠三角城市更為立體,也使得內地故土更為人性。當然,各式各樣的文字有著自己不同方向的延伸,可能是有關城市生活的真實答案與秘密,也可能是曾經的民族地域之上文人墨客的想象與浮世的交相寫照。可無論我們翻開哪個活生生的文本,都是相得益彰的雙城記,徜徉其間,歷練感懷。其二,民族地域尋根寫作成為尋根文學的一種延伸。作家邱華棟在評價《鮑坪》時認為:“該書可以稱得上一部獨特的地域詞典,也可以說是尋根文學的延續。印象中可稱得上地域詞典寫作的尋根小說代表有韓少功等,他們發現了地域,構造了自己的文學世界。
尋根文學最早是從劉心武開始的,從那里開始了尋根文學的書寫,一直到現在都有發展,直到現在出現了沒有文學之根和沒有鄉愁的人,地域詞典式的寫作可說是尋根文學的一種延伸。尋根文學以每十年一變的發展至今,信息量已包括了民族的、個體的生命體驗,而且鄉村發生的巨大變化已經要用各種學說來解讀了。我們可以持續不斷寫出《中國人在梁莊》、‘中國人在鮑坪’或‘中國人在哪兒’這樣的書,它反映的是持續的群體的文化記憶,有如《馬橋詞典》《哈扎爾辭典》一樣,是多元文化碰撞下的產物,但寫作的差異性可以很大。”①哪種民族文化不曾面臨顯赫一時的片段、落魄演變的歷練、茫然無助的將來?正因如此,他們才更加強烈地顧恤過去,緬懷由農業社會逐步變為工業社會后已然淪喪的傳統文化。如果他們不肯活在新的生活里,生命將會是“將現在轉化為過去的救贖和補償”,“重復、反照、封閉而不是開展、繼續”,那么注定只能在現實的殘酷與記憶的芬芳之間徘徊、撲空、失重、永不超生。正如擅將歷史人物推入鄉愁之境的白先勇,其“最后的貴族”系列最悲憫之處恰巧在于沒有了一丁點兒鄉愁的牽絆,那種自在看似超脫于殘酷與芬芳之外了,實則是歷史身份的消亡與悲愴的虛無。尋根的書寫往往將情感詩化,用詩歌一般的情韻和意境來象征人物的悲劇情懷,使悲劇主題上升到人生哲理和歷史意義的高度。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民族就是一個歷史的符號,是所有“他鄉客”所特有的“文化鄉愁”的佐證。民族文化的升降浮沉表現了那種地域文化甚至整個社會形態的滄桑變幻,寄寓著作者對過去、對自己最美好時光的哀悼和對“已經逝去的美”的懷念,激蕩出禮魂思舊的情韻。但大多作者都不能在現實關系中全面而準確地解釋歷史性的悲劇沖突,所以只能含淚將人物交與超出沖突者自身的命運去擺布,而只以悲天憫人的文學情懷唱盡那“一種繁華、一種興盛的段落,一種身份的消失,一種文化的無法挽回,一種宇宙的萬古愁”。②
當一大批所謂的“無鄉愁”作者形成了尋根文學的斷層之后,又用他們新的態度、新的角度與手法繼續新一輪的尋根,在說明“尋根”魅力的同時,也說明這種傳統型寫作有隨時被消解的危機,這也正是南方乃至全國少數民族文學所要面臨的生態問題。如果說尋根文學“每十年一個變化”,不如說“每十年一次反思”來得更為準確,文學的法則應該是亙古而永恒的,那些基本的東西依然不可撼動地堅守在那兒,因此珠三角民族文學對地域尋根寫作的執著與延續,只能說明地域尋根寫作自有其存在的道理,同樣也說明人們對漸行漸遠的文化記憶的不舍與挽留。其三,在這場文化沖突中,少數民族文學不能不面對由落差而凸顯的種種局限性:南方民族的地域性尋根寫作,到底應該是一部私人意義的地方志,抑或應該是婀娜多姿的生態圖?什么才是擺脫了民族寫作夸飾性贊美、凸顯地域與民族復雜性的夯實而地道的民族新作?怎樣寫出被現代文明摧逼之下的南方少數族群的生存狀態,當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那被毀掉的鄉土、流失的傳統卻無能為力之時?身處南方的文學博士李德南認為:“南方民族文學的寫作者們應當在書中使用獨屬于他們自己的語調以及他們關于民族生活的私人經驗來講述民族地區的人情風俗、風物地理,因為……至關重要的私人經驗是不可或缺的,有私人經驗在內的文字才會有獨特性。然而,寫作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經驗要能夠被其他讀者所理解與認同,就要在書寫中自覺地以自己的民族身份、游子身份、某一代人的身份來重構、再現具有公共性質的經驗。”①當下的中國還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這個多變的時代,人類共有的話題諸如陌生與標識、他鄉與故鄉、現代與尋根的關系凸顯了出來。綜而觀之,南方珠三角民族文學以中山民族作家群體為代表的作品,致力于將各種文化融于一體,關照草根生存的狀況,這樣的嘗試對整體民族文學的寫作是有啟發的。《鮑坪》以及其他在珠三角地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學創作,對過往的民族生活有著相對客觀的描寫和合乎邏輯的細節品質,平實樸素的文字風格與內容基本協調,但在情感的深度挖掘與文字的品質與風格化方面仍有提升空間。如果僅僅停留在記憶的復述、簡單的不舍、空洞的懷鄉,什么身份、經驗都必然缺乏堅實的支撐,更談不上對現有生存狀態的準確呈現與升華。
一直以來,我們的少數民族寫作中似乎形成了一些習慣,在表現獨特性的同時過于依賴少數民族民俗風物中的獵奇成分,從而夸大了民族審美的陌生化。在一些浮夸的表象之下,民族文學流于地方志、生態圖、個人志也就是必然的結果,而民族文學若要與其他漢語言作品站在同一級臺階上較量,必須揚長避短。基于對以上問題的梳理與分析,南方珠三角民族文學寫作的走向也逐漸清晰:如何從更立體的層面去抒寫細節和情緒,使我們民族文學在歷史的蛻變中成為相互了解的最佳途徑;如何在一個小的場域里寫出大的時代背景,在市場經濟大潮下表達出尊重自我內心的寫作姿態;如何寫出地域民族的復雜性和細致鮮活的人性,包括對民族問題的干預、穿透和對民族文化的深層審視,令我們的民族文學做到真正的自省。總而言之,如何有分量地替少數民族發聲,這肯定也是我們今天的南方珠三角少數民族文學不可回避的核心問題。
作者:阮波
- 上一篇:歷史文本下的現代影像敘事范文
- 下一篇:茶文化在世界的傳播分析范文
擴展閱讀
- 1民族旅游與民族文化論文
- 2民族品牌戰略
- 3傳播民族志
- 4民族品牌戰略
- 5藝術民族性
- 6民族企業官商關系
- 7民族地區旅游
- 8民族主義情結
- 9民族科技提升近況評估
- 10民族文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