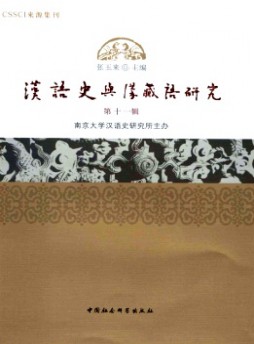葛浩文的漢語學習與文學翻譯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葛浩文的漢語學習與文學翻譯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前言
關于美籍漢學家葛浩文,中國學者最初是從他的幾部文學專著知曉他的。葛浩文對中國新文學和以蕭紅為代表的東北作家群的獨特觀點為他在中國文學界贏得了贊譽。上世界八十年代,他的專著陸續在香港和臺灣出版,之后傳到大陸,其中一些評論曾開啟了人們對東北作家群作品的重新認識和定位。而今人們對葛浩文的印象更多地是從翻譯家這個身份形成。因為自從研究并翻譯了蕭紅的系列作品,葛浩文就把研究重心從文學評論轉移到中國文學翻譯上來。他翻譯作品數量之多,使之成為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翻譯史上第一人。但中國大陸翻譯界對葛浩文的研究不過是近十幾年的事情,尤其是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作為獲獎作品譯者的他無疑更迅速更廣泛地得到人們的關注。提到翻譯家葛浩文,在學者界有很多標簽貼在他身上:“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夏志清)、“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接生婆’”(JohnUpdike)、“中國二十幾位作家近五十部小說的譯者”、“幫助中國作家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的第一功臣”。毫無疑問,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過程中,葛浩文是目前貢獻最大的翻譯家,沒有之一。對他翻譯思想的研究,大陸學者主要是通過葛浩文的一些文章和專訪獲悉,其中2002年發表在《華盛頓郵報》上的“TheWritingLife”[1]被引用頻率最高,另外有關葛浩文的專訪,如季進的“我譯故我在——葛浩文訪談錄”[2],舒晉瑜的“十問葛浩文(漢學家)”[3]是也關注率很高的兩篇。通過這些文章和訪談,葛浩文闡釋了自己在翻譯和文學方面的基本立場和看法。在2014年11月的這次采訪中,葛浩通過自己多年的翻譯經驗,從更深層次理解翻譯和文學,其中也也透露出很多新內容和新觀點。TranslationReview的一期刊登了學者JonathanStalling對葛浩文在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的訪談。在采訪中,葛浩文憑借自己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深刻理解,闡釋了中英文學翻譯的基本問題:如何處理小說翻譯中的復雜結構、異化與同化、漢語音體(thesoundregisters)轉換、譯者責任實現等問題。甚至對中國當代文學和中國作家創作提出了自己的期許和建議,另對年輕譯者也給予了建議,澄清了中國學者對他翻譯的一些誤解。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最初發表于網絡的文章——“譯者之聲:對霍德華•葛浩文的采訪”中,葛浩文還談及了自己鮮為人知的求學經歷,尤其提到了恩師許芥昱先生。本文重點選取采訪中葛浩文關于自己早年學習漢語經歷的敘述,和其對他之后文學翻譯的影響,具體到對小說翻譯過程中一些棘手問題的解決,以期對中國從事葛浩文研究和文學翻譯研究的學者起到幫助作用。
二、漢語學習經歷
(一)和臺灣的不解之緣據葛浩文講述,他之所以最后從事文學翻譯工作都緣于年輕時在臺灣的那段漢語學習經歷。在這次JonathanStalling的訪談中,葛浩文提及大學畢業后去臺灣之前的一段經歷。他曾當了一個學期的小學教師,終因不喜歡這份工作而辭了職。越戰開始,因父親之前在造船廠工作,他便應征海軍,卻被派到臺北。雖也曾想去越南參加轟轟烈烈的戰斗,但發現自己心所向往的地方是臺北,那個靠近戰場的地方[4]。初到臺灣,葛浩文完全不懂語言。或許是命運使然,亦或許是當地文化、山水風景或某種莫名的原因,他被臺灣這個地方深深吸引,兩年后葛浩文突然開竅想學漢語。雖既非語言學家,也不是亞洲研究專家,但卻產生了學習漢語的沖動,后竟發現自己很擅長學習語言。這個在臺灣學習漢語的經歷竟為他后來從事漢英文學翻譯奠定了基礎,也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二)學習漢語葛浩文最初以請家教上門的方式學習漢語。所請老師教法別具一格。用葛浩文的話講,就是在情景中學習語言,用類似教小孩學說話的方式講授,注重語言的實際運用,與現在學生學習語言的方法不大相同。或許這也不失為是一種好的學習方法,但葛浩文覺得不適合自己。于是跟家教學習約一年半,他從海軍退役,開始了較為正規的語言訓練。當時臺北師范大學的普通話培訓中心(theTaiwanNormalUniversity’sMandarinTrainingCenter)接受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實行一種軍事化而非學術性的管理方式(anon-scholasticway)。葛浩文在此學習漢語的時間至少在一年半左右。期間學過小學、初中教材,也學習過專業的報刊閱讀。據葛浩文講,這期間的學習并未使他達到能夠使用漢語進行嚴肅寫作的水平。后因父親病危,不得不中斷學業,返回美國。但他坦言在臺灣學習漢語的那段時間成了他人生當中最快樂的時光。
(三)與許芥昱及詩歌學習1、鮮為人知的師生情返美后的葛浩文由于缺乏從事研究經驗,不知自己該做什么,后在長灘州立學院老師的建議下去舊金山州立大學讀碩深造,在那里遇到了“第一位真正的老師”許芥昱(Kai-yuHsu)先生。葛浩文對許評價頗高,稱其為一個了不起的人(aremarkableman)。實際上,許芥昱不僅在漢語學習方面引導葛浩文,而且直接影響了他博士階段的深造,甚至包括他之后所從事的中國近、現代文學翻譯事業。在JonathanStalling的采訪中,葛浩文詳細回憶了他跟許芥昱相處的幾件事情。以下是葛回憶自己第一次拜見許先生的情景:Hesatmedownandhesaid:“What’syourbackground?”Isaid:“Ican’tsay;I’membarrassedtosay.”Hesaid:“Forgetbackground,whatareyourinterests?”Isaid:“I’mnotsure.”Hesaid:“Whatdoyoudo?Whatcanyoudo?”Isaid:“IcanspeakChinese.”Andhesaid:“Let’shearit.”AndsoIdid.Hesaid:“Canyouread?”AndIsaid:“Alittle.”“Canyouwrite?”Isaid:“Notatall.”Hesaid:“We’lltakeyou.”SoIwentintohisclassandIstayedthere,gotamaster’sdegree—somehowtheygavemeamaster’sdegreeafterayearandahalf.從上可知,許芥昱為人非常謙和,行事利落,識才方面眼光獨到。對于當時幾乎一無所長的葛浩文,已在亞裔華人圈頗有影響的許芥昱竟毫不遲疑地將其收下,并在葛畢業后推薦給當時任教于印第安納大學的柳無忌先生(LiuWu-chi)。其次,葛浩文還深情回憶了許芥昱贈送他書法作品的一件小事。博士畢業,葛浩文在舊金山母校謀得一職,工作第一天在走廊里見到許芥昱:Inthehallwayheaskedme:“Canyoustillintonethatpoem?”Isaid,yes,andIdidthewholething.“Notbad.”Thenextdayonmydeskwasapieceofhiscalligraphy—hewasagreatcalligrapher—withthefirstfivecharactersofthatpoem.葛浩文回憶自己當時看到這些字,已經忍不住淚水盈眶。且多年之后再次談及此事,也是不禁滿眼含淚,因為他說這是許先生給他“一輩子的禮物”(Thisisthegiftofalifetime)。不幸的是,三、四年后的一天,一場暴風雨沖走了許芥昱先生所住的“天堂路”(ParadiseLane),人們最終沒有發現他的尸體。幾天后,在UCLA任教的葛浩文被召回,在許芥昱的追悼會上致詞,背誦了那首唐詩以表道別。在采訪中,他這樣回憶:SoI—theycalledmeback—andIspokeathismemorial.Isaid:“Ijustdon’tknowwhatwordstosay,hewasmyteacher,hewasmymentor,hewasmyfriend,hewasmybenefactor.”葛浩文用“老師、精神益友、朋友、和恩人”來相容許芥昱,足見兩人間深厚的師生情誼。而這些是葛浩文之前很少(或從未)對外提到過的。2、詩歌學習碩士期間,葛浩文通過學習逐漸理解漢語拼音并進一步加強對漢語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在欣賞中國詩歌方面他取得了長足進步。在許先生的熏陶和影響下,葛浩文對中國詩歌特有的音律產生了濃厚興趣,這對他日后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翻譯、處理文學作品中詩歌、戲劇等的翻譯有不小幫助。因許芥昱的緣故,葛浩文在研究生階段所選課程均和中國古典文學相關。許先生在文學教育方面沿襲中國式傳統教法:讓學生通過吟誦、背誦來理解古典詩詞;在學問研究方面卻是西方式的:讓學生以研討會交流的形式進行學習。葛浩文在許先生的示范下吟誦五言、七言唐詩,之后博士階段師從柳無忌研究元曲,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與元劇有關。元劇中很多唱詞的音韻和詩歌極為相似,這些都歸功于許芥昱教給他對唐詩、元宋早期散文等詩詞韻律鑒賞的知識(ObviouslyKai-yuhadputthatinmyhead.)。而據葛浩文講,他日后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翻譯時之所以選擇莫言作品最多,翻譯之所以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莫言作品中,聲音成了表現主題的重要手段和內容。而葛浩文對于中國文學作品中的聲律特性則非常著迷。
三、漢語學習和文學翻譯的一些問題處理
葛浩文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對外傳播起了積極的意義。他的譯文常給人一種簡潔、整齊和音律美的感覺。在這次JonathanStalling的采訪中,葛浩文以最近翻譯的莫言《檀香刑》為例,暢談了他在處理小說翻譯中的大量戲劇唱詞和其它語言敘述體方面的重要問題。
1、戲曲唱詞的翻譯莫言創作小說時喜歡利用復雜的結構形式,《檀香刑》每章都以一段山東地方戲—茂腔(貓戲)獨唱開始,且隨著故事發展,戲曲吟唱往往和故事情節相互交織,聲音效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說《檀香刑》幾乎是莫言作品中戲詞出現最多的一部。在小說“前言”,莫言說自己童年記憶中兩種聲音在他一生中揮之不去:火車和貓戲。而火車聲在作品中多已是一種象征意義,貓戲則多表達在聲音層面。對于每章開始部分的唱詞,葛浩文的基本譯法是:第一稿先盡量捕捉戲詞意思,然后參照作者“前言”部分的敘述加深理解。對于并非表達意思,僅為達到某種音律效果,配合特殊樂器演奏的戲曲唱詞,葛浩文采用不同譯法,重現或創造相同效果。譯文中,葛浩文有時用正式語言(formalEnglishtranslations),有時使用敘事散文(narrativeprose),并以斜體表示。他坦言自己早期學習元劇的經歷為翻譯提供很大幫助。翻譯貓戲中敘事性唱詞(narratives)時,葛浩文說自己將自己當觀眾,卻也像演員似的常常唱了起來,以此剝離“詞殼”(vocables),“打撈”重要信息,獲取聽覺而非視覺上的重要聲調和音韻(thesoundandrhyme),最后將這些轉換為英語中具有詩歌、戲劇、唱詞性質的語言。與章首的戲詞不同,章節中的戲詞加入了很多其它因素,所以翻譯時須在意義、韻律、形式和聽覺等各方面尋求一種平衡(Thatisthebalanceofmeaningversusmetrics,versusformandauralityandallthat.)[4]。葛坦言有時會因中英押韻的巨大差異不得不做出某種犧牲,但基本做到確保戲曲唱詞中音律正確、韻腳保持,盡力做到讓目標讀者感覺譯文聽起來很棒[4]。有關文學翻譯中戲劇、詩歌等的內容和音律誰主誰次的問題,在采訪中葛浩文以自己翻譯小說《北京娃娃》的一個故事來說明。他回憶《北京娃娃》中有段“校規校紀”,都是些長短整齊、豆腐塊樣押韻的文字,葛浩文說為此曾費神很久,最后想到英語里類似結構的一首詩,各行字數相同,每行都押韻,就像小說里面的校規一樣。所以他在翻譯時借用了這首詩歌。因覺得原著并非正統嚴肅小說,不必逐句費心思量,所以如此處理,只需將作者意圖傳達即可,有時作品聲音的傳遞、詞語的躍動感(jumpiness)等對他來講更為重要。事實上,作為聽眾有機會欣賞到專業戲曲演員表演莫言《檀香刑》的采訪者JonathanStalling也盛贊葛浩文的翻譯,認為其巧妙地串合了小說中敘事者的念和主角的唱,時而哀傷,時而狂怒,傳達了原著戲曲的精髓,體現了譯者的精打細磨和創新,完全達到了文學作品應有的效果。
2、語言敘述體(narrativeregister)的翻譯葛浩文在采訪中講到他在翻譯每個偉大作家作品時尤其關心的另一問題—語言的敘事體。首先他對敘事體進行了如此解釋:“Wespeakatdifferentlevels.Intermsofwordchoiceandsentencestructure,intermsoftonality,inallkindsofways,wespeak,allofusspeak,atdifferentlevels.”實際上,敘事體泛指因出身、教育、經歷、性格、場景等差異而形成的具有階級差異的語言體。在《檀香刑》中,莫言塑造二十世紀初中國不同階層使用不同敘事體的人物形象。這對中國二十世紀包括二十一世界受過教育的讀者來說理解起來并無大礙,但葛浩文講他在翻譯時,考慮到美國出版商和美國讀者,不能用維多利亞時代英語進行翻譯,以免給讀者造成兩種錯覺:小說人物是講英語的中國人;和小說人物是講著讓人無法理解英語的中國人。因此只能小心措辭以再現小說人物性格。同時他坦言雖然費了很大功夫,甚至花費了比莫言創作更長的時間做翻譯,但在人物語言敘述體方面并非都做到了一一體現差別,或許還需日后再做調整。如小說中有一個受過正規教育的中國官員和他那個沒受過教育的情婦的語言。他說兩種語言不在同一個水平上,但也不能相差太遠,使一個極其文雅一個極其粗俗。葛浩文承認誤解和誤譯在所難免,令人敬佩的認真態度和謙虛作風可見一斑。
3、方言和特殊方言的翻譯眾所周知,方言翻譯是任何文學翻譯當中比較棘手的問題。在這次JonathanStalling的采訪中,葛浩文也談及此問題,并給予較為詳細的解答。葛浩文講,對于中國現當代小說中出現的諸多方言,在英語為母語的目標讀者缺少同類語言和相應“社會語言之鏡子”(sociolinguisticmirrors)的情況下,為盡可能傳遞作家意圖,譯者有時不得不創作一種變異的語調形式(formsofdifferentiationoftone)。而對于某些特殊方言,如莫言作品中出現的體現性別差異的農村方言,葛浩文稱一般還是會參考英語中的性別語言進行翻譯,盡管常常感覺很難脫離漢語(尤其是僅有漢語才能達到某種效果時)去調整方法將其用英語翻譯出來。[4]對于常規正式方言如何進行翻譯?首先涉及到方言的鑒別問題。葛浩文稱他通常得利于自己很好的語言功底,如對閩南語的了解和較大漢語詞匯的掌握。碰到不理解的語言,首先猜測會不會是方言,然后借助一些工具如字典和谷歌、百度等網絡工具進行查詢。有時會遇到特殊方言,比方言還方言(moreidiolectthandialect),如某些地方對某些詞語的特定重復使用,使其變為方言的一部分。也有小說中的特殊方言僅是作者的口頭禪(tic)或對某些語言的特別使用而已。葛浩文提到賈平凹小說中到處可見的西安方言和陜西山區話,常讓自己苦惱。那么如何處理這些呢?是否將這些方言翻譯成一種聽起來很酷的、說唱的、陌生的或其它語言呢?葛浩文認為在更廣或全球化層面上講,答案并不唯一,有時肯定,有時否定,有時兩者兼而有之,主要取決于小說本身。譯者倘若能找到恰當的俚語式、地方語式或稍古語類或不常用的詞語表達同樣的意思,當然會使用,如果實在不能找到,便不用了。因為畢竟源語讀者看小說時并不在意這些方言,目標語讀者也不在意,譯者就沒必要折磨自己。
四、結語
作為學者,葛浩文雖是以學習古典漢語、中國古典文學為始,之后開始研究和翻譯蕭紅及東北作家群,最終卻從文學評論轉移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翻譯的道路上,直到現今,可見他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愈來愈多的關注和關心[5]。他一生豐富的經歷和學者身份轉變造就了獨特的漢學家身份。所以在從事中國文學對外翻譯時,葛浩文更能以一種不同方式和目光審視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問題。他對目標語讀者的關注、譯者主體性的認識、中國翻譯文學命運的判斷等,甚至對于中國作家如何才能在全球背景下進行創作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走近葛浩文,了解他的學者經歷往往更能直接理解他的翻譯目的和手段,也更能幫助中國文學接近世界讀者。
作者:張彩虹 單位:西安科技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
- 上一篇:功能翻譯理論下的兒童文學翻譯范文
- 下一篇:翻譯碩士文學翻譯錯誤及歸因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