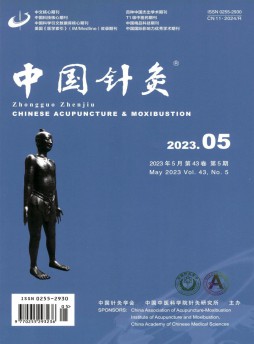中國詩性文化特征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詩性文化特征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中國傳統的“詩性文化”產生于“亞細亞的古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感性與理性未經徹底分化的“早熟”狀態,其主要特征為:(一)在所有的藝術產品中,詩歌具有主導和擴散的地位。(二)在所有的文化產品中,藝術具有主導和擴散的地位。(三)“禮樂文化”的行為準則使人們的言談舉止均具有著藝術的特征。(四)“世俗文化”的信仰空缺使藝術具有了準宗教的功能。(五)屬于漢藏語系的民族語言所具有的模糊性、多義性和音樂性特征與藝術的表達之間有著一種天然的親和關系。上述特征的分析不僅有助于我們從結構和功能的角度來重新理解傳統文化,而且對當今中國的美學理論和藝術實踐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一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習性,一種文化有一種文化的特征。說到中華民族,人們常用“詩性民族”、“泛美文化”等概念加以概括,然而這些習而不察、用而不知、語焉未詳的概念背后究竟有多少根據呢?對于它們的理解是否有助于我們的文化反思呢?筆者在《多維視野中的儒家文化》一書中曾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做過一番簡單的比較,認為由于“古典的古代”與“亞細亞的古代”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使得西方人在進入文明時代的進程中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分裂得比較徹底,從而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的也將感性和理性分裂的比較徹底;而中國人則更多地保存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天然聯系和原始情感,從而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的也更多地保持了感性和理性相互滲透的原初狀態。表現在文化結構上,西方人以相互對立的兩極最為發達,在感性方面有體育,在理性方面有科學;而中國古代既沒有奧林匹克式的體育傳統,也沒有畢達哥拉斯學派似的科學精神。相反的,在中國的文化結構中,藝術和技術則占有了極其重要的地位,因為無論藝術還是技術,都既非單純的感性,也非純粹的理性,而是將二者統一在一起的。這不僅符合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心理結構,而且也為“詩性民族”、“泛美文化”等課題的研究廓清了一些障礙(詳見拙作《多為視野中的儒家文化》第五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將在此基礎上從藝術產品、文化產品、行為方式、信仰方式、語言特征等五個方面加以分析,并在進一步反思我們自近代以來在藝術和美學方面所走過的彎路。說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首先是因為“詩”這種文化產品在中國藝術中占有著特殊地位。從春秋的“詩經”到戰國的“楚辭”,再到漢魏的“樂府”,從“唐詩”到“宋詞”再到“元曲”,詩這種形式雖然千變萬化,但卻始終占據著中國藝術的主導地位,并滲透到以后出現的其他藝術形式之中:不僅戲曲“以詩為詞”,小說“有詩為證”,而且書法也要寫詩,繪畫也要提詩。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真正含義,是將“意境”作為一切藝術所追求的最高目的。從這一意義上,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傳統的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其次,說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不僅是因為詩的精神主宰著中國藝術的整體精神,而且也由于以詩為靈魂的藝術精神影響和左右著藝術之外的文化產品。在感性活動方面,中國的體育并不以開發人的肉體極限為目的,也從來不陷入狄俄尼索斯式的迷狂,而是在感性宣泄中強調理性的制約,在肉體的拼搏中注重智慧的較量。中國的武術不同于西方的拳擊,它不僅要打得準、打得狠,而且要打得巧妙、打得漂亮。即要在花拳秀腿之中創造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最能代表中國體育精神的不是足球,而是太極拳,它不是一種忘乎所以的肉體迷狂,而是強調身與心的統
一、氣與力的和諧。直到今天,我們在國際體育競賽中的強項大都帶有藝術的成分,如體操、跳水、技巧之類,而在足球、田徑等單純感性較量、張揚肉體迷狂的項目中,我們則常常處于先天的弱勢地位。說到底,中國人的體育觀念和西方人有著明顯的不同:中國人不僅要以力量、以速度為原則,更要以美為原則;而在西方人那里,即使是所謂的“健美”活動,也不惜為了考察人的肉體極限而將其變得畸形……。在理性方面,中國的科學并不以開發人的理性能力為目的,也從不陷入阿波羅式的精神沉醉,而是使理性的運演不脫離經驗的內容。正如中國的體育活動往往具有藝術特征一樣,傳統的科學活動也常常具有審美的性質。例如,張衡的“地動移”既可以看作是一件科學儀器,也可以看作是一件藝術精品;而傳統的許多中醫方劑則采取歌訣體。這同西方人將科學的發展引向邏輯化、思辨化、超驗化的軌跡完全不同。正因如此,中國人可以通過反復測算而為圓周率的值找到一個相當精確的數據,但卻不可能建立起一種歐幾里德式的幾何學體系;中國人可以通過反復實踐而建造起天壇祈年殿式的精美建筑,但卻不可能建構起一個牛頓式的力學體系。中國的文化傳統使人們長于實踐理性而短于思辨理性,因而不少科學成果都具有工藝特征。例如,指南針不是電磁學,造紙術不是物理學,傳統的火藥不是依據化學方程式配制出來的,而活字印刷更不具備理論科學的特征。如此說來,我們長期以來引以為自豪的“四大發明”并非科學,而只是工藝……。總之,中國的文化產品,有著感性和理性相互融合的整體特征,這使得一切文化產品都在向藝術和工藝靠攏。不僅體育和科學活動有著藝術化的傾向,其他活動也是如此,我們常把戰爭和外交活動稱之為軍事藝術、外交藝術,這其中的意味便很令人深思。第三,不僅中國古代的文化產品滲透了藝術精神,而且中國古人的行為方式也具有著審美的品格。與依靠法律來約束人們外在行為的西方不同,中國古代主要仰仗倫理來調節人們的社會活動。《樂記·樂本篇》云:“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這樣一來,“樂”這種廣義的藝術,便不僅成了“禮”的合法補充,而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機構成。只有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才能夠理解孔子“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的意義所在。在“禮樂文化”的構架內,人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不僅要符合“禮”的規范,而且要具有“樂”的儒雅,即具備審美的特征。因此,就在西方的經院哲學家們通過邏輯或數學等手段來揭示宇宙、乃至上帝的奧秘時,自隋、唐而開始的科舉制度卻要將寫詩和作文看成是每一個國家官吏所首先應具備的素質。這種對國家的統治者和管理者的美學要求,在世界范圍內都是極為罕見的……。與儒家不同,道家是反抗禮樂文化的,但其“乘物以游心”(《莊子·人間世》)的逍遙精神更容易讓人們以審美的態度來對待全部生活。無論是在老子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四十一》),還是莊子的“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莊子·大宗師》)都顯得比儒家更加接近于藝術的境界。因此,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們可以不懂天文、歷算知識,但卻必須用琴、棋、書、畫來修養身心。這種特有的行為方式和休養方式,難道不正是“詩性文化”的顯著標志嗎?第四,從信仰方式的角度上講,中國的傳統藝術的過分發達,在功能上有著彌補宗教信仰的特殊意義。我們知道,在具有宗教傳統的西方社會,藝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起著引導人們走向上帝的中介作用。與之相反,在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社會里,藝術的境界可以撫慰人們的情感、陶冶人們的性情,從而起著準宗教的功能。正因如此,被稱為中國思想主要支柱的儒、道、騷、禪四家,無不以審美和藝術為其最高境界。孔子畢生“克己復禮”,但在關鍵的時刻還是道出了“吾與點也”(《論語·先進》)的名言;莊子畢生“絕圣齊知”,但其“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莊子·天下》)的文章,顯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藝術精品;楚騷思想自不待言,其中的神人、仙女并不是信仰的對象,而是審美的化身;佛教本來是從印度一帶傳入的宗教,但中國化了的禪宗卻揚棄了其中的思辨內容和行為戒律,把它引向了充分自由的審美境界。唯其如此,我們才能理解,中國古代為什么沒有《圣經》,但卻有了《詩經》。這種“以詩為經”的文化現象,在世界范圍內也是獨一無二的。第五,從語言的角度上講,說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也有著相當重要的理論根據。與印歐語系相比,屬于漢藏語系的漢語在詞匯上具有多義性、模糊性的特點,在語法上具有靈活性、隨意性的特點,在語音上具有因聲調而帶來的音樂性的特點,這一切自然無助于邏輯性的表述和科學性的思維,但恰恰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藝術性的思維(參閱加爾通、西村文子《結構、文化和語言——印歐語系語言、漢語、日語比較研究》,《國外社會科學》1985年,第8期。)。一個民族的語言,不僅是一種特殊的表述方式,而且是一種獨特的思維、感受、乃至存在方式。從這個“存在的家園”出發,中國人自古就以一種詩性的思維和詩性的態度來對待世界。精通近十種語言的辜鴻銘指出:“漢語是一種心靈的語言、一種詩的語言,它具有詩意和韻味,這便是為什么即使是古代的中國人的一封散文體短信,讀起來也像一首詩的緣故。”(《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頁)二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發現,文化的比較不應該局限于元素性、整體性的,而應該擴展為結構性、功能性的。從結構性、功能性的角度來看,感性和理性徹底分裂的西方人有其相應的文化優勢;而感性和理性分裂得不夠徹底的中國人亦有其相應的文化優勢。如果說西方的優勢在科學、在體育,那么中國的優勢則在藝術、在工藝。用西方的科學標準來衡量中國,“必須承認,就中國人的智力發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地限制了。眾所周知,在有些領域中國人只取得了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么進步。這不僅有在自然方面的,也有純抽象科學方面的,諸如數學、邏輯學、形而上學。實際上歐洲語言中‘科學’與‘邏輯’二字,是無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對應的詞加以表達的。”(辜鴻鳴《中國人的精神》第36-37頁)反之,如果用中國的藝術標準來衡量西方,也會發現其陷入的誤區。著名藝術評論家勃納德·貝倫森在比較西方與東方藝術時曾經指出:“我們歐洲人的藝術有著一個致命的、向著科學發展的趨向。”(轉引自《中國人的精神》第39頁)以“摹仿說”為理論依據,西方自古希臘以來便以對現實生活的反映與認識作為藝術活動的最終目的,因而從解剖學角度來研究雕塑,從透視學角度來研究繪畫,從幾何學的角度來研究園林,從歷史學角度來研究小說……。結果是研究來研究去,惟獨是忘卻了藝術自身的美學目的。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近代,我們都知道,巴爾札克是西方19世紀最為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家了,他的《人間喜劇》包括了96部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分為“風俗研究”、“哲學研究”和“分析研究”,可謂“研究”得到家了。對此,恩格斯曾有過高度評價:“他在《人間喜劇》中為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歷史,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沖擊描寫出來……。在這幅中心圖畫的四周,他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我從這里,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后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致瑪·哈克奈斯》,《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190頁。)無論這部“歷史”如何卓越,無論這其中所體現的“知識”如何豐富,然而歷史只不過是歷史,知識只不過是知識,“文學”畢竟不是“經濟學”或“統計學”,它所包含的歷史和知識與其所應該具備的美學價值完全是兩個范疇的東西。在這種將文學變成“百科全書”的科學化傾向的同時,西方人的理性沖動還有著用藝術進行“形而上思考”的宗教化、哲學化的傾向。如果我們對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甚至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這些被西方人所稱道的文學名著加以分析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它們與其說是藝術上的成功,不如說是哲理上的勝利。不要以為這是個別的、暫時的問題,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現象竟變得日益嚴重起來。難怪黑格爾曾發出藝術最終將讓位于哲學的慨嘆,現代博物館里那琳瑯滿目的“觀念藝術”已足以證明了這位哲學巨匠的預見能力。如果說科學精神、哲學精神這兩種緣自阿波羅崇拜的理性因素支配并扭曲著傳統的西方藝術的話,那么到了現當代以后,一種緣自狄俄尼索斯崇拜的感性迷狂又乘火打劫地闖入了西方藝術的殿堂。打開電視,我們隨時都可以看到那些所謂“大投入”、“大制作”的好萊塢式的“巨片”。那種以、警匪為內容,以追車、槍戰為模式的用金錢堆積起來的作品,不惜調動高科技手段,并通過大量的驚險動作和破壞性鏡頭來刺激人們的感官、滿足人們的欲望。難怪馬爾庫塞在去世前的一次談話中會憤然地指出,現代西方的藝術已經變成了一種智力上的自淫!除此之外,當然還有那些聲嘶力竭的“搖滾樂”和幾近瘋狂的“霹靂舞”……。如果說前一種誤區是將藝術引向科學,那么這后一種誤區則是將藝術引向體育。事實上,服用興奮劑是搖滾歌手和體育名星們常犯的錯誤,而這一錯誤則剛好表現了一種文化的誤區。研究者們可以并且常常籠統地講,西方藝術已經完成了由古代的“再現”向現代的“表現”相過渡的歷史性轉折。然而細加分析,我們也許會發現,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西方藝術在感性與理性的統一上總是顯得那么的生硬和艱難,這一切甚至在所謂的“現代派”的藝術“精品”中也暴露得一清二楚。面對著畢加索那幅怪模怪樣的《格爾尼卡》,翻閱著喬伊斯那本人欲橫流的《尤利西斯》,我們不禁要問:深刻而又狂放的西方人,這難道就是你們所要追求的藝術理想嗎?與西方相反,在具有“詩性文化”的古代中國,無論是自發的藝術創作,還是自覺的藝術理論,都沒有將感性和理性割裂開來,也沒有使藝術淪為科學或體育。在雕塑和繪畫方面,中國人一開始就不以純粹科學的手法來摹仿自然,而懂得如何在一種“似與不似之間”而獲得“氣韻生動”的美學效果。在詩歌和小說方面,中國人一開始就不以純粹客觀的態度來再現生活,而懂得如何“想象以為事,惝恍以為情”,以達到一種“登山而情滿于山,觀海而意溢于海”的精神境界。在戲曲藝術方面,中國人一開始就不去追求舞臺時空的真實幻覺,而懂得如何利用程式化的規則和虛擬化的手段將舞臺和道具都變成表演活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以獲得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感體驗。在園林藝術方面,中國人一開始就不追求簡單的對稱和機械的構圖,而是懂得如何處理陰陽、動靜、虛實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實現一種“神與物游”、“物我兩忘”的審美理想。甚至,在書法寫作之中,中國人都懂得如何發揮自己的想象,如何孕育自己的情感,從而在“意在筆先”、“得意忘言”的創作中將單純的筆墨線條演繹成為一種登峰造極的藝術形式……。漫步雕林,我們當然也會贊嘆古希臘《擲鐵餅者》那精確的骨骼和隆起的肌肉,然而如若將其與漢將霍去病墓前那幾座稍加斧鑿便渾然天成的動物雕塑加以比較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究竟哪個民族更懂得“藝術”。漫步園林,我們自然也會贊美凡爾賽宮前那對稱的噴泉、整潔的道路,以及被切割成幾何圖案的花卉與草坪,然而如若將其與蘇州拙政園那山重水復、柳暗花明,直至將天地自然融為一體的園林藝術加以比較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究竟哪個民族更富有“天才”……。正因如此,與巴爾扎克將文學著作寫成“編年史”的努力剛好相反,司馬遷卻使一部真正的史書具有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美學價值。正因如此,即使是《紅樓夢》那樣洞徹古今、勘破生死的作品,也絕不會像《哈姆雷特》那樣,擺出一副哲人的面孔,與讀者討論什么“tobeornottobe”之類的玄學問題。在“詩性文化”的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中國藝術,很少陷入一種純粹感性的欲望宣泄,也很少進入一種純粹理性的思辨誤區。這不僅是出于“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政治需要,而且是由于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很容易將感性與理性的東西親密無間地融合在一起。因此,無論是一篇短文,還是一首小詩,都可能給人以咀嚼不完、回味無盡的余地。因此,在閱讀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時,除了文字上的障礙之外,人們很少會遇到費解或難懂的現象,有的只是能否體驗或產生共鳴的問題。因為說到底,“懂”與“不懂”的問題,是一種知識問題、哲理問題,而體驗和共鳴的問題,才真正屬于藝術和審美的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不能說中國藝術比西方藝術更為深刻,但卻比其更加符合美學規律。三不幸的是,近代以來,由于理論和實踐上的雙重原因,這種“更加符合美學規律”的“詩性文化”卻中斷或扭曲了。在理論上,我們常常有一種誤解,認為一種文化較之另一種文化或者具有全面的優勢,或者具有全面的劣勢。按照這一思路,不少人以為,既然船堅炮利的西方科學比中國發達,西方的藝術也毫無疑問地應當成為我們效法的對象。于是,從“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并“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詩料”(梁啟超《夏威夷游記》)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到具有“全盤西化”色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及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我們從前蘇聯引進的那一套以“反映論”為基礎的“文藝理論”體系,我們便一步一步地引進和確立了西方的藝術觀念,并用它來評價和批判我們的傳統藝術,用它來指導和規范我們的現實創作。在實踐上,由于近現代以來,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過于沉重,致使文學藝術不得不承擔起其美學使命之外的思想啟蒙任務,因而上述理論的轉向也恰恰符合了實踐的需要。于是,從“譴責小說”到“普羅文學”,從“白話新詩”到“抗戰戲劇”,藝術的理性內容日漸突出了,藝術的政治觀念愈發明確了,藝術越來越變得更像匕首、更像投槍了;與此同時,藝術的美學價值也就越來越淡薄了。由于政治和經濟的諸多原因,我們當然不能脫離這一階段的社會背景來簡單地否定“詩性文化”的上述轉型。但是,當我們從啟蒙主義的政治立場上充分肯定近代以來上述“革命”之重大成就的同時,我們是不是也應考慮一下它在文化和美學上的缺失呢?當然,我們沒有權力簡單地責備前人,如果我們處在他們的歷史背景下,我們也會義無反顧地將文學藝術投身于更為重要的社會變革;然而處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是否有權力沿襲并發展前人所無法克服的歷史局限,并將其導向更為極端的誤區呢?反思是必要的,反思又是艱難的。在思想原則上,我們必須勇敢地打破那套習以為常的整體文化觀念;在理論操作上,我們必須謹慎地把握好以下尺度:第一,人類的共同性是絕對的,而文化的差異性則是相對的。無論是“古典的古代”,還是“亞細亞的古代”,都是人類的古代。因此,我們切不可將中國與西方文化結構上的差異絕對化。正如感性與理性分裂得不夠徹底的中國人也有自己的體育與科學一樣,感性與理性徹底分裂的西方人在藝術和工藝方面依然留下了杰出的成果。第二,文化結構的差異導致了藝術觀念的差異,但藝術觀念的差異并不簡單地等同于藝術成就的高低。必須看到,在對具體藝術作品的評價中,我們不僅要考慮其審美價值,還必須考慮其再現社會生活、表達人生理想等政治、歷史影響,以及材料、工藝、技法等多重因素。所有這一切,并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觀念所能決定的。但是,正如康德在承認“依存美”比“純粹美”更為普遍前提下還要探討“單純美”一樣,我們也必須充分地意識到,探討文學藝術的文化本質是何等的重要。其重要性并不要論證中國古代的藝術成就高于西方,而在于論證我們傳統的藝術觀念更具有美學價值,因此可以沿著這條道路為人類文化做出新的貢獻,而沒有必要舍本逐末地效法西方。第三,由于審美活動與意識形態以及整個社會生活之間的復雜關系,我們很難用“革命”與“保守”等標準來簡單地評價一個民族、一個時期的藝術實踐和文化轉型,我們也很難用“進步”與“落后”等尺度來簡單地判斷一股思潮、一部作品的文化價值和美學意義。在澄清上述界限之后,我們便可以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諸多問題進行重新的思考。如,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中西文化中已被公認的藝術經典?我們應該如何評估中國近代以來為啟蒙事業所付出的美學代價?白話文運動在何種意義上是成功的,在何種意義上又是失敗的?自由體新詩在什么地方突破了格律體舊詩的束縛,又是什么原因而未能留下唐詩、宋詞式的經典作品?以及我們是否應該以爭取諾貝爾獎作為嚴肅文學發展的方向?我們是否應該以美國“大片”作為通俗藝術學習的楷模?如何評價藝術作品中的科技含量?怎樣看待藝術作品中的理性內容?最重要的是:在世界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文學藝術究竟應該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個性并為人類做出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