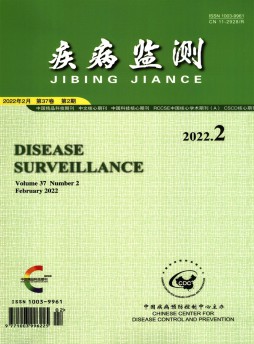疾病隱喻與文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疾病隱喻與文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蘇珊·桑塔格對于西方文化中“疾病隱喻”的分析,揭示了人類文化在疾病隱喻中表現出來的問題。她的批評實踐觸及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問題:隱喻修辭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身體的文化與道德意義以及疾病與“他者”的建構。
[關鍵詞]蘇珊·桑塔格;疾病隱喻;《疾病的隱喻》;文化研究
一、隱喻修辭與意識形態
對于“隱喻”,蘇珊·桑塔格采用了亞里斯多德的定義,即“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而所謂“疾病隱喻”,就是把疾病作為形容詞,即說某事物“像”或“是”疾病,是指這事惡心或丑惡,在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上不正確。桑塔格在論述中引用了西方文化中的許多疾病隱喻,比如,“看任何一個大城市縱橫交錯的平面圖,就是在看纖維瘤的縱橫交錯”;“西藏的那種隱修生活方式,對文明來說,是一種結核病”。這告訴我們,隱喻這種人類創造性思維形式和修辭手段,可能是危險的,應該警惕和摒棄那些在文化上不正確、在意識形態上具有欺騙性和鼓動性的隱喻,尤其是疾病隱喻。
作為一種常識,人們總是認為隱喻修辭的巢穴是文學語言,它使文學描繪顯得生動、形象和充滿想象力。然而,這一常識逐漸為當代西方知識界所顛覆,隱喻不再被視為文學語言的專長,而被確認為是語言、甚至思維的基本形式與特征。美國當代認知語言學家納可夫和約翰遜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們在其名著《我們賴以生活的隱喻》中指出:“隱喻在日常生活中是無所不在的,不但存在于語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為中,我們賴以生存和思考的一般概念系統,從本質上說都是隱喻性的。”這一觀點指出,人類賴以思維的語言概念都是隱喻性的。比如,“長江口”、“瓶頸”、“桌子腿”、“箭頭”、“了如指掌”中的身體隱喻;“人生道路”、“社會舞臺”、“把溫度調高”、“情緒高漲”中的空間隱喻;“大腦是臺機器”、“人類社會的肌體”中的結構隱喻等等。如此看來,人類思維根本不可能廢除隱喻,然而,隱喻是否就是一干二凈、毫無問題呢?身為癌癥患者,出于對隱喻修辭的敏感和對疾病隱喻的痛恨,桑塔格說:“當然,沒有隱喻,一個人就不可能進行思考。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存在一些我們寧可避而不用或者試圖廢置的隱喻。”
在桑塔格看來,疾病隱喻是一種雙向的映射結構,一方是難以治愈、危及生命的疾病,另一方是某種被認為丑惡、淫邪的壞事物。通過其間建立“相似性”,疾病隱喻既可以輕易地把某個所謂的壞事物描繪為邪惡的,又使某種疾病的邪惡和道德色彩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對于疾病隱喻的普遍使用,桑塔格說:“當我們感到了邪惡卻又不再擁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學的語言來理智地談論邪惡時,我們怎樣才能做到謹慎?為了去了解‘極端的’或‘絕對的’邪惡,我們于是尋求合適的隱喻。然而,現代的疾病隱喻都不過是些廉價貨。那些真正患病的人聽到他們的病名常常被當作邪惡的象征拋來拋去,這于他們又有何助益?”從古至今,對疾病的厭惡和恐懼,都廣泛存在著,尤其是那些病因不明、難以治愈的重疾。而且由于各種非醫學話語(迷信話語、道德話語等)的推波助瀾,不僅給這些疾病涂上了神秘色彩,還使疾病獲得了非常豐富的文化與道德意義。由此,疾病或疾病意象就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積累和攜帶著人類的恐懼和非常復雜的文化與道德意義。當人們無法理智地思考和描繪“極端”或“絕對”的邪惡時,疾病意象就成為一種唾手可得的、廉價的修辭方式,疾病也就成為邪惡的象征。由于人們在疾病隱喻中不斷地把疾病與其他可惡和不道德的事物相提并論,疾病與邪惡之間似乎劃上了等號,疾病的邪惡和不道德意義也就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這對病人,無異于雪上加霜。
在桑塔格看來,政治領域的疾病隱喻從來都不是清白的,它的目的無外乎煽動暴力,并使嚴厲的措施正當化,因而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的修辭手段:“癌癥隱喻卻尤其顯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種慫恿,慫恿人們去把復雜的事情簡單化,亦不外乎是一種引誘,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熱,也誘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萬般正確的”。關于政治話語中的疾病隱喻,桑塔格列舉了許多例子。如,阿拉伯人常常把以色列說成是“中東的瘤子”;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義稱作馬克思主義的“癌瘤”;納粹宣稱血液中混有其他種族血統的人都“是”梅毒患者。可以說,政治話語中的疾病隱喻,很可能是對疾病意象的暴力運用,它激發的不是理性思考而是非理性的狂熱。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疾病意象所積累和攜帶的恐懼與邪惡被拋向了某個政治事件,從而把這一事件定性為徹頭徹尾的邪惡,這就大大增加了指責者的本錢,使得嚴厲的措施合法化。
英國學者安德魯·本尼特和尼古拉·羅伊爾在論及比喻(明喻和隱喻)時指出:“對修辭性語言的操控與開發對于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會甚至經濟制度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由我們用以談論它的各種修辭手段所調控的。”這兩位學者的觀點強調隱喻等修辭手段在人類政治、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強調各種語言修辭與某一文化的思維方式、文化意義與意識形態價值系統之間的聯系,從而提醒人們注意隱喻等修辭手段潛在的意識形態意圖。桑塔格對于疾病隱喻的分析正是一種隱喻修辭的文化與意識形態批判,她的批評實踐讓我們再度審視這樣一個事實:隱喻,不論它在文學藝術和日常表達中創造了多么美妙的言詞,它都是一種修辭;而按照其本義,修辭是一種使用語言或其它符號去說服他人和影響他人態度的技巧,因此,在很多情況下,說某事物“像”或“是”另外一個事物,并不是為了更好地、更鮮明地說明和形容這個事物的實際狀況或特征,而是為了“說服”的目的,這時的隱喻就成為了一種政治動員和意識形態宣傳的手段。
隱喻是一種表情達意的修辭手段,也是一種文化“癥候”,因為它攜帶和傳達了某種文化假設、道德意義與意識形態意圖。因此,對于許多形式的隱喻,應該保持一種警惕和謹慎的態度。比如,戰爭(或軍事)隱喻就是一個值得揣摩和審視的隱喻,因為“戰爭被定義為一種緊急狀態,犧牲再大,也不過分。”當然,在某些情況下,戰爭隱喻還是可取的、必需的,如搶險救災中的“眾志成城”、“奮戰到底”、“人民戰爭”等等這些喚起團結和激發斗志的隱喻。對于戰爭隱喻,我們要警惕的是它可能激發的非理性、狂熱和盲從。
二、身體的文化與道德意義
桑塔格明確指出其寫作《作為隱喻的疾病》一文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發想象。不是去演繹意義(此乃文學活動之傳統宗旨),而是從意義中剝離出一些東西:這一次,我把那種具有唐吉訶德色彩和高度辯論性的‘反對闡釋’策略運用到了真實世界,運用到了身體上。”在文學藝術領域,桑塔格提倡的“反對闡釋”是一種形式主義美學宣言,目的是反對把文學藝術減縮為內容、意義和思想而忽視了文學藝術中蘊含的感性體驗。因為在她看來,闡釋就是通過各種話語賦予世界以意義,無論這些意義是道德的、政治的,還是宗教的:“不惟如此,闡釋還是智力對世界的報復。去闡釋,就是去使世界貧瘠,使世界枯竭———為的是另建一個‘意義’的影子世界。闡釋是把世界轉換成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倒好像還有另一個世界)。”以上論斷,可以視為桑塔格的“反文化”宣言,一種對于資本主義文化道德與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影子的世界”)的全面反叛,因為正是這套意義與價值系統禁錮著人們的思維,妨礙了人們通過“聽”和“看”來獲得對于世界的體驗。桑塔格對于疾病的道德意義的剝離,是其文學藝術領域的“反對闡釋”策略在身體與疾病問題上的運用。
在當今文化研究的視域中,身體不僅是一個生理的、自然的實體,而且是一個文化價值觀念與社會權力銘刻其中的場所。英國的阿雷恩·鮑爾德溫等學者指出:“人的身體是文化的客體盡管人的身體是由一種不容置疑的自然基質組成的,其外觀、狀態和活動都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組成。”[6]從我們身體的外觀,到狀態,再到活動,都具有某種文化意義與價值規范。大多數文化研究學者對于身體的關注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文化如何塑造和規訓我們的身體,比如,文化如何為社會個體的男性化或女性化提供向導和訓誡;二是批判某一文化賦予某種身體形式(性別、種族和階級)的意義與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如黑人的身體往往攜帶了更多的壓制性、恥辱性意義。桑塔格的批評實踐屬于第二種,它關注的對象也是身體,是患病的身體,它的目標是清理疾病的道德意義。
對于疾病,桑塔格是一個堅定的科學主義者,她堅信:“所有那些病因已被查明、并且能被控制和治愈的疾病,最終都被證明只有一個生理原因———如雙球菌之于肺炎,結核桿菌之于結核病,維他命缺乏之于糙皮病———因此,極有可能,將來也會為癌癥找到類似的單一的東西(即單一的病因和單一的治療方法)。”基于這種對疾病的科學主義或“生理主義”看法,桑塔格歷數了特定時期的西方文化如何以非科學的話語,尤其是迷信話語、道德話語,建構有關疾病的“神話”和文化道德意義的現象。其中,桑塔格尤其反對疾病的宗教迷信解釋和“心理學”解釋,因為這些有關疾病的幻象和神話,不僅透露出人們對于疾病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貧乏,而且全都認定患者自己對患上疾病負有責任,比如,《伊利亞特》、《俄狄浦斯王》中所體現的古代世界把疾病當作上天降罪的工具;結核病被認為是那些敏感、消極、對生活缺乏熱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的病,這些人在活力和生命力方面有明顯缺陷;癌癥被認為是一種激情匱乏的病,癌癥患者往往是那些性壓抑的、克制的、無沖動的、無力發泄火氣的人。
疾病是否應該有道德意義?桑塔格有關疾病的“去意義”策略和“生理主義”態度得到了許多學者的支持。然而,當這種“生理主義”涉及艾滋病時,桑塔格就遭到了許多批評。對此,英國學者安吉拉·默克羅比就曾指出:“她的小心翼翼和謹慎態度激怒了批評家。她避免談論艾滋病的文化意義和艾滋病的政治意義緊密結合的程度。”默克羅比認為,艾滋病的意義比癌癥更加深遠,與身體政治的結合也更加緊密,艾滋病與性冒險、、同性戀有著密切的聯系,而且還可以傳染給所有人。因此,桑塔格對于艾滋病的文化與道德意義避而不談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對于這種爭議,當今世界的官方主流文化對于艾滋病問題大都采取了一種折衷的態度:可以從各自的立場對導致艾滋病的某些行為進行道德評價,但對于患者與疾病本身則操持一種給予同情和反對歧視的態度,這無疑又淡化了疾病本身的道德意義。
人類生活在一個文化意義的海洋,其中有許多意義是有關身體的壓制性、恥辱性意義,它們構成了桑塔格所謂“影子的世界”的一部分。桑塔格力圖去除患病的身體所承載的道德意義,呼喚一種更加開明、寬容和進步的文化的到來,這種文化將表現出更加鮮明的樂觀主義和人道主義。不僅如此,桑塔格的批評實踐還彰顯了當今文化研究一貫的批評路線和立場:在人類的歷史上,圍繞著下層階級、女性、黑人和少數族裔的身體形式,有著非常豐富和復雜的文化意義與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對于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來說,擯棄和清理那些具有壓制性、歧視性的意義與價值,是一條遠未走完的道路。
三、疾病與“他者”的建構桑塔格說:“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疾病有關社會個體的身體,也會轉化為一種社會身份。只要某種特別的疾病被當作邪惡的壞事,那么大多數患者一旦獲悉自己患了這種疾病,總會覺得在道德上低人一頭,于是患者就獲得了一種他者身份,一個健康王國的“他者”。桑塔格的批評實踐所代言的群體,就是作為“他者”的某些疾病的患者。她的相關論述一方面讓我們看到了患者或病人被“他者化”的過程,另一方面又展示了與疾病有關的其它形式的“他者化”過程,它們有的基于地緣和民族問題,有的基于政治和殖民統治問題。
黑格爾曾使用過“他者”這一概念,他認為如果沒有對“他者”的承認和認識,人類個體無法獲得自身的“自我意識”。比如,主人和奴隸是互為定義的。表面上主人好像無所不能,但實際上,他需要奴隸來確認自身,即他的自我意識的獲得依靠奴隸的存在。在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哲學傳統中,“他者”也是主體建構自我形象的要素。“他者”(特定群體或個人)的存在幫助或強迫主體選擇一種特殊的世界觀念和價值觀念來確定其自身的位置在何處。英國學者丹尼·卡瓦拉羅指出:“‘他性’是所有社會身份中的一個基本要素。他者就在我們之中。當一種文化、社會或團體把某個個體排斥做他者時,它試圖排除或壓制的實際上是它自身的一部分.”在文化研究的視域中,特定社會和文化中的“他者”,是社會權力結構中處于弱勢的群體,如女性、黑人、作為殖民地的國家和民族、少數族裔等等;而“他者”作為一種弱勢群體的社會身份,總是積累和攜帶了大量消極的、壓制性的文化意義與價值觀念。桑塔格的批評實踐促使人們認真審視病人的“他者”身份及其潛在的不公正。
病人,尤其那些身體出了嚴重問題的人,或被認為是由于虛弱而應該受到特殊照顧的弱者,或被認為是性格和生活習慣有缺陷的人,或被認為是已經沒有發展前途的人,或被認為是由于自身的邪惡或不道德而應該得到懲罰的人,或被認為是行將就木的人。無論各種社會話語把疾病的來源歸因于天譴、不良生活習慣、遺傳或性格,患上重疾的病人都是一種很容易產生恥辱感的作為“他者”的人。比如,得知自己患了癌癥的人總是傾向于對自己所患之病三緘其口,因為癌癥很可能被當作一樁丑事,會危及他的生活、晉升機會、甚至他的工作。可以說某些病人的“他者”身份,不僅給他帶來精神上的恥辱與痛苦,還會影響到其生存資源的獲得。
桑塔格特別指出,那些致命的、對身體外觀(尤其是臉部)有特別損害的疾病最容易獲得道德意義。可以說,人類對于身體完美的追求,是疾病獲得恥辱性意義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人類身體力量、美麗和健康的贊美是文學藝術的傳統主題,這似乎為人類的身體提供了一個理想標本,嚴重背離這一理想的身體都是“他者”。在論及西方文化如何把殘疾人排斥為“他者”時,英國學者萊恩·伯頓指出:貫穿有記錄之歷史的對殘疾人的一貫的偏見,都是由“身體完美”的理想和對“完美神話”的追求引起的,這種對身體完美的追求將引起包括恐懼、害怕、焦慮、厭惡、懷疑、憐憫、過度保護等一系列常見的社會反應。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類社會與文化建構了許多基于身體疾病或缺陷的“他者”,病人、侏儒、殘疾人、智障者等等,他們都是社會與文化中的“他者”,都因為自身的“他者”身份而飽受恥辱。比如,為了追求身體(和道德)的完美,希臘人譴責殘疾———火神赫菲斯托斯就因跛足而被流放到地獄;羅馬人贊同殺死虛弱的嬰兒的習慣,還把殘疾人當作一種娛樂工具,他們讓侏儒和女奴隸進行格斗表演;中世紀時期,殘疾的身體常被當作為撒旦工作的證據,尤其是不健康的嬰兒,還被認為是被仙女偷換后留下的又丑又笨的孩子。
桑塔格還特別關注與疾病有關的其他形式的“他者化”過程,她指出:“在對疾病的想象與對異邦的想象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它或許就隱藏在有關邪惡的概念中,即不合時宜地把邪惡與非我、異族等同起來。被判定為邪惡的人總是被視為或至少可能被視為污染源。”作為“他者”的異族、異邦、異域(通常是原始地區)或敵人,往往被想象為疾病的傳染源。這種想象成為建構“他者”的手段,成為各種形式的排外、歧視和敵對宣傳的工具。
“他者”的存在,是一種文化與社會不和諧、不公正的體現,而基于疾病、殘疾等身體形式的“他者”建構尤其顯得詭秘。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乙肝歧視”、“艾滋歧視”和“SARS恐慌”以及對殘疾人的各種偏見仍然存在。把某些病人和殘疾人建構為“他者”,反映出某種文化在克服死亡恐懼和身體焦慮時的無力與自私,反映出這種文化對死亡的陰郁與悲觀態度。
[參考文獻]
[1]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程魏,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3]吳憲忠,朱鋒穎.隱喻理論多維思考[J].北方論叢,2006(3):56257.
[4]安德魯·本尼特,尼古拉·羅伊爾.關鍵詞: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M].汪正龍,李永新,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76.
[5]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M].程魏,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9.
[6]阿雷恩·鮑爾德溫,等.文化研究導論[M].陶東風,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75.
[7]安吉拉·默克羅比.后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M].田曉菲,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8]丹尼·卡瓦拉羅.文化理論關鍵詞[M].張衛東,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9]萊恩·伯頓.社會學與殘障[M]//丹尼·卡瓦拉羅.文化理論關鍵詞.張衛東,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131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