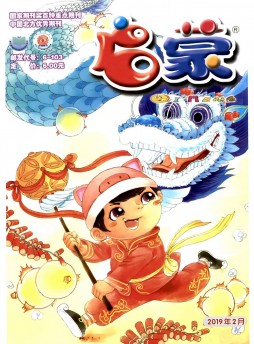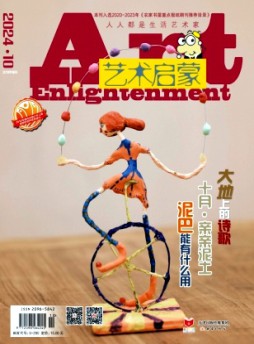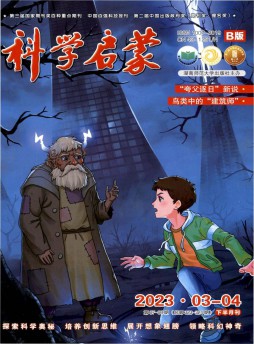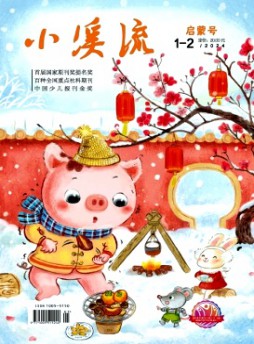啟蒙策略與文學變遷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啟蒙策略與文學變遷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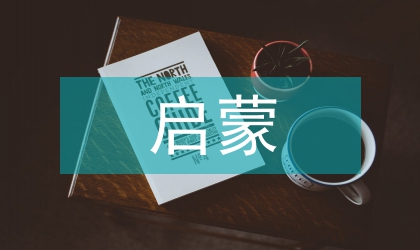
中國20世紀初期的兩份重要報刊《安徽俗話報》①和《新青年》皆由陳獨秀主創,且都以啟蒙為職志,但是不同的歷史語境卻使之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歷史風貌,并產生了不同的歷史效應。因此,由同一位文化革命先驅所創辦的這兩份雜志,可以歷史性地透視出中國現代啟蒙策略的調整以及由此給文學帶來的巨大變遷。
一、從“開啟民智”到“喚醒青年”:啟蒙策略的歷史性調整
有感于“外患日亟,瓜分立至”的亡國局勢,陳獨秀認為:“謂中國人天然無愛國性,吾終不服,特以無人提倡刺激,以私見蔽于性靈耳。若能運廣長舌,將眾人腦筋中愛國機關撥動,則雖壓制其不許愛國,恐不可得。”陳獨秀在第一期便開宗明義闡明了辦報的“兩大主義”:“第一是要把各處的事體,說給我們安徽人聽聽,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邊事體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人無錢多讀書的人,看了這俗話報,也可以長點見識。”由此,《安徽俗話報》預設了相應的讀者群體:讀書的、教書的、種田的、做手藝的、做生意的、做官的、當兵的、女人、孩子們……幾乎遍布社會的各個階層。這樣的一個讀者擬想范圍顯然大大超出了不識字或少識字的“下層民眾”,而是體現出極為廣泛的讀者訴求。與《安徽俗話報》同時的《中國白話報》,在記者與讀者的通信中曾經對同一時期相關報刊的讀者群做了一個比較性的定位:“我這報并不是一直做給那般識粗字的婦女孩子們看的,我還是做給那種比婦女孩子知識稍高的人看……所以說話不免高些。……而且那程度可以合著婦女孩童的報,如今也有好幾種了,譬如杭州白話報,寧波白話報,安徽俗話報,江西新白話,那思想淺近一點的人,都可以一看便懂。”②這也恰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安徽俗話報》的實際讀者群顯然是“庸眾型”的中下層社會民眾。作為一個歷史個案,《安徽俗話報》卻正體現出了中國20世紀初期的總體啟蒙特征——“開啟民智”作為社會變革、歷史進步的癥結性內容已經被提到了議事日程。啟蒙先驅梁啟超對這一時期的歷史性課題也有過闡述:“夫群治之進,非一人所能為也,相摩而遷善,相引而彌長,得一二之特識者,不如得千百萬億之常識者,其力愈大而效愈彰也。”③所以自清末以來的各類白話報,盡管在讀者設定上略有差異,或宣稱以蒙童婦孺為主;或聲稱要開通下層社會,為中下等人說法;或者干脆以開通婦女界為指歸,但從整體上卻構織了一種以“普及常識”為基本啟蒙策略的歷史景觀,而“啟牖民智”與“白話報”的歷史血緣關系也由此生成:“前者著眼于中下層社會,更煥發全體民力,是目的;后者用其方便,重其效果,是方法。”④對于《安徽俗話報》而言,除了這一共有的總體歷史責任承擔之外,還體現出創辦者自身獨特的啟蒙導向。陳獨秀一再申明:“這報的主義是要用頂淺俗的說話告訴我們安徽人,教大家好通達學問明白時事。”但是,綜觀全部《安徽俗話報》,“瓜分危機”才是記者積潴胸中不吐不快的塊壘,而諸如“日俄戰爭”、“洋人開礦筑路”等時局也自然成為報刊重點關注的“要緊的新聞”。被瓜分的亡國危機是一個時時被提及,一次次被強化的啟蒙關鍵詞,因此,盡管《安徽俗話報》宣傳旨在使當地人“通達學問明白時事”,實際屬于單純的“知識啟蒙”的范圍非常小,而且就這些地理、歷史、天文、衛生、兵事、實業等知識而言,也往往是作為“亡國危機”和“愛國救亡”的延伸性話題出現的,因此,向民眾宣傳亡國與救亡的道理才是其啟蒙的實質性內容。
從《安徽俗話報》到《新青年》,一個最為顯著的變化是啟蒙策略的調整:啟蒙對象由下層民眾移向了“敏于奮斗、勇于自覺”的青年知識分子。《青年雜志》自2卷1號起,改名為《新青年》,雖是一字之差,卻歷史性地突顯了這一雜志的精神新質——“青年”成為啟蒙的關鍵詞。陳獨秀在“社告”中宣稱:“國勢陵夷,道學衰弊,后來責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啟蒙者這一矚目于青年的啟蒙理念根源于以歷史進化論為依托的社會有機體理論。“青年”被認定為中國社會肌體健康發展,免于淘汰的新鮮細胞。因此,“喚醒青年”,培養先覺的精神界戰士,成為此一時期啟蒙者的共識。這一具有歷史預見性的啟蒙策略事后也得到了很多先驅者的認同。基于對“個性”與“自我”的推崇,魯迅就曾多次表述過對于“少數”的期待:“與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眾人而希英哲?”⑤雖然在為《新青年》“吶喊”之前,魯迅也向“金心異”(錢玄同)表達了自己對于“鐵屋子”的憂慮和猶豫,但最終還是認同了“喚醒少數,毀掉這鐵屋子”的希望。直到1925年魯迅還堅持這一啟蒙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而且還是準備‘思想革命’的戰士,和目下的社會無關。待到戰士養成了,于是再決勝負。”⑥1939年,在評價“”時也對這一啟蒙策略給予了肯定:“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由《安徽俗話報》時期面對廣大民眾的“運廣長舌,開啟民智”,到《新青年》時代矚目于少數青年的思想覺悟,表明中國近代以來的啟蒙運動已經被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境界。
從《安徽俗話報》到《新青年》所展示出的啟蒙策略的歷史性調整,其根本動因源于中國自身的歷史境遇和知識分子的不斷覺悟。作為這一歷史轉捩點的關鍵性人物——陳獨秀,正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分辨出了自己的歷史角色期待”。辛亥革命的挫敗使陳獨秀進入更深刻的歷史性反思,并對中國思想界自明中葉以來受西方文化沖擊所產生的“七次覺悟”有了更深刻的歷史洞見,按照陳獨秀的這一分析,《安徽俗話報》的出現大致處于覺悟的“第四期”:“清之末際,甲午之役,軍破國削,舉國上中社會,大夢初覺。稍有知識者,多承認富強之策,雖圣人所不廢。康梁諸人,乘時進以變法之說,聳動國人,守舊黨泥之,遂有戊戌之變。沉夢復酣,暗云滿布,守舊之見,趨于極端,遂成庚子之役。雖國幾不國,而舊勢力頓失憑依,新思想漸拓領土。”以“”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所激發的歷史性覺悟,促成了清末以來以開啟民智為核心的啟蒙浪潮,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可以說是這一啟蒙浪潮的思想光源。而由《安徽俗話報》到《新青年》,中國歷史再次發生了急劇的變動,辛亥革命推翻了專制帝制并建立了共和。陳獨秀洞見出中國歷史的癥結:“三年以來,吾人于共和國體之下,倍受專制政治之痛苦……然自今以往,共和國體,果能鞏固無虞乎?立憲政治果能施行無阻乎?以予觀之,此等政治根本解決問題,猶待吾人最后之覺悟。”《新青年》的創辦正是處于保存“共和”還是復活“專制”的歷史飄搖期,這將取決于新舊思潮大激戰的最終結果,《新青年》所加于自身的歷史責任正是力圖促成這第七期覺悟,使“共和”這一現代制度得到真正實現,而問題解決的根本癥結則在于國人的最后覺悟——倫理的覺悟:“倫理思想影響于政治,各國皆然,吾華猶甚”,“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⑦。所以在陳獨秀看來,復辟帝制,毀棄共和僅僅是“惡果”而非“惡因”,主張別尊卑、重階級、壓抑民權的綱常禮教才是制造專制的根本原因。因此,由《新青年》所發動的思想啟蒙,其最終關懷雖指向根本的政治制度,但卻落實于倫理思想的層面,而能充當思想變革先鋒的,只能是具備新思想的“新青年”。因此,塑造“新青年”、“倡揚新思想”成為此一歷史時期的啟蒙主題。而正是由這一代倡導新文化運動的青年知識分子們,共同開創了一整套的現代思想文化價值體系。從《安徽俗話報》到《新青年》,“啟蒙”的對象由普遍意義上的廣大民眾轉向了少數精英知識分子,看似是一種思想的退守,而實質上卻實現了重大的歷史性躍遷,正是這次啟蒙策略的調整也終于造成了文學的革命性變遷。
二、從“舊調譜新詞”到“文學革命”
啟蒙運動與文學新思潮相濡相嬗、相互促動的關系自近代以來已經形成了一種特定的歷史景觀,但是這種籠統的共識卻遮蓋了不同歷史時段的啟蒙給文學帶來的變化。身兼革命家與啟蒙者雙重身份的“第一代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實際上始終擔負著救亡與啟蒙的雙重歷史重任,因此,他們始終是把政治革命、思想覺悟、文學變革等多重內容作為整體救亡的一項綜合性工程來對待的,這也賦予了“啟蒙”一種復雜而包容性的歷史品格。雖然在不同歷史時段基于迫切的時代需求會凸顯不同的維度,但是“文學”始終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以《安徽俗話報》和《新青年》為標志物的不同啟蒙階段中,“文學”始終占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同的啟蒙方略卻使文學從形質上到價值設定上產生了巨大的差異,而正是啟蒙策略的歷史性調整才使文學在《新青年》時代獲得了革命的動力,獨享了歷史創生點的輝煌。
1.“開啟民智”對舊有文學資源的倚重
清末以白話報為手段、以開啟民智為核心內容的啟蒙浪潮,雖然也倚重“文學”對于啟蒙的便利功效,但是面對見識短淺的中下層民眾,必然調動能被民眾理解、接受的舊有文學資源。《安徽俗話報》在“章程”中把第八門設置為小說,其定位是:“說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漢,大家請看,包管比水滸、紅樓、西廂、封神、七俠五義、再生緣、天雨花還要有趣哩。”第九門設置為詩詞:“找些有趣的詩歌詞曲大家看得高興起來,拿起琵琶弦子唱唱,倒比十杯酒、麻城歌、鮮花調、梳妝臺好聽多了。”這其中透露出兩個重要信息,一是《安徽俗話報》中所設計的文學性內容并沒有區別于舊有的小說戲曲與民間小調,甚至有意與之接軌;二是以“有趣”相標榜,以贏得讀者。標榜“娛樂和消閑”是白話報招徠讀者的必然選擇。要想切實收到啟蒙效果,關鍵是要有人看,而要想使普通民眾看得懂,就要使內容有趣,能夠和底層民眾的審美經驗相契合,取代他們既有的娛樂形式,諸如手中的鴉片煙,廟里的說書等等,但是又不能陳義過高,曲高和寡,白話報中的小說和詩詞等文學類內容的設置正是力圖起到這樣一個替代性作用。
出現于《安徽俗話報》中的“文學”,共有兩大類:第一類是小說和戲曲。小說從形式到內容的一個共同特征是以白話章回體的通俗樣式服務于當下鮮明的啟蒙主旨——曉諭被瓜分的民族危機、激勵愛國意識,所以其中大多數作品都是以當時的日俄戰爭作為主要內容,連小說中人物的名字都具有鮮明的政治隱喻色彩,如閔自強、朱先覺、張國威、揚國光、夏振武、華勃興、寧立群、李自立、張閫權(女)、張無謂(女)等等。作者更是毫不掩飾地借這些符號式的人物大講愛國救亡的大政方針,在這一點上,《安徽俗話報》與稍前時期梁啟超所倡導的“政治小說”從功能上毫無二致,文學幾乎完全成了宣講政治觀念、批判時事的工具,小說的趣味性可想而知。而戲曲也是以皮黃戲為主的傳統舊戲。與稍后《新青年》同仁對中國傳統皮黃戲的徹底掊擊截然相反,《安徽俗話報》時期的陳獨秀竭力為傳統戲曲辯護:“現在的西皮二黃,通用當時的官話,人人能懂,便容易感人;你要說他俚俗,正因他俚俗,人家才能夠懂哩!”其實這番話并非表明陳獨秀真心欣賞這些傳統戲,不過是作為啟蒙者看到了戲曲對民眾的巨大感染力。與此一歷史時期的啟蒙對象和啟蒙內容相對應,戲曲內容也多是以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古代民族英雄的事跡來激勵民眾的愛國心。《安徽俗話報》中的第二類文學——“詩詞”,更是一種“舊調譜新詞”的民間俚俗樣式。以“民間歌謠”為啟蒙工具并不是陳獨秀的首創,在梁啟超創辦的《新小說》中就設有“雜歌謠”一欄,本著“棄史籍而采近事”的創作方針,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創作了“新樂府”、“歌”、“行”、“粵謳”等多種形式的歌謠,借以宣揚啟蒙思想,但是強烈的文人旨趣畢竟與原生態的民間歌謠相去頗遠。《安徽俗話報》雖然以頗具文人色彩的“詩詞”命名,但卻與文人的創作大相徑庭,基本是流行于當下民間的原生態的俚曲俗調,諸如五更調、十二月曲、十送郎君、十杯酒、梳妝臺等,只不過都置換上了啟蒙性的內容,卻保留了原有的說唱形式,因此更接近民間藝人的時事說唱。可見,在開啟民智的啟蒙階段,民間通俗文學樣式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最有效、最便捷的啟蒙工具。綜觀《安徽俗話報》中的“文學”,全部都是以舊有的文學樣式導人時代性救亡內容,啟蒙者正是要借助這種民間傳唱的通俗樣式與普通民眾相溝通,以達到啟蒙的最大效果。但是面向民眾的啟蒙對于舊有文學樣式的倚重,必然使文學自身受到禁錮,甚至使文學深陷于“準文學”的泥淖,無法獲得革命性變革的契機和動力。
2.“思想革命”時代文學與民眾的疏離
從《安徽俗話報》到《新青年》,由時代所促成的啟蒙理念的調整和啟蒙策略的變遷促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出現和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覺醒,并由這一代知識分子建構起了一整套思想、政治、文化的現代圖式,尤其催生了“文學革命”的發生,可以說“思想革命”構成了“文學革命”的內在動力,而“文學革命”又成為“思想革命”的同一表述方式。因此,從《安徽俗話報》時期專注于民眾啟蒙而采用的趨俗、悅俗的文學方式,到五四思想啟蒙時期一變而為知識分子專意于營造個性化的藝術世界,致使“革命”后的新文學在與五四“思想共同體”達成高度精神和諧的同時卻疏離了普通民眾。
在《新青年》創辦者的最初構思中,“文學”并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革命性”的話題出現的,盡管陳獨秀也提及西方文學潮流和作家,但所談都非文學自身,而是意在抽繹文學背后所隱含的思想性內涵,尤其是文學在“科學”的光照下所發生的精神巨變:“十九世紀之末,科學大興,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謂赤裸時代,所謂揭開假面時代,喧傳歐土,自古相傳之舊道德、舊思想、舊制度,一切破壞。文學藝術亦順此潮流由理想主義再變而為寫實主義,更進而為自然主義。”可見,與“科學”相伴生的“寫實主義”才是被強調的重點。在啟蒙者眼中,“寫實主義”主要不是被作為一個文學流派或創作方法來對待的,更是一種人生觀和世界觀,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表征。在《歐洲文藝史譚》中,陳獨秀一再稱道的現代三大文豪:左拉、易卜生、托爾斯泰,都是以“誠實描寫世事人情”見稱的自然主義大師。但是陳獨秀所關注的并不是這些大文豪的文學藝術,而是其思想的力量:“西洋所謂大文豪,所謂代表作家,非獨以其文章卓越時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這一切都表明,陳獨秀此時所談及的文學,皆別有懷抱,文學不過是被拿來作為現代科學思想的有利佐證,“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乃與自然科學、實證哲學同時進步,此乃人類思想由虛入實之一貫精神也”。五四“文學革命”顯然是內生于“思想革命”的一個重要維度,因此,革命后的“新文學”在與“思想者”達成精神共振的同時也與普通民眾產生了巨大的疏離。盡管五四新文學是以“引車賣漿”之流所使用的“白話”取代了傳統士大夫認為“古今之至美”的文言,但是新文學并未就此彌合與販夫走卒之間的鴻溝。“白話文”實際是把五四新文化倡導者們導入了一個啟蒙的思想共同體,這個思想共同體既疏離了口語白話的實際運用者,更拋棄了抱著古文字殘骸的傳統士大夫。作為啟蒙思想共同體的一種表述方式,以白話創造的新文學顯然也與底層社會的審美經驗難以搭界。
文學與普通民眾的心理距離實際很難找到一個具體的量度,只能做一種證據式推定。《青年雜志》1卷5號“國內大事記”欄目中曾經刊載了“教育部協辦注音字母傳習所”一事,公布了一項統計結果:“國之強弱文野,以教育之能否普及為衡,即以全國識字人民多寡為標準。據各國統計,以德居首,英法美日次之,大都逾百分之九十。我國則千人中僅得七人而已。”由此可以推斷,以千分之七的識字人口,能于文學上有所造詣,再更進一步能夠棄舊圖新,勇于提倡新文學的“新青年”,顯然都是社會中居于思想金字塔頂端的“精英分子”。以《狂人日記》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所體現出來的先鋒性、探索性和思想沖擊力,只能激動這一部分青年人的心,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則成為“存在著的無”。新文學與普通民眾的疏離更可以通過啟蒙對于舊戲的排抵乃至廢棄作為另一有力反證。在所有文學門類中,戲曲之于民眾的關系最為直接,也最為密切,因此,從啟蒙先驅梁啟超到《安徽俗話報》時期的陳獨秀都不曾小覷戲曲的作用,并以之作為“開啟民智”的有效方式。而在五四啟蒙時期,中國舊戲(主要是影響最大的“皮黃”)則遭到了徹底否定,而且這些新文學倡導者們都一再申明自己對這種大眾通俗化的娛樂方式既沒有興趣,也沒有精深的研究。最早主張舊戲改良的劉半農在提出改良方案后立即聲明:“然余亦決非認皮黃為正當的文學藝術之人,余居上海六年,除不免之應酬外,未嘗一人皮黃戲館。”而另一批判舊戲的新文化人傅斯年也表明:“我對于社會上所謂舊戲、新戲,都是門外漢。”由這些“門外漢”而倡導中國戲曲改革,當然只有否定一維。傅斯年認為“中國舊戲實在毫無美學價值”;錢玄同更是不容分說,直指舊戲為“野蠻”;就連曾經對于舊戲的啟蒙效用極端看好的陳獨秀也一改從前的言論,一方面自然表明了陳獨秀文學觀念的轉變,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作為知識分子和“新青年們”的啟蒙導師,本能地要遠離這種淺俗的大眾文化娛樂形式。
可見,新文學倡導者是不屑與這些大眾化的俗文學相溝通的,自然對于舊戲也毫無改良的誠意,只是一味要推翻。新文學家們這種不容辯解的批判,顯然是急于要為西方話劇的泊入清理場地,因此,幾乎所有新文學倡導者都眾口一詞,建設的途徑“只有興行歐洲式的新戲一法”,但是這一西方現代話劇究竟屬于民眾還是屬于這些倡導新文學的知識分子呢?演出便是最好的試金石。“上海新舞臺開演《華倫夫人之職業》,狹義的說來,是純粹的寫實派的西洋劇本第一次和中國社會接觸;廣義的說來,竟是新文化底戲劇一部分與中國社會底第一次的接觸”,而接觸的結果則是一個大大的失敗。演出失敗的結局方使新劇家們重新認識到“娛樂性”——這一被指認為通俗文學的“墮落性”標志——應該在“新文學”領域重新得到認識。這一失敗的嘗試也顯示,被新文學倡導者們所鐘情的“新文學”實際上與民眾是頗為隔膜的。由此也可以反證,五四啟蒙所催生的文學革命,以及由此創生的新文學,實際上是純粹運行于知識階層的一場運動。
自近代以來由“開啟民智”的啟蒙運動所聚攏起來的“文學”與“民眾”的親密關系在“五四新文學革命”后再度分裂:新文學為新知識分子所擁有,而舊戲、通俗文學仍舊在最廣大的民眾階層占據著市場。新劇家余上沅后來也不得不承認:“近十年來舊劇盡管受著不斷的打擊,但毫無影響,雖則寫實主義,也會光顧到我們程式化的劇場,無何,舊劇仍是屹立不動,縱使西方的戲劇,要想和我們苦戰,也休想成功的。”新劇家頗為深切地意識到:“一個國體的變換,固然容易,但藝術的興趣是逐漸養成的。”啟蒙者對于“舊戲”的廢棄,同時對于西方話劇的引進,實際上使“戲劇”這一原先與普通民眾緊密相連的藝術樣式純化、升格為現代知識分子所認同的新文學門類,同時也使之與民眾嚴重疏離,這不僅僅是“戲劇”,也是五四新文學的共同情狀。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五四啟蒙和五四新文學的歷史性價值,若以“脫離民眾”的陳詞濫調來判定五四啟蒙的失敗,更是對于歷史的嚴重誤解。
“啟蒙”的長遠目標和最終指向顯然是最廣大民眾的普遍覺醒,但是從邏輯上講,“啟蒙”卻首先應該在知識階層展開,由他們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價值體系,而后才能使啟蒙的光芒逐漸照耀到整個社會。五四新文學與民眾的疏離狀態正是啟蒙思想共同體的凝聚期和現代價值的建構期,這也正是五四啟蒙的巨大歷史價值之所在。新文學與大眾之間的距離是一個長時期的歷史調試過程,此后一浪接一浪的“文學大眾化運動”正是二者不斷尋求最佳契合點的努力。
注釋:
①《安徽俗話報》1904年3月在安徽蕪湖出版,半月刊,每期40頁。至1905年8月停刊,共發行了22期。
②林獬:《通信》,《中國白話報》第11期,1904年5月15日。
③梁啟超:《新民說·論進步》,《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版,第58頁。
④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62頁。
⑤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頁。
⑥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頁。
⑦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1916年第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