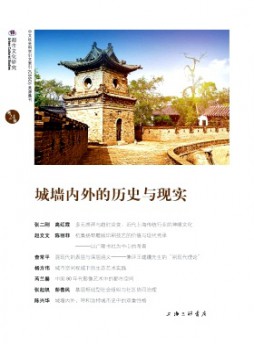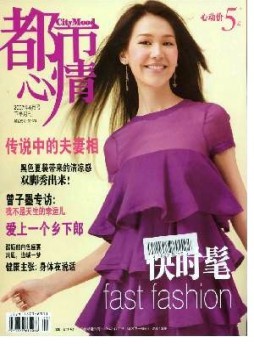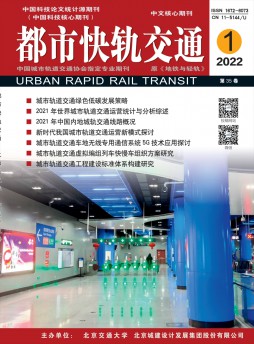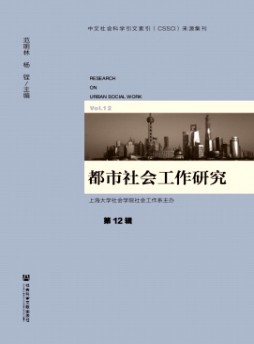都市文學在人文精神重建中的意義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都市文學在人文精神重建中的意義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以張欣為代表的嶺南都市作家以嶺南都市為背景,描寫了嶺南商業都市中蕓蕓眾生的生存狀態。作品中展現出來的價值選擇、人際溫暖以及人文情懷對現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塑造有著積極意義。
所謂人文精神,即以人為本,既肯定人的價值追求的自由選擇,也涵蓋真正、自覺的“仁、善”理性意識,是世俗現實與理想信念、外在物質與內在精神、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的有機統一在人的行為中的體現。以張欣為代表的嶺南都市作家,以嶺南都市為寫作背景,不僅揭示出轉型時期都市人性的缺失與變異,更顯現出都市中人性的堅守與承擔、心靈的美麗與善良。他們處于人生困境,卻努力生存;他們務實,又敢于擔當;他們功利,又相互關心,極具人情味。在他們身上,映射著作者對都市人的人生價值的思考,對美好人性的弘揚,其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一、價值選擇中人文精神的體現
人文精神的體現,既尊重人的多元化選擇,也注重人的內在修養、道德責任,二者相互結合,相輔相成。在生活中,體現出來的是人的價值選擇向度,是為滿足俗世物質需求與精神意義的結合而體現的效果。廣東的廣州、深圳等城市率先實行對外開放,市場經濟的理念在人們的思想中逐漸占了主導地位。現代商業語境允許人的務實、肯定人對現實利益的把握,激勵人對自我的解放,刺激著人實現自我價值,但也成為人類精神困境的根源。傳統文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文價值逐漸被消解,人的價值選擇出現錯位,個人凌駕于集體,索取超越了奉獻,本能替代了人格,利益取代了理想[1]109-121。長此以往,人的追求向形而下欲望傾斜,價值關系出現失衡,最終陷入精神的困境。《深喉》中的沈孤鴻,表現出的即是人性變化的過程。湯因比認為:“人類因為其本性中具有精神性的一面,所以他們知道自己被賦予了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尊嚴性,并感覺到必須維護它。”[1]126久任副職的沈孤鴻,確實具有著“人”的自覺意識,他明白官場之姿態,也能妥善處理物我的關系,自覺抵制誘惑,保持了自我的獨立與清廉。然而隨著權力的上升,他便工作中一意孤行,生活中與人攀比。功利的誘惑,讓沈孤鴻價值的選擇開始出現錯位,一步步被權利與欲望奴役,尊嚴喪失,人之“非人”,“求生”之路被自己隔斷。市場經濟的主導、現代商品觀念的影響、社會風氣的浸染,慢慢在日常生活中成為個人價值選擇的風向標。
在各種不良理念的充斥下,蕓蕓眾生,幾乎都變成了一個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凡事都講利益,有用則做、無用則舍,最終因“缺乏支撐起意義和存在感的價值觀”而成為“空心病”患者[2],陷入精神虛無狀態。張欣的作品,承認人的價值選擇的多樣性,尊重人世俗的生活理念,肯定人正當功利的思想狀態;但反對享受超越奉獻的功利,批判異化人性的物質欲望,否定凌駕于群體之上的個人主義。她以不同的主人公的人生際遇向讀者揭示:在當下社會,唯有把世俗價值與人文終極關懷相結合,把現實利益追求與內在精神相統一,人才能真正感覺充實。過度追求形而下的欲望是人文精神缺失的體現。陸彌(《為愛結婚》)、梅金(《不在梅邊在柳邊》)等都是因此而陷入精神困境的代表人物。在《為愛結婚》中,陸彌是一個孜孜追求家庭關懷的女性,然而家庭環境與社會功利背景的交互影響,注定了她人生的悲劇。在家里,父母重男輕女,陸彌處于邊緣地帶,哥哥陸征是她唯一的溫暖來源。然而,陸征生病,讓陸彌再次看清家庭背后的冷漠與自私:為了金錢,父母、嫂嫂威逼自己舍棄現有的愛情。陸征吞藥自殺,陸彌便徹底成為“孤兒”。這時,陸彌的人性開始扭曲—金錢被異化為她的人生目的。為了金錢,她放棄原則,甘當狗仔隊;為了金錢,她丟掉尊嚴,用自己的痛苦作秀,以換取同情;為了金錢,她泯滅人格,以無恥的行為獲取并出賣別人的隱私。金錢的奴役,內心的扭曲,讓陸彌一步一步走向人性的深淵,親情成為夢魘、婚姻成為墳墓、愛情變為心魔,害人害己。作者通過敘述,揭示出深層的內涵:人性是否健康,與傳統、與現實、與個人價值的選擇有著密切的關系。陸彌的悲劇,在于父母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在于社會金錢至上的主張與人性的冷漠,更在于她自己內心無法消解的價值追求。簡單地說,就是人性與社會大背景相互交錯的結果。與陸彌有著相似遭遇的梅金(《不在梅邊在柳邊》),雖同樣因為兒時的遭遇,才產生了金錢、權利至上的價值選擇,但根本原因,是她在金錢、權力面前不能守住自己,為追求金錢而把自己當成商品,才導致了她人文精神的失衡、人性的缺失,最后落得人財兩空的結局。
作品中,作者對陸彌、梅金等人的選擇給予了寬容,對她們的人生遭遇給予了同情,對她們價值選擇的錯位則給予了批判。對于錢、欲,她曾尖銳地指出:“錢這個東西或許沒有缺點,但是一旦擁有,人生的秩序會戲劇化的重新排列,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有時候便成為悲劇的根源。所以對它始終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3]在人的成長過程中,金錢、物質雖可暫時滿足人的存在感,但若沒有理想信念,不能堅守自我底線,久而久之,人就會在物質或欲望中迷失自我、陷入困境。因此,張欣認為:“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隱秘的天平,如果一邊是欲望、名利、金錢或者苦難,另一邊便是靈魂、良知、自省、堅持或者感動。”[3]人性的發展,需要金錢等外在的生活內容,也要保持內心價值的道德選擇。只有二者緊密結合,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目標才有可能實現。《終極底牌》中的江渭瀾,即是金錢、苦難與靈魂、責任相結合的人物。音樂世家的出身,讓他有了浪漫、超越現實利益的情懷;軍人的經歷又讓他積淀了底蘊,保持了人性中的情義與責任。他的價值選擇顯示出與現代功利社會不符的悲憫氣質:對待金錢,他不高尚,甚至承認“家庭關系就是金錢關系,沒什么道理可講”[4],但他又坦然、理性,不會產生過多欲望;對待家庭,他勇于承擔;對待員工,他以身作則,也不拖欠工資;對待客戶,他給予寬容,處處充滿人情味;對待苦難,他掙扎,但踏實堅定,具有堅強的意志。江渭瀾的人文精神,使他面臨理想與現實沖突時,不以世俗物質為恥,比如苦難當頭,為了生存,他不得不耍點小聰明,冒用別家公司名字;卻也在浮躁現實中獲得了少有的安詳,與人為善,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務態度,不搞砸別人的牌子。作者通過江渭瀾告訴讀者,人文精神不是鏡花水月,它與現實緊密相連;也不是利益第一,而是隱含著靈魂的救贖與良知的傳達。穆時英曾經說過,文學的終極意義在于為生存的斗爭,而這個生存的斗爭,不僅意味著活著,更意味著一種“正確的生活”[5]。張欣等嶺南都市作家的作品,或從負面展示人生際遇、或從正面體現人生價值實踐,向讀者展示了人生應行走的方向和道路,雖非研究者公認的經典,但其中對現實的描繪、對人生價值的拷問、以及蘊含的文化關懷和人文價值更接地氣,可以影響讀者形成正確、理性價值觀,有助于引導讀者不斷地抵御外來誘惑,堅守自我。這正是完成文學終極社會意義的所在。
二、人際溫暖中深化人文精神
嶺南地區,原本就有務實的特質,而經濟浪潮的推動,更強化了人們的“實用”意識,即個人化、實用化、利益化勃興。實用主義的驅使,使社會形成“他人即地獄”的模式,自私、冷漠、精神麻木現象成了常態,都市中的人逐漸陷入精神的迷茫。“當我們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焦慮和迷惘時,便習慣性地埋怨物質世界的冰冷……即便是回到過去,同樣會有其他的問題存在,這便是因為人的心靈是非常脆弱和焦渴的,也非常容易貧瘠和荒蕪,這便是人始終都在尋找精神家園的原因之一。”[6]“文學中總有一些東西幫你宣泄掉了另一些東西,譬如說苦悶、困窘、無助和悲涼,同時它還能灑下甘露,滋潤心田。”[7]藝術的目的,不僅在于重現現實之殘酷、精神之迷茫、人生之困境,更在于探索人文精神,尋找救贖之出路。而人文精神除了以人為本、尊重人的價值選擇外,還有“善”的內涵。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就是真、善的統一,就是由真、善而達到美的效果。儒家講究“仁者愛人”,道家推崇“上善若水”,現當代社會,人文精神更是體現為友善、和諧。張欣是寫人性之善的作家之一,其作品雖反映出經濟社會的無情,卻又于無情商業關系中注入了人性之情,傳達出人文精神中善的因子。她的作品最能令人感動的不是親人之間的溫馨畫面,也不是朋友之間的深厚情義,而是普通人甚至陌生人之間的那點溫情微光。一點微弱之光,卻能帶給人極大的溫暖。作者借江渭瀾之口告訴世人:“人這一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心安置好了。”[8]唯有心安,人才會踏實。為追求心安,他放棄音樂夢、青梅竹馬、家人,承擔起戰友王覺的責任,只為那一句承諾;為追求心安,要不到政府工程款,他便賣掉房子給工人發工資和還建材商貨款;為追求心安,開發商跳樓,他則認為人死賬死,要給孤兒寡母留下一條后路;為追求心安,他明知做一個好人沒有什么用處,但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去做一個寬容、無私、勇于承擔的好人,并且教育下一輩也要做一個好人。
在利己主義橫行的社會,“獨善其身”、“兼濟天下”,好似一種遙遠的記憶,而人文精神的失落卻比比皆是。江渭瀾追求的心安,行為中表現為寬容與淡然,不僅僅體現出善之美好,更暗含了人文精神“以人文本”的核心本質,即尊重人生存的權利,包容他人選擇的自由。也正因為追求“心安”,才更因陌生人的一絲相助,便在冷漠的都市中開出朵朵溫情之花。正因如此,作為同事,槐凝總是在呼延鵬最無助的時候給予支持和幫助(《深喉》);作為鄰居,小美媽盡管世俗,但在緊要關頭卻成為如一的精神依賴(《對面是何人》);也因如此,本不相識的管凈竹和焦陽雖承受都市人的壓力,忍受著內心焦慮和痛苦,但內心的那份善良卻讓他們在物欲的社會中相互取暖,守護著彼此內心最為柔弱的部分(《依然是你》);富二代劉嘻哈,更是為無辜的何四季四處奔走(《用一生去忘記》)。“他們之間擦出的火花,是真正的人性關懷。是小人物安放靈魂的憩息方式。是我們心靈中最軟弱的那個部分所期待的撫慰。更是冷雨飄零、舉目無親時出現的那把舊雨傘。”[7]不管是傳統還是現代,金錢、利益一旦成為關系紐帶,總會使人陷入精神的虛妄之中,而江渭瀾的包容、張豆崩的善良(《終極底牌》)、呼延鵬的正義(《深喉》)、李希特的追求(《對面是何人》)、槐凝的支持、曹虹的不離不棄(《依然是你》)則給冰冷的都市注入了一劑脈脈溫情,成為都市“欲海里的詩情守望”[9]。文學的功用在于思想的引導,張欣小說中人文精神“善”的體現,不僅為讀者提供了一條宣泄內心苦悶的途徑,更是社會轉型時期的一股清流,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浸入讀者的內心,從而帶動讀者向著振興人文精神邁進。以此而言,嶺南都市文學中展現出來的人性之善,在現代社會人文精神重塑中也可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小結
都市化依然發展,都市人的觀念在不斷地變化與調整,無論是在都市中沉淪還是在都市中升華,其結果均來自于人內心價值的形成與影響。尤其是處于學習時期的青年學生,他們處于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現代高效卻浮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他人即地獄”的社會環境、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無疑可能成為他們現在或者未來精神的桎梏。鐘曉毅對張欣如此評價:“人的心靈中也有一盞燈,點亮它,人的心靈空間就極為廣闊,人生的意義、價值和目標就會明朗,人就會走向高尚和美好;熄滅它,人則會在難以自拔的狹隘中,在陰晦不明的黑暗中迷失。……在某種意義上說,張欣可作這樣的‘點燈人’。”[10]張欣如此,嶺南其他作家亦是如此。他們“站在‘人’的立場上,弘揚‘人’的精神,確立‘人’的價值。”[9]作品中批判或宣揚的生存理念、對傳統人生價值觀的繼承、嶺南文化中的包容性和融合力,不僅可以讓為生存而奔波的勞心勞力者看到生存的希望;更可以讓校園中的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多一份人文關懷、少一分利益之爭,在繼承和創新的融合中不斷成長、成熟,最終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就此意義而言,嶺南都市文學雖非經典,但其對“人”的價值的確立、對人的精神家園的尋覓,對現代社會人文精神的重塑,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李建華.趨善避惡論———道德價值的逆向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徐凱文.功利的教育、焦慮的家長、空心的孩子三敗俱傷,我們還要繼續愚蠢下去嗎?[EB/OL].
[3]張欣.對面是何人:代序[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1.
[4]張欣.終極底牌[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3:89.
[5]穆時英.關于自己的話[M]//嚴家炎,李今.穆時英全集:第3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5.
[6]張欣.依然是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7]張欣.上善若水[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108.
[8]張欣.終極底牌[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3:92.
[9]程文超.欲海里的詩情守望———我讀張欣的都市故事[J].文學評論,1996(3):71-75.
[10]鐘曉毅.在紅塵中安妥靈魂———素描張欣[J].北京文學,2015(8):67-69.
作者:李景云 單位:廣東金融學院
- 上一篇:圖書館期刊文獻的管理探討范文
- 下一篇:民營企業文化發展現狀及對策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