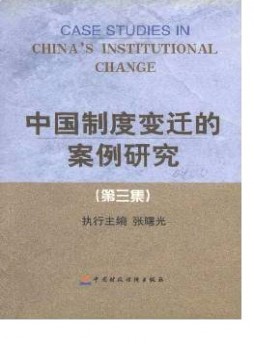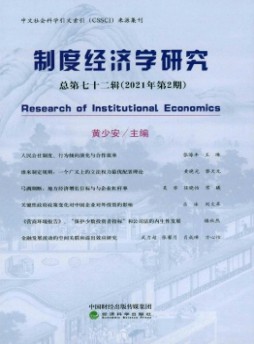典權(quán)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典權(quán)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縱觀世界各國,并沒有與之吻合的規(guī)定,可以說典權(quán)是中國傳統(tǒng)物權(quán)交易的典范。隨著債與擔保方式的發(fā)展,國外也出現(xiàn)了類似的制度。如法、日的不動產(chǎn)質(zhì)權(quán),德國的擔保用益,都與典權(quán)有相似之處。但是,結(jié)合西方經(jīng)濟發(fā)展背景和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分析,兩者是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不動產(chǎn)質(zhì)和用益擔保實質(zhì)都屬于擔保物權(quán),其著眼點是“物”的對“債”的擔保功能,其核心是債的實現(xiàn),側(cè)重的是對債權(quán)人的保護。而典則不然,典權(quán)著眼于“物之利用”以及對“出典人的保護”。保護的根基在于中國幾千年來“重孝”之文化傳統(tǒng)。雖然,現(xiàn)在很多學者對“典”的性質(zhì)有過激烈的爭論,并試圖在“擔保物權(quán)”和“用益物權(quán)”之間給典權(quán)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但是,筆者認為,典權(quán)是現(xiàn)代我國民法中為數(shù)不多的、完全未受外國法律影響而獨立存在的一項中國固有的法律制度,在物權(quán)特點上有著自己的特殊性。而想要在西方立法體制下,給典權(quán)給予完美的地位,肯定是不可能的。
為何否定典權(quán)的中國文化特色。其實,總結(jié)典權(quán)廢除論的各種觀點,最大的焦點就是典權(quán)存在的文化基礎與現(xiàn)實意義,或者說是社會功能上。“一是保留傳統(tǒng)文化特質(zhì)的固有法情節(jié);二是設立典權(quán)供公民選擇適用,即“典權(quán)備用論”。但是,典權(quán)作為古代物權(quán)交易中一項廣為流傳、并經(jīng)久不衰的制度,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密不可分。如果,用現(xiàn)代人功力主義的“功能觀”來看待典權(quán),否認文化的基礎和底蘊,那么法律等一切形而上的制度便徹底淪為社會的工具。而所謂“民法”應是從群眾而生的典型“市民社會的法”,它的運作更是離不開市民社會的文化基礎。否認典權(quán),實際上就是在否認傳統(tǒng)的文化特色和習俗。
典權(quán)制度存在的中國文化遺存的必要性。法律實施過程中,大量引進的西方制度卻遭遇瓶頸。筆者不禁疑問,為什么那些在西方好用的制度移植到中國就不行了呢?其實很多學者已經(jīng)探究到原因,這正是因為很多的制度設計逐漸遠離了中國的文化基礎。我國近代物權(quán)制度也同樣如此。多數(shù)觀點都認可了典權(quán)“扶弱救貧”“重孝保業(yè)”的文化基礎,但是再從文化底蘊中探究就會發(fā)現(xiàn),典權(quán)更體現(xiàn)了儒家“均貧”“中庸”之道。在儒家思想中,生產(chǎn)的最終目的不是利益的最大化,分配比生產(chǎn)的意義更加重大,分配的均衡才是社會和諧的關(guān)鍵。從主觀上講,典權(quán)制度傳遞的這種和諧價值在現(xiàn)代社會尤其必要,這在文化遺存上也不失為一項寶貴的財富。客觀上講,如果說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使人們的觀念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典權(quán)“救弱扶貧”“保護家產(chǎn)”的傳統(tǒng)觀念受到挑戰(zhàn)。然而,由于我國幅員遼闊,經(jīng)濟發(fā)展不平衡,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必然也不會同步。典權(quán)作為傳統(tǒng)文化,根深蒂固的存在于習慣中,這種文化型觀念的改變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有學者認為,傳統(tǒng)觀念與習慣之轉(zhuǎn)變不可能整齊劃一,縱然只有少數(shù)人依循傳統(tǒng)習慣設定典權(quán),物權(quán)法上也不能沒有相應規(guī)則予以規(guī)范。
典權(quán)制度存在的現(xiàn)代文化扶持的可能性。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城市改革的深入,典權(quán)面臨的最大的挑戰(zhàn)就是其存在的地產(chǎn)現(xiàn)實發(fā)生了改變。商品房大量進入市場,私人房產(chǎn)迅速增加。在物資豐富的今天,人們的選擇也變得多樣而隨意。對物的“唯一依賴性”降低。試問“不愿失去不動產(chǎn)”的心理在現(xiàn)代還依然存在嗎?“變賣家產(chǎn)”的心理情結(jié)在現(xiàn)代文明中是否還能找到文化的扶持?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說典權(quán)在封建社會存在的文化基礎是以“重孝”“守業(yè)”而衍生出的對變賣家產(chǎn)的顧忌。那么現(xiàn)在“守業(yè)”的思想應該仍然存在,因為即便是房產(chǎn)迅猛增長,但對于不動產(chǎn)擁有者來講,仍會有一處是“情有獨鐘”。基于這樣的心理,文化上的扶持便有了支撐。首先,典權(quán)在實現(xiàn)對物最大化利用的基礎上,又兼具了融資功能。由于出典人回贖權(quán)存在著喪失的可能性,這就使該制度本身具有了一定督促性。這與其他融資方式形成的外在壓力不同,對回贖權(quán)喪失的擔心形成了一種內(nèi)在壓力,尤其是在抵押物權(quán)需變價受償,而誠信機制又欠缺的情況下,典權(quán)更能促進在融資上誠信的建設;其次,典權(quán)在最終實現(xiàn)各方利益時程序相對簡單,這在現(xiàn)代社會追求簡便、效率的對物利用上,便有了經(jīng)濟理念上的支持。
典權(quán)制度與誰來為不想失去不動產(chǎn)者提供法律幫助。從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在關(guān)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quán)法(草案)》修改情況的匯報中可以看出,立法者似乎認為在我國現(xiàn)有的制度中已經(jīng)有了對典權(quán)制度的替代。對于融資,抵押和質(zhì)押可替之;而典權(quán)保護“家產(chǎn)不敗落”的功能,也可以通過附買回條件的買賣來實現(xiàn)。但是,由于典權(quán)有其固有的內(nèi)容,這兩種制度的替代也會是不完整的。抵押雖然可以達到籌集資金的目的,但是擔保的數(shù)額只能小于不動產(chǎn)本身的價值。在實踐中,所融資的金額是遠遠小于不動產(chǎn)價值的。并且,對于抵押權(quán)人,對抵押物除了一個優(yōu)先權(quán),不享有其他任何的利益。同時,如果抵押物的價值降低,則抵押權(quán)人也要承擔借款不能受償?shù)娘L險。而這一點,在典權(quán)完全可以避免。還有一種替代方式,是附買回條件的買賣。對于不愿失去所有去的出賣人來講,如果通過協(xié)議商定附買回條件,雖然表面上可以達到目的,但實則不然。由于我國物權(quán)變動采取登記主義,并且實行物權(quán)行為區(qū)分原則。也就說,當買賣達成,雙方進行了物權(quán)登記,那么原權(quán)利人的所有權(quán)就已經(jīng)消滅了。至于合同約定了附條件買回的條款,對原所有權(quán)人來講也只能是債權(quán)意義上的保護。這樣的保護明顯弱于典權(quán)在物權(quán)意義上的保護,而對于那些不想失去不動產(chǎn)者來說更容易成為一紙空文。
現(xiàn)代社會中典當行的興起似乎使典權(quán)制度迎來了新的運作契機,這也是典權(quán)在現(xiàn)代文化中存在的有力證明。一方面,在對資源有效利用上,典權(quán)具有較大的靈活性,相比于抵押和出租,典權(quán)對使用途徑的限制更小。這便與現(xiàn)代民法文化中倡導“意思自治”“個人自由”相互輝映;另一方面,典權(quán)在融資上對借款人形成的是心理上的壓力,這與自覺還款,民法誠信建設也非常有利。總之,傳統(tǒng)的典權(quán)雖然具有濃厚的固有文化支撐,那么新環(huán)境下運作的典權(quán)也賦予新的文化內(nèi)涵,使之能夠適應新的文化土壤。(本文作者:黎婉婧單位:四川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