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戲形態(tài)及其佛教文化辨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陽戲形態(tài)及其佛教文化辨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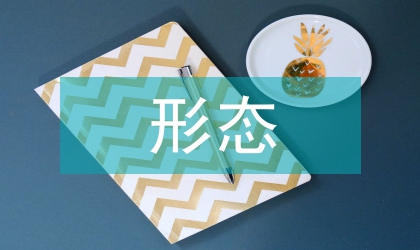
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的提出和“武陵山片區(qū)區(qū)域發(fā)展與扶貧攻堅計劃”的實施,武陵山片區(qū)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搶救、保護等工作被提上日程。而陽戲作為該地區(qū)廣泛流播的民間文化事象,它以多樣化的表演形態(tài)和濃厚的佛學思想深刻影響著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研討區(qū)域文化的本源是學界的重要研究內(nèi)容之一,所以探索陽戲與佛教文化滲透、融合的軌跡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陽戲是武陵山片區(qū)流播廣泛的民間文化形式,有儀式型陽戲、儀戲結(jié)合型陽戲和民間小戲型陽戲三種基本形態(tài),具體對應的分布區(qū)域為:黔北①、黔東北的桐梓、正安、道真。沿河陽戲表現(xiàn)為儀式戲;渝東南的武隆、彭水、酉陽、黔江陽戲?qū)儆趦x戲結(jié)合性質(zhì);秀山陽戲、鄂西的鶴峰、來鳳陽戲、湘西的張家界、永順、花垣、吉首、鳳凰、懷化陽戲,以及黔東南的天柱、錦屏、黎平陽戲為民間小戲性質(zhì)。透析武陵山片區(qū)陽戲形態(tài)的多樣化主要從它們的演出劇目、角色行當、音樂唱腔和演出時空等方面觀照。
(一)儀式性陽戲
黔北、黔東北地區(qū)巫儺之風甚盛,形成了多種形態(tài)共存的“儺戲群”[1]。在這里陽戲是儺戲的一個品種,表演形態(tài)為儀式戲。例如黔北正安縣志強村巖子頭屋基王姓人家還梓潼愿戲[2],戲壇上供奉的神靈是“四圣天子”,除川主、土主、藥王“三圣”外,還有梓潼神。梓潼神,亦稱“七曲文昌帝君”或“文昌帝君”,是一位專司“功名”和“續(xù)嗣”的神祇,因其具有角色扮演的性質(zhì),所以又稱“梓潼戲”“梓潼愿戲”。從表演形態(tài)看,儀式性陽戲表演有一套酬神還愿、驅(qū)邪納吉的固定儀式程序貫穿始終。如上所述的王姓人家還梓潼愿,演出的出目有《開響》《開壇》《立樓》《安師》《安營扎寨》《申文》《紅山路》《下天門》《開財門》《送子》《投梓潼表》《出神》《搭橋》《領牲》《上領牲錢》《回熟斷愿》《打關》《勾愿》《打唐二》《造船》《差營倒寨》《圓滿》《掃火堂》[2],每出儀式的結(jié)構(gòu)簡練,形成組合性的“儀式群”,而每出儀式中又包含若干彼此相聯(lián)系的儀式元。如《安師》一出分“開場啟語”“請神”“奠酒、通口意”“領受”“保管”“推遣、漂食、交錢”“撤愿、削罪”“安位”七個儀式元,形成一個“閉合式”儀式出目。整個儀式的所有出目皆圍繞著“請神—酬神(敬神、娛神等)—送神”的基本程序進行。儀式性陽戲表演時,角色裝扮有戴面具、涂面、提線木偶等形式。在正安、沿河、湄潭的陽戲壇上,多數(shù)角色戴著面具表演,尤其是二郎神、靈官、藥王、梓潼神等主要神靈必須沿襲戴面具表演的傳統(tǒng)。部分角色,如太子、丫角將軍、丫角仙娘、儺壇祖師在戲壇上呈現(xiàn)木偶神形象。角色涂面的方式主要用于神祇故事戲中的旦角化妝,如《桃山救母》中的姨娘、《孟姜女》中的姜女、梅香等。木偶與藝人的演、唱分體式和藝人之間的幕后唱臺前演的“雙簧式”表演還時常能夠看到。無論哪種扮演方式,都是壇師通過唱念頌神詞的形式來敘述情節(jié),這種情況下,壇師的角色功能重在推進儀式,所演“戲”的成分不多,更甭提角色分工。唱腔樂器方面,該地區(qū)陽戲的唱腔屬板腔體。演唱法事儀式用神歌腔,又稱“端公調(diào)”“土腔”“唱神腔”,中間夾有部分曲牌,主要源于傳統(tǒng)戲曲或花燈、花鼓戲。伴奏樂器往往帶有法器性質(zhì),如鑼、鼓、鈸、鐃、鉸子、木魚、撒板(蓮花落)、牛角、海螺、師刀等,特別是演“跳判子”“跳小鬼”類似劇目,僅以鑼作輕音伴奏。從演出時空角度看。黔北陽戲的演出時間主要集中在春節(jié)前后,演出地點選在愿主的堂屋、正對堂屋的院壩及村外的曠野。可見,黔北陽戲是一種驅(qū)儺民俗與演神祇故事戲相結(jié)合的儺戲類型,其形態(tài)早于其他地區(qū)的陽戲。
(二)儀戲結(jié)合性陽戲
渝東南的武隆、彭水、黔江、酉陽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商貿(mào)交通要道,文化多元亦是該地區(qū)的特色。陽戲即呈現(xiàn)儀戲過渡的二元制形態(tài)結(jié)構(gòu),雖然有系統(tǒng)的事神儀式活動貫穿演出的全過程,但較之毗鄰的黔北陽戲仍體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娛樂性。以重慶酉陽興隆村陽戲壇為例,陽戲的儀式性質(zhì)亦非常明顯。一方面,從陽戲“跳戲”的目的看,分兩類。一類是還愿祈神,在許愿主人的家里演;另一類是祀神祭祖,在掌壇老師的家里跳。兩者都具有祀神性質(zhì),祭祀玉皇上帝、關圣帝君、老郎太子三位主神,還有二十四位護法菩薩、姜郎相公、龐氏夫人、了愿仙官、尉遲恭、秦叔寶,以及關公的左右護法神關平和周倉。其次,陽戲仍以儀式程序為演出框架。以酉陽陽戲壇為例,其實際演出分“三大部分、七小段落”。第一部分包括“請神”“關爺鎮(zhèn)殿”和“龐氏夫人鎮(zhèn)臺”三個段落;第二部分唱正戲;第三部分主要包括“送神”“關爺掃殿”和“掌壇老師投蛋”三個段落。第一、三部分的程式內(nèi)容固定,祭祀性較強。“唱正戲”部分重在戲劇表演,它夾在“請神”“送神”的框架內(nèi),遵循“請神→龐氏夫人鎮(zhèn)臺→演唱正戲→送神”的演出儀軌。第三,角色裝扮的面具被置于祭祀的語境中。演出時角色仍需佩戴面具,多數(shù)面具按照生、凈、丑的行當佩戴,表演結(jié)束后,面具要統(tǒng)一放在神龕上。不過,戲中的旦角采用涂面的扮妝形式表演,這是陽戲壇上的新變化。另一方面,“戲份”已占很大比例。渝東南陽戲的儀式性質(zhì)顯見,同時又具有豐富的戲劇因素。陽戲壇上祭祀神祇的形式體現(xiàn)了它的儀式特點,而祀戲神老郎太子則顯示它的戲劇性,例如,“老郎太子神”被尊置于神壇的中心位置,左為關圣帝、皇生,右邊為包丞相、元帥。雖然演出形制建構(gòu)為“請神→酬神→祈神→送神”的主體框架,但在實際表演過程中,儀式部分比較簡約,祀神過程不像在黔北陽戲壇上那樣繁瑣。儀式不是自始至終地貫穿,而是有了娛樂性戲劇表演的間隔,就連祀神儀式《關爺鎮(zhèn)殿》《關爺掃殿》也在弱化儀式性質(zhì),《龐氏夫人鎮(zhèn)臺》的儀式性更是淡化了許多,基本完成了戲劇化的蛻變。該地區(qū)陽戲雖然還沒有脫離儀式,但那僅是“程序”的遺存,表演形式已不再是單一角色的照本宣唱。初具戲劇的演劇形制。渝東南陽戲演出有了初步的“舞臺”,如酉陽陽戲演出由堂屋走向院壩,且要橫掛紅布底幕,把表演場區(qū)和“戲房”前后分開。幕后“戲房”內(nèi)設一方桌,樂隊圍桌擊樂伴奏。服飾、道具品種豐富,并呈現(xiàn)世俗性的“非法器”特點。服飾豐富多彩,有蟒袍、軟靠、褶子、短衣、裙、長褲、女帔紅帕、紅裙。主要道具有槍、短刀、弓箭、錘、蚊掃、折扇、朝笏、手帕等。另外,渝東南陽戲“正戲”部分演出的劇目多,大多是劇情曲折的大幕戲,演出形式由“重唱誦”轉(zhuǎn)向“重表演”。在表演時間和地點也較黔北陽戲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演出時間由觀眾和演員來定,突破了掌壇師和愿主擇期的傳統(tǒng)慣例,演出地點也不局限在堂屋的神龕前,寺廟、祠堂、街頭、庭院都可以演出陽戲。雖然說是在演戲,但還算不上完全意義上的戲劇表演。首先,唱腔簡單,板式分為“一字”和“二流”。一字不受節(jié)拍限制,二流由板眼的節(jié)拍限制。唱腔按角色行當或人物身份來標識,如皇帝唱【皇生腔】、文臣唱【丞相腔】、將帥唱【元帥腔】、山寨王唱【大王腔】。其次,伴奏樂器仍以大鑼、大鈸、鉤鑼、鼓等武場樂器為主,并且對應的曲牌結(jié)構(gòu)簡單,如【長路園】【鬧臺】【一二三錘】【喜鵲鬧梅】【三緊四松】【猛虎下山】等。總之,渝東南地區(qū)的陽戲與儀式漸行漸遠,越來越傾向于服飾、舞蹈、音樂等方面的藝術性訴求,反映了陽戲向輕“儀”重“戲”的方向演進。
(三)民間小戲類型的陽戲
民間小戲形式的陽戲在武陵山片區(qū)流行最廣泛,北起鄂西的鶴峰、來鳳,中到重慶的秀山、湘西的花垣、張家界、鳳凰,南至湘西南部的懷化、黔東南的天柱、錦屏、黎平等地。此類陽戲表演追求趣味性,從傳統(tǒng)劇目《背包過河》《蠢子送妻》《丁瞎子鬧館》《河邊洗裙》《賣紗學打》《筍園調(diào)情》《曬鞋講書》《算命討小》等可見一斑。維系陽戲運作組織由“戲班”代替了“戲壇”,演出人員也由“壇師”變成了活躍在民間的藝人。常規(guī)的陽戲班最初僅有七人組成,小旦一人,丑一人,小生一人,正旦兼老旦一人,生兼花臉一人,鑼、鼓各一人,表演節(jié)奏緊湊,經(jīng)常出現(xiàn)一演員兼演多角色的情況。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于劇本內(nèi)容拓展、戲路擴大,需要文場、武場、小戲、連臺戲都要能演,有的戲班要十多人或二十人左右。戲班角色分工明確,不但生、旦、凈、丑行當齊備,而且行當類型有了較大發(fā)展,按照戲中人物年齡、職別、性格區(qū)分為小生、老生、花旦、小旦、善丑、惡丑等。同時,角色表演注重舞臺效果和表演程式,講究“四功”“五法”的舞臺演出效果,顯然符合傳統(tǒng)戲曲藝術表演的要求。這類陽戲的演劇服飾種類多,“生旦凈丑,袍帽冠服無所不具,偽飾女旦,亦居然梨園弟子,以色媚人者。”
扮裝不見面具,而是戲中角色依照戲劇臉譜涂面勾臉。同時,積極吸收地方劇種臉部化妝的技法,如陽戲中小丑的“蛤蟆臉”就是采用花燈戲的開臉方法。陽戲音樂曲牌豐富,男、女行當分腔,唱腔風格高亢、粗獷,擅用拖腔,幫腔用嗩吶。同時與花燈藝術相融合,在聲樂方面也積極吸收花燈調(diào),舞臺動作也常見花燈戲中的“套子”“圈子”“矮子步”等表演形式。可見世俗性陽戲距祭祀酬神的意義最遠。但舉行儀式曾是該類陽戲演出的重要內(nèi)容,只是當?shù)孛癖姲褌鹘y(tǒng)民間故事、民歌等內(nèi)容和花燈、花鼓等地方曲藝形式大量融入了陽戲表演中,濃化了陽戲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風格。世俗性陽戲無論從演出劇目、角色行當、音樂唱腔、服飾化妝、舞臺表演皆已具完備的戲劇因素,成為一種廣場、舞臺表演藝術。至此,陽戲被稱為“地方劇種”。
儺戲孕育和形成于儺禮、社祭的民俗歌舞儀式,它深受民間宗教的影響,亦有制度宗教的痕跡。道教作為根植于中國的傳統(tǒng)宗教對于儺戲的影響毋庸贅言,但是武陵山片區(qū)處于梵凈山佛教文化輻射區(qū),它的文化藝術形式體現(xiàn)著顯著的佛教印記。下面以該區(qū)域陽戲的壇班組織、實物道具、表演內(nèi)容和儺技形式方面給予論述。首先,陽戲壇組織的佛教性質(zhì)。在武陵山區(qū),不少陽戲壇師承佛教。例如酉陽陽戲壇有完整佛教性質(zhì)的法譜,法譜上排列著掌壇法師的字輩順序:智惠清凈、道德圓明、真儒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廣宿、本覺昌隆、能仁圣果、常遠寬洪、惟傳法應、致愿會容、兼池界定、永濟祖宗[9]。過職、取法號儀式是佛教壇傳承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掌壇師把陽戲的演唱技藝和作法行科等內(nèi)密傳承給后人要舉行“過職”儀式,對被傳承人來說叫“請職”。師尊按“法譜”給請職者取法名,只有取過法名、請過職的法師日后方可作掌壇師獨立行壇,主持演出。掌壇師去世后,要把他的法名寫入“頂敬”,一個陽戲壇的“頂敬”即為該戲壇歷代先師的宗師牌位,記錄本戲壇的傳承譜系,它從思想上起到維系壇班組織的作用。壇班往往立有壇規(guī),成員入班要在掌壇師的帶領下面對壇規(guī)宣誓。例如湄潭縣高臺鎮(zhèn)王氏陽戲壇班在為新恩弟子舉行入壇度職的法事儀式上,向弟子宣讀的“戒令壇規(guī)”具有佛門教義性質(zhì):新壇弟子,既承佛法,從此以后,乃稱佛門弟子,凡有戒言,汝可聽受:一不得輕蔑佛法,儼然恭敬有靈。二不得輕師慢教,出入請問師尊。三不得欺壇枉社,□人引進敬神。四不得貪香挽火,奉請不得推辭。五不得逞能夸夸嘴,要學曾子□顏。六不得三觀二意,帶信來請莫行。七不得偷眼觀色,敲打吹唱要精。八不得道人好歹,輕慢只在要精。
九不得越式亂抓,要用不得減省。十不得始勤終怠,科規(guī)熟練方行。以上所言,當戒施行,即今傳度圓滿,功德周全。②要求壇班成員戒賭、戒淫,徒弟對佛法要儼然恭敬,對師尊要畢恭畢敬,學藝要勤勉,以期精通百藝。平日匠不談師,師不談匠,不能說三道四。以此強化壇班成員的組織意識,規(guī)范他們的日常行為。第二,文物實證陽戲壇受到佛教影響。在武陵山區(qū)北部的陽戲壇抄本中常見佛教信息,例如正安陽戲抄本后面常注:“釋門萬應壇”(《上云臺》)“巫門弟子黃法舟記”(《桃山救母》)。從“釋門”“巫門”可見壇班的佛教或半佛教性質(zhì)。在中橋村陽戲壇有兩塊晚清時期刻板,其中一塊上刻:“太子千千秋法輪常轉(zhuǎn)佛日增輝”。黃永忠陽戲壇班的祖師權杖頭上刻著觀音菩薩雙手合十端坐蓮花臺的雕像。湄潭縣抄樂鄉(xiāng)羅耀森儺戲壇上的楹聯(lián)亦見佛教信息,上聯(lián):“道傳東震旦梵音流演悟門生”,下聯(lián):“東土傳經(jīng)演教歷代古今宗師”。黔北還愿陽戲壇常用木魚作為樂器,壇師戴五佛冠或為七佛冠,并且刻有“僧”“佛”“法”字樣。旗幡類道具有如來大幡、觀音幡、金剛幡等,法師的“佛法僧寶”印和神案前張貼“佛光普照”的鎮(zhèn)壇字符皆能表明該區(qū)域陽戲壇班的性質(zhì)。第三,陽戲表演內(nèi)容的佛教性質(zhì)。首先,倡導多做善事,多行善舉方能保平安降吉祥。如唱梁王稱帝事:昔日樵夫去打柴,惡風暴雨打?qū)怼Zs得樵夫沒處躲,遠望古廟靠石崖。樵夫進門參佛祖,參過佛祖把頭抬。佛祖頭上一片瓦,一點泥水滴下來。樵夫見了心不忍,揭下斗笠蓋如來。四十九年梁王帝,曾將斗笠蓋如來。斗笠化作皇王帽,蓑衣化作袞龍袍。③梁王帝窮困時在古廟以斗笠、蓑衣為如來佛遮雨擋風,佛祖對其善舉報恩,佑其披龍袍、戴皇冠。這樣,善惡有報,天理昭然。同時,仇怨相報,福禍相依。民國初年本《三圣領牲》中唱:昔日螳螂去捕蟬,又被黃雀站樹尖,黃雀又被弓箭打,打鳥之人被虎吃,老虎得吃歸山去,又被枯坑在路旁,老虎跌落枯坑內(nèi),枯坑又被黃土堆,黃土高上生青草,青草又被太陽曬,太陽又被云遮住。白云又怕黃風吹,古來一報還一報,仇報仇來冤報冤。此唱段在武陵山區(qū)陽戲壇上傳唱流行,常見于不同文本中,如《孟姜團圓》《楚漢相爭》中皆有同樣的唱段。其次,反映佛教的生命觀。佛教生命觀最突出的是“眾生皆有佛性”的平等觀、“與樂拔苦”的慈悲觀和“戒殺護生”的因果報應觀。例如“戲耕牛”唱段:世間辛苦是耕牛,說起耕牛有根生,當初世上無耕牛,父子三人使鋤頭。老的挖得青煙起,少的挖得汗長流。觀音菩薩見不忍,金釵化作一只牛。才去田中吃口水,口口聲聲罵瘟牛。陳谷爛米年年有,無錢就去賣耕牛。一人當時合了價,賣去廚房做菜牛。牛兒牽到校場壩,劈頭就是一斧頭。左一刀,右一刀,牛兒割得好心焦。作一掄,右一掄,牛兒割得好心疼。皮子將來做鼓打,骨頭將來連秤稱。今世吃牛肉四兩,來世還牛肉半斤。周身四體都吃盡,仇報仇來冤抱冤。④這里體現(xiàn)了佛教濃厚的尊重生命、關愛生命的思想。陽戲班借演“目連戲”倡導人類關注自身的前途命運,戒殺護生,從心理層面有效地約束人類的行為。此外,陽戲壇上的各種儺技活動,不得不說與佛教“報惡”手段有關。據(jù)《酉陽直隸州總志》記載,祀神戲壇上儺技多種:有上刀桿者(置木桿于地,以三索系之,木上縱橫置刀有三十六柄,有七十二柄與百二十柄者,巫跣足履刀而上。至中,有挺心刀尤危險。其頂上則布平板,登頂則立板上,為病者祈禳),有滾刺床者(以草木刺鋪地為床,巫赤身翔跌其上),有打粉火者(以蕎麥粉為之),有作牛角道場者(為兇死者佛事,則以僧巫分行,其各如此),大約既為此技,則左道邪術,驅(qū)使鬼魅者,有之,未可盡以為欺枉也[12]。即為至今陽戲壇仍流行的“上刀梯”“滾釘床”“踏紅鐵鏵”等,尤其是“設橋案”儀式與佛教“過奈何橋”頗有相通之意。至于佛學思想在陽戲壇經(jīng)歷了怎樣的滲透、融入過程,下文將作進一步考證。
武陵山區(qū)的陽戲壇上佛音縈繞,佛跡處處可見。那么,“酬神還愿”祀“三圣”的陽戲是怎樣與佛教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呢?考察佛教、陽戲傳入武陵山區(qū)的先后關系,相對于當今廣泛傳播的陽戲來說,由異域入華的佛教倒是本土文化。以享有“武陵之源”美譽的梵凈山為例,自宋代建造西巖寺開始,逐漸成為“古佛道場”,并賦予多種佛教內(nèi)涵。至明初四川佛教禪宗開始崛起之后,佛教開始大規(guī)模地傳入黔地。明末清初重慶梁平縣和忠縣的禪宗弟子往返于川、黔、渝三地,黔域佛教始才得以迅速發(fā)展[13]。清道光年間,梵凈山香火很旺,祀佛香客多,寺廟亦具一定規(guī)模,“(報恩寺)每歲夏間,朝禮者遠近幾萬余人,川楚之民咸在焉。”“廳屬寺觀之建,由都市以達村落,道相望也。寺以供佛,觀以奉道。廳地寺居其九,觀居其一。緇黃之資以為生者,不下千余人。”道光《思南府續(xù)志》亦有相同內(nèi)容記載⑤,其中更甚者,在“六月中,遠近男婦燒香朝禮者不下萬人。磴道崎嶇,險處垂二分尺。朝禮者攀鐵縆而上,前人之踵接后人之頂,魚貫而從,備嘗怖苦,期以邀福”。梵凈山《下茶殿碑》記載:“數(shù)百年進香男婦,時來時往,若城市然。”“佞佛者朝謁名山,號稱進香。往往結(jié)黨成群,攜老扶幼,此風他省亦間有之,近日惟吾銅尤盛。其期以六月朔為始,于月終為止,倡首者謂之香頭。先日斂錢制黃旗一方,或百人,或數(shù)十人為一隊,導之以旗,每人身背黃袱,烏烏唱佛歌,前呼后應,舉國若狂。”至此,梵凈山成為這一區(qū)域趨之若鶩的佛教圣地。同時,梵凈山具有較強向周邊區(qū)域播灑佛教思想的張力。湖南省龍山縣卡洛坪彭家梯瑪做法事稱“做菩薩”、“玩菩薩”,不管敬什么神,都稱“敬菩薩”,梯瑪戴的是五佛鳳冠。黔北仡佬儺壇多是“巫佛兩教”“壇班或人士”所為,其中的“酬東岳”儀式,又稱“酬泰山”“酬佛”,陽戲壇《佛科書》中的“梓潼表”其開篇唱“法寶化身如來佛……”。可見,佛教對該區(qū)域巫儺文化的影響之深。梳理文獻發(fā)現(xiàn),佛教思想在西南地區(qū)的傳播要早于陽戲文化,域外的陽戲自播入武陵山區(qū)始,即受到佛教的影響、浸透。為解釋這一結(jié)論,我們先看“陽戲”與“佛”的融合軌跡。“陽戲”之正名首現(xiàn)于明正德年間的江西《瑞州府志》:陽戲,傀儡戲劇也,民或從而神之。執(zhí)而弄者曰“棚戲”,摯而弄者曰“提戲”,謂之“還愿”。
形態(tài)為“傀儡戲劇”,性質(zhì)是“酬神還愿”。這是最早的“陽戲”形態(tài),與佛無關。至康熙年間為“陽戲,即傀儡戲也,用以酬神賽愿”。到民國時期,這一地區(qū)的陽戲則為“始為神,繼為優(yōu)”的戲劇表演,亦沒發(fā)現(xiàn)有佛家影響的痕跡。不過,上述“陽戲”是在江南地區(qū)的演出形態(tài),這時文獻上還沒看到有關武陵山區(qū)陽戲的文字記載。在武陵山區(qū),甚至整個西南地區(qū),“陽戲”最早文字記載見清康熙年間董維祺修《涪州志》卷五:涪俗,凡人疾病,不專于延醫(yī),必延道侶,設供神像,鳴金鼓吹角誦經(jīng),禳解于焚符火熖中,以卜其吉兇。病愈則延巫師,演陽戲以酬之。可知,酬神還愿陽戲最遲在清康熙年間的重慶涪陵地區(qū)已流行。具體的演出形態(tài):一定要請“僧侶”扮演,讓他們“鳴金鼓吹角誦經(jīng)”來“禳解”“焚符”“卜其吉兇”。陽戲一出現(xiàn)即有僧侶“誦經(jīng)”的佛音相伴。在黔域,“陽戲”文獻記載始見于清道光年間《遵義府志》卷二十:“歌舞祀三圣,曰陽戲。三圣,川主、土主、藥王也。近或增文昌曰四圣”。該《府志》對“禳儺”的“端公”和陽戲的演出形態(tài)有詳細記載:《蜀語》男巫曰端公……巫黨椎鑼擊鼓于此,巫或男裝或女裝,男者衣紅裙,戴觀音七佛冠,以次登壇歌舞,右執(zhí)者曰神帶,左執(zhí)牛角,或吹,或歌,或舞,抑揚拜跪以娛神,曼聲徐引,若戀若慕,電旋風轉(zhuǎn),裙口舒圓。《田居蠶室錄》陽戲壇上有佛的飾物“觀音七佛冠”。前文所舉中橋村陽戲壇上“法輪常轉(zhuǎn)佛日增輝”的刻板和黃永忠陽戲壇班上雕菩薩觀音的祖師權杖頭等具有佛教意義的實物,極有可能隨和“佛冠”在同一時期融入陽戲壇。同治年間,佛教對陽戲壇的影響更深入。《酉陽直隸州總志•風俗志•祈禳》(1863年修)載:凡咒舞求佑,只用男巫一二人或三四人,病愈還愿,謂之陽戲……有作牛角道場者(為兇死者佛事,則以僧巫分行,其各如此),大約既為此技,則左道邪術,驅(qū)使鬼魅者,有之,未可盡以為欺枉也。“為兇死者佛事”標明陽戲壇為喪家做道場,主持佛教性質(zhì)的儀式活動,此戲壇極有可能為佛教壇、壇師為佛教徒。至此可見,與今天所看到的佛教性質(zhì)的陽戲壇幾無二致,佛學思想與陽戲文化也就圓融于一體了。概而述之,早期江南地區(qū)的陽戲只是“酬神還愿”的“傀儡戲”,與佛無關聯(lián)。而武陵山區(qū)的陽戲初始出現(xiàn)就有佛的因素,并且從“佛冠”到“僧侶誦經(jīng)”直至“僧侶分行”執(zhí)行佛事道場。沿著這條線索,足以洞悉這樣一個事實:佛教對陽戲壇的影響逐步深入、滲透,最后達到佛教文化混融于陽戲壇的現(xiàn)狀。
陽戲是武陵山區(qū)一項重要的民間文化形式,在該地區(qū)它有儀式戲、儀戲結(jié)合戲和民間小戲三種基本形態(tài)。況且,它們在武陵山區(qū)的區(qū)域分布非常規(guī)律:黔北、黔東北的陽戲為儀式戲,渝東南的陽戲?qū)賰x戲結(jié)合性質(zhì),鄂西、湘西、黔東南的陽戲為民間小戲。佛教氛圍濃厚是武陵山區(qū)陽戲的顯著特征。這點從陽戲壇組織的佛教性質(zhì)、壇班上的器物道具、表演內(nèi)容的思想傾向等方面皆有足夠的體現(xiàn)。探究陽戲與佛教文化融合的線索,發(fā)現(xiàn)在武陵山區(qū)佛家思想的傳播要早于陽戲文化,域外的陽戲自播入武陵山區(qū)始,即受到佛教的影響和浸透。
作者:吳電雷 單位:貴州民族大學 西南儺文化研究院